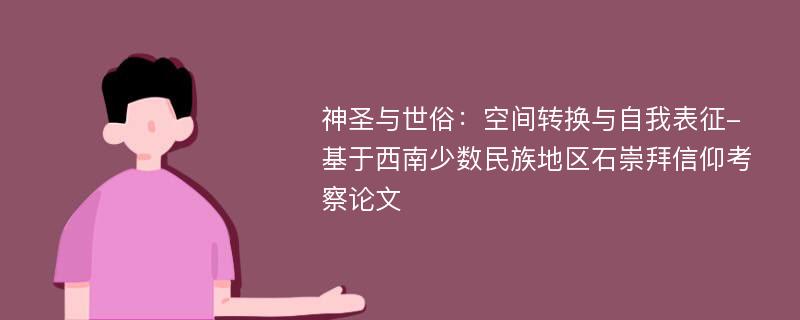
神圣与世俗:空间转换与自我表征
——基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石崇拜信仰考察
蒋楠楠 杨嘉铭
(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西南民族大学,四川 成都 611130)
摘要: 神圣与世俗是人类生命与精神在空间存在的两种维度和两种样式,二者间不仅有着理论上的辩证逻辑,而且有着生活中的现实关联。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羌族、仡佬族、苗族、白族以及藏族等少数民族均具有独特的石崇拜信仰,这些少数民族以“石”为尊、以“石”为祖,“石”既作为“常见物”出现在其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的世俗性,也作为“显圣物”存在于其宗教信仰中,具有特殊的神圣性。本文通过对川、黔、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石崇拜现象的深入田野调查发现,“石”通过禁忌和仪式不断的在神圣与世俗的二元空间中进行自然转换,并借助颜色认同和独特外形选择的双重途径来进行着自我表征。
关键词: 神圣与世俗;石崇拜信仰;西南少数民族;显圣物;空间转换;自我表征
整个世界被划分为两大领域,一个领域包括所有的神圣的事物,另一个领域包括所有的凡俗的事务,宗教思想的显著特征便是这种划分。[1]就神圣与世俗而言,究其词源,其最早出自于拉丁语“sacrum and profanum”。“Sacrum”原意是指那些隶属于神或由神来掌控的事物,其关乎到与宗教相关的场所;而“profanum”原意是指庙宇前的地理区域和相应的地点。从释义关联来看,二者均有地点或区域之意。诚然,二者也有相异之处,这既体现在空间上的对立与区隔,也存在于相关事务的发生领域。此外,由于神圣强调神性更强调品性,且这种品性需通过供奉和献祭来实现,因此这不仅涉及到宗教的道德性,而且也强化和加速了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性。然而,就本质和内在逻辑而言,二者俨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正如涂尔干(Emile Durkeim)所言,人类的精神生活里许多方面都难以划分出神圣与世俗的现象,二者间并未见有明确的区隔,相反,互相的关联性常被视为一个连续统(continuum)的组成部分。[2]
一、辩证逻辑与现实映射
(一)辩证逻辑
论之神圣,其具有超自然、超经验、超理性、超逻辑且无限的性质与特征。奥托(Rudolf Otto)在其著作《论神圣》以及《神圣者的观念》中认为,“‘神圣’即‘神圣者’,它是宗教领域中一个特有的解释与评价范畴,具有原创性、宗教性、非理性以及道德性。”[3]神圣与宗教密不可分,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在其经典之作《神圣与世俗》中认为,宗教是人类学的常数,而神圣则是宗教的常数,同时也是宗教的根基,宗教围绕神圣以及神圣性而展开,缺少了神圣性,也就无所谓宗教。然而,神圣并不等同于宗教,从宗教看神圣只是人类对神圣的一种解读方式,且无论是最原始还是最发达的宗教,均由显圣物(hierophany)①通过神圣实在的自我表征构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完全不同的存在性的自我表征是构成我们这个自然世俗世界的组成部分。[4]
言之世俗,其具有自然的、经验的、理性的、逻辑的和有限的性质和特征。人们是在世俗中用语言以及具体的行为去体会和表达对宇宙万物的认知。同样,人们也在世俗中发现并体悟所崇拜的万物神灵。换言之,神圣的事物以及象征体需凭借世俗这一媒介呈现出来,世俗作为神圣传递神秘力量的中介载体,具有典型的不可或缺性。因此,神圣之物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拟人化的存在,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是神圣的,一个仪式就足以使得这些东西具有神圣的意义。神圣事物如一块石头或一棵树之所以神圣,是因为有特定的仪式围绕着该物,对任何宗教而言,不管他如何等齐划一,都必须承认神圣事物的多样性。[5]
那么,讲述者—历史教师为什么要选择鳗鱼这种当地十分常见的水生动物作为描述对象呢?因为从形态上看,它既像阴茎,又像游动的精子,代表了自然中永恒的生命力。从象征意义上说,它既可作为人类欲望的隐喻,又可作为自然介入人类的工具。小说中有个细节特别耐人寻味。讲述者—历史教师的父亲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患了失忆症。在被问到关于战争的回忆时,他总是回答他什么都不记得了。但他却会回想起那古老的战壕泥沟中的古怪故事,“比如,无数条一向生活在低湿地的佛兰德鳗鱼,对于破坏它们栖息之地的惨死战争不为所动,竟然游到了被洪水淹没的战壕和弹坑里,对它们来说那里绝对不乏腐烂的食物……”[2]130
统观圣与俗,二者具有同一性、一致性以及异质性。神圣往往发端于世俗,从宇宙到生命、从时间到空间、从神话到历史、从生活起居到节庆习俗以及从婚姻制度到生育制度,无不涉及圣与俗。神圣不但是指一种对上帝众神或者精灵的信仰,而且也是对生活中神圣的渴望。人类社会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只要对生命和宇宙万物仍心存敬畏,就一定会从世俗中回归神圣。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人类崇拜的各类神灵以及崇拜物都是对宗教神圣的一种外化形式,神圣赋予了各类神灵各自不同的品性、神性、功能与职责,而崇拜物的神圣又常与世俗中的需求保持一致。
(二)现实映射
神圣与世俗既有理论层面的内在关联,也有客观现实中的宗教表达。人类的宗教现象与人们所接触的一种“超自然”的神圣密不可分。这种神圣是主体与客体的结合,是由绝对意义的神圣实体以及相应的人们对神圣所具有的一种既敬畏又向往的心理体验所构成。神圣自身天然笼罩着一种强大且不可抗拒的神秘的力量,作为一种超世俗存在,其具有强大而显著的威力,对此,奥托将其视为一种“令人畏惧的神秘”,并将这种神秘解释成一种“完全相异性”。②在这种不可抗拒的威力和力量下,崇拜者内心升起了一种“畏惧”和“敬畏”,这种情感在原始社会之初表现为对“离奇”、“怪诞”以及“不可控”自然现象的畏惧,奥托将其称之为“原始人的宗教”,原始人的宗教的真正标志表现为对魔鬼的畏惧,即使这种畏惧在获得了特殊的或者更高、更纯粹的表现形式很久之后,那种先前曾经是其一个方面的原始激情类型仍有可能以其原始的原初质朴形式在心灵中爆发出来,并被再次体验到。[6]这表明当魔鬼或鬼魂崇拜演变成神灵崇拜时,这些神灵依然对崇拜者的内心产生“令人畏惧的神秘感”。概念化的“神秘”意味着那些隐匿的、难以理解的、超出概念和理解力的以及异乎寻常且陌生充满禁忌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显圣物。
笔者在走访位于贵州和四川两地高山峡谷地带的羌族、苗族以及仡佬族等村落时发现,他们在描述其崇拜山神、石神的缘由时,都会表达出巨石或怪石让人产生一种神秘且不可控的感觉。③由于神圣具有非理性和非逻辑性的特征,人类对神圣的认知往往超越了自身认识系统和认知水平,因此,对于石崇拜者而言,在面对神圣时,其内心是自由的且不受任何理性思维逻辑所控制的,这使其对于神圣和显圣物的信任与依赖也是完全发自于内心的“直觉感受”,是对神圣最虔诚的表达。
二、空间结构与空间区隔
(一)空间结构
在神圣和世俗的空间,其不同部分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价值以及性质。对于宗教徒而言,空间并不是均质(homogeneous)的,当神圣以任何显圣物表征自己的神圣时,这不仅是空间均质性的一种中断,更是一种绝对实在的展示与其所属的这个广垠苍穹非实在性的对立。正是神圣的自我表征,才从本体论的层面构建了这个世界。在一个均质而又无限浩瀚的空间中,不可能有任何的参照点,因而也无任何方向得以确立其中。只有显圣物才揭示了一个绝对的基点,标明了一个中心。[7]
可见,即使是世俗世界中的一块普通石头,在人为的精雕细琢之后也能成为神圣世界中镇宅保平安的“石敢当”。人们雕刻精致的吞口形象并将其附着于石头之上,从而使其信仰的功能与象征意义发挥到了极致,这也使之更符合人们的心理预设。
综而论之,对于宗教人而言,显圣物所在的空间是神圣的,非均质的,它将所在世俗空间中的均质性打破,造成中断并使之区别于其他空间。空间由于显圣物的存在,使其实现了从世俗到神圣、从均质性到非均质性的转变,而神圣空间的特殊性又对人们的行为和心里产生了影响。伊里亚德认为,“世界中心”在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中表现为各类不同的自然崇拜、显圣物或是庙宇与祠堂等标志性建筑,它们既代表着“中心”,同时也象征着神圣空间内的秩序,神圣空间的“中心”以及秩序在羌族民居的内外空间中得到了完美诠释。
笔者在深入走访川西羌族聚居区后发现,无论是被誉为“邛楼”的羌碉还是羌族的传统民居,其主要的显性建筑材料均为石头、木材以及黄泥,其建筑结构一般分为三层,即底层养牲畜、中间人居住以及顶层供神灵。④此外,羌族建筑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羌族人将“白石崇拜”信仰和风水观念贯穿其中。无论是建筑的整体结构还是修建过程,均有石头参与其中,石头不仅作为世俗之物存在于羌族人的物质生活,而且也作为显圣物渗透到羌族人的精神生活,如羌族民居中的“立神塔”,⑤其处于羌族民居的顶层,是一个神秘的非均质的神圣空间的“中心”和秩序所在,羌族民众一般会在此供奉白色的石英石,在屋顶四角也会安放白石,也有人家把尖形的白石组成四角或八角,放置于屋顶转角或拐角处。对此,笔者就为何在屋顶安放白石等问题询问了汶川龙溪乡的老释比WZS,他口述道:
我们羌族人在房顶放白石是因为房顶离天最近,白石是代表我们羌族的各路神仙,白石放在房顶可以直接带来贴身的保护。我们的《释比唱经》里也有“房顶纳察砌的好,放上石板真平坦,上立白石需恭敬……一家烟火发百家,百家烟火传千年”的说法。
可见,在羌族人的思想意识中,顶层是最接近宇宙众神的居住之所,是神圣空间中的 “基点”与“中心”所在,将神圣的显圣之物——白石供奉在顶层,在空间结构中,将顶层与其他空间相分离,凸显了神圣与世俗的分界。同时也将白石所具有沟通天地的功能与象征意义表达尽致。
(二)空间区隔
1.禁忌区隔
涂尔干以象征和二元对立的方法拓展了神圣与世俗的研究空间。他认为,神圣与世俗不仅存在着空间区隔,而且二者可以转化。神圣事物既受到禁忌保护又被禁忌隔离,凡俗事物作为实施这些禁忌的对象,必须对神圣事物敬而远之,这种关系是宗教信仰的重要表现,它们不仅表达了神圣事物的性质,也表达了神圣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神圣事物与凡俗事物之间的关系。宗教仪式中所体现的各种行为准则,则规定了人们在神圣对象面前的禁忌。[8]换言之,禁忌是区隔神圣与世俗空间的重要介质,最根本的神圣空间需要禁忌来彻底区分显圣物与世俗物。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石崇拜信仰中,作为显圣物的石头本身就是神圣空间中重要的中介物,但凡与其神圣性相关且围绕显圣物所产生的各种禁忌,都可以绝对区隔空间中的神圣与世俗。笔者在贵州务川龙潭村的田野调查中得知,当地仡佬族在每年举行的“九天母石”⑥祭拜仪式前后,对于组织者、朝拜者等都有许多相应的禁忌规定,如所有人在祭祀仪式的前一天均不可饮酒 (这属于典型的宗教禁忌),从饮酒禁忌来看,世俗空间中禁止饮酒,是因为在即将到来的神圣空间中的神圣仪式中,酒是敬石和敬神的祭品,此时的酒是神圣的。这说明作为供奉的祭品同样也存在着神圣与世俗的空间差异。因此,在圣物的性质中,存在着某种独特原因,这种原因导致了相互隔离和相互排斥的状态。[9]
从某种意义上讲,宗教信仰体系中的禁忌体系来源于神圣观念、神圣空间中的神圣对象以及崇拜者内心对神圣的尊崇与情感。石头作为显圣物存在于神圣空间中,已然具有了与世俗中石头相对应或者相对抗的特征,此时的石头存在于一个独特的神圣世界中,与一切人与事进行区隔。
2.场域与仪式
综上,无论是关乎民族存亡的《羌戈大战》还是可歌可泣的“万年孝”,都无不印证了白色与白石信仰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
以羌族的室内空间格局为例,作为房屋中心的堂屋一般与大门相对,是羌族人家中重要的神圣空间所在,卧室与厨房分布两侧,猪圈与粮仓则位于房屋之外。⑦笔者在四川理县桃坪羌寨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一户羌族人家堂屋的神龛旁放着一块白石,户主CG告诉笔者:
白石是羌族神灵的代表,同时也是羌族的祖先,将白石与神龛放在一起,每天祭拜祖先也拜神灵。
可见,在供奉白石和神龛的场域内,其是祖先和神灵降临的神圣之地,“天地君亲师”的牌位、祭坛以及供品所处的空间位置都说明此处的与众不同。小小的堂屋,既是世俗的生活空间,也是神圣的祭祀空间。堂屋以神龛作为基点进行区分,且由神龛、白石和香炉等一些特别的象征符号来进行圣俗空间区隔,特别是有仪式在堂屋举行时,其作为神圣空间的标志更加明显。尽管堂屋空间是开放的,但依然可以区分出我者与他者、神圣与世俗、洁净与污秽,这些神圣与世俗在空间上的区隔又完整的融合在一个空间里,并在羌族人的世代生活中得以继续保留与传承。
三、“俗中显圣”的自我表征
显圣物本身是世俗之物,但却因为其可以表征神圣而发生了质的改变,换言之,显圣物既是神圣的又是世俗的,是“俗中显圣”的自我表达和自我表征。世俗之物一旦被选中且被赋予了神性,其就具有了特殊的身份和价值。然而,作为得以表现神圣的客观存在并达到“俗中显圣”的介质而言,必须具备两方面的特质,一是表征神圣的物质并非神圣本身,所以其一定是属于有限的、世俗的且自然的存在,从而成就崇拜者体验神圣的现实性和真实性;二是该介质只具有象征意义,它可直指神圣和无限的终极,并成为沟通天地人神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如神圣可以以一块石头来表征,显圣物的特殊身份使其从世俗之域进入了神圣之域。一块神圣的石头仍然只是一块石头,但是相对于那些认为一块石头能够自我以神圣示人的人而言,这块石头当下的存在已经转化成一种超自然的存在。[10]
石有圣俗之分。就石的神圣性而言,一般都是民族传说与石之外形双重契合的结果,民族传说造就了石的神圣形象,使其具有了神秘特质,而石头独特的外形又促成了形象的物化,使其成为神的载体;就石的世俗性而言,其物理形态决定了其本身是世俗的,只不过在其被赋予了神性之后,其作为显圣物被拟人化和神圣化,并成为信仰者和崇拜者的膜拜对象。然而,作为显圣物的某一块石头是如何脱嵌于世俗并嵌入神圣之中,且在其成为神圣的显圣物之后又如何“俗中显圣”等问题仍值得深入分析。对此,笔者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发现,神石的确定主要有基于特殊颜色的认同以及基于外在形态的选择两种路径。
依孔子提供的标准,刚毅木讷近仁,阴柔显然不在此例,士大夫最好蓄上胡子,仗剑走天涯,贴身戴着的玉佩按进行曲的节奏发出脆响,配合威武雄壮之姿,步入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一)基于颜色认同
在我国西南地区的羌族、藏族、普米族以及纳西族等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着白石崇拜现象。某种程度而言,白石崇拜不仅是一种实物崇拜,而且也是一种色彩崇拜。这种尚白习俗与当地民族的历史建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因素密不可分。
1.神话传说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4](P265-266)
笔者在川西岷江上游的羌族村落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羌族的白石崇拜与神话《羌戈大战》有着互为源头的说法。
相传居住于西北草原的古羌人,在被迫的迁徙过程中,其中一支为敌兵追至川、青交界的补尕山。羌人的祖先天女木吉卓从天上抛下三块白石,变成了三座大雪山,阻止了追兵前进,于是羌人得以南下到达松潘大草原,并继续南迁至如今的汶川、理县和茂县地区。后来,羌人在此地游牧的时候,受到了被称为“戈基”的部落的侵袭,戈基力大善战,羌人不敌,准备逃离,此时羌族人梦中得到了天神的启示和帮助,奋起与戈基大战。天神命两族于日补坝决战,羌人以白石作为武器对付戈基人的白雪团,首战告捷,之后又在天神的帮助下,大获全胜。羌人从此在岷江上游安居乐业。为报答神恩,羌族人就以白石作为天神的象征。[11]
至今,在川西羌区,无论是山间、田地、屋顶、门窗以及室内,均可见对于白石的供奉。此外,笔者在四川羌区茂县的黑虎乡调查时发现,当地妇女常年佩戴白帽,羌民称之为孝帽。⑧关于孝帽的来历,笔者询问了当地一位80岁的羌族老人CZM,他口述道:
我们这里的小孩儿都会带一种“虎头帽”,以保佑孩子平安。女孩儿一般从十几岁开始缠头帕(头的四周缠上头帕),除了结婚那天将白色的孝帽换成黑色外,这种孝帽一般会佩戴一生,所以我们也称这个帽子为“万年孝”。戴“万年孝”主要是为了纪念名叫格吉从宝的黑虎将军,他带领羌民数次打退清军围剿,后来被奸细所害,黑虎寨的老百姓们听到噩耗异常悲痛,后来大家决定,所有男子头裹青纱,所有女子从生到死头戴白布做成的虎头孝帕,并约定这种孝仪万年不改。
神圣与世俗的空间区隔还体现在场域和仪式等方面。原始社会初期,人类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在宇宙空间中确认自己并构建秩序。在世俗的自然空间中,自然灾害、疾病以及一切无法解释的现象被人们想象成恐怖的鬼怪世界,对此,人们急需建立与之相对应的神圣空间以保佑自身,此时,一个个与神沟通的场域得以形成,这一区域与世俗空间内的秩序相区隔,从而保证显圣物在神圣空间中的地位,同时,人们在神圣场域内建立起自己的宗教场所以确立神圣空间内的秩序与规则。
2.符号象征
神话传说有时是历史的一种佐证,这块神石被选为显圣物客观上也是对神话传说的一种佐证。此外,神石凹凸不平的不规则外形与神石传说的高度契合也使得这块石头“标新立异”,这使其更容易进入“神圣”序列,从而成为“神石”。
该类维修集约范式有助于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但由于日常维护与集中维护、应急维修分别由不同的维修主体负责,不利于维护责任的界定。
虽然不同颜色在不同宗教信仰中有着不同的寓意和作用,但诸多宗教信仰中大都有对白色的深刻解读。如佛教,其以白色代表慈悲、宽容和安宁,“慈悲为怀,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就是手持白瓶,身着白衣,站于白莲之上的形象;又如道教,其也尤喜白色,尚白是道教的信仰之一,白色在道教中是被赋予了最高精神的 “道”,《淮南子·原道训》中载:“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13]此外,无论是黑白阴阳分明的太极图,还是四象中的“右白虎”以及五行缺金中的“白水晶”等,均是独具道家特色的“白”。
加拿大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学生的自主参与性很高,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自2017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第41号令)明确指出高校应当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教育和引导学生承担应尽的义务与责任,鼓励和支持学生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8]。
对于藏族的尚白习俗而言,其主要源于受到苯教(藏族原始宗教)的影响,苯教崇尚自然万物,相信万物有灵,因此,自然界中的雪山等白色自然物,逐渐成为苯教崇拜的对象。出于对自然的敬畏,以白色为主的神袛形象也开始出现并不断在藏族人的思想意识中得到强化和延伸。白色逐渐成为藏族人民心中稳固、纯洁、祥和、安宁和高尚的象征。
3.宗教渗透
(二)基于外形选择
笔者认为,世俗世界中的石头借助某种力量与介子脱离凡俗成为显圣物,并通过自我表征来达到“俗中显圣”,除了基于颜色的因素外,还有基于特殊外形的选择。
1.巨石崇拜:民族之源的“九天母石”
笔者在对贵州务川龙潭村的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现,当地仡佬族人称自己为从石旮旯(石头众多之地)中走出的民族,他们对石头有着特殊的民族情感。特别是矗立于龙潭村2公里外洪渡河畔的“九天母石”,更是因其巨大且独特的外形而被当地仡佬族人视为其祖先的化身。“九天母石”不仅是仡佬族人心中的“圣石”,而且围绕该石还伴有相应的传说与仪式。该村寨老SFJ告诉笔者: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庆伍认为,中国白酒行业正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消费者为王的时代更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因此开创黄淮流域核心白酒产区新时代势在必行,对此,他提出了3点建议:首先,重构“淡雅浓香,黄淮名酒”的区域概念,提高中原白酒的地位,如强化产区表达,以中高端白酒品牌拉动区域白酒整体发展,并加大品牌概念的输出;其次,构建四省白酒技术创新联盟,突出产区整体风格和个性品味;再次,建立四省白酒战略协同机制,“趁势而上”加强竞合,“借势发展”重创新,“顺势而为”谋转型,最终“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助推行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土地流转速度的加快,农业规模经营得到快速发展,全市农村各类专业大户达到125户、家庭农场58个、农民合作社310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8家,其中经营土地面积超过200亩的有16家,经营土地面积最多的达到1200亩。
远古时期,天有九重,九重天的天主派他的大儿子潜祖下界到此,并将其封为蛮王(也称濮王)。从此以后,蛮王在这里繁衍生息,成为了仡佬人的祖先,“蛮王仡佬、开荒劈草”的传说在这里世代流传,这里也成为仡佬人祭天朝祖的圣地。每年清明时节,各地的仡佬族同胞都会相聚在此举行隆重的仡佬族祭天朝祖仪式。
从人类学的角度而言,仡佬族的巨石崇拜行为既有万物有灵原始信仰的内因驱动,也有石旮旯生态环境的外因造就,这使得“九天母石”成为仡佬族神圣世界中具有自我表征功能的显圣物,成为其所属宇宙时空之中的超然之物。
2.母石崇拜:子嗣传承的“乞子石”
在规划未来时,照料者对专业人士或机构的不信任是影响其选择的又一重要因素。Hatfield和Lefley发现,服务系统所提供服务的协调程度低或助益不大,以及服务人员缺乏兴趣或欠缺有素的训练等,都会影响未来安置规划的制定。一些照料者表示不相信这些机构,担心钱被骗,认为机构或许只是表面宣传做得好,他们去世后心智障碍人员无法得到安全保障。这些潜在风险令照料者不愿做出确切的安排或计划。Bibby也发现,对现行政策和未来服务缺乏信心、与专业人士关系差是影响未来安置规划制定的主要阻碍因素之一。
阿里偏着头,想了想,觉得阿东说得有理。于是他不等阿东开口教他怎么磕头,便使劲磕了起来。墓穴尚未封口,水泥边毛毛糙糙。等阿东制止他时,他的额头已经磕出了血,水泥边沾上他的血印。
在我国民间普遍存在着拜石祖和乞子石的习俗。《郡国志》载:“乞子石在马湖南岸,东石腹中,出一小石;西石腹中,怀一小石。故僰人乞子于此,有验,因号乞子石。”[15]《太平寰宇记》载:“乞子石在四川宜宾南五里,两石夹青衣江对立,如夫妇相向。故老相传,东不从西乞子将归。故风俗云无子者祈祷有应。 ”[16]
上述崇拜现象在笔者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得到了印证。云南剑川石钟山石钟寺有一处石窟,石窟内有一石(形似女性生殖器),当地人将其称为“阿央白”(女阴石),时至今日仍有妇女前来祭拜。此外,云南丽江的东坝子地区(主要以白族和纳西族为主),当地妇女会膜拜一块圆锥形的大石(形似男性生殖器),当地的纳西族妇女RLR告诉笔者:
地质构造是指地壳内部的岩层在地壳运动下使其形状和位置发生改变后留存下的形态,即节理、褶皱和断层。边坡的滑坡和塌陷通常是沿着岩体的构造面形成的,其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构造面的某些物理力学如抗剪切力与抗压力的强度较小,特别是沉积岩层内每个岩层之间具有较软的次生矿物,受地下水和降雨的影响,减少了岩体的抗剪切力,从而破坏边坡的稳定性。另外,边坡损坏的种类受地质构造对滑坡岩体的影响控制。
在我们这里,如果婚后不生孩子,妇女们都会来这块大石前拜一拜,如心愿达成,怀孕时还需回到这里还愿,孩子平安出生后也要来祭拜,之后才能给孩子取名。
总之,无论是剑川石钟寺的“阿央白”,还是东坝子的圆锥石,这些原本世俗之物由于被赋予了灵性而成为神石。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是人类从远古时期就将生殖崇拜和性崇拜作为一种原始信仰,而母石崇拜就是生殖崇拜的一种外在物化的表现形式;其二是“人生人”的现象对原始社会的人们而言充满了神秘和不可思议,于是人们将其想象为是感生、卵生、石生或洞生等方式的产物,这一点在许多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以及人类起源的神话中均有体现。
3.祖石崇拜:拯救先祖的“救命石”
1.2.1 试验设计 设置4个光照强度,分别为:一层遮荫(P1,47.3%透光率),二层遮荫(P2,15.1%透光率),三层遮荫(P3,7.3%透光率),全光照(CK,100%透光率)。每个处理4株,3次重复,共48株。试验于2016年5月1日开始,共进行180 d,在试验期间每个处理进行相同的水肥管护。
贵州乌当区云锦石头寨是一个苗族聚居村寨,石头寨之名正是源于村寨中供奉着一块“神石”。笔者在当地田野调查中发现,该石的外在形态略显粗糙,其形中等大小且呈现不规则状,神石的表面有三到五个不规则小孔(形似箭孔)。对此,该村寨的苗王LCF告诉笔者:
相传当时我们的苗王在此打仗的时候,是这块石头挡住了敌人的乱箭,使苗王转危为安,我们的祖先认为这一定是有神灵相助,并认为这块地方是风水宝地,从此以后,我们的祖先便在这个地方生存了下来,并将这块石头供奉为神石,神石就是我们祖先的化身,现在神石前依然香火不断。
笔者追问:“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村民会来祭拜神石”?苗王口述道: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美好生活需要除了物质和精神需要,也包含对美好环境的需要。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人们对于健康的饮食、新鲜的空气、蔚蓝的天空必然更加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没有人类的永续发展,伟大复兴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4]
一般是在要出远门或者想祈求平安的时候,只要希望祖先保佑的事情都会来祭拜神石。祭拜时要备上香烛、纸钱和贡品,然后在神石面前磕三个响头。此外,如果有小孩去摸这块神石,或者在它旁边玩耍,大人是不能够阻止的。因为我们苗族认为这块神石是祖先神灵的化身,他在这个地方存在了千年,我们认为他也希望子孙后代来陪伴,所以小孩来他身边陪伴是给他带来欢乐,大人如果阻止,祖先会认为是大人不让它享受这份天伦之乐,因此会惩罚大人。
中华民族崇尚儒家文化,而白色又是儒家色彩体系中最为重要且富有意义的正色。《周礼·冬官·考工记》中载:“画绩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12]白色不仅有庄重、圣洁、安宁、高贵和风度的内涵象征,而且有悲伤、死亡、哀悼和纪念的情感折射,因此白色也成为众多少数民族所崇拜的一种颜色,如白族不仅以白命名本族,而且在其文化信仰中也崇尚白色;纳西族不仅在其经典的《东巴经书》中将白色崇拜视为其民族文化中的主体,将白旗视为神灵和胜利的象征,而且其重要的保护神“三朵”也是一个面如白雪、身穿白衣的神袛形象;此外,羌族独特的白石崇拜也与尚白习俗紧密相连,羌人自古就有尚白习俗,一切以白为上。可见,色彩本身作为一种象征贯穿于文化之中,而白色更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渗入到了西南少数民族的信仰文化之中。
4.石敢当信仰:精雕细琢的“庇佑石”
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作为一种信仰习俗,在传播中不仅形成了包括立石、开光和祭祀等环节在内的一系列专属仪式活动,而且在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还不断与各地特有文化相关联,形成了具有典型地方特色的民间镇物和丰富的信仰文化。如泰山石敢当在羌族地区被称为“泰山石”、“吞口”或“解救石”,泰山石敢当移入羌区后,除继续保留原有泰山文化中的相关元素外,还融入了羌族自身的白石信仰、建筑文化、吞口面具以及门神文化,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羌族石敢当。⑨
羌族石敢当与汉地石敢当最具差异性的是其加入了西南傩文化中的面具吞口形象。⑩笔者认为,在其夸张狰狞的造型和艺术魅力背后,实则隐含着一种宗教力量的存在和变形。四川理县桃坪羌寨的羌民YSP告诉笔者:
羌族石敢当与羌文化是同步的,我们羌族石敢当与别的地方完全不同,我们家这个石敢当吞口形象额头上有火纹,这与我们羌族崇拜火相吻合,脸上有笑纹,这也和我们羌族地区出土石棺葬双耳罐上的纹饰相同。
2.6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6。
四、结论与讨论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神圣与世俗不仅是建立在理想与现实之上的对于生活的划分,同时也是人们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态度。神圣是一种与人们超自然、超经验和超世俗的现象发生关系时的态度,其虽无形但却可通过信仰之物、仪式展演、宗教语言、神秘空间以及神圣者的心态进行表征与呈现。而世俗恰与神圣相对,其具有自然性和经验性,属于非宗教范畴,是人们生活的日常,无论是宇宙万物还是人类生活,在世俗中都是有形可见且可以具体表达。
一个民族对色彩的倾向,既体现了民族文化的沿袭,也体现了这个民族的审美取向,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的生动反映。[14]笔者在四川阿坝的马尔康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许多藏族人家将房子刷成白色,并在房子顶部立白石作为辟邪之物。在松潘地区,笔者也见到当地藏民将白石立于青稞田地之中,他们认为青稞田中的白石是圣物,是青稞田的守护神。此外,当地传说格萨尔王就是头戴白盔,身穿白甲,像一个白色雄狮站在雪山之上的形象。
神圣与世俗既有理论层面的内在关联,也有客观现实中的宗教表达,这点在少数民族的民间信仰体系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从西南地区的羌族、仡佬族、白族以及藏族等少数民族的石崇拜信仰习俗和与之相应的仪式可知,神圣与世俗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即虽圣俗有别,但圣需俗来表,俗需圣来佑。
注释:
①伊里亚德引入了“显圣物”一词,意指显现和具有神圣性的事物。
②“完全相异性”是一种与日常相对的、超出自然与现实、“虚无”以及“非均质的”存在状态。
③特别是在发生泥石流、地震等自然灾害时,这种惧怕心理更被强化,所以会从心理上信奉、崇拜和敬畏这些山石。
④如今由于卫生观念的普及,传统的建筑结构大多由三层改为两层,喂养牲畜的一层会另外修建。
⑤每个羌族房屋都会在顶楼修筑一块地方,被称为“立神塔”,这个专门用来敬神的空间和圣地,羌语称为“勒色”,所以也称“勒色塔”。
⑥一座矗立于洪渡河畔的巨石,被当地仡佬族视为其祖先化身。
⑦羌族人家的堂屋里,一般正中间摆放着一张供桌,桌上供奉神龛,神龛上方悬挂“天地君亲师”条幅,神龛里面一般都会摆放香炉。此外,堂屋也是释比举行请愿和还愿的地方。
⑧这种孝帽顶端竖起成虎头状,孝帽后面还留有两节白色飘带。
⑨羌族石敢当一般多放于羌族碉房大门左侧,上为面目狰狞且口中含剑的吞口形象,下为泰山石敢当且左右常刻有“日、月”或“敕令”字样。
⑩吞口乃面具文化变异,面具本身带有驱鬼性,其始终被认为是驱鬼保护神。
参考文献:
[1][5][8][9]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45.51.50.433.
[2]范可,杨德睿.“俗”与“圣”的文化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8.
[3][6]鲁道夫·奥托.神圣者的观念[M].丁建波,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7.22.
[4][7][10]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M].王建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3.2.3.
[11]《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Z].北京:学苑出版社,1990:525.
[12]崔高维校点.周礼·仪礼[Z].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82.
[13]刘安.淮南子[Z].陈静,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25.
[14]宗政.藏族的白色崇拜析源[J].西藏民俗,1998,(4).
[15]李昉.太平御览·第一卷[Z].夏剑钦,王巽斋,校点.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474.
[16]乐史.太平寰宇记[Z].北京:中华书局,1985:134.
Sacred and Profane:The Space Conversion and the Self-Representation--Based on the Stone Faith Investigation in Southwestern Minority Areas
JIANG Nan-nan YANGJia-ming
Abstract: Sacred and Profane are two dimensions and two modes of human life and spirit in space.They not only have dialectical logic in theory,but also have realistic connection in life.In the Southwestern Minority areas of China,the Qiang,Gelao,Miao,Bai and Tibetan all havehave unique faith about stone.These minorities regard stone as their ancestor.As far as stone is concerned,itnot only appears in their real life as a common object,but also exists in their religious faith as ahierophany.In this paper,the author investigated the phenomenon of stone worship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Sichuan,Guizhou and Yunnan.Analysis of the stone is how to transformed naturally in the Sacred and Profane dual space through taboos and rituals,explains the stone is how to accomplish the process of self-representation through the dual ways of color identification and unique shape selection.
Key words: Sacred and Profane;Stone Faith;Southwestern Minority;Hierophany;Space Transform;Self-Representation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681(2019)02-0222-07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南少数民族石崇拜文化的宗教人类学比较研究》(批准号:16XJZ003)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8-12-25
作者简介:
蒋楠楠(1981-),女,吉林四平人,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
杨嘉铭(1946-),男,藏族,四川康定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俗学、民族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 先 巴]
[责任校对 徐长菊]
标签:神圣与世俗论文; 石崇拜信仰论文; 西南少数民族论文; 显圣物论文; 空间转换论文; 自我表征论文; 厦门大学论文; 西南民族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