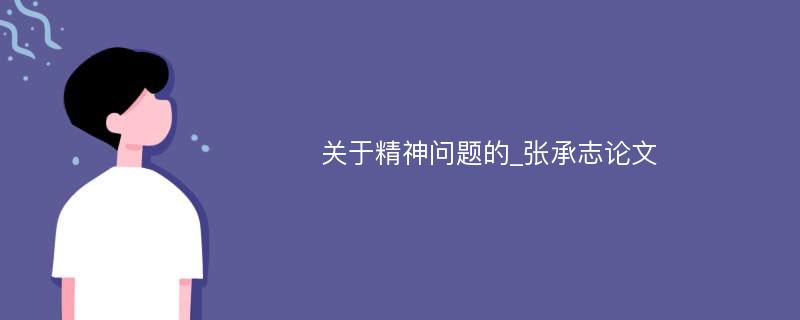
就精神问题致摩罗先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论文,罗先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摩罗兄:
我非常兴奋地阅读了你的几篇大作,它们引发了我的思考,当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有些我是强烈反对的。但我相信我们之间有共通的基础,因此我非常愿意借这个机会阐明我的看法,这与我所理解的人文精神相关。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我最早对你产生兴趣是由于你身上那种强烈的俄罗斯情结。这其实是许多人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包括我自己。但是,90年代以来,这却很少成为我们的一个话题。人们更愿意从罗兰·巴特、德里达、福科以及马克思·韦伯、哈贝马斯那里找寻思想,因为人们发现,90年代以来,现代性越来越构成一个问题,这是我们的知识传统所难以应付的。象80年代一样,我们习惯于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家那里寻求帮助,这里面隐含着的是一种进化主义观念,我们天真地以为,中国的明天就是西方的现在。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思维需要采用西方的,而中国的反思现代性话语也需要依靠西方。90年代所谓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盛行是80年代思维方式推进的必然结果。所以,人们尽管讨厌那个拿着后现代大棒跳来跳去,东砍西劈的小丑,但明智的学者更愿意把他与真正富有创造力的后现代主义者区分开来,不愿因此而放弃对福科等人的兴趣。但是,用后现代理论来表达与思考当下中国的处境和问题,从根本上无法摆脱两难境地:中国的现代化并未完成,这里面暴露出来的现代性问题与西方问题有很大差异,而西方理论并不能整合成的一种可能性让我们同时思考现代化与现代性,一些学者在福科与哈贝马斯之间徘徊,也就是这个道理。
但人们由此而悬搁了一个本应关注的问题,那就是鲁迅在世纪初就提出的对弱小民族国家的思想与文化的关注,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些在现代化国家的挑战面前,被逼走向现代化的所谓“后发”国家。它们的经验与中国更为相似,包括伟大的俄罗斯思想与文化,已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精神资源,它对我们其实有很大的吸附力,记得以前在《读书》上读过一篇文章《为什么我们同受煎熬》,讲述的就是这个意思。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是,这些国家如何应付西方的挑战?它们依照什么方式使自己强大起来?它们强大以后,又暴露出什么可怕的问题?而俄罗斯思想则为我们提供了双重资源:如何应付和反抗西方的挑战,以及如何应付与反抗国家组织行为本身的挑战。
我相信,人文精神诞生的前提就在于人们终于醒悟到了我们所面临的双重挑战,所以,提出这一“口号”的人们既不是西方主义者,也不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不会关心如何用西方的标准改造中国,也决不以反西方与民族主义为立场,他们超乎两者之上,而竭力注意在西方的挑战与国家的反抗与应付中出现的一系列的后果,在这些后果中,他们真正关怀的是个人的命运,是具体的每个个体的命运。因为西方的冲击涉及到人的个体命运,而且西方冲击所导致的国家组织行为,所谓“全民总动员”,同样关联着每一个个体的命运。这是必须注意的是,在全盘西化受挫之后,民族主义的泛滥已指日可待,以新权威主义、新儒学到极为粗鄙化的“中国可以说不”,都朝着同一方向汹涌奔去。俄罗斯思想中同样有着一体化的极权主义的色彩。而人文精神一旦被简化为“精神”、“道德”、“崇高”等是非判断极为鲜明的名词,是非常容易被民族主义所利用的,后者同样打着神圣的旗号,没有这个旗号,就没有能力实现一体化。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为我们所使用的标准的多重性而感到困惑,当我们批判理想主义的时候,自由主义甚至虚无主义成为我们的依据,而一旦发现自由主义的缺陷和虚无主义的危险,我们又在一定程度上回到理想主义那里。1995年的形势,似乎逼使许多知识分子在张承志与王朔之间选择一个立场,反对王朔的人们认同张承志,或者回避张承志的问题;反对张承志的人们又把王朔的问题遮掩得严严实实。仔细思考一下,一长段时间里有许多困难被制造出来:传统与反传统、现代与反现代、激进与保守、物质与精神、欲望与道德……互相排斥,宣扬自己的一套,而每一套在排斥了对立面之后,其缺陷也暴露得越来越厉害,人文精神也不幸被人为地纳入到这些两难境地中,被宣传或被攻击为是反物质、反欲望、反现代化的。
一个真正关怀个体命运的人不可能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不可能陶醉在东方专制大国的迷梦中,对现代化给个人带来的影响的思考并不意味着就是要复古,制造现代化与复古主义两难的人们其实是要阻止人们对其中一项的质疑。对个体命运的关怀更不可能意味着阉割人的欲望与物质要求。鲁迅指出:“接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不应该被读解为对人欲的弃绝,他的“个人精神自由”的主张是要求人们摆脱物质主义对人的奴役,也就是别尔嘉耶夫的意思,他明确地表示,个体的精神自由之中包含着人的物质欲望要求,但显然,他们都反对将个体仅仅理解为是一种物欲的主体。鲁迅显然发现了用物质主义回应西方挑战的危险性。目前,人文精神必然要对抗市场乌托邦所鼓吹的消费至上、享乐至上的意识形态,它所导致的对人的发展的丰富性的扼杀已经开始,并将持续地进行下去。一位大名人宣称先解决吃饭问题,后才能谈人文精神。这种面包与自由的关系问题早已被别尔嘉耶夫所解决。自由必定包含面包,如果一种制度承诺给你面包,条件是放弃你的自由,那么必须清楚的是,这面包并不是某一个人或派别能赐予的,而是你自己应得的,同样你有权利争取你的自由。因此,面包与自由的两难是被制造出来的。
有许多人不能理解人文精神为什么要强调立场和言说的依据,我本来也不能接受那些用这个口号扫荡文坛的人们的说法,而且自己也发现没有一个稳定的立场,所以有人戏称我为“骑墙派”。但我觉得需要有一个立场来检验一切价值和观念,它并不能轻易地解决所有困扰我们的问题,但可以提供我们一个说话和写作的依据。有朋友认为,现在最紧要的是建立最低限度上的认同问题,一种每个人都应遵循的“共同伦理”。我当然同意,目前许多混乱现象表明这种共同伦理是急需的。但知识分子批判的依据恐怕并不仅仅是共同伦理可以提供的。比如宣传,这在最低限度的社会准则里绝对是允许的,但对广告的批评也同样允许。王朔的创作是允许的,对王朔的批评也应该允许,当然,批判某种现象绝不意味着要用权力去消灭对象,后者会导致可怕的专制。但人们现在有意地混淆批判与专制行为的区别。聪明的王朔很刻毒地把两者混为一谈,似乎人文精神对他的批判成了专制主义对他的迫害。在王蒙看来,人文精神批判他,极左也批判他,所以两者是同一回事。共同伦理要防止的是各种野蛮与无序力量对共同社会的践踏与破坏,当然包括那些假神圣之名行野蛮之事的力量,也必须提防,但绝不用来提防与扑杀人类对精神自由的需求,但有些人却睁着双眼说昏话,把“正当”标举为“理想”,居然将王海作为他的理想旗帜。一旦“正当”被提升为理想,最低限度的规范就成了禁锢心灵自由的力量,其危害性并不比专制主义小。而视张承志的理想为奥姆真理教,连篇累牍地大加斥骂,也实在卑劣。
谩骂张承志与对张承志的批判是两回事,人文精神并不认同张承志式的未加质疑的理想主义,学者朱学勤早已推出了他的大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但朱学勤恐怕无法预料的是,有些人在不断地引用“道德理想国”这个词,来反对人们对道德与理想的呼吁,来为自己的非道德行为作辩护。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回避对理想主义的质疑。张承志在90年代当然有很大的贡献,在我看来,他是在当代最早敏感到双重挑战的作家。他第一次有效揭示在所谓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与日本对中国的“不义”,并提醒人们不能站在西方的立场上看中国与第三世界。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否则非常容易得出民族主义的结论。他更大的贡献,至今未被理解的是第一次有效地揭示在市场乌托邦的推进过程中,国家内部出现的新的“不义”,这也是张炜的主题。他们发现,在一片凯歌声掩盖下,一部分人在掠夺另一部分人,在破坏另一部分人的家园,他们发现凯歌声掩盖的底层苦难的存在。他们至少有一个立场,站在底层苦难民众那里观察整个世界。张承志的“人民”概念,指涉的就是在底层,在贫瘠的土地上生存着的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民众,并将他们提升为一种道德的、精神的存在,他必须将他们提升,才能形成他的立场,而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就象你所指出的那样,“人民”被美化了。“人民”这个抽象的概念不再可能指涉每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不仅西方人、都市人被开除出“人民”的队伍中,而且任何个体,只要与他的精神要求相背,就会被指认为堕落甚至成为他的敌人,人民/个体的内在紧张是张承志所无法解决的,而在清洁的精神中宏扬一种复仇主义,更必须受到批判,因为其前提是可质疑的。
因此,我同意你的“个人”的立场取代“人民”的立场。但我绝对反对你对“人民”所下的一连串判词。本来,“个人”是可以用来消解“人民”,使之转为对每一个个体的临时指涉,但你用“个人”来对抗“人民”,并使这个词继续发挥文化作用,这意味着你为了确立知识分子的“个人”的批判地位,而把非知识分子群体——“人民”置于知识分子之下。谁说“人民”只是批判和悲悯的对象?谁能论证“人民”没有美德只有流民习气?张承志把“人民”推向神圣的位置,你把“人民”置于脚下,同样是非常可疑的。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着的人们,千差万别,民间既可以藏污纳垢,也能延续精神的火种。每个人经验不同,与不同的人们建立联系,但谁也无法论证,他所见的人们的特点就是“人民”特点,因此,任何关于“人民”的判词都是虚假的、想象的,是在过度行使知识分子的言说特权。既然这个词不能在我们的语言中消失,那么,我希望它是一个不确定的开放性概念。“人民”即不在我们之上,也不在我们之下,而对于一个持个体精神自由立场的知识分子来说,对“人民”的关注理应转化为对每一个具体的生命的关注。蔡翔的那篇《底层》所表达的丰富而复杂的情感于我很有启示。我们都是从“人民”乌托邦中走来的人,内心深处保留着乌托邦的情感记忆。我不认为它应该被抛弃,而应置放在恰当的地方。我坚持相信,在纯朴的民间,有着我们至今未曾真正发现的美好的世界,但我绝不因此将它推向可膜拜的高度,也绝不因此掩盖日常生活中也时常目睹的来自底层的暴虐。我们都来自底层,对此不会没有记忆。“人人都有吃饭的权利”,这个命题是个人精神自由立场的一个部分,如果这个权利无法落实而在社会的另一侧则过度消费、肆意淫乐,那么这个社会肯定违背了公正原则。但这个命题不能推导出为了使人人获得吃饭的权利而必须消灭已有的精神自由。我从《俄罗斯思想》一书中读到了米海依洛夫斯基的一段话:如果人群“闯入了我的房间,打碎了别林斯基的塑像,烧毁了我的书籍,我不会向乡民们俯首贴耳。如果我的手没有被束缚住,我将战斗。”比义和团更无序的力量在这块土地上萌动,这股力量所攻击的往往并不是掠夺者,而是无辜者,因此他们自己成为掠夺者。今年戴厚英女士被残杀事件提醒人们,在审视社会所掩盖的“不义”的同时,不能漠视破坏一切的野蛮力量。但是,这种野蛮力量并不能使我们丧失对底层的美好的一切的感知能力。
个体精神自由的立场,意味着对具体的个体命运的关注,对个体摆脱各种奴役走向人间之爱的期待,对扼杀个体生存与发展的任何力量的反抗与批判。但我们不能把关注与期待转化为谴责。我非常不同意你对当代知识分子的批判。自然,与俄罗斯相比,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确实缺少很多精神素质。但是,你因此而批判了许多具体的有名有姓的知识分子,却是我不能接受的。鲁迅曾将受压迫的人分为奴隶与奴才。奴隶者,迫于生存而不得不听从主人的驱使;奴才者,乐于听从驱使者甚至替主人去迫害他人,以此为快。蔑视奴才是应该的,对待奴隶首先应该有一份同情心。有些人,确实做了让人恶心的事,但前提是他的脑子被换掉了。在劫难中的知识分子,责备他们不争、不清醒,太容易,也太省事了。但很可能遮掩了一个至今没有解答的问题:为什么知识分子甘愿被改造?为什么他们一个个都低下了头?我并不愿意认为这是一个道德尊严问题,一个人格操守问题,否则,我们很难理解那些富有傲骨的强者为什么也难逃这种命运。我更倾向于把这作为一个问题。我们需要重新研究那段历史,不再简单地判之为野蛮与封建,而应考虑到知识分子也曾自觉建构当代文化,两者有着相一致的追求。知识分子自我的丧失与他们自身的文化观念的失误有关。请阅读那本《中午的黑暗》,它详细地阐述了一种“铁的逻辑”,怎样使一个无辜者承认自己有罪。因此,与其谴责他们的怯懦、麻木,不如去思考他们何以如此,那些道德高尚的人们何以如此。
蔡翔在《神圣回忆》一文中区分了“神圣”与“神圣之物”,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你可以发现,对以往专制社会的人格的批判,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意见,第一种审视的是苟且偷生、怯懦与平庸,因此提倡精神、理想,第二种则认定精神、理想对人们的施暴,因此提倡用人欲的解放来抵御专制主义的卷土重来。这两种观点都可以找到无穷的例证,因而互相攻击对方与专制主义的血缘关系。但是,一个现代专制社会同时能制造出神圣的理想与斗士,和扭曲的苟安的人性。这种理想确实是排斥人欲的,但是,用蔡翔的概念来说,这不是神圣本身,而是神圣之物。上帝、种族、民族、党派、人民、革命等都曾充当过神圣之物。蔡翔强调,神圣就是神圣这个词本身。我想,他的意思是要守护神圣的不可言说性质,它来自心灵的直觉,是对现有自我的超越的期待,是对生存的终极意义的关怀。在一个古老的国度遭受强烈冲击,以往的信念动摇之后,对神圣的关联意味着重建价值与信念的渴望。但它非常容易转变成对神圣之物的制造,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促成个体将自己献祭出来,依照它的命令行事。对听从指令的斗士的暴虐行为的批判,对在神圣之物高压之下的灵魂扭曲现象的批判,应该归结为对神圣之物的由来、发展和倾覆的整体过程的批判,而不能限定在对具体个人的谴责上。我觉得,要求一个无知的13岁孩子忏悔,要求一个年老的软弱无比的文化人舍命抗争,却有些过分。
现在的问题是,坚持神圣的人们并没有冷静地反思神圣之物的危险性,反对神圣之物的人们同时否定了对神圣的追寻。两者并没有被有效地区分开来。所以,人们很自然地从那些重建理想主义的人们身上嗅到红卫兵的气息,而为了警惕这种危险性,就干脆提出了一个普遍的命题:理想杀人。而沉醉于物欲、践踏最基本的道德规范的流氓主义者被赋予伟大的意义,据说他们是真正的解放了的新人,有助于“消解”专制幽灵,因此,对他们的任何批判都成了专制的帮凶。我并不愿意区分两种危险性哪一个更大。现在已不可能回复到红卫兵时代,但只要看看当今的民族主义的思潮,就应该警惕未来的某种可能性。而痞子行为非但不能抵抗专制,反而为专制的复活提供了一种借口。
一位我很敬重的朋友警告我,在“个人自由”这个概念中间加上“精神”一词,非常可疑。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强调的是自由的物质基础,以及个人拥有“消极自由”的权利。这当然是对的,是必须做到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但是,仅止于此是远远不够的。我希望“精神”这个词是别尔嘉耶夫所解释的那个概念,它包容了物质的、肉体的,以及最基本的权利,但远远大于最低限度。因为没有对最低限度的超越,个体就不可能探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更不可能给“神圣”感以恰当的位置。仅止于此,个体自由很可能走向自我中心主义,一种在现有规范许可的范围之内的自我中心主义。你可以发现,在90年代,“个人性”、“私人性”、“个人自由”这类词的使用频率是很高的。通常在人们谴责一种文化或创作现象缺乏社会责任感的时候,这类词就会搬来为这种现象辩护。“我爱美元”的宣言、占有女性的幻想、私人生活的展览等等都受到这类词的庇护。而如果以最低限度的自由为尺度,你无权批判它们,因为这类现象并没有触犯法律、损害他人,是允许存在的。人们确实无权动用物质的力量对付它们,但是,个人精神自由的立场使我们有权利批判这类现象,因为精神自由在守护最低限度的规范的同时,强调对现有的自我的批判与超越,强调个体必须免受自我中心主义的奴役,走向对人间的关怀。在“神圣之物”倾覆之后,在“上帝死了”的一片欢呼声中,自我中心主义无限扩张在90年代堂而皇之,公开亮相,不仅在流行文化那里,就是在高雅的文化小品和随笔那里,都充斥着自我中心的趣味和情调。把他人的生死甘苦拦在窗外,再也无法体会另一个世界的孤苦无援。这已经成为90年代文化和文学中最致命的弱点和缺陷。这一切,是“消极自由”、形式上的正义所无法解决的。我认为,个人精神自由包含着对一种“大精神”的期待,是鲁迅式的“心事浩茫连广宇”的境界,一个要饭婆子在雪夜的死亡,会给他的内心造成强烈震撼;是穆旦式的“丰富的痛苦”,心灵的每一种创伤都与人间相关,别尔嘉耶夫认为,“当他(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便诞生了。”我相信,这与从鲁迅到穆旦的传统是相通的。这种精神自由的传统意味着个体能越过肉体的限制,关怀世界上某个角落里的婴孩的眼泪,能与目不识丁的受屈辱的汉子进行灵魂的交流。如同鲁迅所说:“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不是从上而下的悲悯,而如同你所说的那样,他人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他人的不幸就是我的不幸。个人精神自由不是要使个人与世界隔离开来,在一己的狭小空间手舞足蹈,而是要拆除个体与个体间的屏障,使灵魂得以相会,彼此得以诉说和倾听,使爱成为可能。我认为这就是大精神,就是神圣。它们不能被悬搁在彼岸,而必须化为此岸的实践。当然,这是精神的实践,必须以精神的方式进行,必须完全摒弃民俗权力的介入,并时时提防它们被世俗权力所利用的可能性。精神自由绝对不能变成精神教条。
我所困扰的并不是它们可不可以实践,而是我们几乎丧失了这种能力。心灵的枯竭与狭小是不可能因理性的反思而发生变化的。有的朋友以为我想用个人精神自由来解决一切问题,这实在是一大误会。我是想用这个立场来解释困扰我自己的文化争论,并摆脱这些争论,从而去发现被这些争论所遮掩的问题,它不能帮助我解决问题,只能使我发现更多的问题。而首先,是发现自我的问题,是自我的“空心人”性质。我们在90年代还是享有一定范围内的个人自由的,但这种自由是那样的轻飘。张志扬在《缺席的权利》一书中指出:“在意义消失之后”,中国人的情绪反应是——“无聊”。这个词大概可以概括90年代文化中那种空洞的自由状态。而90年代的许多小说也确实展现了这个主题,但似乎是以欣赏的方式展现的,结果是创造了更多的“无聊”。我们离摆脱无聊状态的时间还遥远得很,就象我们离精神自由的距离一样遥远。但我并不愿意因此而放弃对个人精神自由的期待,并以此为立场观察一切问题,包括自我。我想这一点上,我和你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