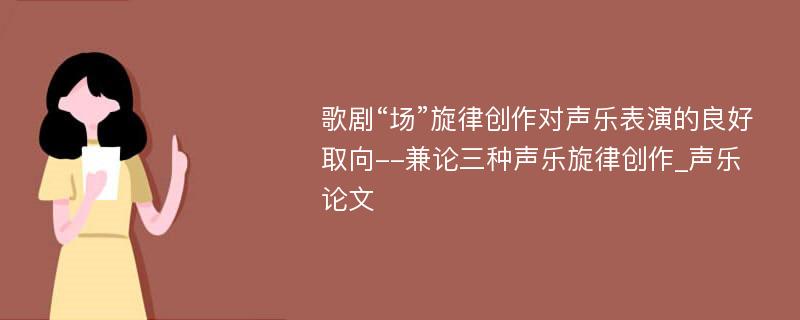
歌剧《原野》的旋律创作对声乐表演的良好导向——兼论声乐旋律创作的三种类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声乐论文,旋律论文,三种论文,原野论文,歌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歌剧是包含音乐、文学、戏剧、舞蹈、美术等多种元素的一种综合性艺术形式。它诞生于欧洲,引进我国也仅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我国歌剧的发展既是中西方音乐文化、美学思想的交会、碰撞与结合,又是西方艺术形式和中国不同阶段社会现实需要的磨合与适应。笔者之所以肯定、推崇歌剧《原野》,是因为二十年来它在中外演出的实际效果,已实实在在地证明了它是一部中西音乐艺术由“磨”到“合”、由结合到化合的成功例证。
《原野》的成功是多方面的:既有曹禺原作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揭示,又有万方歌剧脚本精彩地歌剧化;既有每位指挥、导演的创造性处理,也有每次演出舞美设计的精心构思;还有演员成功的二度创作等等。本文要研究的是音乐创作中对声乐演唱的一种导向作用,这种导向作用能使声乐演唱的中西结合避免片面和走入歧途,对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健康、全面的发展给以正确的引导和推动。
要研究歌剧《原野》如何对声乐演唱产生这种作用,必须首先阐明笔者对声乐演唱技术方面中西结合的一些基本观点,以及对声乐作品中旋律创作的一些分析、思考的方法。
在演唱技法上,中西双方有相同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用较深部位稳定、有力、柔韧的气息支持发声,保持声、气平衡,用特定的共鸣模式使声音加强和美化。不同之处在于:西方传统歌唱喉位较低,甚至把喉位置于最低位置,因此咽管相对较长,舌体、舌面较为放松、张力小,歌唱时声带上方、下方同时产生共鸣,高、低频兼有,为整体共鸣。而中国传统歌唱一般状况下喉位大约放在中等位置,咽管调节得较短、较细,舌体和舌面因语言动作造成的张力明显高于西方,口腔共鸣在总共鸣中占的份额明显高于西方歌唱,声带上方共鸣较多,声带下方共鸣则不明显,为部分共鸣。
西方歌唱中字和声的地位并重,既要声音圆润、优美、整体共鸣,又要语言清晰、语气正确生动,强调字、声利益的协调、统一;中国传统歌唱的理念是以字行腔,字领腔行,虽然追求字正腔圆,但是在字正基础上的腔圆。西方声乐中抒情的旋律往往有独立的音乐表现意义;中国声乐中抒情的旋律则往往从属于歌词,成为语言音调的美化和延伸。因此,西方从旋律进行的独立音乐形象出发,审美上就要追求旋律线条进行的平稳、均衡、统一、连贯,也带来演唱技术上气息和声音共鸣位置的平稳、均衡、统一、连贯。这种演唱的声音形象给人一种竖立、稳定、均衡、典雅的感觉。中国传统歌唱中,语言的表现手段比西方更丰富和多样化,辅音的成阻、持阻和除阻都可有不同的力度,不同元音音素多强调元音本身应有的不同色调,舌体根据元音需要在口腔中摆位后,始终保持舌面张力,在延长音的每一刹那都要强调此元音的特色,多强调对比性,要求根据普通话或地方话四声的需要以及表情的需要应用多种润腔的手法。由上述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中国传统歌唱是更接近语言层次的歌唱艺术,而西方传统歌唱是更多超出语言层次的歌唱艺术;或者,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歌唱较接近广义歌唱,西方歌唱更多追求狭义歌唱;也可说西方传统歌唱是具有更多器乐特点的歌唱,中国传统歌唱是具有更多人声语言特征的歌唱。
笔者对中西传统歌唱如何借鉴、继承,如何取舍、结合的观点是:学习、吸取西方歌唱的整体共鸣、抒情延长音时的自然颤音和声音形象的竖立感,继承、保留我国传统歌唱中对语言的讲究和发挥中国语言多种多样表现力的优长;在民族综合风格(即普通话语音基础上的中华民族共性风格)的歌唱中,在正确语言动作和语气基础上减少口腔共鸣在总共鸣中所占份额;在民族地方风格的作品中则更多保留我国传统歌唱技术特色,鼓励、保护各种民间演唱种类、特色和形式的同时,鼓励并推动职业歌唱家做到从修养到技术应能适应更多时代、地域和不同中外作曲家的作品,使自己的演唱既有中国风格和特点,又能与世界声乐艺术的审美共性相接轨。
声乐是音乐和文学紧密结合的艺术种类。绝大多数声乐作品都有歌词,因此在声乐作品的旋律创作中往往存在旋律表现意义和歌词表现意义的关系问题。歌词擅长表意,有叙事功能,而旋律则擅长表达不同感情、心境和情绪的起伏,所以说“语言穷尽之处正是音乐的开始”。音乐和文学结合有三种形式:纯音乐中的标题音乐以一个人们知道的故事做背景,用音乐表达人物个性、环境或戏剧气氛。配乐朗诵是以和词句情绪一致的音乐做背景,配合并加强朗诵所体现的文学感染力。而声乐中的歌曲、歌剧等作品则是把歌词和特定音符固定搭配在一起同步进行,是音乐和文学结合最紧密的一种形式。虽然紧密结合在一起,但词和音乐的结合是有其可分性、可变性以及相对独立性的,不然就不能解释同一旋律也能填入不同的词以及可以为同一首歌词谱写不同旋律的现象。综观中外众多声乐作品,我们可以把旋律写作分成如下三种类型:
1.带有主题或动机性质的有个性的旋律。此旋律有相当强的独立形象和表现意义,它的重音和进行方向与歌词的情感一致,可以做到不与语言的四声相悖,但决不依附于歌词的四声和为歌词的语调束缚住自己的走向。这种旋律引人联想的形象和情绪,远远超出和它配合的歌词的字面含义,而给听众的想象力和情绪理解以更大的空间,使听众更好地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升华。因此这种旋律具有飞翔性。西方声乐作品中此类型旋律较多,如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中巧巧桑的终场咏叹调《晴朗的一天》中歌唱的第一句旋律以及陆在易作曲的《我爱这土地》中歌唱的第一句旋律。下文中称此种旋律为旋律一型或第一型旋律。
2.旋律本身具有美感,但像好看的花纹、图案,通用性强,缺乏个性和对某个角色的针对性。这种旋律可按情绪类型的不同分别用于或思考、沉吟,或平稳叙述,或激动述说,或高昂的激情宣泄等不同的歌词。我国从宋代的词牌到元杂剧、清代的京剧和各地方戏的板腔、曲牌,莫不具有这种性质。这种旋律也可用于多段歌词反复的分节歌,也可在旋律大走向大体不变的基础上,根据歌词的四声语调调整小的旋律走向。西方声乐作品中有这种类型,但这种创作理念更多出现在中国戏曲和现当代某些群众化的分节歌形式的创作歌曲中,如美丽其格作曲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和时乐潆作曲的《歌唱二郎山》,以及京剧的西皮原板、二黄导板等板腔。下文称此种旋律为旋律二型或第二型旋律。
3.第三种类型旋律独立性很少,它们是歌词语音的美化和延伸,多数音符的运动、走向都和语言的四声一致。音乐本身有节奏和调式上的运动美,与歌词表达的情绪也吻合,唱起来自然、流畅,充满语言的音调美。但若去掉歌词,只唱旋律,音乐就会苍白无力,因此这种旋律不能从音乐角度提供给听众更多的想象力。这种旋律更多出现在西方朗诵性、宣叙性的歌唱和中国曲艺及说唱性的创作歌曲中,如郭颂的歌曲《新货郎》、先程作曲的《老司机》以及说唱艺术单弦、二人转中的很多曲调。下文称此种旋律为旋律三型或第三型旋律。
三种旋律类型因其不同的审美性质对演唱者具有不同的导向作用:第一型旋律因以旋律表现力为主,音乐就会引导歌者走向更加通畅的整体共鸣,让字与字、音符与音符之间更均衡、连贯、统一,只有这样旋律之美才能得到体现,这样的歌唱才更多超出语言层次,能在整体感觉上收放自如,使听觉在联想上产生飞翔感;第三型旋律必然要加强语言动作的舌面张力,使口腔保有更多的共鸣份额,必然要使用多种多样的方法增强语言的生动感、亲切感,使人感到歌唱的生活化,感到歌唱的亲切自然,只有这样,叙述、叙事的功能才能更好地发挥;第二型旋律是中间类型,其中说和唱的“利益”较为均衡,但也都难以充分发挥。按原始状况,西方擅长第一型旋律,兼有第二、三型旋律;而中方擅长第二、三型旋律,引进西方音乐后,才出现第一型旋律。
从我国的歌剧史上看,我国的歌剧作曲不是只用第二、三型旋律,就是只用第一型旋律;不是写成较西洋化的模式,就是写成类似民歌、戏曲的民族地方风格。歌剧《原野》则根据艺术表现需要采取宽角度审美的创作概念,横跨和融合了三种旋律类型,因此对声乐演唱产生了独特的引导作用。
如在序幕的混声合唱中为了表现旧中国农民在地主、恶霸、官僚重压下的愤恨和痛苦,其音乐写作手法一下就占据了两端。既有用“啊”、“欧”等虚词唱出充满小二度、大二度不协和音程的和弦,又有在男低音长音基础上其他三声部的或齐唱或独唱,还有无固定音高在不同声区说出的“黑呀!”、“恨哪!”、“冤哪!”等情绪化的实词。这样,序幕中音乐的独立表现力和语言、语气的独立表现力都得到了体现。①(见钢琴缩谱第2页第20-27小节及第4页第38-42小节)
再以仇虎的歌唱旋律为例。仇虎在第一幕中的咏叹调《焦阎王,你怎么死了》,其中有明显属于旋律三型的、和语调语气结合紧密的宣叙调的句子,在宣叙调进行到情绪最激动时,也极少量地使用限定节奏的道白(见缩谱第21-22页第142-151小节)。在歌词“下大狱,一呆就是八年”时,宣叙调实际已发展为咏叙调,旋律走向激昂,音乐已跃出字面意义,表达了满怀深仇大恨的情绪。咏叙调后面咏叹调已然开始,音乐的音调已独立表现出仇虎不屈服、不妥协,坚持反抗、报仇的个性(见缩谱22-23页第156-163小节)。在咏叹调的高潮,两个并列乐句号角般的高昂音调,旋律本身充分表达了从监狱逃出的仇虎砍断锁链后渴望复仇的豪情(见缩谱第24页第176-179小节)。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旋律从第三型随情感发展到第一型,语言的表现力和音乐的表现力轮番走到前台担当主角,引导演员的歌唱技术走向说、唱全面发展。
在第二幕仇虎的咏叙调及他和金子的二重唱中,作曲家又按照旋律一型写出仇虎优美、真挚的爱情主题,以音乐表达了他性格中爱恋、柔情的一面。这个音乐主题在第四幕和金子诀别前的二重唱中又得到了再现和发展(见缩谱第68页90-111小节及201-203页340-373小节)。这个属于旋律一型爱情主题的音乐形象和仇恨的主题不同,必然引导演员的用声在通畅的整体共鸣基础上,做到音色优美、柔和、连贯且富于音量上的伸缩性。
仇虎的歌唱旋律还使用第二型旋律表达了一种在复仇过程中的戏谑,但这戏谑中充满了阴森的复仇气氛。如第三幕中焦母与仇虎的对唱中,仇虎唱的《初一、十五庙门开》旋律是民歌风,虚词很多,地方风格很强,当然语言的表现力也强。这种民歌风的旋律很动听,但并没有感情和个性,具有相当的通用性。(见缩谱第97页第38-43小节)这段演唱的音乐风格和第一幕中仇虎的咏叹调形成很大的反差,和第二幕中的爱情主题也明显不同。它必然引导演员更突出语言的色调和口语般、生活化的表现力,不强调西方的那种统一和连贯,也不强调共鸣的一致性,在呼吸弹性上用歌声表现风格和语气是主要的。
综观仇虎的歌唱旋律占全了三种类型,涉及了语言的平淡叙事、复仇的豪情、爱的柔情、民歌风的俏皮四种表达风格。面对作品多样的要求,一位演员怎会不走向具有横跨中西、纵涉综合风格和地方风格的全面能力之路呢?
金子的旋律也同样涉及三个种类。如第一幕中金子的咏叹调《哦,天又黑了》中,歌词“这一天天啊,长得永远过不完哪,等来了早晨,又熬到夜晚”的内容是叙述的,情绪是低落的。在这里,作曲家让音乐服从语言、语调的表现力,在五度范围内加入调式外的半音音程及下滑音的手段,使旋律渐渐下行,在表达了叹息般情绪的同时,生动地突出并美化了语言的语调和语气(见第51页第461-467小节)。这样的第三型旋律的写法强烈诱导演唱者突出语调美、语气美,在作品规范中使唱法民族化。在沉闷的煎熬中,金子的性格不是认命,而是萌生出一种获得自由、追求幸福的理想和渴望。在这首咏叹调的歌词“多想有那么一天,太阳亮得耀眼。云高高,天蓝蓝,我变成一只小鸟”处,整个音乐用和声和调性变化的手法,以交响乐队主导进入一种明亮的色调。乐队和金子的演唱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以“对唱、重唱”式的配合塑造着金子心灵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见缩谱第52-53页第472-482小节)在这里旋律跃出了语言叙述的表现层次,音乐的独立表现力上升为主角。这种第一型旋律,主题形象鲜明的旋律自然在语言清晰的基础上对演唱者加强了使歌声通畅、整体连贯和音色亮丽丰富的导向,演员投入角色和音乐后,自己就会追求一种歌声上的飞翔感。
这种以语言为主和以音乐为主的旋律写法,不但可以共处于一段选曲中,在金子的音乐里,还能共处于一个乐句中。如第二幕中金子的咏叹调《啊!我的虎子哥》的前两个乐句,歌词“啊!我的虎子哥,你这野地里的鬼。这十天的日子,胜过一世”处,其中第一句开始的“啊”字是g[2]的延长音。浓缩进这个音的语意之外的含义十分丰富。包含十天来和仇虎重逢,住在一起的幸福体验、留住虎子不放他走的强烈愿望、对自己命运的感叹、对自由的追逐——这必然要求声音在整体共鸣基础上的集中和控制,此时的写法是旋律一型的。此句的后半部分唱到“野地里的鬼”时,音乐突出了语气和语调的生动。以音乐为主又过渡到了语言为主,加进了旋律三型的原则。第二句也是一样,“这十天的日子,胜过一世”中,“这十天的日子”是叙述,“胜”字大跳上行,使感情的飞翔性再次突出,“一世”从节奏到音调又是那样符合语气和语音,给人的感觉既亲切又得到情感上的充分体验。(见缩谱第65页第57-66小节)
和仇虎的唱段一样,金子在第二幕中和仇虎一起回忆青梅竹马的童年时也有一段民歌风格的属于第二型的旋律。(见缩谱第80页第265-276小节)旋律本身淳朴、优美,和语言音调又是那样匀贴,必然引导演唱者以语言的表现力和动听的民歌旋律自然结合,同步表达出一种具有民族地方风格的两小无猜的情调。这样,金子歌唱旋律种类的跨度也带来了一种音乐上的要求,既要求演员具有整体通畅、声音竖立、连贯、强弱控制自如的能力,又要求具备鲜明的民族风格以及语调、语气上的灵活和多样的表现力。
焦大星的歌唱旋律有以语言叙述为主的宣叙调,也有以音乐本身表现力为主的咏叹旋律,至少也是跨了两种旋律类型。如在第三幕中大星、金子的对唱、重唱中的开始处,大星唱:“金子,金子,刚才我做了一个梦”时,音调完全是从属于语言叙述的宣叙调。在“一个梦”三字时,还用半音下行造成很自然的说的感觉,属于第三型旋律。这段宣叙调的起始句过后,随歌词“梦见你头也不回,一步一步走了”的逐渐唱出,音乐的形象性和表现力逐渐上升,到“越走越远,消失在天边”时用等音转调的手法,以音乐形象描绘了在大星梦中,金子越走越远,渐渐离开的形象,写法回到旋律一型。(见缩谱第138页第448-454小节)
在第一幕大星的咏叹调《哦!女人》的呈示和再现的爱情主题中,作曲家应用了旋律一型的音乐主题的手段,以鲜明、美丽的音乐形象表达了大星对金子的珍爱之情。然后以一些旋律三型的叙述性旋律表达他在母亲和妻子面前的两难境地。最后这个爱情主题和乐队配合再现时由乐队先奏出主题,声乐接句尾,做了有变化的再现,也充分表达了大星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以及对婆媳矛盾的困惑。(见缩谱第36页第308-348小节)和虎子、金子的音乐一样,焦大星的音乐也是引导演员走向宣叙和咏叹、语言和音乐表现能力的全面性。
无论哪个民族或国家,歌唱的风格和方法都是由作品引导和限定的。因此创作的理念对歌唱的理念有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近百年来,西方音乐的体裁、形式、技术、方法引入之后,我国开始有了近现代意义的作曲概念:除我们传统的调式、调性外,引入了西方的大、小调体系;在歌曲、歌剧创作的抒情唱段中多使用方整的、中长句的大小调体系的方式,用主题和动机的观念塑造音乐形象;用脱离地方风格的民族综合风格去叙事和抒情。这样的创作,自然要求并引导演唱者脱离戏曲、曲艺的传统歌唱方法,更多应用西方传统歌唱的理念和审美追求。另一方面,也有作曲家更注重应用中国传统的调式,着意改编地方色彩很强的民歌或创作出接近民歌、戏曲风格的歌曲、歌剧,这些作品被我们称作民族地方风格。这样的声乐作品必然要求和引导演唱者较少应用西方传统歌唱方法,而用更接近我国传统歌唱的方法。由此,也就逐渐在歌唱界形成了西洋的和民族的两种风格的演唱。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这两种演唱类型的分别越来越明显:一方面,以学习西方歌唱方法为主的这一部分演唱者被称作美声唱法,他们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以西方古典歌剧选曲和艺术歌曲的演唱以及参加国际性比赛上,对于中国作品的演唱较少,因此西方唱法中国化的步伐更加缓慢。虽然他们能唱第一类型的旋律,但很多人只重视共鸣和音域,对中国语言的教条化处理不能让听众感到清晰、自然。另一方面,不少以演唱中国作品为主的歌者,特别是擅长演唱地方风格、色彩性作品的歌唱家,自己认为学习、吸取了西方传统歌唱的方法,做到了对民族歌唱的出新,实际上他们从未理解和掌握西方歌唱的真谛,反而陷入一种误解,也未真正继承我国民族传统歌唱的优长,他们只是处于使歌声亲切甜美的愿望,在喉头高的状态或不稳定的状态下歌唱,呼吸较浅,歌声有时平直,有时抖动过快,吐字只为了亲切、可爱而发嗲,根本没有继承民族传统歌唱吐字的分量、语言的过程美以及多种多样的表现力。甚至有人走向了流行风格,形成了所谓“民通”。这部分歌唱家适合唱第三或第二类型旋律,而对第一类型的旋律不适应,不胜任。当然,也有少数歌唱家对中西双方的传统歌唱技法都进行了较认真的涉猎,进行了较深入的学习,在中西歌唱的优势契合上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由上可见,作品的写法是中华民族风格和西方创作技术观念真正有机的结合出新,还是从作品角度就使中、西或“洋”、“民”泾渭分明,这成为我国民族声乐发展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能使两种或两部分演唱者殊途同归;解决得不好,将加速其分道扬镳,使我国声乐艺术的发展走上歧途。
歌剧《原野》的音乐创作在旋律上的成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语言表现力和音乐表现力的比例和关系的处理上跨越和包容了全部三个类型;二是三种类型的变化、过渡不是生硬、孤立的,而是完全根据角色和剧情发展内在需要的自然转换,又有着角色音乐个性的统一性。这就使得演员不会在某一类型旋律中从唱法走向极端,而影响自己适应另一种旋律类型。这种导向作用本身就以作曲技法的中西融合,促进了演唱者审美和技法的中西融合。笔者在二十年的《原野》演出中注意到一个现象:比如扮演金子一角的,有以西方传统歌唱为基础的邓桂萍、叶英,也有以民族歌唱著称的万山红和韩延文。民族女高音本来以唱民族地方风格为擅长,演了金子一角后,人们发现她变了,水平提高了、全面了。对歌剧《原野》,你无法把它归入“三种唱法”或“五种唱法”的哪一种;你无法让它在“洋”和“民”两个方面找到自己的归属。这就走向了我们理想的道路。它是中国的、现代的,又是世界的。中、西的优长在它的核心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化合了,出新了。不仅中国老百姓接受、理解、喜爱这部作品,在西方同样也得到肯定和赞扬。
当然,这部歌剧也还有缺点和可以继续修改、完善之处。如对焦母的音乐仍有中国政治观念上反面人物的简单化、脸谱化的问题,可用更丰满的音乐描绘她的内心;几位主要角色的声乐旋律仍然有展开不够的问题,如仇虎的音乐原来在第一幕爱情主题呈示后很短就结束了,后来增加了和金子的重唱后有所丰富,但仍然展开不够。
好的声乐作品确实能滋养、培育好的歌唱家,好的声乐作品确实能促进演唱的整体进步和提高。在演唱的中西优势契合中,能力全面的歌唱家的不断涌现和成长,反过来也能更好地促进好的作品的涌现,并使其变成舞台上的活的音响和形象。在歌剧、艺术歌曲这些外来的艺术形式中,无论演唱还是创作,都共同面临一个外来音乐体裁和技术中国化的问题,这个问题首先是找准思路和方向,正确的思路和方向无非三个点:西方传统的优点、我们传统的优点以及当代中国人的现时和长远需要。前两点以第三点为判断标准,第三点靠前两点的优势契合或化合来实现。具体做起来,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学习,把中西双方的传统弄懂、弄通,避免误解。在作曲方面,只会写洋腔洋调的人,往往其中国民族音乐的根底太浅;只能写某种民歌、戏曲风格作品的人,往往没有真正好好地学过西方音乐。这个道理放在演唱上也是一样。我们相信歌剧《原野》在以后的演出中会进一步完善、提高,以更新的版本和姿态出现在它上演的三十年、四十年或更久远的纪念日。我们更相信中国歌剧会出现更多成功的或更高水平的剧目。中华乐派或中国声乐学派就要靠像《原野》和众多优秀作品这样扎扎实实地一砖一瓦、四梁八柱的积累才能建设起来。像歌剧、交响乐、清唱剧这样的“高雅音乐”形式是民族心灵的窗口,只要我们思路对头,锲而不舍,中华民族当代音乐艺术终会赢得和我们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发展速度同样的地位。
我们赞扬《原野》!我们呼唤更多《原野》式的成功!
作者附言:此文作为提交论文,曾在2008年6月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第三届年会暨纪念歌剧《原野》上演二十周年研讨会上宣读。
注释:
①文章中使用的钢琴缩谱为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金湘音乐作品选集”歌剧《原野》(作品40号),文中只夹注该乐谱的页码和小节数,下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