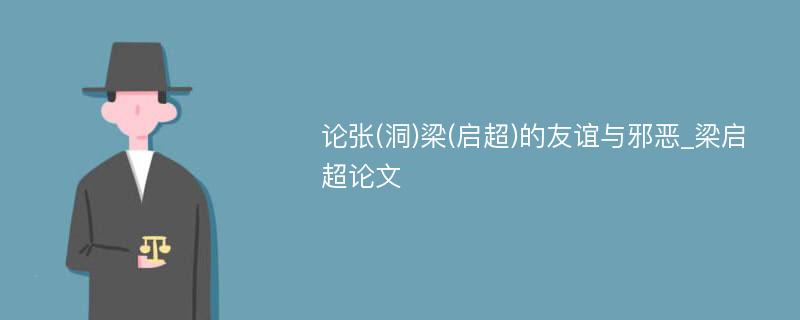
论张(之洞)梁(启超)交谊与交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交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05)01-0001-06
张之洞和梁启超均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名人。他们都深受传统文化的 熏陶,取得过科举功名,也都不同程度地主张学习西方。但二人资历和在晚清政坛中的 地位悬殊,梁启超比张之洞小36岁,当他尚在科举之路苦苦攀登时,张之洞已享誉官场 ,成为著名的洋务大吏和教育家了。他们二人发迹的道路也有所不同,张之洞以翰苑清 流起家,继而历任封疆,又以大办洋务、教育而蜚声中外。梁启超则以助乃师康有为发 起“公车上书”和以其妙笔文章而崭露头角。早在甲午战争前,梁启超就十分仰慕张之 洞,维新运动兴起的历史机遇,使他们由相知到相交,既结下师生交谊,又展开了学术 论争。戊戌政变后双方反目交恶。张、梁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了维新运动的进程,以 往有关论著虽有涉及其中一二事,但语焉未详,所论也未必妥切,迄今尚无专题论文面 世。(注: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 民出版社1993年版)均述及梁启超1897年初到武昌拜谒张之洞的事;冯天瑜、何晓明《 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论述了张之洞与维新运动的微妙关系;汤志钧 《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对张之洞干涉《时务报》也有所论述。黎仁凯《 论张之洞与维新派之关系》(文史哲1991年第4期)也论及了张梁武昌会晤及张之洞荐举 梁启超诸事。笔者爬梳张、梁的集子及《汪康年师友书札》等资料,发现一些能反映二 人关系的资料,于是撰成此文。)本文拟以维新运动前后为中心,就张梁交谊、交恶及 其原因作一较系统的考察。
一
梁启超知晓张之洞是在1884至1885年之间。1884年初冬,梁启超赴广州应考,中秀才 ,次年入广东最高学府——广州学海堂读书。此时,梁启超阅读了张之洞撰写的《书目 答问》一书,该书是指导士子学习经史、词章、考据诸学的入门书。梁启超说:“启超 乡曲陋学,十三(指虚龄)以后,得读吾师(指之洞)训士之书,乃知天地间有学问之一事 。”[1](文集之一《上南皮张尚书书》P104)梁说的“训士之书”,便是《书目答问》 ,对梁启超起了启蒙作用。恰巧1884年夏,张之洞由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来到广州。 梁对近在咫尺的前辈学者与地方最高军政长官自然不会置若罔闻。中法战争后,张在广 东大力兴办洋务与教育事业,先后设立广雅书局、洋务处、枪弹厂、水陆师学堂、广雅 书院,并筹建织布局、倡修芦汉铁路等,成绩斐然。这些不能不使学子梁启超钦羡和仰 慕。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更以缔造江汉自任,宏图大展,赢得了许多官僚士大夫的 景仰,成为与李鸿章相颉颃的洋务大吏。时人评论说:“现今有为之士,不北走北洋即 南归武汉,朝官外出可寄托者,李(鸿章)与张(之洞)耳。”[2](P82)1893年2月16日, 梁启超致书汪康年:“张芗帅,今世之大贤也,其于铁路之利,久己洞烛,而于兴铁路 之事,久己蓄意,而其权力,又可以昌言于朝廷、力争于当路,则非我辈纸上空谭之比 例”;他还拿张之洞同古代的王安石、张居正相比,认为“芗帅权位虽不逮二人,而才 力实过之”,因此劝汪康年“力赞芗帅”修造铁路[3](第2册P1828-1829)[4](P686-687 )。汪康年系张之洞的幕僚,梁启超与其常有书信来往,并从中了解张之洞及其幕府的 情况,如他致函汪氏说:“闻香帅幕中,有一梁姓者,……弟度其人之无能为也。君所 见之人,所闻之事,望时相告。”[5](P34)这些都表明,早在甲午战争前,梁启超就十 分仰慕张之洞的才识和功业,而且关注他的幕府。
张之洞知有梁启超其人,应是1889至1894年间。1889年广州学海堂专科生季课大考, 梁启超四季均名列第一,9月应广东乡试,16岁的他中举人第8名,主考官李端棻钦羡其才学,便托副考官王仁堪做媒,将小妹李蕙仙许配给他。时任两广总督、向来注重兴学育才的张之洞,对这位学海堂的高才生、少年举人的双喜临门和李端棻考场选妹婿佳事或许会有所闻。同年冬,张之洞奉调离粤赴鄂任湖广总督,二人失去了相互结识的机会。1890年春,梁启超首次赴京会试落第,同年秋,经陈千秋介绍入广州万木草堂,做了康有为的弟子。1891年夏,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一书刊行,此书惊世骇俗,在学术界和官僚士大夫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康有为由此名声鹊起。作为康氏高足、“从事校勘”并协助出版该书的梁启超,名字也渐为世人所知。1894年,给事中余晋珊上书弹劾康有为“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其时客居京师的梁启超马上为之奔走,运动沈曾植、黄绍箕、张謇等人疏通重臣大吏营救乃师。[6](第4册《康南海自编年谱》P128)其时梁启超所结交的人员,大多都与张之洞有交谊或是张的门生、幕僚。因此,身兼封疆大吏与学者的张之洞不会不知晓梁启超这位学界新秀。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梁启超联络在京应试的举 人1300多人,发动了“公车上书”,请求废约拒和、迁都、变法,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 幕,康梁也因之登上政治舞台而名扬中外。官僚士大夫对梁启超刮目相看了。此时的张 之洞正如日中天,在甲午战争中以其主战言行和积极筹划抗战和保台活动而博得了时论 的普遍赞誉;战后又上呈《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了变法救亡的主张,赢得了有识之 士的景仰。唐才常盛赞张之洞的“直言敢谏、不避权奸,一时无两”,认为“凡有人心 者无不敬之慕之哀之痛之”[7](P270)。严复也认为张之洞“极足有为”,曾希望陈宝 琛引荐他加入张之洞幕府。可见张之洞是当时众望所归的人物。
变法救亡的共同愿望和维新运动兴起的历史机遇,促成了梁张交谊。1895年8月,康、 梁在京开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梁启超、汪大燮担任主笔,刊出的 论说,多出梁启超之手。接着,康梁等人开始筹设强学会,在帝党官僚和地方大吏中筹 集资金和寻找奥援。张之洞捐5千金充会用,维新派对他尤为见重,推其为会长。[6]( 第4册《康南海自编年谱》P257)这为张之洞与康梁的交谊作了铺垫,也揭开了张之洞与 康梁维新派合作的序幕。11月初,康有为南下江宁(南京),居20余日,与署理两江总督 张之洞共商开办上海强学会,“香涛颇以自任,隔日一谈,每至夜深”[6](第4册《康 南海自编年谱》P135)。他又捐资1500两,命幕友梁鼎芬、黄绍箕偕康有为赴沪筹办会 事。不久,在张之洞和康有为的策划下,上海强学会成立,维新人士黄遵宪、汪康年、 黄体芳、张謇、沈瑜庆、章太炎等纷纷入会,并出版了《强学报》。于是《上海强学会 序》署张之洞之名(实康有为代撰)在《申报》刊出,而《上海强学会后序》则直署康有 为之名。这种配合默契的安排,无异向世人宣布,张之洞与康梁维新派己携手走上维新 之路,张之洞也成了维新派的同路人。[8](P88-89)
但天有不测风云。1896年1月,御史杨崇伊参劾强学会“植党营私”,导致慈禧太后封 禁京师强学会和《中外纪闻》。“善趋风势”的张之洞害怕受到牵连,便以不同意用孔 子纪年为由,不得不关闭了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以免触犯慈禧太后。然而,维新 思潮蓬勃兴起之势已不可遏止,张之洞也未改变与维新派合作的初衷。他变换方式退居 幕后,积极支持汪康年、黄遵宪用上海强学会之余款筹办《时务报》。为避免再生瓜葛 ,“南皮不愿出名”,这笔余款也未明言是上海强学会所余,只作为汪康年“捐集”之 款[9]。张之洞还通过汪康年聘梁启超担任该报主笔。
梁启超于1896年4月抵达上海,与汪康年等人筹办《时务报》,张、梁开始了实质上的 合作,张在自己统辖的地盘内为梁开展维新活动提供了良好的舞台。8月9日,《时务报 》正式发行,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任主笔。梁启超以其新颖见解和生辉妙笔,宣传维 新变法,提倡新文化和改革旧习俗,抨击封建专制制度,著名的《变法通议》就首先在 该报连载。《时务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出版仅一个多月后,张之洞 便饬令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他说“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 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所录外洋各报,皆系就本文译出,不比 坊间各报讹传臆造;且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 令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各局、各书院、各学堂订阅此报,共288份,由善后局拨 付报款[10]。在他的倡导影响下,山西、湖南、安徽、浙江、江苏、贵州、江西等省也 纷纷效法官销《时务报》,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影响。时人评论说:“时务报蔓延最广, 论者比之明夷待访录。张之洞提倡尤力,札行湖北全省州、县官,各备资购阅。”[6]( 第1册P366)又云:“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 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11](第4册P47)这两篇 评论,一表之洞提倡之功,二赞启超文笔之妙。随着《时务报》风行海内,张、梁携手 合作赢得了饮誉神州、相得益彰的社会效果。
梁启超名满天下成为社会新宠,张之洞想进一步拉近二人关系。1896年冬,张邀请梁 赴鄂见面并打算拉他入幕。其时梁启超致函夏曾佑说:“超被伍(廷芳)使苦邀出游,又 被南皮(之洞)欲夺入鄂,悉未应之。将留海上、开堂讲学。”[5](P55)梁启超对伍廷芳 之邀不屑一顾,他认为“伍使为人庸劣乖谬,待其僚属无人理,且绝非欲办事者”[5]( P55)。而对张之洞的邀请,梁则不会置之不理,不久,梁、张即在武昌会晤。
二
1897年是梁启超与张之洞关系中具关键性的一年,是二人从相知、倾慕合作转入相见 和建立师生交谊的一年。是年1月18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梁启超至武昌 湖广总督衙门谒拜张之洞。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有一段叙述:“当戊戌变法之前, 梁启超过武昌投谒,张令开中门及暖阁迎之,且问巡捕官曰,可呜炮否?巡捕以恐骇听 闻对,乃已。定制钦差及敌体官往见督抚者,始呜炮开中门相迎,若卿贰来见,但开门 而不鸣炮,余自两司以下,皆由角门出入。梁启超一举入耳,何以有是礼节。盖是时己 有康梁柄国之消息,香翁特预为媚之耳。启超惶恐不安,因著籍称弟子。”[6](第4册P 301-302)此出自顽固派之手,把老于官场世故的张之洞描写成不懂礼仪且颇含揣测成分 ,是否合符史实,有待查考。但张之洞相邀之厚意和梁启超执弟子礼是无疑的。这可从 会晤后第二天晚上,梁启超给汪康年、麦孟华的信中得到证实:“十六日适南皮娶侄妇 ,贺客盈门。乃属节庵(梁鼎芬)入与之言,其午乃入见。南皮撇下诸客延见,是夕即招 饮,座中惟节庵、念劬(钱恂)两人相陪,谈至二更乃散。渠相招之意,欲为两湖时务院 长,并在署中办事,以千二百金相待。其词甚殷勤,又其辨过于伍(廷芳)。超大窘,无 以拒之。然沪上实不能离,鄂事实无可办,故决不能就。哀求节、念二人善为说辞,彼 皆南皮之党,不肯援手,实在无法,唯求穰兄(汪康年)相救,写信与南皮,言报馆必须 超,或可耳。”[3](第2册P1841)可以看出:张之洞以优厚待遇劝梁入其幕府,梁虽婉 言辞谢其美意,无奈张及其幕僚苦苦相邀,所以梁才请汪康年为之说情。梁启超为什么 不受聘?主要原因是他倾心办报,舍不得离开正蒸蒸日上的《时务报》,也想在上海“ 开堂讲学”,而在武昌则没有具体事可做。此外,双方的“论学不合”也是原因之一。 但这次历史性的会晤结下了张、梁的师生交谊。梁启超既诚惶诚恐,又喜不自禁,开始 对张执弟子礼。他回到上海后写信给张之洞,追忆武昌晤面之情形:“赐以燕见,许以 尽言,商榷古今,坐论中外,激言大义,不吝指授,刍荛涓流,靡不容采,授攴愧赆, 殷勤逾恒,宁惟知己之感,实怀得师之幸”;信中即尊称张之洞为“吾师”,盛赞张之 洞兴学育才之成效,并说“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 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故为今之计,莫若用政治学院之意提倡天下”,并 向张之洞提出了学堂课程改革的建议[1](文集之一《上南皮张尚书书》P105-106)。可 见,武昌会晤建立的师生交谊,把二人关系推向了高峰。
以往有些论著谈张之洞参与维新运动,以“投机”或“假”立论,这有失偏颇。梁启 超对张执弟子礼,也非一时心血来潮。他与张之洞合作,首先是出自变法救亡的共同愿 望,其次在推动社会改革与文明进步问题上确实存有许多共识。
其一,在兴修铁路问题上,张之洞倡修芦汉铁路,梁启超赞赏有加,曾致函汪康年, 劝其“力赞香帅”修铁路。他说:“今诚能于南北冲途成一大路,而令商民于各直省接 筑,则十年之间,如身使臂,臂使指,与今日电线相应,转弱为强之机,可计日而待也 。”[3](第2册P1829)梁又上书湘抚陈宝箴:“今日救中国,下手工夫在通湘粤为一气 ,欲通湘粤为一气,在以湘之才用粤之财,铁路其第一义也。”[6](第2册P592)张之洞 知悉梁热衷修铁路后,1897年夏,曾荐举梁启超参与筹划修铁路。梁氏《三十自述》称 :“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大理寺卿盛宣怀连衔保奏,有旨交铁路大臣差 遣,余不之知也。既而以札来,粘奏折上谕焉,以不愿被人差遣辞之。张之洞屡招邀, 欲致之幕府,固辞。”[12](上P366)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中也有张之洞荐举广东举 人梁启超的记载。梁启超虽然没有加入张之洞幕府,也没有接受修铁路的差遣,但已表 明了双方对修铁路的共识和愿望。
其次,在戒缠足、兴农学、兴女学等社会改革问题上,梁启超大力宣传和组织各种学 会;张之洞则积极支持、参与这些改革社会的活动,并力邀梁启超赴鄂商谈。1897年夏 秋间,梁启超、汪康年等在上海成立戒缠足会和农学会,张之洞不仅为之作序,请求列 名参加,并捐款支持。他致函说:“戒缠足叙,呈教。农学会请附贱名,谨捐银五百元 ,已交汇号。甚盼卓老(指启超)中秋前后来鄂一游,有要事奉商,欲得磐桓月余。”[1 3](第12册P10347)这封信中所说的“戒缠足叙”,即《戒缠足会章程叙》。梁启超议定 了该章程后,不仅自撰了《戒缠足会叙》,还邀张之洞为之作序。汪诒年说:“梁君( 启超)所拟章程既定稿后,南皮张孝达尚书时为两湖总督,特为作序以重其事。”[5](P 70)仔细检读梁、张各自所写的序文,便会发现二人所见略同。譬如,梁启超指出缠足 的危害“是率中国四万万人之半,而纳诸罪人贱役之林,安所往而不为人弱也。……而 吾中国满蒙旧俗,幸未染此,后妃崇贵,同屦依然”[1](文集之一《戒缠足会叙》P121 )。张之洞也列举了缠足之危害,认为缠足使“此四万万人者,己二分去一,仅为二万 万人。……吾华民之禀赋日薄,躯干不伟,志气颓靡,寿命多夭,远逊欧美各洲之人, 病实坐此。试观八旗满蒙不缠足,广东沿海不缠足,其人气体之强,即胜各省,信而有 征”[13](第12册P10060-10061)。两相对照,文字表述虽异,其实寓意相同。张之洞还 特意在文中赞扬了梁启超:“梁君卓如合南北之贤者数十辈,倡为此会,并为之说,其 意美矣。”[13](第12册P10061)时务报社收到了张之洞的序文后,梁启超急催汪康年刻 板印刷:“张香帅序定何时刻?此期似不能不刻。……今得香帅序尤当大振军声,不可 更示人以失望。”[3](第2册P1867)他在《医学善会叙》一文中,也对“南皮先生叙不 缠足会”加以赞扬。可见二人相互推重,张为梁的活动加油助威,梁则希望借助总督大 人的支持以扩大改革的社会影响。此外,二人均重视农业改革,梁设立农学会,张请附 名参加;梁撰有《农会报序》,主张讲求农学,区分门类“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 由;远摭欧墨(美),以得其立法之所自”,主张学习西国农学新法[1](文集之一《农会 报序》P131)。张之洞也认为“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要讲求修农政,兴农学,在武 昌设立农务局和农务学堂,分设农桑、畜牧、森林等专业,聘请美国农学专家当教习, 购买美国新式农具和棉花、谷物、果品良种进行试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梁启超还对 张之洞所办的洋务事业多有赞扬,1897年,他撰《记自强军》一文,称赞张之洞署理两 江时编练的自强军,“所闻自强军者,全军操练仅八阅月,马军乃一月有余耳,而其士 躯之精壮,戎衣之整洁,枪械之新练,手足之灵捷,步伐之敏肃,纪律之严谨,能令壁 上西士西官西妇观者百数,咸拍手咋舌、点首赞叹。……惜夫中国之大,而可观之兵, 只有此数也”[1](文集之二《记自强军》P32-33)。其赞赏、钦羡之情溢于言表。可见 此时二人是相互支持、相互借重的。
再次,在改科举、废八股问题上,梁启超认为:“惟科举一变,则海内洗心,三年之 内,人才不教而自成,此实维新之第一义也。”[6](第2册P546)1898年4月,梁启超联 合举人百余人,上书请废八股取士制度,都察院和总理衙门均不肯代奏。为此,他设计 了由维新同志拟稿十折,筹集三千金,分馈台官,请求他们一个月内上陈改科举、废八 股奏稿十折的方案。[6](第2册P546-547)作为教育家,张之洞对科举八股取士之弊也十 分清楚,他主张书院、学堂开设西学课程和奏请清廷对新式学堂毕业生给予奖叙,就是 对科举制的挑战。他说:“救时必自求人才始,求才必自变科举始。”[13](第12册P10 688)1901年6月,曾请求清廷宣谕议改科举,讲求实学。但他深知科举事关重大,直到1 905年才正式奏请废科举。梁启超说:“即如八股取士锢塞人才之弊,李鸿章、张之洞 何尝不知之,何尝不痛心疾首而恶之。张之洞且尝与余言,言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矣, 而不闻其上折请废之者,盖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 童生之怒,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已也。”[1](专集之一《戊戌政变记》P84)可见,他 们二人曾商讨过改科举、废八股的问题,并早已取得了共识。
总之,此时的梁启超与张之洞,出自对变革社会的共同认知和志趣,已建立起相互倚 重、支持的合作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
三
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开展,张之洞与梁启超的矛盾论争也日益凸显。究其二人之矛盾 ,主要源于学术与政见的歧异,诱因是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抨击汉学家、倡民 权等文章,遭到了张的抵制干涉。梁启超说:“文襄以报中多言民权,干涉甚烈,其时 鄙人之与文襄,殆如雇用者与资本家之关系。年少气盛,冲突愈积愈甚。”[6](第4册P 254)当时,《时务报》刊出了梁启超的《论科举》、《论学会》等文,猛烈抨击了汉学 家纪昀和倭仁,引起了张之洞及一些幕僚的不满。其幕僚顾印愚致书汪康年说,报中“ 有诋纪昀语,河间大怒,广雅亦不平,此无益而有损之文,以后请加检对也”(注:河 间指张之洞幕僚纪钜维,直隶河间人,纪昀同乡;广雅指张之洞。《汪康年师友书札》 (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284页。)。另一幕僚梁鼎芬则撰文辨驳,并嘱汪康年 要多加小心:“卓如诋纪甚,诋倭尤甚,仆有文辨之,本要刻板,再思中止,他日存集 可也。以后文字真要小心。”[3](第2册P1900)鼎芬为避免关系弄僵,并未刊刻该文。 但启超并未收敛,尔后又发表了《知耻学会叙》,揭示了官、士、商、兵、民等“无耻 ”的种种迹象:“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 而敢于司李,瞽聋跛疾,老而不死。”[1](文集之二《知耻学会叙》P67)张之洞读后更 为不满,即致电陈宝箴、黄遵宪说:“梁卓如所作《知耻学会叙》,内有放巢流彘一语 ,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恐招大祸。……若经言官指摘,恐有不测,《时务报》从此 禁绝矣。”并嘱他们“此册千万勿送”[13](第9册P7404)。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 中也说:“梁启超已到,其报中有一段文字,诋中国人太过,香帅嘱毁之。”[5](P86)可见,梁启超与张之洞在报刊宣传舆论导向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并由此导致了双方的笔墨之争。
其实,张、梁的分歧论争很大程度上源于学术流派和文化观的不同。张之洞崇尚古文 经,为学兼师汉宋,“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13](第12册P 10631)。康梁学派则崇奉今文经,演绎公羊学,讲孔子的“微言大义”。张对康梁学派 的主张早有不同看法,他不同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曾多次劝说康有为“勿言此学” ;他也称民权说为“奇怪议论”,曾表示“学术不敢苟同”。康梁则坚持自己的学术见 解,梁启超曾致书汪康年兄弟说:“弟之学派,不为人言所动者,已将十年”,而且“ 自信吾学必行。”[5](P59)梁启超排斥古文经,不赞成考据学,认为“此考据家旧习, 吾党正排斥不遗余力,必不宜复蹈之”[5](P81)。他曾讥讽张之洞的幕僚缪荃孙“抱此 敝帚(指考据学)以自炫”。1897年春,崇奉古文经学的章炳麟一度在《时务报》任编撰 ,因学术上与梁启超、麦孟华门庭各异、常相抵忤。章说:“春时在上海,梁卓如等倡 言孔教,余甚非之”,“麟自与梁、麦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5](P81-82 )正因为如此,次年春,张之洞特邀古文经学家章炳麟入幕,到武昌主持《正学报》, 原因是“之洞以其尚左氏而抑公羊,故聘主笔政”[2](P126),来同康梁的今文经学相 抗衡。可见,双方早已互存学术门户之见。
就文化观而言,张之洞与梁启超都在探索如何规范中西文化之路,但观点各不相同。 张之洞合汉宋中西,以求体用兼备之学,认为“六经皆圣人经世之书,西国富强之术, 不能出其范围”,坚守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文化观,且这一观点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 同。梁启超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 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 ,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梁启超则试图突破“中体西用”论的束缚,去 构建一种融通中西的新文化模式,于是他“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 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1](专集之三十四《清代学术概论》P71)。梁还 说:“张香涛纠率许多汉学、宋学先生们著许多书和我们争辩,学术上的新旧之斗,不 久便牵连到政局。”[14](P29)梁启超的这些叙述表明,维新运动时期确实存在着张之 洞等人“中体西用”文化观与康梁维新派融通中西文化观之间的论争,这种论争虽然还 属于学术论争的范畴,但已悄悄地向政治斗争转化。
由于学术流派与文化观的不同,就注定了张、梁之间的交谊与合作必然是短暂的昙花 一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梁交谊日益疏淡。《时务报》发生的梁启超与汪康年之争 ,张之洞站在汪康年一边;梁鼎芬对《时务报》的频频干涉,也一直得到张之洞的支持 。继而梁启超离沪赴湘主讲时务学堂,政治上除宣传民权外,“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 失政,盛倡革命”;学术上“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1 ](专集之三十四《清代学术概论》P62)。湖南一些守旧士绅对此大为不满,一面上书总 督张之洞,一面大肆攻击维新派,宣称“梁卓如来湘,苟务申其师说,则将祸我湘人, ……公羊之学,以之治经,尚多流弊,以之比附时事,更启人悖逆之萌”[15](卷6《叶 吏部与石醉六书》)。他们甚至请求清政府诛杀康、梁。梁启超说:“时吾侪方醉心民 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湘中一二老宿,睹而大哗, 群起掎之。新旧之讧,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御史某刺录札记全稿中触犯清廷忌讳者百 余条,进呈严劾。戊戌党祸之构成,此实一重要原因也。”[5](P84)他说的“一二老宿 ”是指王先谦、叶德辉。荻葆贤说:“于时王先谦、叶德辉辈,乃以课本为叛逆之据, 谓时务学堂为革命造反之巢窟,力请于南皮。赖陈右铭中丞早已风闻,派人午夜告任公 ,嘱速将课本改换。不然不待戊戌政变,诸人已遭祸矣。”[5](P88)梁启超虽因巡抚陈 宝箴的暗助而未被祸,张也未加深究,但其“别康梁”之念头已经萌生。因此,当维新 运动继续发展,帝、后党争逐渐走向激化之时,张之洞撰写了《劝学篇》,以示同康梁 划清界线。张之洞的幕僚刘禺生说:“张之洞本新派,惧事不成有累于已,乃故创学说 ,以别于康、梁。”[2](P126)辜鸿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文襄之作《劝学篇》, 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16](上P419)其实,早在梁、张见面交 谈时,梁、张之间的“论学不合”已初露端倪。张之洞的幕僚罗振玉说:“及梁氏(启 超)赴湘,文襄邀与谈竟日夜,始知其所主张必滋弊,乃为劝学篇以挽之,然己无及矣 。”[6](第4册P249)可见,张之洞作《劝学篇》是与康梁断交的先兆。
四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第二天慈禧太后谕令查拿康有为。张之洞获悉后为洗刷 自己与康梁的关系,立即致电孙家鼐:“康己得罪,上海官报万不可令梁启超接办。梁 乃康死党,为害尤烈。”[13](第9册P7657)这是张、梁断绝交谊、反目交恶的开始,二 者的学术论争也随之转变为政治斗争,感情虽断,笔墨之仗并未停息。
张、梁交恶,除了上述学术上的原因外,其社会角色和政治地位的差异也是重要原因 。张久任封疆大吏,官高权重,是既得利益者,重守成务实,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无不受其社会角色和政治地位的制约。梁启超仅一举人,起初无职无权,但年少气盛, 自称“思想浪漫得可惊”;又说“启超常持一论,谓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为陈胜吴广 ,无自求为汉高,则百事可办”[1](专集之一《与严幼陵先生书》P107)。以初生牛犊 不怕虎的精神,渴望效法陈胜、吴广来改造社会和提高社会地位,这与张之洞忠君守节 差若天渊,政治上不“门当户对”,其交谊必然是脆弱而短暂的。
康、梁等逃亡日本后不久,康转赴美国,梁则仍留在日本办《清议报》。张之洞致电 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梁启超、王照尚在贵国,《清议报》馆尚开,此事是一大患 ,有碍中东大局。梁启超乃康党渠魁,尤为悖悍,其居心必欲中国大乱而后快。务望阁 下设法婉达政府设法令其速行远去,断不宜在日本境内。”[13](第9册P7755)张之洞把 梁启超视为叛逆,要求日方驱逐他,实属落井下石。此时,张、梁已反目成仇,梁撰写 的《戊戌政变记》等论著,对张之洞的称呼大多由原先的“吾师”或“南皮先生”改为 “张之洞之流”或直呼其名了。他说:“如李鸿章、张之洞之流,亦谓西法之当讲者, 仅在兵而已,仅在外交而已。”[1](专集之一《戊戌政变记》P143)又说:“荣禄、张 之洞所言兵,民贼之兵也,……民贼之兵足以亡国。”[1](专集之二《自由书》P39)其 论著中讽刺挖苦张之洞之词屡有所见,兹举《戊戌政变记》中一例:“德人据胶州,欧 洲列国分割支那之议纷起,有湖南某君谒张之洞诘之曰,列国果实行分割之事,则公将 何以自处乎?张默然良久曰,虽分割之后,亦当有小朝廷,吾终不失小朝廷之大臣也。 某君拂衣而去。”[1](专集之一《戊戌政变记》P69)尔后,梁又写了《呵旁观者文》, 认为张之洞是旁观者中的“为我派”,是“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是“朝梁夕晋 ,犹以五朝元老自夸”之人,他说:“张之洞自言瓜分之后,尚不失为小朝廷大臣,皆 此类也。”[1](文集之五《呵旁观者文》P71)上述话常被一些论者作为张之洞卖国和卑 鄙的论据。然深思之,此话不可轻信。翻检梁之文集,早在1897年9月德人强占胶州湾 之前,梁启超在《知耻学会叙》一文中,就曾不指名地斥责无耻的“老氏之徒”安于城 下之辱,“求为小朝廷以乞旦夕之命”[1](文集之二《知耻学会叙》P67),其时不可能 是指张之洞。为何在德人占胶州湾之后梁又描述了“湖南某君”的故事扣在张之洞的头 上呢?其实,张是封建的卫道士,绝非卖国者和旁观者。梁是借“湖南某君”之口来贬 斥张之洞,因为此话与张之洞戊戌至庚子年间的言行及其为官处世之道大相径庭。张之 洞其时反对两湖“独立”,他策划“东南互保”和参与庚子议和都是站在清廷一边同外 国列强讨价还价。[17]不过,此话倒可以作为张、梁间已反目成仇的证据。此时的梁启 超,新历政变亡命日本;张之洞为洗涮自己,不惜攻击康梁。梁在恩怨交加的情况下写 的《戊戌政变记》,往往受感情驱使或为政治宣传而言过其实,不是严肃的史学著作。 有研究者曾说,《戊戌政变记》“实为康梁应急的政治宣传品,而非纪实的信史”[18] 。笔者颇有同感。
梁启超对张之洞撰写的《劝学篇》也加以抨击,说它“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 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虽然,其于今者二三年中,则俨 然金科玉律,与四书六经争运矣”[1](专集之二《自由书》P7)。从而喧泄了自己的不 满。
平心而论,在戊戌政变的政治风云中,张、梁的心态都有不同程度的扭曲。1900年, 为慈禧议废立一事,梁启超忿怨交加再次上书张之洞说:“从前之交谊,既已尽绝,非 惟阁下绝启超,抑启超亦绝阁下也”,但是,二人同居中国,同戴一皇上,因此“私情 虽绝,而公义未绝”。接着,梁就张之洞不谏阻已亥建储一事,对张兴师问罪并加以嘲 讽,说“吾不知阁下曾有何面目以见天下人,更有何颜以自读光绪五年之奏议也。…… 即以阁下之无耻,但使清夜扪心自问,亦未必无天良发现之时”,由是他怀着对张之洞 “天良发现”的一丝希冀,用激将法劝张“亡羊补牢”,“率三楚子弟,堂堂正正清君 侧之恶,奉太后颐养耄年,辅皇上复行新政”。但他又料定张之洞为保自己的地位和身 家性命,不会接受他的建策。该文紧后分析了张之洞所处的地位,认为张必将落得“欲 归新党,而新党不屑有此败类;欲附贼党,而贼党亦不愿有此赘瘤,卒至进退失据,身 败名裂”的下场[1](文集之五《上鄂督张制军书》P63-66)。这篇洋洋二千余言痛快淋 漓戳中要害的上书,与其说是向张之洞建策,倒不如说是发泄对张的怨恨以及对张的挞 伐。张之洞终于无言以对。同年,梁启超还写了上粤督李鸿章书,虽然对李鸿章也有批 评,但仍尊称李为“大人”或“公”,并一再叙及对李的感激之情。梁启超对张、李的 态度,可谓泾渭分明。1901年,梁启超为李鸿章作传,将李鸿章同张之洞作比较,认为 “张不足以望李之肩背”,他说:“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 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好名故常趋巧利”,并说张之洞“虚骄狭 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之有常识有大量,尤相去霄壤也”[1](专集之三《中国四十 年来大事记》P81)。这一明显褒李贬张的评论,自不免有失偏颇。但若洞悉梁对李、张 二人的恩怨,其作上述评论也就不难理解了。
总之,张之洞和梁启超都是近代史上的过渡型人物,他们都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求变 ,梁启超的“流质多变”和张之洞的“善趋风势”,都是这种求变的反映。对时代的感 悟和求变心理,促成了张、梁的相知与交谊;但他们二人变法纲领不同,社会角色不同 ,学术门庭、文化观各异,而政治风云的变幻,又促使他们反目交恶。他们的交谊、交 恶是当时社会上两种势力既求同存异合作,又有矛盾斗争的缩影,它对维新运动的历史 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4-10-28
标签:梁启超论文; 张之洞论文; 康有为论文; 时务报论文; 南皮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科举制度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