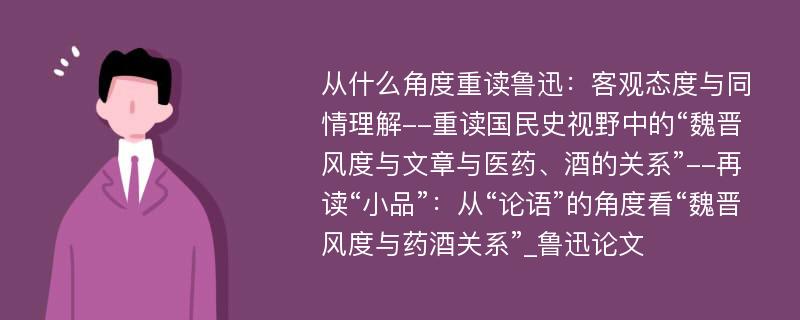
“重读鲁迅”笔谈——从什么角度评论鲁迅这个人——重读鲁迅:客观态度与同情理解——重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从国民史的视角看鲁迅——重读鲁迅:从对“鲁迅语录”的认识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笔谈论文,魏晋论文,风度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20[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0—114X(2006)04—0136—12
编者的话(特约主持人袁国兴教授):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巨人。鲁迅的创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
“经典的”比“普通的”涉及的问题更复杂、范围更广泛、历史意蕴更丰厚。鲁迅创作文本诞生伊始便好评如潮,但不可否认其出发点和目的并不尽相同,而且随着鲁迅创作经典化的实现进程,这一点也愈加突出。正因如此,对鲁迅的重新理解和再评价一直就没有停止过。鲁迅的“深刻”与他关注的问题、思维的方式、思考的方法以及表达的独特性有关,而这些在今天还远未过时。因此,在许多场合和许多领域,我们都仿佛和鲁迅不期而遇,他让我们汗颜,让我们警醒,让我们想得更多。
2006年,鲁迅已经离开人世70周年。“重读”鲁迅,这是我们对鲁迅先生的最好纪念。
从什么角度评论鲁迅这个人
刘纳
刘纳,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006
妙语连珠的钱钟书的一句玩笑话流传极广:吃鸡蛋何必见母鸡呢?这个比喻具有浓郁的现代阐释学意味和后现代色彩。
在漫长的年代里,中国人习惯于相信“文如其人”,而西方人也信奉“风格即人”。也就是说,20世纪之前,无论在中国、在西方,人们不怀疑作家/作品、人/文之间的一致性关系。但是在进入20世纪之后,这种一致性关系受到强大的理论挑战——从艾略特的非个人化创作原则、叶芝的面具理论、容格的集体无意识说与原型理论,直至罗兰·巴特和保罗·利科尔分别宣布“作者死了”。
然而,对于中国现代作家,我们当真能够把作品与它的作者分开吗?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不仅仅依仗文本——它们还依仗时代风云,也依仗作者的生命风度。比如对于鲁迅,我们很难做“作者之死”的设想,虽然他确实已在70年前死去。
陈独秀在鲁迅逝世一年多之后说:“世间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他概括自己“对于鲁迅之认识”:“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①
近年来,人们也常被告知:鲁迅“也是人”。很明显,说到鲁迅“也是人”,与说他的兄弟周作人“也是人”,那意味有所不同。说周作人“也是人”,论者通常挟带“理解之同情”,意在说明他虽做了汉奸也有可谅之因,也并非一无是处,而说鲁迅“也是人”,则在于披示人间的鲁迅并非一无“非”处。
从“人”的角度评论鲁迅有什么意义吗?“人”究竟有什么共性?食、色?恋生恶死、喜怒哀乐?这些不是哺乳动物共有的吗?鲁迅说:“倘以表现最普遍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通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通常所说的“人性”,不过是动物性罢了。与其他动物相比较,人其实是最缺少共性的类种。人可能拥有了不得的崇高和智慧,却也可能表现出不齿于动物的凶残与愚蠢、卑鄙与贪婪。
鲁迅是“人”,这当然确定无疑,而确定无疑的事未必特别值得重视。鲁迅至今能引发那么多人的探究兴趣,却并非因为他是“人”,并非因为他也须“营养,呼吸,运动,生殖”,也会算计怎么挣钱和怎么花钱,也会生气、骂人……而是因为他提供了其他许许多多“也是人”的人提供不出的东西,是因为他——他的著作和他的思想、他的性格和他的行为方式——是现代中国独异的存在。
在中国知识界广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一书的作者保罗·约翰逊说:“我特别看重这类证据:知识分子告诉人们该如何行事时,他的道德和判断力的可信程度。他们在生活中是如何管理自己的?他们对自己的家庭、朋友和同伴,表现出了几分忠诚?他们在处理性和金钱问题时,是否公正?”② 被这位作者称为考察“私人档案”的方法和角度已被推广开来,于是,我们看到了对鲁迅“做人”、“待人接物”和道德的尖锐质疑,比如有人以鲁迅与胡适做比较,问道:“假如他们还是两个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人的话,我们更愿意和哪一个人成为朋友?哪一个人更容易成为我们的朋友?你更愿意和哪一个人共事?”这位论者的结论是:“我想多数人是会选择胡适的。”③ 也许这结论是对的,从“做人方式”说,胡适确实可能比鲁迅好相处,比鲁迅要随和得多。然而,对于鲁迅,能用中国“多数人”心目中的“好人”尺度去衡量和评论吗?
鲁迅很不随和。他明确主张:“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会随和的,只有和事佬。”(《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他提倡韧性,其实他本人的性格更多地表现出刚性。刘劭《人物志》论人品性,以“中和”为最高,这在中国社会里是会得到“多数人”认可的。而鲁迅的性格与平和通达、端谨圆融无缘,他语出惊人又语出伤人,他不怕树敌实际上也在不断地树敌。他深思而并不慎行,世事洞明却并非人情练达。他激愤、焦躁,没有好心绪,“好心绪都在别人心里了”(《致曹聚仁》)。他为什么不能活得平和些?舒服些?快乐些?他不是名气不小挣钱也不少吗?
鲁迅与之做过朋友又翻了脸的林语堂从中国文化中寻找到获得现世幸福的秘诀,著名的《生活的艺术》讲述了一种“轻逸的,近乎愉快的哲学”,那便是“把积极的人生观念和消极的人生观念适度地配合起来”,在“尘世的徒然匆忙和完全逃避现实人生之间”产生出“和谐的人格”。鲁迅则对“生活的艺术”没有兴趣,他不会愿意以调整自己的精神性格来求得现实生活中的快乐与顺遂。鲁迅曾区分“生存”与“苟活”,他强调“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他注意到“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华盖集·北京通信》)在私人书信里,鲁迅屡屡留下愤懑的感慨:“我真觉得不是巧人,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致曹靖华》)他认为果戈理“是老实的,所以他会发狂。你看我们这里的聪明人罢,都吃得笑眯眯,白胖胖……”(《致萧军》)。鲁迅不是巧人、聪明人,假如他“会发狂”,也并不是令人惊愕的事。古人说,怒则伤肝,思则伤脾,忧则伤肺。鲁迅则把“怒”、“思”、“忧”占全了。
“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这是鲁迅对晋朝服药文人性格的概括,却与鲁迅生前死后受到的批评、攻击十分相像。鲁迅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做过演讲,而后整理为一篇极漂亮的文章。虽然鲁迅本人并不服药,酒量也有限,而他对“脾气都很大”的嵇康阮籍的理解和亲近感渗透在对魏晋风度的论述中。
据许广平回忆,鲁迅曾说自己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这话也被研究者引征并加以论述。但“士大夫”会是鲁迅的自我身份定位吗?——他从来认为自己非庙堂之器。“士大夫”和“名士”是古代中国文人的两途,鲁迅从传统文化中更多地承继了“名士”的流风遗绪。他本人,的是魏晋风度。
鲁迅一再拒绝“导师”和“领袖”的身份,他一再声明自己的“力不从心”:“‘指导青年’的话,那是报馆替我登的广告,其实呢,我自己尚且寻不着头路,怎么指导别人。”(《致李秉中》)“因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人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华盖集·北京通信》)
鲁迅的透彻使他从不敢拥有“将来一定好”的确信。对于“将来的黄金世界”始终存有疑心,却又要向着这“黄金世界”去努力,鲁迅的思考在格外犀利的同时又格外沉重。因而他“并不想劝青年得到危险,也不劝他人去做牺牲,说为社会死了名望好,高巍巍的镌起铜像来”。他说出了最深刻又最浅显的道理:“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力”(《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20世纪中国历史行进道路上洒满了牺牲者的鲜血,回顾历史,鲁迅当年对“牺牲”的态度愈益显其独异。也因此,鲁迅不可能成为“领袖”式的人物。
鲁迅深知自己不适合做革命领袖。他说:“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两地书·八》)在经历了1927年的风云变幻之后,他沉痛地写道:“我疑心吃苦的人们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于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实在很苦痛。但这也因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缘故。倘是革命巨子,看一点牺牲,是不算一回事的。”(《三闲集·通信》)
近年来,美国学者詹姆森的一句话经常被中国人引征:“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④ 詹姆森正是通过对鲁迅作品的分析得出这一结论的。而我们只能在这样一个维度上认可“政治知识分子”的说法:即身处大动荡时代的中国,鲁迅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不可能没有政治意识,不可能不表现出政治倾向,即使有人想远离政治,现实政治也不容你远离。但鲁迅不是政治家,他是政治意识强烈、政治倾向鲜明的文人。
至于陈独秀认为需要郑重其事地指认鲁迅“是个人”,是因为至陈独秀写《我对于鲁迅之认识》的时候,对于鲁迅这个人已经“世间毁誉过当”。而比“毁”和“誉”之间的反差之大更令人慨叹的,是毁者和誉者持论的角度往往与鲁迅本人的身份定位相错。
正如陈独秀在说鲁迅“是个人”时所强调的,鲁迅是“有文学天才的人”。他是文人,是文学家。他思想的犀利性、洞见性主要基于感性个人体验,而出之以文学性的、并非政治性也并非哲学性的表达。他的思想方式和语言方式都带有浓重的个人印记,他建立起了独异的意义世界和语言世界。
从“天才”文学家的角度,去评论、研究鲁迅这个人的独异性——我想,这是更适当的角度。
注释:
① 陈独秀:《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上海《宇宙风》10日刊第52期,1937年11月21日。
② 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页。
③ 谢泳:《两个不同的文人群体》,见一土编:《21世纪:鲁迅和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541页。
④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40页。
重读鲁迅:客观态度与同情理解
黄乔生,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北京 100034
2005年新版《鲁迅全集》的出版是鲁迅研究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其编纂注释方面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为重读鲁迅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以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鲁迅与左翼文学、鲁迅与东亚、鲁迅与胡适等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更分明显示着鲁迅研究已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鲁迅思想仍然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丰富资源。
重读鲁迅,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回到鲁迅,还原真实的鲁迅,努力理解鲁迅生平思想的历史文化背景。这就是所谓的客观态度,是正确理解鲁迅的基础;另一方面,还应该强调同情理解。最近若干年来关于鲁迅的争论很多,其中不乏否定鲁迅思想、质疑甚至污蔑鲁迅人格的言论,有些观点乍看起来似乎也本于事实,言之凿凿。对于鲁迅这样的文化巨人,后世产生争论,这本身是正常现象,每个历史人物,随时都要接受重新评价。但重新评价应该有两个基本标准,一是实事求是,二是同情理解。对待已不能张口说话和操笔为文的历史人物,信口雌黄并不费力,也较为安全,更有为翻案而翻案者,哗众取宠,追求独异,仿佛得了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批评过的那种旧时代做文章的“秘诀”:“翻天妙手,与众不同”。既然“翻天妙手”易于奏功,历史的老种子随时随地都会生根发芽,因此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我们提倡同情理解,提倡对历史人物持善意和温情的态度,正是基于反对这样的倾向。单单追求历史真实,斤斤计较细节,可能会以点带面、以偏概全,损害对鲁迅的整体把握。这一点,我在“鲁迅与藤野”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发言中已约略谈到过。我指出这样一种倾向:学者们努力于考证真实,是值得钦佩的,进而在考证的基础上指出鲁迅著作中的失误,也是正确的态度,但是,再进一步,因此推测鲁迅的写作动机,并从心理上猜测鲁迅、藤野等历史人物,生出更多的矛盾和是非,得出缺乏善意的结论,其结果是导致对鲁迅整个文章的否定。有关鲁迅留学日本及鲁迅与藤野关系的研究,本身并不复杂,最近几年却引发如此多的争论,过去似乎是定论的问题,产生了新的疑问。这说明:我们认为对研究对象认识得很充分了,开掘得很深了,其实不然。鲁迅的很多思想作品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时代在变化,一些矛盾消失了,新的矛盾又产生出来。
有些否定鲁迅的言论,之所以看起来言之有据,似乎也颇能动人,其原因,是言论者往往从现在的立场、现在的社会发展水平来分析历史人物,当然就不免看到鲁迅的落伍,鲁迅的片面和狭隘,鲁迅的固执等等。指出鲁迅的不足,自然也是好事,但在评价的时候,却不能丢弃同情理解,温情和善意。所谓的善意和同情理解,就是要客观地将鲁迅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具有标本价值的存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历程的创造者和见证人,就是把鲁迅看作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严肃认真思考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乃至世界的和谐,怀着真诚向善的心来批判丑恶现实、呼唤美好理想的文学家,而不是一个弄虚作假、耍弄刀笔的没有德行的文痞甚至流氓。
要而言之,更好地重读鲁迅的关键,是处理好客观态度和同情理解的矛盾,并做到二者的融合。理解鲁迅,要尽量减少主观色彩,从鲁迅作品的客观意义来理解和接受,努力做到冷静客观,并从鲁迅当时历史时期的角度设身处地分析事件和人物,从中体会鲁迅的感情和思想观念。
毋庸讳言,以往的鲁迅研究,有过多的主观色彩,受牵制于各种恩怨,党派的,民族的,国家的等等,有些争论最后远离了鲁迅文本,或者说把鲁迅当作一个工具,片面强调他的思想中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捧之者将鲁迅奉为绝对和永远正确,贬之者则斥之为一无是处。
例如,鲁迅对于革命的论述,最近在讨论鲁迅与左翼文学的时候常见论及。关于鲁迅思想的转变,关于他的左倾,关于他对政治斗争暴力革命的看法,过去我们认识不足。主要问题是单一和片面,总希望以一个概念就说得全面透彻。鲁迅在广州生活工作时间很短,但思想却有着剧烈的变化,经受了思路轰毁的痛苦,既印证了从中国历史观察得来的想法,又对革命有了切身的体验,从而形成自己的观念:革命很容易变成反革命。革命毁灭辛苦获得的成果,特别是文明积累,往往将好的坏的一起扔掉。而且革命者的动机不纯,素质低下,使革命事业背离了革命的初衷。由此到晚年,鲁迅对政治与文学关系及阶级斗争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
但鲁迅的思考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而且并没有得出绝对正确、永远适用的结论。他是敏锐的观察者,积极的探索者,但不是最终审判者。尽管他对革命运动怀着疑虑,但他仍然期望大变革,期望社会的进步,人性的改善。我们在解读鲁迅时,不能根据我们今天的需求片面地强调鲁迅的某些言论,不是把他当作导师和绝对正确的标尺,而当作帮助我们深入探索的思想资源。我们学习的是他的思维方式,他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为表达对社会不公平的强烈不满,就特别强调鲁迅金刚怒目的革命精神,或者为了追求和谐,就极力宣扬鲁迅对暴力斗争的批判,都是用鲁迅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既缺少客观性,更没有充分认识鲁迅思想的复杂性。
又如,最近一个时期,因为感到全球化的巨大压力,人们越来越注重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也因此出现了对鲁迅的激烈反传统态度的指责,或者转而大力弘扬鲁迅对传统文化的精研传承之功。这里存在的问题仍然是没有全面理解鲁迅,仍然是以偏概全,只不过以前以彼偏,现在则以此偏,性质相同。我们需要以历史的世界的眼光来看待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鲁迅一生做了不少高质量的学术工作,在继承中国文化传统方面做出了贡献,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也须注意,他的着眼点不是单一的中国文化传统,他的思考范围非常广泛。他将自编的《中国文学史讲义》改为《汉文学史纲要》,便是准确地定位了汉语言文学,其眼光之远大,在当时既具特识,今天看来也属罕见。正因为他具备了世界文学的修养,才能较为客观正确地看待中国文学传统。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对鲁迅翻译成就的评价。如果我们具备了鲁迅那样的世界文学的阔大眼光,就不会纠缠于一些枝节问题,就少了意气和怨愤,也就少了冷漠的批判和苛刻态度,而多了理解和会心。对鲁迅的翻译成果的研究和评价,过去做得很不够——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也不能不说是受了一些近乎全盘否定的判断的影响,有人提出“硬译”说,使普通读者以为鲁迅的翻译读起来拗口而乏味,没有价值。这种否定的意见的根源之一,就是只从一己的主观感受,只从当今语言发展的现状,而没有从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角度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题。中国文学(语言)在其漫长的演变过程中接受了很多外来成分,大大地丰富了自己。鲁迅的志愿是,不但要吸收外来进步思想,而且也要丰富汉语的表达功能。他的翻译文字数量,几乎等于创作,如此苦心经营,需要后来者的同情理解。我相信,如果怀着温情和善意,如果对他的翻译文字做全面深入的研究,是断然不会做出“硬译”甚至“生吞活剥的翻译”的评价的。
客观评价固然必要,同情理解更不可或缺。如果没有细致的阅读和深入的研究,如果没有对民族先贤的尊重和温情,是会把一位文化巨人的遗产束之高阁或者弃若敝屣的。如何将两种态度融合起来,是当前研究者的重大责任。
重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郑家健
郑家健,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州 350007
1927年9月间,鲁迅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所做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一篇重要的理论文献。它在探讨鲁迅的思想发展尤其是鲁迅与传统文化关系等方面有着独特的学术意义。关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研究,学术界已经形成三个相对明确的解读方向。一,人们由此探讨鲁迅思想、创作与魏晋文学的历史关系;二,由于这篇演讲发表在1927年9月间的广州这一特殊的历史时空体,加上鲁迅在后来致陈睿的书信(1928年12月30日)中也说过:“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这就促使后来的研究者不断地追索文本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这两个解读方向各自都有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面世。此外,还存在第三个解读方向,那就是把这篇演讲与《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学术论著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从中探讨鲁迅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在这方面,以王瑶先生的论述最为独到,他在《中古文学史论·重版题记》中说道:
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工作的方法论来看,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等著作以及关于计划写的中国文学史的章节拟目等,都具有堪称典范的意义,因为它比较完满地体现了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又是历史科学的性质和特点。……他能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史中找出普遍性的、可以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然后从这些现象的具体分析和阐述中来体现文学的发展规律,这是对文学史研究工作者具有方法论性质的启发意义的。①
王瑶先生在该书中承认自己研究中古文学史的思想和方法,是深深受到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的影响,他曾把鲁迅的这一文学史方法论概括为“典型现象法”②,即从纷繁复杂的文学史进程中选择可以反映文学史的历史特征的文学现象,然后,在具体的历史展开过程中,充分把这些现象同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相联系,同文人的生活和作品相联系③。比如,鲁迅把他拟写的六朝文学的一章定名为“酒、药、女、佛”,这四个字指的都是文学现象,关于“酒”与“药”,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已有精彩的论述。“女”与“佛”主要是用于描述弥漫于齐梁的宫体诗和崇尚佛教以及佛教翻译文学的流行④。
我认为,王瑶先生上述的阐述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的文学史研究方法论最精辟的概括。但是,这些结论是否已经穷尽了这一演讲所内含的全部方法论精髓呢?我认为,还远远不够。在此文中,还有两个十分独特的文学史研究方法论并未得到充分的探讨:即关键词研究法与心理分析法。所谓的心理分析法,用鲁迅此文中的话说,就是要“明于知人心”。他在文中先引述《庄子·田子方》中的一段话:“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正是这一独特的方法论所介入的分析视角,使得鲁迅对魏晋时期人物的精神和思想有着深刻的洞见。他以锐利无比的眼光看出隐藏在嵇康、阮籍等人内心深处的隐痛,看出他们表面上是礼教的破坏者,但内心“实在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鲁迅这一对嵇康、阮籍等人精神结构和人格结构的悖论的发现,不仅对探讨魏晋文学精神,而且对分析魏晋的自然论玄学都有着重要的学术启发⑤。黑格尔曾说:什么是智慧?智慧就是在别人认为矛盾已经钝化的地方能看出矛盾仍然尖锐地存在着。我认为,正是心理分析方法给予鲁迅独特的智慧方式,使他对历史以及历史上人物有着与别人不同的洞察力。比如,他在此文中对陶渊明的评价就别出心裁,他说:“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我认为,正是这种“明于知人心”的深刻的介入与分析视角,才可能使鲁迅的文学史研究能不断得出与旧说迥异的独到新见。
由于篇幅的原因,在这里,我着重谈一谈所谓的关键词研究方法。鲁迅在谈到汉末魏初的文学时,用了四个关键词: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当然,这四个关键词并非鲁迅首创,它来自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在《讲义》中,刘师培以按语的方式对所提到魏晋文学的“清峻”、“通脱”、“壮丽”等风格做了颇为精当的艺术分析,这是鲁迅进一步阐释的基础。但是,我认为,鲁迅对这四个关键词的阐释并非仅仅像他自己在这个演讲中所说的那样:“我的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所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详一点。”更重要的是,他把这四个关键词放在汉末魏初的历史情境之中,充分考察到当时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对这四个关键词内涵的形成所具有的深刻影响。以“清峻”为例,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风格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只有综合多方面的历史因素。汉末魏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动乱的年代,崇尚刑名之学、推行名法之治,是统治阶层的一个必然选择,所以,曹操在《以高柔为理曹椽令》中说:“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拔乱之政,以刑为先。”史籍多称“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鲁迅把汉末魏初文学的“清峻”特征的形成就是放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加以阐释,他说:“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方法是很严的,因为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与刘师培的阐释不同,在这里,关于“清峻”的解读,已不是单纯的审美判断,而是渗透了诸多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因素。不仅关于“清峻”的阐释是如此,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鲁迅对其他三个关键词的阐释都是如此,这种对历史语境关联性的敏感是鲁迅运用“关键词”研究方法的最大特征。
当然,从方法论的发展史来看,鲁迅虽然运用了关键词的研究方法,但这还不是一种方法论的自觉。作为人文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之一,“关键词”的研究方法直到近年来才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时间上,它最初是发生于上世纪7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中。“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在1976年出版了《关键词》一书,该书考察了131个彼此相关的“关键词”,在考察中,威廉斯发现每一个词都可能存在意义转变的历史、复杂性与不同用法,及创新、过时、限定、延伸、重复、转移等过程;而且,词义本身及其引申的意涵会随时代而有相当的不同与变化⑥。威廉斯说:“我称这些词为关键词,有两种相关的意涵:一方面,在某些情境及诠释里,它们是重要且相关的词。另一方面,在某些思想领域,它们是意义深长且具指示性的词。他们的某些用法与了解‘文化’、‘社会’(两个最普遍的词汇)的方法息息相关。”⑦
威廉斯在讨论关键词时,常常偏重于历史考察。比较而言,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鲁迅并非在考察他所运用“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等关键词的词义流变,但他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与威廉斯在《关键词》一文中所运用的方法有着内在的相似性,即他们都十分重视将关键词的内涵与历史语境串联在一起,重视建构关键词与各知识领域间的相互关系性⑧。比如,对“通脱”的理解,鲁迅在文中说道:汉末魏初文学崇尚通脱的原因,“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流’讲得太过分,便成了固执。”“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影响,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这可以说就是一篇简明扼要的汉末魏初思想流变史,以“通脱”为关键词,鲁迅精辟地分析了为什么汉末魏初的社会文化思想会发生“出儒入玄”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如何内在地影响了文学思想和风格的新变。——这就构成了以关键词“通脱”为中心环节的相互关联、相互质证的阐释循环。
我曾经说过:研究中的关键词就像夜空中的星星,正是这星光点点使黑暗的夜空变得绚丽多彩,变得深邃幽渺。一个关键词的准确选择,常常会使你在百思不解之中,豁然开朗。当然,在理论的推进过程中,关键词的外延和内涵会在一定限度内发生变异,这是思维的必然。我想,这种变异性也许就是为什么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比起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会给后人更多的文学史研究方法论启示。
注释:
①③④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重版题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② 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见《王瑶文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
⑤ 进一步研究可参阅余敦康:《魏晋玄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⑥⑦ 威廉斯:《关键词》,三联书店,2005年,第7~9页。
⑧ 刘建基:《译者导读》,见《关键词》,第5~6页。
从民国史的视角看鲁迅
秦弓
秦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732
进入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做了大量的还原工作。开始是本体还原,即把神化或者扭曲的鲁迅还原为本来的鲁迅,继而发现只有把鲁迅放回到他所生活的历史时空中去,才能准确地把握鲁迅的特征及其价值,于是就有了历史还原。历史还原的范围不可谓不广,如民主主义革命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近现代史、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但有一个重要的视角却屡被忽略,这就是民国史。乍看起来,民国史与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然而,当我们仅仅以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时,一些在民国史视角看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甚至完全被遮蔽掉。
民国作为一个历史形态,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鲁迅的后半生生活在民国的氛围里,自然不能不受其影响和施与影响。从民国史的视角看鲁迅,会发现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这里仅就面临民族危机时鲁迅的姿态来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民国期间,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中国始终面临着内部民族分裂、外部列强侵夺的危机。日本军国主义者1928年先是制造济南惨案,继而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很快占领东北地区,1932年发动“一·二八”事变,紧接着炮制伪满洲国。而后,日本又策划建立“蒙古国”,1936年5月伪“蒙古军政府”成立,由日本控制。与此同时,华北地区也遭受日本蚕食。对于这种局势,国民政府虽然多次抗议,并在长城沿线组织武力抵抗,但相对于日本的粗暴强硬来显得软弱无力。为此,民声鼎沸,文坛上多有反应。
鲁迅对这些问题基本上未予正面关注,对于济南惨案、尤其是“九·一八”事变所昭示的民族危机,锋芒主要是指向政府当局,抨击政府的软弱无能与围剿苏区、压制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攘外必先安内”行径。他在《答文艺新闻社问——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里认为:“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在这里,鲁迅认为中国的军阀是侵略者的“仆役”,而把日本侵占东北看作进攻苏联的开头,所以,鲁迅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里面,把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比附为当年成吉思汗后裔“西征”“斡罗斯”的第一步,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实,这并非鲁迅个人的姿态,而是整个左翼阵营的姿态。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左翼作家的反响远远不如民主主义作家与自由主义作家强烈。这种姿态,是建立在左翼立场与官方立场的对峙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国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协调一致上面。
左翼向来是自认为代表民众利益的,但是,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在知识分子对待民族、国家问题的态度上,左翼却并非具有绝对的代表性。“九一八”后,张恨水等通俗作家率先创作“国难小说”。老舍在《猫城记》里描述说,外务部部长在国难当头之际,只忙着给儿子娶媳妇,在街上唱大戏,敌军入境,政府除了空言抗议之外,最高的国策就是逃跑;与此同时,也讽刺了“大家夫斯基”、为牟取私利而聚集一起的“哄”以及对“马祖大仙”的偶像崇拜。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知识分子对新疆问题十分关注,一直强调来自苏联的威胁,主要意见分为两种:一种为派遣大员安抚论,一种为派遣军队弹压论。诗人孙毓堂没有直接参与论争,但他通过以汉代西征大宛为题材的长篇叙事诗《宝马》表现出自己乃至自由主义作家群体对民族与国家危机的严重关注。
鲁迅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完人,我们不应要求他对一系列事变明确表态,也不应苛求他永远正确,但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人文知识分子,一个作家,一个国民,应该怎样对待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却是不能不加以考量的。我们并不是简单地要寻找巨人的瑕疵,而是要对鲁迅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并且透过鲁迅这一个案,认识民国时期民间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认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是怎样发生纠葛的。
经典作家,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既可以从中发掘宝贵的精神源泉,用以慰藉我们的心灵,推进当代精神文明建设;同时,也借此作为一个观察历史的窗口,审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姿态与心理状态。鲁迅研究所要研究的不只是鲁迅,鲁迅研究的无限空间与巨大魅力也正在这里。
重读鲁迅:从对“鲁迅语录”的认识谈起
袁国兴
袁国兴,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006
当代中国人对鲁迅的了解和认识,主要通过阅读鲁迅创作的文本,自从鲁迅登上中国现代文坛,鲁迅形象就是被他自己所书写的。然而,书写和阅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鲁迅书写了自己,另一方面人们也在阅读中建构起了有关鲁迅的种种意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化领域,“鲁迅语录”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存在,当人们讨论和研究一些问题时,常常会想到或引证鲁迅“怎样说”,仿佛这样一来就增加了自己言说的分量和可信程度。可是当人们如此这般的时候,往往淡化了鲁迅是在什么场合下、针对什么问题、想要表达什么意向的具体分析。这可能是一切伟人、经典所常常遭遇的困境。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的先哲们极力倡导“得意忘言”的最高阅读境界。我们对鲁迅不可能得其意而忘其言,因为忘其言也往往难得其意。可是在我们熟读鲁迅时,多想一想鲁迅的“言”、“意”之间关系却是必要的。比如,鲁迅曾经在《华盖集·青年必读书》中说过,“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这只是鲁迅在特定条件下,为了强调看外国书的必要而发的言论,不能看作是鲁迅对中国书的全部态度。在“鲁迅的语录”中类似的话语还有很多,比如“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坟·论睁了眼看》),中国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呐喊·狂人日记》),梅兰芳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第三种人”(《花边文学·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等等。这些话的好处是一针见血,犀利而富有感染力,但它们都强调了事物的某一侧面,都与特定的语境和话语意图有关,同样不是鲁迅对中国人、中国历史、中国传统艺术的全部和一贯态度。以上话语的“言”、“意”之间关系都经过了“艺术”的处理,当我们研究鲁迅、认识鲁迅,追究鲁迅的思想、鲁迅的精神和鲁迅的真实话语意图时,对二者之间的差别不能不给予应有的注意。有意无意地把“鲁迅语录”与其复杂的情感倾向割裂开来理解的现象,目前还大量存在——字面意义探究得多,暗潜的意义关注得少,这是我们重读鲁迅,鲁迅常常需要重读的一个重要原因。
毋庸讳言,“鲁迅语录”的表意层面与鲁迅思想的深层关怀之间的关系需要认真辨析,除了一般的“言”、“意”不能完全通译的原因而外,也与鲁迅的话语方式和文化姿态有关。鲁迅主要是以一个文化斗士,一位不知疲倦的社会批评家身份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的,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历来人们没有太大的分歧。但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人们却有可能拉伸或缩减一些“鲁迅语录”的意蕴含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人们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比如社会革命者可以认为“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横眉冷对”“千夫所指”,是对社会反动势力的强硬反弹;可是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立场上审视,把鲁迅的言语看作是他自己心声的流露,是他生活境遇的一种文学反映,那么我们也可以把上述“鲁迅语录”视为是鲁迅对自己的私生活、自己的家庭温馨与一般社会对自己私生活的干预和挤压的一种回答。“鲁迅语录”是精辟的,但人们阅读“鲁迅语录”的方式有时显得迟滞。如果我们认定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是一位文化斗士,那么我们还必须承认,鲁迅是一个语言天才,是一个善于书写、精于表达的文人。他有思想家的特点,但比普通思想家更锐气;他有文学家的气质,但比一般文学家更睿智;他有革命者的勇气,但比许多革命者都更通达。他善于旁敲侧击、冷嘲热讽、借古喻今,言语表达极为丰富。我们在阅读鲁迅时,在何种意义上回归了鲁迅的言语本体?“死读”——就字、词、句的书面意义凝滞、呆板地阅读鲁迅不能完全读懂鲁迅;“空读”——脱离开鲁迅的喜怒哀乐个体经验来阅读鲁迅也难于洞悉真正的鲁迅。而有意无意让“鲁迅语录”空疏起来的危险,自从鲁迅作为文化斗士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当代大学生对鲁迅往往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现行的各种教科书中显现出来的对鲁迅的阅读态度有关。翻开我们的中学和大学教材,有关鲁迅的阅读文本选择大都强调他文章的思想性和战斗性一面;这是鲁迅的风貌,但并不是鲁迅风貌的全部,甚至也不是鲁迅称之为鲁迅的最核心部分。因为鲁迅思想的诱人之处,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上别人无法取代的地位,与鲁迅思想的复杂性、丰富性、及其特别的思想表达方式有关。与斗士的精神面貌相对应,鲁迅还有作为一个中国文化转型期普通知识分子的一般性情感。在鲁迅的杂文小品中,许多深刻的思想表达,都显示了非文学而不能的特点。比如《过客》、《狗的驳诘》、《立论》、《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小杂感》等等,它们都是“思想”的精品,更是文学的瑰宝。但这样一些作品却很少出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不大愿意以文学家的眼光去看待鲁迅,不论是鲁迅的生前还是身后,也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一直都是鲁迅遭遇误读、被人“浅读”的重要原因之一。鲁迅本来主要是站在文学家立场上出牌的,是一个善于用文学性语言表达自己情感的人,可是在相当的时期和在相当的范围内,人们又常常不全神贯注地用文学的尺度来衡量鲁迅的创作(这里主要是指对鲁迅杂文小品的态度),这样一来,使得鲁迅本来是文学性的作品和文学性的语言有时也被人赋予了过多的“语录”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反省和回归对象的本体,是鲁迅需要和能够被人不断重读的又一个原因。
在上述思考中我们感到,对鲁迅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类型的理解,自觉不自觉地制约和影响了人们对鲁迅的阅读。众所周知,鲁迅一生只写了两本薄薄的短篇小说集和一本短篇历史小说集,没有写过长篇小说,在人类进入“印刷文化时期”,小说成为主要的文学样式时①,怎样理解鲁迅对小说写作的态度,如何阐释中国现代最伟大作家的创作方式与流行样式的某种不协调呢?人们有意无意地淡化鲁迅的文学家立场,台湾名嘴李敖质疑鲁迅的文学创作成就,都与对此的认识有关。应该承认,鲁迅的文学意识,包括在这一文学意识中衍生的文学写作类型和写作方式,与我们当下的理解有所不同。在人类社会中,从来就不存在一种统称为文学的东西,文学是对在各种不同写作类型中涌现的某种共同倾向进行概括的一种综合性称谓。在“19世纪末以前,文学研究还不是一项独立的社会活动:人们同时研究古代的诗人和哲学、演说家——即各类作家”②。当文学被赋予“用文字书写的一种艺术样式”的意念以后,人们发现诗歌、戏剧、小说和散文最为典型。而这些写作类型无论中外都有过漫长的发展历程,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写作范型。在中国,虽然小说、戏剧也有可观的成就,可是中国的小说原本指的是文人“小品”、“道听途说”的奇闻逸事以及在“讲说”“市场”上发展起来的“长篇故事”,这与西方主要缘自于史诗传统的“虚构叙事”类小说文体有所不同。既不同又相近,一方面人们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同一个东西,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在各自的理解中遗留和打上一些差别的痕迹,尤其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鲁迅的小说和文学意念与中国古代小说文学意念有一定渊源关系。他的小说带有文人小品的色彩,因此他没有写“长篇故事”;他的散文小品又有“小说”的意蕴,因此到晚年他专心致志地写“杂文”。我们可以把他小说集《呐喊》中的《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兔和猫》、《鸭的喜剧》等,与我们前文探讨中曾经提到的鲁迅杂文小品中另一类更有文学性的作品,比如《过客》、《狗的驳诘》、《立论》、《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等做一对比,便会感到,二者的区别远没有达到人们意念中两种文体应该有的差别那样大。对于这一点鲁迅自己也是承认的,他在《呐喊·自序》中说,钱玄同找他给《新青年》写稿,促使他“一发而不可收”,写了“十余篇”“小说模样的文章”(《呐喊·自序》)。他把《呐喊》所收的作品看作是“小说模样的文章”,绝不是自谦,而是一种文体样式的自觉。从来没人否认鲁迅“小说模样的文章”是文学作品,那么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所指,在鲁迅的心目中也应该包括“小品”、“杂文”类的创作。在鲁迅的文学意识中,杂文和小品相近,小品和小说也不泾渭分明,这也可以在鲁迅的“语录”中找到佐证。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一文中,他对自己“创作怎样才会好”的经验总结之一是:“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写成Sketch,决不将Sketch材料拉成小说。”③ 可见二者的文体规范在鲁迅心目中是最为接近的,创作方式上也应该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鲁迅的前期创作主要写小说和小品,后期创作主要写小品和杂文,反映的文学意识是相通的。可以这样说,鲁迅的创作方式和创作成就,是在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孕育出来的文学创作绝响,他的小品文学意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宝贵遗产,前人没有他那样的文学自觉,后人缺少他那样的文学才能,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文学家的鲁迅为什么一生钟情于小品杂文。对鲁迅文学家气质的认定也需要对鲁迅的文学意识进行必要梳理,我们重读鲁迅、鲁迅需要重读,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注释:
① 参见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30页。
② 乔纳森·卡勒:《文学性》,见佛克玛编:《问题与观点》,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0页。
标签:鲁迅论文; 文学论文;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汉文学史纲要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论文; 关键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