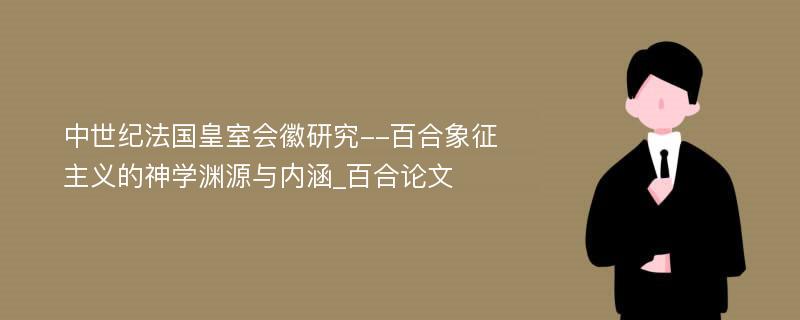
中世纪法兰西王室徽章研究——百合花象征主义的神学渊源及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兰西论文,神学论文,王室论文,百合花论文,徽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文化相对落后或人们的交流主要以口耳相传为基础的社会里,象征符号往往具有颇为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信息传输功能。对于诸多不可名状的抽象事物,人们通常将之转化为象征性实体并加以尊崇膜拜,似乎只要赋予它们以某种可以感知的形式,其神秘感便可把握了。中世纪的法国亦莫能外,在这里,滋养象征主义(注:这里所说的“象征主义”与19世纪后期在法国出现的“象征主义”文学艺术流派有着原则区别。前者是将抽象的事物具体化,使之可知可测;而后者在相当程度上则是将具体的事物抽象化,使之神秘莫测。)的土壤极为丰厚,其中宗教领域的情形自不必说(注:参见约翰·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159-185、209-222页。),即便在世俗生活中,有关现实世界的许多观念也都有着各自的象征载体;在诸如此类的象征符号中,从感召力度、出现频率以及人们的熟悉程度看,具有典型意义的当数王室的百合花徽章(注:徽章,西欧历史上通常称之为“纹章”(法文héraldique,英文heraldry或coat of arms),由一组特殊图案构成,一般绘于盾形物或能代表吉祥的其他形状的牌物之上;在古代西欧各国中,显贵家族、市政会议以及大学等通常将之作为自身的特殊标志。本文在涉及“纹章”这一语汇时,一般依从汉语的表达习惯,称之为“徽章”。)。那么,王室百合(注:据考证,中世纪法国王室徽章上的图案实际上是三叶草或香根鸢尾花,但它们与百合花极为相像,因此中世纪的法国人一般认为二者是可以互换的,将王室徽章上的图案直接视为百合花并无不妥。因而,在中世纪法国,不论是王室本身,还是普通民众,都毫无例外地将百合花看做为王室徽章。参见Collete Beaune,The Birth of an Ideology,California,1991,p.197。)是何时出现于法国政治生活之中的?这一象征符号最为根本的渊源是什么?其具体内涵如何?它与中世纪中后期法国王权的强化有何关系?关于这些问题,在我国学术界尚未见有系统的分析;西方学术界对之虽有一定的研究,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却是见仁见智,观点纷呈。由此看来,对法兰西王室百合作一深入的研究还是很有必要的,它不仅可以弥补我国的法国史研究领域中的某些空白,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我们开辟了一个研究封建时代法国社会政治史的新视角。
一 王室百合的发轫历程以及有关王室百合起源问题的争论
在探讨法兰西王室百合的历史之前,有必要对徽章(纹章)在中世纪西欧的一般性起源略为说明。从源头上看,徽章的出现首先是军事装备变革的结果。11-12世纪,西欧骑士的头盔和铠甲由原来的半裸型向封闭型转变,骑士的脸部与躯体几乎被完全遮住;其安全系数虽有提高,但骑士的身份或所属阵营却不易判别。因此在征战时,骑士便在各自的盾牌上涂上各种特殊标志以做区分,徽章的雏形由此肇端(注:中世纪西欧各地的徽章多取盾牌之形,其基本源流即在于此。参见乔治·泰特《十字军东征:以耶路撒冷之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70页。)。在其发展初期,这种特殊的标志基本上只是从战人员的识别符号,但是到了12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各种识别符号特有的象征功能逐渐得到世人心理上的认同,它们开始从军事领域走进日常生活,并进而与采邑、份地乃至家族联系起来,最终成为一种不可侵犯的世袭符号,此即徽章。
作为众多徽章中的一种,法兰西王室百合可以考证的历史亦始于12世纪,而且其发端到完善也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将这一演化流程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萌芽时期:12世纪至13世纪初。路易六世统治(1108-1137年)时,在王室的德罗(Dreux)铸币场铸造的小枚银币上,出现了十字符号,并饰有百合花图案。路易七世当政(1137-1180年)时,在王室铸造的银币上,百合花被置于中心位置,其四周配有一组颂扬基督的文字,即“基督凯旋,基督统治,基督指挥”。腓力二世(1180-1223年)时,百合花图案不再局限于王室铸币上,国王印玺的印顶上面亦开始出现百合花,从事十字军征讨的法国骑士军队的军旗以及受王室庇护的修道院的院旗也都装点着百合花。路易八世(1223-1226年)时的情形又有一些新的变化,国王印玺的印顶上面刻有盾形徽章,而徽章的中心图案便是百合花;另外,路易八世在其加冕典礼上所穿的王袍上亦点缀着百合花图案(注:详见G.Saffroy,Bibliographie historique et nobiliaire,Paris,1964,Vol.I,pp.102-105,547-549;Braun von Stumm,"L'origine de la fleur de lys des rois de France du point de vue numismatique",in Revue Numismatique,Vol.13,1951,p.43-58。)。纵观一个世纪左右的历史进程,作为一种特殊的徽章,百合花在此时期呈现出一系列草创性特征,如:图案尚无确定的形式,钱币、印玺及旗帜上的百合图形多有不同;在不同的图案中,百合花的数目亦有很大差异,如单朵型、双朵型和多朵型;而且,这一时期的百合花徽章只是国王本人的象征符号,尚未上升为家族性的徽章,因而对王室支系(或旁系)并无直接的约束力。
初步发展时期:13世纪(主要是路易九世统治时期,1226-1270年)。路易九世是中世纪法国颇有作为的一位君主,在其主政期间,王室领地进一步扩大,王室的权威不断加强。与此相伴,百合花徽章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尽管说此时的百合花仍属国王个人的徽章,但它在其他方面的变化却是较为显著的,其主要表现是:首先,就单朵而言,百合花开始具有确定的形式,其基本构造如下:三枚花瓣,没有雌蕊,底部为一个三枚萼片基座,图案中部(即花瓣与基座之间)有一细长横杆,百合花即附着于横杆上。这种图案不仅具有简洁易识、便于制作之特点,而且还可能暗示了数字“三”的神奇威力(路易九世是以笃信宗教而著称的君主“圣徒”)(注:Guillaume de Nangis,Chronique,Vol.I,Paris,1843,p.182.)。其次,百合花图案的传播范围比前一时期有较大扩展。1238年以后,王室管辖下的法院系统普遍接受了百合花图案,不论是初级的巴伊法庭(bailliages),还是高级的君主法院,其印章上均刻有百合标志;在法国南部,王家公证人在1261年以后开始使用带有百合花图案的印章;附属于王室领地的或领有国王“特许状”的城市亦在其印章上加上了百合花。可以说,百合花图案在多种场合的频繁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王权不断强化的这一历史事实。另外,在路易九世时期,饰有三朵百合的徽章亦时有出现,虽然说其地位尚未确定,但这种一徽三花的形式却为后来的法国王室所采用,其先导作用是不宜低估的(注:参见M.Prinet,"Les variations du nombre des fleurs de lys dans les armes de France",in Bulletin Monumental,Vol.75,1911,pp.469-488。)。
进一步发展时期:14世纪至15世纪中叶。从腓力四世(1285-1314年)开始,法国进入等级君主制时期,王室的权威和影响范围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扩大,百合花的地位亦随之提高。首先,百合花由国王个人的象征物演变为家族性徽章。从腓力四世统治中期开始,不论是王室直系,还是王室支系,凡是具有法兰西王室血统的所有成员均须佩戴百合花徽章(王室公主亦可佩戴百合,但却不能将之传给自己的子女(注:由此可以引申出女子不得继承王位这一基本原则。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见陈文海《〈撒利克法典〉在法国中世纪后期的复兴和演化》,《历史研究》1998年6期。));这一原则的施行具有双重效用,一方面,它使得百合花成为一个特殊群体的“出身权”的标志(即“佩戴百合徽章=具有王室血统”),另一方面,它也使得百合花成为“归顺”、“服从”的标志(不论是直系成员还是旁系成员,也不论是身处巴黎还是远居外省,只要佩戴百合花徽章,就表明他有义务接受法兰西国王的最高领导),这对于加强王室家族的凝聚力应当说不无作用(注:参见R.Chabanne,Le Régime juridique des armoires,Lyon,1954,p.297。);为了使徽章规范化,1376年,查理五世(1364-1380年)更明确颁令,规定饰有三朵百合的盾形徽章(百合为金黄色,徽章的衬底为天蓝色)为法兰西王室徽章,王室的象征符号由此变得更为鲜明。其次,百合花图案的流传范围更趋广泛。14世纪时,度量衡器具、王室建筑、珠宝、布匹以及许多教俗团体的徽章上,均出现了百合花的图案;由此可以看出,百合花已经成为法国王室对全国施行统治的普遍性标志,王权的触角已经遍及各个领域,大有“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意味。
完善时期:15世纪中叶以后。百年战争结束以后,法国的政体逐渐由等级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过渡,王权的神圣色彩愈益浓重,国王与王室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亦因此变得更为森严。在此情形下,国王与王室其他成员佩戴同样的三朵型百合徽章显然已不合时宜。因此,在查理八世(1483-1498年)时,法国王室明确规定:作为法国王室的标志,三朵型百合徽章居于至尚的地位;在一国之中,只有国王一人享有与之相仿的尊威,因此也只有国王才能有资格佩戴三朵型百合徽章,而王室普通成员只能佩戴饰有两朵或一朵百合花的徽章图案。因此,从15世纪晚期开始,饰有三朵金黄色百合花的天蓝色徽章成为法兰西国王的专有标志,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18世纪末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19世纪上半叶的“复辟王朝”时期,三朵型百合一度死灰复燃)(注:参见R.Mathieu,Le Système héraldique francais,Paris,1946,pp.1-11。)。
如果说法国王室百合徽章的出现时间和演变轨迹尚属有稽可循的话,这一象征符号的渊源问题则显得扑朔迷离,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赋之以殊然不同的答案。早在绝对君主制时期,即已有人对王室百合进行追本溯源。17-18世纪时,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王室百合图案是由古代兵器(长矛、梭标或战斧)演变而来的;1653年,在法兰克人早期首领希尔德里克一世(约457-481年,克洛维之父)的墓穴中出土了蜜蜂状的宝石饰物,于是又有人断称,宝石饰物上的图案最终转化为王室百合。19-20世纪时,有关王室百合起源问题的解释依旧色彩斑斓。有人认为百合花图案源于古代罗马神话中海神尼普顿(Neptune)的武器三叉戟;有人认为它是古代罗马“束棒”的衍生物;另有一些人则认为其源头是古代亚述、克里特或埃及的某种形象;还有人从抽象的词源学角度对之进行考释,认为“百合花(fleur-de-lys)”的本意是“充盈的光芒”,而后者恰恰又是“圣灵”的另一称谓,因此“百合花”意即“圣灵”(注:详见F.Oppenheimer,Frankish Themes and Problems,London,1952,pp.171-235。)。
从上述可见,对法兰西王室百合起源问题的各种解释大都具有求古求远的倾向,它们或将之置于悠久的上古时代,或将之置于遥远的异国他乡;其探索精神固然可贵,但其具体的诠释却难以自圆其说,它们基本上只是根据某些表象而作的主观上的推理或猜测;这些解释既没有(或许根本不可能)为我们提供其“象征原型”向王室百合转化的演变图,也无法圆满说明由“原型”脱胎而来的王室百合在中世纪法国所具有的象征内涵。至于说从词源学角度将百合花等同于“圣灵”的解释也同样不能令人信服,近年来已有学者对之提出质疑和批判(注:ColleteBeaune,The Birth of an Ideology,pp.203-204.)。笔者认为,要想准确理解法兰西王室百合的起源问题,比较稳妥可靠的途径是将之放在中世纪法国特有的精神文化氛围中进行考察,而没有必要在上古与中世纪之间作某些勉为其难的牵线搭桥(当然不是一概排除中世纪对上古的继承)。从有关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中世纪的法国,象征主义充斥着每一个领域,而每一种象征几乎均是孕育于神学摇篮之中;中世纪的法兰西人又自称是世界上最为虔信基督教的民族,而且,法国国王也被视为最为虔诚的基督徒君主(注:参见约翰·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第12-15章;陈文海:《民族形象·民族空间·民族情感——中世纪中后期法兰西民族观念形成轨迹探析》,《世界民族》1998年4期。);由此可以推断,既然法兰西民族和法兰西国王享有“最信基督”的君主之誉,那么,王室的标志(当时也是国家的标志)与基督教神学应当不无关联。如果沿着这一思路去分析王室百合的起源,问题或许可以迎刃而解,王室百合的象征内涵也将不再令人难以捉摸。
二 王室百合的神学溯源
从源流角度来说,在基督教神学体系中,百合花形象起初并无什么神秘色彩,但经过教会神学家经年累世的演绎与修正,百合花逐渐失去其原有的朴素性特征,并由此进入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蜕变历程,它首先成为耶稣基督的象征,继之又变为圣母玛丽亚的标志;而自中世纪中期起,法国王室对圣母的尊崇日益浓烈(随处可见的圣母院或圣母教堂是其最为直接的表征),在此背景下,圣母及其百合花标志也就自然而然地与法国王室产生了难以割舍的联系。关于这一转变过程,我们可以结合有关材料对之做一具体剖析。
第一,《圣经》中有关百合花的描述。在古代世界,百合花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花卉;从自然属性来说,它具有生长繁盛、色泽鲜艳和芳香沁人的特点。基督教经典《圣经》对此多有述及,如“我是沙仑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没药汁”;“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我必像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等等(注:经文依据中国基督教协会翻译出版的《圣经》(南京,1996年):《雅歌》第2章,1、2、16;第4章,5;第5章,13;第7章,2。《何西阿书》第14章,5。《路加福音》第12章,27。)。由此可以看出,在《圣经》里,百合花既无神秘面纱,也无神圣色彩,它只是作为自然界中的一种自然物而被常常用来喻拟美好的事物或美妙的意境(如女子的美貌、少女的乳峰、女子的腰肢以及美男子的仪容等等),这便是百合花在基督教神学体系中的本来面目。
第二,百合花神圣化的第一次变奏。既然《圣经》中将百合花视为“美好”和“美妙”的代名词,这就为善于附会的中世纪神学家提供了演绎的空间。从公元4世纪起,教父们开始赋予百合花以神学象征意义,并将之与灵魂的美丽联系起来,进而成为耶稣基督的象征。圣安布鲁斯(Saint Ambrose,340-395年)认为,基督是“山谷中的百合,是贞女的王冠”。在伪麦里托(Pseudo-Melito,生卒时间不详)看来,百合花既是救世主耶稣,又是那些浸透着天堂光芒的圣徒。生活于8世纪的本笃派僧侣、副主祭保罗(Paul the Deacon)亦将耶稣基督视为一株百合,花的外表呈白色,象征着基督的纯洁无瑕;其内部则为金黄色,这是基督权力的标志;他认为,百合花芳香甜美,其花茎曲直有序,优雅别致地向世人指明通往天国上帝的路径;而且,百合花具有与众不同之处,它鹤立于丛生的荆棘之中,其醒目的地位让人们的视线无法回避(注:Collete Beaune,The Birth of an Ideology,p.205.)。在基督教神学家们的笔下,百合花的形象已远远超越了《圣经》赋予它们的原始特征,其自然属性已经沦为其神秘性的一个底衬。到10世纪时,百合花已经成为某些特定价值观念(如信仰、公正、纯洁等)的象征,而这些价值观念则是通往“天堂至福”的必要前提。
第三,百合花神圣化的第二次变奏。11-12世纪,百合花的神学象征开始由基督转向圣母玛丽亚,圣母在法兰西基督教神学体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在此我们有必要追溯一下圣母的“发迹”历程。在中世纪早期,玛丽亚并无特别显赫之处,尽管她由圣灵感孕而生耶稣,但她依旧是木匠约瑟(Joseph)之妻,一位没有神性的凡人妇女。从8-9世纪起,玛丽亚的地位趋于上升,她开始以尘世教会的“预兆”之形象而出现在基督徒面前(即有了玛丽亚,才有了教会),同时,玛丽亚的尊号亦不断涌现,如“海洋之星”、“天国女王”以及“通往救赎的阶梯”等等。不过,只是到了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玛丽亚才与百合花联系在一起。当时的著名学者、夏尔特尔主教富尔柏(Ful-bert de Chartres,960?-1028年)认为,玛丽亚不仅具有一切常规的美德,而且她还拥有一种超常规的美德,即“贞洁”,因而她理应成为荆棘丛中的百合,成为基督徒追求救赎的指路明灯。11世纪末,鲁柏·德·都茨(Rubert deDeutz)更进一步,他开始将玛丽亚与教会等同起来,在他看来,二者具有许多共同的本质特征,如贞洁纯真、普施恩泽等,而且二者都是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主教(注:详见H.Coathalem,Le Parallélisme entrela sainte Vierge et L'Eglise jusqu'à la fin du XIIe siècle,Roma,1974。)。自此以后,玛丽亚逐渐成为救赎体系中的主角,法国人对玛丽亚的崇拜之情亦日渐高涨(注:公元1000年前后宗教情感的转变并非是法国独有的现象,在意大利、德意志等地也都有所表现,不过却以法国为甚,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方面,教会宣扬的公元1000年“末日审判”的神话破产以后,基督教世界的“人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微弱的复苏,人们普遍觉得基督的“神性”距离他们的现实生活过于遥远,因而人们试图在基督教神学体系中寻求一种较为贴近现实的精神寄托,具有慈母形象的圣母玛丽亚便是其最佳人选。另一方面,就法国而言,世俗生活中盛行着所谓的“骑士道德”,它所提倡的敬重妇女之行为准则(且不论其是实是虚)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中世纪法国人对圣母玛丽亚的崇拜。)。
12世纪时,法国宗教领域中对玛丽亚及其百合标志的阐述更趋系统和具体。在西多会(注:西多会是12世纪法国影响最大的修院势力,其详细情况可参阅C.沃伦·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192-194页。)(Cistercian)下属的各修道院,包括修院建筑本身在内的所有物品均被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圣母玛丽亚;西多会的领袖人物、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鼓动者圣伯尔纳(Saint Bernard,1091-1153年)及其信徒大力传播玛丽亚的“圣母—百合”形象,玛丽亚由此成为尘世一切人等的代言人和一位普世之母,而她的百合形象是其美丽绝伦的象征,百合的纯洁色彩则是其美德所折射出来的光辉(注:详见P.Bernard,Saint Bernard et Notre Dame,Paris,1953。)。12世纪法国著名的神学家和历史学家基伯·德·诺让(Guibert de Nogent,1053-1124年)对“圣母百合”神秘性和神奇性的渲染更具神韵,他认为,这种百合没有花茎,而且,即使其根子被截去,它也能照常开花,其情形就像玛丽亚本人那样,即使没有男性的介入,也能够怀孕生子。玛丽亚的“圣母—百合”形象并未囿限于神学著作之中。在12世纪出现的圣母塑像中,其披风上开始饰有百合花图案,主教团徽章以及以玛丽亚之名铸造的教会铸币上也开始出现类似图案。在兰斯大主教热尔韦(Gervais)下令铸造的教会钱币上,有一十字符号,在由十字隔出的四个扇形面上均饰有一朵百合花;其后继者又在铸币上加上了“圣玛丽亚”(Sancta Maria)字样。兰斯铸币的信誉较高,在北部法国曾一度广为流通。不久以后,当法王路易六世决定铸造王室货币时,其模型便直接采自兰斯铸币(只是其色彩稍有不同)(注:F.Oppenheimer,FrankishThemes and Problems,pp.203-204,218-219.)。王室百合与圣母百合之间的关联由此可见一斑。
第四,法国王室对圣母玛丽亚的崇拜与王室百合的茁壮成长。在浓烈的宗教氛围与法国特有的骑士道德精神的综合推动下,法国王室对圣母玛丽亚显示出西欧其他各国王室所不可比拟的炽热情怀。例如,在建筑方面,自12世纪前期的路易六世开始,法国王室即不断兴建圣母教堂,并将王室领地内已有的教堂全部置于圣母之名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王领之外的其他地区,许多教堂则是以某些“圣徒”命名的),甚至连供王室成员做圣事、行圣礼的宫廷小教堂也被奉献给了圣母,而且王室还向众多的圣母院或圣母教堂赠予大量的土地及诸多特权(名义上是献给圣母玛丽亚)。在艺术风格方面,哥特艺术是位于法兰西岛的王室精心培育出来的一种美学风格,它所创造的一系列光彩照人的圣母形象(如头戴王冠的圣母、耶西树圣母以及领报圣母等等)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王室精神旨归的体现。不仅如此,甚至连法国王室的某些特殊性事件亦被蒙上了圣母的光环,据称,腓力二世、路易八世以及路易九世等人的降临人世均是圣母玛丽亚施恩的结果,这时的圣母已经成为具有神奇功能的“送子观音”。对于圣母的这些善举,国王们当然会举行朝圣以示谢恩,例如,路易七世(腓力二世之父)因喜得贵子而于1140年去隆蓬圣母院(Notre-Dame-de-Longpont)朝圣,1145年又相继去了卜伊圣母院(Notre-Dame-du-Puy)和里埃斯圣母院(Notre-Dame-du-Liesse),而且,在其要求之下,他死后还被安葬于自己生前所建的巴波圣母院(Notre-Dame-de-Barbeaux)。另外,法国王室还宣称,每当国王处于危难之际,圣母玛丽亚总会鼎力相助并使之化险为夷;如果国王率军出征,圣母也会适时伸出援助之手以使国王终能克敌制胜。13世纪初,腓力二世在与英国国王争夺大陆领土的军事争斗中曾数度逢凶化吉;为了感怀圣母的恩典,在每次“得救”之后,腓力二世都要在奇迹发生地修建圣母教堂或竖立圣母塑像以为纪念;后来,他还在首都巴黎的城墙上竖起一尊圣母雕像,一方面是为了表达对圣母的崇拜之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永远沐浴着圣母的恩泽(注:详见A.Latreille,J.Palanque,E.Delaruelle,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en France,Paris,1963,pp.14-16。)。
通过上述各种途径,法国王室成功地利用并传播了对圣母玛丽亚的信仰,并最终使得圣母崇拜成为法国王室不能忘怀的“宫廷习俗”,甚至可以说,玛丽亚已经成为法国王室中一位永不消亡的“神圣母亲”。在此背景下,圣母百合所具有的各种崇高品德(如纯洁无瑕、公正无私、信仰坚定、拯民水火、完美无缺等)也就顺理成章地延及法国王室,国王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尘世上带领臣民脱离苦海,走向彼岸的“荆棘丛中的百合”。关于法国王室百合与圣母玛丽亚之间的这种关联,中世纪后期的神学家以及许多虔信基督教的学者多有论述。14世纪后期,法国作家巴泰莱米·德·格兰维尔(Barthélemy de Glanville)在《伟大的万物之主》一书中写道:“百合花被运到教堂并被置于上帝和圣母面前。……万能的上帝将之赠予所有基督徒国王中最为高贵者——法兰西国王”(注:Barthélemy de Glanville,Le grand propriétaire de toutes choses,Paris,1518,pp.94,138.此书原为拉丁文,后由Jehan Corbechon译为法文。)。如果说格兰维尔对二者关系的表述尚显暧昧,那么,15世纪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15世纪上半叶,著名贵族、历史学家罗伯·布隆代尔(Robert Blondel,生于1380-1400年间?卒于1461年以后)曾写下一段流传颇广的话语:“在一个久远的年代,圣母选择了这片美妙的土地,……在这片蔚蓝色的土地上,栽下了三株金黄色的百合”(注:R.Blondel,Oeuvres complètes,Rouen,1892,Vol.I,pp.88,123.)。当法国最终在百年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后,百合花的神秘色彩更趋浓重。15世纪末,作家奥利维埃·马亚尔(Olivier Maillard)曾不无自豪地将圣母百合与王室百合并作一处而加以颂扬,他认为:尽管魔鬼撒旦(指英国人)向百合发起猖狂进攻,但在上帝的帮助之下,百合依然盛开如故;而且,百合具有神圣的慈悲心肠,对一切善者均予以护卫,它既是“万福”的圣母玛丽亚,同时也是终将获享天国至福的仁慈的法兰西国王。大约与此同时,旅居法国的意大利文人吉奥瓦尼·维瓦尔迪(Giovanni Vivaldi)对王室百合的圣母色彩更是着意铺陈,他曾写道:法兰西国王在自己的徽章上饰有百合花,而此花恰恰又是最为纯洁的圣母之象征;由此可以证明,国王热爱并尊敬圣母,而且在圣母的恩典之下,国王成为臣民得救的可靠保证(注:Collete Beaune,The Birth of an Ideology,p.209.)。从以上所述的历史演变轨迹中可以看出,到15世纪后期(亦即绝对君主制初步发展时期),圣母百合与王室百合之间已经形成一种辩证的互动关系,对圣母玛丽亚的狂热崇拜带来了王室百合的欣欣向荣;同时,对百合花的顶礼膜拜又进一步强化了圣母玛丽亚与法兰西王国(尤其是王室和国王)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法国王室百合的这种神学渊源以及随之而带有的神圣色彩既是法国中世纪文化氛围的产物,也是法国王室及其御用文人和御用神学家苦心经营的结果。
三 王室百合的象征内涵
在中世纪法国王室百合的成长历程中,基督教神学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王室百合这一构图简单的象征符号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蒙上神秘且神圣的色彩并为社会所普遍接受,与它所具备的丰富的神学底蕴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强烈的宗教象征意义有着颇为密切的关联。但需要明确的是,作为国王、王室乃至整个法兰西王国这一系列政治实体的标志,百合花的象征内涵并不可能仅仅局限于纯粹的神学范围之内;实际上,神学只是王室百合借以发展壮大的一顶华盖,随着王权的逐步强化,百合花的象征内涵势必要在原有的神学基础之上演绎出某些特殊内容,以利于法国王室进行有效的社会政治统治。可以说,王室百合是神学与政治的混合体,其中神学是依托,政治为根本。
王室百合的象征内涵并非是一个静态的范畴,不同时期的人们曾对之做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关于这一问题,可分为几个阶段进行考察。第一,13世纪后期:神学色彩占据统治地位。尽管说王室百合在12世纪已初具雏形,但对其象征内涵作较为系统的诠释却迟至13世纪后期(即法国由割据君主制向等级君主制过渡时期)。受王室百合的神学渊源以及当时浓厚的宗教氛围之影响,时人几乎不约而同地将王室百合的象征内涵与基督徒的德行联系在一起,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在腓力四世时曾任文卷保管官(custos cartarum)和王家正式史官的吉约姆·德·朗伊(Guillaume de Nangis)所作的解释。他认为,王室百合的三枚花瓣分别代表信仰、智慧和骑士制度,它们是法兰西有别于其他国度的特色之所在,这是因为法兰西人对基督教的信仰最为虔诚,法兰西人的智慧远在他人之上,法兰西的骑士制度亦是基督教世界中最为完美的;三枚花瓣的排列顺序是:信仰之瓣位于中心,智慧之瓣位于右边(右首的地位比左首略高一筹),骑士制度之瓣位于左边,即“骑士制度(左)—信仰(中)—智慧(右)”;左右二者相互协作,鼎力支撑着居于中心地位的“信仰”,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法兰西王国在现世和来世的救赎(注:Guillaume de Nangis,Chronique,Vol.1,Paris,1843,p.182.)。朗伊对百合图案的解释迎合了法国王室利用宗教发展王权的需求,而且,朗伊作为王家史官所享有的特殊地位更使他的解释一度具有准官方色彩。
第二,14世纪至15世纪上半叶:王室百合的宗教蕴涵依然浓郁,但体现世俗精神的解释亦偶有显现。从14世纪起,有关王室百合的著述渐趋丰富,对王室百合象征内涵的认知亦开始出现歧异,其中别具一格的是夏利(Chaalis)修道院僧侣吉约姆·德·迪古尔维尔(Guillaume de Digulleville,1358年卒)的观点。他是分三个层次来构建王室百合的象征内涵的。首先,对三枚花瓣的解释:左瓣代表负责守卫疆土的军事贵族,右瓣代表教士和王室顾问,中央的那一瓣则是极富生命力的正义之剑——法兰西君主的象征。其次,对百合徽章底部图案的解释:百合花的萼片基座代表法兰西的普通民众,它是三枚花瓣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最后,对百合徽章的总体解释:它象征着神秘化的法兰西王国“躯体”,其中的不同部位各具功能,它们相互协调,共同运作,最终使得正义之树常青不老(注:A.Piaget,"Un poème inédit de Guillaume de Digulleville,le Roman des fleurs de lys",in Romania,Vol.62,1936,pp.317-358.)。迪古尔维尔虽为僧侣,但他对王室百合象征内涵的解析已大大越离了基督教神学轨道,百合花已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世俗意义。不过,由于迪氏的理论较为繁琐,加之当时的法国王室对宗教的笼络功用极为重视,因而对王室百合的这一世俗化解释并未广泛流传。
这一时期,对王室百合最具权威性的解释来自王室本身。1376年,王室颁发特许状,决定在利马伊(Limay)修建一所则肋司定修道院(Célestins)。在特许状中,王室对百合花的寓意作了明确阐述:百合花是法兰西王国的象征,是王国一切美德和繁荣昌盛的标志,它向全世界昭示了法兰西王国的伟大;同时,百合花本身就是“三位一体”,它无与伦比地展现了法兰西王室的尊严和崇高(注:参见P.Lefébure,"Lemonastère des Célestins de Limay",in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historique et archéologique de Pontoise,Vol.44,1935,pp.7-106。)。在王室对百合图案的内涵做出明确定位以后,一些追随王权的文人墨客开始对之进行逻辑引申,他们认为:百合花是上帝给予法兰西的恩典,它是上帝与法兰西之间爱意与联盟的标志,只要它能使上帝愉悦,这种爱意与联盟便会日益增进,且永不终结;百合花具有非凡的生命力,任何外来力量(如狂风暴雨、丛生的荆棘、瑟瑟的寒风等等)都不可使之屈服衰亡;而且,百合花还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越发美丽,愈益多彩;与百合花一样,法兰西的君主制度虽然已经非常古老,而它依旧焕发出勃勃生机(注:参见Barthélemy de Glanviue,Le grand propriétaire de toutes choses,p.4;R.Blondel,Oeuvres complètes,Vol.1,p.148。)。通过将百合图案喻解为“三位一体”,法国王室成功地把王权与神权糅合在一起,它向世人表明法兰西君主制度的存在和延续得到了上帝的特别恩准,这对于法国王权朝神圣化方向迈进应当说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注:15世纪中后期,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论证自己的绝对权威时声称,他的高贵与尊威“是由百合花恩赐的,而百合花是由上帝赠予的,并且上面有着上帝的印记(即‘三位一体’)。”参见Réponse du dauphin auxambassadeurs de Charles VII,法国国家图书馆,法文抄本2831号,2-14页。)。
第三,15世纪下半叶以后:在神学光环的衬托之下,王室百合的政治色彩日益鲜明。百年战争的创伤弥合以后不久,从查理八世(1483-1498年)时起,法国开始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在此背景下,对王室百合象征内涵的解释也随之发生了某些变化。15世纪80年代,长期客居法国宫廷的意大利人吉奥瓦尼·德·莱戈尼沙(Giovanni de Legonissa)曾为查理八世著书,专门探讨王室百合问题。在王室百合的内涵和特征方面,莱戈尼沙并无什么新的发现,但他却将百合花的地位抬升到了一个特殊的高度,他认为,百合花可以战胜一切可能出现的恐吓和威胁,因而它完全有能力主宰上帝曾经允诺于它的三块土地(指法兰西、意大利和德意志);不论是罗马教皇还是(神圣罗马)帝国雄鹰,都终将置于百合花的那面保护性旗帜之下。与内文相配合,莱氏在手稿的卷首配有一幅醒目的插图,在这幅图中,佩戴百合徽章的法兰西君主气宇轩昂,他一手拿着教皇的三重冠,另一手则握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冠(注:A.Linder,"L'expédition italienne de Charles VIII et les espérances messianiques des juifs",in Revue des études juives,1978,pp.179-186.)。数年以后,前文已经提及的另一意大利人吉奥瓦尼·维瓦尔迪又为路易十二(1498-1515年)写了一本专论王室百合的著作,书名为《三朵百合的胜利》。在此书中,维瓦尔迪详细总结了王室百合的象征内涵,如数字3象征“三位一体”,百合花所呈现的金黄色象征法兰西王权的经久不衰,百合徽章的天蓝底色则象征着百合花是来自天国上帝的赠礼,如此等等(注:关于百合徽章上的两种颜色,详见M.Pastoureau,"Et puis vint le bleu",in Europe,1983,pp.43-50。)。通过对王室百合的全面考察,维瓦尔迪得出结论:法兰西国王是上帝的扈从和斗士,在上帝的恩宠之下,他的统治将是无可匹敌、充满荣耀的,他将以摧枯拉朽之势去扫除各种形式的暴政和野蛮。可以看出,维瓦尔迪的观点与莱戈尼沙是一脉相承的,在他们的笔下,百合花已经成为法兰西国王孔武有力的象征,法国王室试图开疆拓土、雄霸欧陆的愿望在此已见端倪。在王室的悉心哺育之下,法国社会上流传的一些文学作品也开始赋予王室百合以强烈的政治色彩,例如,15世纪末16世纪初出现的一首诗歌即对百合花的威力作了正中王室下怀的描绘:“它们将战胜其他一切徽章,它们将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它们将聚居于法兰西王国,通过战役和战争,它们将比尘世上任何其他徽章都更令人敬畏”(注:Jean Divry,Les Triomphes et L'origine desFrancais,Paris,1508,p.7.)。随着百合花政治内涵的不断发展,王室百合的神圣地位在日常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亦开始具有程式化的表现形式,这一点可以集中体现在国王葬礼的某些重大变化上;从15世纪后期开始,在为已故国王举行的葬礼上,王冠和饰有百合徽章图案的旗帜不再与死者一同下葬,百合花旗只是在死者的墓前降半以示志哀。这一变化表明,法国王室已将百合徽章与王统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法兰西王统是永恒的,作为王室的标志,百合花当然也应当是永不枯萎的,它必将随着法兰西王统的传承而延诸万世(注:参见陈文海《试论中世纪法兰西的王统理论》,《世界历史》1999年1期。)。
由百合花图案的源流及演变历程可知,法兰西王室百合徽章与基督教神学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是宗教土壤养育了法兰西的王室百合。王室百合诞生以后,其象征内涵的神学色彩经历了一个渐趋弱化的过程,它曲折地反映了王权与神权之间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同时也反映了法兰西王权由弱到强的历史行程。从一定意义上说,百合徽章的历史已经成为中世纪法国社会政治史的浓缩。
标签:百合论文; 法兰西论文; 徽章论文; 法国国王论文; 花论文; 中世纪论文; 西欧中世纪论文; 象征主义论文; 基督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