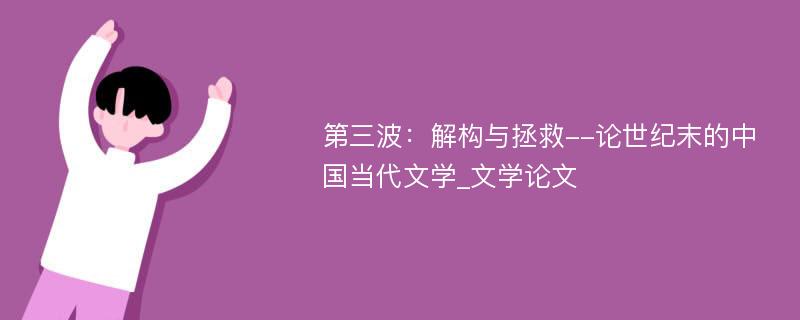
第三次浪潮:解构与拯救——关于世纪末中国当代文学的谈话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世纪末论文,中国论文,浪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间 1994年9月28日子夜
地点 福州福建省画院403房。
题外话:开完北村近期小说作品讨论会,第二天,朋友们就将各奔西东。谢春池与王干相约就“第三次浪潮”聊一番。一时无录音,谢春池只好笔录,故他无法完全与王干对侃,至多只能间歇地插话和简短地表述。后来,在整理时他把当时的一些想法以“自忖”补到谈话录里。
谢 我认为这个讨论会的意义已超出北村本人,北村的小说作品和这个讨论会本身。你在会上发言谈到,中国当代文学第三个浪潮即将到来,对此,我也有同感。我觉得这个提法不仅充满新意,而且,是从另一个维度来考察我们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
王 你说的不错。此次来福州开会,印象很好,福建的同行们,很努力也很认真地进行着当代文学评论的研究工作。北村作品讨论会从理论上确实提出很多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我以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已经涌过两个浪潮。
谢 这就是你在会上提出的,第一个是朦胧诗讨论引起的,第二个是方法论讨论引起的。这个论断使福建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因为,朦胧诗的讨论引发者是福建女诗人舒婷,最初的讨论是在1980年初春的《福建文艺》上展开的,这年11月在福州召开了讨论会。方法论讨论会我记得是在厦门大学召开的,时间是1985年3月。
王 我以为第一浪潮的意义在于文学的审美功能的恢复。长期以来,我们把文学的功能仅仅局限在宣传和教育两个方面,而忽略了审美这个最为重要的功能。以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的出现,给中国文坛带来大冲击,记得当时争论最激烈的是“看不懂”这一个问题。
谢 其实,现在回头去读一读舒婷,还有北岛、顾城们的诗,已经不存在“看不懂”的困难了。
王 没错,朦胧诗的讨论和接着的寻根文学的讨论意义重大,此后,对于审美性的文学作品,读者们懂了,因为阅读的通道打通了,没有看不懂的了。有不少文学作品,是一种感觉或情绪的表现,其解读的语码不在于教育的功能。故而,我认为,朦胧诗的讨论为以后出现的现代小说作了一次铺垫作了一个预告。
第二次浪潮的兴起以方法论热为标志。全国方法论热的兴起与新时期文学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启蒙运动是联系在一起的。新时期的重要特征和国情是实现四化。记得徐迟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文学与现代化》……
谢 徐迟的这一篇文章引起一场争论,赞同者有之,批判者有之,持中间态度的有之。
王 文学的现代化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是对西方文化的认同。
谢 或者说是:接轨。
王 接轨?也可以说是接轨。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方法论热。后来,很多西方哲学的引进,莫不与此有关。如尼采、叔本华、弗洛依德、萨特,等等。方法论的讨论已不仅是方法问题,而是进入了本体,亦即内容问题。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世界新的认识的参照。比如,科学主义的方式出现,是启蒙的产物,方法的更新,思维的改变。此前,尽管论说的是新时期文学,但,维度仍留在一元化的水平,只以认识论及意识形态或理想作为参照。运用的仅仅是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话语。但是,方法论的引入,给我们一个契机,一面旗帜。对一元论的否定,把思维的单一化改变了。与此同时,主体论出现,它是哲学的,内容性的。方法论和主体论之间发生了有意或无意的混淆。符号学或叔本华等人的东西,均以方法的名义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大量引进西方哲学,总会被限制,于是,找到一种转换形式。
谢 在方法论热的时候,我隐约觉得文学似乎在科学之中消失了。
王 幻觉,我要说的一个词是:幻觉;不少人以为方法论热会解决许多文学的根本问题。文学毕竟是文学,其偶然性、突发性、等等,不是科学能够简单测定的。不过,方法论热确实把西方文化哲学的这个领域打开了。这时,涌进了大量西方的理论著作和小说。
谢 我们有了许多新的文本参照。
王 中国文坛出现了许多热,最热的莫过于魔幻现实主义了。作家争相仿效,评论家纷纷评论,一时间蔚为大观。这就产生了双重效应。即作家与评论家的双重效应。当作家看不懂西方的文学作品,即读西方的文学评论,看西方评论家怎样看西方的文本──之后,就进入创作;当评论家看不懂西方的评论,即读西方的文学作品,看西方作家以怎样的文本被评论──之后,就进入评论。这时候,西方给我们提供的主体是:方法;客体是文本──各种方法与各种文本。我们在极度饥饿之时进入极度饱和状态,很多消化不良的文章问世了。可以这么说:85年前后的中国文坛,是振奋、兴奋。
谢 是亢奋!
王 对,是亢奋!人们对中国文学充满希望。与此同时,文化寻根热出现。文化寻根热与引进西方的方法论和主体论完全不同,是一种对应。
谢 不仅是对应,而且是对立,对抗。
王 有对立,有对抗,但,更是对应。文化寻根不是科学的产物。本土地域,民俗风情,痴迷梦幻,这都是反科学主义的。从文学的角度看,寻根文学对叙事方法的研究,使叙事发生本质性变化,对先锋小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当时出版了一本书,叫《走向世界文学》,参照拉美爆炸文学,提出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循环轨道。
谢 如此说来,寻根文学与方法论的本质是一样的。
谢 本质是一样的,即走向世界。对象是西方文化,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批判也有这个背景,构筑了现代神话。文化要现代化,研究也要现代化,即现代科学化。这种浪潮的方向与改革开放的人文环境有关。寻根文学经过85至88这四年的发展,为先锋小说和实验小说的兴起作铺垫。方法论热乃至寻根文学热,影响了理论家,更影响了作家,特别是小说家。
谢 先锋作家自始至终参与这一阵阵的“热”之中。
王 不仅参与,甚至应用。文体的操作性改变了,从前和今天不一样了。不讲究叙事方法不行了。
谢 先锋作家无疑受到西方强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各方面的。
王 苏童受弗氏的影响很大,叶兆言有解构主义的影子。格非本人在大学教文艺理论,自然很重视书卷气、学者性和现论性。北村当评论编辑。可以看出,方法论影响巨大,它改变了作家的思维维度。从前的观念瓦解了,人们对世界与人生的看法变得多种多样。
谢 (自忖:不错,人们对世界与人生的看法变得多种多样,但,难道仅仅是方法论热兴起之故吗?似乎并非如此。中国封闭的大门打开,这不只是对外不再封闭,对内也不封闭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多种多样其中有许多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恢复。)
王 不过,当我们回顾方法论热,就发现一个问题,即“赶”“超”西方的意识过强。
谢 (自忖:这种“赶”“超”与大跃进年代的那种“赶”“超”有没有包含着同质,是否又是某种民族的劣根性在作崇?)
王 此种结构是:希望有理想模式,使民族走向世界。一时间,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最受欢迎。价值很明显,即对西方简单的认同,简单的分析与解剖。
谢 对西方简单的认同,分析与解剖似乎是个必然的阶段,否则,是无法更丰富地化为己用,进入更高层次上的创造的。
王 但当初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来不及消化,来不及反刍,短时间里,西方百年文化我们如何能很好地接受呢?89年以后,这一切似乎到头了,现代性神话不是终极,西方所有的话语好象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在文学方面,学西方即没有中国特点,用西方理论来进行研究,如语言学、符号学,也难于奏效。能指所指的问题没有解决。
谢 这个时候,就得反观自身了。任何丢弃自身的做法,都难于把对方融入自身。
王 汉语语言很复杂,有自身的特点。而我们的语言学发育不良,在应用语码和符号时,发生很多问题。我们发现自己对西方了解不透,学得不透,对不上号。西方那一套语码很快搞不下去,它很难进入作品文本分析。面对西方,我们终于明白有两个矛盾有待解决。(1)我们没有体系传统;(2)我们没有体系训练。因而,理解和应用发生障碍。当热情消退,也宣告西方神话的破产。张艺谋现象的出现,又说明了一些问题。张艺谋所做的就是与西方接轨。他自认为按西方的话语、方式和程序即可接轨,然而,熟悉之后还无法接轨。
谢 为什么?
王 西方需要我们的是什么?是沈从文、钱钟书。
谢 沈从文和钱钟书并不能与西方接轨。
王 沈从文和钱钟书都是反西方的。
谢 这是否印证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论断。
王 我们暂且不讨论这个论题。还是从张艺谋深入下去。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是带展览性的,猎奇性的,西方人是以“旅游性态度”来看这些影片的。西方是看,我们是被看。
谢 (自忖:张艺谋现象窃认为是比较复杂的,很难一言认蔽之,而这个现象争论由来已久,我不能苟同这几位电影艺术家们的艺术追求是一种“带展览性的、猎奇性的”的看法。西方是看,我被看,这没错,同样我看时,西方亦被看。问题是怎样看,怎样被看。如果从世界性和人类性的高度看和被看,情形又将如何呢?)
王 我们对西方的热情和理想消逝。加入大家庭,我们一厢情愿。
谢 反差太大?
王 我们渐渐明白,如此走向世界文学是不可能的,按照西方语码,西方要求我们的语码,是不能接受的。那些并不能代表民族的真正的东西,或是我们正要抛弃的。于是,出现新写实小说。理想破灭,而对现实,就无可奈何。新写实小说不关注西方,逃离西方,亦不参照西方的文本,只是认同现状而对中国现实写作。
谢 (自忖:此说基本属实,但,新写实小说,难道就没有受到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的冲击,从他们的某些文本上看,难道就没有某些西方文学的影响在里面?)
王 当精神极度疲软,先锋作家出现了,解构,反讽,调侃,对历史采取怀疑态度。他们的作品为什么老是“年代不详”,因为找不到确定性价值。先锋作家把历史拆成碎片,在语言的迷宫里自我陶醉,放逐精神理想,成了其文学风貌。先锋小说拆除深度模式,没有激动人心的东西,有的是失望、绝望。不断的消解,后现代的出现正符合精神疲软的状态。
谢 (自忖:我总觉得新写实小说与先锋小说是那个阶段中国文坛两个互补的又难于割裂层面,同时又是构成中国人精神空间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
王 后现代是一种文化意识,完整的谱系,全方位的展开。中国人很快就接受,如王朔。对价值的亵渎,对传统的践踏。太相信之后,就什么都不相信,怀疑了。
谢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文化现象,很值得探讨。不过,若以王朔论,还是有不少中国人无法接受的。
王 后现代的出现,与我国传统文化有关。老庄、嵇康等古代圣贤给我们带来一种天然的消解。后现代互为文本,互为因果,没有中心,互为消解。与打麻将极为相似。打麻将人人都得改变“叙述”方向,其作为后现代文本极佳,它就是不断消解,且没有中心,打多少都经久不衰,娱乐中蕴藏文化性格,不执着随遇而安。丧失指向,是最好的消费。
谢 这与商业文化的勃兴有极大关系。
王 且是主要的原因。它不是理论上带来的,大量的媒介出现填补精神空白。为对抗空,对抗消解,就出现了另外一些人,如张承志。
谢 张承志无疑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他是一个独行者。他的《北方的河》、《金牧场》和《心灵史》在文坛与读者中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王 张承志始终有一种信念和理想,尽管不断变化移动。他对母亲的歌唱,对红卫兵精神的肯定,朝圣,等等,他一直以他的精神向度对抗滚滚红尘,尽管他推崇的宗教是偏僻的教派,但人们关心的不是教义而是对抗尘世的方式。
谢 可以这么说,张承志是当代文学第一个真正走入宗教的作家,我宁愿把他看成是走入精神大境界,而不是在一般意义上成为教徒。正如我没把北村看成是一个教徒,而是一个皈依宗教的优秀作家。
王 北村与张承志不同在于他是经过了喧嚣走入宗教的。
谢 完全摈弃喧嚣。
王 这其实是另一种亢奋。寻找心灵安放的方式,灵魂的容器的置放。其价值无法评判,这是一次重新对自我精神的拯救。另一位有影响的作家张炜写了《九月寓言》,没有明确提出宗教问题,但,对抗现时的思潮,对抗现代文明。
谢 与贾平凹一样。
王 本质一样。张炜这种逃避,是对绝对价值的含混,但,指向明确:到民间去,到自然中去,找到心安。这也是一种与后现代方式的对抗。还有一个何士光,以《乡场上》闻名文坛,近期出版一本书,书名《如是我闻》,副题《走火入魔启示录》,完全的现实主义写法,从个人的体悟去写佛,写禅,写气功……
谢 一本奇书吧?
王 非常有意思。重新思考生存问题,心灵拯救的抗世俗的书。讲的道理未必是先进,思维向度是新的,探讨当代人灵魂如何处置。其叙事文体,亲切,不喧嚣,却又是载道的。文以载道久违了。
谢 (自忖:文以载道究其实质,并没有错,只是长期以来,被当成唯一的功能而排斥文艺最主要的审美功能,至使文艺走向极端。另则文以载道也得观其载什么道,倘若载的是“左”道,那么其祸害是不可估量的,历史已有明证。)
王 假如我们不认识已经涌过去的前两次浪潮,重新提出“道”,那么,我们就不会意感到第三次浪潮即将到来。
谢 重新提出的“道”,是什么样的“道”?
王 每个人提出的道都不一样,拯救灵魂的方式各人也不同,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对解构进行对抗与批判,相信有一个绝对价值,至少是寻找一个绝对价值。信一个“一”,这个“一”在北村那里是神性和主,在别人那里是其他的什么。不管其意义如何,对人的终极关怀,提到道的位置上了。
谢 (自忖:在这世纪末,人是走到一个尽头,这就必然呼唤一个新的起头,世界和人类该是一直在这大循环中吧。世纪末的中国文学是否也一样,是否也是置于死地而后生?走入宗教是一条路,不走入宗教是否就没有路?我认为路绝非只有一条,精神世界原比物质世界宽广。)
王 当下的文学创作,出现了对神性、佛性、对天地灵性的肯定和向往,在后现代的废墟上开出几剂药方,上述几位作家都有开药方的倾向。能不能对抗后现代的消解?能不能解决家园的问题。成为今后的焦点。这是世纪末的选择与价值的选择。这场冲突即:解构与拯救的冲突。
谢 那么,在这一场冲突中,人和文学的基点在哪里?
王 一部分人认为神──真理可认拯救日夜颓废堕落的文化现实;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消解得还不够,还要不断消解。故而,我们提出“新状态”这一概念。其重要特点是“游走”。找不到价值规范,价值体系,不能轻易地相信某一个价值体系,也不能在脑子里消解,把自己消解,只好游走。对所有的价值都可以靠近,但,不轻易相信,似是在路上的状态。需要价值但不知其在何处。采取游走的作家如王安忆,她的《纪实与虚构》是个例证。一边消解历史真实性,一边又看重心灵的真实;一边喜欢语言的游戏,一边又肯定抒写的重要性。后现代的那种守望与守灵不见了。
谢 “游走”一词的确很准确地把世纪末的某种生存状态表达出来,当下的中国文人的大多数似乎都处在这种困境。
王 游走本身也是一种价值,无价值的价值;处于边缘,没有明确的背景,以价值走动去获得价值。
谢 如此看来,再一次关于价值的讨论势在必行了。
王 不错。近期一些同行们对人文精神的讨论即对价值的讨论,但,其视点的重建似乎站在旧时代之上,而那个旧时代又是虚拟的。我认为我们从来就没拥有过一种完整无缺的人文精神。
谢 我很赞同另一个说法,即我们所谈论的人文精神实则是文人精神。
王 若有,也是碎片式的,间断和瞬间存在式的。没有人文精神,重温旧梦,会使文学简单化、情绪化。找不到价值体系,就必须把价值的讨论序幕揭开。
谢 北村作品讨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就不同寻常。
王 北村作品讨论会把精神向度具体化,把价值取向明晰化。听说北村作品讨论会已开过两次了。
谢 两次都在去年下半年,一次在北京,一次在厦门。
王 有了前两次,为什么还要再开一次?不仅是对北村小说的器重,更重要的是北村的小说确有话题可以反复说。也诚如你所说,所有的话题都还没来得及展开。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我提出第三次浪潮的。新的价值大讨论在解构与拯救之间。这个本世纪末的重要话题超越领域、年龄和性别。文化转型,价值失范,后现代通行无阻,“众声喧哗”是现象不是目的,更不是价值定位。
谢 在我看来,价值的定位其实质是人的定位,人的精神空间的定位,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可悲的,没有信仰的人呢?这个问题已经不可抗拒地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了。
王 总而言之,还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走向世界,从宏观考察中国文学,如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又不用西方的谱系、话语;如何使中国文学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目前,两者之间处在漂浮状态,互不接爱,双重拒接,只有这个状态改变了,才可能升起一轮新的太阳。
标签:文学论文; 第三次浪潮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读书论文; 张承志论文; 作家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