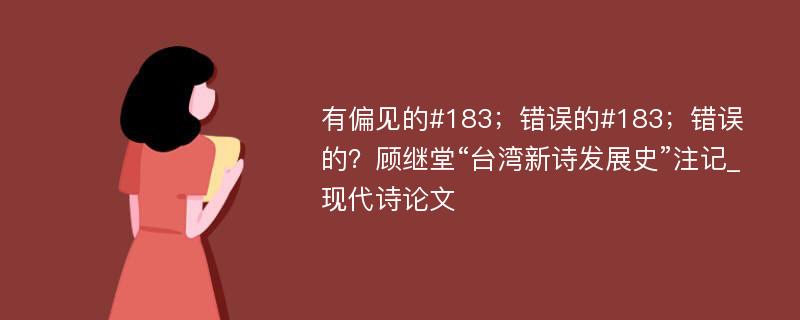
偏颇#183;错置#183;不实?——古继堂著《台湾新诗发展史》初探笔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偏颇论文,台湾论文,发展史论文,不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争鸣篇:关于“大陆的台湾诗学”的论争(二)
编者按:我刊1995年第1期曾以“关于‘大陆的台湾诗学’的论争”为题,转载《台湾诗学季刊》的争鸣文章,为读者提供海峡两岸诗学交流的信息。1996年3月,《台湾诗学季刊》第14期,又推出“大陆的台湾诗学再检验”专辑,刊登台湾诗评家的10篇文章,对古远清、古继堂、王晋民等人的著作提出批评,随后又在第15期刊出古远清、古继堂等的反批评文章。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现象。其实就是台湾诗评家之间的意见,也并不一致,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例如,文治先生在《如果渐成事实》一文中,指责近两年来大陆诗评家评论台湾诗的文章,“通篇只有叫好鼓掌赞美的声音”,“从来不敢或不愿道及台湾诗的缺失”,但在同一期刊登的漫画中,却又讽刺大陆诗评家把台湾诗人“辛辛苦苦炖的肉给狗吃了”。
海峡两岸隔绝40多年,开始文学交流只是近10年的事,而且交流的渠道又很不畅通,因此,通过对话和讨论,将有助于化解彼此的敌意,也有助于创作的繁荣。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期只是选登批评“二古”的文章和“二古”的反批评文章,今后如有新的文章推出,本刊还将继续转载。
1
1988年9月中旬,两岸开放探亲,台湾六位诗人结伴访问北京[1],参加一连串的欢迎会、座谈会、餐会,以及在北京图书馆举办的《海峡两岸诗歌朗诵会》,这是睽违40年两岸诗人的首次接触,颇为引人瞩目。
记得在北京《诗刊》举办的欢迎会上,到了老中青三代六、七十位诗人,就在那次座谈会上,笔者与古继堂初次晤面,稍后他又到咱们寄宿的“竹园宾馆”小叙,并携来他尚未定案的《台湾新诗发展史》目录及前几章原稿,希望我等能提供一些补充的建议。当时因旅途劳顿,笔者浏览过目录一遍之后,初步的印象是:对台湾年轻一代的介绍尚须加强。其中本书第十四章第十二节有关苏绍连的部分,就是根据笔者提供的资料而草成。……
第二年(1989)5月,古著《台湾新诗发展史》,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同年7月,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本书的台湾版。
“台湾版”与“大陆版”不同的地方是:“书前增列了——
艾青/《台湾新诗发展史》台湾版序
古继堂/台湾文学和诗中的“偶数现象”
——《台湾新诗发展史》台湾版自序
又大陆版第十一章(下篇)“台湾新诗回归的前奏”(一),共分五节,其中仅以第四、第五二小节分别介绍《葡萄园》诗刊和文晓村的诗路。而台湾版仍为第十一章,内容则易为“台湾新诗回归的前奏”(一)——“葡萄园诗社”。第一节/从明朗到中国的《葡萄园》诗刊。第二节/文晓村。第三节/古丁。第四节/陈敏华。第五节/李佩征。全文从331——358页。较之大陆版内容增加约三、四倍之多。
再其次,大陆版篇末“本书主要参考资料书目”,共列出68条;台湾版则删去最后18条,变成50条。其中如陈义芝《听那一片汹涌而来的钟声》,罗青《理论与态度》,许南村《试论蒋勋的诗》,掌杉《试论吴晟的吾乡印象》,李魁贤《台湾诗人作品论》,张默《中国现代诗坛三十年大事记》……等等,俱被删除,笔者不解以上所录资料篇目,对本书写作均具参考价值,为何删掉,有无其他特别用心,令人费解。
2
综观《台湾新诗发展史》全书概分绪论(五节),依次“上篇”——台湾新诗的诞生和成长期;以下区分一~五章,历述台湾新诗和五四运动,台湾新诗的发萌、奠基、成长发展、断层期到“跨越语言”一代的诗人(分节介绍陈秀喜、詹冰、林亨泰、陈千武)。“中篇”——台湾新诗的再兴与西化期;以下区分六——十章,历述台湾新诗的重新起点,现代派的崛起与论争,现代诗社和它的诗人群(分节介绍纪弦、郑愁予、羊令野、林冷、方思、方莘、方旗、罗英。)蓝星诗社和它的诗人群(分节介绍覃子豪、余光中、罗门、蓉子、詹虹、杨牧、周梦蝶、向明)。创世纪诗社和台湾的军中诗人(分节介绍痖弦、洛夫、张默、叶维廉、商禽、辛郁、管管)。“下篇”——台湾新诗的回归期:以下区分十一一十四章,第十一章介绍“葡萄园”诗社,已如前述。第十二章笠诗社(分节介绍白萩、赵天仪、李魁贤、非马、许达然、杜国清)。第十三章,台湾诗坛划时代事件——乡土的浪潮,第十四章,从回归崛起的台湾青年诗人群(分节介绍吴晟、蒋勋、高准、罗青、施善继、林焕彰、向阳、郑炯明、李敏勇、张香华、朵思、陈明台、渡也、苏绍连),卷末有后记及参考书目。
就整个目录来看,似属一本设计相当周延、脉络分明的“台湾新诗发展史”的架构。其中优点大致如下:
·对台湾新诗诞生的历史背景,萌发,以及对张我军、赖和、杨华等人的资料掌握,大体均能言简意赅,勾勒出比较清晰的轮廓。
·对“笠”诗社的方向和诗人的介绍,比较深入而贴切。据作者供称本书初稿有关“笠”的部分,曾经非马、杜国清、许达然三人过目,并补充修正若干资料,可能是主因之一。
·对纪弦《现代诗运动二十周年感言》的批评,颇为中肯。纪弦在该文中说:“现代派运动都是依照我的性格而行之,我要办诗刊我就办了,我要组织诗派我就组了,一旦我感到厌倦,我就把它停掉,把它解散掉,一切不为什么,完全是一个高兴不高兴的问题”。古继堂明确指出:“纪弦大力组织现代派,台湾的现代派并没有真正组织起来,而当他宣布解散现代派,台湾的现代派却真正发展起来……”以上论点,诚然一针见血。
·对诗人诗作个别的介绍与诠释,远比对诗社、诗坛整体的观察为佳。(但误导之处也不少,容后再议。)
·如从1923年算起,台湾新诗已历经七十余载,本书所需搜集、阅读、查核的资料难以估算,作者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完成,确是做到了他人所不敢做的事。
由于它是第一部《台湾新诗发展史》,且在两岸同步发行,出版初期的确引起不少回音,但台湾的诗人、学者,以极严肃的治史态度,钜细靡遗来评论列述这部书的优缺点,似乎尚未出现。以下特以笔记方式,将本人对本书初步阅读所发现的疏失,抽样胪列如下:
诗人分类归属,张冠李戴
·本书第八章“现代诗社和它的诗人群”,第六节一并介绍方思、方莘和方旗,可能作者受到台湾某些批评家所指证的“方派”之说。实则方旗在台湾诗坛出现较晚,他从未在《现代诗》季刊上发表诗作,方莘也仅有一首《诠释》,发表在《现代诗》第23期(1959年3月20日出版)[2],他是蓝星诗社的同仁,曾有诗作《月升》等14首,选入《星空无限蓝》(蓝星诗选),罗门、张健编,1986年6月,九歌出版社,既然二位“小方”都不是现代派,以何理由硬把他们列入,令人不解。
第十四章,介绍七十年代的青年诗人群,而把高准(第四节),张香华、朵思(第十节)等三人列入讨论,匪夷所思。根据拙编尔雅版的《台湾现代诗编目》诗人出生年表,高准(1938年生),张香华、朵思(均为1939年生),7年前,他(她)们都是五十开外的人,怎能以青年诗人或新生代加诸他们的头上。
古继堂对台湾六十年代崛起的诗人,似乎特别礼遇和高举,以下特抽样条列:
·羊令野……,他曾任军中首席诗官,因此对台湾诗坛有居高临下的威势(见本书第148页)。
人们对《创世纪》实行超现实主义路线后的抨击,洛夫首当其中,因此洛夫是台湾现代派大将中赫赫有名的人物。(见本书第284页)
·罗门是台湾现代派的十大诗人之一。……(见本书第205页)
向明是台湾现代派诗人中一位“中国化”的诗人。(见本书第254页)
·代表着国民党军中诗人倾向的《创世纪》诗刊,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其较强的政治色彩,这是艺术的不幸,也是创世纪自我设置的一副镣铐。(见本书第264页)
·痖弦,是创世纪诗社创办人之一,他以少胜多,以两本诗集《痖弦诗抄》、《深渊》夺得台湾现代派“十大诗人”之一的桂冠。(见本书第273页)
·叶维廉是台湾现代派诗人中最难懂的。(见本书第300页)
以上随手所摘,古继堂介绍诗人、观察诗社、任意枉下断语,为治史者立下一个不良的例证。他说羊令野是“首席诗官”,这个封号不伦不类,把洛夫、向明、痖弦、叶维廉、罗门,一律划归为“现代派”诗人,确属乱丢帽子。台湾“现代派”为纪弦于1956年2月在台北创组,众所周知,除罗门曾参加旋又宣布退出外,其他几人分属蓝星、创世纪诗社,与现代派均无瓜葛,古氏当初如在行文中说他们的诗风有现代主义的倾向倒无不可,可惜他对“派”与“主义”之别不察,终因一字之差,而意义相距千里矣。
再说,“创世纪”诗社,是当时几位服务海军的青年所创的同仁诗刊,与国民党政权毫无关系,何来政治色彩。至于早期所出刊的“战斗诗特辑”[3],只是该刊拓展创作素材的手法之一,在卷前的“宣言”中曾有如下表白:“今天诗人的任务有二:一是对外要与毒素的的思想、消极的情绪、颓废的意志搏斗,二是对内要与腐朽的主题,低级的风格,陈旧的形式厮杀”。古氏据此而判定“创世纪”为国民党服役,纯属大胆虚妄的猜测。
评介诗人标准,南辕北辙
这部厚达506页的《台湾新诗发展史》台湾版,绝大篇幅花费在对各代诗人诗风与诗社诗潮的评介与铺叙上。由于作者选择资料来源与考据功夫,做得不够细密扎实,致使一些熟悉台湾新诗发展史料的人士,读过本书之后,总觉得怪怪的,下面仍一一条列:
·对蓝星诗社的介绍,作者采用罗门的《蓝星的光痕》[4]的说法:“从1964-1984年,罗门、蓉子成为蓝星诗社不死的灵魂”。(见本书第181页)又说:“复刊后的蓝星,罗门是主要当家人之一,因而罗门的诗歌主张,当然会影响蓝星”。以及“蓝星是现代派中的温和派”(见本书第184页)……。以上论点是作者误用了罗门的资料,根据笔者的理解,早期蓝星以覃子豪马首是瞻,以后历次改组复刊,大多由余光中主导,罗门、向明、张健、詹虹、方莘……等人协助参与。综鉴罗门最大的长处,是把个人资料洋洋洒洒,一点一滴,装订成册,一字排开,为他将来个人的纪念馆作准备,至于为诗社诗坛服务,那不是他的第一志愿。
对诗人个别评论标准不一,有些诗人零缺点,有些诗人缺点一大堆。譬如他在综合余光中的结论:“……有的诗表达不够含蓄,有的结构比较松弛,有的诗意被政治意识所破坏等等”(见本书第205页);而对赵天仪的评定则是:“他不仅注意到自己作品的社会性、时代性和批判性、而且十分注意美的熔铸和表现,在他丰富咏物和写景之作中,对美的追求表现尤为突出”(见本书第373页)。 对叶维廉诗作的评介,既不统一且前后矛盾,先是说他“严格地把自己的作品限制在‘名理前的视境’状态中,舍去对事物来龙去脉的描绘与交待”(见本书第301页),而后又转为“诗人描写生活,反映人生,再铸自然,不介入生活,是不智之举”(见本书第307页)而对李敏勇的评述,则出现如下的赞赏:“李敏勇把语言作为诗的住所和显像的药水,他不断解放被禁锢的语言,这种对诗和语言诚恳的认识,是李敏勇视野开阔,不断拓宽诗的创作天地的思想基础”(见本书第468页)。
仅举以上数例,足以了解古继堂对诗人评价的判定,南辕北辙。某些十分杰出的诗人,在他的视觉里反而缺点一箩筐,反之某些平庸的诗人则较少发现其缺失。笔者以上铁的论证是否主观,请有识的诗学史家和读者明鉴。
全书校勘粗疏,错误百出
以下仅抽样列举“人名错误部分”注[5]和“其他错误部分”,供有心人士对照改正:
a、人名错误部分
苏绍莲(苏绍连)
杨唯晨(杨维晨)
亚微(亚媺)以上见本书“结论”第5页。
林方年(林芳年)见第三章第43页。
丁颖(丁颍)
沈宇(沉宇)
巫宁(巫宁)(“宁”为简体,出现在台湾版,不妥。)
陈奇平(陈奇萍)
蔡其津(蔡淇津)
马郎(马朗)
曹继梦(曹继曾)
薛子行(薛志行)以上见第八章第121页。
史徒卫(司徒卫)
方华(方莘)以上见第九章第181页。
贝翔(景翔)见第九章第269页。
丁永泉(丁雄泉)见第十章第272页。
林雄(林峰雄)见第十三章第403页。
傅正文(傅文正)见第十三章第407页。
鐘顺文(钟顺文)见第十三章第413页。
詹彻(詹澈)见第十四章第420页。
叶翠萍(叶翠苹)见“后记”第496页。
b、其他错误部分(抽样)1.“目次”第1页“台湾诗的诞生和成长期”,应更正为“台湾新诗的诞生和成长期”。2.“绪论”第4页,列举吴望尧(在美国),应属误传,诗人现旅居宏都拉斯。3.第五章第87页,附注[1]《笠下诗影》,应更正为《笠下影》。4.第九章第185页“中国诗人联宜会”,(“宜”为“谊”之误)。5.第九章第254页“中国若大一个诗坛”,(“若”为“偌”之误)。6.第九章第260页,附注[1]《蓝星的光痕》(文讯月刊第1期,1984年),应更正为1983年7月。7.第十章第269页,“创世纪第11期扩版,采用24开本”,应改为20开本。8.第十章第四节第294页“洛夫”,引用他的诗句“云吊著孩子,飞机吊著炸彩”(“炸彩”为“炸弹”之误。)9.第十章第五节第296页“张默”,引用他的书名《上升的风景线》,应更正为《上升的风景》;《雪泥,河灯》,应更正为《雪泥与河灯》。10.第297页引用张默的《驼鸟》一诗最末一句:“一把张开的伞”,应更正为——“一把张开的黑雨伞”。11.第297、298页,引用《内湖之晨》诗句:
“一片青翠,蜿蜓在我的呼吸里”(“蜓”为
“蜒”之误)。
“伴著拎来的松枝”,(“拎”为“拾”之误)。
“喔!天真正的亮了”,应更正为——
“喔!天是真正的亮了”。12.第十章附注[2]第327页“台台《中国时报》”,应
更正为“台湾《中国时报》”。13.第十章附注[18]《诗人辛郁访问记》页(方生),页字下面,漏掉数字,“方生”是访问者的笔名吗?14.第十二章第359页书眉“台湾新诗回归的前奈”。
(“奈”系“奏”之误。)15.第十三章注[7]第418页《东阳光下挺进——诗坛
需要不纯的杂志》。应更正为《在阳光下挺进
——诗坛需要不纯的诗杂志》。
注[9]《七十三年文批学评选》,应更正为《七十三年文学批评选》。16.第十四章第474页,朵思小说集《紫沙巾和花》
应更正为《紫纱巾和花》。17.第十四章注[3]第492页,《许南村,系陈映真的
笔名)“系”应更正为“係”。这是两岸开放后简
体字泛滥造成的结果。
以上所列错误,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全书各章引用各人诗句,笔者没有时间一一查对,但其中定有不少错误。
为此,笔者特别举台北版的两部当代文学大系为证:一是1989年5月九歌出版的《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李瑞腾编)二册,共1332页,二是1993年5月正中书局出版的《当代台湾文学评论大系》《新诗批评》(孟樊编),《文学现象》(林耀德编)二册,共1172页,请大家仔细阅读这两部大书其中所引诗人作家笔名或书目资料,可说校勘极为精细,几乎找不到错误,不论从治史的态度、校勘的认真来论,均可作为古氏今后学习借鉴的对象。
3
本文以笔记方式行之,点点滴滴,无不以具体的事实数据为证,指出本书的若干错误和疏失,(当然还有笔者未能发现的一些优点和疏漏),以便作者他日改写的参考。
何况作者在“后记”中已经恺切说明“由于资料不足,和本人水平所限……本书带有很强的探索和探讨的性质,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本人诚恳希望台湾及海外的诗人、学者、读者,给予批评指出”。笔者推测他说的这番话并非客套,故而坦诚提出一些拙见如上,我不愿再见到像向明与古远清那样,曾经因批评观点不同而形同路人,两岸从事诗学批评者,应有雅量“闻过则喜”,如果我这篇笔记,遭到古氏或其他人士真诚而具卓见的反批评,我也会拍手叫好,如果是擦黑板式的否定,那也就无批评的气度可言了。
其实,治史,并非任何人都可轻易尝试,你是否具有“宏观的远景,独特的主张,客观的态度,和犀利的笔触”,以上缺一不可,笔者认为古继堂当初的企图心实在太大,如果把本书定名为《台湾新诗发展史稿》可能较妥,如他一开始即抱定从事《台湾新诗史料汇编》的心情,提供搜集诚实可靠的史料,给某些更具实力宏观的文学史家来治台湾新诗史,懂得自省,藏拙扬优,可能他今天在两岸的声誉就豁然不同了。
附 记
本文以《台湾新诗发展史》1989年7月台北文史哲出版社的“台湾版”为评述蓝本。
(原载《台湾诗学季刊》第14期)
注释:
[1]两岸开放,首次于1988年9月上旬赴大陆结伴访问的台湾六诗人为洛夫、管管、辛郁、碧果、张默、张坤等,当时造成不小的波澜。
[2]《现代诗》季刊目录汇编,于《创世纪》37期(1974年7月)、第38期(1974年10月)、第39期(1975年1月)共3期连载,为了寻找方莘究竟有无在《现代诗》发表诗作,最后终于觅得《诠释》一诗的出处。
[3]《创世纪》第4期(1955年10月)曾出刊“战斗诗特辑”,计刊出纪弦、吹黑明、洛夫、张默、钟雷、辛郁、王岩、金剑、彩羽、银喜子、艾江、溪边草等多家的诗。卷前有“诗人的宣言”一篇,说明出刊这个特辑的主旨,由洛夫执笔,引文为其中最末一节。
[4]《蓝星的光痕》,罗门执笔,见《文讯》月刊创刊号第106-112页,1983年7月。
[5]“人名错误部分”,光是“现代派”同仁名单即错误连连,为此笔者特向鲁蛟兄借得《现代诗讯》第一期(1958年2月出版)查对“现代派”第一、二批名单,古氏介绍“现代派”的名录,经笔者本次改正后,不曾再有错误了,请大家放心引用。
标签:现代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