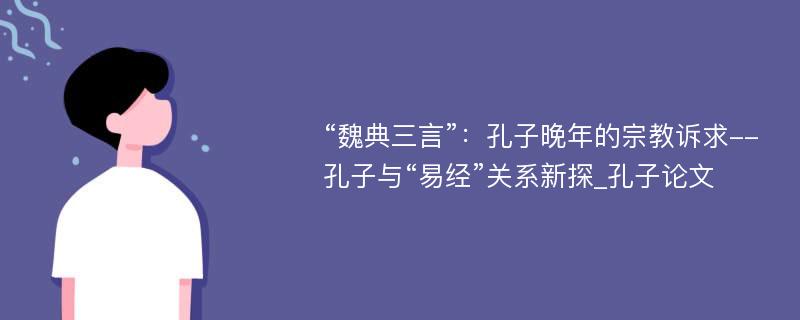
“韦编三绝”:孔子晚年的宗教诉求——孔子与《易经》关系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易经论文,新论论文,晚年论文,三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7)01 —0034—08
引言
我妈妈年近花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她有一本《金刚经》手抄本,是她自己从别人那里抄来的(她上过初中,能认得字)。字写得歪歪扭扭,有些生涩;至于本子,则是中学生们常用的那种软面数学练习簿。她每天早晚都要翻开手抄本念一遍《金刚经》,久而久之,这手抄本就被她翻得蓬松发毛,白纸变污,有几页甚至还破了,被用透明胶带粘补着;同时,手抄本的脊背也用透明胶带紧固住以防掉页。去年春节,我特地买了一本装帧精美、纸质硬朗的《金刚经》送给妈妈,建议她把那个破旧手抄本仍掉,用这本新的。妈妈虽然高兴地接受了我买的新《金刚经》,但却一直让它在抽屉里放着,平时依然还是用那个手抄本。我颇有些不解,于是有一次当她拿出手抄本准备念经时就好奇地问她为什么有新的不用,反而要用那旧的破的,她掂着手抄本笑着说:“这个用惯了,念起来顺口也顺心。”这时,我恍然大悟,所谓“顺口也顺心”,其实就是一种宗教感情。应该是一种纯洁而专注的宗教感情使妈妈不愿舍弃破旧的手抄本;就是那样一种纯洁而专注的宗教感情驱使着妈妈日复一日地翻念手抄本,并使手抄本越来越破旧。然而,手抄本越是破旧,就越能满足妈妈的宗教感情,从而也就使她越加爱惜手抄本。我敢断言,即使将来有一天,手抄本破得不能再用了,妈妈还是不会把它扔掉,相反,而是会把它作为圣物收藏起来,甚至供奉起来。总之,破旧的手抄本负载着妈妈无限的宗教感情,满足了她那纯真的宗教诉求。相比之下,我虽然是研究佛教的,也有《金刚经》文本(比妈妈的《金刚经》手抄本在外观上要好得多),但是,由于我不是佛教徒而只是个研究佛教的学者,所以我对《金刚经》就只有学术上的诉求而没有宗教上的诉求。我不会像妈妈那样每天按时地去翻念《金刚经》,而且,如果有一天我所使用的《金刚经》文本旧了破了,我可能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扔进废纸篓里而去买本新的。
妈妈那本破旧的《金刚经》手抄本时常浮现在我眼前,并且有一天终于向我显示出了其非凡的意义,因为它使我联想起了孔子的“韦编三绝”。我认为,孔子晚年“韦编三绝”地读《易经》就像我年老的妈妈天天翻念破旧的《金刚经》手抄本一样,是一种宗教行为;或者说,“韦编三绝”体现了孔子晚年深刻的宗教诉求。然而,我担心我的这个观点太过突兀,可能会不得人心甚至触犯众怒,至少有人会笑话我如此心中没数,怎么可以将自己的妈妈与圣人孔子相提并论呢?不过,敬请读者稍安毋躁,我会为这个观点举证并文责自负的。
一、“韦编三绝”及其相关学术背景
“韦编三绝”的典故出自《史记·孔子世家》,曰: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期,书是用牛皮绳(“韦”)编连起来的竹简,《易经》就刻写在这样的竹简上。“韦编三绝”说的是,孔子晚年读《易经》,多次翻断了牛皮绳。我们都知道,牛皮绳——哪怕是很细的牛皮绳——都是很坚韧的,一般不容易断。当时人们之所以想到要用牛皮绳而不用其他的材料(比如麻绳)来编连竹简,可能就是因为看到了牛皮绳具有无比坚韧的特征。孔子多次翻断了用来编连竹简的牛皮绳,可以想见孔子肯定是天天读《易经》且不知读了多少遍,否则绝不可能出现“韦编三绝”的现象。
“韦编三绝”这个故事本身很平常,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问题是如何解读它,如果我要把“韦编三绝”与宗教联系起来,说“韦编三绝”体现了孔子晚年的宗教诉求,那我就不得不面对来自与此有关的已有学术见解的挑战和相应学术氛围的压力,如下:
(一)《易经》从来就没有被学界认为是一部像《金刚经》那样的宗教经典。既然《易经》不是宗教经典,那么孔子“韦编三绝”地读《易经》又何以能体现其宗教诉求呢?
(二)“韦编三绝”从来都是在学术的意义上而不是在宗教的意义上被诠释的,比如匡亚明说:“《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年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可见他曾进行深入的研究。孔子曾吸取书中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来教育弟子。”(第293页)[1] 金池说:“孔子学习《易经》‘韦编三绝’。意思是说,孔子学《易》,把连贯《易经》竹简的熟牛皮绳都翻断了多次。此时的孔子已经接近七十岁了,他那种勤奋学习和认真研究的精神实在可嘉。”(第205页)[2] 作为源自典故的一个成语,“韦编三绝”在词典中被作了这样的解释:“孔子晚年很爱读《周易》,翻来覆去地读,使穿连《周易》竹简的皮条断了好几次(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后来用‘韦编三绝’形容读书勤奋。”(第1307页)[3] 凡此种种,皆是明言“韦编三绝”体现了孔子晚年对《易经》深刻与勤奋的学术关怀(具体表述略有不同)——这是到目前为止对“韦编三绝”的唯一理解和主宰话语,而我居然要给“韦编三绝”赋以宗教意义,这岂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三)对于孔子这个人究竟有没有宗教关怀,学界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即根据《论语》中所说的“敬鬼神而远之”(《雍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未知生,焉知死”(《先进》),“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等来断定孔子是一个缺乏宗教关怀和没有什么宗教情感的人,这样的观点显然不支持我赋予“韦编三绝”以宗教的意义。不过,对我更为不利的是,我国学界似乎存在着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学术禁忌,即对于中国的历史名人总是讳言其与宗教的关系(哪怕他是一个宗教徒),唯恐宗教玷辱了他的一世英明,比如,谭嗣同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的著作(如《仁学》)中也充满了佛学的元素,但是历来研究谭嗣同者都只谈其作为维新变法勇士的一面,而不谈其作为佛教徒的一面。① 试想,在这样一种学术氛围中,如果我从“韦编三绝”中读解出了孔子晚年的宗教诉求,岂不是坏了孔子作为中国最著名历史人物的形象?
总之,以上三方面所构成的学术背景十分不利于我将“韦编三绝”与孔子晚年的宗教诉求联系起来,但是,“不利”并不就等于“不能”,“不利”并不能阻止我对“韦编三绝”进行宗教解读。窃以为,“韦编三绝”只有从宗教的向度去考察才能“得其所哉”。不过,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明确孔子究竟是如何看待《易经》的,因为,孔子之所以要“韦编三绝”地读《易经》,这与他如何看待《易经》即对《易经》的看法有关。
二、孔子对《易经》的看法
这个问题可分两点来阐述:
(一)《易经》本是一部占卜之书,这是孔子那个时代的社会共见,但是孔子却慧眼独具,不落俗套,对《易经》进行了重新的审读和定位,“使之成为培养人,完善人,修己达人的义理之书”(第331页)[1],使之成为一部引导价值观、宣扬人文精神的书。《论语·子路》中有载: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这是在“南人”中间流传的格言,大意是说,人若无恒心就做不成大事(“巫医”在当时的社会是很受人尊敬的职业),而“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则是《易经》“恒”卦九三之爻辞。孔子很赞赏“南人”的那句格言,并引用此一爻辞来支持它,“意思是《恒卦》上说的这两句话,不是占卜的话,而是鼓励人做什么事都应持之以恒”(第331页)[1],否则就会自取其辱。在这里,孔子引用《易经》中的爻辞,并不是像坊间那样用它来占卜,而是用它来表明某种价值取向,这是对《易经》所作的三百六十度转读,也是对《易经》意义的全新诠释。在帛书《要》中,孔子更是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对《易经》的诉求完全不同于“史巫”,他说:
《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后事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
孔子并不是不知道《易经》是一部占卜之书,但他首先关注的则是“其德义”,而非“其祝卜”,这使得许多人怀疑他所说的《易》是不是真正的《易》。对此,孔子显得很坦率,他说,我与那些以《易》作占卜的“史巫”只是“同涂(途)而殊归”罢了。正是这种“同途殊归”的创新精神使得孔子敢于作《易传》“十翼”以引领《易经》脱离传统的占卜话语而进入价值领域。然而,我们都知道,孔子在学术上是“述而不作”的,即对古代文献只是进行删定和整理,不作己意之诠释,但是,他又为何偏偏要“作”《易传》以释放自己对《易经》的独特悟解呢?这实际上反过来证明了我们不能从学术的角度来理解孔子之“作”《易传》;或者说,孔子“作”《易传》并不是他的一项学术工作。② 如果孔子是在以学术的态度来对待《易经》,那么他就会实事求是地将其看作是一部占卜之书(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绝不会“作”出一部不注重占卜的《易传》。③
(二)《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请注意这里的“修”字,在中国古代学术中,整理和编辑文献叫“修”,如修“四库全书”,修方志;而对文献进行注疏则叫“治”,如治《论语》、治《老子》,等等。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的学术工作,不是“修”就是“治”,别无他事,而对于孔子来说,他的学术工作就只有“修”而没有“治”,即“修”《诗》、《书》、《礼》、《乐》。④《史记·孔子世家》对孔子之“修《诗》、《书》、《礼》、《乐》”有如下具体的描述,曰: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而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紧接着这段引文,《史记·孔子世家》就提到了“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完整的引文前文已出)。这里有一个细节容易被忽略,那就是,《史记·孔子世家》为什么不像说孔子“修《诗》、《书》、《礼》、《乐》”那样地说孔子“修《易》”,而只是说孔子“喜《易》”、“读《易》”呢?这是个问题。另外,《论语》中说孔子“五十以学《易》”,帛书《要》中说孔子“老而好《易》”,《易纬·乾凿度》和《孔子集语·六艺》中又都说孔子“五十究《易》”,总之,在现在所能见到的相关考据资料上都不见有说孔子“修《易》”的,这是为什么呢?这只能说明孔子确实不是像对待《诗》、《书》、《礼》、《乐》那样地对《易经》进行学术整理——孔子删定过《诗》、《书》、《礼》、《乐》,但却没有删定过《易》。相传《易》有三种,即《连山》、《归藏》和《周易》,三《易》其实都不是孔子定的⑤,孔子只是选择了当时还在流行的《周易》原原本本地来读罢了,不曾动得其中一字。孔子为什么在改动《诗》、《书》、《礼》、《乐》的同时不去改动《易》呢?孔子为什么愿意对《易》作全新的诠释而不愿意改动其中一个字呢?孔子的这一做法难道不会使人想起宗教徒对于宗教经典“一字不能动”的崇敬态度吗?
我们都知道,孔子对古代文献进行学术整理是有其社会关怀之目的的,即用这些经过他删削整理的文献来教育国君和民众,以达到政治施为和道德风尚之良性回归,这就是他“修《诗》、《书》、《礼》、《乐》”的意图所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众。”这就很明确,孔子“修《诗》、《书》、《礼》、《乐》”并“以《诗》、《书》、《礼》、《乐》教”,使弟子们能“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也就说,在孔子充满社会关怀的“修——教”实践中⑥,并没有涉及《易经》,孔子的“喜《易》”、“读《易》”、“学《易》”、“好《易》”和“究《易》”并不含有社会关怀的期许。孔子“韦编三绝”地“读《易》”,并不是为了从《易经》中发掘进行社会教育的资源,并不是为了从《易经》中找到根治社会疾病的良方,而是为了提升自己个人的生命品质,这就是《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自谓之“我于《易》则彬彬矣”。所谓“彬彬”,也就是“文质彬彬。”《论语·雍也》云:“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读《易》”实在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一名“文质彬彬”的君子。可以说,孔子的“读《易》”是面对个己生命的私人生活,而其“修《诗》、《书》、《礼》、《乐》”则是面对社会公众的学者生活,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综上所述,孔子与《诗》、《书》、《礼》、《乐》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学术(包括教育)的关系,孔子希望通过《诗》、《书》、《礼》、《乐》的“修——教”实践以完善社会;而孔子与《易》的关系则并非是一种学术的关系,孔子“喜《易》”、“好《易》”、“学《易》”、“究《易》”,并“韦编三绝”地“读《易》”,乃是为了藉此完善自我以达到君子的境界,简单地说就是,孔子以《易》“修身”而以《诗》、《书》、《礼》、《乐》“平天下”。
三、“韦编三绝”与孔子晚年的宗教诉求
要阐明“韦编三绝”的宗教意义即“韦编三绝”体现了孔子晚年的宗教诉求,光靠传统的考据方法是难以奏效的,因为目前所能找到的相关考据资料不完全、不充分。有鉴于此,我在这里不得不在尊重考据资料的基础上征诸宗教学的方法来审视“韦编三绝”,因为这种现代方法将有助于填补由于考据资料不足所造成的意义空档,从而将不完全的考据资料串连成一个意义整体。
我们都知道,我国现有所谓的“五大宗教”,即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其中,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外来宗教,且都是汉代以后才传入中国的;道教虽然是中国本土宗教,但也是到了汉代以后才有的,所以,在孔子那个时代是没有“五大宗教”的,孔子所仰赖的宗教当然也不可能是这“五大宗教”。再者,现在学界有很多人主张儒学是宗教,但孔子那个时候也没有所谓的儒学,儒学是孔子死后人们才慢慢鼓捣出来并与孔子挂上钩、尊孔子为其创始人的,这与道教成立后之尊崇老子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即使承认儒学是宗教,孔子也不可能从当时还“无何有”的儒学中寻求什么宗教寄托。总之,我们不能站在现代宗教的角度来考察孔子的宗教诉求,而应该回到孔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宗教生态中去发现孔子生命中的宗教。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版)之第四章第五节叫“孔丘对于古代宗教生活的反思”。在这一节中,冯先生根据《论语》所载孔子谈及“天”和“天命”的多条语录⑦ 来推证以“天”为“宇宙的最高主宰者”的“这种宗教思想在孔丘的思想中仍保留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冯先生的意思并不是说孔子在其个人生活中尊崇这种以“天”为“宇宙的最高主宰者”的宗教——有人将这种宗教称为“中国的国教”[4],我们这里不妨称之为“天教”——从而具有合乎“天命”的精神境界(亦即现在所常说的“天人合一”),而是说孔子对这种流行于当时的“天教”有所认识,有所研究,有所反思⑧,说得直白些就是,在冯友兰先生看来,孔子研究和反思过“天教”,但并不信仰“天教”,因而其个人并没有源自“天教”的精神境界⑨,这就好比说某人是研究佛教的但却不信仰佛教因而没有佛教境界。冯友兰先生将孔子的个人生活与“天教”割裂开来,恐怕还是前文提到的那种弥漫于中国学界的对中国历史名人与宗教之关系讳莫如深的学术心态的反映,因为,依笔者愚见,冯先生引用来证明孔子对“天教”有所认识有所反思的那些“子曰”语录,其实都不能算是对“天”和“天命”的客观认识和理性反思,相反倒是孔子内心感受的真实流露,比如《论语·颜渊》中载:“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这话不用解释,大家也能从中感受到孔子对于“天”的宗教性情感(冯先生的其他引用,参见前文的相关注释)。因此,我的结论是:孔子对于“天教”不但有客观的认识,而且他自己还是个虔诚的“天教”信徒——合乎“天命”就是孔子的宗教追求,“韦编三绝”地读《易经》就是孔子的宗教“日课”(就像我妈妈之每天读《金刚经》手抄本)。此时,在孔子的眼中,《易经》早已不再是一部占卜之书,而是一部讲“天命”能满足其价值追求的书——孔子作《易传》“十翼”就是要将隐藏在《易经》中的“天命”表达出来。(10)《易传》中的那句现在都还常常被人用作座右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名言就体现了孔子以“天行健”这一“天命”为归趣的价值追求。“天教”本来是朴素而自然的,没有文字经典,是孔子转读了《易经》,将《易经》立为“天教”的文字经典,并作《易传》“十翼”以诠释其中所蕴含的“天教”教义(11)——“天命”,这就不但使作为“中国的国教”的“天教”上了一个台阶,具备了现代宗教的雏形,而且使《易经》从占卜之书升级为宗教经典(“占卜”是术数之一,不属于以个人生命关怀为旨归的宗教)。
也许孔子将《易经》从占卜之书解读为宗教经典在当时并没有什么社会意义,因为当时的社会大众主要还是将《易经》看作是占卜之书,一般不会认同孔子的做法,这是社会风气和社会习惯使然。可以想见,孔子当时乃是逆社会的主流意识而立《易经》为讲“天命”的宗教经典,这其实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是,就其个人而言,孔子对《易经》的宗教解读完全是其真情实感的流露,他想在《易经》中满足宗教诉求的愿望也是十分迫切的;正因为这种愿望十分迫切,所以孔子天天读《易经》,以至于读到“韦编三绝”。试想,为什么孔子读《诗》、《书》、《礼》、《乐》就没有读到“韦编三绝”呢?这是因为孔子《诗》、《书》、《礼》、《乐》只是学术上的需要,因而不会反反复复地天天读;而孔子读《易经》则是宗教上的需要,因而就会反反复复地天天读,这就好比我是个佛教研究者,所以就绝不会而且也没有必要天天去读《金刚经》,而我妈妈作为一个佛教徒,则会天天去读(念)《金刚经》——这就是学术和宗教对经典的不同态度和不同处理。总之,唯有为满足宗教上的需要而天天读反复读《易经》,《易经》才有可能“韦编三绝”,否则是难以解释“韦编三绝”的。这是我在妈妈的《金刚经》破旧手抄本的启发下展开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当否待议。
美国宗教心理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曾指出,“宗教领域大体划为两个分支,‘制度的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和‘个人的宗教’(personaL religion)。‘制度宗教’注重的是神性,主要表现为崇拜、献祭、神学仪式、教会等;反之,‘个人宗教’最关心的是人,或者说是人的内在性情构成了兴趣中心。”(第62页)[5] “个人宗教”意味着“作为个体的人在孤独中的情感、行为和经验,按他们的领悟,是他们自身处于和神圣者(the divine)的关系,此一神圣者可能是他们所专注的任何事物。”(14) 按照詹姆斯的这种宗教分类理论,显然,孔子“韦编三绝”地读《易经》乃是一种“个人宗教”的行为,孔子所关注的“神圣者”就是“天”,就是他从《易经》中诠释出来的“天命”——孔子所崇奉的“天教”没有神,没有教会,也没有神学仪式。
附录:几条补证
这篇论文其实是我去年写的,因为考虑到文中的观点与学界的流行看法相左,所以一直束之高阁不敢拿出来发表。我自知人微言轻,怕“吃不到羊肉反惹一身臊”。不过,我一直暗认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至少不是捕风捉影。后来,我又发现了一些能支持我的观点的佐证,心喜莫名。但是,当我想把这些佐证插入原文时,发现非得对原文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造不可,这是我所不愿尝试的,于是我就干脆仿效余英时的做法(13),将这些后来发现的佐证作为附录陈述于下,但愿不是画蛇添足。
(一)《论语》中有两条可以互证的材料,一是说孔子“五十以学《易》”(《述而》),一是说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为政》)。孔子将《易经》看作是讲“天命”的“天教”经典,孔子“韦编三绝”地读《易经》,从中读到的就是“天命”,正因如此,所以孔子五十岁学《易》,也就能在五十岁“知天命”,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年而喜易”,为什么是“晚年而喜《易》”而不是年轻时就“喜《易》”呢?孔子对于《诗》、《书》、《礼》、《乐》可是从年轻时就开始关注了,为何对于《易》却要直到晚年才关注呢?这是因为孔子对《诗》、《书》、《礼》、《乐》的关注是学术性的,而对《易》的关注则是宗教性的。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往往有这样一条生活轨迹,即当其年轻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得不到施展时,老了就会退隐到某一宗教中去寻求精神慰藉。孔子显然也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只是由于他那时还没有宗教,所以就选择了退隐到《易经》中去寻求精神慰籍,在“韦编三绝”读《易经》的过程中实现其宗教诉求。孔子曾表达自己的人生哲学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孔子就是在“天下无道”而难以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之抱负的情况下退隐的,那么他“隐”而何为?现在一般的看法都是说孔子退隐后从事文献整理和教书育人的工作,这当然没有错,不过,除此之外,我们似乎还应该关注孔子退隐后的私人生活空间。黑格尔曾说:“历史的人物没有享受到什么快乐,所谓快乐只能在私生活中获得。”(第31页)[6] 作为一个历经坎坷而郁郁不得志的历史人物,孔子晚年难道就没有诉诸宗教的私人生活而只是一味地承担整理文献和教书育人的社会责任?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而且从老年心理学的角度看,孔子晚年应该不会只是注重社会角色的扮演而不去寻求个人心灵的归宿,从而走向宗教。当然,我们也不能反过来说孔子晚年只是寻求个人的宗教归宿而不再关心社会。窃以为,孔子晚年是“大隐隐于市”,其中,“隐”满足了他的宗教诉求,而“市”则又满足了他的社会关怀。唯有两者兼具,才是真实的晚年孔子。
(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谈到了《易经》在孔门的传授情况,曰:“孔子传《易》于瞿(即商瞿子木),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14) 我们都知道,孔子“有教无类”,“自行束脩以上”皆可来学,且孔子以后,“儒分为八”,儒家的传授也是公开而多向的,但是,唯独《易经》,孔子却只将其传授给商瞿子木,商瞿子木以后,也是代代单传,这样一种传授体系颇具神秘性(15),与儒家“开门办学”的风格极不协调;而且作为孔子“传《易》链条”之各个环节的人物(如商瞿子木、楚人馯臂子弘、江东矫子庸疵等)都不象孔门的其他人物(如子路、子思、孟子等)那么为人所熟知,同样亦颇具神秘性。为什么孔子在传授《诗》、《书》、《礼》、《乐》时都是如此地公开和大众化,而在传授《易经》时却要如此地神秘兮兮,连他自己的儿子也不传授呢?(16) 我们只能从宗教的角度来理解孔子“《易经》单传”的这种神秘现象,因为这种非家族内部的“单传”(17) 只有在宗教中才会发生。
孔子视《易经》为讲“天命”的宗教经典,因而不用它来公开教育广大弟子,只是私自传授给与他有着同样宗教情结的商瞿子木,难怪子贡要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对于子贡的这句话,学界一般都理解为是孔子不讲“性与天道”,实际上,只要仔细品读这句话,我们就不难发现,子贡的意思是说,孔子是讲了“性与天道”的,只是孔子所讲的“性与天道”他没有机会听到,“不可得而闻”。那么子贡作为孔子最亲近的弟子之一,怎么会听不到孔子讲“性与天道”呢?原来,“性与天道”就是“天命”(18),孔子只有在讲到《易经》的时候才会讲“性与天道”,而孔子又只对商瞿子木一个人讲《易经》,这样子贡自然就听不到孔子讲“性与天道”了;不但子贡,而且像子路、冉有、公西华等孔子的其他弟子也都是听不到的,只有商瞿子木一个人能听到孔子讲“性与天道”。
(四)孔子在《礼记·经解》中认为《诗》、《书》、《礼》、《乐》、《易》和《春秋》“六经”具有不同的作用,他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在孔子看来,学习《易经》能使人“洁静精微而不贼”,其中“洁静”是指人内心的清净安宁,“精微”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尚书·大禹谟》)之概括,意指“人心”与“天命”(即“道心”)的契合无间,亦是“天人合一”的意思;“不贼”,“贼”是伤害之意,“不贼”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若能做到“洁静”和“精微”,那么,他的心灵就不会受到外境的伤害。很显然,《易经》的这种能使人“洁静精微而不贼”的作用完全是一种宗教性的作用,相比之下,《诗》能使人“温柔敦厚而不愚”,意即温柔敦厚但不愚昧;《书》能使人“疏通知远而不诬”,意即“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但又不乱说;《乐》能使人“广博易良而不奢”,意即心胸开阔但不放浪形骸;《礼》能使人“恭俭庄敬而不烦”,意即礼节得体,不令人烦(对人施礼不得体,反会令人生厌);《春秋》能使人“属辞比事而不乱”,意即言辞恰当,不语无伦次,这些作用很显然都不是宗教性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6—10—23
注释:
① 不过,我的《谭嗣同与佛学》一文却冲破了这一禁忌,彰显了谭嗣同的佛教徒形象,揭示了其维新变法思想和实践的佛教背景和佛教底蕴,参见方克立主编《湘学》(第三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204—238页。
② 这就好比季羡林有时也写散文和诗歌,但写作散文和诗歌显然不能算是他的学术工作,尽管他是个著名的大学术家。
③ 当然,学界对于《易传》究竟是不是孔子所作,还是存在着争议的,但是《易传》为孔子所作的考据资料要更充足些,也更为学界多数学者所认可,参见徐芹庭《论孔子与周易之关系兼评欧阳修钱玄同之误说》,载《易经研究论集》,台湾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1月版,第417—428页。
④ 虽然《庄子·天运》中提到:“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但《庄子》中所记载的有关孔子与老聃(即老子)的对话只是庄子借助孔子和老子两人的名声所设计的寓言故事,并非事实,因而不足为凭。
⑤ 关于《连山》、《归藏》和《周易》的基本情况,不妨参见[唐]孔颖达《周易正义》,中国书店1987年9月版,第7—8页。
⑥ 学界一直认为孔子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以“六经”教育弟子,如匡亚明说,孔子“对以往教学中用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文化典籍进行整理、删定,使之成为定型的教本。”(匡亚明《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3月版,第276页)实际上,至少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关孔子整理《易》和《春秋》以及以《易》和《春秋》教育弟子的记载。关于《易》与孔子的关系,本文将讨论,而关于《春秋》与孔子的关系,只能另案处理了。
⑦ 计有:“获罪于天,天所祷也。”(《八佾》)“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吾谁欺,欺天乎?”(《子罕》)“天丧予!天丧予!”(《先进》)“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另外,孔子的学生子夏说:“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冯先生认为这“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乃是子夏从孔子那里听来的,因而也是孔子说的。
⑧ 蒙培元甚至走得更远,他说:“如果说,在孔子时代,天的宗教神学意义还有相当影响,那么,孔子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从根本上动摇和瓦解了天的神学意义。”(参见蒙培元《敬畏之心》,http://www.confucius 2000.com/schoLar/jingwei.htm)在蒙培元看来,孔子不但认识“天教”,而且还瓦解了“天教”,这就使得“天教”更与孔子的个人生活无关了。
⑨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之第四章第八节专门探讨了“孔丘对于他自己的精神境界的反思”(此节标题),在那里他认为孔子个人生活中的精神境界是“乐”和“和”,与“天”和“天命”无关。
(10) 《易传·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句话极具涵概力地表达了《易经》是取法天地所作成的,是“天命”(即“神明之德”和“万物之情”)的体现。
(11) “天教”最原始的经典就是自然界的天地(或者叫宇宙)本身,中国古代不有“天经地义”之说吗?后来,孔子将《易经》立为“天教”的文字经典;再接下来,孔子作《易传》以解释蕴含在《易经》中的“天教”教义即“天命”。“天教”中《易经》与《易传》的关系就象犹太教中《旧约》与《塔木德》的关系一样。
(12) 参见詹姆士《宗教经验种种》(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Macmillian Publishing Co.,Ine.,First Collier Edition,1961,第42页。詹姆斯同时还将“制度宗教”称为“二手宗教”,而将“个人宗教”称为“一手宗教”,其意思是说,在“制度宗教”中,教徒的宗教经验是通过神、教会和神学仪式等中介而获得的,故谓之“二手”;而在“个人宗教”中,教徒宗教经验的获得完全是个己的心灵自觉,无需其他中介的作用,故谓之“一手”。
(13) 余英时的《方以智晚节考》初版于1972年,不过,此后十几年内,余英时又不断地发现有关方以智晚年事迹的新资料,但他并没有依这些新资料对该书的初版进行修改,而是在1986年再版此书时,在初版文本后续以“方以智晚节考新证”、“方以智死节新考”和“方以智自沉惶恐滩考”三节,对相关的新资料作独立的考证分析。余英时在谈到这种学术方法时说:“《方以智晚节考》初版刊于1972年。十四年来有关密之生平之新史料层出不穷,每睹有可以是正原书之疏误者辄记而存之。积久则连缀成篇,以补前愆,先后共得三篇,凡七万言,几与旧考相埒。……兹汇合新得旧考于一编,勒为定本。至旧考之误则不加改正,以见先后论断因资料不同而变迁之过程。”(参见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三联书店2004年8月版,增订版自序)。
(14) 班固《汉书·儒林传》之记载与此略有出入。
(15) 试比较《坛经》中所载的禅宗传承体系:“释迦文佛首传摩诃迦叶尊者,第二阿难尊者,第三商那和修尊者,……二十八菩萨达摩尊者,二十九慧可大师,三十僧璨大师,三十一道信大师,三十二弘忍大师,惠能是为三十三祖。从上诸祖,各有禀承。”
(16) 《史记·孔子世家》中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众。”《论语·述而》中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朱熹《四书集注》曰:“雅,常也。”可见,“雅言”即是经常说起的意思。孔子经常在弟子面前说起《诗》、《书》和《礼》。总之,《论语》中不乏孔子以《诗》、《书》、《礼》、《乐》教育众弟子的记载,但是“《论语》与弟子言,从不及《易》。”(参见魏源《庸易通义》,载《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3月版,上册,第101页)另外,据《论语·季氏》中载: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孔子的儿子叫鲤,字伯鱼。孔子也只是要求伯鱼学习《诗》和《礼》,未及《易经》。
(17) 所谓家族内部的“单传”,大至皇帝将王位传给长子,小至父亲将一项手艺传给儿子,都是属于家族内部的“单传”;而非家族内部的“单传”一般只有在宗教中才会发生,比如宗教首领的更替。
(18) 《中庸》首句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清代学者李光地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大抵在天谓之命,在人谓之性;在心则谓性,在事则谓道。”(参见《榕村语录》,中华书局1995年6月版,第111页)在李光地看来,“天命”、“性”和“天道”这三者是“三位一体”的关系,“性与天道”皆导源于“天命”。关于“天命”、“性”和“天道”之间的这种关系,亦可参见[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82年5月版,第267—268页。
标签:孔子论文; 易经论文; 宗教论文; 国学论文; 论语论文; 金刚经论文; 史记论文; 孔子世家论文; 儒家论文; 周易占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