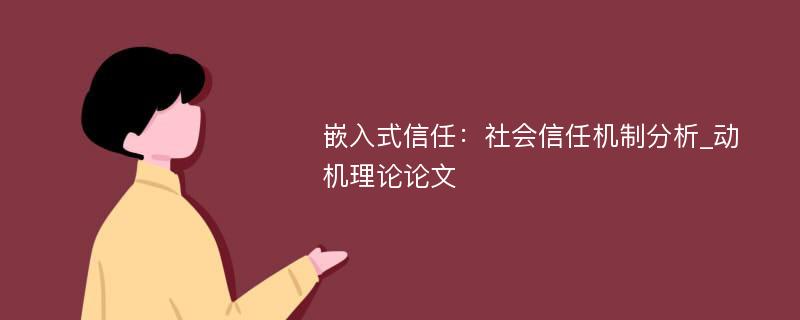
嵌入的信任:社会信任的发生机制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制论文,发生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信任”是除政府与市场之外、影响社会秩序的第三个基础性要素(叶初升等,2005)。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与完全陌生的人、初步相识的人、非常熟悉的朋友,还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家人,个体都可能遭遇到信任问题,需要做出是否信任他们的决定。信任问题的如此普遍性引起了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的热情关注。信任为何可能?什么样的人更值得信任?什么样的人更倾向于信任别人?不同社会背景、经济背景、文化背景的人们的总体信任水平有什么差异?影响信任水平的因素有哪些?这些问题是信任研究者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试图回答的基本问题。来自社会学的相关研究表明,信任问题并不仅仅是个体性的问题,它“嵌入于”(Embedded)并深刻地受制约于特定行动者存在的社会背景(Luhmann,1979;孙国峰,2002)。这一发现,拓展了人们对信任的发生、存在机理的理解。但是,现存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信任的社会嵌入性的强调,很少有研究关注社会嵌入是如何影响信任的产生与运作的。基于此,本文试图对社会嵌入影响信任的机制进行初步探讨。
在进一步的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清楚界定本文言及的“信任”。现存的关于信任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参见向荣,2005),本文采用理性选择理论对于信任问题的界说。我们假定行动者是理性的:信任唯有在行动者认定他们对于他人的信任的收益会超过不信任的收益时才会发生。此种定义与威廉森(Williamson)界定的“计算理性”(Calculative trust)基本相似(Williamson,1993)。在这里,所谓的利他性信任(Altruistic trust)(参见Mansbridge,1999)并不在本文的考虑范围之内。在反复的、长期的交往互动过程中,长期无法得不到珍重、回报的纯利他性行动甚少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的“以直报怨”、“以牙还牙”正是这个道理。行动者是否信任他人取决于其对受信人(Trustee)回报其信任的能力与动机的考量。科尔曼在其《社会理论的基础》(1999)一书中清楚地指出了信任情境(Trust situation)的四个基本要素:托信人(Trustor)的信任使得受信人可能珍视或滥用信任;如果信任被滥用,托信人将感后悔;但是如果其信任被珍视,托信者将从其对他人的信任行为中获益;信任意味着托信人自愿将自己的资源转交到受信人手中,由其支配控制;托信人对于他人的信任与受信人对其信任的反应之间有一个时间差。可见,信任是一个包含风险与回报算计过程的行为。当行动者认为自己对他人的信任能够得到他人的珍视并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收益时,他(她)将选择信任。
在理性选择理论看来,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决定着信任游戏将如何进行。第一是托信人的信任倾向(Trustfulness),也就是托信人相信他人的程度。第二个因素则是受信人的可信度(Trustworthiness),也就是受信人对于他人对其信任的珍视程度(参见Buskens & Weesie,2000)。托信人的信任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于受信人的可信度的预期。如果托信人认为受信人将会滥用其信任,他(她)将选择不信任。反之,如果托信人认为受信人将会珍视自己对他(她)的信任,他(她)将选择信任受信人。基于这一考虑,本文将重点考察个体信任他人的倾向性,并将受信人的可信度当作影响信任倾向的自变量来处理。
二、信任的社会嵌入性
当我们将信任界定为个体相信他人的倾向性时,并不意味着这种倾向性是内在于特定个体的人格系统。经验告诉我们,同一个体对于自己在相同情境下遭遇的不同的人、以及在不同情境下遭遇同一个人时,常常呈现出不同的信任水平。甲在A种情境中对乙的信任,并不意味着甲在A种情境下会信任乙之外的其他行动者,也不意味着甲在B类情境下还将信任乙。信任与否,不只在于个体的人格特征,非固定不变。行动者倾向于根据特定信任情境的特征以及与其互动的他人的可信度来决定是否托信于他人。
信任游戏首先是嵌入于游戏参与者之间所具有的多次交往关系的特性之中。在一槌子买卖中,买卖双方都不会在“信任”的作用下将自己的资源或者权力让渡给对方。如科尔曼所言,托信人的信任或者不信任行为与受信人的相关反应之间总有一个时间差,并不同时发生。因此,行动者的信任投资无法在一次性交易中得到回报。绝大多数的信任游戏都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中,在这个社会情景里,行动者相互遭遇并且渐次与对方的朋友圈、熟人圈多次、反复发生联系。这种互动、交易行为的反复发生是构成信任发生的重要交往性背景。从实际生活中可以看到,人们在和新客人交易的时候,常常会非常谨慎,不惜成本签下繁琐的交易合同。另一方面,对于自己的老客户或者信得过的朋友推荐的客户,他们往往显出村落社会里人们之间才有的“随意”,可能不签任何正式协议合同就将自己的资源或者权力先让渡给对方,相信对方将会信守承诺,在未来予以回报。这种随意的安全性保证正是来源于他们过去的经验,它切实地节省了行动者的交易成本。由此可见,信任行为的发生是嵌入于过往的互动经验之中并受其制约。
个体的信任倾向亦受制约于其所在的社会文化背景。阿尔蒙特(Almont)等人发现,在具有不同的政治文化的国家里,人们的信任水平往往并不一致。比如,美国、英国等老牌民主国家的社会信任水平就要高于意大利、墨西哥等新兴民主国家(Almont&Verba,1963)。按照福山(1998)的研究,根据信任水平来划分,世界不同国家可以分为低信任度社会(如中国)与高信任度社会(如美国)。此一看法得到韦伯相关研究的支持。在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韦伯特别指出,受制约于传统的儒教道教文化,中国社会是一个信任水平尤其低的国度,其中只存在所谓特殊性信任(Particularistic trust),而少有普遍性信任(Universalistic trust)(韦伯,1993)。关于社会文化对信任水平的影响,普特南(Putnam)进一步指出,因为区域文化的不同,同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的信任水平也可能不同。比如,意大利的南部地区与北部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就存在很大差异(Putnam,1993)。
按照福山的观点,信任其实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是社会共享的道德规范的产物(福山,1998)。这种关于信任的文化解释,令人信服地指出了社会文化对于信任的影响,看到了信任在社会文化中的嵌入性。但是,将信任当作是社会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当作是个体在特定社会文化影响下的自觉或不自觉行为的解释却缺乏充分的经验证据支持。实际上,社会文化对于个体信任倾向的影响,也可能来自于该种文化对于滥用信任的行为的惩罚与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文化其实是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如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而对信任产生影响的。比如,在我国的传统社会里,“言而无信者”通常会遭到其所在村落、社群、社区的唾弃疏离。这就涉及到制度学派对于信任的解释(参见Warren,1999)。由于在特定的信任情境中个体的信任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受制约于受信者的可信度,而受信者的可信度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面对托信人信任的动机(是珍重还是滥用),因此,在那些对于个体的信任动机能够予以充分监控的制度环境里,行动者以及整个社会的信任水平都会相对较高。相反,在一个缺乏对滥用信任的受信人的有效惩戒制度的社会中,行动者对于他人的信任的风险将会倍增,其托信决策将会更加小心谨慎。由此,个体的信任倾向以及社会的总体信任水平也将相应降低。这种基于对制度环境的认识的信任,卢曼(Luhmann)称其为制度信任(Luhmaan,1979)。它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于社会制度的信赖。在这里,相关的社会制度实际上扮演着信任的保障机制的角色。
对于制度对信任的影响,一个有效率的政府、法律系统至关重要。有效的执法系统可以让滥用信任的受信人得到惩罚,增加其滥用他人信任的成本,减少其收益。因此,公正、透明、有效的法律制度对于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都是必要的。这种制度的存在,可以增加人们对于制度保障的信赖水平。正如霍布斯指出的,一个有公共威权的社会体制的存在,可以有效防范社会成员之间的尔虞我诈,确保相互信任在社会成员中的存在(参见王绍光等,2002)。有效的公共威权体制、执法系统能够确保托信者的信任的收益,同时,也有效惩罚滥用他人信任的行为。这正是法治国家的社会信任水平通常高于人治社会的逻辑所在。
从上可见,信任其实是一种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所谓的“嵌入式”(Embedded)信任(参见Granovetter,1985)。它不仅取决于信任情境中各方行动者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更受制约于信任情境自身的特征(如文化、制度)等因素(Snijders,1996)。如同众多的社会学者对于信任问题的研究指出的那样,这种嵌入性对于信任游戏的展开会产生重要的影响。那么,社会嵌入性(Social embeddedness)是如何影响作为理性选择的信任行为的发生呢?
三、信任的发生机制:经验与控制
作为理性行为的信任的发生,是建立在行动者对于信任可能带来的收益与成本的比较的基础之上。这种理性的比较所需要的信息,则主要通过两种基本机制来获得:一是根据过往的互动经验来判断受信人的可信度,我们把由此种机制生成的信任称为“经验为基的信任”;二是根据对受信人滥用信任的动机的控制能力来判断受信人的可信度,我们把经由此种机制生成的信任称为“控制为基的信任”。
(一)经验为基的信任
在决定是否信任他人时,行动者对于自己与他人的信任游戏(Trust game)的很多面向(如他人的动机、互动赖以发生的具体社会情境的属性等)可能并不熟悉。因此,他(她)通常不具有充分的信息去作出完全理性的决策。这时,行动者可能根据过往的经验做出信任他人与否的决定。这样的信任,我们称之为“经验为基的信任”。它的生成、运作,依赖于对过去互动经验的习得。
即使不具有充分的信息,行动者对于自己对他人的信任被滥用可能带来的损失都会作出初步评估,尽管他们无法完全准确预测损失将具体有多少。另一方面,受信人也知道托信人会评估自己的信任被滥用时的损失。在这些初步信息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决定是否信任他人,行动者可以从过去的信任情境(Trust situation)中获得其他行动者的动机(Incentive)、信念(Belief)以及其他特征等信息,并根据这些过去的经验来决定当前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过去的信任情境,既可能是发生在受信人与托信人之间的,也可能是发生在其他第三者与受信人之间的。一个为过去经验证明为可信的人,在现在、未来的类似信任情境中很可能被再次为他人信任。否则,受信人将不被新任。不少社会学研究文献对信任游戏中的如此学习效应已有所论述(参见Granovetter,1985;科尔曼,1999)。
在经验主导的信任中,托信人往往只考虑自己从过去的类似信任选择中得到的收益,以及当前的信任行为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回报,受信人的可能收益则不被考虑在内。这种信任分别有两种不同的运作机制:一种是信念为基的信任模型,另一种是选择强化的信任模型。在信念为基的信任模型中,行动者单纯根据自己对于其他行动者的可信度的认知、信念来决定是否托信于其,而不考虑其他行动者的行为模式的变化。至于行动者对于他人可信度的认知与信念的变动、更新,则是根据其他行动者的过去行为而定。在选择强化的信任模型中,行动者的托信行为则是根据其自身过去的托信行为带给他们的收益而定。倘若他们满足于彼时的收益,那么在现在或未来的类似情境中,他们就将继续信任他人。否则,行动者将倾向于保留他们的信任。换言之,过去信任游戏中的正面经验有利于促进信任的增长,而负面的经验则会抑制信任的发生。
上述论断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的支持(参见Gulati,1995;Heckathorn,1996;Macy & Skvoretz,1998等)。根据经验为基的信任的发生机制,不少研究着手探讨了在两难的信任情境之中的行动者的行为选择。这些研究设计,大多允许行动者根据自己对目前行为选择后果的满意情况来修正其在未来信任游戏中的选择。研究表明,在这个条件下,合作问题、公共产品问题通常都能得到良好的解决。这些研究发现显示,过去经验主导的信任能够良好地协调好行动者之间的交往模式,促进信任与合作的发生。过去经验之于信任决策的如此效应,无论是在双边的信任游戏中,还是在多边的信任游戏中,都有充分显现。比如劳勒尔(Lawler)等人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多边信任游戏关系中产生的正面经验显著提高了其后的信任水平,诱发了信任行为的发生(Lawler & Yoon,1996)。巴特(Burt)和内茨(Knez)的研究则表明,在一个信息共享的绵密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存有的信任游戏经验,既可能促进信任的生成,也可能降低该关系网络中的信任水平(Burt & Knez,1995)。
(二)控制为基的信任
与建立在过去经验基础之上的信任不同,行动者关于是否托信他人的决定,也可能根据其对受信人滥用其信任的损益情况、对其滥用信任的动机的评估而定。当行动者确信受信人滥用信任的行为只能降低其收益时,他(她)将倾向于做出信任受信人的决定。相反,如果行动者认为受信人滥用信任的行为将会给受信者带来比珍重信任的行为带来更多的收益时,行动者将选择不信任。按照理性选择理论,行动者的行动目的在于效用(Utility)的最大化。在这个目标的导引下,行动者总是选择那些能为其带来最大效用的策略、行动方案。因此,只有在现有的社会控制体系能够确保滥用信任的收益少于珍重信任的收益,或者行动者自己可以及时有效地惩罚滥用信任者、控制其滥用信任的动机时,行动者才可能会托信于人。
受信者滥用信任的动机受到外在多种因素的制约。首先,托信者与受信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性的相互依赖关系是影响受信者是否会滥用信任的重要因素。如果信任游戏只是一次性的,行动者就没有机会在未来惩戒滥用信任者、进而控制其滥用信任的动机。相反,当游戏双方存在着长期性的相互依赖,那么,滥用信任者就面临着在将来得不到托信人的信任的风险。这就意味着受信人需要付出重新找其他交易人的成本。当这种成本大于滥用信任所能带来的回报时,作为理性人的受信者滥用信任的动机将会显著降低。在此种状况下,托信者的信任倾向偏高,而受信者的可信度也相应增高。
当受信者不必长期依赖于托信人时,托信人对受信人滥用信任的动机的控制能力将会显著减弱。比如,在托信人不再信任他(她)时,受信人可以转而与其他行动者交易。但是,如果托信人不只是单一的行动者、而是由多个行动者构成的网络群,并且网络群体成员间可以充分地对受信人的可信度进行讨论、沟通时,受信人滥用信任的动机将得到进一步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对信任的滥用不仅将导致受信者在未来无法得到被其滥用信任的托信人的信任,也得不到托信人社会网络内其他行动者的信任。因为托信人所在网络群体内的信息沟通,关于受信人的不可信的信息被广泛传播,其名声被毁。由此,其被信任的可能性降低。这种孤立,显著增强了滥用信任者将后的交易成本,能够有效降低受信者滥用信任的动机。可见,信任游戏参与者所在的社会网络状况对于信任水平的维持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不过,这种可以有效沟通信息的网络并不总是存在。一方面,有的行动者并不乐意将相关的信息与其他人分享;另一方面,有的行动者更没有自己所属的社会网络,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通过法律、规章等正式的制度建立起来的社会控制体系对于受信人滥用信任的动机的控制显得特别紧要。当托信人明确自己可以依赖这种正式的社会控制体系来确保受信人不会产生滥用信任的动机时,行动者将可能做出信任受信人的决定。否则,信任选择会更加谨慎。因为这个原因,一般的,在法制健全的法治国家,社会的信任水平通常高于人治的专权国家。健全的社会控制体系能够及时有效地对滥用信任者予以惩罚,进而削弱一般受信者滥用信任的动机,提高整个社会的信任水平。
(三)经验与控制并重的信任
在作出是否信任他人的决策时,经验与控制并不总是分离的。如果可能,行动者更倾向于同时利用这两种不同的机制进行决策。这种经验与控制并重的信任能够更大程度地确保托信人的信任行为给其带来的回报。博弈论有关合作行为的研究为此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论支持。例如,为了研究合作行为的发生条件,阿科瑟罗德(Axelrod)设计了一种反复发生的囚徒困境式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如果游戏双方都选择合作,那么,双方都将获利;如果一方选择合作,另一方选择背信,那么背信者将获得比双方都合作时候能够获得的利益更多的利益,而合作方则将一无所获;如果双方都选择不合作,那么,双方的收益都将小于双方都合作的收益。为了找到一个在此种游戏中的最好行动策略,阿科瑟罗德邀请来自于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与数学等学科领域中的博弈理论专家分别设计出自己的行动方案。他特别提醒方案设计者可以利用已经进行的互动、游戏经验来决定现在是选择合作还是背信。在所有14名专家都提交他们的游戏方案后,阿科瑟罗德让这些方案来参加由他主持的电脑模拟囚徒困境联赛(Computer Prisoner's Dilemma Tournament)。令人惊讶的是,在联赛中最终胜出的(收益最多、积分最高)方案竟然是设计最为简单的“以牙还牙”(TIT FOR TAT)的策略——不主动背信,但是一旦对方背信,立刻予以报复,一旦对方开始合作,立刻予以合作(参见Axelrod,1984)。此种“以牙还牙”策略的成功充分表明:第一,行动者会根据过去的互动经验来决定当下是否信任他人,是否与人合作;第二,行动者会通过惩罚手段来控制他人滥用信任的动机,确保自己的合作行为不被滥用。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我们在将信任的发生机制区分为经验主导的信任与控制主导的信任时,我们并不能将这二者视为相互排斥、互不兼容的。实际上,也存在着阿科瑟罗德设计的游戏中呈现的第三种信任,行动者同时根据经验与控制体系的状况综合考虑而做出的信任选择。
四、结论
作为理性行为的信任的发生,总是受制约于特定的交往性与社会性背景。行动者在决定是否信任他人时,常常需要评估他人过去是否可信、滥用信任的动机如何、存有什么样的控制系统来防止他人对其信任的滥用。由此,我们区分出信任发生的三种不同机制:经验主导的信任、控制主导的信任以及经验与控制并重的信任。在经验为基的信任发生机制中,行动者根据自己或他人与受信者的交往经验来判断其是否可信。过去经验里受信者的可信度越高,行动者越倾向于选择信任他人;过去经验里受信者的可信度越低,行动者越不倾向于选择信任。由于作为决定是否信任他人的经验既可能来自于行动者自身,也可能来自于行动者社会关系网络中曾经与受信者交往互动过的其他成员,因此,随着行动者关系网络密度的增加,信任水平也将相应提高。在控制为基的信任发生机制中,行动者根据现有的控制受信者滥用信任的动机的能力来判断受信者守信的可能性。这种控制为基的信任,是在对受信者滥用信任的可能回报的评估的基础上形成的。当行动者确信受信者对其信任的滥用将会受到惩罚,以致其回报不如珍重其信任时,行动者倾向于信任此人。否则,行动者则将保留自己的信任。在控制为基的信任发生机制里,托信人的社会网络以及正式的社会控制体系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现实中,行动者也可能同时根据经验与控制能力来决定是否托信他人。
经验与控制这两种信任发生的基本机制,对于社会信任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首先,信任是基于对成本与收益的比较的理性行为。在实际生活中,行动者是否信任他人的决定并不由个体的人格特征决定。其信任他人的倾向性,受制约于过往的经验及其对受信人滥用信任的动机的分析。因此,道德说教之于社会信任建设的功效值得质疑,除非这种说教能够增加信任的回报或者不信任、滥用信任的成本。其次,行动者所在的社会关系网络内的信息共享有利于促进信任水平的提高。如果关系网络内的行动者能够有效地交流、沟通关于受信人滥用信任的信息,滥用信任者未来要得到他人的信任会变得更困难,其滥用信任的成本将相应增加,进而导致其滥用信任的动机减弱。由此可推论,提高行动者分享有关受信人可信度的信息的意愿、促进这种信息的交流的措施将有利于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再次,对于受信者滥用信任行为的控制与惩罚,既可能来自于在信任游戏参与者所在的社会关系网络内发挥作用的闲言碎语(Gossip)、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也可能来自于由国家力量所制订的法律、规章等正式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一个公正、透明、高效的政府、法治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效的社会控制体系,可以显著促进社会信任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