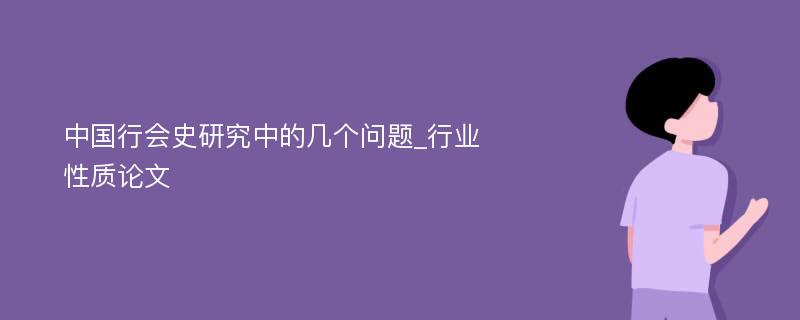
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会论文,几个问题论文,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的工商会馆与公所,亦即一般论著所说的行会,是中国进入近代以前就已存在的同业组织。这种传统的同业组织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曾在社会整合与经济运作进程中,产生过比较重要的作用。因此,行会一直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受到许多学者重视的课题,相关的成果也为数不少。从现有研究进展看,虽然成果甚多,但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需要加以比较和分析。本文拟就中国行会史研究中涉及的下列几个问题,在介绍和评论学术界观点的同时,谈谈笔者的见解。
一、中国行会的产生
中国的行会究竟产生于何时?早期曾有个别学者认为,中国“行”的存在最早可以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但这种说法并无多少依据。稍后也有人认为,在周末至汉代已有工商业行会存在。例如全汉升指出:说中国行会在远古已具有雏形,以及以为中国行会至少有二千年或二千年以上历史的说法,都难以得到证实。“然而,无论如何,从周末至汉代这个时候起手工业行会已有存在的事实了”[1] (P16-17)。但全汉升的这一结论也未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对行会始于何时这一问题并无定论,迄今仍有种种不同见解。
20世纪上半叶,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行会始于唐宋时期的“行”。日本学者加藤繁曾对唐宋时期的“行”进行过专门探讨,虽然他没有明确地说唐宋时期的“行”就是行会,但却认为“从唐代中叶以后到北宋中叶以后市制崩溃的时代,同时也是商业组织的行发展的时代”。加藤繁还特别指出:“行的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是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的机关。而共同利益中最主要的,大约就是垄断某一种营业。”[2] (P355)这实际上是认为唐宋时期的“行”已具有了一些行会的特征,是“有几分类似欧洲中世纪基尔特的商人组织”。
到20世纪50年代末,有的学者已经非常肯定地认为行会产生于唐代,兴盛于宋代。刘永成指出:“中国行会开始于唐代”,“到宋代,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行会也日趋兴盛”[3]。彭泽益也较为明确地指出:“一些散见的史料表明,至迟在八世纪末(公元780~793年),唐代已有行会组织的雏形存在。”他还说明“认为唐宋的‘行’不同于行会组织的观点,实际上,是忽略了中西封建社会的差异性,简单地以西欧行会为模式来套中国行会”;唐宋时期的中国行会虽然制度不甚完备,但它确已出现[4] (P5-6)。陈宝良不仅认为“中国商业性行会的组织,大概从唐代已经形成”,而且指出“这种商业社团与民间的宗教社团关系非浅”。因为在唐代,民间流行宗教“社邑”,而有些社邑则由商业同行合力组成。只是唐代的行会在行内自相分别,自成社邑,以避免与民间其他宗教社团相混杂[5] (P215-216)。另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有个别学者认为,“行会在中国的正式出现,应始于隋”[6],但赞同此观点者并不多。
不少学者对中国行会产生于唐宋时期的见解持有不同意见。其主要理由是:团、行系由官府出面组织,而且团、行并未制定与行会相似的规定,不可能具有行会的性质。例如傅筑夫强调宋代的“团”与“行”都不是商人自主成立的,而是缘于外力的强制,即因应官府科索而设立,并且主要是服务于官府,也没有任何管制营业活动的规章制度,因而并不是工商业者自己的组织,与欧洲的行会相差甚远,当然不能称之为行会[7] (P417)。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也认为,宋代的团与行虽然有时也维护工商业者本身的利益,“但它毕竟是官府设置的机构,不是本行业自己的组织,这与西欧的行会或基尔特的建立,有根本的不同。”另外,在行业内部也“并不贯彻均等的原则,存在着兼并之家和大小户分化的现象,也未见有限制开业、扩充或限制雇工、学徒人数的记载,这也与西欧的行会有基本的不同”[8] (P134)。
由上可知,关于中国行会究竟产生于何时,史学界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笔者认为出现严重分歧的焦点有二:一为行会是否只能由工商业者自行设立,不能由官府出面组织?由官府出面创立行会并加以某些控制或限制,是不是中国行会产生过程中不同于西欧行会产生的特点?这主要关涉到研究行会的理论与方法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二是唐宋时期的“行”是否具有限制竞争、保护同业垄断利益的行会特征?这方面主要只是史实的考订问题,需要发掘更多的有关史料进行更为充分的论证。
对于上述这两个关涉中国行会产生的焦点问题,笔者认为都应该结合中国长期处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来加以考虑。在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封建社会中,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与各级官府是不可能不发生关系的,事实上这两者也一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与此同时,工商业者同样不能不与官府发生各种关系。如果认为行会只能由工商业者自行设立,不能由官府出面组织,那么不仅在古代的唐宋时期,甚至到了近代,中国的工商业者也不可能建立任何组织。因为中国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近代,这种官府与工商业发展的密切关联始终存在,连近代各种新型工商组织的建立也与官府直接相关,甚至也是由官府出面组织的。例如作为近代中国新型商人社团组织的商会,之所以能够在清末的1904年以后能够迅速在全国各地相继建立,即是由于清朝商部奏准制定颁行了《商会简明章程》。该章程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省垣或埠,均应设立商务总会;商务发达稍次之地则设商务分会;前此所设商务公所等类似的商人组织,一律改为商会[9]。章程颁行之后,清廷又谕令各省督抚晓谕商人,劝导设立商会。商部也向各省颁发劝办商会谕帖,大力宣传设立商会的重要作用,阐明“商会一设,不特可以去商与商隔膜之弊,抑且可以去官与商隔膜之弊,为益商务,良非浅鲜[10]。事实表明,商会虽然是由官府出面组织的,但它成立之后,在整个近代中国都发挥了工商业者新型社团组织的重要作用。不仅仅是商会,近代中国同业公会的正式产生也同样是如此。1918年,北京政府农商部颁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及施行细则,首次在法律上承认了同业公会在行业经济管理方面的重要功能与作用,使工商同业公会很快得以普及。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将原《工商同业公会规则》修改为《工商同业公会法》及实施细则,1938年南京国民政府又再次颁布新的《商会法》和《同业公会法》。这些都可以表明,由官府出面督导建立工商组织,是中国古代和近代一以贯之的共同现象,也可以说是不同于西欧工商组织产生的一个明显特点。
另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由于留存的资料不充分,现在要想比较全面地论证唐宋时期工商组织在各方面均具有行会特征,显然难以做到。事实上,这种做法本身即有值得商讨之处。首先,此一论证的前提是以西欧的行会作为某种模式,套用中国的传统工商组织,与之相符者才承认是行会,反之则否认其具有行会性质。这样的思维路径,将西欧的行会视为固定不变的单一模式,显然有失于简单化和绝对化,忽略了各国行会之间的差异。因此,中国的行会在某些方面不同于西欧的行会并不奇怪。其次,唐宋时期是中国行会产生的初期阶段,这一时期的中国行会也不可能在各方面都像西欧的行会那样,具有典型的行会特征。任何事物在其产生的初期阶段,都很难在短期内即达到完善的程度,行会当然也是如此。而到明清时期以后,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演进,中国的工商行业组织即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出行会的特征,这说明中国的行会有其自身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进程。
其实,关于中国行会的产生特点,有些学者在论述行会产生的时间时已附带进行了说明。彭泽益认为中国行会的产生有中国的特色,它是在专制统治高度强化,宗法等级极其森严和富商大贾畸形膨胀的基础之上产生的,当然会有别于在政治分立、商业资本相对弱小的环境中,按马尔克原则组织起来的西欧行会。魏天安比较了中国与中世纪西欧社会、政治、经济的诸多不同,阐明在宋代行会产生的过程中,由于参加行会的人并不具有西欧行会成员所拥有的市民权力,大的工商业行会都与官榷商品和政府消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在经济上常常成为政府的附庸,各个行会只能在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前提下,谋求自己的存在和部分经济利益。“宋代是中国行会的初步形成时期,手工业与商业尚未分离,工商业者的力量也较弱小,因此,外部力量的干预较之明清时期更为强烈,是十分自然的。”[11]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封建制度存在着许多不同于西欧的特点,阻碍和延缓了中国行会的产生。汪士信即指出,中国和西欧的诸多不同是导致中国行会出现时间较晚的主要原因:一是我国封建制度所特有的官手工业和与之相适应的匠籍制度,限制了民间手工业发展,也限制了行会的产生;二是地方官府为科索目的而采用的编行制度,使手工业者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志组织行会,因为另组行会就是犯上作乱,被一概禁止;三是我国封建城市的成因和西欧不同,手工业者人数比较少,政治地位绝对地低,在封建政治的高压下,也很难组成自己的行会;四是在清代以前我国手工业发展程度低下,发展速度缓慢,还没有达到能够组织起手工业行会所需要的高度[12] (P238-241)。傅筑夫则断言,直至宋代,中国的手工业生产结构仍以家庭为基本核心,生产技术亦完全由家庭保密,这是中国手工业没有欧洲中世纪那种基尔特型行会制度的一个直接结果;反过来说,生产技术世代相传,每个生产者可凭家传的独得技术而独立自主地经营,并能在激烈竞争中保持着自己所开辟的市场,这一切使欧洲中世纪基尔特型的行会制度不可能在中国产生[13] (P345)。不能说上述这些因素对中国行会的产生没有产生影响,但是认为中国的行会因此而无法产生,则尚需做进一步的论证才能令人信服。
二、关于会馆是否属于行会的争论
中国的行会不仅具有不同于西欧行会的产生特点,而且在组织形式上也独具特色,以致在行会史的研究中同样引起了一些争议。一般而言,中国的行会包括公所和会馆两种组织形式,公所具有行会性质并无明显争议,但会馆是否属于行会性质的组织,在学术界尚存在一些争论。西方和日本学者早期在对会馆、特别是工商业会馆进行调查研究时,大多倾向于认为会馆是行会的一种组织形式。国内学者早期同样也大多如此,如全汉升明确指出:会馆一方面是同乡的团体,另一方面又是同业的组合,可说是同乡的行会。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大陆学者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也较多地仍然是将会馆等同于行会组织。
例如20世纪50年代末刘永成撰写的有关论文,认为在会馆制普遍出现后,会馆便成为中国行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可以看成是中国行会发展史上的重要变化[14]。李华认为明清时期北京的行会大体可分为三类,其中之一即是同乡同行或同乡数行商人,为保护自身的利益而建立的行会组织。稍后,李华还撰写另一篇论文进一步指出,工商会馆具有行会的性质,它从表面上看是以地域性而组织起来的,但有着共同的经济目的,有着为发展自己而制订的行规,因而不能一概视为同乡会[15]。
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有学者对明清时期的会馆是行会性质组织的结论提出了质疑。吕作燮接连撰写了两篇论文,认为将明清时期的会馆视作与西欧行会相同性质的组织,系沿袭早期日本学者的成见,是值得商榷的。早期明朝会馆与工商业者毫无关系,是同乡组织而不是同行组织,也并非工商业行会。对于苏州、汉口、上海等工商重镇的工商业会馆,吕作燮也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些城市的公所具有行业组织的特点,而行业性会馆同样多属于地域行帮组织,与行会有很大区别[16]。马敏认为不能不加区别地笼统将会馆看作是行会组织,他以明清时期会馆、公所数量最多的苏州为例,说明尽管苏州90%左右的会馆都与工商业有关系,但其中绝大多数只是以地域性商帮为基础的同乡会性质的组织[17] (P177)。还有学者认为会馆和公所都不能说成是行会性质的组织,例如谢俊美指出:“会馆公所同行会组织有联系,行会在相当程度上利用了会馆公所,加强对工人的控制,但它却不是行会这一类组织。”[18]
但是,也有不少学者针对上述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徐鼎新指出:将会馆、公所截然区分成不同性质的社会团体,是拘泥于会馆、公所的称谓,而忽视了对其实质的考察。就上海的情形而言,会馆、公所在一部分同乡、同业团体中是通称的。因而会馆、公所的名称既不是划分同乡、同业团体的标志,也不是区别是否行会组织的依据。[19] 王笛则以四川的会馆为例,说明“会馆在当时发挥着工商行会的作用”,因为会馆既是地域观念的组织,又是同业的组织[20] (P561-562)。彭泽益认为,“明清时期的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的结论在逻辑上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因为明清时期的会馆虽的确有一部分并非工商业会馆,但有的会馆则是属于工商业会馆,且为数不少。[4] (P13)
蒋兆成通过考察明清时期江南一部分地区的情况,明确指出:会馆、公所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产品的规格标准、市场价格、原料分配、学徒人数、年限等,均有比较具体的规定,所以其行会组织性质及其经济职能是非常清楚的[21] (P432)。吴慧通过综合分析许多地区会馆而得出的结论是:手工业会馆的行会性最强,专业性行业会馆次之,地域性包括几个行业的同籍商人的会馆又次之。纯地域性会馆(内部不分行业)只起着同乡共聚、祀神宴会以敦乡谊之所的作用,但这种性质的会馆数量并不多[22]。
还有学者阐明同乡与同业并不是划分会馆和公所的绝对标准,有些虽名为会馆,实际上却是同业组织;有些虽名为公所,却又是外乡工商业者团体。高洪兴以上海的会馆、公所为例,说明上海最早建立的商船会馆,即完全是行业组织。另外,“还有一些会馆、公所的组织者既是同乡,又是同业”[23]。彭泽益也指出:在一些地区,会馆、公所名虽不同,实则性质无异。中国行会机构所在地的名称除了会馆公所以外,还有许多名目,如流行于广东、广西等地的“堂”即是其中的一种,另有一些地区还以庙、殿、宫、会等名设立行会。范金民针对以上种种看法,认为会馆、公所有着一定的共同点,在名称上往往是相通的。考察其内部实质,应从地域或行业的角度,将会馆和公所分为地域性和行业性两大类。但他仍然认为只有行业性会馆、公所才属于行会组织。[24]
笔者认为,上述各家之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相比较而言,不拘泥于会馆、公所的名称,而对其进行具体的考察与分析,看其是否具有行会的特征,可能会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如果不加区别地笼统将会馆都等同于行会,确实存在着一些难以解释的问题。因为有些会馆主要不是由工商业者发起建立,建立之后也主要只是发挥联乡谊、敦乡情、襄义举的功能,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行会。例如明清时期的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五方商贾,辐辏云集,百货充盈,交易得所,故各省郡邑贸易于斯者,莫不建立会馆”[25] (P351),苏州也因此成为会馆数量较多的城市。但具体考察苏州迄于晚清的50余所会馆,其创建者一为工商业者,如钱江(绸商)会馆、仙翁(纸商)会馆、东越(烛商)会馆、大兴(木商)会馆、武安(绸商)会馆、毗陵(猪行)会馆等;二为地方官员和商人共建,如岭南会馆、三山会馆、江西会馆、邵武会馆、吴兴会馆、安徽会馆等,这类会馆也称仕商会馆;三为地方文武官员创建,计有湖南会馆、八旗奉直会馆两所。以上这三类会馆中,纯由商人创建者,属于行会性质的行业组织应无疑义。纯由地方官员创建者,在初期阶段属于同乡团体而非行业性组织也应无明显争议。而由地方官员和商人共建者,则需要进行仔细考察,不能轻易下结论。这类会馆通常存在着两种情况,一是兼具同乡团体和地域商人组织两种性质,二是商人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其性质也以商人组织为主,具有明显的地域或行业排他性,可以划为行会的范畴。
另外,也不能单纯以会馆由何人创建来判断其性质。有些会馆在创立时虽有地方官员参与,但建立之后随着各方面情况的改变而相应出现变化,官员的影响日益淡出,商人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逐步向行会性质的商人组织演变。如果始终囿于其创建者不单纯是商人,有地方官员参与,断定这类会馆一直是同乡性质的团体,不注意其建立之后的发展变化,也难免失之偏颇。还有些初建时仅为同籍商人的会馆,后来也发展成为行业性会馆,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例如苏州大兴会馆原为江苏各府木商所建,到道光以后允许他省在苏州的木商加入,成了木业商人的共同会馆。杭州线商在苏州建立的武林杭线会馆,在太平天国以后也请苏帮线商加入,变成了苏杭线商的共同会馆。
总之,在判断会馆是否属于行会性质的商人组织时,既不能简单笼统地说会馆都是行会,也不能说会馆都不是行会,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而且不能用凝固不变的眼光看待各个会馆,要以动态和发展的眼光作长时段的考察,这样才能避免简单化和绝对化的缺陷。
三、传统行会的功能与作用
外国学者较早即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探讨过中国行会的功能与影响。有学者认为中国行会在政治方面的势力与影响较弱,也有认为很强者。前者以魏复古、韦伯、梅邦等为代表,后者以哥尔、朱尼干等人为代表。日本学者清水盛光曾详细分析上述各家之说,其结论是中国行会在政治方面的影响是软弱无力的。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割据主义而受到外延的限定,另一方面因为国家官僚势力的存在而受到内涵的限定”,归根结底则是由于“都市之空气并不自由”。清水盛光还认为,“中国行会的特征是政治势力的脆弱性和其活动范围只限于经济生活”,换言之,行会在经济上对成员的统制力非常强大[26]。这一结论大体上是能够成立的,因为中国的行会确实在政治上不仅没有任何权力,实际上也较少开展这方面的活动。同时,中国行会在经济上对同业的限制与约束较为严格,由此可以说行会在经济上具有较强的势力。但是,将行会的活动及其影响仅仅限于经济一个方面,恐怕也与历史事实多少有一些出入。
在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行会无疑有其独特的功能与作用。特别是到明清时期,行会已较为普及,在各方面所产生的多重作用与影响更是令人注目。具体说来,中国传统行会的主要经济功能与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划一手工业产品和商品的价格、规格和原料分配;控制招收学徒和使用帮工的数量;限制本行商店、作坊开设数目和外地人在本地开店设坊;规定本业统一的工资水平。其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业内和业外的竞争,维护同业利益,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手工业和商业的运作具有某种规范作用。对中国传统行会在经济方面的这些功能与作用,许多学者都曾给予详细论述,而且认识也比较一致。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行会虽采取各种措施力图限制竞争,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会内部就因此而不存在竞争。事实上,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晚清时期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之后,即使是行会极力想限制竞争,也不可能完全达到目的。
另还应补充的是,除了经济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之外,中国的传统行会还具有西欧行会所不具备的某些功能。例如许多行会都十分重视联络乡谊,救济同业,办理善举,尤其是外地工商业者和商人建立的会馆、公所,更是将其作为重要职责。因为外乡人在他乡异地无论是经商还是经营手工业,往往会遭遇更多的困难,需要相顾相恤。传统的中国又是一个非常重视乡土人情的国度,外出经商者常常按地域籍贯形成商帮,遇事即互帮互助,行会作为工商业者的组织也自然而然地承担了这方面的职责。如同苏州蜡笺纸业绚章公所建立碑文所说:“身等朱蜡硾笺纸业帮伙,类多异乡人士。或年老患病,无资医药,无所栖止;或身后棺殓无备,寄厝无地。身等同舟之谊,或关桑梓之情,不忍坐视。……现经公议,筹资……建立绚章公所,并设义冢一处,……身等同年,轮流共襄善举。”[27] (P98)这些救济同乡或同业的善举活动,大大减轻了工商业者的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那些贫困无依的工商业者在有病求医和死后安葬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同时还增强了行会的凝聚力,对于吸引工商业者加入行会也不无影响。
组织同乡或同业商人举行供奉祭祀活动,是中国行会在宗教方面的功能与职责。在中国民间,祭奉神灵的迷信思想较早即比较盛行,工商业者也不例外。在“五方商贾,辐辏云集”的东南都会苏州,“各省郡邑贸易于斯者,莫不建立会馆,恭祀明神,使同乡之人,聚集有地,共沐神恩”[27] (P350)。行会供奉的神灵,一般来说可以具体分为乡土神、行业神和财神三类。同乡工商业者组织的行会多供奉乡土神,打破地域的同业行会则多供奉行业神,俗称为“祖师爷”,供奉财神则不受地域和行业的限制,比较多的是将关公这位在中国历史上以侠义肝胆而闻名,绝不见利忘义的著名人物作为财神。行会除日常供奉神祗,每逢所供神灵的祭日,更是隆重举行宗教性的祭祀仪式。“无论是以乡土神、祖师爷或财神为崇祀对象,藉着对这些工商业者可以依赖的神祉举行共同崇祀的宗教活动为号召,确实是各工商团体发起人得以招募成员进行结社的一项有效手段,是团体组织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透过团体组织的共同举办祭祀活动,更可以使祀神活动办的更有规模,吸引其他工商业者加入结社。”[28] (P90)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功能与作用,行会还具有其他一些功能。例如行会通过制定一系列的规范,包括对产品质量的严格要求,对相恤相助的提倡,在道德方面可以培养成员勤勉、信用、互助和提高人格地位的积极功能。不仅如此,行会的社会功能也不应忽略。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开始重视对行会、尤其是会馆的社会功能进行深入研究,这称得上是一个新的拓展。王日根的专著《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即是探讨这一新问题的力作。该著论述了明清会馆对地方社会整合以及中外文化整合的影响,说明会馆是流动社会中的有效整合工具,也是对家庭组织的超越,以及对社会变迁形势的适应与创造,在推进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邱澎生的博士论文《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1995年)是着力研究商人团体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与影响的代表作,邱文主要从结社法令、经济政策、市场经济、都市社会四个方面,考察了会馆公所和商会等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尤其是对会馆、公所的功能与作用提出了不少新的学术见解。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地区的会馆、公所在地方事务中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例如清代上海会馆、公所在地方事务中即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具体表现主要是对地方公益事业的捐助、对地方政府所需行政经费的报效以及代办某些政府税捐、代地方政府对同乡成员实行有效的管理,以及当晚清社会剧变之间对地方自治的积极参与等几个方面[29]。事实上,那些具有行会性质的会馆在功能方面是不断扩展的,“会馆的设立,起初主要目的是在保护各省间往来贩运的商人和远离家乡移民的权益,但后来会馆逐渐发展到在政治、宗教、社会各方面都有相当影响的机构”,各会馆都有“首事”与地方官进行公务联系,参与当地税捐征收、消防、团练、重大债务清理、赈济款项的筹措和发放、育婴堂和其他慈善事业的管理、济贫和积谷等,由此愈来愈多地参与地方事务,在许多城、镇、乡,地方事务若没有会馆首事的参与是难以进行的。
不过,学术界在早期论述行会的作用时,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认识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例如,行会是否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就是一个意见分歧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行会限制同业竞争、保护同业独占垄断利益的功能,必然会阻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期黎澍指出:“行会制度是与资本主义经营相反对的制度,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才可能被突破,并使得在它控制下的手工工场成为资本主义的。”[30] 20世纪60年代初期,彭泽益曾提出“行会组织妨碍着城市手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已为大量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结论”,并认为在中国封建城市的行会中很难产生出资本主义萌芽,例如苏州的丝织业揽织形式的生产,“只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在逐步摆脱了劳役义务和行会强制的基础上……才取得了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的意义和性质”[31]。
当时,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刘永成指出:在清代苏州地区的各业作坊中那些带有浓厚封建性的行会陈规,还保留了下来。这些规章制度虽然阻碍着手工业作坊的进一步发展,但它确实对于当时手工业作坊的生产活动不起主要的作用。从表面上看行会的规定十分繁杂,对会员的限制也很严格,但不能从形式上去看待这些条规。清代手工业行会在限制手工业的经营和发展方面,确实起着一定的作用,但这仅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分工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商品经济的活跃所引起的自由竞争的发展,反过来又影响着行会的发展和行规内容的变化。因此,“行会的限制作用,必须由客观物质条件来决定”。就苏州的具体情况而言,“不是自由竞争被禁止,而是有所发展”[32]。洪焕椿以明清苏州地区的工商会馆为例,也认为应该肯定其积极作用,“根据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所反映的具体情况看来,把会馆、公所不加区别地一概看作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封建行会组织,而看不到它在商品竞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33]。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主要即是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该著考察明后期几个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后,认为“并未发现行业组织阻碍萌芽产生的事例”。另还通过对清代若干行业手工业公所的分析后,得出结论说这些手工业性的公所,主要是技艺性行业和饮食、服务性行业,与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行业无关。“这就是说,有公所和行规的手工业性行业,大体未见资本主义萌芽,而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行业,却少见公所组织的行规。”该著比较强调行规的有无,认为即使像佛山的冶铁业、景德镇的陶瓷业、苏州的染坊业、上海的沙船业,虽确有会馆或公所组织,但是经过考察,“这些组织并无行会性质的行规,也未对资本主义萌芽起什么阻碍作用”[8] (P305)。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认为:清代前期的行会对手工业的发展起着束缚、延缓的作用,但不能过分夸大,那种认为凡是有行会存在的行业中,就决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即过于机械呆板[34] (P398)。
20世纪90年代以后,彭泽益认为史学界对行会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一直存在着矛盾的和模糊的认识,使之成为长时期扰人困惑的问题。完全否认某些行会对当地本行业中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起了阻碍作用的观点,是一种回避事实的态度。因为“行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阻挠和干扰资本主义的兴起,已为大量历史事实所证明,几乎成为尽人皆知的历史常识”[4] (P20-23)。但是,范金民以清代江南的公所为例,说明其创立宗旨和所处的社会背景与西方行会不同,它并没有像西方行会那样限制内部竞争,垄断外部市场,严重阻碍生产的发展。江南行业性会馆公所的不断增多,实力的不断壮大,是江南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标志,它们是江南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促进和有利于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个别行业公所在招收学徒、生产规模、商品价格等方面的种种限制,束缚了同业的手脚,不利于行业的生产和发展,但这样的公所不占主流,发挥的作用更属有限,不能以这样的公所来理解和评价江南所有的公所[35] (P271)。
应该承认,行会在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比较复杂,其中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影响。在考察这一问题时,也应注意区分不同的历史时期,当商品经济需要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特别是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之后,传统的行会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不仅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而且也迫使许多行会不得不进行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