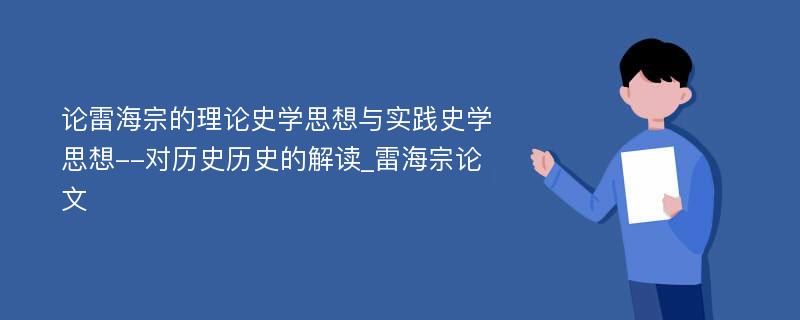
论雷海宗的理论史学与实践史学思想——解析《历史过去的释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释义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过去的释义》一文,(注:此文原载于1946年1月13日的《中央日报》(昆明版),2002年由王敦书先生编入《伯伦史学集》。)系雷海宗先生58年前的撰述,此文篇幅虽是短小,思想却为精博,涉及到了历史学内诸多重要的问题,诸如,关于历史认识论和历史价值论的一些问题。它虽非专为学术而作,却具有颇为可观的学术价值;进而言之,其思想价值更甚于学术价值。笔者将从此文切入,对雷海宗的理论史学和实践史学思想进行三个方面的论析。
一、辨析历史
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历史学界掀起了一场颠覆性的变革,以梁启超等人为首的一批学问大师,对传统史学进行了深刻批判,拓宽了中国历史学界研究的领域,增多了历史研究的方法,提出了不少的史学主张,成果繁多,流派辈出。但是,在历史研究领域内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的同时,史学认识论方面的探究却是极少人问津,没有多少推陈出新的迹象,尽管出现了一些为时人奉为圭臬的史学观点,但要么缺乏理论提升,要么失之于一端,(注:近代以来的史学大家,诸如,梁启超认为史家要“有心识”、“怀哲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陈寅恪的“诗史互证”、顾颉刚的“考而后信”,傅斯年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的工作就是整理史料”,这些基本上是一些新的史学方法论,虽不乏真知灼见,却较少涉及“历史的性质是什么”的认识论问题,并且他们这些思想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少有人能从哲学的高度全面深刻地看待历史,当时中国的史学认识论研究发展显得有些停滞。
雷海宗先生在《历史过去的释义》一文中提出了“过去为二”的历史观,(注:王敦书先生在多篇文章中谈及或论述了雷海宗先生这一理论,如《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雷海宗》(载于《世界历史》1995年第6期)、“《西洋文化史纲》导读”(见《西洋文化史纲》雷海宗撰 王敦书整理、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伯伦史学集〉前言》(此文以《雷海宗的生平、治学特点和学术成就》为题刊于《历史教学》2003年第2期)诸文;侯云灏先生也在《雷海宗主要学术贡献述论》(载于《烟台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4期)一文有所论述;本文此处与以上论述的侧重点和分析方法有所不同,其文意在述评,本文志于阐发。此外,“历史”和“过去”,尽管二者有很大程度的语义重合,但毕竟不是同一概念,“过去”是相对于“现在”而言,“历史”则是相对于“现实”而言;在应用的具体情境中,实难将二者明确区分;并且,雷海宗先生在文中有几处将二者联用,虽似为不科学,却有深层意义,这与其独特的历史概念有关,请参看本文第三部分。)认为历史有两种,一种是“绝对的”,是客观的,是历史中的过去,也即历史现实与历史事实;一种是“相对的”,是主观的,是史学中的过去,也即历史认识和历史学中的事实;同时,两者都具有真实性,仅是意义层面上有所差异。(注:于沛先生在《历史认识中的“历史事实”问题》将这一问题进一步细化了,文载于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卷;同时,英国历史学家W·H·沃尔什和美国历史学家克尔贝克尔也有相关论述(其汉译文,分别见,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一辑“古典传统与价值创造”,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231页,以及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82-299页)。)这一别具一格的史学见地。可以说是对当时史学理论研究的一种提升。
“把过去的事实看为某时某地曾经发生的独特事,而不问它与再远的过去或再后的未来的关系。把它看为超然而独立的既成事实,那个过去是固定的,是已定的,是一成不变的,是万古如此的,是绝对不可挽回的”。(注: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59页)这就是雷海宗所说的“绝对的”历史,它是历史中的过去,是历史事实。它是否发生,或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发生,都是不为人类意识所改变。他还举了长平之战等实例来说明。人们不能否认历史上发生了这次战役,除非当时的战场不在长平,或战场不在长平,而只能换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它,例如,“周赧王五十三年”的秦赵决战;不能否认它的结果“秦败赵”,除非不是这场战役,或当时战场上作战的双方不是秦赵,而只能说某些秦军被某些赵军打败或“赵败于秦”。这些“绝对的”历史,“都已过去,就已经过去的方面言是永不会再改变分毫的,已经如何,就是如何,任凭后人的如何赞成或如何反对,也不能把这些事实取消,修改或增删”。(注: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59页。)这种“绝对的”历史,作为一种客观实在,其意义和价值是主观认识的产物,是人们赋予的,“对于过去只能就他对于现在的看法与对于未来的希望而给它一个主观的意义”;(注: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3页。)但由于人们无法认知这种历史,(注:“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事物是纯粹的可知,或绝对的不可知”,“历史可以认识,但决不等于说,历史是可知的。如果可知的本意是全知,那么,历史就是不可知的;如果可知的原意是有所知,那么,历史就是可知的”(雷戈:《哲学主义的历史》,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52页)。本段下面几处文字所说的“历史不能为人们所认识”,是绝对意义上的,“可知”即“全知”,“不可知”为“不可全知”。)正如他所言,“孔子之为孔子,已经过去,万古不变,但这个绝对的孔子,我们永远不能知道”,(注: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0页。)对于历史的本貌,无论是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来说,我们无法完全探知,也不可能完全探知,这就导致人们赋予它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义和价值。不能认知或完全认知,是因为,我们研究历史时,不是直接与历史形成互动,而是通过记载历史的文献、史书等历史文本来认识历史。历史是生动的和全景的,而历史文本却是死板的和切面的,历史文本不可能将历史的本貌完全地、准确地反射出来。就孔子一例而言,“不只文献漏载的孔子生活事实或日常琐事,我们无法求知,专就文献可征的孔子嘉言懿行而论,某一嘉言,某一懿行,孔子说时作时的心情,原因,背景与目的,我们大部分也永不能知”,(注: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59页。)我们所认识的只能是历代文本中的孔子。并且,由于历史和历史文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二者只有通过“转义”才能联系在一起,而“转义是所有话语建构客体的过程,而对这些客体,它只是假装给以现实的描写和客观的分析”,(注:[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版,第2页。)以至于通过分析历史文本来认识历史的历史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类似于盲人摸象的活动。历史文本数量的增减不会影响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本身的变化,进而言之,即便是把所有历史记载和表述总和起来也不能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在雷海宗看来,历史事实是人们,包括历史学家在内,所不能认识的,能认识它的只有那些“宗教家的上帝,哲学家的天理,文学家的造物主”,他们(她们或它们)“可以刹那间而纵观过去,俯视现在,而明察未来,一眼而见全体,能明了历史的整个意义与绝对意义”。(注: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3页。)总之,这种“绝对的”历史,并不是“普通历史学的历史知识”,“当为一种哲学的见解则可,作为一种文学的慨叹对象也可”。(注: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59页。)
而什么是“普通历史学的历史知识”?这要涉及到另一种历史,即“相对的”历史。雷海宗认为,“史学的过去是相对的,是瞻前顾后的”;“一件事实对于已往的关系,对于未来的影响,在当时的地位,对今日所有的意义,都必须研究清楚,那件事实才是真正的历史知识,才成为历史学的事实,才有意义,才是活的”。(注: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59-260页。)这一历史不同于“绝对的”的历史,后者只具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不具有逻辑上的前后联系,是“超然而独立的既成事实”,而前者不仅仅具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还更多地具有逻辑上的前后联系(注:卡西尔认为,历史现象的连续性,“既是逻辑意义上的也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其具体论述见,[德]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李小兵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72页。)——“对于已往的关系,对于未来的影响”,是“瞻前顾后”的;后者是客观事实,“是已定的,是一成不变的”,而前者是“理智的和想象的综合”,(注:[德]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李小兵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是“活”的,是不断变化的;后者强调的是它的历史真实性,它的原本情况是怎样,而前者强调的是它的现实真实性,它于今具有何种意义;后者是“既成”、不能“取消,修改或增删”的,前者是后生的,是人们对“既成事实”的解读和再创造,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对过去的活动认识”;(注: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2页。)后者是全面的、整体的,而前者是片面的、局部的。总之,史学中的历史是具有浓厚主观色彩的、文本性质的历史,与历史现实相对应,是人类意识的产物。
在篇首,雷海宗就讲到,“我们用‘过去’或‘历史’一词时,实际就有两种不同的意义,而用时又往往把两义混用而不自觉。这种不自觉的混淆,是许多误会的来源。”(注: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59页。)语句虽短,却是一语中的,直指传统历史观念弊端的要害。这一高度注重史料而极端忽视思辨、不能将客观历史和主观历史区分开来的无意识错误,正是中国的历史研究出现多有量的积累而少有质的提高的奇怪现象的症结所在。总而言之,雷海宗在遵循中国旧有的辨伪求真复原的史学传统的基础上加以突破,着眼于寻理求义致用,从哲学的高度来分析了历史性质和如何理解历史的问题,这一论析为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二、重构历史
从“历史”的第二种含义,即史学中的历史,我们可以推演出另一个论断,在认识历史的同时,我们更多的是在重构它,进而塑造一个新的“历史”,这种历史既是有别于历史现实的又是从这一母体中诞生出来的历史文本。可以这样比喻,历史现实犹如真迹,而历史文本就是历史现实的摹本;在真迹不可求得的情况下,摹本的实用价值显得尤为重要;并且,人们在临摹摹本的时候往往是将其作为真迹看待的,书法爱好者在临摹《兰亭序》的唐摹本(冯承素本最佳)时,不认为自己临摹的是冯承素的字体而认为是王羲之的字体,以至于摹本在某种意义上取代了真迹的地位;历史文本也是如此,也在某种意义上取代了历史现实的地位,甚至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也认为是在研究历史现实本身而不认为自己是在研究历史文本,自己所说所讲的是在复原历史而不是创造新的历史文本。(注:“展现所有的事实,让它们为自己辩护”和“这不是我讲,而是历史通过我的嘴来讲的”,这是客观主义史学家的典型言论,其详细论述,见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的《什么是历史事实?》一文(其汉译文,辑于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正是基于对这一认识误区的发现,雷海宗先生在文中提出了当代人重构过去历史的观点。“我们生于现在,创造未来,这是人所共晓的,一般所不注意的,是我们也创造过去,每一个时代所认识的过去,都是那个时代的需要、希望、信仰、成见、环境、情绪等所烘托而出的。以上种种,没有两个时代完全相同,所以同一的过去,也没有两个时代对它的看法完全相同。”(注: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0页。)当代人依照历史现实这一真迹以自己的方式制造了摹本式的历史文本,不同时代的后代人又根据本时代的实际情况照着以前的摹本式的历史文本以自己的方式制造出又有所不同于前人的摹本式的历史文本,这样就赋予历史了多重面孔,并且,这些面孔又是次第变化的。雷海宗仍以孔子为例,通俗地阐述了他这种史学思想。孔子的本来面孔,我们无法复原,只能从后世的文献资料里看到他的多重面孔中的一个或多个。在孔子百年后的《论语》中,他被“看为圣人,看为诲人不倦的大师,看为不得志的大才,看为中国传统与正统文化的提倡者”;再后百年的《荀子》中的孔子就“远不如《论语》中的孔子之超然”,具有了“争求仕进”的一面;到了汉代,“孔子又变成为素王,成为后世定治平大法的未卜先知的神人,成为黑帝之子,有人母而无人父,成为微言大义的《春秋》作者”;(注: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0,261页。)其后虽有变化,仍是推崇尊拜的对象;而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以来,出现了“孔子万恶观”,孔子遭到新文化干将们的猛烈挞伐,“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注:李大钊:《孔子与宪法》,《新青年》2卷2号,转引自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92页。)其流毒“不减于洪水猛兽”。(注: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2卷6号,转引自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92页。)总之,原本的孔子不能求得,唯能求得的是历代历史文本中的孔子,不同时代的人们,在不同的环境中,根据不同的需求,以基本相同的历史文本为素材,不断地塑造着不同的孔子;而这些不同的孔子从某些角度看又是真实的、同一的。如孔子一样,历史中的过去不能尽知,唯能尽知的是史学中的过去,它们不过是数量上有所增加而质量上(针对真实度而言)有所变化的、已失“真迹”的摹本而已。
为什么当代人能重构过去的历史呢?原因有二。客观上,历史学作为“仅仅只是具有经验性上的确定性的知识”,它的推理和结论,与数学中的一加一等于二这种纯逻辑推理不同,都不具有“不可置辩”的“确定性”;(注:[德]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邓晓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并且,它是通过研究记录和反映研究对象的载体(或媒介)——历史文本——来认识它的研究对象即历史现实的,“往昔已逝。它已经过去,仅能由历史学家通过大不相同的媒介,诸如书籍、文章、纪实作品(documentaries)等等,而不是作为实际发生的事件再现于世人面前”,(注:Keith Jenkins,Re-thinking history,Routledge,1991,p.6.)由于载体(或媒介)众多,而记录和反映历史现实的方式又不是一式的,所以,对同一对象的认识便出现千人千面、百代百姿的现象。主观上,人们在认识历史时,总怀有一定的价值观,要问它的意义何在;然而,“但一谈到活的意义,与此时此地此人此景有生动关系的意义,问题就复杂了”,“没有任何一种事实能有百世不变的意义。此代认为第一等重要的事,彼代认为无足轻重。此地认为可赞的事,彼地认为可憾。此人认为平淡的事,彼人认为意味深长”;(注: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0页。)在特定的价值观的指导之下,符合“此时此地此人此景”的价值取向的就是历史,否则便被视为杜撰,被排除在历史之外;更有甚者,为了某种需要而对历史涂脂抹粉,有意塑造出一个新的“历史”。即便是力图复原历史原貌的历史学家,也在不自觉地制造着新的历史文本,他的研究有赖于“那些我们称作历史文献和历史遗迹的东西”,他“不仅要搜集这些(对历史现实的理解)断片,他还必须完善这些断片并对它们加以综合,把它们纳入一个前后一致的秩序中,向我们揭示它们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这种理智的和想象的综合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注:[德]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李小兵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82、83页。)所以,历史学家复原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更像历史现实的历史文本而已,而不能视为历史本身。
在雷海宗先生看来,“绝对的真实永难求得,即或求得也无意义”,而“有意义的过去,真正的历史知识,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对过去的活动认识”。(注: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2、263页。“活动认识”,疑为“活的认识”之误(此系王敦书先生指出)。)这一思想,与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思想有某种契合,“收集死凭证与写下空洞的历史是一种替生活服务的人生活动”,“当生活的发现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目前被我们看成编年史的大段大段历史,目前哑然无声的许多文献是会依次被生活光辉所扫射,并再度发言的”。(注:[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页。)二人都认为,人类精神是历史的灵魂,是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关键因素;历史一经发生便成为无意义和价值的“死历史”,而记载它们的文献资料的价值,仅在于后世人需要给某段“过去史”赋予新的时代精神,即“再变成现在”时而为之服务;总之,随着时代的演变,同一历史也随之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和阐释而“复活”,从而显示出不同的“真实”面孔。
三、创造历史
尽管雷海宗和克氏的观点有共通之处,但两人的着眼点不尽相同,作为理论家意义上的克氏关注的是历史认识本身,而有政论家倾向的雷海宗则更多注重它的现实意义,也即历史如何为现实服务进而创造新的历史的问题。(注:雷海宗先生,曾经精心阅读并翻译过克氏的这本《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的某些章节,其中的一部分在《史学》第一期(1930年,光华书局出版)刊发,其译文多有独到之处,但为保持本文的文风一致,所引克文,仍采用傅氏译文。从《过去历史的释义》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克氏的史学思想,既有吸收又有创新,其细节非本文所关注,故略而不述。)
“关于过去的每一新发现都会改变我们对现在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期望;另一方面,当前状况中的每一变化和对未来期望的每一变化都会修改我们对过去的认识(revises our perception on the past)。在这一复杂的背景里(in this complex context),显而易见,历史是作为对过去的反思——从未与现在和未来隔绝的反思——诞生的。”(注:Ernst Breisach,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eval & moder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2nd ed,p2.)在某种意义上,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不会间断的连续体,它们之间的连续不仅仅是时间上的次第替换,而更多的是在相互影响、互相渗透的互动中的演化推进。并且在这种互动中,三者会逐渐明朗化,首先,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过去的认识会不断修正进而接近过去的事实本身,如尼采所言,“有关过去的言语(der Spruch der Vergangenheit)一直是一种神谕(ein Orakelspruch),只有成为未来的构建者之时,了解现在之后,他才会理解它”;(注:iiFrederick Wilhelm Nietzsche,Nietzsche Werke(Band I),Alfred K? rner Verlag in Leipzig,1923,p337)其次,随着历史经验的增加,人们对现在的认识会更加正确,它并且还会在未来的实践中得到检验;最后,对过去的理解和思考逐渐理性化,和对现在的认识更加正确,都将有助于对未来的预测,使之更加科学化,从而使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缩小,理想会在那个人们预期的、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上变为现实。所以,以过去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不仅仅是关于过去的考证学问,而更多的是作为对过去的反思来指导当前活动和服务于建构未来的学科出现的。在历史的长河里,随着时间之流,过去、现在和未来,不断在推演置换。“人们如果对历史学不感兴趣,那么,可以断言,他将因此失去对社会、对人生、对生活、对命运这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系统性理解”,(注:雷戈:《哲学主义的历史》,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44页。)也正是因为关注这些问题,人们才到历史中寻求可资借鉴的事例、方法、观念等。“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注:[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页。)对历史的关注,其实质上也就是对现实的关注;恰如伯伦先生所言,“我们对于过去的了解,也是我们今日生活不可分的一部”,(注: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2页。)无论对过去如何理解都要从现实生活出发、为现实生活服务,将历史思维融入到现实生活之中。各个时代的人们认识过去的历史,是基于自身所处的活生生的现实,为超越旧历史创造新历史服务。正是生活在鸦片战争以来这个风云际会社会激变的时代背景之下,出于对中国时局的关注和民族命运的忧思,在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下,深刻分析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雷海宗才提出并论证了独特历史分期理论——“中国文化再生说”。(注:许多学人用“中国文化两周说”或“中国文化三周说”来概括雷海宗这一史学思想,此类做法实为取其名而失其实,雷先生这一思想的要旨在于强调变和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他认为中国文化可以通过吸纳外来文化来实现自我更新和“再生”,而没有在时间上和周期上加以限定;此学说的创立旨在唤醒国人为中国的民族存亡和文化续绝既要自信又要努力,正如他的原话所说,“第二周文化已是人类史上空前的奇迹;但愿前方后方各忠职责,打破自己的非常纪录,使第三周文化的伟业得以实现!”(见辑于《伯伦史学集》中的《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从学理上看,它是一套对中国历史演进历程的一个更理性和更形象的论证分析;(注:那种以五种生产方式的演变来套中国历史发展的做法,在当今史学界基本上被放弃;按朝代划分中国历史的做法,基本上仍在流行;以“中华帝国”的观念来考察中国历史的做法逐渐为时人接受。不管理论上的合理性成分有多大,它们都只能停留在学理探究的程度而缺乏实践性。)从实践上看,它能给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以一个更清晰明确的定位——处在中华文化交替更新的阶段,为我们民族的未来走向指明了一个大方向——中华文化的复兴。
过去、现在、将来这三者,不仅在学理上联系密切,并且在实际中更是密不可分,生活现实中的人,几乎同时生活在这三个世界之中,“他们(科学家们)发现我们将其作为‘现在’、‘感觉到的’现在实际经验的时间跨度(the span of time)大约仅为五十分之一秒长”。(注:Ernst Breisach,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eval & moder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2nd ed,p.2.)也就是说,科学研究表明,我们所谓的“现在”事实上仅仅有五十分之一秒的时间,此前为过去,此后为未来,致使常人无法将三者在实践上区分开来。而学理上将三者区分开来,仅仅是为了方便研究而已。若将这一学理上的区分应用于现实生活,无异于按图索骥的蠢行。雷海宗正是察觉学理上的过去、现在、未来与现实生活中的过去、现在、未来有不能套用的差别,认为历史研究不能画地为牢,不能割裂过去、现在、未来之间联系,机械地、片面地看待历史,而应该在纵向上和横向上拓宽历史研究的视界,将立足点延伸到未来,打通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壁垒。这样就突破了一般史学上的历史概念,从纵向整体史观(注:雷海宗先生的整体史观有两种,一种为横向的全史观念,在他的《西洋文化史纲》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另一种为纵向的通史观念,体现在他的“中国文化再生说”理论。)来考虑,赋予历史以新的意义——过去、现在和未来都被视为历史的一部分,这种历史概念具有浓厚的哲学意义。(注:安希孟先生在《历史和历史哲学》(文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一文中阐述了史学和哲学上的两种不同的历史概念的区别。在看待问题之时,雷海宗的历史观和哲学观是浑然一体的。)由是,历史研究必须关注现实和构想未来。并且,对未来进行构想,不仅在学理上需要,而且在现实实践中也同样需要,“在我们探索未来时,仍需要历史学家在多方面提供建议:需要他们去发现未来人类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设置一种前提并确定人类活动的范畴、潜在的可能性以及因果关系”。(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雷海宗不仅在学理上强调历史的整体性,并把这一思想贯彻到实践之中,强调历史学对现实实践的指导意义,认为历史研究虽然是以过去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它的最终目的却是指向未来的。诚如顾准先生所言,“历史的教训所能照亮的只是未来,而未来倒确实有待于历史去照亮它的”,“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的现实,和规划未来的方向的”;(注:顾准:《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327-328页。)只有这样,历史学才具有真正的完整意义。
从根本上讲,历史学是因“我是谁,从何而来,向何处去”这三个基本问题的提出而产生,也必将为解答这三个问题而存在,并且为之不断展开。雷海宗反对不顾现实的历史思考,反对将历史学仅仅视为考据学或史料学,注重历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历史学的现实性和有用性,并且提出劝告,“历史的了解是了解者整个人格与时代的一种表现,并非专由乱纸堆中所能找出的一种知识”,“有心的人,为何不抖去由堆满败简残篇的斗室中所沾的灰尘,来到海阔天空的世界大吸一口新鲜的空气!”(注:雷海宗:《历史警觉性的时限》辑于《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3,216页。)在他看来,历史学家具有双重身份:对过去的考古者和对未来的预言家。认识和复原过去的历史仅仅是他们任务的一个方面,其另一方面,意义更为重大一方面,是为认识现实情况进而创造新的历史提供长远预测和智力支持。只有如此,才能证明和实现历史学的学科价值、历史学家的身份价值以及既生活在现实中又生活在历史中的普通大众的人生价值,他创立“中国文化再生说”的意义正在于此。
由上可知,一方面,雷海宗非常注重现实和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反观历史,对其进行重新解释,并赋予它新的意义;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注重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前后联系,不管对历史如何重新解释或赋予什么意义,都不仅仅是为了描绘出一个对现实无用的历史摹本,更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将这种新解释和新意义化为人们思维的一部分,培养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历史使命感,激发国人推动历史发展的热情和信心,创造未来,“独创自己满意的新世界和文化”。(注:雷海宗:《历史的形态与例证》辑于《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57页。)
总而言之,雷海宗是一位“双料”的历史学家,既能在书斋里做一些与现实关联不大的考据和理论研究,并取得突出的成就;又能走出书斋关注时局,思往追来,独创“中国文化再生说”,并将它贯彻到实践中,鼓舞时人为中国文化第三周的兴起而努力奋斗。在《历史过去的释义》这篇文章里,他主要探讨了历史的两种含义、史学中历史的主观性和时代性以及研究历史的现实性及其未来指向性等问题,提醒学人注意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历史,告诫既生活在现实里又生活在历史中的人们,不仅要重构过去的旧历史,而且更要努力创造现在和将来的新历史。这三个方面的论析,构成一个有机整体,首先,正本清源,指出历史或过去是具有主客观之分的,从认识论上纠正中国历史研究自古以来存在的根本性错误,还给历史学一个客观理性的面孔;其次,开源引活,历史研究必须体现一种时代精神,在求真的基础上赋予历史以新的意义,给中国的历史理论研究开辟了一块新天地;再次,汇渠成川,从价值论上来肯定历史学长久存在的生命力不仅仅在于对过去的求真更在于对现实和未来的致用;最后,百流归海,他将这三方面融为一家之言,形成了他有别于当时众多流派的史学思想。虽然存在着总体架构略显粗糙和个别结论稍有偏差的瑕疵,(注:雷海宗先生的这些史学思想,放在一个学术开放和思想客观的时代里审视,其理论基本上没有什么错误,仅仅是有一点主观主义的倾向,这一错误倾向没有使他走上历史虚无主义,却为他的史学思想注入了巨大生机。惟有的不足是,历史没有将机会赠与这位历史学家,让他有时间来对这些思想进行认真反思和更细致的阐述和更缜密的论证,有关他这些史学思想或者历史思想的修补工作就只能遗留给我辈和我辈之后的学人来完成。在历史研究中,我们不能仰视或俯视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样都得不到客观的结论,而应该以平视的眼光对之。排除政治威权之下的衍生物和人身攻击之外,学理上对雷氏思想的研究仍然存在着误区和空白,雷海宗的思想是在强调历史研究和历史认识中的相对的和主观的成分,将这一认识扣上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帽子实为不妥;其实,雷海宗先生是一位求真与致用并重的历史学家,在学术上强调历史学的求真性质并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在实践上注意历史学的致用价值并将其学术成果应用到现实之中,而这种应用不是在杜撰屈枉历史事实之后的功利主义应用,我们是否应该就此给雷先生再扣一顶实用主义的帽子呢?对于这么一位受过中西两种文化熏陶和研究领域广泛的大师,我们是否应该轻而易举地对其思想做出客观准确的分析和评价?)但对当时的历史学界来说,这些思想可谓独具慧眼,少有人能够企及;并且,也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他提出“中国文化再生说”,勾画出了中国历史演变的独特的画面,虽然已过去多半个世纪,这一理论至今仍有不容低估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只惜,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数十年以来,它们或遭曲解误读,或受批驳斥责,亟待世人给予正确的解读和客观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