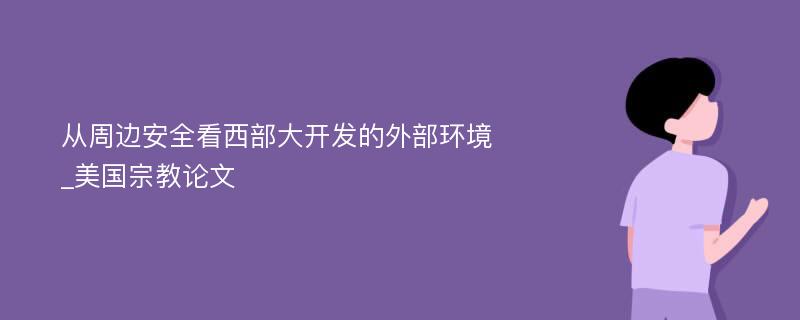
从周边安全看“西部大开发”的外部环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开发论文,外部环境论文,全看论文,西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剧烈的地缘政治变动,有助于中国经由古代的“丝绸之路”和欧亚腹心地带建立一条方便进入中亚、西亚、南亚以至欧洲的陆上通道。随着我国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随着近期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正式启动,“西到”的概念不再只是对历史的丰富联想,而是被赋予了崭新的意义。利用传统陆路通道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现代化的立体交通,加强与外部国家的经济及其他方面的联系,以此推动边疆地区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发展,这一思路近年来在国内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和认真研究,实践方面也作出过一些有益的探索。但是,伴随扩大开放而来的周边安全问题同样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只有以最小的战略成本克服来自外部不稳定因素的负面影响,我们才能在扩大西部开放的同时确保国家对外安全和维护西部地区的安定局面。
一、中国西部的周边安全
历史地看,“西部”(或借用古代的称法“西域”)概念在中国从来就与外部威胁存在直接的联想。中国在历史上长期遭受来自西部、北部草原游牧民族的侵扰。如秦汉时期有匈奴,隋唐时代有突厥,五代、北宋时期有辽(契丹)和西夏(党项),然后是宋与金(女真)的长期南北对峙,后来又有蒙古铁骑从中亚大草原入侵并入主中原,最后是满族长驱直入统治了整个中国。历史解释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游牧民族的不断入侵是中国历代外部安全的主要威胁。当中央政权稳固强大之时,入侵引发的只是西北边陲地区的战争;但一旦中央政府积弱不振或鞭长莫及,整个北部地区则往往陷入频繁的战乱之中,以至边疆沦陷甚至中原地区也会长期处于异族统治之下。这类历史事件不乏其例。只是,高度发达的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因此即使中原地域被征服,但最终结局总是源于中原的华夏文明征服了相对落后的外来胜利者,从而保持了统一的中华文明发展的连贯性。作为民族象征的万里长城能够屹立数千年不倒,也能生动说明防御外来侵略和确保对外安全历来是中国统治精英们思考的头等大事。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海洋霸权的建立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东方开始在完全被动的条件下与西方发生了日益频繁的接触。对中国外部安全的主要威胁也随之从陆地移向海洋。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中,中国遭受的无数次侵略都是从海上开始的,东南沿海地带成了近代以来我国安全防御中最薄弱和最致命的环节。但必须注意的是,即使在这段时期,来自北、西北和西南陆疆的外部威胁也从未消除。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一有沙皇俄国对中国西北、东北大片领土的侵略,二有英属印度对我国西藏领土主权的侵犯。这些侵略造成的后果至今仍未完全消除。与早期的游牧民族入侵不同,19世纪起中国在西北方向受到的威胁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当时的沙俄大肆向外扩张,从中亚、西伯利亚两面挤压中国,成为威胁中国北方的主要侵略者,中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丧失了大片领土。前苏联在冷战时期也曾欲对中国发动入侵并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形成长期的沉重压力。因此,旷日持久的外部威胁使我国的陆地疆域及纵深地带的态势发生了显著改变,随着20世纪60、70年代中苏关系全面破裂和中印之间的交恶,这些变化的战略急迫感方引起我们重视。东起乌苏里江,西至帕米尔高原,中国陷入苏联的半包围圈中,重工业基地东北三省直接受到苏联军事打击的威胁,连华北中心地带也在敌方闪电战的有效攻击范围之内;在西南边境,中国却不得不面对日益强大、复仇心切并欲与中国一争高低的印度。
观察我国西部地区的外部周边环境,冷战后的形势发展为我们勾画出一幅更清晰的地缘政治轮廓。从地理毗邻、民族跨境、宗教同缘、文化相关以及未来发展互动等因素考察,西部的外部周边环境带有特征明显的地缘战略内涵。这一区域的范围大致与古代广义所称的“西域”相近,包括大部分毗邻、靠近我国西北、西南边疆的外部区域,即中亚、高加索、西亚及南亚部分地区,习惯上也通过阿富汗和克什米尔走廊将南亚次大陆的主要地区包括在内。在这一广阔地区,冷战结束主要体现为一系列重大历史性事件的发生,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海湾战争、中东和平进程、在中亚和高加索新建立起一批独立国家以及南亚印巴战略平衡被打破等。这些变化不仅改变了该地区的力量均势,改变了自二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而且开始了该地区地缘政治的实质性重组。
从我国的西部周边安全着眼,中亚和南亚的变化尤其值得重点关注。在中亚,新兴穆斯林国家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废墟上重建,该地区在全球能源和战略安全方面的重要意义日渐突出,各派国际势力争相扩张影响和进行渗透;在南亚,克什米尔冲突有升级之虞,印巴的核军备化进程加快。这些重要发展为我国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注入了新的要素。无论从地缘、安全、宗教、民族、文化和经济等多方面看,中亚和南亚地区的稳定都与我国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些地区与我国的新疆和西藏毗邻,其形势变动不仅直接影响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也关系到我国西部地区的整体发展乃至中国国力在本世纪的总体增长。必须重新认识这一区域的重要性,也必须重视这些地区安全形势对我国的综合影响。
二、中亚的不稳定因素
苏联解决以及一批新兴中亚国家的建立,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中国西部和北部的安全环境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积极方面看,苏联的解体从根本上缓解了中国在边境地带受到的强大军事压力,俄罗斯要彻底恢复元气尚待时日,因此至少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西、北方向出现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危险大大减弱,发生边界冲突的可能也降到历史的最低点。现阶段中国不仅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协商解决了大部分边界遗留问题,并通过对话就在各自边境地区削减军备和信任建设达成了共识。特别是目前成功运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在信任建设和地区安全领域进行合作的典范,多方强调加强在政治、外交、经贸以及安全领域的合作,承诺将中亚建成一个和平、和睦、稳定与平等合作的地区(“上海合作组织”原包括中、俄、哈、吉、塔五国,最近已接纳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
但是,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也产生了新的不确定因素,我们不应低估并必须面对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中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崛起是最主要的安全隐患和现实威胁。从全局范围看,冷战结束后的国际与地区环境对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在该地区的散播扩张都极为有利。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国家遭遇的挫折不仅为某些过激宗教政治思潮的泛滥创造了空间,也为其生存提供了合理性。美国和西方从自身现实利益出发,只要这些势力能有助于中亚地区摆脱俄罗斯的控制,有利彻底消除前苏联式政治、经济模式的影响,同时只要这些势力不以极端行动刺激西方的安全神经,就愿意对它们的主张和行动给予支持。
从地区范围看,“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化”(或称“泛土耳其化”)两大势力在整个中亚地区有相当强的号召力。其原因之一,在于少数国家出于自身利益极力促成这些思潮的泛滥,利用宗教势力扩大对这些国家的影响。(注:亓成章:《当代国际政治理论与热点问题》,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第225-226页。)其原因之二,这些思潮能填补后苏联时代在意识形态领域留下的真空,提供某些民族、文化的认同与权威性。在此大背景下,一些带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宗教极端派别空前活跃,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上升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巴尔干、高加索、中亚、阿富汗和克什米尔,从地缘上看,大致沿着中国的西部边境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孤地带,也基本囊括了欧亚大陆的腹心地带。
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存在某些共通的特征。首先,它们很少例外地将宗教、民族和政治问题搅在一起,以期从国际社会唤起广泛的同情和支持。第二,他们一面提出有吸引力的宗教与政治主张,另一方面为达到目的又肆无忌惮地从事绑架、暗杀、爆炸和其他恐怖活动。第三,为了获得充分的可用资源,它们往往将控制地区变成毒品的生产与输出基地。据可靠统计,阿富汗目前所产的鸦片为世界其他地区鸦片生产总量的三倍。仅1999年一年,阿富汗生产的鸦片就达到4600吨,在前一年的基础上翻了一倍。(注:Zhang Xiaodong,'Thd Making of China's Westem Strategy',Asia Times(Special Report),3/28/2001)独联体中亚国家也被公认为是国际犯罪团伙从阿富汗向欧洲贩运毒品的中转要道。
我国境内目前有10个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人口在两千万左右,其中大多数生活在西部,尤以西北地区集中。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除人数众多的维吾尔族外,还有不少哈萨克族(90万)、塔吉克族(30万)和吉尔吉斯族(10万,也称柯尔克孜族)。新疆与哈、吉、塔、俄、巴和阿富汗接壤,相通的语言、历史和宗教文化传统很容易在边境边建立起沟通的桥梁。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能通过严格的边界控制及其他措施有效地切断新疆与中亚地区之间的联系,但现在要做到这点却不现实。就民族、语言和宗教而论,新疆与西部地区存在着意义深远的联系。通过西部的国际走廊进行人员、物资和信息的双向流动,不仅是新疆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结果,也是新疆乃至整个西部地区进一步发展的必备条件。然而近年来的事实表明,我国的新疆已成为境外宗教极端派别、恐怖主义势力和毒品走私集团觊觎的对象,也就为“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渗透的主要针对目标。事关新疆安全与稳定的这一严峻问题目前已引起国内学术界和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三、南亚次大陆的冲突
南亚地区的印巴冲突是另一个与我国西部开发相关的外部不稳定因素。印巴冲突以克什米尔问题为焦点,争端已持续存在半个多世纪,曾触发过两次大规模的印巴战争以及多次低烈度武装冲突。众所周知,印度在南亚是起绝对支配作用的地区大国。由于外部大国的作用,印巴之间的战略平衡维持了半个多世纪。但是苏联解体、尤其是美国冷战后对其南亚政策的调整,完全打破了该地区原本就显得脆弱的平衡。
苏联解体后,巴基斯担作为美国冷战时期防御苏联南下的前线国家的重要性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已不存在。不少美国舆论今天甚至倾向于将巴看作是由腐败政客、军事寡头控制下的捣乱国家,激进的宗教极端势力和好战的军人政治成了该地区不稳定的主要因素。美国并将巴不顾一切发展核、导能力与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威胁和扩张相联系。与此相反,随着近年来美国南亚政策的调整到位,美国将过去的“歧路人”印度却视作国际社会的模范成员,基本认可了印度历来自翊的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形象,并认为它能在推动世界的民主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还认为印度是负责任的国家和南亚地区秩序的维护者。这也部分解释了美国对印度敢于顶住强大的国际压力进行核试验、以安全作为纯粹的借口事实上表示了理解。
由于旧有战略平衡被打破,克什米尔问题很可能再次触发两国间的全面战争。1999年爆发的印巴卡吉尔冲突就向世人敲起了警钟。鉴于印巴两国已实际拥有核武器的现状,将来如果冲突进一步加剧,将很难排除在南亚出现核危机的可能。印度目前在战略上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急欲在南亚甚至在南亚以外地区获得充分的行动自由,一劳永逸地解决与巴基斯坦之间的争端。但南亚的核军备化使得任何一方要想通过实力解决争端的可能性比过去更小,出现核对抗的可能性增大。巴基斯坦在战略上处于绝对劣势,面对印度稳操胜券的优势有可能孤注一掷。总之,克什米尔已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热点地区之一,就与我国的战略相关性而论更是如此,因此必须警惕。
对中国来说,印巴主要围绕克什米尔的冲突完全可能引起我西部边境地区的紧张,南亚形势的不稳也关系到我国西南边陲的安宁,也会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破坏性影响。但最大的危险则是中国有可能会面对一场本完全不愿卷入和完全可避免的外部冲突。况且,中印边界争端至今未得解决,仍是我国西南周边安全的一大隐患。因此南亚地区的稳定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战略利益。尽管克什米尔冲突有复杂的历史渊源和政治背景,但引发和加剧冲突打破了该地区的稳定,并很可能触发周边地区的不稳,而且也为西方大国直接插手该地区事务提供了方便。这些都不是中国愿意看到的。中国对此早就发出了告诫。同时印巴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印关系的健康发展,影响了相互之间的信任和理解,从长远看不利于该地区的稳定。
四、“西部大开发”中的周边安全对策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加速,尤其随着目前“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逐渐展开,我们与邻近我国西部的外部周边环境的接触将变得比过去更为密切,中国在这些地区有着广泛的利益,它们体现在多个方面,需要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进行友好的合作。这一问题值得国内学术界与政府有关部门去进行具体深入的考察研究。但从根本上看,预防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确保周边的安全与稳定是 一项重要的基本任务,也是未来时期内决定中国西部开发战略能否顺利实施和中国西向开放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从中国西部地区的周边安全着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对策。
1.同与我国西部稳定相关的主要地区性大国发展、保持良好关系
在与我国西部接壤、毗邻或与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发生社会文化关联的中亚、南亚和西亚地区,一些地区性主要国家能对维持本地区的力量平衡起到关键作用,也能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包括哈萨克斯坦、印度、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土耳其目前是我国新疆境内的民族分裂主义在海外的主要基地;印度则是极力鼓动“藏独”、长期从事民族分裂活动的达赖流亡集团总部所在地;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伊斯兰世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哈萨克斯坦却与中国间存在漫长的陆路边界,也是最大的兼具伊斯兰教和突厥特征的中亚国家。与这些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应是我国在西部地区开展成功外交的主要重点。只要这些国家能够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充分认识到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给地区稳定带来的严重危害,就能够对改善和发展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和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施加积极的影响。从目前看,中亚国家基本上对中国承诺共同反对民族分离主义;(注:李宝俊:《当代中国外交概论》,(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186页。)印度也深知利用“西藏问题”伤害两国关系的严重后果,申明中印在反对民族分离主义的问题上有相似处境,并提出中印联合对付宗教原教旨主义。(注:新华社,1999年3月23日。)从近年来的情况看,中国并不反对跨境民族团体间的经常性交往,并真诚欢迎与邻国在相互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建设性对话。事实上目前西部扩大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将为这一正常交往提供更多的机遇和更好的条件。但中国历来强调不以民族和宗教问题为借口对他国内政进行干涉,同时也坚决反对他国对我国的民族宗教事务横加干涉。
2.通过机制加强与俄罗斯及其他有关国家的合作
安全领域内的地区性跨国合作为共同防范和消除外部不稳定因素提供了某种有效的机制保证。应该承认,由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由于宗教和民族构成的复杂特点,也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相关各国间无法避免的国家利益冲突,中国要与其他各方建立完全信任仍存在着不少困难。但必须认识到,中、俄、中亚以及南亚部分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是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跨境犯罪活动的受害者,因此相关国家在这些方面存在明显的共同利益,也表明了这些国家在安全领域内具有加强合作的潜力。反之,如果中国与这些国家缺乏理解与合作,很难真正有效地遏制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泛滥。事实上,不少国家近年来均在积极探寻地区安全合作的可能途径。对我国而言,通过建立和强化多边合作机制,在促进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同时确保稳定与安全是值得尝试的努力。在此方面,“上海五国”框架提供了一个相对成功的范例。通过该合作机制近期的运作,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在共同打击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上已取得一些初步进展。初始着眼建立边界信任的单一框架如今已发展成一种多边、多方位、多层面的合作机制,对预防、消除各类不稳定因素、促进相互间的经贸合作产生了重要意义。“上海五国”机制的顺利运转证明更多的国家已经意识到在安全方面加强合作的重要意义。最近乌兹别克斯坦已被接纳进“上海五国”机制,连印度等国也对参加“上海五国”机制表露出明显的兴趣。从现状看,在该机制中起有关键作用的中国与俄罗斯应鼓励更多的相关地区国家加入这类形式的合作。只有通过大规模的信息交流、人员培训和协同努力,才能有效切断这些国际性犯罪组织间的网状联系,特别是它们的资金、人员的流动和武器、毒品的跨境走私。
3.在南亚奉行更加平衡的外交政策
南亚地区的稳定从总体上说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反之,印巴的长期争端和冲突将对我国的国家利益产生明显的负面作用。巴基斯坦作为我国的传统友好国家,在世界伊斯兰教国家中有较大的影响力。中巴两国应在多方面保持合作,遏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扩张,从而优化我国西部开放的外部环境。但也应看到,巴国内近年来宗教极端势力日益强大。对其国内政治的干预能力增强,如不在与巴政府合作的基础上对之严加防范,势必将对我国新疆境内的民族分离主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注:Tara Kartha,'Pakistam and theTaliban:Flux in an Old Relationship?',Strategic Analysis(IDSA),10/2000,p1319.)
印度是南亚地区举足轻重的头号大国,也是中国西南部接壤的最大邻邦。两国关系尽管自80年代底以来有了明显改善,但印度在战略上始终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近年来因印度以“中国威胁”为借口进行核试所引发的危机就很说明问题。(注:林良光等:《当代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第97-100页。)印度目前对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可能产生的战略辐射持谨慎观望态度。因此中国在争取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的同时不能在战略上掉以轻心。但同时也应注意,印度与中国在世界多极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问题上存在不少共同利益,印度也公开申明愿意消除障碍与中国发展正常关系,并且由于南亚事实上的核军备化和美国南亚政策的调整,该地区的战略现实已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中国需要从自身战略利益的高度出发,在客观分析该地区战略现实的基础上作出相应调整,在南亚执行更为平衡的政策,这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
4.密切关注西方大国在该地区的战略意向
中亚和南亚目前已成为全球敏感地区。由于中亚在未来全球能源安全上的重要性,中亚独联体国家正在成为各种国际势力对抗和竞争的热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更是凭借强大的综合实力加强对中亚国家的经济与政治渗透,以求在掌握未来全球能源供应的控制权和遏制俄罗斯、中国对该地区的影响。以美国等西方大国作后台的国际石油、天然气跨国公司纷纷到中亚国家抢滩,在资金、技术和政治影响方面已占明显优势。(注:K.Subrahmanyam,'Asia's Security Concems inthe 21th Century',Jasjit Singh,Asian Security in the 21th Century,NewDelhi,1999,p17.)南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已开始明显上升,美国冷战后重视与印度发展密切关系,近期来在战略上拉拢印度遏制中国的迹象已趋明显。(注:Sadiq Ahmad,'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a NewRethinking i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Increasingly Sites India as aCounterpoise to China',Outlook,5/7/2001.)需要指出的是,美印之间尽管仍存在不少矛盾,但对“中国威胁”的话题却有共同语言。从多种因素判断,印度完全倒向美国共同对付中国的可能性不大,但美印双方必定都会利用对方这张牌来制约中国。
两年前的科索沃战争和北约成立50周年宣言标志了一个转折点,美国与北约极力推动的“新干涉主义”开始成型,其最充分地体现为对南联盟内部极端派别“科索沃民族解放军”和对俄境内车臣非法武装的公开支持。西方的这种做法事实上鼓励了国际社会各种各样的分离主义势力。无论西方国家为这一新的世界政治理念寻找何等依据,但我们必须正视科索沃战争和双重人权标准展示在我们眼前的严峻现实。尤其不容忽视的是,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不少势力始终利用“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对中国施加政治高压,在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打压。鉴于公开声明这种新的强权机制以及存在对其他国家滥用该原则的先例,中国需要对美国及西方以人权压主权、打着“维护人权”和“民族自决”的旗号加强对我直接干预的可能性保持高度警惕。此外,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一直紧握全球霸权不放,绝不希望看到中、俄及中亚国家加强多边合作、积极探索地区安全新途径的努力,试图通过大北约的扩展在战略上遏制俄罗斯和中国。目前北约的触角已伸及高加索和中亚,并保持进一步扩张的势头。因此也需要对该趋势发展对我国周边安全和西部地区外部环境带来战略威胁进行研究和预测。
标签:美国宗教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中亚民族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政治论文; 南亚历史论文; 经济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