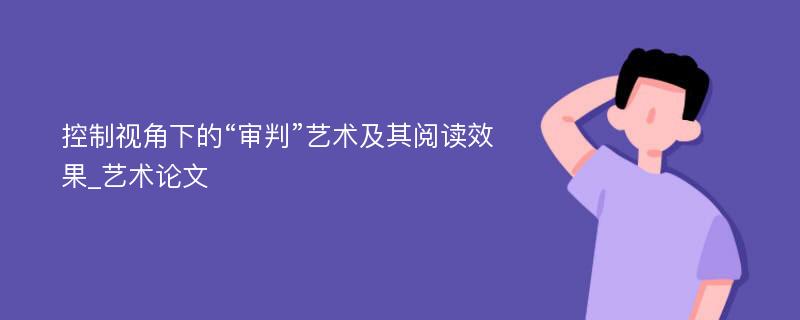
《审判》视角控制艺术及其造成的阅读效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效果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卡夫卡小说的思辨性很强,表现了丰富的多解释性,而且有一种令人震惊的沉闷、冷肃之气,显示出极为独特的创作个性。本文拟从其代表作《审判》中视角控制艺术方面,揭示其小说这一阅读效果之形成原因。
关键词 视角控制 叙事空缺 认知侧面 情感成分
有人认为卡夫卡的小说相对于他的信件而言是更为“私人”的东西,卡夫卡也认为他的小说是“我梦幻般内在生活的表现”。实际上卡夫卡的小说不是他的“内心独白”。与之相反,他的小说执拗地避免直接描写他内心极度焦灼的心理挣扎,而只表现激起他想像的东西,即用日常现实中的东西重造一个特异的生存情态,力求以足够的丰富性把自己对环境的感受、对个人生存境遇的独特体验、对生存意义的思考完整无遗地保存在这个生动的形象世界里,并以笔录式冷漠细致的笔触把这个与他的内心世界统一的形象世界描绘出来。
《审判》被称为“卡夫卡的最伟大作品”。(马克斯·布洛德语)非常能代表他的“卡夫卡式”表现主义的艺术风格。因此,探讨《审判》中叙事因素的操作方法对把握卡夫卡小说的表现艺术很有帮助。加缪说:“卡夫卡的全部艺术在于迫使读者反复阅读”。与他的许多作品一样,《审判》同样具有使读者不得不一读再读才能有所发现的理解困难和令读者震惊的冷肃之气。《审判》何以具有这样的阅读效果?在《审判》中究竟是哪些叙事因素的异常运用才使它显示出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作品极不相同的特征呢?这些在阅读中自然而然产生的问题恐怕并不易作出全面透彻的回答,下面仅从其小说叙事中视角控制来管窥造成这一阅读效果的原因。
一、视角控制造成理解困难
《审判》在叙事上采用的是内聚焦,属第三人称限制叙事视角,其视角严格控制在K可以确定的世界之内,即这个视角只观照K能感知、认知的部分,K是视角关注的唯一焦点。作品也随这个视角在时间中对K的行为、感官感知、心理认知的观照而展开。正是由于这个特定视角的作用,使得作品的叙述只能以K 在时间流程中的行为和感知内容作为对象,作品所传达的内容就只能是K的认知范围中的内容。超出K的认知领域之外——K所不能认识的一切事实,作品都无权传达, 即使那些事实对作品的理解极为重要。这样作品在叙事中就出现了许多空缺,给读者在理解作品时留下了许多惑人的盲点。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对事件的前因后果缺乏交代。由于《审判》的视角紧随K的意识而推进, 故事好象就发生在K的感觉和理智之中,而不是发生在K的身外,这决定了叙述者只能是K的行为和心理的传达者,它不可能也无权跳出K的感觉与理智之外,跳出约瑟夫·K感觉中的“现在”时间之外,对K所不明了的事件的前因后果作“回叙”或“预叙”,给读者作出必要的交代。因此读者就和K一样不知道那天早上突然降临到他头上的那桩无头案的起因; 不知道“自己为何受控,更不知道由此而引起的其他指控”;也不知道是谁以何种罪名对K实行了最后的判决。不交代事件的起因, 整个故事就没有一个现实的确定的基础,整个故事的背景也显得“不可知”、“神秘”,显示出一种子虚乌有的荒诞意味。对故事的结局——即是谁以何种罪名判决K死刑——不作交代,同样消去了故事的现实确定性, 导致故事本身不合常情,染上很浓的非理性色彩,故事的合理性、确切性也被抽去,显得异常、扑朔虚幻。造成了隐晦的象征意味,给理解作品的真实意义带来困难。其二、对隐藏在事件之后的各种关系和内幕缺乏必要的交代。《审判》严格控制在K 的行为和心理领域的视角决定了叙事者又只能传达K的认知领域内的事实,而不能传达K所无法明了的一切事实,而这些事实又可能是整个故事中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环节。这些事实在叙事中被忽略,势必造成《审判》叙事中不可弥合的空缺,使读者和K一样对这桩案子的内幕茫然无知:这个法院和法庭的性质怎样? 它们究竟以何种罪名审判K?霍尔德律师与K在一起从不谈案子的实质,他对K的案子究竟知道些什么?他为案子采取了哪些措施? 又有什么进展?在幕后操纵K的案子的是谁?又是谁在审理K的案件?他们掌握哪些关于K的“犯罪事实”?最终又是谁对K实行了裁决?这一切对K 和读者都是谜,不可解开。不仅如此,由于《审判》中视角关注的是K的意识, 其他人物是通过K的“眼光”来展示,这种视角使K好象永远只能处于其他人物的关系和各种他所不明了的关系之外,他虽然生活在这些关系之中,却始终不能融入这些关系之中,而与这些现实的关系相疏离、隔膜,不能真正透视那些关系。这表现在叙事中就使小说对各种关系的叙述异常模糊、暧昧不清。例如:画家蒂托雷里与法庭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他对那些法官和案件本身又了解些什么?还有那处在多角关系之中、难辨是非的法院洗衣妇和莱妮。她们的出场不仅突兀、而且行为也显得不合常情,令人难以理解。这些在作品中也总是表现得闪烁其词,读者无法对此有一个切实的认识。
可见,《审判》由于视角限制,使叙事产生了很多空缺。但《审判》不象侦探小说。一般的侦探小说文本一开始形成的叙事空缺最终要随情节的发展而得到填补,最终要通过主人公的一系列活动去揭开事件的真相,一开始让读者困惑不解的疑虑,文本最后会一一作出解释。阅读结束了,读者的疑问也全部解开。但《审判》并非如此, 由于限制于K的感知范围内的视角所造成的叙事空缺到文本结束也没有得到填补,读者一开始产生的疑虑在阅读结束后仍从文本的叙事里得不到澄清。读者和K一样毫不知情地就坠入一桩不知端由的案件之中, 既不能实际接触这桩案件,又始终不能摆脱这无形的审判,在这桩无头案里奔突、挣扎、直至筋疲力竭,最后只能任其神秘地处死。
这些隐藏在K 的视角之外没有最终给予填补的空缺直接给作品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非理性面纱。小说的整个故事就建立在一个没有来由的无头案上。案子本身的虚幻使围绕案子发生的一切(即整个故事链)都悬浮于虚无之上,整个小说世界的现实性也就极为淡薄,不合常情但又不无存在的可能。人物行为没有明确的动机,人际关系暧昧不清,人物生存背景也模糊、不实际,他们的身上没有现实生活中的人身上赖以生存的现实成分,象一具具影子在隐隐约约的舞台上演着一个无头的悲剧,没有音乐,只有一个冰冷的背景和灾难临近时跫跫的脚步声。卡夫卡就是这样,运用一个极受限制的视角,造成叙事中难以弥合的空缺去弱化凝聚在人物身上的现实成分,增加事件中的虚幻、非理性因素,按照另一种不合常规的逻辑来把读者“重新放进一个即无意图又无航迹的现实里”。(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把读者“从生活的习惯中拉出来。事件不再像日常被动的现实里那样连贯了:它们被剥去了因为符合传统而被称之为逻辑的破衣,它们的前面不再有理由,后面也没有它们的解释……,常规的三段论被摧毁了”(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这种使故事中各个事件缺乏必然因果联系,建立在非理性基础上的叙事,必然导致叙事的不确定神秘化倾向,给读者理解作品带来困难。
而且,这种局限于K的可确认范围内的视角,把K推向类似于真实的生活流之中,K象生活于现实中的每个人一样, 得不到超出他生活之外的启示,生活对他来说只是一些混乱要尽快理清的关系,他被迫自己设计自己的命运,自己推进自己的故事,自己去确认自己的存在。然而他可以确认的世界实在太缈小,除了确实的内心信号,来自自己感官的真实感受外他还能确定、把握什么呢?他不能知道他为何受到审判,不能知道隐藏在这桩子虚乌有的案件之后的内幕,甚至他本人都无法实际接触这桩关于自己的案件,被排斥在自己的案件之外,永远不能接近审判着他的“法官”,对存在于自己身外的一切关系都“不可知”或“不可信”。这种对K身外世界和关系不作观照的视角,就把K确认的缈小世界与他身外他所“不可知”的关系世界对立起来。巨大的无边的“不可知”包围、挤压着他可确定的缈小世界。K就象是一点萤火, 在这个因“无所知”造成的漆黑世界里闪着微茫的光,随时他将被无边黑暗中潜伏的灾难所吞噬。他的日常生活就处在这种不安和灾难逼近的气息中,然而他始终不知道逼近他的是来自何方、怎样一种性质的灾难。在这个令他迷惘的世界里,他得不到回答,也感受不到一丝温情的抚慰。在无情的追逐着他的“审判”里,他无所适从,为莫名的焦虑和惶惑所支配,最终被耻辱地象狗一样地处死。
卡夫卡的灰色神话粉碎了读者对这个世界许多天真的梦想,“我们从习惯、义务和俗套的昏沉中被唤醒、被要求弄清是怎么回事”(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使读者看到在这个世界表面使人放心的虚伪秩序中,存在着令人震惊的不人道和逼人的荒诞,某种尚未进入我们意识的超人异已的灾难“随时都可能将人类和他们的创造、梦想、价值一起吞没”。(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同时我们也可以生动地感受到象卡夫卡这样一个瘦弱的生灵在现实的挤压下,在其灵魂深处折磨着他的对现实真切而尖锐的绝望、恐惧和无以复加的焦虑。这些都是文本通过视角对K 的心理感受进行观照后直接传达给读者的东西,但那审判着K、高踞在人之上的“法”,那种始终在压迫着K的陌生的敌对的社会力量,又是一股怎样的力量呢?它来自何处呢?这些因视角限制而无法观照的东西,或用这种特定的限制于K的感知、 心理范围的视角故意疏漏的东西,文本所未直接传达的声音就只能靠读者自己去破译,或者在对作品“一读再读”之后在作品外去寻求答案。
二、知觉侧面的强化和情感成分的相对弱化形成作品的冷肃文风。
里蒙·凯南在她的《叙事虚构作品》中把聚焦侧面分为感知侧面、心理侧面(包括认知成分、情感成分)和意识形态侧面。在《审判》里,由于意识形态侧面表现并不明显,而且与本文关系不大,在此毋庸赘述。下面主要就其他几个倾面考察《审判》冷肃之风形成之原因。就《审判》的叙事来看,文本视角扩张了感知倾面,认知成分也被有条件地强化,而情感成分却无条件地被弱化。
1、感知倾面的扩张。象许多现代表现主义小说一样, 《审判》对聚焦者的感官知觉内容进行了扩张的表现,其视角对K 的感知内容观照精细,表现在叙事上就是文本对K视听世界作了细致描写。 《审判》自始至终没有让视角偏离K的感知内容,K的任何一点感知似都处在这个视角的观照之下。这个只关注K的视角甚至伸向了他的感知深处, 随时追踪K的感觉。K走进法院大楼,这个视角也追随K的眼睛, 让法院的“外部现象”展现在读者眼前。“他旁边有一个没穿鞋子的人……,两个男孩正利用一辆小推车玩跷跷板,一个面容憔悴的年轻姑娘穿着睡衣,站在吸泵前打水……”。紧接着这个视角又跟随K 的眼光延伸到大楼内部“不少女人一手抱着孩子……,几个即将成年的姑娘除了围裙以外,似乎没穿别的衣服……,每间屋子里床上都躺着人,有的是病人,有的在酣睡,还有的已穿好衣服,但依然赖在床上养神……。”法庭里“天花板下面是一圈楼座,那儿也挤得满满得,人们即使弓了身子站着,头和背也会碰到天花板,那里光线暗淡、尘土飞扬、烟雾腾腾……”。在这里卡夫卡利用视角对K的视力所见作了细致的观照, 让读者看到法院杂乱、阴暗而又肮脏的外表。随即视角频频推移,一会移向K 的听觉,一地又移向K对环境的生理反应。那法庭上洗衣妇放荡的尖叫,法院办公室污浊的空气和那些麻木机械、卑躬屈膝的被告,都随视角观照角度的推移逼真地表现出来。K在法院办公室头昏眼花,闷热难当, 让姑娘把天窗打开一点儿,但“大量煤烟却随之冒了进来。”读到这里,读者也和K一样对办公室窒闷污浊的空气产生难以忍爱的生理反应。 这个始终追踪着K的生理和心理感知内容的视角,把K感觉中的法院活画出来,形成一幅幅污浊、脏乱、令人窒息的画面,同时剥去了貌似庄严的“法院”的神圣外衣。不仅如此,这个视角还对K感知到的旅馆、街道、画家的画室、律师的办公室也作了细致的观照,这个视角所表现的这些生活空间无不显得压抑、灰暗、没有人的生气。从文本的叙述可看出,视角对感知侧面的扩张主要为了突出K感觉中他所生存的环境。 这个环境污浊杂乱,没有温情,没有欢笑,令人窒息,毫无生机。使读者逼真地感觉到K所生存环境的非人道,感受到一个异化世界那种悲凉、腐朽、 沉闷逼人的气息。同时对感知世界的细致表现,对空间世界的精细描写,也增强了叙事的客观性,文本叙事也变得更为冷漠。
2、认知成分有条件地强化。在文本中,卡夫卡大量表现K在时间中面对环境及他人的意识流动状态,即小说视角对K 的意识的观照是文本的主体,在这一点上,《审判》接近于意识流小说。但《审判》在表现K梦魇般的意识时又不同于意识流小说。 许多意识流小说都反映人物内心激烈的意识冲突,表现人物的灵魂的挣扎、奔突及欲望的强烈冲动。《审判》中K的意识流动却平静、滞重。 其受限制的视角似乎有意不让K去摸索、去寻求、去放飞、燃烧自己的思绪,也不让K对环境作出明显的情绪反应。文本中K 的意识活动只表现为对当下的外界信息作出简单的反应,其意识活动无目的、散漫、浮泛、随机产生。人物似乎被动地去接受临到他头上的一切,陷入象谜一样的关系中又不试图去探究这些关系。K毫无理由地被审判,被无端地推入一个无头案中, 却不见他有不满或愤怒的情绪反应;置身于一个毫无生气、令人窒息的环境却不见他厌恶、痛恨之情;即使最后被糊里糊涂地处死也不见他有恐惧或抗争的意识流露。这说明小说视角在对人物的认知成分作观照时是有所节制的,这个视角并未深入到人物的意识情绪深处,只简单肤浅地观照人物最基本的反应,使人物似漂浮在生存的表层,麻木地应付着简单或复杂的一切。无目的,也无对策;对一切无动于衷,又为不可名状的焦虑弄得惶恐不安。这个视角极为克制的限制观照,造成的唯一阅读效果就是让读者触目惊心的看到,处天异化世界的人的生存状况,K 完全被莫名的,无边的焦虑所占据,焦虑扩张到他的每一根神经里,攫住了他的整个意识,他被焦着在这一不安的情绪里,其他情绪,心理活动被抑制,从意识中挤出。
3、情感成分无条件地弱化。 《审判》特定的视角从不对人物(如K、 布尔斯特纳小姐或其他人物)作动情观照一即叙述者在叙述中未曾流露出对人物的主观情绪,也不把视角推向人物的情感深处,不对人物的内心情感的变化作细致入微的观照。文本视角对情感的漠视既使叙述行为本身毫不动情,表现得极度的冷静和客观,而且又使文本中人物身上的情感成分遭到完全的放逐。表现在小说的文本中,就既不见叙述者对K的情感反应,也不见K有何情感的流露。这一点从K 与几个女人的关系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一个深夜K 突然吻起了布尔斯特纳小姐,但此时视角并没有紧随K的行为伸向K的情感深处。因而在叙述中丝毫不见K热烈的情感反应,他似乎在机械地、突兀地做着这一切。 这冷漠的视角把K变成一个毫无感情的人,象是一只没有灵魂的影子。 以后他又无缘由地迷失于法院洗衣妇的诱惑,并且在律师的女仆莱妮的引诱下之苟合。卡夫卡运用这种视角表现出的双重冷漠与享利·詹姆斯的“非人格化叙述”小说有很大不同。虽然卡夫卡与享利·詹姆斯同样在叙事中表现对人物和事件无动于衷的超然态度,都不让视角带上情感的变色镜去观照人物与事件,不让作者和叙述者的情感通过视角介入叙事。但享利·詹姆斯却无疑没有放弃让小说视角对人物内心情感特定的观照,叙述中仍表现了人物丰富的内心情感。而卡夫卡不仅滤去视角中的情感因素,而且也不让视角去观照人物情感世界。叙述者对人或事件无情感反应,叙事行为变得客观冷淡,文本中的人物也似乎失去了正常人所应有的情感,显得冷漠无情。
由此可见,《审判》中的视角控制显示出感知倾面的相对强化和情感成分无条件弱化的倾向,视角比较关注K 的感知内容和浅层次的意识流动而放弃对K内心强烈、丰富的个人情绪的观照,使得在叙述中,K的感知内容得以扩张表现,而情绪、感情活动始终处于受控制的状态,在这个特殊视角所延伸到的世界里,人们所能感知到的无不令人窒息,四处充斥着冰冷无情的物。另一方面人们的人性成分又遭无情的压抑,人已形同于物,表现得异常麻木、冷漠、无动于衷,人已被环境彻底异化。卡夫卡正是通过视角的一明一暗,一显一隐的观照,一个异化了的世界里,沉闷、毫无生气,压抑人的不人道表现到了极致。同时又在这个局限于K的行为、心理范畴内的视角中, 把异化世界处于敌对的陌生的社会力量控制之下的人那种无所适从、焦虑不安、无法自主的悲凉,客观真实地表现出来,让读者震惊地感受到人的特性正在被这股异已的力量所吞噬,人已形同于物。另外这种一扬一抑的视角控制抽去了叙述行为本身、抽出了叙述对象的情感成分,使文本显示出异乎寻常的冷肃之气。
泛情的叙事固然能激起读者强烈的共鸣,控制的叙事同样可以用逼真的客观让读者触目惊心。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作家是否直接从卡夫卡那里得到启示,这不得而知。但他们(如余华、残雪等)的文风的确比较接近卡氏小说,特别是最近残雪发表的《历程》(见《钟山》1995年第一期),其灰暗、迷离、窒闷、冷漠的格调已非常近似《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