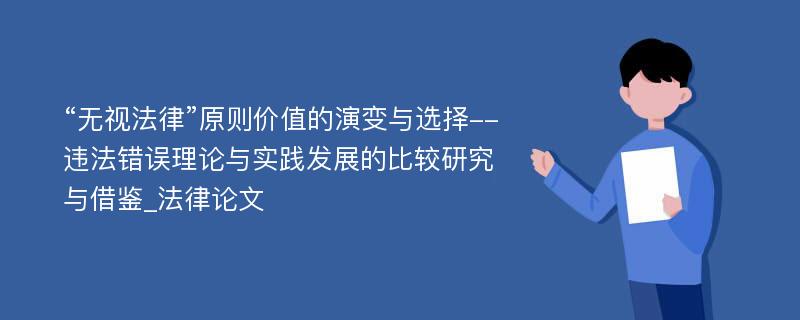
“不知法不免责”原则价值的嬗变与选择——违法性错误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比较考察及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法论文,原则论文,错误论文,理论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知法不免责”(Ignorantia juris non excusat)原则起源于一概不允许认识错误的诺曼底时代的绝对责任,它意味着行为人“在作为主观的犯罪成立要件的犯意中,不要求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① 在传统上,理论界一般将刑法中的错误分类为“事实错误”与“法律错误”。事实认识错误在13世纪的布莱克顿(Bracton)的教科书中,已经被承认为抗辩理由;与此相对,关于不知法律或者法律认识错误,却一直不影响犯罪的成立乃至不影响量刑,于是形成了以下局面:不知法律有害,但不知事实无害(Juris ignorantia noeet,faeti nonnocet.)。换一个角度来说,不知事实免责,但不知法不免责(Ignorantia facti xcusat,ignorantia juris non excusat; Ignorantia exeusatur,non juris sed facti; Ignoramia facti,non juris excusat.)。正因为如此,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上一直重视区分法律错误与事实错误。② 20世纪以前,世界各国在处理“法律错误”时均毫无例外地坚持“不知法不免责”的原则。
但是,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的日益复杂化,社会对犯罪的考察和惩罚由犯罪行为转向了行为人,人类文明进程的发展迫使“不知法不免责”这一古老的原则作出了让步,刑法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理论界关于违法性认识的内容、违法性认识的本质、违法性认识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违法性认识错误的概念以及违法性错误的处理原则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许多新的学说,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更以观念是否为具体之犯罪成立要件为区别标准,将错误分为涉及构成要件客观事实之“构成要件错误”(Tatbestandsirrtum)与涉及行为违法性之“违法性错误”(Rechtswidrigkeitsirrtum)或称“禁止错误”(Verbotsirrtum),以代替昔日“事实错误”与“法律错误”之区分。③ 刑法学界一般认为:“所谓违法性错误,也称为法律上的错误,是指行为人的行为从客观上来看,尽管该行为是法律上所不允许的,但自己错以为允许,换句话说,是行为人由于错误而没有违法性意识的情况。”④ 在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大量与“不知法不免责”原则相悖离的立法例和判例,“不知法不免责”原则这一处理违法性错误的铁律正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悄然松动。
我国刑法没有规定违法性错误及其处理原则。在我国刑法学界,学者们对违法性认识问题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对违法性认识在我国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违法性认识的内容、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之间的关系也存在较大分歧。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对违法性认识错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违法性认识是否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和违法性认识错误是否阻却故意两个问题上。在我国,违法性认识不是犯罪故意的内容、“不知法不免责”的观点仍然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我们认为,由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不同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国家的犯罪构成理论,违法性认识在我国犯罪构成要件中地位和作用应当重新考虑;由于我国社会的日益复杂化,“不知法不免责”原则应当予以修正。
正是基于“不知法不免责”这一违法性错误处理原则在世界各国的嬗变和我国违法性错误理论研究、立法、司法的现状,我们立足于我国目前的犯罪构成理论,对违法性错误处理原则进行了比较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不知法不免责”原则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嬗变
在英美法系,确立“不知法不免责”原则最古老的判例是英国1613年的Vaux案。该案判旨认为,即使不知英国法律,但由于认识到被起诉的事实,不知法律也不成其为抗辩理由。从英国的判例来看,“不懂法不作为抗辩的理由”具体包括以下三种情况:其一,行为人由于客观原因(如常年在外、公海航行等)不知道某法律的施行不得作为抗辩之理由。例如,在1880年的Burns v.Nowell案(伯恩斯诉农维尔案)中,船长在航海期间,不知国家于1872年施行《诱拐禁止法》而违反该法运载南洋诸岛的当地居民。尽管该案件中的船长并不知道相关法律的规定,但他最终仍被判决有罪。其二,外国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在行为地是犯罪不得作为抗辩的理由。例如,在巴洛勒特案[Rex v.Barronet( 1852) LE.&B.1]中,一名叫巴洛勒特的法国人在英国参与了杀人决斗,尽管不知道英国的法律禁止决斗,英国法院仍然以“不知法不得作为抗辩理由”判决他犯有谋杀罪。其三,行为人事先征询过相关法律人士(如律师)或者法定资格的官员然后实施的自认为是合法的行为也不得作为抗辩的理由。例如,如果法律规定了房屋的最高售出价格,行为人D在帮助协商的房屋出售价格高出了法律规定时,即使他认为这个价格没有超出法律规定,他仍然具有犯意。“即使D就自己将从事的行为咨询了法律专家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是行为是合法的,对他行为的认定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否则会导致“律师的建议高于法律”的局面。⑤
英美法系国家之所以确立“不知法不免责”原则,其主要理由是:其一,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即应当知道法律。布莱克斯顿说:“具有辨认能力的任何人,不仅应当知道法律,而且必须知道法律,并推定其知道法律,因此,法律认识错误在刑事法上不成立任何抗辩理由。这是罗马法的格言,也是我国法律的格言。”⑥ 其二,维护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政策的原则之一是,负有遵守法律义务的人不得主张不知道法律。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任何人都必须遵守法律,否则,社会福利与国家安全就得不到保障。因此,不允许以不知法律为理由逃避法律责任。法秩序具有客观性,法律是具有客观含义的规范,刑法所表现的是通过长期历史经验和多数人社会舆论形成的客观伦理。当法律与个人的信念相对立时,法律处于优先地位,故法律认识错误不是免责理由。⑦ 其三,刑法得以有效实施的保证。司法机关往往很难查明行为人是否不知法律,如果被告人主张不知法律就免责,刑法就难以有效地实施。“假定实体法规范不被推定为人所共知,诉讼上就会遇到许许多多难以解决的困难,甚至连实体法都无法实施。假设被告人说:‘我不知道法律上规定这种行为是犯罪’,被告人的这句话是不需要再有另外的证据证明的,因为他本人就是证据;但是控告一方要反驳这句话往往是很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所以,出于诉讼上的考虑,不知法律不应当作为免责辩护的理由。”⑧ 如果法律认识错误是免责事由,则被告人常常主张法律认识错误,事实上又难以证明,因此根本不可能裁判。⑨“如果那种辩解(即不懂法)有效,结果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认为法律是如此这般,他将受到似乎法律就是如此这般的待遇。也就是说,法律实际上就是如此这般。”⑩
进入20世纪以后,英美法系国家“不知法不免责”的违法性错误处理原则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以下以美国和英国为例加以说明:
(一)美国违法性错误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在司法上,美国大量的判例承认“不知法不免责”的例外。这种例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因信赖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和地方法院判决而发生的违法性错误可以免责。例如,因信赖州最高法院的判决而实施的行为不可罚的State v.O' neil案。美国衣阿华州最高法院于1902年和1906年两次判决认为,将贩卖、购入麻醉饮料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的法律,违反了合众国宪法。State v.O' neil案的被告人信赖上述判决,于1908年实施了贩卖、购入麻醉饮料的行为。但在1909年,衣阿华州最高法院变更了以前的判决,认为将上述行为规定为犯罪的法律符合合众国宪法。于是,地方法院其后对上述被告人作出了有罪判决。但该有罪判决被衣阿华州最高法院撤销,理由是:信赖自己所属州的最高法院判决而实施的行为,应作为“不知法不免责”原则的例外而免除责任。又如,信赖地方法院判决而实施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判例(Wilson v.Goodin,1942)。其二,因信赖具有某种权限的行政官员的意见而发生的违法性错误可以免责,例如美国1911年的State v.White案。案情是:被告人实际上没有选举权,但事先基于选举人登记官员的决定,误认为自己具有选举资格,于是作为选举人登记。原审法院判决被告人有罪,但密苏里州最高法院撤销了原审判决。理由是:虽然认为任何人都知道法律,但事实上,连受到最严格训练的法官有时也难以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法律。在本案中,被告人是根据具有选举资格审查权的行政官员的决定实施的行为,如果认定被告人有罪则过于苛刻,因为行政官员自身犯了错误,对被告人提出了不适当的意见。(11) 其三,因为真诚地误解了法律而发生的违法性错误可以免责。例如,1933年的“United States v Murdock”案。法庭认为,国会并不会认为一个人因为真诚地误解了税法的规定而应当成为犯罪人,特别是在行为人误解繁杂的税法之情况下。美国刑法学者Michael L.Travers认为Murdock案是“在税收犯罪方面出现的对运用普通规则(解决)法律错误例外的一个标志”。(12) 其四,因信赖法律家的意见而发生的违法性错误可以免责。例如,美国法院1949年裁决的龙格案[Long v.States65A·( 2D) ( 1949) ]中,被告人龙格在决定第二次结婚以前,曾就离婚是否有效、能否第二次结婚的问题与律师商量过,律师告诉他离婚有效,可以再婚。他在做好结婚的准备后,在提出结婚申请之前,又与律师商议,律师与他一起去了Cleck of the Peace事务所,作为保证人在他的第二次结婚申请书上签了名。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的错误是法律的错误,应当适用“不知法不免责”的原则。但是最高法院认为,被告人在实施行为之前曾做了善意的努力,为了认识和遵守法律采取了在美国法律体系下是最适当的手段,在他相信自己努力的结果而诚实地实施了行为的情形下,将被告人作为犯罪人处罚是明显的不公正,从而推翻了原审法院的判决。(13) 美国1991年Cheek v.U.S.案、1998年Bryan v.U.S.案、1964年Bouie v.Columbia案等,都是关于这一例外的判例。(14)
在立法上,美国《模范刑法典》第204条第(1)项规定:“关于事实或法律的不知或错误,在下列所定场合,即可作为抗辩:(a)其不知或错误在否定证明犯罪基础要件所必需之目的、认识、确信、轻率或过失时;(b)由其不知或错误所证明之心理状态,经法律规定可作抗辩时。”可见,在上述情况下,法律认识错误与事实认识错误同样可作抗辩理由。不仅如此,第204条第(3)项还承认没有上述规定也例外可作抗辩的情况。第(3)项规定:“确信其行为在法律上不构成犯罪时,如有下列所定情形,可作为对基于其行为所生之罪的追诉的抗辩:(a)行为人不知规定犯罪之制定法或其他成文法规的存在,且在实行被追诉的行为时,其法令尚未公布或处于其他不能知悉法令存在的状态时;(b)基于相当理由,信赖包括:Ⅰ、制定法及其他成文法规;Ⅱ、法院的裁定、意见或判决;Ⅲ、行政命令或许可;Ⅳ、就规定该罪之法律的解释、适用或执行在法律上负有责任的公务员或公共机关正式解释等公开法律见解而实施行为,其后该法律见解变得无效或错误时。”第204条第(4)项还规定:“第三项之抗辩,被告人应以优越的证据予以证明。”由此可见,上述第(3)项的规定,实际上是对美国法院判例的条文化。《模范刑法典》公布后,美国许多州的制定法,都仿效了《模范刑法典》的“错误”条款。例如,《伊利诺州刑法典》关于“行为人合理地相信他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法律错误可作辩护理由的四种情况是:(1)这个罪是由尚未公布的而且行为人也不知道的行政法规或决议规定的,或者虽已公布但依据实际情况他是不可能知道的;(2)行为人行为的根据是后来决定被废除的法规;(3)行为人行为的根据是后来被撤销的法院决定或意见;(4)行为人行为的根据是由有解释权的官员对规定犯罪的法律、决议或行政法规所作的正式解释。(15)
由上可见,在美国的制定法和判例中,“不知法不免责”原则的例外已经得到普遍承认。美国之所以承认“不知法不免责”原则的例外,是“由于行政机关非常发展,在实际惯例上,行政机关的裁决在许多场合具有最终的决定力,因此,行政机关成了在各自的部门里具有权限的机关,故应允许个人信赖行政机关的解释。信赖具有权限的行政机关的意见的人,与其说具有违反法律的意图,不如说具有遵守法律的意思,因此,不能因为行政机关意见的错误而将行为人认定为犯罪人”。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生活复杂化,对于包含了现代商业生活最复杂局面的法规,信赖其专业人员的意见所实施的行为,没有理由追究行为人的责任”。(16) 正是由于社会的复杂化等原因,使得法官对法律的见解发生变化,使行政官与法官对法律的见解不同的情况增多,对因信赖其中一方而实施的行为不能予以责任非难的情况也逐渐增加。美国法院判例的变化正反映了这一点。
(二)英国违法性错误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英国学者Ashworth指出:“在英国,虽然不知或误解法律不成立抗辩,但该原则实际上已经被部分修正。”他列举了以下几点:其一,根据“不知法不免责”的原则,如果是对私法的认识错误就成立抗辩,如果是对刑法的认识错误则不成立抗辩,但有的场合,即使是对刑法的认识错误也可能成为抗辩,即有些场合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制定法规定的犯罪成立条件,没有这种认识就不成立犯罪。其二,更明显的例外是,1968年的《盗窃罪法》(Theft Act)与1971年的《毁弃罪法》(Criminal Damage Act)承认法律认识错误成立抗辩。《盗窃罪法》第21条第(1)项规定的是恐吓罪(Blackmail),作为成立条件的“要求”必须是不当的(unwarranted)。据此,既然被告人确信“其胁迫是实现要求的正当手段”,即使不合理也不能认定为不当的。即关于正当性的认识错误,在盗窃罪法制定以前不成立抗辩,但盗窃罪法制定之后成立抗辩。《毁弃罪法》第5条第(2)项规定,如果被告人认为其损坏行为被法律允许,则不成立犯罪。可见,在恐吓罪与毁弃罪方面,“不知法不免责”的原则已被修正。(17) 英国1946年《法律文书法》第3条规定,如能证明在被指控的犯罪实施期间,文书局还没有发行这部法律文件,这就是被指控犯有该罪的人的一个辩护理由。除非能够证明在所提出的犯罪实施期间,已经通过适当方式把该文件的大意通知公众和与之直接有关的人,或者通知了被告人。(18)“英国下议院并非没有意识到将行为人信赖官方指示而行事作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的一项抗辩。在1974年控制污染法中,行为人‘谨慎地获得了当地相关官员咨询意见后而实施行为’(took care to inform himself from persons who were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information)是没有执照处置废弃物行为(offence)的合法抗辩理由”。(19)
在英国1985年的刑事法草案以及修改后的1989年刑事法草案的起草过程中,英国的起草者们也讨论过像美国《模范刑法典》那样,对“不知法不免责”的原则作例外规定,特别是提出将信赖判例与公共机关意见而实施的行为作为抗辩理由。但讨论结果是不能承认上述情况为抗辩理由。(20) 对违法性错误仍然采取了与以往一样严格的态度,并没有像美国的《模范刑法典》那样对上述原则作例外规定。英国的司法机关也严格遵守“不知法不免责”的原则,不承认不知法律或误解法律是抗辩理由。
英国学者总结说:“在英国法律委员会1989年刑法典草案中,不知法不免责的基本规则被保留下来,但议会同时保留了创设例外条款的权利。而有关‘能够导致违犯行为(offence)缺乏过错要件(fault)的不知法律是合法抗辩理由’的现行规则也同样被保留下来。刑法典草案在第46条指出:符合以下情形,行为人触犯法律文件(a contravention of a statutory instrument)的行为不构成犯罪……(b)行为时,有关机关尚未采取合理的措施使该法律文件的目的与主旨(purport)为公众或可能受其影响的人或行为人所注意和知晓。”(21)
二、“不知法不免责”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嬗变
大陆法系各国,最早对判例所采取的传统观点提出异议的是费尔巴哈(A.T.Feuerbach),他从道义责任说的立场出发,主张故意之中包含违法性的认识。(22) 后来逐步形成了不同的学说。其一,违法性认识不要说。认为违法性认识不是故意的要素,行为人没有认识行为的违法性不影响故意犯罪的成立。违法性错误不阻却故意犯罪的成立,行为人仍构成故意犯罪。此说的理论基础是:(1)国民应当知晓法律;(2)“不知法不赦”、“不知法有害”的罗马法谚;(3)以违法性的意识为故意的要件会招致法律松弛。(23) 其二,违法性意识必要说(严格故意说)。认为故意的认识内容不仅包括对犯罪事实的认识而且包括对行为的违法性的认识。行为人如果没有认识其行为的违法性,就不构成故意犯罪;如果行为人对这种没有认识违法性有过失,而刑法又有处罚过失犯罪的规定的话,就按照过失犯罪处理。否则,就按无罪处理。因此,违法性认识是成立故意的必不可少的本质要素,是故意与过失的分水岭。(24) 其三,法律的过失准故意说。认为故意以有违法性认识为必要,但如果行为人虽然没有违法性认识,却对此有过失的话,这是一种法律的过失,对于这种“法律的过失”应当与故意同等看待,按故意犯罪处理。在存在违法性错误时,虽然阻却故意,不成立故意犯罪,但却要按照故意犯罪处理。(25) 其四,限制故意说(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说)。认为故意的成立,违法性认识是不必要的,只要行为人具有违法认识的可能性就足够。在行为人存在违法性错误时,还要具体分析行为人是否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则构成故意犯罪;没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不构成故意犯罪。(26) 其五,责任说。认为违法性认识及认识可能性不是故意的要素,而是独立于故意之外的责任的要素。故意的成立,无需违法性认识,但如果行为人没有违法性认识且没有认识的可能性,阻却责任;有认识的可能性则减轻责任。在行为人存在违法性错误的场合,在构成要件评价阶段,仍可认定为构成故意犯罪,但如果行为人没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则在责任阶段,排除责任;如果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则减轻责任。责任说目前在德、日刑法学界已有众多的追随者,并且德国法院也采此说。(27) 其六,折衷说。认为行为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违法,一般都不能作为排除犯罪的理由。因此,在一般情况下,行为人对违法性的认识,不是故意成立的必须的内容。但是在以下情况:(1)行为人认为自己行为属于刑法中的“正当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具有排除犯罪故意的效力;(2)在行为人尽最大努力仍不可能得到对法律规定的正确理解的情况下,行为人不知道法律的具体规定,也可以作为排除犯罪的理由;(3)尽管对违法性的认识不是故意的内容,但如果行为人既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违法,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的话,也应该排除犯罪的存在。(28)
大陆法系各国的立法、司法实践逐渐地摆脱了“不知法不免责”原则的影响。以下分别加以说明:
(一)意大利刑法关于违法性错误的规定
《意大利刑法典》第5条规定:“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责任。”这是在大陆法系刑法中最为典型地体现“不知法不免责”原则的立法例。但这一规定已被意大利宪法法院1988年第364号判决宣布为部分违宪。根据该判决,在行为人尽最大努力仍不可能得到对法律规定的正确理解的情况下,行为人不知道法律的具体规定,也可以作为排除犯罪的理由。(29) 对此,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帕多瓦尼指出:该判决的内容在实践上结束了是否应将危害行为作为故意认识对象的讨论。行为的“客观违法性”应该是故意的认识对象之一,因为它是使典型事实成为犯罪的法定条件。(30) 尽管意大利宪法法院的判决宣布《意大利刑法典》第5条部分违宪,在不具有知法的可能性的情况下不得适用刑法典第5条,但是多数刑法学者认为:行为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违法,一般都不能作为排除犯罪的理由。因此,在一般情况下,行为人对违法性的认识,不是故意成立的必需内容。(31)
(二)德国刑法关于违法性错误的规定
在1952年3月18日联邦法院刑事联合部对一个案件的决定中,对故意成立条件的解释清楚地表明:禁止的错误,在不能避免时,就阻却责任;在能够避免时,不阻却责任,但可以使责任减轻。(32)《德国刑法典》第17条规定:“(法律上的认识错误)行为人行为时没有认识其违法性,如该错误认识不可避免,则对其行为不负责任。如该错误认识可以避免,则对其行为依第49条第1款减轻其刑罚。”(33) 不可避免的法律认识错误可以免责,而可以避免的法律认识错误只能减责。德国著名刑法学家耶赛克在评论这一规定时指出:“我们首先可从反面推论,该规定已经明确地将不法意识作为完全责任非难的前提。该规定所积极肯定的是禁止的错误:如果行为人欠缺不法意识,若其不知是不可避免的,他所为的是没有责任的行为(第1句),行为人若能够避免错误,则故意的构成要件所对应的刑罚将根据刑法典第49条第1款的规定予以减轻处罚(第2句)。因此,不法意识构成责任非难的核心。因为无论是否充分了解面临的法律规范而作出行为决意,本身便表明欠缺法律心理,正是由于该欠缺才对行为人进行谴责。法律规范发出的法忠诚呼吁,应当对行为人的意志形成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有意识反抗法律者,表明一个认真的国民背弃对受刑法保护的法益的尊重要求。但是,即使行为人欠缺完全的责任非难所必要的不法意识,换句话说,即使存在禁止错误,也同样能够考虑责任非难,当其错误是可以避免的便属于该种情形。”(34)
(三)日本刑法关于违法性错误的规定
作为责任故意的要件,不需要违法性意识,这是过去有力的见解,但是,今日的学说几乎不采用它。(35) 日本刑法是更接近于违法性认识不要说的,1974年的《改正刑法草案》第21条规定:“虽不知法律,也不得认为无故意,但根据情节可以减轻其刑(第1项)。不知自己的行为为法律所不允许而犯者,就其事有相当的理由时,不罚(第2项)。”《日本刑法典》第38条第3款规定:“不得因不知法律而认为没有犯罪的故意,但根据情节可以减轻刑罚。”(36) 居于主流地位的判决一般采用违法性的意识不要说的立场,但也有许多下级法院在判例中开始承认法律错误在具有“相当理由”时,可以阻却故意和责任,违法性意识不要说的立场也开始动摇。从昭和40年开始,下级法院不断根据限制故意说或责任说的立场,作出“在违法性错误上,具有相当理由的场合,就不成立犯罪”的判决。此后,日本最高法院在1978年和1987年的两个判决中都肯定了在具有相当理由的场合,没有违法性就不成立犯罪的见解。(37)
(四)法国刑法关于违法性错误的规定
1810年《法国刑法典》对违法性认识问题未作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推定公民知法。1994年《法国刑法典》第122—3条指出:“能证明自己系由于其无力避免的对法律的某种误解,以为可以合法完成其行为的人,不负刑事责任。”法国学者在评论这一规定时指出:过去,法国刑事法律有一个始终得到最佳保障的信条,那就是:不考虑(行为人)“对法律的误解”。我们知道,按照最高司法法院原来的意见,所谓“对法律的误解”既不能构成“具有证明行为人不受刑事追究之效力的事实”,也不构成“得到法律承认的理由”。这一规则甚至扩张到行为人对法律的“不可克服的误解”(不可避免的误解)。所谓“对法律不可克服的误解”,是指被告不可能通过自己了解情况,或者不可能通过向第三人了解情况来避免其错误(误解)。尽管最高司法法院曾作过一项判决,似乎承认“不可克服的误解”可以看成是行为人不受刑事追究的原因,但是,法院后来作出的判决更加具有限制性:在后来的案件判决中,最高司法法院即使承认“误解具有不可克服性”,但仍然排除将这种误解作为“不受刑事追究的原因”。最高司法法院之所以采取这种严厉立场,完全是出于社会生活必要。然而,理论界却对法院判例采取的这种“不可弯曲的立场”提出了批评,特别是在行为人产生“对法律不可克服的误解”的情况下,这种立场更有待批评。对一个公民来说,要想尽知在《政府公报》发布的无数法律条文那可是太困难了。正因为如此,新刑法典最后草案的制定者在第42条中增加了一项条款:“能够证明自己系由于其不可能避免的对法律的误解,以为可以合法完成其行为的人,不负刑事责任。”(38) 从法国刑法规定来看,虽然在立场上确认了“不可克服的法律误解”可以阻却责任,但对不可克服作过于严格的限制解释,仍然会消解这一规定的意义。
三、“不知法不免责”原则在我国的嬗变与理性选择
我国刑法未规定违法性错误及其处理原则。刑法学界一般将法律错误称为法律上的认识错误或违法性认识错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及法律后果所作的主观评价与法律规范的评价不一致。具体来说包括三种情况:(39)(1)行为本不构成犯罪,但行为人却误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犯罪;(2)行为本身构成犯罪,行为人却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是犯罪;(3)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在刑法上的罪名、罪数、量刑等方面存在不正确的理解。可见,我国刑法理论所讲的违法性认识错误既包括行为人对行为性质的认识错误,也包括对法律后果的认识错误;不仅包括对自己的行为违法性的错误认识,而且包括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合法性的认识错误。其中的“法律”特指刑法,因此,违法性认识错误实质上是指刑事违法性的认识错误。其实,在我国上述法律上的认识错误的三种情形中,第一种情况、第三种情况与犯罪的成立与否无关,只有第二种情况才是国外违法性错误所研究的内容。
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对违法性认识错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违法性认识是否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和违法性认识错误是否阻却故意两个问题上。其主要观点与国外基本相同,但在内涵及表述上却存在较大区别:其一,违法性认识不必要说。认为违法性认识不是故意的内容,不阻却故意的成立。其主要理由是:我国刑法规范与我国社会主义的行为价值观、是非观是一致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及其结果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就会被刑法所禁止、所制裁,具有正常理智的公民都会了解这一点。因此,违法性认识是人们应当知晓的范畴,不存在有无的问题,故不需要考察有无违法性认识。(40) 其二,违法性认识必要说。认为违法性认识是故意内容,阻却故意成立。(41)“根据我国刑法主客观一致的原则,如果某个人不知道,而且显然没有可能认识到自己有意识的行为是违法的,因而也不可能认识到它的社会危害性时,应该认为是无认识,那就是意味着该行为欠缺意识因素,就不能认为他有罪过,也就不能认为他构成犯罪。”(42) 其三,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必要说。认为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是故意成立的要件,阻却故意的成立。如果有充分理由表明行为人虽然认识了行为事实,但确实不知且根据当时的情况也不可能认识行为是触犯刑法的,就不构成犯罪的故意。(43) 在我国上述学说中,“违法性认识不必要说”是通说。纵观世界各国违法性错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状况,我们可以看出如下发展趋势:其一,逐步修正其违法性错误的理论与实践,使之更加符合其国情。其二,在坚持“不知法不免责”原则的前提下,允许大量的免责或减轻责任情形的存在。其三,严格限定不知法律免责的条件,以避免以不知法律为理由而逃避刑事责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违法性错误理论也应当与时俱进,汲取国外违法性错误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和立法、司法经验加以修正。
首先,“违法性认识不必要说”的立论依据并非完全科学、合理,存在令人难以信服之处:其一,“违法性认识不必要说”已不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不知法不免责”的原则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当低下、法律关系简单且总量不大、自然法在法律体系中占据主要地位、统治阶级还可以经常采用超法律手段来解决被统治者的刑事责任问题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从20世纪初期开始的近一百余年来,人类在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法律已经成为社会管理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法律类别被不断细化,新的法律层出不穷,法律条文更是数不胜数。不仅一般公民无法知晓国家的全部法律规定,产生法律认识错误在所难免;即使是专门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的律师也只能熟悉部分法律,需要专业分工。“在当代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变动加快的时代背景下,情况就不同了。新的法规不断涌现,一年的立法量超过工业革命前一个世纪甚至几个世纪的立法量。人们很难在有限的时间内了解那么多的法律,特别是有些专业性条例和行政性法规,它们同千百年来逐渐形成的道德规范联系很少,因而不容易凭社会习惯和生活常识来判断这种行为是否违反法律。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不看具体情况再死守‘不知法律不免罪’这个原则,有时就会同人情道理相悖。”(44) 当然,笔者也注意到,关于违法性认识的程度,即其中“法”的内涵与外延有“实质违法性说”、“刑事违法性说”、“违反整体法规范说”等多种观点。(45) 在我国,违法性认识一般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是否违反刑法禁止性规范的认识。即便如此,“在附属刑法中,有着数以千计的刑法条文,没有人能够记住”。(46) 因此,“违法性认识不必要说”“如适用于古代社会,其时道德与法律并无显著之区别,人民对简单之行为规范,成知共守,固可自圆其说。至于现代社会,法令纷繁,虽司法之士,亦未必尽知,焉能期待人尽皆通晓,且法律为抽象之规定,常需间接推理,始能体会,是以法律之认识较之事实之认识,更为不易。则传统主张法律错误,不能阻却责任之理由未能说明矣。”(47) 其二,在现实生活中,国民不知晓法律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国民应当知晓法律,纯属一种法律拟制。这种假设是一种国家专权主义的表现,不符合民主社会发展的要求。在现代刑法理念中,罪刑法定原则已经深入人心,合理划分由司法机关行使的刑罚权与公民享有的自由权之间的界限,使刑法成为了公民乃至犯罪人的大宪章。只有在行为人意识中存在规范的或违法的认识,才能期待行为人形成不实施犯罪行为的反抗动机,正是因为行为人存在违法的认识,却违背了法规的期待,实施了行为,才能够对行为人进行法律上的非难。(48) 因此,国民应当知晓法律的法律拟制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存在着冲突。同时,主张“违法性认识不必要说”的学者也承认,虽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违法性是互为表里的,认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自然也会知道这种行为是为法律所禁止的,不需要把违法性的认识专门列为故意的内容,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绝对化,不能排除个别例外的情况。(49) 这种例外情况就是某种行为一向不为刑法所禁止,后来在某个特殊时期或某种特定情况下为刑法所禁止,如果行为人确实不知道法律已禁止而仍实施该行为的,就难以认定行为人具有犯罪的故意。(50) 可见,推定国民应当知晓法律的“违法性认识不必要说”理由过于绝对化,与罪刑法定原则保证公民权利的本质特征相冲突。其三,“违法性认识不必要说”无论是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都随着历史的发展在逐渐没落,乃至于现在持此学说的学者几近于无。(51)
其次,严格限定不知法律免责的适用条件,不会招致法律的松弛或鼓励法盲。有人认为,如果要求公民对刑事违法性有认识,则会导致公民主观认识因素成为判断行为是否犯罪的重要因素,法盲的存在就会合理化,法盲不知法而免责也会成为犯罪分子逃避法律惩处的借口。因为,不知法本身就是有害的,其害并不比知法犯法之害小。所以,刑事违法性认识肯定论的观点最终将导致国家对犯罪的惩处而自身所设立的法律受到阻碍,刑法的实施将变得艰难,刑法的目的也难以实现。(52) 其实,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对于因正当理由而存在违法性错误的行为人免除或减轻刑罚处罚,只是作为一种例外,数量不会太大,而对于没有正当理由而存在违法性错误的行为人并不能免除或减轻刑罚处罚。正如陈兴良教授所指出的:以为将违法性认识作为归责要素会大量地放纵犯罪,这未免是危言耸听。就自然犯而言,从其客观行为中一般都可推导出主观上的违法性认识,而要提出反证几乎是不可能的。至于法定犯,尤其是发生在各个经济领域的经济犯罪,主体均为从事各特定行业之业内人士,其违法性认识也可直接推定,除非在极个别情形中存在反证。因此,对于归责要素的违法性认识,是必不可少的,也并非不可证明。(53) 同时,我国历来有“不教而诛谓之虐”的古训,这是儒家文化中具有人本内涵的政治遗产之一。因此,教——也就是教化,应该是国家的职责。公民对法律的不知乃至于误解均是国家不教之过。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应当将其不利后果转嫁给公民个人,就在我国这样一个公民法律认知程度不高的国家,尤其应当避免不教而诛,应当通过普遍而深入的法制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认知程度。“对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的人进行非难,是不当的、苛酷的,无益于行为人规范意识的觉醒。”(54)
第三,合理确定违法性错误的地位,不会引起我国刑法理论体系的崩溃。我国刑法学界有人担心,“如果将违法性概念引入,不但涉及犯罪故意概念的变化,更会导致犯罪概念、犯罪构成理论乃至整个刑法理论大裂变,毫不夸张地说,这将意味着传统刑法理论大厦的崩溃,现行刑法也不得不因此而作休克性修改。”(55) 笔者认为,只要合理确定违法性错误的地位,不会引起我国刑法理论体系的崩溃。其一,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存在更大的差异。英美法系犯罪构成采取的双层次模式:第一层次是犯罪本体要件,包括犯罪行为和犯罪心态。第二层次是责任充足要件。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采取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的“三元”模式。而我国犯罪构成理论采取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的“四个方面”模式。既然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犯罪构成理论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可以存在违法性概念,也可以存在违法性错误处理原则及其例外,而更加接近大陆法系的我国刑法理论也理应可以容纳违法性错误理论。其二,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存在许多相同之处。国外的犯罪论体系均包括客观要素和主观要素,其犯罪成立的条件中都包含了责任要素。正如我国学者所指出的:各国刑法总则,通常都规定了责任能力、故意过失、错误,这便是对责任的规定。概括起来,责任的要素包括责任能力、故意过失、违法性的意识与期待可能性。这些要素决定了责任是否存在。但对上述要素的地位或相互关系仍然有争议。(56) 就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而言,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需的,行为人具备的刑法意义上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其中的辨认能力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在刑法上的意义、性质、后果等的分辨识别能力,即行为人认识自己行为是否为刑法所禁止、所谴责、所制裁的能力。可见,辨认能力本来就是针对行为事实及其违法性而言的,包括了行为事实的辨认能力和违法性的辨认能力。因此,在我国犯罪构成的理论中,违法性认识实质上已经作为责任要素包含在行为主体的责任能力之中了,属于行为主体辨认能力之一。如果行为人有正当理由能证明自己是由于不可避免的原因,确实无能力认识自己行为违法性的,可以考虑其属于无责任能力人、减轻责任能力人。在这种情况下,违法性认识能力就被刑事责任能力所包含,在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中就不需要再考虑行为人是否认识到了行为的违法性,从而避免了违法性认识是否犯罪故意内容的长期争论,并保持了我国刑法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也体现了我国刑法理论对大陆法系、英美法系有关违法性错误理论的扬弃。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借鉴违法性错误理论与实践最新成果,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我国《刑法》“犯罪与刑事责任”一节中明确规定:“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责任。但行为人有正当理由能证明自己是由于不可避免原因,确实无能力认识自己行为违法性的,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节免除、减轻或从轻处罚。”然后,再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对“正当理由”和“不可避免”的判断标准进行严格的界定,以避免该规定被滥用。行为人的违法性认识能力应当综合考虑行为人的社会地位、个人能力、个人认识能力及价值观念的合理运用等进行判断。当行为人对于其行为是否涉及不法有所怀疑时,行为人即负有查询义务。“避免一种禁止性错误的手段是思考或者询问。更准确地说,这种可避免性取决于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是相互依赖建立起来的:行为人必须本来有机会对自己举止行为可能具有违法性进行思考或者询问。在存在这个机会时,行为人必须完全不去努力查明真相,或者这种努力必须非常不充分,以至于从预防的观点来看,不能认为排除责任是正当合理的。当行为人不顾自己当时已经具有的机会,仅仅在一个过分狭窄的范围内来努力认识法,那么,就只有当他作出了足够努力来认识不法时,他的禁止性错误才是可以避免的”,“当有人尽管缺乏法律知识,但是依靠自己业余学习文献,形成了一种在结果上与值得信赖的法律工作者在实施构成行为不端时所说的相符合的法律意见,这时也仍然同样必须把禁止性错误作为不可避免看待。”(57) 因此,对于确信自己之行为合法,应有客观的根据,这些根据包括:(1)行为人因客观事实不知法律;(2)信赖法规、判决或解释;(3)信赖公务机关见解;(4)信赖专业机关见解;(5)信赖专家意见;(6)其他客观情况。
注释:
①Cross & Jones,Introduction To Criminal Law,para,6.72( 11th ed.R.Card 1988) 。
②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201页。
③林山田:《刑法通论》,台大法律系1998年增订六版,第178-179页。
④[日]大谷实:《刑法总论》,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页。
⑤参见[英]J·C·史密斯/B·霍根:《英国刑法》,李贵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以下。
⑥Blackstone: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27( 1765) 。
⑦J.Hall:General Principles of Criminal Law,380( 2d ed,1947) 。
⑧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以下。
⑨J.Austin: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497( 4th ed,1879) 。
⑩同注⑤引书,第95页。
(11)张明楷:“英美刑法中关于法律认识错误的处理原则”,载《法学家》1996年第3期。
(12)Michael L.Travers:Mistake of Law in Mala Prohibit a Crimes,62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1301( 1995) :UNITED STATES v.MURDOCK,290 U.S.389( 1933) 。
(13)参见冯军:《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206页。
(14)Arnold H.Loewy:Criminal Law,4th Edition,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英文影印本),第142-143页。
(15)同注⑧引书,第94-95页。
(16)[日]福田平:“关于法律错误学说的考察”,载《神户法学杂志》1952年第2卷第1号。
(17)Ashworth:Excusable Mistake of Law,( 1974) Crime.L.R.652。
(18)[英]鲁伯特·克罗斯等:《英国刑法导论》,赵秉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
(19)Michael Jefferson:Criminal Law,5th Edition,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英文影印本),第287页。
(20)The Law Commission,Criminal Law,A Criminal Code for England and Wales,vol.2,para.9.6。
(21)同注(19)引书,第288页。
(22)刘明祥:《刑法中错误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23)同注④引书,第256页。
(24)同注②引书,第207页。
(25)刘明祥:《错误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117页。
(26)[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2页。
(27)[日]木村龟二:《刑法学词典》,顾肖荣等译,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55页。
(28)[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评注版),陈忠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188页。
(29)陈忠林:《意大利刑法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30)同注(28)引书,第187页。
(31)同注(29)引书,第121页。
(32)洪福增:《刑事责任之理论》,台湾刑事法杂志社1988年版,第153页。
(33)徐久生/庄敬华译:《德国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34)[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538页。
(35)同注(26)引书,第391页。
(36)张明楷译:《日本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37)同注④引书,第262页。
(38)[法]让·帕拉德尔/贝尔纳·布洛克:《法国新刑法典》,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309页。
(39)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版,第158-159页。
(40)高铭暄主编:《新编中国刑法学》(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页以下;王作富主编:《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41)贾宇:“论违法性认识应是犯罪故意的必备条件”,载《法律科学》1997年第3期。
(42)朱华荣:“略论刑法中的罪过”,载甘雨沛主编:《刑法学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
(43)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7页。
(44)同注⑧引书,第94页以下。
(45)莫晓宇:“知与恶——故意犯罪中的违法性认识”,载《法学评论》2006年第4期。
(46)[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犯罪原理的基础构造》,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12页。
(47)林瑞富:“阻却责任事由各国立法理由之比较研究”,载《台湾刑事法杂志》第28卷第3期。
(48)同注(45)引文。
(49)陈兴良:“违法性认识研究”,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4期。
(50)同注(40)引书,第173页以下,第88页。
(51)赵秉志主编:《刑法总论问题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52)刘艳红/万桂荣:“论犯罪故意中的违法认识”,载《江海学刊》2003年第5期。
(53)同注(49)引文。
(54)李海东:《日本刑事法学者》(上),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成文堂1995年版,第155-156页。
(55)谢望原/柳忠卫:“犯罪成立视野中的违法性认识”,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3期。
(56)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199页。
(57)同注(45)引文,第625、6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