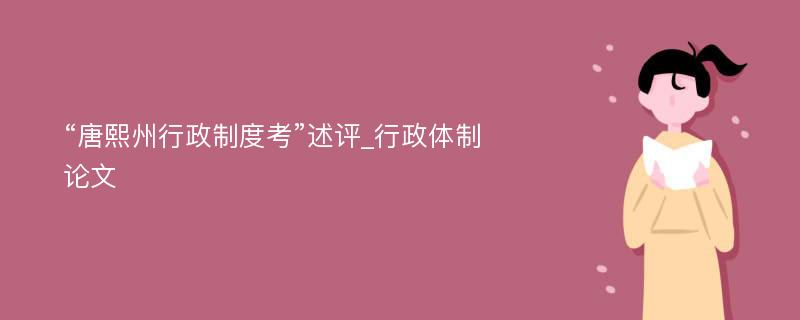
《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评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论文,行政论文,唐西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代的西州,从贞观十四年(640)设立,到贞元十一年(795)被吐蕃占领,存在了150多年时间。虽然西州存在的时间不太长,没有与唐朝共始终,但西州存在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所提供的历史资料,比唐朝其他任何地方所提供的历史资料都丰富得多。这些资料,目前统称为“吐鲁番出土资料”,主要包括出土文书和墓志等。利用这些资料,学术界在唐代的土地制度、军事制度和人口等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大有进步。唐代前期的地方制度,传世史籍虽有简略的介绍,但留下了太多的空白,吐鲁番资料这方面的内容,则是空前丰富的。遗憾的是,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却比较薄弱。李方的大作《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充分利用这些新的出土材料,结合传世的史籍文献,深入进行研究,成为今天这个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
吐鲁番有关唐代地方制度的历史资料虽然十分丰富,但由于这些材料当年作为废弃的官府文书制成葬具,或剪成鞋样,或裁成帽状,埋葬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两个古墓群中,文书的残片断字太多,真正利用这些资料,首先有一个艰难的识读过程。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出土的官府文书,都是当时行用的原始实物,文书的格式、简称、略语、习惯用法等等,对于今人而言,都是难以逾越的阅读障碍。于是,构成了这样一种现象:这些资料可以证明当时的制度,但不明白当时的制度就很难阅读这些资料;大家都知道吐鲁番文书中蕴藏着重要的地方制度资料,但阅读的艰难让很多人望而却步。李方却知难而上,于是有了《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的出版。
李方很早就开始了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她本科时就学于武汉大学,而武汉大学历史系是研究吐鲁番文书的中心,这种教育背景是不容忽视的。工作以后,她曾出版《敦煌论语集解校证》一书,虽然属于古籍整理类,但由于此书乃整理研究近七十种敦煌、吐鲁番文献而成,因此,实际上也涉及到古文书的识读工作。她参加过唐代出土墓志的整理工作,对于别字、俗字等也有学术上的训练。她又主持过《吐鲁番出土文书人名地名索引》的编撰工作,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全面系统整理,更奠定了后来研究的基础。
《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是李方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在博士论文之前,她已经有了许多相关研究,特别是一组西州官吏的系统考证论文,赢得了学界的公认和好评,甚至成了其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李方已经成为最熟悉吐鲁番文书的学者之一,尤其是西州部分的吐鲁番文书。
《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共有五章:第一章是西州都督府(州)县司机构;第二章是西州上佐、参军的职掌;第三章是西州官吏的兼摄及升迁;第四章是西州官府的运作及相关制度;第五章是西州的少数民族部落及其相关问题。这些章节利用新资料,或者推陈出新,或者另辟蹊径,不仅注意讨论官制中的具体问题,而且重视体制的整体运作;不仅注重西州地方的特殊性,而且注意与唐朝地方制度的总体关系。因此,《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虽然讨论的核心是西州地方行政体制,但实际上对于唐朝特别是唐前期的地方制度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西州地方与内地相似的有关制度,这部专著提供了目前唯一系统的论证。
贞观十四年(640),唐朝灭高昌王国设立西州,同时在西州设立安西都护府,后来,安西都护府迁移到龟兹(今库车),中间又有几次回迁。安西都护府的军事职能很明确,那么它与西州是什么关系呢?学界对此有不同看法。有一种看法认为,当安西都护府驻地西州时,西州不再设都督府,而降格为西州。李方不同意这种看法,并提供了足够的资料,证明西州从显庆三年(658)安西都护府迁往龟兹以后,就一直是都督州。唐朝地方建制最重要的是州、县两级制。州一级以长官名称区别,可以分为都督州与刺史州。都督既是动词也是名词。如果都督(动词)多州,则长官都督(名词)同时担任首府州的刺史,而其他一般州的长官只是刺史。在特殊地区,虽然只都督一州,也是都督州。长官的名称既可以称为都督,也可以称为刺史。而这样一来,容易造成与一般刺史州长官的混淆。李方辨明资料,确证西州为都督州。
利用出土资料与传世资料共同考证历史,是历史学的二重证据法。但是,出土资料与传世资料记载有时会有出入或矛盾,这是历史考证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传世的典籍记载,唐代的县级机构中,除京县、畿县之外,一般只有二曹,即户曹和法曹。但在西州的资料中,李方经过认真考证,发现除了户曹和法曹之外,还有兵曹,这就超出了历史文献的记载。于是,联系到学界曾经讨论过的敦煌县是否存在司兵的问题,大谷文书2840号表明,敦煌县是有一个司兵机构的,但学者多不认可。从吐鲁番到敦煌,都出现了县级司兵,李方因此肯定新资料的价值,指出县级设立司兵,在唐代并不是偶然现象,不能因为传世史籍没有记载就否认出土史料的意义。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县级机构的新认识,而且提供了研究方法上的新启示。
当然,吐鲁番出土地资料并非都与传世史籍的记载相冲突。李方指出,比如州上佐(长史、司马和别驾)这一职务,根据《唐六典》等文献的记载,其主要职掌是辅佐州长官纪纲众务,具体责任是充当朝集使入京奏计,在处理文书时充当通判官。这些在吐鲁番出土资料中都有证明。再比如别驾,史籍记载通常由皇族担任,而且多不赴任。吐鲁番文书中,别驾确实少于长史和司马,与史籍记载相吻合。这些都反映出西州在制度上与内地一般州总体上是一致的,西州的资料可以证明内地相同的问题。另外,西州属于边州,又有自己的独特性。这个问题在上佐的职掌上也充分地反映出来。比如,长史的具体职掌,在西州的资料中可以看到是负责民族事务,负责差兵,甚至判县事。而司马,掌兵员配置,专知仓库,判勾官等。中原地方的上佐是闲散冗官,西州的上佐工作却很繁忙。
这一类问题,当然不仅表现在西州上佐的职掌问题上,参军的职掌也一样。按照《唐六典》的记载,参军的职掌主要是“出使、检校及引导之事”。李方通过吐鲁番出土资料,为理解这个记载提供了翔实的证明。比如她指出,参军检校就是兼任其他职务,西州参军不仅检校勾官、检校功曹、检校仓曹、检校户曹、检校兵曹,而且还检校仓督等职事。而在中原,传世文献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参军事多是休闲无事,在西州,参军却很繁忙。新出考古资料,提供了更丰富的证明,经过李方的论证,也丰富了我们对于唐代地方体制的认识,或者有助于我们对传世资料的认识,或者提升了我们的认识,至少不会再局限于传世文献的记载。
设官分职,在政务分工的基础上设立官职,以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这是我们对官制甚至政治制度的通常想法。我们了解的中央集权体制,更把这个行政原则推广到各个地方,以至于地方与中央的机构往往对应存在。但是,如果仅仅这样理解,就会出现粗疏的过错,因为在地方上,官吏之间的兼摄十分多样化,如果完全按照官吏的名称去理解他的日常工作,可能完全不着边际。是李方对唐代西州的具体研究,纠正了我们过于简略的印象。李方研究西州的兼摄官,分成参军检校、差遣官、摄官、一般代理等四种类型,同时指出西州兼摄官的特点就是临时性,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原来制度的因素,如参军检校本来就是制度的规定,说明制度之中原本就存在地方官员的兼摄基础;又有盛唐以后新情况的因素,即差遣官系统的发展;还有西州独特的地方因素,即边疆地区阙官多,战事多,官员之间互相兼职,有不得已的理由。
西州因为资料相对丰富,李方把西州当作了解唐代地方体制的一只解剖的麻雀,所有的论题既有西州特色但又不局限于西州。地方官员的升迁,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唐代,对于官员的任命和升迁,有一定的回避制度,但是吐鲁番出土的资料却显示,这种回避制度是很有限的,因为西州更多的地方官员都是就地升迁的,对此,李方搜集了大量证据,并进而区分出两种类型,一是胥吏升为判官,一是品官升为高级官。一般官员如此,高级官员也如此。比如最高的地方长官西州都督,裴行俭就是先当西州都督府长史后来升为西州都督的。文官如此,武官也如此。为什么会是这样,李方不仅提供了资料,而且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一方面“与唐前期社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同时“与西州地处边疆有密切的关系”。
当然,一部著作因为涉及到太多的资料,在具体资料的理解上难免有仁智之见。论证过程中,资料的取舍问题也会因人而异。但是,这些对于这样一部建树甚多的学术著作而言,都不是必须举证的问题。
李方研究西州行政体制,是把西州作为唐朝前期地方制度的一个特例来进行分析的,所有章节的基本思路都是如此,给我们的启发也是如此。通过阅读,我们不仅了解了西州的具体问题,透过西州,更了解到唐代前期地方体制的基本状况和差异。这里,不必再把这部著作的各个章节都一一介绍,因为每一章节的学术价值都是很高的:既有新资料,又有新问题,更有新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