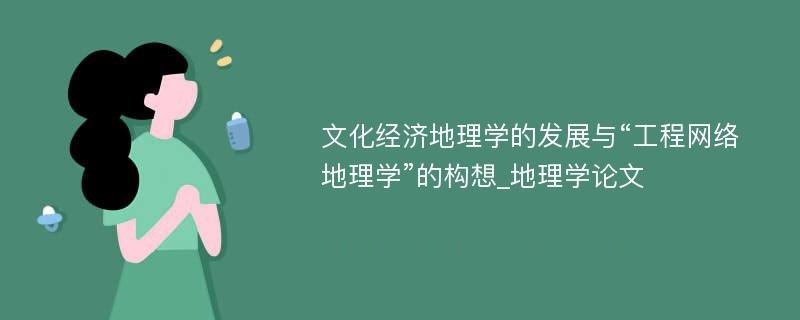
文化经济地理学进展与“项目网络地理学”的提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地理学论文,地理学论文,进展论文,项目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0-02-25
中图分类号:F11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0)02-0001-07
1引言
西方发达国家从撒切尔-里根时代强调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开始,有关“文化”与“经济”相互对立的旧有认知,逐渐解体,文化(艺术)的经济价值日益超越其教化与美学的传统价值,文化创意产业逐渐成为1970年代末期以来,西方国家从城市、地方到区域,探讨解决传统制造业全球转移所致产业空心化和经济衰退问题的重要举措,推动了西方国家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转型;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后,文化领域逐步开放,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日渐推进到文化体制改革,有关文化事业单位的改制问题、以及随后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创意产业理念,进入政府、媒体和学界的视野[1],2009年国务院正式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①,标志着中国对文化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的全面认同。目前,国内外对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经济的关注,从政府文件、会议论坛、论文发表、图书出版、网站建设、机构设立、高校招生、媒体报道等多个方面,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西方地理学界最近提出“文化经济地理学”分支学科的说法[2],一方面反映了地理学界试图通过学科内部的回顾总结,突出自身对“文化经济”的研究关注;另一方面,也案例式地具象化了西方经济地理学学术取向,如何逐渐摆脱先前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导的研究思路,转而接受“文化转向”的影响。中国地理学家也初步介绍了(西方)地理学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1,3,4]。本文试图在相对广阔的人文社会科学版图,进一步说明地理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和学术地位,思考文化经济地理学如何深化研究途径,初步提出“项目网络地理学”的研究议题。
2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学科以及地理学的相对缺失
不论西方世界还是中国,有关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政策话语的正式提出,主要开始于新千年以后,以英国政府的创意产业报告[5]及其全球影响为标志。当然,早在此前,学术界特别是“二战”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领域,非常重视对当时美国经济高速繁荣时期“文化工业”的批判及其“消费”问题的关注;不过,涉及文化“生产”方面的研究相对较晚。尽管如此,早在1980年代中期,地理学家就发表了好莱坞电影产业的研究论文[6]。不过,这一今日被归为文化经济的研究主题,一度让位于有关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创新为主题的经济地理学,可能因为以美国硅谷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比文化经济更为突出。尽管如此,文化产业对地理学家的吸引力,从新千年以后逐渐恢复,西方地理学期刊如《环境与规划A(Environment andPlanning A)》在2002年、2006年分别组稿发表“新媒体”专辑[7]和“创意经济”专辑[8],《增长和变化(Growth andChange)》在2008年组稿发表了“文化商品链”专辑[9],《经济地理学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也在同年组稿发表“地理学与文化经济”专辑[10],地理学家还编辑出版了《文化经济读本》[11]。
地理学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关注,延承了学科本身的旧有传统,即主要将研究取径关联于一贯感兴趣的有关全球化或全球生产链、城市化、产业集群、产业区、城市和区域发展等经典问题;通过揭示创意、创新或文化创意产业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影响,实现其政策应用价值。当然,地理学家参与讨论“文化经济”或“文化创意产业”新概念时,提出了“认知—文化资本主义(cognitive-cultural capitalism)”[12],强调当前和未来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标志就是文化经济。
相比地理学家在工业地理学、城市化和区域发展、全球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地理学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真正关注才刚刚开始[10]。地理学有关文化创意产业的区位、空间和地方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文化经济的就业、公司和产值等主要指标的地图绘制、以及区位变动情况的分析等等,这类研究虽然非常直观地提供了文化经济的基本信息,但其研究价值并未被地理学圈外广泛认知②。不过,西方地理学者最近几年所开展的与现实和政策更紧密关联的研究,逐步显示出地理学家日益强大的政策影响力和学术建构力,例如,英国地理学家Andy C.Pratt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贸发大会(UNTCAD)所做的研究,包括文化经济统计[13]以及被译成中文出版的《2008文化经济报告》[14],推动了国际社会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倡导和相关政策的制定;美国地理学家Richard Florida有关“创意阶层”和“创意城市”的研究③,富有广泛影响力,为文化经济开辟了新的领域和政策视野。
不过,中国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的地理学者屈指可数,且主要关注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和园区现象[15-17]、包括城市文化设施或文化空间的布局问题[18,19],不仅没有成为中国人文地理学内部的重要研究方向,也没有进入推动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知识话语和决策核心。事实上,中国制定文化创意产业政策所依据的知识来源,除了通过各地文博会或论坛等形式,邀请国外政府、学界、业界人士发表言论,从而获得西方经验以外,国内学者的知识贡献相对有限,且参与者主要不是地理学家,而是多年来组织出版地方性(如深圳、上海、北京)和全国性年度文化蓝皮书的主编和作者[20,21],这些作者当中很少有地理学家。中国地理学一直强调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方向,但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差距很大,急需重视。
“文化创意产业”常常与“创意产业”、“版权产业”、“内容产业”、“文化产业”、“数字内容产业”等说法混用。我国主要使用“文化产业”,以区别“文化事业”,但目前日益流行“文化创意产业”一词,它被认为广泛涉及电影、电视、出版、音乐、新媒体、计算机游戏、动漫画、广告、视觉艺术、建筑和设计、表演艺术、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多个领域。我国对文化产业范围的划定,主要以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为标准④,除了包括以上类别,还特别包括类似电视机、照相机、计算机这样的文化产品和设备制造部门⑤,不过,研究者和决策机构主要关注基于文本、符号、内容、创意、艺术、设计、版权的核心门类,因此,与核心门类密切相关的一些学科,特别是“文化研究”、媒体和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文化与艺术经济学、媒体经济学、文化与艺术社会学、艺术管理学、以及关注文化创意公司的组织研究、经济社会学等等,构成了当前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学科。
其中,“文化研究”以及媒体和传播学的很大部分主要关注媒体文本的“内容”表达、符号学批评,说明媒介(内容)对社会的框架作用和认知建构,而文化研究的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批评文化艺术商业化过程的负面影响;媒介或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偏重于讨论媒体产业所有权集中与垄断对公共价值的侵害、以及权力与产业的关系;社会学视角多关注公众的媒体接受与文化艺术消费问题[22],最近,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创意劳动(力)问题[23];媒体经济学和文化艺术经济学试图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概念,例如“公共产品(merit goods)”概念,讨论文化艺术的价值和独特性,特别是通过对表演艺术“成本弊病”的揭示[24],说明政策补贴的合理性;受到新经济社会学影响的组织研究和管理学领域,主要关注文化、艺术、创意产业的职业分工与合作生产等组织过程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官方政府特别是国家政府和超国家机构,如欧盟(EU)、联合国(特别是UNESCO和UNTCAD)、经合组织(OECD)、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等,推动了文化(产业)政策和贸易问题的关注。
从目前流行的文化产业教科书[22]以及文化经济学手册[25]所罗列的广泛主题来看,很多议题尚未进入(经济)地理学视野或关注甚微,例如,文化产业内部的合作生产与组织问题、文化产业的价值链开发、文化内容和符号的创作与解读、文化产品的市场营销和消费、创意和创新研究、创意阶层和劳动力市场问题、文化艺术公司的运作和管理、文化产品的价值理论和价格问题、文化产业投融资问题、文化产品的版权交易和法律问题、国际贸易问题、文化产业政策等;当然,与空间有关的议题,如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和园区、创意城市、文化产业与区域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地域分异和全球分工等,逐渐显示出地理学视角的独特贡献。虽然理论上,几乎所有与文化创意产业有关的各种议题,都具有(明显或不明显的)空间性,都值得采用地理学视角加以关注,但地理学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对忽视,被批评为是对地理学的某种讽刺,特别是对文化转向之后的地理学的讽刺[26]。
3地理学介入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文化经济地理学⑥
运用地理学视角关注文化创意产业的学者和研究成果,尽管相对有限,但最近有增加趋势,主要表现在西方学术界,不仅在地理学圈内,而且在地理学圈外受“空间转向”影响的其他学科⑦,也开始有意或无意地运用了关注空间的地理学视角,开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跨学科研究。地理学内部发出了“文化经济地理学兴起”[2]的声音。
3.1经济地理学的介入
经济地理学的加州学派(Californian school)主要关注并解释文化创意产业在城市和区域空间中的区位分布与变动问题[27],如洛杉矶电影产业区位分布的变化[6],与该产业逐渐走向弹性生产方式有关,电影产业从集中到垂直解体,意味着电影产业的投资、制作、发行、放映等环节相互分离,电影制作公司从集中于“好莱坞”走向分散分布,甚至走出国门,以至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28]发展成为美国好莱坞电影的拍摄基地[29]。这种偏重于从城市、国家、跨国、全球等宏观地理尺度,考察特定门类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延续了以往经济地理学对全球生产网络(GPN)或劳动分工之空间表现的传统主题[27]。不过,经济地理学对于GPN[30]或跨国生产体系地域分工和地域关系的注重,逐渐构成了从传统经济地理学依据地域资源禀赋,解释产业和区域发展,转向重视社会空间“关系”视角的曼切斯特学派(Manchester school)关系地理学[31],强调非经济、非贸易关联性[32]的重要,特别是创意人才之间的关系和人际网络资源(而非公司间业务关系),对于创意公司区位选择和创意产业发展,更为关键[33]。
经济地理学家还试图解释文化创意公司为什么表现出“共处(co-location)”城市内部特定空间、形成创意集群的现象,例如,伦敦影视后期制作公司集中在Soho区,主要原因不是房租便宜,而是为了获得非正规知识、新想法以及密集的交流和互动[34];广告创意人员集中在此,并不只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是因为Soho提供了一个可供人闲逛(hanging out)、从外围建立合作网络关系并进入网络中心的场地[35],这些解释与传统经济地理学将(制造业或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解释,要么归功于劳动力或人才市场的汇聚、中间或互补性产品及服务的供应、知识溢出等产业因素所带来的内部经济,要么归功于Jacob所说城市本身的外部性经济[36],有所不同。构成了有关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强调社会关系网络的集群研究范式(cluster paradigm)[37]。对创意集群的深入探讨,必然走向对创意(creativity)、创新(innovation)、知识和学习的研究,因为文化创意产业本身就是基于符号、文本、情感、知识和学习的“认知—文化经济”[12],在这一研究中,经济地理学家特别强调地理空间临近性,有利于面对面非正式交流,形成默会知识、实践知识和创意场域[38];受到文化转向影响的经济地理学者,将研究尺度缩小到工作场所,考察文化经济合作过程中能力信任关系与情感信任关系的建立与知识转移[39];少数学者进一步分析了知识的空间性以及流动性,说明本土知识或地方知识的价值,以及知识的跨国流动、多国文化公司和全球管道对于文化经济的作用[40]。这类强调对文化创意产业(如广告业[41])的理解,要关注对知识、学习、创新、创意机制的考察以及地理临近性的作用和创意环境(milieu或buzz)的研究主题[42],构成了所谓地理学研究文化经济的斯堪的纳维亚学派(Scandinavia school)⑧。当然,最近十几年来以制度学派为研究特征和实用导向的经济地理学,主要强调地方语境与情境(context)因素,特别是地方、区域和国家的产业政策、管制方式等等,对于文化经济活动(如广告产业[43]、媒体产业[44])及其空间性的影响。
总之,经济地理学所参与的文化经济研究,虽然还相当零碎,基本体现了西方经济地理学从传统视角到关系转向、制度转向和文化转向[45]的各种影响。从经济地理学家对文化创意产业各类指标分布图的制作、集聚形态的辨识和解释、到产业内部关联性(包括全球分工和生产网络)机制的考察、再到更为抽象的学习、知识、创新和创意研究及其地域表现、或地理临近性作用的研究,构成了西方经济地理学对文化经济研究的基本贡献。
3.2城市地理学的介入
文化创意产业空间分布的另一特征表现为城市指向、特别是集中分布于所谓“世界城市”的区位特征[27],这一现象被解释为城市相对于农村、大城市相对于小城市,具有独特的有利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软”区位因素[46]。不过,城市地理学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从关注城市本身,转向关注文化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城市因素,这与关注产业本身(对城市发展和城市空间影响)的经济地理学思路不同,或者说本体论不同,例如,早期关注城市更新问题的(城市地理学)学者,主要说明艺术家和创意人才如何通过对城市废弃空间的绅士化过程,推动城市复兴;而后来关注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地理学)学者,主要说明城市旧工业建筑为艺术家如何提供了有利于创意和创新的loft式工作室[47],并发展成为创意空间或集群。
这种城市地理学的经济地理学融合,或者说经济地理学的城市地理学融合,推动了地理学者从城市出发,阐明创意人才为什么因城市本身(而非公司)受到吸引。强调城市所具有的集聚化和网络化功能,有利于创意和创新所必须的社会交往,当然,城市所提供的实质性特征,也很重要[8]。例如,城市的尺度不大不小,小到可以影响当地文化、大到可以作为通往全球的门户,为国际市场提供通道[48],非常适合文化产业的发展;城市的人口密度高,有利于创意阶层与不同人群发展和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49];城市所提供的适合休闲和美学感觉的自然与建成环境、文化艺术设施、娱乐场所、俱乐部、艺术家工作室、创意集群等等,构成了某种独特的创意环境和氛围,有利于创意人员的社会交往、同行关注[37]、情报分享、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的知识转移和溢出;城市的多元文化和多样性品质,能够提供某种允许某些特殊人才在特定地点和时段自由发展的舒适“道德温度”[50]。
3T创意城市理论[51]强调城市的宽容度(tolerance)、以及高度汇聚的技术(technologies)与人才(talents),特别有利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随着更广义的创意经济以及知识经济的提出,人人都有创造力的观点,获得了支持,创意城市理论通过吸收洛杉矶学派的观点,强调建设合作型文化社区,激发城市普遍创造性[52],形成聪明城市、智慧城市或3C城市,即具有创造力(creativity)、竞争力(competition)和社会凝聚力(cohesion)的城市[53]。创意城市的发展还可通过建立城市之间的合作网络,释放和实现城市的创造力,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创意城市网络(global creative cities network)计划⑨。
城市地理学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或有关创意城市的研究,表面看来,不太关注文化创意产业内部具体的生产和运作方式,而更关注人(包括生产者、相关者乃至作为生产者的公民消费者)或创意劳动者,对城市物质性空间和非物质性要素的需求,研究结论和导向具有很强的面向打造创意城市的政策工具价值,强调综合性创意环境(creative milieu)的营造[52]。
3.3文化地理学的介入
主要关注地域文化或文化因素(而非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对文化生产、消费或文化经济的影响[54],不过,所谓地域文化,在城市语境下⑩,就是指不同城市的特殊性,因此,与关注创意城市的城市地理学研究,存在某种重合,即主要探讨地方(或城市)独特的物质景观、创意氛围、集群环境、社会关系网络等,如何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影响因素;当然,更为精细的文化地理学研究指出:“地方”不仅有制度内涵,还有文化含义,可为文化产品及其工作者提供某种地理声誉、品牌效应和认同感,作为情感产品的文化产品,需要吸收地方独特的符号资源、风格和传统,进行文化艺术的创作和生产,形成基于地方的创意[55,56],例如,音乐作品和乐队演出往往带有地方风格,地域出身不同,演出报酬也不同[57];艺术家对所在地原生态文化的嵌入性,从其作品表现和创作过程来看,可能偏重于物质层面而非精神嵌入[58];广告设计以及旅游策划等文化咨询类服务公司,相对集中于某些地点,如深圳华侨城,是因为华侨城的良好形象,能够提高这些创意公司的要价能力[15];城市某些特定地点具有为创意阶层提供合作机会、建构社会关系网络、激发创意的独特作用[59,60]。文化地理学特别关注文化创意产业与所在地方(或地点)之间相互作用的递归关系[61],例如,广告创意人才在伦敦的流入流出,加速了伦敦文化经济的再领土化和伦敦亚文化的去领土化[62]。
总之,关注地点(place)、地方文化因素对文化创意产业影响的文化地理学研究,与关注创意城市和创意环境建设的城市地理学研究、以及强调文化经济活动集聚于特定空间如创意集群[63]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呈现出基本观点和研究思路的某种一致性,虽然这些研究所选择的空间尺度有所不同[8],涉及地点、创意集群、城市、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生产网络等从微观到宏观的各个尺度;这种一致性体现了地理学家对于经济活动之地域嵌入性的高度关注,以及服务于地方发展的地理学一贯导向。
但是,地理学家服务于文化经济政策的应用目标,并未完美实现,主要原因是地理学家所开展的以往研究,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内部机制仍然缺乏深入了解,包括对彼此差异较大的不同门类文化创意产业如新旧媒体产业、艺术产业、广告和设计服务业等等的内部机制,缺乏研究,因此,如何深化以往从区域、城市、集群和地点、甚至全球生产链出发的文化经济地理学研究,是一重要问题。本文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首先是要深入了解文化经济与其他经济或产业门类的差别,反思地理学的研究单位和研究方法,才能真正实现地理学家以制度建设和政策设计为实用目标的研究取向[64,65]。以下初步提出“项目网络地理学”的设想。
4深化文化经济地理学的切入点:“项目网络地理学”?
4.1文化经济的独特性:“项目”和“项目网络”生产模式
文化产业被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因而被称为认知资本主义、认知—文化经济[12]或符号象征经济[66],这一经济形态的最大特点就是基于“项目”和“项目网络”的生产模式,它改变了产业的整个市场结构、竞争结构,包括劳动力雇佣模式、工作方式、资本和生产资源的类型、来源及其组织调度和采购方式、风险处理方式和权力关系结构。例如,创意或知识,而非交通运输成本或作为存量存在的实物原材料及其地理来源,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为适应该产业的高风险特征,文化公司将风险分担在个人肩上,加大了创意工作者的个人责任,知识、责任和财富的分配也因此跨越所有职位以及公司边界[67]。
从产业或生产的角度来看,1970年代晚期,西方电影、出版、电视、唱片等行业的文化内容生产方式,就已逐渐从福特制大众生产模式,即创意、制作、发行等产业环节高度集中的垂直一体化模式,转向纵向解体和分离,形成高度柔性的经济体系[66],建立起少数大公司与大多数中小公司并存的市场结构,大公司原本采用的院内(in-house)集中生产模式,转变成与众多中小公司以及自雇和自由职业者分包、合作、基于特定项目的“项目网络(project network)”生产方式[68],强调围绕临时“项目(project)”组成核心团队或主创的工作模式,这种模式甚至引发“公司终结论”的出现;目前,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消费者参与文化创意和内容制作的合作创作或开放式创新,不断涌现,文化创意产业被认为是某种社会网络产业[69],显示出与厂房经济和流水线经济等传统模式迥异的特征。
所谓文化经济的项目网络生产模式,主要是围绕一个个、一次次、不同的、临时的、任务型的“酷(cool)”项目,对生产要素加以组织、管理、运作及其价值实现。每一本图书、每一部电影、每一个艺术作品、每一次广告运动,都是不同的文化产品、文化“项目”,需要通过组织各种不同人才及其所拥有的异质性技能与知识、形成特定项目团队而运行[70],并随着项目的完成而解体。例如,电视节目制作公司为完成一部电视剧,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通过电视频道编辑与制片人合作,寻找导演、脚本作家和摄影师,组成核心团队或摄制组,然后再依据各自的人际关系网络和职业关系网络,寻找其他相关机构和合作者,构成一个临时的项目生产网络,直至该部电视剧制作完成并播出而解体;下一部电视剧或电视节目的项目网络参与者及其组织与构成,可能完全不同。当然,项目参与者通过长期、多次的项目生产与合作,使得组织间或公司间关系与创意工作者人际关系的总合,逐渐沉淀下来,形成某种相对稳定的“项目网络(project network)”[71],每家公司、每一在文化创意领域求生存的自由工作者,都可能建立起相对稳定但并非不变的“项目网络”,连接着项目、项目成员、公司及其所嵌入的组织场域(organizational field)以及更广泛的、从地方到国家的制度环境,超越了单个项目的边界[72],构成所谓特定地方或产业的(知识池)资源池(pools)[73]。文化创意产业的运作实践,就建立于并存在于这样的项目网络或资源池当中。
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谱系来看,新媒体行业、艺术策展行业、广告业和时装秀等等文化创意领域,所存在的大量基于项目或项目网络的生产方式,并不是地理学家的发现,而且,这种生产模式与公司地理学以公司为中心,所开展的弹性生产模式或创新生产模式有所不同,后者强调经济地理学家所熟悉的公司之间的合作网络、企业集群和产业区[74],而项目网络生产模式十分强调对个人及其劳动和创意技能的组织,因此,人际关系或社会网络非常重要,例如,电影工作者、艺术家的人脉关系对于工作机会的获得以及项目团队的组织,很关键[75]。项目网络的运作和人际关系的积累,建构了文化产业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基本信息和结构,例如电影行业中演员的A名单或B名单等[76],便于劳资双方的相互寻求、减少风险,反过来维系了该项目网络的独特生产模式。因此,从项目和项目网络出发,是深化文化经济地理学进一步探讨文化经济规律及其发展政策的重要途径。
4.2地理学者对文化经济项目网络的研究尝试
虽然,建筑项目、工程项目等一直以来就是基于项目的产业,项目管理(学)甚至发展成为管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11),但地理学家对项目生产模式的关注很有限,这可能与地理学家长期以区域(城市)、产业、以及较晚才得以重视的公司为研究单位的传统有关。不过,西方少数地理学家,特别是德国经济地理学家Gernot Grabher,在研究文化经济时,注意到其明显而独特的基于项目和项目网络的生产模式,初步开展了经验研究和理论探讨,成为项目网络地理学研究的先锋。一方面,他没有放弃地理学一贯重视的“地域”概念,另一方面,他特别吸收了组织管理学中项目和项目网络的概念,提出项目、公司、人际关系、地域、网络等等的集合,构成“项目生态(project ecology)”[35,70],从而挑战以往经济地理学研究公司、网络、知识、学习及其空间性时,忽视项目与项目网络的传统认识[77],强调以项目(而非公司)作为考察地域经济的研究单位,围绕项目参与者,探讨项目网络及其运行的地域特性(localities),以及和制度设计[73,78]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社会网络的项目网络,本质上就是某种信息和知识网络[69],因此,对项目网络或“项目生态”中知识和学习问题的重点关注,日渐形成经济地理学的德国学派[79]。不过,虽然Grabher于2002年专门组稿地理学家,撰写与新媒体产业项目研究有关的论文[7],试图吸引地理学家对文化经济之项目和项目网络生产方式的关注,但这一领域并未获得明显跟进,地理学界也没有提出“项目网络地理学”的议题。
5结论和讨论
西方地理学界在文化经济研究方面,日益获得独具学科特色的进展,但相对于更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地理学在文化经济领域仍然存在大量待开垦空间,其中之一便是密切关注文化创意产业基于项目和项目网络的社会—经济组织模式,目前,有关这一议题的讨论虽然极为有限,不过,地理学家在这一领域仍会大有所为。一方面,以往的地理学研究视角和主题不乏相关知识的积累,如强调(产业)关系和(公司内外部)关联性、生产网络的公司地理学、关系地理学等;另一方面,只要地理学家再次转换研究单位,从区域、产业、甚至公司,转向“项目”,同时开拓跨学科研究视野,引入新经济社会学以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等等,结合地理学空间视角的独特优势,不难产生新的知识贡献。事实上,项目网络地理学研究范围不应局限在文化经济领域,一切基于“项目”和“项目网络”的生产组织模式,都可开展地理学视角的研究。有关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多个层面,对项目网络地理学加以全面探讨、从而建构分支学科的设想,作者另有撰文。
注释:
①全文见:http://www.gov/cn/jrzg/2009-09/26/content_1427394.htm。
②就笔者亲身经历而言,一些非地理学家往往将地理学家擅用的地图表达或可视化手段,委婉地说成是“形式美”,言下之意,无实质价值。
③可参见其官网:http://www.creativeclass com/richard_florida/。
④有关《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可详见:http://www.stats.gov.cn/tjbz/hyflbz/xgwj/t20040518_402154090.htm。
⑤我国的文化产品出口额之所以世界第一,主要原因是统计中包含了大量设备产品,而在创意和内容产品方面,仍然很弱。可参见:参考文献[20]。
⑥本节的文献来源不考虑作者是否来自地理学专业机构或地理学家社群,只要运用地理学研究视角、关注文化创意产业或文化经济问题,都可作为地理学介入文化创意产业的评析对象。此处的“文化经济地理学”主要是指将“文化经济”作为本体论加以讨论的研究,不是指受“文化转向”影响的从文化因素解释经济现象的经济地理学认识论或方法论。
⑦例如,传播学者研究媒体产业时对“空间化”的关注,详见:(加拿大)文森特·莫斯可著,胡正荣译,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
⑧或许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国家对于知识经济和创新的独特认识,特别是对知识共享价值的认同,使得瑞典最早发明了所谓“盗版”工具的音乐分享软件Napstar。
⑨可参见其网站:
http://portal0.unesco org/culture/admin/ev.php?URL_ID=24544&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reload=1191657808。
⑩目前,大量研究都以城市为尺度,反映了创意产业的城市集中性,也暗示着城市以外创意经济不太显著,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乡村或非密集区的创意产业研究。
(11)有关项目管理学的一般性介绍,可参见:http://wiki.mbalib.com/wiki/%E9%A1%B9%E7%9B%AE%E7%AE%A1%E7%90%86。
标签:地理学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地理论文; 文化创意产业论文; 项目组织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地理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