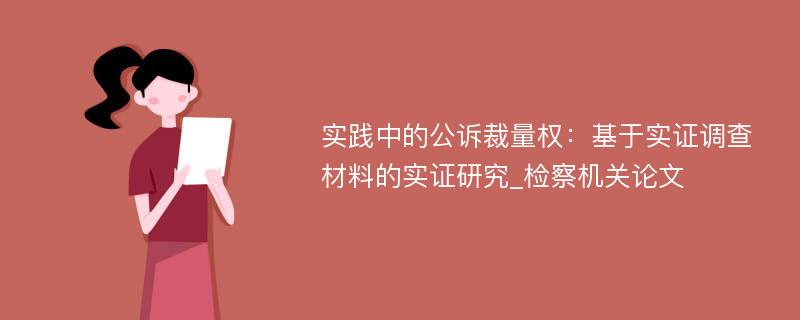
实践中的公诉裁量——以实证调查材料为基础的经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经验论文,基础论文,材料论文,实践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1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0766(2007)04-0131-09
一、研究范围与方法
作为刑事司法的世界性趋势,公诉裁量超越了法系的界分而广泛地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公诉制度之中。这正如一名论者所言,所有的制度都或多或少允许一定的自由裁量权[1]。即使是传统上严格控制公诉裁量权的大陆法系国家,公诉实践中也存在大量的裁量行为①。与此不同,我国刑事诉讼法与公诉实践都倾向于严格控制检察机关的公诉裁量权,酌定不起诉运作的空间十分狭小②。这与我国现阶段刑事司法的公信力和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的认知态度等因素相关③。
但上述仅表明我国检察机关基于刑事诉讼法显性存在的公诉裁量权(酌定不起诉权)非常小,却不意味检察机关在案件处理中不存在其他一些裁量行为。况且,两大法系公诉裁量的实践也表明,公诉裁量的内容主要包括有罪不诉、有罪缓诉、减少罪名、降格指控等几个方面的内容[2]。这意味着酌定不起诉可能只是反映公诉裁量状况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公诉裁量主要由宽泛的公共利益或者公诉政策导引的背景下④,尽管我国公诉制度中考量的政策性因素与法治国家的公共利益或公诉政策难以完全等同,但两者都承担调控公诉制度运作的共同属性,意味着我国公诉实践中同样可能存在基于公诉政策的裁量行为。比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2年出台的八项关于案件处理的政策中,就隐含了公诉裁量的内容⑤。一些资料也证实我国的公诉实践确实存在基于某方面政策的裁量行为⑥。这表明,要获得我国公诉裁量的具体状况与全面图景,不能将视角仅仅局限于规则意义上的酌定不起诉。
本文试图更全面与更精确衡量公诉裁量在我国公诉制度运作中的实际状态。我们在C省选择了四个基层检察院,一个是位于经济发达地C市Q区(简称为A检察院),一个处于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地N市S区(简称B检察院),还有一个是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信息相对封闭的Z市R县(简称C检察院),至于M市G区的检察院(简称D检察院)则是作为我们预调查的实践对象。在样本案件的利用上,以下原因使得青少年犯罪案件和涉及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的案件⑦ 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青少年犯罪案件非常普遍,但实践中还在推行青少年保护的刑事政策,并受到各级公安司法机关的重视,如果在处理这类案件中证明有裁量行为存在,那么就为整个公诉裁量状况提供了一个相当可靠的指标;涉及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的案件,尽管在具体范围上十分宽泛,但检察机关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却直接涉及检察机关能否为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保驾护航”,体现出检察机关在社会转型期与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的关系,同时,这些案件与一些常规刑事案件相比,事实与证据更为复杂,牵涉的社会关系也更为广泛,甚至还充满了政治角力,因此这类案件更可能出现裁量的情况。还需要交代的是样本案件的选取方法:由于青少年犯罪的案件比较常见,我们采取了抽样的方法来提取;考虑到涉及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的案件较宽泛,我们并没有遵从实证调查通用的抽样方法,而是根据检察官提供的线索,直接提取这些案件。
必须强调,尽管笔者承认我国规范意义上的公诉裁量过小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赞成我国公诉裁量的制度架构应该改进,但本文无意去证明,也不主张通过剧烈的制度变革来扩大检察机关公诉裁量的范围。因为公诉裁量尽管重要,但绝非最重要,其具体状况应该在诸多价值体系中维持一种平衡,达到公诉制度运作效果上的最佳。至于是否应当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制度变革来改变我国公诉裁量状况并不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更多是一个立法者与司法者以及社会公众的价值选择问题。就本文的直接目的而言,它仅仅试图展示现阶段公诉裁量的具体状况以及对其的分析与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反思我们应该通过哪些改革来完善我国公诉裁量行为规范。
二、公诉裁量的具体状况
案件处理结果应该是考察公诉裁量状况的最佳指标。如果能够量化案件处理结果包含了公诉裁量因素,则表明实践中存在公诉裁量。下面我们将根据前文设定的研究范围,介绍青少年犯罪案件与涉及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案件的处理结果,以及是否包含了裁量的因素。
(一)青少年犯罪案件
强调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保护,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刑事政策。它要求检察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遵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做好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⑧。从这一政策的实际内涵与价值预设来看,它赋予了检察机关一定的裁量权。实践中青少年案件的处理是否存在裁量因素呢?调查表明,青少年犯罪案件的处理结果包含了公诉裁量的因素。
表1反映的是我们按季度均分随机调取四个检察院2003-2004年审结的100件青少年犯罪的处理结果⑨。在样本案件的137名犯罪嫌疑人中,有2人被检察机关不起诉,约占1.4%。考虑到我国不起诉比例极低的现实,这个比值应该不算太低,甚至还可以认为是高的⑩。我们还注意到,在此样本中还有4人的案件被公安机关撤回。由于这样的处理意味着检察机关终止了审查起诉程序,因此,可以认为,在此样本中检察机关终止了对6名犯罪嫌疑人的追诉程序,约占样本案件犯罪嫌疑人总数4.38%。同样还可以看到,在改变公安机关认定的罪名、建议从轻处罚、减少指控事实方面分别有4人,39人,18人,约占样本案件犯罪嫌疑人总数的2.91%、28.46%、13.14%。由上,首先可以认为青少年保护刑事政策在公诉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但并不能将这些情况理解成是检察机关的裁量行为。因为一如我们所知,即使将数据中的“改变公安机关认定的罪名”与“减少公安机关认定的事实”理解为降格指控与选择指控,但这些处理还可能是因为证据本身无法支持公安机关认定的罪名与事实。倘若真是如此,上述情况与公诉权的正当性相关,而与公诉裁量无关。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现在的问题就是探究上述“改变公安机关认定的罪名”与“减少公安机关认定的事实”的真正原因。在卷宗已移送法院保存的情况下,我们将调查的重点转向了访谈。
表1:四个检察院关于青少年犯罪案件的处理情况单位:人 %
检察院
处理情况 A(N=51) B(N=39) C(N=27) D(N=20) 合计(N=137)
酌定不起诉1 0 0 1 2(1.46)
起诉但建议从轻处罚
15 11 7 639(28.46)
建议公安机关撤案 2 1 0 1 4(2.91)
改变公安机关认定罪名
0 2 1 1 4(2.91)
减少公安机关认定事实
7 5 4 218(13.14)
访谈结果表明,检察机关作出“改变公安机关认定的罪名”与“减少公安机关认定的事实”处理决定的原因,不仅很难归结于案件的证据问题,而且也不能完全认为是检察机关追求指控成功的心理动机。检察官在访谈中首先都承认在处理青少年犯罪案件时,一般都有“轻刑化”的考虑。B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表示,“现在要求保护未成年人,而说到保护无非就是多一些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处理,我们遵照执行,院里一般也会支持。”毫无疑问,仅此还远远不能回答上文提到的问题,但检察官“轻刑化”的考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暗示了案件处理中可能出现公诉裁量。在进一步的访谈中,很多检察官承认,在青少年案件中减少公安机关认定事实的现象,相对于非青少年案件要常见一些,甚至改变罪名的现象也有发生。检察官表示,由于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好,又是初犯或偶犯,因此就对一些有疑点的事实直接减少或者建议公安机关撤案做其他处理,不退回补充侦查或者要求公安机关进一步收集证据。确实,在此样本中只有8件案件适用了退回补充侦查,相反倒是发现了5份检察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背景的调查笔录。这表明,数据统计中出现的现象应该可以理解成是公诉裁量在青少年犯罪案件中的体现。还有检察官直接表示,在一些青少年犯罪案件中减少事实或者改变罪名与案件本身的事实和证据无关,就是为了做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处理决定。这一情况更是直接说明青少年犯罪案件中有公诉裁量的现象存在。
综合数据与访谈的情况,可以认为公诉裁量在青少年犯罪案件中有一定程度的体现,最为明显的体现就是检察机关一般做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处理决定。就这些裁量行为的具体形式而言,不仅涉及狭义的诉与不诉,而且还有广义的降格指控与选择指控等方面的内容。实践中青少年犯罪案件占到四个检察院所处理案件的40%以上,由此可以推测,检察机关整体上的公诉裁量可能并不像我们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小。
(二)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方面的案件
调查同样表明,检察机关在处理涉及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的案件时,也存在选择起诉、降格起诉与终止诉讼的情形。
我们提取了四个检察院从2000-2005年涉及社会经济与管理的67件案件(共有犯罪嫌疑人106名),并对具体处理结果进行了统计(表2)。在A检察院的24件案件(涉及犯罪嫌疑人37人)中,没有不起诉,起诉但建议从轻或者从重处罚的有7人,建议撤回处理有3人,改变公安机关认定罪名有1名,减少或者增加公安机关认定事实的有5名。在B检察院的19件案件(涉及29名犯罪嫌疑人)中,没有不起诉、起诉但建议从轻或者从重处罚的有8人,建议撤回处理有2人,没有改变公安机关认定罪名的情形,减少或者增加公安机关认定事实的有4人。在C检察院的16件案件(涉及27名犯罪嫌疑人)中,不起诉1人,起诉但建议从轻或者从重处罚的4人,建议撤回处理的4人,改变公安机关认定罪名的1人,减少或者增加公安机关认定事实的4名。在D检察院的8件案件(涉及13名犯罪嫌疑人)中,不起诉的1人,起诉但建议从轻或者从重处罚的3人,建议撤回处理的1人,减少或者增加公安机关认定事实的2人。不难发现,在此样本中,建议从轻或者从重处罚出现的比例最高,约占总犯罪嫌疑人数的20.75%左右;其次是减少或增加公安机关认定事实的情形,约占犯罪嫌疑人总数的14.15%左右;再次是建议撤回处理情形,约占总犯罪嫌疑人数的9.43%左右;在此样本中,还有2名犯罪嫌疑人罪名被改变与2名犯罪嫌疑人被不起诉。
表2:四个检察院涉及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案件的处理情况单位:人 %
对象检察院 A(N=37) B(N=29) C(N=27) D(N=13) 合计(N=106)
处理结果
不起诉0 0 1 12(1.89)
起诉但建议从轻或从重处罚
7 8 4 3
22(20.75)
建议撤回处理 3 2 4 1
10(9.43)
改变公安机关认定的罪名1 0 1 02(1.89)
改变公安机关认定的事实5 4 4 2
15(14.15)
就表面形式而言,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看做是公诉裁量的具体表现,但我们还不能据此就认为实践中一定存在裁量行为。在没有排除上述处理是因为证据问题而“不得不”作出某种公诉决定的情况下,它们只是预示实践中存在公诉裁量的可能。进一步的阅卷与访谈证明上述判断只是我们的一种谨慎。
在阅卷中不仅感到检察机关因证据问题调整公诉决定的并不多见,而且还发现了一些相关案例。C检察院处理的一件牵涉公众意见的交通肇事案就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典型(11)。由于此案的犯罪嫌疑人经济状况非常糟糕,并连连遭受不幸,且肇事汽车为贷款所购买,因此犯罪嫌疑人所在地的群众联名要求检察机关酌情考虑这些情况,从轻处罚。承办此案的检察官将具体情况汇报后,此案在检察长的协调下,作出了酌定不起诉处理。访谈的情况也表明,样本案件中绝大多数的公诉决定是检察机关基于某种特定目的而形成的裁量性处理。在访谈中,检察官承认检察机关在处理涉及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方面的案件时,特别是在一些各方面领导都关注的案件之中,有一定的裁量行为。C检察院的检察长在访谈中坦言,为了达到社会管理的目的和某种社会效果,检察机关会在法律范围之内有一些裁量行为(12)。B检察院的一位副检察长与公诉科长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谈及裁量的深度与广度时,接受访谈的检察官都表示,无法进行准确定量,具体裁量有一定的灵活性,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综上,即使考虑证据对案件事实认定的影响,上述样本案件的一些处理结果可能还是包含了一定的裁量行为。据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涉及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案件的处理中同样存在裁量行为,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广义上的降格指控与选择指控。应该指出,由于样本案件数量非常少,上文有关数据并不能准确体现实践中涉及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案件的裁量概貌,但上述数据足以证明实践中存在一定的裁量行为。
三、公诉裁量状况的初步结论与具体评价
(一)初步结论
上文是我们以青少年犯罪案件与涉及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案件为例证,对检察机关公诉裁量状况的考察。考察的结果揭示出我国公诉实践中存在着除酌定不起诉之外的另外一些裁量行为。毫无疑问,上述结论还只是停留在一种描述意义上,并不能涵盖实践的丰富内容,更遑论当下公诉裁量的内容。下面将根据上文的初步讨论,进一步分析当下公诉裁量的具体状况。
首先,在裁量行为的具体形式上,实践中的公诉裁量与法定的公诉裁量有一定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践中出现了现行刑事诉讼法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都没有规定的一些属于广义公诉裁量意义上的降格指控与选择指控。如前所述,在样本案件的243名犯罪嫌疑人中,检察机关改变侦查机关认定事实的共有29人,约占样本案件犯罪嫌疑人总数的11.93%,被检察机关改变指控罪名的有6人,约占样本案件犯罪嫌疑人总数的2.47%。尽管还很难完全确认这些行为一定就是降格指控与选择指控,但访谈与案例还是能够基本认定实践中存在类似的裁量。二是在终止公诉程序上,实践中除了有法定的酌定不起诉之外,还有一种规则之外的“建议侦查机关撤案”的形式,且其适用的比例远远高出酌定不起诉。比如,在上述青少年犯罪的137名犯罪嫌疑人中有4名犯罪嫌疑人就采用了这样的形式,在涉及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样本案件的106名犯罪嫌疑人中也有10人通过“建议侦查机关撤案”的形式终止了公诉程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总共的243名犯罪嫌疑人中只有4名犯罪嫌疑人被适用了酌定不起诉。
其次,实践中公诉裁量的深度与广度受到了一定的控制。在裁量的深度方面,表现在总体上出现裁量性处理结果的案件比例不高。如前所述,在所有的243名犯罪嫌疑人中,真正出现裁量性处理的犯罪嫌疑人比例不足24%。除此之外,另外两方面的事实也体现了这一点:一是检察机关终止公诉程序的案件比例非常之低,在243名犯罪嫌疑人中只有14人被终止了公诉程序,约占样本案件犯罪嫌疑人总数的5.76%;二是公诉裁量的主要表现还是事实的增减,这约占了样本案件犯罪嫌疑人总数的11.93%。在裁量的广度方面,调查表明实践中出现裁量性处理的案件范围并不广泛,常规性案件一般不会有裁量性的处理,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类案件中,一是青少年犯罪案件,二是轻微的伤害案件(包括轻微的交通肇事案件),三是牵涉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的案件。而且就是这三类案件也不一定就会包含公诉裁量,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检察机关是否需要通过公诉裁量来达到一定的目的。比如,在轻伤害案与交通肇事案中,检察机关进行公诉裁量的基本前提就是犯罪嫌疑人必须积极赔偿受害人的相关损失,显然这与检察机关彻底化解纠纷的考虑有关。另外,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的一些牵涉被害人意见与公众意见的案件没有出现裁量性处理的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实践中公诉裁量的案件范围受到了控制(13)。
尽管裁量的深度与广度在实践中受到一定的控制,但以下两点同样值得重视:一是在具体案件的裁量结果上,即裁量的深度上,实践中并没有体现出一定的规则性与规律性,相反却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更多时候取决于案件的具体情况与所牵涉社会关系的复杂程度;二是在裁量的广度上,涉及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的案件出现裁量性处理的可能性大,而一般性案件可能性小。
最后,在裁量行为的实际标准上,实践中的公诉裁量除了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条件之外,更为具体的标准实质上是具体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可能是全国统一性的,也可能是地方性的政策。由于公诉裁量更多的由政策来导引,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何实践中公诉裁量在案件范围上受到一定的限制,而在裁量结果上有一定灵活性。正如青少年犯罪案件中之所以会有一定的公诉裁量,与实践中推行青少年保护的刑事政策直接相关。四个检察院酌定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主要为青少年的现象就可以作为其很好的注解。表3显示,四个检察院从1999-2004年的酌定不起诉中,青少年案件分别占有75%、80%、60%、100%。同样,实践中在涉及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案件中出现的一些裁量行为也直接与检察机关在案件处理时考量了一些政策性因素有关。事实上,我们在查阅被调研单位文书档案时,就发现了类似这样的一些表述:“公诉工作要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要以社会的稳定与长治久安,要以经济的发展为尺度,将个案的审查工作与整体的公诉工作结合起来”,“在公诉工作中要考虑案件处理的社会效果,在一些敏感性或者影响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案件中要将政策与法律有机结合,避免案件的处理结果带来不利的后果。”因此毫不奇怪在一些案件中要考量法律之外的政策性因素,案件的处理结果也就难免不渗透进裁量性的因素。相反,在一些不牵涉政策因素的案件中,很难有公诉裁量出现。一旦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上述关于青少年犯罪的样本案件中出现的公诉裁量基本上都体现了有利于青少年的特点,而出现在涉及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案件中的公诉裁量却大多是为了达到某种社会治理与管理的目的(14)。因此,我们可以将实践中存在的公诉裁量理解为一种政策性的公诉裁量。
表3:四个检察院1999-2004年酌定不起诉案件中青少年案件分布情况单位:件 %
检察院A(N=16) B(N=5) C(N=5) D(N=2)
青少年(件)
12 43 2
实际比值(%) 75 80
60 100
(二)具体评价
以上是我们关于实践中公诉裁量状况的一些初步性结论。之所以称为初步性结论,主要是因为调查地域的局限性与样本案件处理结果可能存在的“流动性”(15)。但无论如何,上述的结论应该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下公诉裁量的一些基本命题。不难发现,在比较法的视域里,上述的初步结论和命题与法治发达国家的公诉裁量表面同构,但也难掩两者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下面,笔者将从三个方面对上述关于我国当下公诉裁量的初步结论作进一步讨论。
首先,上文多处指出实践中除存在酌定不起诉之外,还有一些程序外部无法显现出来的对事实与证据的裁量。正是因为其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存在于案件处理过程中,因此它不仅导致我们无法准确地判断出这样的裁量行为在面上到底有多大,只能依据点上的数据来揭开其隐秘的面纱。应该承认,在公诉裁量调控公诉制度运作与公诉制度应该回应公共利益需求的意义上,这些公诉裁量具有相当的积极作用。不管是样本案件公诉裁量的整体效果,还是在调查中发现的一些个别案例都体现了这一点。甚至一些表征公共权力收缩,尊重案件当事人纠纷解决意愿的裁量在我们的调查中也有发现(16)。可见,国外起诉裁量权扩张理论基础的社会公信模式与恢复模式在我国当下公诉裁量的实践中都有一定的体现(17)。当下实践中出现的这些情形无疑值得肯定与鼓励。
如同法治国家公诉裁量出现的制度与理念性危险一样(18),当下的一些公诉裁量行为同样也隐藏着这些危险,这除了上文提到的在案件范围上不确定性的特点难以契合现代法治的平等性价值之外,更为现实的危险还在于裁量的专断性与任意性。这种任意性与专断性不仅可能存在于检察官的案件处理环节,也可能发生于检委会的案件讨论之中(19)。在检察官层面,由于不存在公诉裁量的具体标准,且检察机关的程序控制机制也无法完全监控检察官的整个案件处理过程,因此检察官的公诉裁量行为事实上处于一种放任状态。上文提到的访谈情况就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在检委会层面,如同访谈表明的那样,检委会可能更多侧重于案件处理的某种效果,遵循的是实用主义与工具主义的逻辑,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公诉裁量将演化成一种“通过法律的治理”。这无疑表明,检委会的案件讨论同样也需要相应的程序控制机制来调控。这些问题,包括裁量案件范围不确定性的现象,与当下公诉裁量没有形成一定的裁量标准和裁量过程的封闭性相关。
其次,上文已经指出实践中公诉裁量主要由国家与地方的各种政策来导引,尽管我们还无法确定出实践中由此形成的公诉裁量在深度与广度上到底有多大。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面对与承认的事实是,各种政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案件的处理,成为处理案件中必须考量的因素,这必将引发我们去思考这些裁量是否具有正当性以及如何来保障这些裁量的正当性。
一如我们在调查中所看到的那样,即使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很难从整体上认为样本案件中的政策性裁量不具有正当性。不仅是因为任何法治国家的公诉制度都没有绝对排除政策的存在,反而还纷纷将公诉裁量的标准定格为为了公共政策或者是公共利益,而不是法律规范,而且我们列举的一些案例也证实当下由各种政策形成的公诉决定符合现代公诉制度所有的正当性价值。我们之所以认为这些公诉裁量具有正当性,主要是因为这些公诉裁量的依据,也即政策本身具有正当性。从这一点来看,应该鼓励与支持实践中基于正当政策或者公共利益而形成的公诉裁量。
在更深的背景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些政策性裁量还可能隐藏着检察院组织在整个权力结构中谋求资源与地位的自主性发展的冲动。这些因素的存在必然“迫使”我们必须将检察机关的政策性裁量引入整个刑事司法的社会政治背景中加以重新审视。对于一些基于非正当政策或者个人意志所形成的裁量,我们认为必须排除。我们指出这一点是想提示,应该在当下的社会情境中来审视与理解实践中的公诉裁量。
四、公诉裁量完善的方向
调查研究表明,实践中存在除了法定意义上的酌定不起诉之外,还存在一些基于某种政策导引以裁量事实与证据为基础的选择指控与降格指控。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而言,这些事实的存在表明公诉实践已经孕育着制度变迁的可能。这些存在的公诉裁量不管是结果,还是过程不是没有任何问题,这也意味着制度的实践同样还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要求。根据上文的分析与讨论,以下几个方面应该成为我国公诉裁量的改革方向。
首先,应该适度扩大现有公诉裁量的范围。公诉制度的历史表明,公诉裁量的范围与检察官公诉裁量权的大小本身可能就是社会发展与公众选择的结果(20)。同样,出现在当下公诉制度中的一些公诉裁量形式也体现了这一规律。毫无疑问,这些事实证明现有公诉裁量的制度架构已经无法满足当下公诉实践的需要,制度的实践已经提出了扩大公诉裁量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公诉裁量的具体范围受刑事司法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的制约,因而在我国公众对刑事司法权威认同度不高与现有刑事诉讼内部结构仍需重塑的情况下,公诉裁量的扩张需要谨慎。我们只能在坚持起诉法定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下,适度扩张起诉裁量的空间。具体而言,下述几方面可以作为调整的方向:第一,在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规定若干例外情况,许可检察机关适用酌定不起诉不以“犯罪情节轻微”为前提。在这方面,除了应将现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存在的涉及人身损害赔偿的轻伤害案件与青少年案件中的“撤案处理”予以规范化与制度化之外,还可以考虑将犯罪行为确因单纯事故造成的也纳入公诉裁量的领域。第二,可以考虑适当地赋予检察官一定控辩协商权力。第三,对于目前已被学界广泛讨论、实践中已经出现的“附条件不起诉”在参考酌定不起诉适用条件的基础上予以制度化,但范围不宜过大。在适度扩大公诉裁量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的是要设置相应的容纳民众意见的制度通道与程序装置,让民众在与法律交涉过程中形成共鸣,培育公众对公诉裁量的认知度,避免民众的不满在非正式渠道中宣泄。
其次,针对实践中公诉裁量主要受政策导引的现实,有必要制定统一的公诉政策,明确公诉裁量中可以考量的因素与情形,以下两点可以作为改革的方向:一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出统一与明确的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公诉政策,确定一些可以在公诉裁量中考虑的因素;二是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地方性检察机关(主要是省级检察机关)可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政策的基础上,根据本区域的具体实际情况,以本区域的公共利益为依据制定适用本区域的公诉政策。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各省级人民检察院还可以根据社会具体发展情势,适时地发布一些指导性的政策与指南,以弥补统一公诉政策可能存在的僵化与滞后。这两方面的改革除了具有正当公诉裁量形式的功效之外,还可以改变公诉裁量在深度与广度上不确定性的流弊以及阻隔非正当政策与个人意志对公诉制度的渗透。同时,统一与明确的公诉政策可以弥补刑事诉讼法关于公诉裁量规定的不足,增强公诉裁量的可操作性。
再次,要针对目前公诉裁量实践中存在任意性与专断性的弊端,建立相应监控机制。针对上文辨析出来的问题,以下几个方面应该作为完善的重点。一是控制检察官案件处理中的不当裁量行为。可以采取发布一般性指导原则与具体个案监督的形式来监督与控制检察官的案件处理过程与行为。二是控制检委会与检察长的裁量行为。对检察长个人意志的控制可以通过检委会集体讨论的形式来制约。对于检委会裁量行为的控制,可以通过上级检察院与目前实践中推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来制约。与上述两个方面改革必须同步进行的是要打破现行公诉裁量封闭性的弊端,使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具体而言:第一,要赋予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是否同意裁量的选择权,在双方不同意或者一方面不同意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处理;第二,要赋予被害人与案件侦查机关对检察机关裁量行为的知情权与异议权;第三,在检察机关终止追诉的裁量中,有必要通知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侦查机关与法院,并由法院审查其裁量过程与结果的正当性。
最后,根据调查的感受,在完善公诉裁量的过程中同样需要考虑如何在检察官内部培养关于公诉裁量的制度文化,改变部分检察官已经固化的行为意识与行动结构(21)。现代组织理论就非常强调组织文化对于组织成员行动一致性的塑造(22)。在刑事司法的研究视域中,也同样强调法律文化对具体刑事司法行为的影响。比如西班牙与日本的研究者在一项比较研究中就指出,“人们都很清楚,法律原则与规范在一个社会真空里并不起什么作用。法律原则与法律规范怎样转换成社会实践,有赖于各刑事司法制度的制度结构和内部法律文化”[3]。要真正地在检察官中间形成关于公诉裁量的制度氛围,一方面检察机关要在组织层面不断地通过话语的形式建构检察官的日常行为,在检察官中间成为一种明示的训练;另一方面要通过检察官之间具体实践的交互作用,形成一种实践化的波及效应,使公诉裁量沉积并内化为一种被检察官视为“理所当然”的案件处理技术与知识。当然,这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们可以将之纳入提高检察官素质的话语行动与日常建设的轨道中。
注释:
①资料显示,德国有50%的刑事案件是由公诉人以裁量的形式撤销案件,参见陈光中、汉斯-约格·阿尔布莱希特主编:《中德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德国公诉实践还表明,刑事诉讼法153a条有关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已经使不起诉政策延伸至中等严重程度的案件,参见弗洛伊德·菲尼、阿希姆·赫尔曼、岳礼玲著:《一个案例 两种制度——美德刑事司法比较》,郭志媛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419页。
②从制度规范角度而言,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的酌定不起诉对象必须是“犯罪情节轻微”和“依照刑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在实践中,各级检察院也严格控制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8年下发的第12号文件中强调符合酌定不起诉的案件(除极个别情况之外),均应起诉。我们调查的四个检察院的上级检察院也都制定了不起诉(包括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比例,并作为检察院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我们在调查中感受到了这一点,不仅酌定不起诉适用程序复杂,而且酌定不起诉适用比例也非常之低。据我们统计,四个检察院从2000年到2005年的酌定不起诉率均不到0.04%,而且不少年份还出现了没有酌定不起诉的情况,其中A检察院在2001年,B检察院在2000年、2001年,C检察院在2000年、2002年、2004年,D检察院在2000年、2003年、2004年、2005年没有出现酌定不起诉的案件。
③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讨论可参见周长军著:《刑事裁量权论——在划一性与个别化之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7-451页。
④比如,英国的《皇家检控准则守则》第4节规定皇家检察官作出起诉决定必须经过证据审查和公共利益审查。此外,为了有效指导起诉,该《守则》还从正反两方面列举了应当考虑的公共利益因素。关于这方面的详细内容可参见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编译:《英国刑事诉讼法(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44-546页;荷兰刑事诉讼法第167条规定的起诉便宜原则允许检察官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放弃起诉或者是起诉,参见何家弘主编:《刑事司法大趋势——以欧盟刑事司法一体化为视角》,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第300页;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3条规定的微罪不起诉,适用的标准也是公共利益,参见张丽卿:《起诉便宜主义原则的比较》,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5卷第3期。
⑤具体内容见http://www.fc70.com/article.aspx? articleid=1273。
⑥这里可以列举出最为典型的三个事例,一是2004年河北省赦免民营企业家原罪的河北省“一号”文件,参见徐昙:《河北省‘赦免民企’原罪决定出台幕后》,载《中国经营报》2004年2月6号;二是黑龙江省绥化市马德卖官案中专案组制定的法外追诉标准,参见《记者披露田凤山双规内幕:“最不像贪官”的贪官》,见http://news.china.com/zh_cn/domestic/945/20031202/11579983_2.html;三是上海在2006年7月以会议纪要的形式明确规定受贿款用于公务可以从宽处罚,参见《上海以纪要的形式明确规定受贿款用于公务可以从宽处罚》,见http://news.sina.com.cn/c/l/2006-09-04/092710914126.shtml。
⑦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这些案件在类型上主要包括:职务犯罪案件、经济犯罪案件与牵涉公众意见的刑事案件。另外,本文还将这类案件的主要特点限定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犯罪行为在当地影响比较大;二是地方党委与政府关注;三是属于涉黑或者恶势力犯罪;四是犯罪行为涉及国家与地方政府重点整治或者关注的某些事项。
⑧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2年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非常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精神。具体内容可参见http://202.115.40.18:82/claw/ShowComplex.Asp? Db=chl。
⑨在A检察院调取了40件涉及犯罪嫌疑人51人,B检察院25件涉及犯罪嫌疑人39人,C检察院20件涉及犯罪嫌疑人27人,D检察院15件涉及犯罪嫌疑人20人的案件;在犯罪的类型上35%为盗窃案件,30%为抢劫与抢夺案件,10%为故意伤害与寻衅滋事案件。
⑩据我们统计,四个检察院近五年来的不起诉率均不到0.6%,酌定不起诉率甚至不到0.04%。全国同类资料也显示了类似情形,北京市1998年共受理审查起诉案件11241件16651人,而全市作出不起诉的共计194人,不足0.12%,其中酌定不起诉的共计58人,酌定不起诉案件占不起诉案件的33%,参见陈光中、汉斯-约格·阿尔布莱希特主编:《中德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检察院2003年与2004年不起诉率分别为0.5%和1.2%,参见谭琼:《透视不起诉制度,提高法律监督能力》,载http://jianchayuan.nanhai.gov.cn/gb/lilun2006-03-2807.htm;北京市顺义区2002年、2003年、2004年不起诉率分别为0.1%、0%、0.3%。参见李旺城:《透视‘撤案’程序危机 提高法律监督能力——对顺义区近三年公诉阶段公安机关撤回案件的实证研究》,载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user/article_display.asp? ArticleID=30148。
(11)A检察院一件改变罪名的案件也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证。犯罪嫌疑人杨××在A区欺行霸市,并多次纠集一些社会无业人员寻衅滋事,社会影响极度恶劣。当地党委与政府多次想将其团伙以涉嫌黑社会犯罪予以打击,但一直苦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在一次专项打击涉黑犯罪的整治活动前,A区政法委专门为此召集公安分局局长、检察院检察长与法院院长开会,表示这次必须将其予以惩办。在以组织领导黑社会犯罪逮捕犯罪嫌疑人之后,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期间,为了确保指控成功,将其罪名改变为非法经营罪。
(12)该检察长还举出了具体的案例。C县在2003年与2004年兴建新县城的过程中,由于拆迁的赔偿问题引发了被拆迁户与当地政府之间的纠纷。一些拆迁户多次围攻新县城的施工单位,并阻止施工的进行。这在当地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C县公安局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逮捕了几名组织者。为了平息这场纠纷,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并没有提起公诉,而是建议公安机关撤回处理。该检察长在介绍完这件案件之后,还专门向我们强调,“如果单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几名组织者肯定构成了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13)一些检察官在访谈中表示,一些案件中会在一定范围之内斟酌被害人与公众的意见,甚至还会主动询问被害人对案件的处理意见,但一般不会只在被害人与公众意见基础上形成案件的处理决定。
(14)以下的一件非法行医案也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大致案情如下:被害人在服用了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草药之后不幸死亡,但各种权威医学鉴定都无法确定被害人的死亡与其服用的草药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在被害人的家属多次上访与当地政府的压力之下,检察机关逮捕并决定起诉犯罪嫌疑人,后来犯罪嫌疑人因疾病取保候审。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期间因恐惧而服毒自杀,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又给检察机关施加巨大的压力,多次围攻检察机关。这样,检察机关就陷入了被害人家属与犯罪嫌疑人家属的双重压力之中。县政法委与两方家属多次协商,由当地公检法三机关各拿一笔钱平息了纠缠了近两年半的案件。
(15)这里所言的“流动性”主要是指,我们无法排除一些样本案件的处理与案件证据本身有关。
(16)比如在一件盗窃案中,由于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与事主有亲密的血缘关系,因而事主不希望起诉犯罪嫌疑人。此案检察机关就作不起诉处理。
(17)英国学者Julia Flonda将现代各国检察起诉裁量权扩张的理论基础概括为三种模式:一是操作效率模式,以德国与荷兰的检察起诉裁量实践为典型;二是恢复模式,美国的“附条件警告”就是其典型;三是社会公信模式,苏格兰的检察罚金制度与德国的刑事处罚令程序就体现了这一点。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讨论可参见Julia Flonda,Public Prosecutors and Discretion--A Comparative study,Oxford:Clarendon press,1995,pp.176-193.
(18)参见周长军:《刑事裁量权论——在划一性与个别化之间》第309-312页,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9)实践中案件处理实质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检察官个人的案件审查阶段;二是案件处理决定形成阶段,这一阶段主要就是检察长审批、检委会讨论。在此案件处理体制之下,实践中的公诉裁量可能存在于检察官的案件处理阶段,也可能形成于案件讨论或者检察长的审批阶段。
(20)大陆法系公诉原则由起诉法定主义到起诉便宜主义与起诉法定主义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就是很好的例证。大陆法系国家在19世纪末期之前,公诉原则上的法定主义就与公众对检察机关权力行使不信任有很大关系,19世纪末期之后之所以出现了起诉法定主义松动的现象,主要原因就在于刑事诉讼制度的健全与公众对检察机关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21)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检察官在错案追究制的压力下,似乎并“不愿意”行使公诉裁量权,就是行使也表现出一定“性情倾向”,即裁量性的处理案件不会招致法律与行政的处罚。这不仅在访谈中有清晰的体现,而且上述涉及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案件的裁量大多发生在检委会层面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22)参见李汉林、渠敬东、夏传玲、陈华珊:《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李海、张德:《组织文化和组织有效性研究综述》载《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