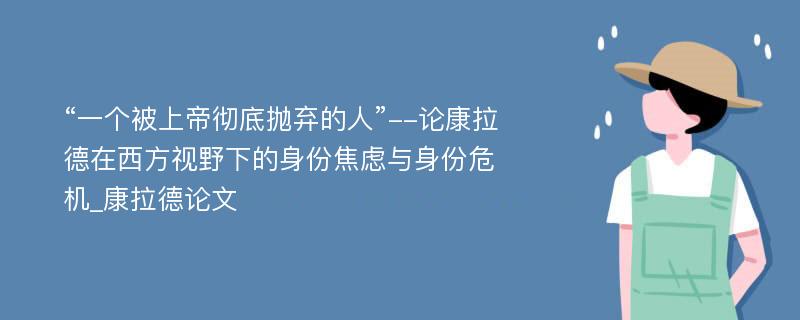
“一个被上帝完全抛弃的人”——论康拉德《在西方的注视下》中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人论文,焦虑论文,上帝论文,危机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29(2006)06-0044-07
《在西方的注视下》是康拉德唯一一部以沙俄社会为背景的小说。作品的主人公拉祖莫夫因为害怕受牵连而告发了革命者赫尔丁,后因不堪良心的折磨而忏悔,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因而遭到革命者的报复。拉祖莫夫在俄文中的意思是“理性之子”。通过刻画这个年轻人及其所面临的理性和道德困境,康拉德不仅表达了一种对于沙皇俄国的仇恨,也表达了一种个人文化心态上的“失根”之痛。
利维斯曾在《伟大的传统》一书中称赞《在西方的注视下》“非常的出色,因而一定要算在可以稳定确立康拉德作为英国大师之一的那些作品之中”。(利维斯:367)但是与他对《黑暗的心》和《诺斯托罗莫》的评论相比,利维斯在该书中对这部作品的着墨并不算多。真正使这部小说走向批评前台的乃是英国批评家莫顿·扎贝尔在上世纪50年代所写的一篇导论性文章《对西方的威胁》(The Threat to the West)。该文将这部作品置于旧俄罗斯时代的历史语境之下,指出康拉德写作此书的意图乃是为“西方人在需要做出道德判断时”提供一种“预言性的警告”。(Knowles:384)
扎贝尔一文由此揭开了《在西方的注视下》的研究史。但随之而来的东西方冷战却使得当时众多的批评家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这部作品的国际背景及其政治性内涵。在这些批评家看来,康拉德独特的个人经历不仅使他具备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身份,很适合“向西方人阐释东方的神秘之处”,(Sherry:234)同时小说也以其“对俄罗斯蒙昧主义的批评”,(Fleishman:224)“有助于西方读者更加透彻地理解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Sherry:234)这种带有强烈政治意味的解读在当时如此之盛行,使作品研究本身也带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以至于评论家托尼·坦纳写道:“太多缺乏判断力的批评已经使得这部小说变成了一本粗俗的、充满着怨恨和反俄罗斯情绪的小册子。”(Knowles:384)
近二十年以来,《在西方的注视下》的研究格局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批评家们逐渐摒弃片面与单向度的传统阐释模式,开始在多向度的多维视角中尝试使用各种新的理论与方法来解读这部曾经被打上厚重时代印记的作品。新视角和新方法的介入,不仅有助于揭示这部作品整体研究的新层面,也有利于揭示这部作品本身哲理上的普遍意义和重要的当代价值。
康拉德在创作《在西方的注视下》第一稿时,主人公拉祖莫夫与被他出卖的赫尔丁的妹妹之间的恋情构成了“小说的中心”,但在作品最后正式出版时,这个“中心”却只占了全书篇幅的大约十分之一。在后来写给友人高尔斯华绥的一封信中,康拉德以一句“拉祖莫夫出卖赫尔丁的心理过程……才构成了小说真正的主题”解释了作此改动的缘由。(Jean-Aubry:65)但是,在批评家罗伯特·汉普森看来,康拉德如此修改的真正意图还在于使这部作品回复到他前期小说“通过一系列背叛来寻求身份”的主题,(Hampson:167)在拉祖莫夫那复杂“心理过程”背后,康拉德其实更为关注的是一种身份的失落与焦虑以及由此相伴而生的认同危机问题。
身份是指从本质上确认某人某物的一系列特征的总和。而认同作为一个心理学术语,则是指一个健全的人格(Personality)在经历了某种危机之后获得的一种具有持续性、统一性和主体性特征的意识和感受。当认同一词用于社会学领域则意味着“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塑造成的、以人的自我为轴心展开和运转的、对自我身份的确认”。(王成兵:9)在社会学家看来,人的认同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自我认同是“一种内在性认同,一种内在化过程和内在深度感,是个人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王成兵:16)而社会认同则是指“人在特定的社区中对该社区特定的价值、文化和信念的共同或者本质上接近的态度”。(王成兵:16)由此,人的认同一旦发生危机,则不仅意味着“人的自我感”和“内在深度感”的危机,也意味着“人与他者的关系以及在人与他者的关系中形成的意义观、价值观和地位感”的危机。(王成兵:19)小说的主人公拉祖莫夫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并非自爆炸案发生之后、赫尔丁闯进他的寓所才开始,而在他曲折的身世之中早已潜藏了产生认同危机的种种诱因和条件。
拉祖莫夫是个私生子。他孤独地活在这个世上,“就像一个在深海中游泳的人”。(Conrad:13)现实生活中与生俱来的身份感的缺失使他对身份本身以及周围环境的认可充满了一种强烈的渴求。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成为“大学里的名教授”。在他看来,“名教授”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其威望足以将拉祖莫夫这个标签变成一个“让人充满敬意的名字”。(Conrad:19)生活虽然清苦,但是拉祖莫夫对未来依然充满信心,一想到考试获胜者的名字将会刊登在报上,他的内心立刻充盈着一种快乐和希望。
拉祖莫夫对成功的期盼也可以说是一种对“自我价值感”和“自我意义感”的渴望。对于普通人而言,生活得有价值和有意义并非一件难事,但是对于拉祖莫夫来说,却意味着他必须通过痛苦的努力将某些身份与认同的“断裂处”重新联结起来。拉祖莫夫外表英俊,却出身卑微。他举止高雅,却没有显赫的家世。他学习勤奋,努力上进,却从不敢发表自己真实的想法。除了偶尔流露出一些含含糊糊的自由主义言论,在生活之中他“几乎没有什么秘密或值得保留的东西”。拉祖莫夫的思想似乎“很容易受到各种观点和权威的左右”。在与旁人谈及各种社会改革问题时,他也总是愿意充当一位“听完了你的看法就马上转移话题”的“高深莫测的听众”。(Conrad:13-14)
拉祖莫夫试图以自己思想和言论的屈从来迎合周围的环境,以换得方方面面的接受和认同。他那种沉默寡言的性格和小心翼翼的处世态度与其说使他具备了一种“节制和谨慎的力量”,为他赢得了一种“思想深刻的声名”,还不如说体现了他早期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的一种征兆——个人语言的丧失。语言既是人类思考生活和把握世界的工具,也是人类交往沟通的载体。在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看来,讲语言不仅是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王成兵:23)因此,拉祖莫夫选择成为“听众”就意味着放弃“表达”,他选择沉默就意味着选择了一种单向性的倾听,而不是一种双向和积极的沟通。他的选择或许有个人心理上的动因,或许有外在社会政治环境的压力,但这种选择无疑表明了“自我感”(Sense of Self)在某种程度上的丧失,也正是伴随着这种自我感的丧失,拉祖莫夫才渐渐失去了“用来交流彼此深邃个人意见的语言”。(罗洛:45)
爆炸案发生的当天,拉祖莫夫正忙于准备考试,他并没有对这起发生在街头的政治事件太过留意。他深知对这类消息表示过多的兴趣并非是件安全的事情,有时可能会招致意想不到的厄运。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此时拉祖莫夫的自我定位感和社会方向感应该说还是非常清楚的。他洞悉这个时代人们内心深处的那种紧张、焦虑与彷徨,他更清楚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他原以为能像以往一样,事态平息之后又能重新钻入那个安静而孤独的外壳。但是,正如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是政治的动物,无论拉祖莫夫对“正常、实在的平淡生活”抱有怎样的“一种紧握感”,(Conrad:17)在那种社会环境中他试图避开政治来重构自我身份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只是一种梦想。在他对暗杀事件“模糊”的反应之中,我们不仅体味到了一种命运的无奈与无情,更读懂了一种人性的脆弱与无助。
赫尔丁逃生之际之所以选择拉祖莫夫,一则他认为拉祖莫夫偶尔也参加过激进的学生聚会,二则他认为拉祖莫夫没有任何亲人。赫尔丁的选择之中可以说包含着一种信任,但这种信任同时也意味着对拉祖莫夫以往构建的自我身份的一种“误读”。拉祖莫夫其实对赫尔丁所热衷的暴力革命并不认同。在他看来,所有革命似乎都是建立在“愚蠢、自欺欺人和谎言”之上的盲从。(Conrad:75)他之所以和激进分子偶有来往,只不过是出于同情或者说是在乱世之中的一种生存策略罢了。因此,相比起对爆炸案本身的冷淡态度,拉祖莫夫不由得对赫尔丁的“不请自到”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如果说,事发之前拉祖莫夫的“节制、审慎和沉默寡言”还只是一种认同危机出现前的征兆,那么赫尔丁的到来则使得拉祖莫夫清楚地表现出了认同危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焦虑感的增强。焦虑是人的一种心理体验,也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心理学家认为,焦虑是人“自身的存在受到威胁时所感受到的那种东西”,焦虑打击的正是人的内在“核心”。(罗洛:25)赫尔丁的选择对拉祖莫夫而言,意味着一种强迫,一种“混乱”,意味着对他从前那种理性、“安全而又有规律的生活”的毁灭。(Conrad:66)
认同一旦发生危机,伴随着“个人语言丧失”的除了有“焦虑感的增强”,还有一种英雄主义维度的失落。在康拉德的前期海洋小说中,我们看到勇敢坚韧的船长与水手穿越风暴,战胜危机,体现出了一种何等磨灭不了的英雄气质。但是在拉祖莫夫身上我们看到的却只是一种畏惧与退缩的凡人性格。拉祖莫夫似乎已无路可走,在送走赫尔丁的计划失败之后,他想到了告密。告密意味着屈从,意味着对某种极权暴力身不由己的认同。但是,他的告密却适得其反,不仅使自己也成了被当局怀疑的对象,也使自己成了一只“无依无靠的猎物”。(Conrad:48)拉祖莫夫明白他已无法摆脱那疯狂命运之神的纠缠。因为赫尔丁,他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政治的漩涡。因为告发赫尔丁,他的精神又陷入了一种道德上的孤独而不能自拔。这种孤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孤独,这种孤独意味着“一种裸露的惊恐……没有人能长时期忍受这种道德上的孤独而不会发狂”。(Conrad:40)拉祖莫夫的确感到自己快要被这道德的压力压垮了,别人生活在这个世上还有落脚之处,但是他在这危急时刻却连一个“秘密的道德庇护所”也没有。(Conrad:34)他多么渴望有人能在这危困的时刻给他以援手,他多么渴望能“被人理解”,能听到“一句建议”和得到“一种道德上的支持”。(Conrad:40)
在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看来,“身份之所以必要,因为它是道德责任的基础”。(劳伦:197)社群主义批评家查尔斯·泰勒也指出,“个人的认同与个人在道德上的方向感有着本质的联系”。(俞可平:67)因此,对身份和认同问题的理解还需要在一种道德的维度中展开。拉祖莫夫在认同危机中所作的选择其实就是一种道德的选择。他相信自己是“一个有着坚定信念的人”,这种信念的底里也可以说就是一种道德归属感,一种对于身份属性以及与他人和社会相认同的极强烈的渴求。他知道告密从伦理上而言就意味着背叛,而背叛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道德行为。在他看来,判断一个人背叛与否,首先得看彼此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道德上的联结”。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对赫尔丁的行为负责,更不明白自己和赫尔丁之间存在着任何的“道德联结”。他只知道,“一个人所能背叛的只有他自己的良知”。(Conrad:39)
拉祖莫夫仿佛是被那无情的命运“抛”入到这“阴谋”之中的,他的痛苦就在于他没有亲人,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去爱,内心之中只有一种空洞而又理想化的对于祖国俄罗斯的“崇拜”。拉祖莫夫的告密并非如某些评论家所言,只是一桩简单的道德错误。他的任何一种选择其实都将给自己带来道德上的负疚感,因此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某种道德上的支点以求得一种精神的平衡。如果说,危机之前的拉祖莫夫对俄国社会政治体制的依赖还只是一种无意识的本能行为,那么此刻这种依赖已在政治强力的高压之下,在某种理性化、合理化和道德化的思考之中转变成了一种有意识的精神认同。
赫尔丁之死并没有让拉祖莫夫感到丝毫的轻松,反而有一种“极度兴奋之后的倦怠”缠绕在他的心头。这种倦怠换言之即是一种道德上的无助、无力与无方向感。他焦虑于自己“荒谬的处境”,仿佛陷入了一个“没有意义、没有兴趣”的世界。当他战栗着从梦中醒来,只觉得窗外射进的光线阴暗而惨淡,没有任何的希望。“这是一个病入膏肓者的苏醒,也是一个九旬老者的苏醒。”(Conrad:63)这种苏醒使他真切地意识到了现实生活中“政治的不确定性”、“自我意志的局限性”以及周围世界的“他者性”。(Hampson:174)拉祖莫夫就像是生了一场大病,他怎么也甩不掉赫尔丁的影子,赫尔丁就像是“一个道德的幽灵”,更像是“一件浸满毒液的衣服”,(Conrad:249)紧紧地缠在了他的身体和灵魂之上,使他时时刻刻不得不以一种扭曲的方式感受着自己行为的道德后果。
批评家科伯纳·麦尔塞说过,“只有面临危机,身份才成为问题。那时一向被认为是固定不变、连贯稳定的东西被某种怀疑和不确定的经历所取代。”(劳伦:195)无论是帮助赫尔丁逃走,还是告发赫尔丁,拉祖莫夫都会有一种背叛感,都会产生一种让他无法承受的来自认同的道德压力。虽然有很多批评家将《在西方的注视下》称为西方的《罪与罚》,但是,拉祖莫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柯尔尼可夫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背叛赫尔丁并非是出于一种自我的意志,而更多的是由于某种无法预料的命运的压制使然。仅此一点而言,也就注定了拉祖莫夫无法和拉斯柯尔尼可夫一样,获得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救赎。在康拉德看来,没有仁慈的上帝,也没有怜悯的人性,“道德选择的结果总是无法逆转的”。(Kaye:152)通过拉祖莫夫的命运,康拉德不仅展现了他的那种建立在基督教传统之上的苛刻的道德观,也表现出了一种古代斯多葛派道德家的遗风。
拉祖莫夫一见到内务部官员米库林就抱怨自己完全被误解了。在他看来,“误解”这个词显然比“被怀疑”要好得多。(Conrad:79)他的心中还存有一丝希望,希望能得到当局的信任和理解。拉祖莫夫的表白给米库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米库林看来,拉祖莫夫那种“独特的气质、多变的思想以及动摇的良知”无疑使他成为了被派往欧洲以打探流亡者情报的最理想人选。(Conrad:245)米库林在这个“不寻常的”、“已经被控制住”的年轻人身上发现了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Conrad:255)他以一种不容拒绝的强硬语气对拉祖莫夫说道:“你往哪儿去啊?……你走的时候像空气一样自由,但是你最终得回到我们这儿……你已经变成了上帝的工具。”(Conrad:246)
从人沦落成为一种“精美、合用”的工具,拉祖莫夫的身份焦虑和认同危机可以说是达至了一个最高点,这个最高点同时也意味着他作为人的主体性的最终消解。主体性与身份认同的关系由来已久。从经验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开始强调身份的主体视角,到休谟、尼采对现代主体与身份观的强烈置疑,再到当下文化研究批评家霍尔认为“后现代主体没有固定或永久的身份”,(劳伦:205)可以说,主体性一直是身份与认同研究的核心概念。由此,身份认同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人的主体性的危机。拉祖莫夫只有成为“工具”,才能成为米库林所说的“我们的人”。而米库林之所以在“工具”之前加上“上帝”二字,也只不过是想以一种虚幻的神圣来“软化拉祖莫夫对自己处境的悲观看法”。(Conrad:256)这个上帝当然不是“无名又无所依靠”的拉祖莫夫的上帝,这个上帝的唯一任务就是给米库林之流送来维护政权和体制的“天意人选”。
拉祖莫夫就像是一个“被上帝完全抛弃的人”。(Conrad:250)他的遭遇既体现了政治暴力对于个体存在的毁灭性影响,也体现了现代人的自我与社会的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方向感的丧失。认同危机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生活如影相随。危机意味着矛盾、对立和消解,但危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意味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和重构身份的可能。赫尔丁对拉祖莫夫身份的“误读”使拉祖莫夫最终顺利地在日内瓦流亡者中站稳了脚跟。在那些流亡者信赖的目光之中,拉祖莫夫仿佛又重新找回了一份自信和自得。但是,当他见到赫尔丁的母亲和妹妹之后,他那稍稍愈合的心灵伤口立刻又裂开了。面对着因丧子之痛而几近精神失常的母亲,面对着纳塔里娅那真诚的问候,拉祖莫夫的内心除了矛盾,更多的还是一份自责、懊悔和“可憎的羞耻感”。拉祖莫夫的灵魂已经“筋疲力尽”。他知道,“日复一日,如果没有一种道德抗衡的力量”,自己是“无法支撑下去的”。(Conrad:194)他醒着的时候感到孤独,而睡梦中“一种异乎寻常的道德孤独感”也像幽灵一样的死缠着他,(Conrad:256)苦涩的爱情与无尽的悔恨让他觉得自己的存在仿佛是一个“活生生的谎言”。他急需一次彻底的忏悔和坦白。这种坦白既是一次心灵的炼狱之旅,更意味着一种灵魂的解脱和主体性的重构。惟有如此,他才能摆脱“自责”和“那谎言的牢笼”,(Conrad:299)才能摆脱“往事中的傀儡身份”(Conrad:48)和那“痛苦而自我否定的生活”。(Conrad:296)
如果说,康拉德在小说前三部分刻画的是拉祖莫夫如何在认同危机中失去了自我,那么在第四部分康拉德则通过描写拉祖莫夫的忏悔,将身份的重构重新定义为了“一种对爱的需要”。(Hampson:187)坦白以前的拉祖莫夫无家可言,但坦白之后的拉祖莫夫却找到了“亲人”。当他被双面密探尼基塔击聋双耳,继而又被电车撞倒之后,是流亡者塔卡拉抢步上前将他扶起,并对围观的行人说道:“这个年轻人是俄国人,我是他的亲人。”(Conrad:305)拉祖莫夫最终回到了俄罗斯的一个偏远小镇。虽然他成了瘸子和聋子,疾病缠身,但却有心地善良的塔卡拉照料着他。不止一个革命者来看过拉祖莫夫,他们都表达了一种相类似的内疚之情。在这些革命者看来,拉祖莫夫不仅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更是一个勇于行动的人。他的忏悔与坦白不仅使他最终获得了一种内心的安宁,更重要的是为他赢得了一种他人的尊敬。康拉德的小说很多时候描写的都是人在两难困境中的遭遇,人要做出一种正确的道德选择,既需要理性,更需要一种内心的力量和勇气。拉祖莫夫的命运似乎表明了,“在每个人的一生之中都有那么糟糕的一刻。一个错误的念头闪入脑海,接着恐惧由此而生——对自我的恐惧,对他人的恐惧……可是又有多少人愿意交出自我而甘愿承受永久的惩罚”。(Conrad:312)
批评家格拉德认为,《在西方的注视下》与康拉德其他“背叛与惩罚”小说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它“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了“人类生活的政治本质”。(Guerard:231)拉祖莫夫出身孤儿,他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渴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一位教授,以完成从“无名”到“有名”的身份塑形。但是赫尔丁的到来却使他追求理想身份的进程突然被终止,使他以一种极不情愿的方式认识到了自我与超我在面对认同问题时所呈现出的巨大鸿沟。赫尔丁毁掉的不仅是拉祖莫夫“唯一拥有”的那种“孤独而又艰苦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所代表的政治暴力也使得拉祖莫夫陷入了一种极其痛苦的道德两难境地。在赫尔丁所代表的“无法无天的革命暴政”和米库林所代表的“无法无天的专制暴政”的双重挤压之下,(Conrad:71)拉祖莫夫别无选择,在出卖他人的同时他也使自己成为了“暴政的奴仆”。(Raval:141)拉祖莫夫既不认同暴力革命,又憎恨专制政治的残暴。他既为流亡者所误解,又为当局所怀疑。他在任何一方都得不到真正的安宁,而任何一方又都在拉拢他。他好像是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推促着,“被驱使”到日内瓦完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Conrad:192)他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一种现代社会的悲剧。透过这层悲剧的底里,我们或许会联想到英国保守主义哲学家埃德蒙·柏克在思考法国大革命的后果和意义时曾说过的一段话:在这个极权的社会体制中,“个体性旁落在外。国家是一切的一切……为达到它专有的目标,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控制权和镇压权——通过洗脑实现思想控制,通过刀枪实现人身控制”。(柏克:13)
拉祖莫夫是现代政治暴力的一个牺牲品。他失落身份就意味着失去自由,而“没有自由,政治就是唯一的宿命”。(Howe:87)身处这样的专制社会,任凭拉祖莫夫如何挣扎,他的命运已被各种抽象的政治信条扭曲得变了形。康拉德历来重视人的道德意识,但他最反对将社会道德责任强加于个人的良知和权力之上,他对拉祖莫夫结局的处理不仅显示了他对于现代社会中个体存在之价值的关注,也显示了他对个体与社会和谐关系的重视。评论家格拉德曾指出,拉祖莫夫的背叛直接导致了他的孤立,并最终导致了自我的毁灭。(Guerard:231)但是罗伯特·汉普森却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拉祖莫夫的背叛的确使他一度陷入了孤立的境地,但是拉祖莫夫在忏悔之后,通过对“独立自我的肯定”,又重新“找到了一种完整性”,并“最终摆脱孤立进入了社会”,同时这种完整性也构建了他与周围世界“建立真正关系的基础”。(Hampson:190)身份问题是“我”的问题,认同危机是“我”的危机。拉祖莫夫在绝望之际曾经痛苦地说道:“我不属于任何组织。”(Conrad:67)尽管他仍能够说出“我”,但是,这个“我”在政治语境的压力之下已变得不那么清晰和确定了。拉祖莫夫首先承受了自我身份感的丧失,继而这种身份感的丧失又导致了他的自我价值感和自我意义感的丧失。从一名竭力远避政治的大学生到一个被卷入政治漩涡之中的政治牺牲品,再到通过勇敢的忏悔成为一个精神上自由的人,拉祖莫夫的命运不仅充分展示了身份认同这一过程的艰难和曲折,更是说明了认同并非是一个终极性的问题,它始终都处于一种不断的建构——破裂——建构的过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