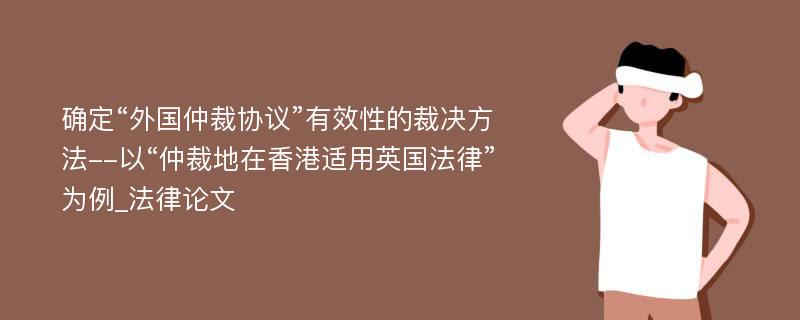
涉外仲裁协议效力认定的裁判方法——以“仲裁地在香港适用英国法”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为例论文,裁判论文,效力论文,协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512(2010)11-0002-09
在我国的涉外仲裁和司法实践中,仲裁协议的效力为常见争议点。从裁判者的角度看,这类争议点通常案情简单,但涉及的法律问题却比较复杂,裁定结论易引发激烈辩论。然而学界关于仲裁协议效力认定的研究,多聚焦于话题性较强的部分,如仲裁协议的效力扩张、独立性(Separability,Severability)及管辖权/管辖权原则(Kompetenz-Kompetenz Doctrine),鲜有从裁判方法的角度对仲裁协议效力认定的一般问题加以归纳。这使得相关领域的文章更像新奇案例的报道与评论。譬如实践中广为人知的简短仲裁条款“在某地仲裁,适用某某法律规则”,其有效与否,法院的判决结果差异甚大。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力求裁判结论的一致性,正是本文的目的。
一、缘起:结果相反的两审裁定
有一例案件所涉仲裁协议及其争议并不复杂,其案情如下。鲁琴(香港)有限公司(下称原告)与广东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下称被告)签订的航次租船合同中约定,“仲裁地在香港适用英国法律”。①后双方因航次租船合同发生争议,原告起诉至上海海事法院。被告以双方约定在香港仲裁为由,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并认为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本案应由香港唯一的仲裁机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进行仲裁。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原告系香港公司,所涉合同系原、被告为从中国上海运往伊朗的5000吨钢材运输而订立的航次租船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②第十六条规定:‘对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审查,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但约定了仲裁地的,适用仲裁地法律: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也没有约定仲裁地或者仲裁地约定不明的,适用法院地法律’。鉴于原、被告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英国法律或香港法律对于涉案合同中仲裁条款的效力如何认定,因此就该仲裁条款效力的审查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关于‘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的规定,本案原、被告仅约定在香港进行仲裁,并未约定明确的仲裁委员会,被告虽主张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是香港唯一的仲裁机构,根据涉案合同中原、被告约定的仲裁条款,本案应由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进行仲裁,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因此,应认定该仲裁条款无效。”基于此,一审法院驳回了被告的管辖权异议。③
被告不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一审裁定。其主要上诉理由为:第一,一审法院直接以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英国法律或香港法律为由,得出涉案仲裁条款效力应适用内地法律审查的结论,违反法律规定;第二,即使涉案仲裁条款效力的审查适用内地法律,也不应适用内地仲裁法第18条。被告(上诉人)为支持其诉请,向法院提交了香港律师的法律意见书一份,用于证明系争仲裁条款是有效的。原告(被上诉人)则同意一审法院的裁定结论,认为被告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都不成立:第一,《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国际仲裁管理程序》规定的建议仲裁条款要求合同必须要有明确的仲裁机构和明确的准据法,而涉案仲裁条款没有约定仲裁机构和适用的准据法,故仲裁条款无效;第二,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本案由原审法院审理,有利于查明事实。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系争仲裁条款是涉外仲裁条款。双方当事人约定:“仲裁地在香港适用英国法律。”根据英国法律的相关规定,系争仲裁条款有效,仲裁适用的实体法应为英国法律,仲裁地在香港,仲裁适用的程序法应为仲裁地法,即香港法律。依据香港《仲裁条例》④规定,系争仲裁条款也是有效和可以实施的。故原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双方当事人的纠纷应在香港进行仲裁。原告称系争仲裁条款没有约定仲裁机构和适用的准据法,依据《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国际仲裁管理程序》规定的建议仲裁条款,系争仲裁条款应是无效的。对此,法院认为《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国际仲裁管理程序》是仲裁机构管理方面的规定,且原告引用的又是建议性条款。而本案适用的香港法应当是香港《仲裁条例》,仲裁条款约定仲裁适用的准据法是英国法律。据此,二审法院依据查明的英国法律和香港法律,认定系争仲裁条款有效,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⑤
对于“仲裁地在香港适用英国法律”这一简略、非典型的仲裁条款,上述两级法院结论相反:一审法院认为无效,二审即终审法院认为有效。此种情形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普遍对二审裁定给予肯定,认为该案表明中国法院正在改变以往倾向于保留法院管辖而否定仲裁管辖的做法,是对发展国际仲裁的支持和良好的推动。⑥
从实在法上看,二审裁定是终审的生效裁定,除非被依法撤销或改判,自然是正确的;一审裁定被推翻,当然是错误的。但是,从学理上看,对错却并非那么分明,裁定结论的不同也不仅仅是因为两级法院的仲裁理念不同。事实上,法官判案不能脱离现行法空谈理念,而法官支持仲裁的价值判断也不能无视现行法。在相同的法背景及案情下(这里不考虑影响司法公正的非法因素),假定两级法官对支持仲裁有共识,案件结果应一致;假定两级法官无共识(这更接近现实),如何保证案件结果的正当性,答案显然在裁判方法上。即便是前一情形,蒙昧于裁判方法,判决结果的一致性也无法保障。
二、解析:裁判正当化过程的要素
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认定,并不需要一套不同于其它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特殊裁判方法。需要说明的是,法官和仲裁员在适用裁判方法上有重大区别,后者的特殊性宜另文论述,本文仅从法官的视角出发。参照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标准流程,⑦涉外仲裁协议效力认定的司法过程如下:
涉外仲裁协议效力争议→管辖权→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裁判
结论的形成也是基于司法逻辑三段论:
T→R (R适用于T所指之任何案件,大前提,即涉外仲裁协议应适用的法律)
S=T (S是T所指之案件之一,小前提,即涉外仲裁协议的存在及真实含义)
————
S=R (R适用于S,即结论)
其中,法律适用就是找法(发现法律)、释法(厘清法律的含义)与用法;三段论公式就是将已经发现并确定含义的法律规范与经认定的事实建立涵摄关系,以规范来评价事实,并得出是否产生该法律规范所指后果的结论。涉外仲裁协议效力认定中,多半存在双重法律发现,即首先是发现冲突规范,其次基于冲突规范确定准据法。而通常的内国案件中,找法就是指确定可以用作裁判依据的实体法。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描述无意囊括涉外仲裁协议效力认定的所有裁判方法,而只是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
(一)一审裁定评析
本案当事人对航次租船合同中仲裁条款的存在及其表述并无异议,只是对该条款的法律评价意见不一致:原告认为仲裁条款无效,故向法院就实体争议提起诉讼;被告认为仲裁条款有效,法院对案件无管辖权,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本案应由香港唯一的仲裁机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进行仲裁。可以说,本案的案情较为简单,争议点也很单一。此时,法官要做的是两件事: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也就是说,为了得出裁判结论,先要确定小前提,再确定大前提,只有前提正确,结论才可能正确。这里,之所以先确定小前提,主要是因为从当事人的告诉出发,才可以更高效地发现法律,进而确定大前提。这样做既符合人的思维规律,也是对法官选法予以限制,即不能武断,必须以案情为起点。
就小前提而言,唯一要做的是确定系争仲裁条款的真实意义。对此,法官要区别事实与评价。当事人提供的并非都是事实。如仲裁条款“仲裁地在香港适用英国法律”的存在,是事实;双方对其有效与否的不同看法,则是当事人对事实的主观评价。固定事实只是事实认定的初步阶段,明确其含义才是关键的一步。仲裁条款是仲裁协议的类型之一,也是一种合同,确定其含义当然要运用合同解释的方法。按照合同解释的一般原理,⑧合同解释的首要目的是发现双方的订约意图。当然,这个意图不是当事人的主观心态,而是合同条文与文字所表达出来的意图;合同解释首选的方法是文义解释。也就是说,合同用语应依其上下文按其通常含义加以善意地理解。当合同的字面意思不止一个时,法官还可基于当事人缔约目的,参考谈判资料,商业合同则尤应考虑交易习惯,作出新的界定,从而找到其最合理的含义。我国1999年《合同法》第125条亦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运用上述原理可以看出,系争仲裁条款中,当事人选择仲裁的意思是明白无误的,仲裁地在香港也是明白无误的。对此,当事人双方也没有提出异议。存在不同理解的主要是后半句,即英国法律是适用于航次租船合同争议,还是适用于仲裁条款,或者同时适用于二者?这既是合同的解释问题,也涉及法律适用问题。单纯从文字上看,确实无法得到唯一的答案。在实务中,法官如把握了此一裁判思路,当会在审理中引导当事人自己加以澄清;如最终不能澄清,法官则应参照当事人的仲裁目的及对此类条款的惯常处理,予以确定。实际上,在仲裁与司法实践中,罕有当事人专为仲裁条款选定准据法的。国际上,在当事人没有选法的情况下,虽然不排除某种情况下推定适用实体争议事项的准据法如主合同的准据法,但通常都是单独确定仲裁条款的准据法。⑨系争条款后半句“适用英国法律”,按英国判例法(如XL Insurance v.Owens Corning,[2000] 2 Lloyd's Rep 500),是指航次租船合同争议和仲裁条款都适用英国法。⑩二审裁定认定的香港律师Nigel John Binnersley向法院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即证明此点。但近期的英国实践却有改变,英格兰上诉法院在C v D([2008] 1 Lloyd's Rep 239)案中认为,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为实体合同准据法,仲裁条款的准据法则是仲裁地法。(11)这与我国和另外一些国家的实践趋同。在番禺珠江钢管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泛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仲裁协议效力案中,其租船合同仲裁条款与本案相似:“仲裁地点:北京,引用中国法律”。最高人民法院认定该条款“没有约定审查仲裁条款效力所适用的法律”。(12)所以严格地说,系争仲裁条款应称之为法律条款,前半句是仲裁条款,后半句是法律选择条款。当然,本案中,无论系争仲裁条款适用什么法律,当事人仲裁意愿是明确的。合同解释的目的不仅在于发现当事人的缔约意图,而且也以有助于实现当事人的合法意图为目标。由此也可看出,所谓支持仲裁的政策,不是司法对仲裁的让步或恩惠,更不是法院的自由裁量,而是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遵守民事法律明文规定的这一原则的必需。
反观一审裁定,事实认定的进路不清,甚至连系争仲裁条款都没有完整引述,完全没有确定裁判的小前提,更看不到合同解释方法的运用,显得较为主观武断。在确认“原告系香港公司,所涉合同系原、被告为从中国上海运往伊朗的5,000吨钢材运输而订立的航次租船合同”之后——其实这一认定与最终的裁判没有直接关系,即援引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关于仲裁的司法解释及《仲裁法》的规定,并认定因双方未举证证明香港或英国法律、被告未提供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可受案的证据,驳回被告的异议。这显然难以令人信服。况且,一审裁定此处未引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7)14号]关于外国法查明的规定,论证的跳跃性也减损了其裁定的说服力。
再看大前提,法官要做的是确定系争仲裁条款应适用的法律。在国际私法上,法院只适用法院地的冲突规范。(13)系争仲裁条款具有涉外性,这一点当事人及法官均无不同看法,也就是说,除非有可以优先适用的国际条约及内国实体法——至少我国在涉外仲裁协议法律适用方面还没有,首先,得适用我国的冲突规范。一审法官也正确地找到:“对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审查,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但约定了仲裁地的,适用仲裁地法律;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也没有约定仲裁地或者仲裁地约定不明的,适用法院地法律。”(14)其次,法官得确定这一有条件的选择性冲突规范的真实含义。与合同解释相似,法律解释的首要原则也是文义解释。当条文的字面意思不止一种时,才可能需要目的解释、历史解释及社会学解释等方法。(15)幸运的是,前述法条含义清晰,并不需要特别界定。这样就进入步骤三,结合上述案情,“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但约定了仲裁地的,适用仲裁地法律”的规定,符合适用条件,据此法官很容易完成找法的初步任务,即发现可适用的冲突规范。
仅有冲突规范,尚无法判断争议的实体问题。质言之,法官还得依冲突规范发现适用于争议实体问题的准据法,才能完成通常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找法环节。首先,法官须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明晰所发现的冲突规范的含义。在冲突法理论上,此时主要涉及识别和连结点的界定问题,前者系确定冲突规范的适用范围是否涵盖已查明的案情,后者是将该适用范围所涵盖之案件指引到特定的法律体系。其次,在确定冲突规范含义的基础上,结合案情即可确定争议实体问题应该适用的准据法所属法律体系。当然,这是指通常情形,不需要考虑先决问题、反致、法律规避等因素。此时,如准据法是法院地法,则找法任务的完成与内国案件相似;如准据法是外国法,法官还需要具体确定、界定该外国法,这就进入最后一个步骤:外国法的查明。在此,当事人或法官谁来证明外国法的内容以及法官如何阐释外国法,是两个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外国法无法查明、外国法的错误适用及其救济以及公共秩序保留,则是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准据法是无法适用的。就本案而言,根据前引冲突规范,不难认定,系争仲裁条款应适用仲裁地香港的法律。香港是不同于我国内地的一个独立法域,内地法院审理涉港案件需参照国际私法的有关规定办理。(16)
对本案而言,一审法官原本应在明确认定案情的基础上找到可适用的冲突规范,继而厘清冲突规范的含义,找到系争仲裁条款的准据法。实务中,法官在此过程中尤应注意释明外国法的查明问题;如外国法无法查明,则应确定替代办法,如适用法院地法。结合本案,一审法官应在认定本案争点是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认定的基础上,依职权确定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关于仲裁的司法解释中的冲突规范(第16条)——被告要求去香港仲裁实际也隐约提出了外国(法域)法的问题。在确定系争仲裁条款适用香港法律后,应合法查明相关香港法律的具体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3条、2007年《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7)14号]第9条,法院应依职权查明香港法律,亦可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证明香港法律。(17)然而,一审法官发现法律的技术不甚成熟,甚至缺乏审理涉外案件的经验,不仅案情的确定不准确,而且虽然正确地找到前引选择性冲突规范,但未加以界定,等于没有发现最终可以真正适用的冲突规范,以致错误地认为系争仲裁条款的准据法是香港法律或者英国法律,亦等于没有确定最后的裁判依据。随即法官又突兀地以当事人没有举证证明香港法律、英国法律的相关内容为由,认为系争仲裁条款应适用内地仲裁法。外国法无法查明,当然可以代之以法院地法。但问题是,内地司法实践并没有采纳外国法“事实”说,即外国法由当事人证明。一审法院没有为当事人查明外国(法域)法设定举证期限,说明其未将外国(法域)法视作一般证据;二审裁定认定了Nigel John Binnersley律师提供的法律意见书,没有提及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11条规定的履行证明手续及接受上诉人在二审提供新证据的原因,也说明法院没有将外国(法域)法当作事实。相反,除合同案件的当事人选择外国法时由其自己提供或证明外,在其他情形下,法院在外国法查明过程中负主导之责:依职权查明,但可要求当事人协助。一审裁定无视法院查明外国(法域)法的任务,轻率地认定应适用我国仲裁法,从而裁定仲裁条款无效,既不能使被告信服,也不能使他人对司法信服。一审法官法律适用思路之混乱、裁判理念之陈旧,于此可见。
附带说明一点,虽然一审法院称其对本案有管辖权,双方当事人也的确未提出管辖权异议,但一审法院的管辖权却存在疑问,受案程序似乎并不规范。依最高人民法院1995年《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1995)18号]第1条的规定:“凡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涉外、涉港澳和涉台经济、海事海商纠纷案件,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仲裁协议,人民法院认为该仲裁条款或者仲裁协议无效、失效或者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的,在决定受理一方当事人起诉之前,必须报请本辖区所属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如果高级人民法院同意受理,应将其审查意见报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未作答复前,可暂不予受理。”有理由推断,一审法院违反了“报告制度”,否则难以理解二审法院的观点。
(二)二审裁定评析
基于以上评析,被告对一审裁定提出上诉是必然的。我国的四级两审终审制,并不区分事实审和法律审,因此二审的裁判方法仍然涵盖事实认定的方法和法律适用的方法。围绕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与答辩,二审对一审裁定进行全面审查。二审裁定书以“转载”一审裁定书起始,简洁地概括了上诉双方的观点与理由,接着认定了Nigel John Binnersley律师的法律意见书,继之对全案作出认定,给出裁判理由后得出结论。写作思路比一审裁定清晰,但裁判方法的运用还有提升的空间。
首先看事实认定。二审需要审查的事实只是与上诉请求有关的事实。(18)本案中,双方在二审并没有提出新的事实,只是对案情提出了新的评价。二审裁定胜过一审裁定之处有:(1)准确地引述了系争仲裁条款;(2)回应了被上诉人的抗辩。但二审裁定与一审裁定一样未确定系争条款的真义,即当事人的真实意图是选择仲裁,仲裁地为香港,仲裁实体问题准据法是英国法。这表明,二审法官同样无认定事实的方法论意识。
再看法律适用。二审法官不仅无双重找法的概念,而且缺乏找法、释法、用法的思维进路。二审法官并没有发现具体可适用的冲突规范,实际上也没有发现系争仲裁条款的准据法。依二审裁定书,“根据英国法律的相关规定,系争仲裁条款有效”,显然,仲裁条款的准据法是英国法——只见结论不见论证;“依据《香港仲裁条例》的规定,系争仲裁条款也是有效和可以实施的”,似乎香港法律也是仲裁条款的准据法;“本案适用的香港法应当是《香港仲裁条例》”,再次肯定本案(即系争仲裁条款的效力认定)适用香港《仲裁条例》。这就与前面认定的“根据英国法律的相关规定,系争仲裁条款有效”自相矛盾。二审裁定关于法律适用主要立基于Nigel John Binnersley律师的法律意见书,而该意见书倒是明确的:系争仲裁条款适用英国法律,仲裁程序适用香港法律,实体争议适用英国法。二审裁定中虽未明文交待,实际上该意见书是二审法院查明英国法、香港法的依据,既然如此,就应该准确理解该意见书的内容。并且,本案的争议点是航次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是否有效,我国有关仲裁协议的冲突规范是选择性的,不存在同时查明香港法律、英国法律的需要。适用过大的大前提,是资源的浪费。总之,从二审裁定书中不难看出,法官没有在理论上理解仲裁条款的准据法、仲裁程序的准据法、仲裁实体问题的准据法这三个概念。这表明,二审法官同样无法律适用的方法论意识。
二审之所以认定系争仲裁条款有效,并非裁判方法的胜利,结论与一审相反,原因主要在于Nigel John Binnersley律师的法律意见书的影响、英国与香港仲裁法的同质性及法官支持仲裁的直觉。事实上,该法律意见书的合法基础倒值得追问:依据我国的冲突规范,本案要查明的为何是英国法律和香港法律,而不仅仅是英国法律或者仅仅是香港法律?如一审无特殊情况而未提供或证明外国(法域)法,当事人能否在二审履行此一义务?
(三)小结
裁判文书是裁判过程及结果的法定载体,是对案件全部审判过程的客观反映与理性总结,体现了法官的办案质量、司法水平与判案能力。涉外民商事案件的裁判,还是国际社会直观感受内国司法环境的一个重要管道。以此为标准,两审裁定书不算合格,虽然二审裁定书优于一审裁定书,且二审结论碰巧在法律上是正确的。判决的结论固然重要,但判决的正当化更重要,缺乏正当化的过程,判决的公正性本质上是偶然的,并且是反法治的。
通过对两审裁定的分析与比较,可以看出二者存在三个共同的缺陷。第一,裁定书的表述不严谨,如错引法律标题,自创管辖权依据(一审法院认为上海同实体争议有最密切的、实际的联系,因而享有管辖权)。裁判文书不是文学作品,必须严谨、规范。第二,司法审判必须依法进行,而两个法院似都忽视了“报告制度”,且二审法院对当事人新提供的法律意见书的认定未说明理由。第三,最重要的是,两审裁定都看不出是如何运用裁判方法的,裁判理由论证不清,且存在形式化的倾向。考虑到两个法院均位于中国最发达的国际性大都市,其法官质素居全国同行之首,前述不足更发人深省。这也充分说明,我国法官所受法律训练不够,法学界应尽快改革教学内容,裁判方法的训练宜处在所有法律训练的中心。这当然不意味着法学院唯一的任务是培养法官。其实,从事法律职业就有可能用到裁判方法。比如本案,被告二审胜诉、一审抗辩不力,与其一审没有律师代理、二审聘请了律师也有关系。律师对案件结果的预测及办案技巧,就需要运用裁判方法。
三、启示:不完全的归纳
“仲裁地在香港适用英国法”这样的仲裁条款,在我国的涉外合同中具有代表性。此类仲裁协议的效力认定,常引起争论。对本案两审裁定书的评析表明,在方法论上保证正确裁判此类案件,是可能的。假定法院有权受案,法官的裁判过程可逐次分解如下。
第一,确定仲裁协议的存在。通常这都不成问题,恰如本案。但偶尔也会产生仲裁协议是否成立的问题,这往往是因为当事人通过多份函电谈判,或者发生了合同转让、援引其他文件中的仲裁协议等情形。证据能够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仲裁协议是诺成性合同,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了生效条件,一般是达成即生效。另外,根据仲裁协议独立性原则,主合同不存在或未生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生效。
第二,确定仲裁协议的真实含义。这就需要运用合同解释的方法,也是仲裁协议效力认定的基础,前文已述。
第三,确定有无可优先适用的实体法适用于仲裁协议。通常这并不多见,如法院地国关于可仲裁性的强制性规定。双边投资、通商条约也常有仲裁安排。
第四,确定仲裁协议可适用的冲突规范并界定其含义。法院只适用法院地国的冲突规范。当前的立法趋势是为仲裁协议规定选择性的冲突规范,以尽量使其有效:首先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如当事人未选择,则适用其他硬性冲突规范。(19)冲突规范的解释需用到一般法律解释的方法,但可能会涉及国际私法上识别、连结点的界定等特殊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鲜有当事人专为仲裁协议选择准据法。前文已述,仲裁条款一般是独立确定其准据法,但在某些国家,如英国,本案系争条款也有可能被理解为主合同与仲裁条款的准据法均为英国法。
第五,依冲突规范的指引,确定仲裁协议的准据法。这其中可能涉及外国法的查明问题。
第六,厘清准据法的含义。这需要运用法律解释的一般方法,于此不作赘述。
第七,无论是冲突规范还是准据法,如存在法律漏洞,法官可采跨国法概念等予以弥补。
第八,基于已确定的法律规则,对争议点作出判断。通常,罕有可能涉及公共秩序保留等问题。
以上分解再次证明,这类案件裁判的关键在于合同解释与法律适用,这是一个裁判方法的运用问题。自然科学的方法在于解释因果关系,而理性与规范科学的方法在于使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正当化。司法判决不在于解释,而在于正当化。(20)法官负有说明裁判真实理由的义务,相比不说理,当下各地法院的判决书开始说理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说理也有个层次问题:强词夺理与武断恣意无异,潦草敷衍有违职业伦理,常人识见、道德直觉乃至法律直觉仅可为判决理由锦上添花,惟有裁判过程中自觉运用裁判方法才是使判决正当化的正途。判决愈正当化,同案同判及公正的可能性就愈大。目前我国法学界关于法学方法论(其中心是裁判方法)(21)的研究刚起步,绝大部分法学院都不能在这一领域为学生提供合格的训练,甚至还未注意到问题的严峻性。现在看来,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官们得自己学习法学方法、裁判方法。这也并不奇怪,法律专业本来就是一个终身需要继续学习的专业,学校无法包办一切。另外,只有法官熟谙并运用了法学方法,司法公正才有技术保障,“任何思想着的法律人必须努力理解法官在裁决个案中所适用的方法”(22)的命题才有成立的可能。怪圈之怪,实际是法学研究和法律实务的中间环节法学教育出了问题。现状之下,理论界指责实务界轻视学理,实务界嘲笑理论界脱离实践,都有失偏颇。
到底是理论反对实践,还是实践反对理论,这还真是一个问题。
注释:
①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本案所涉仲裁条款,一审裁定书并未完整引述,二审裁定书引述为“仲裁地在香港适用英国法律”。而在国内的报道中,该仲裁条款被表述为“香港仲裁,适用英国法律”;国外的报道则是“Arbitration in Hong Kong and English law to apply”。意思相近,但表述不同,或许是中外文翻译的差异。本文作者没有见到租约原文,对仲裁条款的引述以二审裁定书为准。
②即2006年9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6)7号]。一审裁定书两次引用该司法解释,标题均有误。
③参见上海海事法院民事裁定书(2008)沪海法商初字第964号,2009年6月9日。
④二审裁定书误写为《香港仲裁条例》。
⑤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9)沪高民(四)海终字第58号,2009年6月9日。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二审裁定书篇幅稍长,此处未直接引用,而是在尊重原意的基础上予以缩写。
⑥参见《“香港仲裁,适用英国法律”是否有效?》,《海口仲裁》2010年第1期。该杂志注明其报道来源于《海事仲裁(上海)通讯》2010年第1期。国外专业机构的报道见:http://www.incelaw.com/whatwedo/shipping/article/Shipping-e-Brief-October-2009/Shanghai-Peoples-High-Court,2010年6月11日最后访问。
⑦参见梁西、宋连斌:《法学教育方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157页。
⑧参见杨良宜:《和约的解释》,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15、27、30页。
⑨参见王昌鑫:《两岸仲裁法之研究——以准据法为中心》,“彰化地方法院”,2004年自版,第53-55页。
⑩参见[英]艾伦·雷德芬、马丁·亨特等:《国际商事仲裁法律与实践(第四版)》,林一飞、宋连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138页。
(11)See Ardavan Arzandeh,Jonathan Hill,"Ascertaining the Proper law of an Arbitration Clause under English Law",5 Journal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425,435,Dec.2009.
(1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番禺珠江钢管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深圳市泛邦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请示的复函》[(2009)民四他字第7号],2009年5月5日。载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编:《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2009年第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
(13)这里隐含了一个法律适用顺位问题,因本案不涉及适用强制性规则、统一实体法或统一冲突规范,故不展开论述。
(1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6)7号]第16条。
(15)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以下。
(16)这是我国一贯的司法政策。如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7)14号]第11条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或商事合同的法律适用,参照本规定。”
(17)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应成为内地法官知法的对象,而不应由当事人提供或证明。反之亦然。
(18)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年修订)第151条。
(19)例见瑞士1987年12月18日《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2010年1月1日文本)第178条第2款。
(20)参见[美]瑟亚·P·辛哈:《法理学:法律哲学》(Surya Prakash Sinha,Jurisprudence:Legal Philosophy),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影印本),第269页。
(21)有关法学方法论的论述,参见舒国滢、王夏昊、梁迎修等:《法学方法论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以下。
(22)引自舒国滢、王夏昊、梁迎修等:《法学方法论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标签:法律论文; 仲裁条款论文; 法院地法论文; 英国法律论文; 合同管理论文; 仲裁协议论文; 冲突规范论文; 法官改革论文; 法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