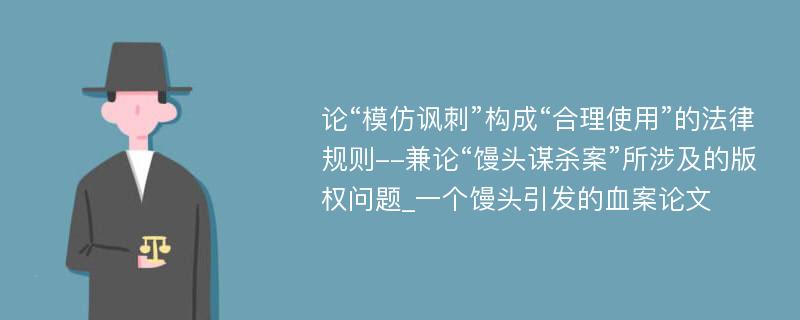
论认定“模仿讽刺作品”构成“合理使用”的法律规则——兼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涉及的著作权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血案论文,馒头论文,著作权论文,规则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日,一部主要利用电影《无极》中画面制作的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以下简称《馒头血案》)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而由此引发的著作权问题则受到了广泛关注。对此,笔者认为:《馒头血案》制作者一方面大量使用了《无极》的原始画面,一方面又通过对这些画面的剪辑、配音和配乐创造出了新的故事情节、视觉效果和美学价值,显然对《无极》进行了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改编”。如果这种未经许可的“改编”不属于“合理使用”,则《馒头血案》制作者将这部短片置于网络之中进行传播的行为无论是否有盈利动机,都必然侵犯《无极》的著作权。①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馒头血案》对《无极》画面的大量使用是否能够被认定为“合理使用”?
需要指出的是:《馒头血案》以一种引人发笑的方式重新组织了《无极》的画面,其中有许多对《无极》本身加以讽刺和嘲弄的成份。这种对《无极》的使用包含了一种特殊的文艺创作形式——“模仿讽刺”。事实上,对于什么是著作权法意义上“模仿讽刺”,“模仿讽刺作品”在何种情况下构成“合理使用”,在国外著作权法中,特别是在美国的判例中已有相当成熟的规则。但是,由于这类作品以往在我国文化中并不多见,无论学术界和司法界对相关著作权问题都缺乏深入研究,也几乎没有任何相关判例和明确的法律规则,以至于在当前的讨论中,几乎无人论及《馒头血案》是否构成“模仿讽刺作品”,以及是否可按照适用于“模仿讽刺”的特定规则认定其构成对《无极》的“合理使用”。为此,本文旨在分析认定“模仿讽刺作品”构成“合理使用”的规则,并对《馒头血案》是否侵犯《无极》著作权作一探讨。
一、“模仿讽刺”的概念:通过模仿原作对原作加以讽刺与批评。
笔者提出的“模仿讽刺作品”一词源自英文parody。② parody的原意是“对作品具有特色的风格加以模仿,以达到滑稽或嘲讽效果”。③ 因此我国学者以往多将其译为“滑稽模仿”。但是,parody的一般含义和它在著作权法中的特殊含义却存在重大区别。将parody译成“滑稽模仿”并没有反映出这个术语在著作权法中的关键意思。在美国版权法理论中,parody特指通过模仿原作内容而对原作加以讽刺或批评的创作形式。《布莱克法律辞典》将知识产权法中" parody" 的用法定义为:
“对知名作品进行转换性使用,以达到对原作进行讽刺、嘲弄、批判或评论的目的,而不是仅仅借用原作引起人们对新作品的注意。”④
在迄今为止对parody著作权侵权方面最为权威的判例——1994年判决的campbell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指出:
“在版权法意义上,(对parody)各种定义的核心……是使用原先作者的创作成份创作出新作品,该新作品至少有一部分构成了对原先作者作品的评论”。⑤
虽然对原作的模仿通常是以引人发笑的形式表现的,但正如下文提到的SunTrust案所说明的那样,“滑稽”或“引人发笑”并不是构成parody的前提条件。但“模仿”对于parody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因为parody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读者、观众或听众对原作内容的熟悉。同时,“模仿”原作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对原作本身进行讽刺或批判,以利用改造之后的原作内容反映模仿者与原作相对立的观点、立场或思想感情,从而达到其他形式文艺作品所无法实现的独特效果——使原作的内容成为讽刺、批判原作本身的工具,即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⑥ 如果“模仿”原作不是为了对原作本身进行讽刺或批判,而仅仅是为了一般的娱乐目的或讽刺、批判与原作无关的其他对象,则由此形成的新作品并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parody。⑦ 出于下文所分析的原因,它也不可能享受著作权法对“模仿讽刺作品”的特殊待遇。
在美国发生的著名案例Suntrust Bank v.Houghton Mifflin中,黑人女作家艾丽丝·兰德尔(Alice Randall)通过对驰名世界的经典小说《飘》(英文名为Gone with the Wind,又译《乱世佳人》)的“模仿讽刺”,创作了一部新的小说《风逝》(The Wind Done Gone)。在《飘》中,作者玛格利特·米歇尔(Margaret Mitchell)对美国南方的黑奴制度大唱赞歌,将白人对黑奴的奴役描写得既和谐又浪漫,同时却对林肯总统发起的解放黑奴运动大加鞭挞,认为北方军队的入侵破坏了南方田园牧歌式的平静生活,造成了社会混乱、道德败坏和人民的苦难。而《风逝》从一个黑人女奴对南北战争前后美国南方社会的感受为视角,重新演绎了《飘》所讲述的故事。通过对《飘》中大量人物、情节和对话的改编,《风逝》表现了奴隶制度之下黑人奴隶的悲惨命运,揭露了白人奴隶主和贵族的残忍、愚蠢和堕落,赞扬了黑奴对命运的抗争和解放奴隶运动为黑人生活带来的历史性转折。在《风逝》中,每一个《飘》中的黑人角色都重新被赋予了新的优良品质,如智慧、美丽和勇气。而《飘》中的许多白人角色却被作者有意地贬低。如《飘》中女主角斯嘉丽(Scarlett)的第一个恋人——文静和高雅的卫希礼(Ashley)在《风逝》中被描写成一个品德不端者;而《飘》的男主角——集智慧、果敢、坚毅、风趣于一身,但却一贯藐视黑人的巴特勒船长(Butler)在《风逝》中却是一个无赖,爱上了黑人女议员,最终破产。因此,《风逝》虽然模仿了《飘》的内容,但却通过对这些内容的改造表达了一种与《飘》截然对立的思想观念和感情,从而形成了对《飘》的批判,构成了典型的“模仿讽刺”。⑧
在另一起著名的诉讼Campbell v.Acuff-Rose Music中,原告为电影《风月俏佳人》主题歌《漂亮女人》(Oh,Pretty Woman)的版权人。歌曲《漂亮女人》与电影一样,以柔和、优美的音乐和富有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名百万富翁与一个虽然以卖笑为生,但却美丽而纯真的女孩一见钟情,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使女孩“麻雀变凤凰”的浪漫爱情故事。而一个名为2 Live Crew的乐队则在保持原曲基本旋律和极个别词句的基础上,重新填写了歌词,极力用粗俗、下流的语言描写街头妓女的肮脏、邋遢和沉沦。同时又通过别具一格的演唱风格和乐器效果使得原曲的旋律变得嘈杂和不和谐,从而与原歌曲无论在所要表现的思想感情还是表达风格方面都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通过对原歌曲旋律、歌词的模仿与改造,新歌曲展现了街头妓女的真实生活状态,由此揭示了原歌曲中所谓“灰姑娘与白马王子”的故事不过是骗人的神话而已,而且达到了对原歌曲强烈的嘲弄和讽刺效果。因此被告的行为也被美国最高法院认定为“模仿讽刺”。⑨
二、具有独创性的“模仿讽刺”是特殊形式的“改编”
各国著作权法都是以规定著作权人所享有的一系列“专有权利”为核心的。每一项“专有权利”都控制或限制着一类行为,如果他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也缺乏法律规定的其他特定依据,如“法定许可”、“合理使用”等,而擅自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则构成对著作权的“直接侵权”。“改编权”即是著作权人控制“改编”行为的“专有权利”。在著作权法意义上,“改编”是指利用原作的基本表达,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⑩
“模仿讽刺”在符合独创性要求的前提下,即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改编”。在对原作进行“模仿”和“讽刺”的过程之中,如果作者不仅保留了原作的基本“表达”(expression),如小说、戏剧的故事情节、音乐的基本旋律、画面或照片中的视觉形象,(11) 而且还加入了足够的独创性成份,如对原作内容进行创造性地转换、调整、拼接,并加入新的表达内容等,使得“模仿讽刺”的结果在整体上具有独创性,就会形成新的“模仿讽刺作品”。
由于“模仿”的结果必然是大量采用与原作相似的“表达”,在“模仿讽刺”的结果符合独创性的要求,从而构成“模仿讽刺作品”的情况下,这一新作品在内容上不可避免地会与原作有实质性相似,甚至往往是高度相似之处。此时“模仿讽刺作品”必然构成原作的“改编作品”。例如,在上文所引述的SunTrust案和Campbell案中,艾丽丝·兰德尔对《飘》进行了创造性改造,完成了长篇小说《风逝》,2 live crew乐队对电影主题歌《漂亮女人》进行重新填词并改变了音乐表达形式,无疑均在原作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但《风逝》大量使用了《飘》的情节;而2 live crew乐队的新歌与《漂亮女人》在基本音乐旋律上相似,这使得它们均成为原作的“改编作品”(又称“演绎作品”)。
在通常情况下,对“改编作品”的后续利用是受到原作著作权“改编权”控制的行为。如果他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而对其作品进行改编,并以发行等手段利用改编之后的新作品,即构成对原作作者“改编权”的侵犯。例如,未经许可即将他人创作的小说绘制成漫画,即是以漫画形式表达了原先以文字讲述的故事,并公开出版发行,就构成对“改编权”的侵犯。(12)
如果作为“改编作品”的“模仿讽刺作品”对原作的改编不能被认定为“合理使用”,则擅自对他人作品进行“模仿讽刺”并加以利用的行为构成对“改编权”的侵犯。因此,作为一类作品形式,“模仿讽刺作品”是否能够被合法地自由创作和利用即取决于它是否为“合理使用”的产物。
三、“模仿讽刺作品”的特殊性质及其法律意义
各国著作权法虽然赋予了著作权人一系列“专有权利”,以保障其能够通过控制特定行为而获得经济报酬。但是,著作权立法的终极目的并非单纯地奖励作者,而是鼓励创作、推动知识传播、文艺的繁荣和进步。因此,对“专有权利”的保护必须与其他一系列广泛的社会政策相协调,与公众参与社会民主生活、从事学术研究和科学教育的自由相适应。某些类型的文艺创作形式或社会活动因具有某种推动、实现这些社会政策与自由的特殊性质,需要有比其他类型作品或活动具有利用现有作品的更大自由。为了实现保护著作权与实现其他社会政策之间的协调,《伯尔尼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都规定各国可在著作权法中规定构成“合理使用”的情形,也就是使用作品行为在不妨碍对作品正常利用、不无故侵害作者合法利益的条件下,(13) 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费用。(14) 如文艺评论、课堂教学、新闻报导分别与言论自由、知识传播和信息共享的社会公共目的相关,只要不超过必要限度对著作权人造成不合理的损害就可构成“合理使用”。因此,在分析“模仿讽刺”是否构成对原作的“合理使用”时,必须分析其是否具有推动其他重要社会政策的特殊性质,是否会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利益,从而值得著作权法予以特殊对待。
(一)“模仿讽刺作品”可以构成对原作的“转换性使用”,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评论”
在各国著作权法中,为了对作品进行评论而适当地引用作品被公认为“合理使用”。(15) 我国《著作权法》也明确规定:为评论某一作品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是“合理使用”。(16) 为什么以“评论”为目的的适当引用可以构成“合理使用”呢?除了上文所述的社会政策原因之外,美国《版权法》中的“转换性使用”理论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一问题,并成为判断“模仿讽刺作品”性质的依据。
所谓“转换性使用”,是指对原作的使用并非为了单纯地再现原作本身的文学艺术价值或实现其内在功能或目的,而是通过增加新的美学内容、新的视角、新的理念或通过其他方式,使原作在被使用过程中具有了新的价值、功能或性质。(17)
例如,文学评论家为了评论一首20字的短诗而在1000字的论文中引用了短诗全文。虽然这种引用构成对短诗的“复制”,但原作——短诗在新作品——评论文章中的作用却发生了一种富有建设性的转换。新作品不是为了单纯地展示这首短诗的艺术价值和魅力、让读者仅仅欣赏短诗本身,而是将短诗作为引子,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对短诗的评价。评论文章的主要价值和功能,不在于它所引用的短诗本身,而在于对短诗的评论部分。如果评论文章获得了良好的社会评论并为作者带来了利益,并不是因为文中引用了短诗,而是因为对短诗的评论在创作上是成功的。
相反,对作品进行的一般性“改编”,如将一部长篇小说改成长篇漫画,却通常并不是“转换性使用”。尽管漫画家投入的大量创造性劳动是漫画作品价值的来源之一,但这种“改编”毕竟只是以漫画的形式讲述了小说中的故事。小说中的主要内容——人物、人物之间的关系、故事情节等均在漫画中得以完整地体现,并且是漫画作品价值和功能的组成部分。换言之,原作的艺术价值和功能在新作品中并没有发生建设性的转换,而是以另一种表现手法被展示和实现。新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功能同时来源于小说作者和漫画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如果漫画作品在市场上获得了成功,并不仅仅是因为漫画本身画得引人入胜,还因为它描绘的是小说中的故事。
美国法院认为:使用越是具有“转换性”越有可能构成“合理使用”。甚至商业性地使用原作也可因此而构成“合理使用”。(18) 这是因为“转换性使用”推进了版权法促进文艺发展的终极目标。笔者认为:在高度“转换性使用”形成的新作品中,原作对于新作在价值和功能上的贡献并不大,要求新作品作者获得许可和支付报酬并不合理,反而影响对作品的创作。相反,如果原作并未被新作加以“转换性”地使用,则新作品的价值和功能很大程度上直接来源于原作,此时要求新作品作者获得许可和支付报酬就是公平的。因此,将以“评论”为目的适当引用认定为“合理使用”的重要法理基础就在于,这种适当引用是对原作的“转换性使用”。
那么,“模仿讽刺”是否能够构成对原作的“转换性使用”呢?对此并不能做出一概而论的回答,而必须针对个案进行分析。美国最高法院在campbell案中指出:如果新作只对原作进行了微不足道的讽刺,却大量使用了原作中的内容,并不构成“转换性使用”。(19)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原作被使用部分的价值在新作中仍然直接被加以利用,从而构成了新作品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并不符合“转换性使用”的要求。相反,如果被“模仿/使用”的部分在新作品中均被改造成了讽刺和批判的工具,使得其原先的美学价值丧失殆尽,原本所论述观点被颠覆、原来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被推翻,则这种使用必然是“转换性”的。
在这种情况下,“模仿讽刺”虽然并不采用评论文体,也缺乏对原作的直接文字评判和论述。但是,它的本质目的和最终效果却与一般“评论”是相同的,都是通过对原作“转换性使用”,使公众从新作品中感受到作者对原作的态度和观点。只不过“模仿讽刺”永远都是表现对原作思想感情的否定评价,而且是以创造性模仿原作内容的方式进行的。
仍然以《风逝》为例,《风逝》虽然与《飘》一样采用了讲故事的小说形式,并大量“模仿”了《飘》中的人物与情节,但作者同时对其进行了大量改动、加入了新的故事情节,并通过不同的讲述角度、语气,将《飘》改造成了一个用于攻击原著思想观点的新故事。在《风逝》中,原著的价值与功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被用于传达与原著截然相反的思想感情和观点立场——对黑奴制度的控诉、对黑人争取自由与解放的讴歌。显然,作者进行“模仿讽刺”的主要目标和实际效果不是让读者欣赏小说中的故事本身,而是使读者强烈地感受到它对《飘》这部小说立场、态度和情感的驳斥、批判和嘲讽。因此,《风逝》作者所进行的“模仿讽刺”是对小说《飘》高度的“转换性使用”。它实际对《飘》产生的评论效果甚至可能超过通常的文字评论。
因此,应当认为“模仿讽刺”对于被模仿和被讽刺的原作而言,可以构成一种特殊形式的“评论”。(20) 在其具有高度“转换性”以及符合下文所述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享受著作权法给予“评论”的特殊待遇——为了讽刺与批评原作而对原作进行的适当模仿,可以成为“合理使用”。
(二)“模仿讽刺作品”必须大量借用原作内容,其“适当性”应从“讽刺”的需要加以考虑
即使是“评论”,引用原作的数量也应当适量。过度的引用会冲淡“引用”的“转换性”性质,从而不利于认定“合理使用”。因此我国《著作权法》为“评论”作品构成“合理使用”设定了“适当”引用的前提条件。一般情况下,认定“合理使用”要考虑被使用部分在原作中的长度与重要性。被使用部分占原作的比例越大,越是处于核心地位,就越难以成立“合理使用”。(21)
顾名思义,“模仿讽刺作品”必须对原作进行“模仿”,而且往往需要以“模仿”方式使用原作中的大量内容,甚至是核心内容。表面上看,这种使用是很难成立“合理使用”的。(22) 但是,“模仿讽刺”这种艺术创作形式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特性——“模仿讽刺作品的幽默或评论,都必须来自于通过扭曲的模仿唤起人们对被讽刺对象(原作)的记忆”;“它的艺术性就在于已知的原作和对其进行模仿讽刺而来的双胞胎兄弟(模仿讽刺作品)之间存在紧张关系”。(23) 只有大量使用原作中的内容,而且往往必须是最核心的内容,使读者、观众或听众想起原作表达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才能树立起批判的“靶子”,并通过对原作在模仿基础之上的改造、创作达到对原作的讽刺效果。如果“模仿讽刺作品”对原作的使用甚少,根本无法让人将新作与原作联系起来,则不可能实现对原作进行批判和讽刺的目的。
正是由于“模仿讽刺作品”在创作上的这种特殊性,美国《版权法》判例承认:必须允许“模仿讽刺作品”充分地使用原作中的内容,甚至引用原作中最突出和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部分,以确保能够“唤起”(conjure up)人们对原作的回忆。(24) 否则,由于原作作者通常不会准许他人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模仿讽刺”,“模仿讽刺”作为一种文艺创作形式将无从生存。这样,就需要为保护和鼓励对“模仿讽刺作品”的创作采用一项特殊政策——只要是为了通过模仿和再创作对原作加以讽刺和批判,就可以使用原作中相应的核心内容。换言之,“模仿讽刺作品”可以比其他形式作品更多地使用原作中的内容。单纯地以原作中有多少内容被“模仿”来判断“模仿讽刺作品”是否构成“合理使用”并不合适。
剩下的问题就在于:在被使用的部分已经足以“唤起”人们对原作的回忆之后,“模仿讽刺作品”还能使用多少原作中的内容?换言之,何种程度的“追加模仿”能够构成“合理使用”呢?
对此,美国法院曾经有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认为:即使对原作的使用超过了“唤起”回忆的需要,只要“模仿讽刺”“建立在作为现代文化组成部分的原作基础之上,对于幽默效果或评论做出了贡献”,仍然构成“合理使用”。(25) 另一种认为:“模仿讽刺”作品对原作的使用应当以“唤起”人们对原作回忆的为限度。(26)
第一种观点显然对“模仿讽刺”过于宽松了。它意味着只要加入了一些幽默的因素,即使对原作的使用远远超出了为“唤起回忆”和“讽刺与批评”所需要的程度,仍然可以构成“合理使用”。这将为以“模仿讽刺”为名,通过对原作进行简单地“幽默处理”而剽窃其内容打开方便之门。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campbell案中指出的那样:将贝多芬的第5交响乐用打击乐表现出来这一想法本身就足以让人发笑了。因为用新方法演绎老音乐所导致的风格差异总会具有娱乐效果。如果允许他人以这种方式轻易地使用原有作品并在事后声称这是构成“合理使用”的“模仿讽刺”,就会削弱版权保护。(27)
而第二种观点则可能过于机械。因为“模仿讽刺作品”很可能需要对原作在各个方面进行抨击和讽刺,而不仅局限于足以让人们想起原作的部分。仅仅将使用原作的限度定为“唤起”人们记忆的必需,将会对“模仿讽刺作品”的创作造成过分的限制。正因为如此,第二种观点在美国也并未得到多少支持,法院的一系列判决都认为“模仿讽刺”可以为了实现最佳讽刺的效果而适当地越过“唤起记忆”的界限。(28)
那么,在两种较为极端的观点之间,判断“模仿讽刺作品”对原作的使用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标准是什么?显然,“模仿”应当“适当”,这与要求为“评论”目的而进行的引用必须“当”实际上是相同的。问题仍然在于:在足以“唤起”人们对原作的记忆之后,何种程度的“模仿”是“适当”的?笔者认为:“模仿”应与“讽刺或批评”相适应,同时还要考虑“转换性使用”的程度。如果被“模仿”的部分经过加工改造之后,达到了对原作进行讽刺或批评的效果,从而实现了“转换性使用”,这种“模仿”就是“适当”的。相反,如果被“模仿”的部分与讽刺或批评的效果并无关系,其原有的美学价值和功能在新作品中并无发生变化,则“模仿”缺乏适当性。换言之,在“唤起记忆”的目的达到之后,对原作的“模仿”越与对原作的讽刺和批判有关,越有可能构成“合理使用”。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模仿”是否是为了对作品进行“讽刺和批评”、“模仿”的必要性如何等问题与文艺理论和实践有关,并非法官所擅长回答的。早在1903年霍尔姆斯法官就对由只受过法律训练的法官来判断作品美学价值的危险性给予过著名的警告。(29) 因此,在面对“模仿”的“适当性”问题时,法官不能仅凭个人印象做出判决,而应当听取双方的举证和专家证言。
在SunTrust案中,这一问题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原告虽然承认《风逝》是对《飘》的“模仿讽刺”,但认为《风逝》对《飘》内容的使用已经超过了为达到“模仿讽刺”目的的必要限度。例如,在《风逝》使用《飘》中的情节中,有一个是将黑奴小孩作为给新出生的白人双胞胎的礼物予以赠送。《风逝》转换性地使用这一情节,以批判原著不将黑人当人对待,可以构成“合理使用”。但《风逝》还继续使用了有关双胞胎的细节描写,如他们天生是红头发,双双在葛底斯堡战役中战死等,这与对原作的批判并无直接关系。对此,法院指出:“文学上的相关性问题的分析是高度主观性的,由法官进行判断并不合适。”(30) 最后,法院在考虑其他因素后,虽然强烈地倾向于认定《风逝》为“合理使用”,但仍然发回重审,要求地区法院进行进一步审理。
(三)适当模仿而形成的“模仿讽刺作品”不会损害原作作者的经济利益
著作权法是以“利益平衡”为核心的。在通过“合理使用”制度允许为保障公民其他政治经济权利而自由使用作品时,著作权法也设置了必要的限制,以防止对作者经济利益的不当损害。《伯尔尼公约》和TRIPs协议为“合理使用”规定的“三步检验标准”之中的核心,也是保护作者的合法利益免受不合理的侵害。美国《版权法》第107条列举的判断“合理使用”第四个考虑因素也是“对原作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显然,如果一种使用作品的行为会影响作品在市场上的正常销售,形成经济学上的“市场竞争”和“市场替代”效果,则必然会损害作者的经济利益。
需要指出的是:在考虑一种使用行为对原作市场造成的损害时,不仅要考虑现实的损害,也要考虑“潜在”的损害。例如,作者出版小说之后,如他人未经许可将小说故事改编成漫画形式并公开出售,并不会与小说的市场形成竞争,相反还可能会提高小说的销量。但是,这种未经许可的改编行为却损害了作者开发小说“改编作品”市场的能力。换言之,小说作者本来可以行使“改编权”、有偿许可他人将小说改编成漫画,从而充分实现其作品的市场价值。即使小说作者尚未许可他人改编作品,甚至暂时还没有这样的计划,但改编者对“改编作品”市场的抢占却会使作者永久地丧失相同的市场,这种“潜在损害”是著作权法所要防止的。
“模仿讽刺作品”对原作的批判、嘲弄和讽刺可能会使人对原作产生厌恶之情而不再愿意购买,这当然会对原作的市场造成“损害”。但是,这种由批判和讽刺所导致的“损害”却并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损害”。一部作品问世之后,作者有权根据著作权法阻止他人未经许可为牟取个人经济利益或声誉窃取作品的内容,如抄袭、剽窃作品或擅自出版改编作品。但是,社会公众也有权依据宪法对作品的内容和思想感情进行评论,包括批评和讽刺。这正是宪法所保障的表达自由。对此,作者无权加以禁止,著作权法也从未赋予过作者这种权利,否则就会使著作权沦为实施限制思想和表达自由的工具。例如,当一部新小说出版后,如果因为文艺评论家发表文章批评其格调低下、艺术表现手法过时而销量不佳,小说的作者必须容忍这种评论而导致的“市场损害”。由于“模仿讽刺”可以构成对原作的“评论”,由其强烈的批评或讽刺效果而对原作市场造成的“损害”同样不是著作权法所应当阻止的。
同时,真正高度“转换性”的、通过“适当模仿”而对原作进行讽刺与批评的作品也不会以其他方式对原作的市场造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损害”。喜好赞扬而厌恶批评是人之常情。如以小说为例,作者们一般都愿意许可他人将小说改编成漫画、戏剧或拍摄成电影。这不仅是因为从中可以获得许可费,更重要的是这种改编本身就是对小说艺术价值的肯定和褒扬。相反,作者们通常却不愿意他人通过模仿自己的小说而对小说进行批判和讽刺,更不会亲自这样做。在campbell案中,2 live crew乐队曾经致函歌曲《漂亮女人》的版权人,要求获得对其作品进行“模仿讽刺”的许可,却遭到了措辞严厉的拒绝。这充分说明作者绝少会去为自己的作品开发一个“模仿讽刺作品市场”。因此,虽然通过适当模仿而形成的“模仿讽刺作品”与一般“改编作品”都来自于对原作的“改编”,但两者不但在使用原作的方式和目的上有重大区别,而且在对原作市场的影响方面也截然不同——前者不会与原作形成直接的或潜在的市场竞争关系,不可能损害其市场价值。
真正的“模仿讽刺作品”与普通“改编作品”在这一点上的差异,也为著作权法对“模仿讽刺”给予较为宽容的特殊待遇提供了经济学上的依据:由于作者一般愿意有偿许可他人对其作品进行通常意义上的“改编”,有关许可费的机制可以通过市场规律自动形成。如小说越是有名,希望将其改编成其他形式作品加以利用的人就会越多,其愿意支付的许可费也就越高。这对于原作作者和改编者而言是“双赢”的结果——作者从作品中获得了充分的经济回报,进一步产生了创作出优秀作品的动力,而改编者之所以情愿支付许可费,是因为成功的改编作品同样能给其带来经济利益,如电影公司改编成名小说拍摄电影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著作权法无需通过“合理使用”制度对这种市场机制加以干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者通常不愿为了经济利益而许可他人对作品进行“模仿讽刺”,或者会要求过高的许可费,以补偿因蒙受批评与讽刺而在名誉和心理上受到的不利影响。这将导致希望对作品进行“模仿讽刺”的人根本无法获得许可,或者不愿支付作者要求的高额许可费。这样,有关“模仿讽刺作品”的许可机制就无法通过市场规律而自动形成。如果著作权法不将“模仿讽刺”在一定条件下认定为“合理使用”、直接许可创作者对他人作品进行合理的“模仿讽刺”,则“模仿讽刺作品”就会因为无法获得原作作者的“自愿许可”和法律的许可而无法生存。这将从根本上违反著作权法鼓励创作和传播优秀作品的宗旨。
当然,如果对原作的“模仿”超过了对原作进行批判和讽刺的需要,演变为仅为利用原作自身的美学价值和功能而窃取原作内容,则可能潜在地损害原作的“演绎作品”市场。(31) 例如,将他人创作的抒情音乐在保留原曲中全部旋律的情况下将其改成摇滚乐,其中虽然可能会因表现手法的改变而带有讽刺的意味,但除非改编者能够合理地论证保留全部旋律是与讽刺目的相适应的,否则这种“模仿”很难被认定为“合理使用”。因为原曲作者一般是愿意许可以这种形式对原曲进行改编的,同时未经许可的改编必然会影响作者开发其“摇滚版”音乐的市场。在Cambpell案中,虽然2 live Crew乐队对歌曲《漂亮女人》的歌词几乎全部重新填写,但毕竟保留了原歌曲的主要旋律,尽管是以打击乐的方式加以演绎。对此,美国最高法院虽然在综合考虑之后,倾向于认定构成“合理使用”,但由于双方未能就2 live Crew乐队的“模仿讽刺”是否会对“打击乐版《漂亮女人》”的市场产生潜在损害进行充分举证,最高法院仍然将案件发回重审。(32)
上述认定“模仿讽刺”构成“合理使用”的三方面分析之间也有高度的关联性。“模仿”越是与对原作的批判或讽刺相适应,“模仿”就越具有“转换性”,因为这必然导致被模仿的原作内容在价值、目的和功能上发生了“转换”,模仿者就越难以获得原作作者的许可,由此而产生的新作品就越不会直接或潜在地损害原作的市场价值。
四、对《馒头血案》的初步分析
应用上文的结论,可以对网络短片《馒头血案》是否构成“合理使用”进行初步分析。首先,如上文所述,《馒头血案》毫无疑问构成电影《无极》的“改编作品”。《无极》的制片人享有对《无极》的“改编权”。利用《无极》的视频画面制作“小电影”并加以后续利用,包括进行网络传播,是受到“改编权”控制的行为。
其次,《馒头血案》当中不乏对《无极》进行“模仿讽刺”的内容。例如,《馒头血案》一面再现了《无极》中的“满神”让幼年时的“张倾城”以终身放弃被爱的权利换取衣食无忧生活的画面,一面配以声音评论:“她总是以荣华富贵来引诱未成年的小女孩”。在《馒头血案》的末尾,又一本正经地在打出“满神”剧照的同时,告诫“家长们一定要告诉你们的子女,如果在外面遇到了一个头发竖起的阿姨,不管她问什么,一定要回答‘不愿意’,以免延误终身大事”。显然,《馒头血案》引用《无极》“满神”的相关镜头,并非为了让观众欣赏《无极》这些镜头所表现的故事情节,而是为了讽刺《无极》中“满神”这一人物的虚伪和狡猾。
再如,《馒头血案》中使用了“张倾城”在小时候欺骗了“谢无欢”、抢回并吃掉了馒头,以及20年后“谢无欢”在“张倾城”面前捏碎了“当年的馒头”、以示报复的镜头。旁白指出:“看,这个馒头已经被吃了,那么谢无欢此时手里捏的这个馒头,是哪里来的呢”?以此揭示电影《无极》在剧情设计上的漏洞——20年前被“张倾城”吃掉的馒头却又被“谢无欢”拿了出来。而《馒头血案》制作者为“谢无欢”镜头的滑稽配音——“关于这个问题,我也说不清,这都是导演的安排”则更加强化了讽刺《无极》编剧水平不高、前后矛盾的效果。对这两组镜头,《馒头血案》最后的评论是——“一个小小馒头就能引发出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尤其是现在孩子的家长们,要重新考虑一下教育子女的方式,让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千万不要学谢无欢这样,因为一个馒头就能记仇20年。”显然,这是在以诙谐的方式批评《无极》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过于离谱,前后事件因果关系过于牵强。因此,《馒头血案》对上述两组镜头的使用也是“转换性”的,是为了揭示和嘲讽《无极》之中的谬误和荒诞之处。
如果自始至终,《馒头血案》都是在以上述方式使用《无极》的镜头,则根据上文对“模仿讽刺作品”特点和相应著作权法规则的分析,这种使用是很有可能构成“合理使用”的。
但是,从整体上看《馒头血案》对《无极》本身的讽刺、批评却并不占很大比例。虽然这种改编同样令人发笑,而且也有嘲讽他人之处(如“郎警官”嫌刘翔跑得慢,挡了他的道),但这种嘲讽却并非针对《无极》本身。根据上文的分析,单纯利用《无极》画面创作新作品的“改编”行为并非“转换性使用”,不能在著作权法中获得与一般“改编作品”相区别的特殊待遇。如果《无极》的著作权人起诉《馒头血案》的制作者侵犯其“改编权”,则后者必须证明自己对《无极》画面的引用在整体上是与对《无极》的讽刺和批评相适应的。而且也不会潜在地影响《无极》著作权人对“改编作品”市场的开发。正如上文所述,对于创作作品的目的、价值和效果,并不是法官能够单凭印象就能做出判断的,而应当取决于争议双方的举证情况以及专家证言。
无论如何,《馒头血案》事件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使我国知识产权法学界第一次真正面对“模仿讽刺”这种特殊文艺创作形式引发的著作权问题。深入研究国外相关理论和判例,细化《著作权法》的“合理使用”规则,应当是《馒头血案》事件对我国知识产权法学界的最大启示。
注释:
①有观点认为只要《馒头血案》的制作和传播不具有商业或盈利目的,就构成“合理使用”。这是不能成立的:盈利动机或商业用途只是考虑使用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一个因素,而绝非惟一因素。例如,没有任何广告的纯个人网站提供最新电影供公众免费下载,仍然是典型的侵权行为。
②笔者将parody的名词形式译成“模仿讽刺作品”,动词形式译成“模仿讽刺”,这种译法我国著作权法学者以往似未提出过。
③Se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 3rd Edition) ,Houghton Mifflin( 1992) p.1317.
④See Black' s Law Dictionary( 8th Edition) ,West Publications( 2004) ,parody.“转换性使用”是一个美国版权法中的专有术语,下文将进行解释。
⑤See Campbell v.Acuff-Rose Music,510 U.S.569,at 580( 1994)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法院将“讽刺”作为“评论”的一种形式,下文将有论述。
⑥美国法院指出:要构成parody,新作品必须“对原作品进行批判性的评论或陈述,以反映出新作品作者一种具有创意的视角,也由此使parody具有了超越娱乐功能的社会价值”,参见Metro-Goldwyn-Mayer,Inc.v.Showcase Atlanta Coop.Prods.,Inc.,479 F.Supp.351 at 357( N.D.Ga.1979) 。
⑦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一些法院在早期的判例中,并没有将parody限定于对被模仿作品本身的讽刺,如Elsmere Music,Inc.v.National Broadcasting Co.,482 F.Supp.741 at 746( S.D.N.Y.1980) ,Berlin v.E.C.Publications,329 F.2d 541 at 545( 2nd Cir 1964) ,但随着判例的发展,特别是美国最高法院在Campbell案中对parody进行定义之后,现在单纯模仿原作品创造滑稽效果,而不对原作品进行讽刺批判的作品,已经不再被认定为版权法意义上的parody了,《布莱克法律辞典》第8版对parody的解释也反映了这一点。
⑧也正是在这一案例中,美国第11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反驳了联邦地区法院有关“parody中必须含有幽默成份”的观点,指出只要通过模仿原作对原作进行批判就足以构成parody,参见Suntrust Bank v.Houghton Mifflin Co.,136 F.Supp.2d 1357 at 1373( N.D.Ga.2001) ,Suntrust Bank v.Houghton Mifflin Co.,268 F.3d 1257 at 1268( 11th Cir,2001) 。
⑨Campbell v.Acuff-Rose Music,510 U.S.569( 1994) .
⑩由于单纯的思想观念、创意等不构成“作品”、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因此如果某人仅仅借用了原作品中的思想观念或创意而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则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对原作品的“改编”。
(11)需要指出的是:有人认为著作权法保护的是作品的“表达形式”,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它会使人误认为著作权法不保护与“形式”相对应的“内容”。事实上,小说的故事情节等内容如果符合独创性的要求,是受到著作权保护的。将小说一字不差地抄袭固然是侵权,对小说以“同义词替换”的方式将每一句话都加以改写,即以不同的表达形式讲述同一个故事,仍然构成侵权。因此,正确的说法应当是著作权只保护“表达”(expression)而非“思想”(idea)。
(12)如果单纯地“改编”而不对由“改编”而产生的新作品进行任何后续利用,则显然构成“合理使用”而非侵权。德国的《著作权法》则干脆规定“改编权”仅控制对由“改编”形成的作品(“改编作品”/“演绎作品”)进行利用的行为。这样一来,单纯的“改编”行为就不受“改编权”控制了,单纯改编者也无需根据“合理使用”主张免责。参见《德国著作权法》第23条;[德]M.雷炳德著:《德国著作权法》,张恩民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页。
(13)“行为只能在特定情况下进行,且不能与作品的正常使用相冲突、不能无故侵害作者的合法利益”,这三个条件被称为“三步检验标准”(Three-step standard)或“三步检验法”(Three-step test),参见《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2款,TRIPs协议第13条。参见WTO:Report of the Panel,United States-Section 110( 5) of the US Copyright Act,WT/DS160/R( 15 June 2000) 。
(14)对“合理使用”制度的表述各国著作权法并不相同。如美国版权法使用的术语是“合理使用”(fair use)、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其他英美法系国家版权法使用的术语是“公平交易”(fair dealing),而大陆法系国家著作权法则使用“对权利的限制和例外”。但相关的法律条款中都允许在特定情况下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费用就可以通过原本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来使用作品。
(15)参见《伯尔尼公约》第10条1款,以及《伯尔尼公约指南》第10.2段。
(16)参见《著作权法》第22条1款2项。
(17)“转换性使用”的概念本身并没有出现在美国《版权法》中,而是美国法院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具体论述散见于大量判例中,在Campbell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指出:判断“转换性使用”的关键是“新作品是否仅仅替代了原作的目的,还是增加了新的东西,具有更进一步的目的或不同的性质,用新的表达、意义或信息改变了原作。”参见Campbell v.Acuff-Rose Music,510 U.S.569 at 579( 1994) 。正文中对“转换性使用”含义的界定是笔者综合这些论述之后的总结。
(18)在美国《版权法》107条列举的供法官用于判断一种对作品的使用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四个因素中,第一项就是“使用的目的和性质”,而美国法院除了考虑使用是否具有商业性之外,更加注重使用是否具有“转换性”。美国最高法院指出:作品越是具有“转换性”,其他不利于认定合理使用的因素的意义就越小。参见Campbell v.Acuff-Rose Music,510 U.S.569 at 579( 1994) 。
(19)See Campbell v.Acuff-Rose Music,510 U.S.569 at 583( 1994) .
(20)美国最高法院在Campbell案中明确认定:“模仿讽刺”(parody)就是一种“评论和批评”(comment and criticism)。参见Campbell v.Acuff-Rose Music,510 U.S.569,at 579( 1994) 。
(21)参见17 USC 107。但是,美国法院和学者们也强调:不能认为只要复制了作品的全部就不可能构成“合理使用”,也不存在一个可以量化的绝对规则,参见Maxtone-Graham v.Burtchaell,803 F.2d 1253( 2nd Cir.) ,cert.denied,481 U.S.1059( 1987) 。
(22)正因为如此,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院在审理Campbell案时认为:“使用原作品的核心内容,使之成为新(模仿讽刺)作品的核心内容等于同盗取原作最重要的精华”,并判决2 Live Crew乐队对《漂亮女人》进行的“模仿讽刺”不是“合理使用”。参见Campbell v.Acuff-Rose Music,Inc.,972 F.2d 1429,at 1438( 6th Cir 1992) ,这一观点被美国最高法院所推翻。
(23)See Campbell v.Acuff-Rose Music,Inc.,510 U.S.569 at 588( 1994) .
(24)See Elsmere Music v.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623 F.2d 252 at 253( 2nd Cir,1980) ,Fisher v.Dees,794 F.2d 432 at 438-439( 9th Cir,1986) ,Campbell v.Acuff-Rose Music,Inc.,510 U.S.569 at 588( 1994) .
(25)See Elsmere Music v.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623 F.2d 252 at 235 n1( 2nd Cir,1980) .
(26)See Berlin v.E.C.Publications,329 F.2d 541 at 544( 2nd Cir 1964) ,Walt Disney Productions,v.The Air Pirates,581 F.2d 751 at 756( 9th Cir.1978) 。甚至还有人试图将这种观点进一步解释为:“只有不超过唤起人们最初回忆的引用才是允许的”,参见Fisher v.Dees案中原告的观点,794 F.2d 432 at 438(9th Cir.1986)。
(27)See Campbell v.Acuff-Rose Music,Inc.,510 U.S.569 at 599( 1994) .
(28)See Fisher v.Dees,794 F.2d 432,at 438-39( 9th Cir.1986) .审理SunTrust案的法院指出“(模仿讽刺对原作品的)使用并不是在其超过了唤起了对原作品记忆的界限的那一刻就侵权了”,参见Suntrust Bank v.Houghton Mifflin Company,268 F.3d 1257 at 1273( 11th Cir.2001) 。
(29)See Bleistein v.Donaldson Lithographing Co.188 U.S 239 at 251( 1903) .
(30)See Suntrust Bank v.Houghton Mifflin Company,268 F.3d 1257 at 1273( 11th Cir.2001) .
(31)美国最高法院在campbell案中指出:在使用了足以确保“唤起记忆”的部分之后,使用者还能使用多少内容将取决于新作品的主要目的和性质,即新作品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对原作进行模仿讽刺,以及新的模仿讽刺作品在市场上替代作品的可能性有多大,参见campbell v.Acuff-Rose Music,Inc.,510 U.S.569 at 588( 1994) 。
(32)See Campbell v.Acuff-Rose Music,Inc.,510 U.S.569 at 593-594( 1994) .
标签: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论文; 著作权法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合理使用论文; 法律论文; 漂亮女人论文; 版权法论文; 风逝论文; 无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