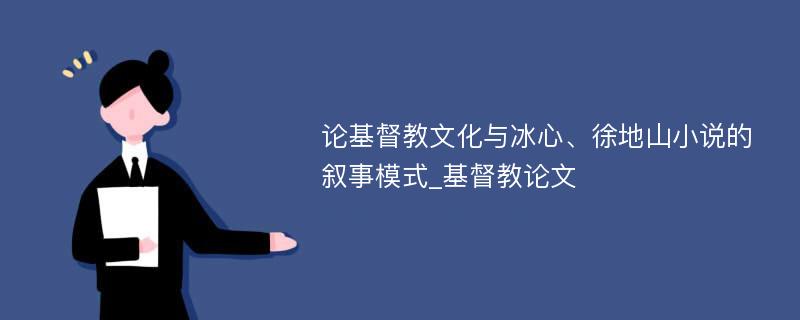
论基督教文化与冰心、许地山小说的叙事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冰心论文,基督教论文,文化与论文,模式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9)03-0052-09
在现代文学史上,冰心与许地山都是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作家,他们都曾经受洗入教,成为虔诚的基督徒;他们的创作都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或描写基督徒的生活,或礼赞基督教的思想,使他们的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基督教色彩。由于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他们的小说叙事模式具有独特性,或多或少受到了《圣经》文本的影响,构成了他们小说创作的独特魅力。
一
冰心于1914年考入了北京的教会中学贝满女中,在4年的教会学校的学习中,在学校开设的《圣经》课上,她系统地学习了基督教的经典;在学校每天上午半小时的牧师讲道中,在每个星期天教堂的礼拜中,她较为深入地了解了基督教教义。考入协和大学(后来并入燕京大学)后,这所教会大学仍然有《圣经》课程。冰心在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说:“中学四年之中,没有什么显著的看什么课外的新小说。……我所得的只是英文知识,同时因着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1:143]在燕京大学,冰心在一位老牧师家里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冰心后来解释说:“因为当时先生说许多同学都在看我的样,我不受洗她们也都不受洗,我说那容易,便那么办了。”[2:102]在冰心的文学修养中,《圣经》对她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她曾经回忆在中学时代仿《圣经》中的雅歌写作的情况:“那时我在圣经班里,正读着‘所罗门雅歌’,我便模仿雅歌的格调,写了些赞美T女士的句子,在英文练习簿的后面,一页一页的写下迭起。积了有十几篇,既不敢给人看,又不忍毁去。……那年我是十五岁。”[3:428]冰心以雅歌的形式赞美“螓首蛾眉,齿如编贝”、美丽善诱的女教员,可见《圣经》对于冰心的深刻影响。
“五四”时期,受了洗的冰心成了基督教团体“生命社”的成员。这个1919年成立的基督教教义辩护团,也叫证道团,“生命社的成员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其共同目标是‘证明基督教的真谛和价值,以及基督教对中国的现实意义’”[4]。“五四”时期,冰心创作了不少圣诗,其中许多诗歌发表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会刊《生命》上。“五四”时期的冰心,无疑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的小说创作受到了《圣经》直接的影响。
许地山小时候曾经跟着一位英国牧师学习英文,这大概是他最初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① 1913年许地山赴缅甸仰光中华学校任教,1916年回国在漳州华英中学任教,在这年间许地山加入了基督教闽南伦敦会,成为一位基督徒。1917年他到北京燕京大学读书,“就为的是一所教会大学,有津贴”[5]。以后“不管到何地,在‘主崇拜日’的时候,他必到附近教堂里和教友一起认真地做弥撒,严格遵守教会的一切仪式规则”[6:101]。1920年许地山在燕大文学院毕业后,又入燕大神学院学习。1922年他在燕大神学院毕业,获神学学士学位。1923年许地山与冰心一起赴美国留学,他人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宗教史和比较宗教学。1927年许地山开始在燕京大学文学院、宗教学院任教,并兼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课程,着力进行基督教、道教史、佛教史等的研究。
1923年许地山在4月14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一文,认为当时中国所需要的宗教应具有如下八方面的条件:“一要容易行的。二要群众能修习的宗教。三要道德情操很强的。四要有科学精神的。五要富有感情的。六要有世界性质的。七必注重生活的。八要合于情理的。”并认为“按耶教近年发展的趋势似甚合于上述的理论”。在当时反基督教的运动中,许地山能如此推崇基督教,可见其对基督教的偏爱与执著。许地山的挚友张祝龄牧师在忆及许地山时说:“他赋性和蔼,对事,对物,对人,不轻易下批评,唯对于基督教,则多有创列,他似乎不满于现代教会固执的教义,和传统的仪文。他要自由,他是纯粹民主性。他以为基督教由希腊哲学借来的‘原质观念’的神学思想,是走不通的。他很赞成奈西亚大会所定的‘耶稣性格论’,而摩尔根教父提倡的‘回到基督运动’论,是他绝对欢迎的。”[7]
将冰心与许地山作比较,作为基督徒的冰心从基督教文化受到了“爱”的影响,潜隐地形成了她的“爱的哲学”。阿英在评说冰心的创作时指出:“无疑的,在她的作品中,也还有基督教思想的血液存在,这些血液,是流贯在她的爱的哲学之中。”[8]作为宗教学家的许地山,强调“宗教当使人对于社会、个人,负规善、精进的责任”[9],并力图“谋诸宗教的沟通”[10:376]。这就形成了他们在创作具有基督教色彩的小说时,呈现出不同的叙事模式。
二
1921年,冰心在她发表于《生命》上的一组圣诗前写道:“圣经这一部书,我觉得每逢念他的时候,——无论在清晨在深夜——总在那词句里,不断的含有超绝的美。”[11:106]可见《圣经》对于冰心的影响。1921年5月21日,冰心在散文《我+基督+?》一文中写道:“基督说:‘我是世界的光。’又说:‘你们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使徒约翰说:‘那是真光,照亮凡生在世上的人。’”“谁愿笼盖在真光之下?谁愿渗在基督的爱里?谁愿借着光明的反映,发扬他特具的天才,贡献人类以伟大的效果?请铭刻这个方程在你的脑中,时时要推求这方程的答案,就是。我+基督+?”[12]“五四”时期的冰心,在反封建的时代浪潮中,将其对于黑暗世界的同情与拯救,与对于基督的信从融汇在一起,以充满博爱之心观照世界、描写人生。
冰心曾经写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不丧掉生命的,不能得着生命。’以众生的痛苦为痛苦,所以释迦牟尼,耶稣基督,他们奋斗的生涯里,注定的是永远烦闷!”[13]以众生的痛苦为痛苦、努力拯救痛苦的人们,成为冰心小说叙事的基本内涵。在冰心的小说中,构成了一种救赎模式,她常常在努力叙写主人公难以摆脱的痛苦时,以一种难以理喻的契机拯救人物走出困境,摆脱痛苦。
小说《最后的安息》中的富家女惠姑到乡村别墅消夏,结识了童养媳翠儿,惠姑以充满了同情和怜悯之心帮助翠儿,她带饼干糖果给翠儿,教翠儿识字,她们之间产生了深厚的友谊,备受婆婆折磨的翠儿感受到了人间之爱。当翠儿被婆婆折磨得奄奄一息时,惠姑的到来给翠儿带来了关爱和抚慰,“她憔悴鳞伤的面庞上,满了微笑,灿烂的朝阳,穿进黑暗的窗棂,正照在她的脸上,好像接她去到极乐世界,这便是可怜的翠儿,初次的安息,也就是她最后的安息。”[14:95]以近似于上帝拯救的情境让翠儿离开着悲苦的世界、走向极乐世界,充满着一种救赎的意味。
《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中的青年凌瑜原先怀抱着救国救民之心投身社会运动,却受尽了挫折,他认为“这样纷乱的国家,这样黑暗的社会,这样萎靡的人心,难道青年除了自杀之外,还有别的路可走么?”[14:75]他烦闷悲苦到了极处的时候,忽然起了一个投海自尽的念头,却在海边遇到了在沙滩上采野花的孩子,孩子劝说道:“先生!世界上有的是光明,有的是快乐,请你自己去找罢!不要走那一条黑暗悲惨的道路。”小说描述凌瑜听到这话语的反应:“这银钟般清朗的声音,穿入凌瑜的耳中,心里忽然的放了一线的光明,长了满腔的热气!看着他们皎白如雪的衣裳,温柔圣善的笑脸,金赤的夕阳,照在他们头上,如同天使顶上的圆光,朗耀晶明,不可逼视,这时凌瑜几乎要合掌膜拜。”[14:77-78]出自孩子口中充满哲理的话语,在不可思议中如天使一般拯救了凌瑜。
《烦闷》中的“他”,“由看不起人,渐渐的没了他‘爱’的本能,渐渐的和人类绝了来往;视一切友谊,若有若无,可有可无”[14:368]。他常常烦闷忧郁,似乎已经窥探了社会之谜。他认为:“人生只谋的是自己的利益,朋友的爱和仇,也只是以此为转移,——世间没有真正的是非,人类没有确定的心性。”[14:363]他回到家中,见到“母亲坐在温榻上,对着炉火,正想什么呢。弟弟头枕在母亲的膝上,脚儿放在一边,已经睡着了。”这时小说写道:“他站住了,凝望着,‘人生只要他一辈子是如此!’这时他一天的愁烦,都驱出心头,却涌作爱感之泪,聚在眼底。”[14:372]母爱的场景使他获得了拯救,恢复了爱的本能。
《超人》中的何彬是一个冷心肠的青年,从来没有人看见他和人有什么来往,他认为世界是虚空的,人生是无意识的,人与人与其互相牵连,不如互相遗弃。他却在梦中见到了“慈爱的母亲,满天的繁星,院子里的花”[14:208],楼下厨房里跑街的孩子禄儿摔坏了腿半夜的呻吟,吵了他的好梦,他送钱给禄儿治病,呻吟停止了,他的梦却依然扰乱着他的心境。何彬搬走前收到了禄儿送的花和留的字条,引起了他热泪盈眶,在他留给禄儿的字条上表达了他获得了拯救:“你深夜的呻吟,使我想起了许多的往事。头一件就是我的母亲,她的爱可以使我止水似的感情,重要荡漾起来。我这十几年来,错认了世界是虚空的,人生是无意识的,爱和怜悯都是恶德。我给你那医药费,里面不含着丝毫的爱和怜悯,不过是拒绝你的呻吟,拒绝我的母亲,拒绝了宇宙和人生,拒绝了爱和怜悯。上帝呵!这是什么念头呵!我再深深的感谢你从天真里指示我的那几句话。小朋友呵!不错的,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14:211]何彬从一个憎世者转变为一个爱世者。
冰心的这些小说中都描写了痛苦者的人生,尤其突出叙写他们各自苦痛的心境。冰心执意写出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导致的绝望心态,写出他们走投无路处于绝境的状况,却以各种偶然的契机让他们获得拯救,使他们从绝境中摆脱出来,尤其获得心灵的拯救。从看破红尘厌倦人世回到摆脱痛苦热爱人生的境界,形成了冰心小说的一种拯救模式,也构成了冰心小说的博爱世界。
三
自称为有情人的许地山②,将文学分为怡情文学和养性文学。他认为怡情文学“是静止的,是在太平时或在纷乱时代底超现实作品”;养性文学“它是活动的,是对于人间种种的不平所发出底轰天雷”,“作者着实地把人性在受窘压底状态底下怎样挣扎底情形写出来,为底是教读者能把更坚定的性格培养出来”[15]。许地山推崇养性文学,他的小说努力将“人性在受窘压底状态底下怎样挣扎底情形写出来”,这形成了许地山小说的一种“天路历程”的叙事模式,他的小说大多执意让主人公经历各种磨难与苦痛,从而凸显性格的坚定与执著。
《商人妇》中的惜官16岁嫁给林荫乔为妻,丈夫嗜赌,债台高筑,惜官典当东西送丈夫去南洋。十年后,惜官飘洋过海来到新加坡找到丈夫,开杂货店的丈夫已另娶媳妇,惜官却被卖给印度商人为妾,印度商人已有5个妻子,惜官受尽了折磨。商人死后,惜官离家出走,并结识了基督徒利沙伯,并常参加她们的晚祷会。惜官仍然想去新加坡找丈夫,她想知道究竟卖她的是谁。她心里想:“我很相信荫哥必不忍做这事;纵然是他出的主意,终有一天会悔悟过来”[16:30]。经历了诸多困苦的她甚至认为, “人间一切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苦乐的分别:你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时是苦,回想时是乐。我换一句话说:眼前所遇的都是困苦;过去、未来的回想和希望都是快乐”[16:31-32]。小说通过主人公惜官的坎坷经历苦难历程,刻画出一位坚定执著的女性形象。
《缀网劳蛛》中的尚洁,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每夜睡前的功课就是跪在那垫上默记三两节经句,或是诵几句祷词”[16:75],“在无论什么事情上头都用一种宗教底精神去安排”[16:81]。外面传闻她有外遇、是淫妇,她却不在意。遇到翻墙企图盗窃不慎摔伤的窃贼,尚洁止住了仆人对他的打骂,说“一个人走到做贼的地步是最可怜悯的”。她让仆人将受伤的窃贼抬进屋,亲自为其疗治,回家后的丈夫长孙可望怒火中烧,用小刀刺伤了尚洁,教会甚至剥夺了她赴圣筵的权利。尚洁平静地离开了家,独自去了马来半岛的西岸,她在那里住了3年,教采珠工人们说英吉利语,给他们念经文。长孙可望受到牧师的教诲而悔悟,他独自到槟榔屿悔罪。尚洁回到了久别的家中,她对朋友说:“我像蜘蛛,命运就是我的网。蜘蛛把一切有毒无毒的昆虫吃入肚里,回头把网组织起来。它第一次放出来的游丝,不晓得要被风吹到多么远,可是等到粘着别的东西的时候,它的网便成了。”“它不晓得那网什么时候会破,和怎样破法。一旦破了,它还暂时安安然然地藏起来,等有机会再结一个好的。”“人和他的命运,又何尝不是这样?所有的网都是自己组织得来,或完或缺,只能听其自然罢了。”[16:88]这种缀网劳蛛式的人生态度,呈现出尚洁性格的倔强与坚定。
《玉官》中的玉官,丈夫在战争中阵亡,她决意守节带大儿子,盼望儿子将来有出息给她立一个贞节牌坊。丈夫的叔伯弟弟粪扫常来骚扰她,劝说她改嫁,以便获得利益。玉官先采取关门的“螺介政策”,后采取了躲避的“飞鸟式生活”。她去了邻居基督徒杏官家躲避,读到了杏官家的圣经,并被介绍去为牧师洋姑娘帮佣,儿子因此入了免费的教会学校读书。玉官入教后逐渐成为了一位“圣经女人”,每天到城乡各处派送福音书、讲道。她结识了看守教会房子的男子陈廉,陈廉帮助她完成祭奠公婆的事务,玉官产生了与陈廉“彼此为夫妇”的念头。儿子入了革命党被捕,玉官请求牧师说情,将儿子建德保了出来,建德被教会送进神学校读书。玉官打算辞去女传道的职业,嫁给陈廉,又因怀疑陈廉是杏官出逃的丈夫,心冷了七八分。建德的妻子病逝后,建德去美国留学,结识了女学生黄安妮。玉官在战乱中被告作通敌逃走的罪犯,落得游街示众的刑罚。儿子学成归国后,黄安妮为他还清了历年教会的费用,到南京政府中谋了个职位。建德与安妮结婚后与玉官分开过,玉官向儿子提出要表彰节妇的牌坊,儿子说旌表节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玉官去教会小学任校长,她将全部精力和财务都放在学校的事业上,教会给她举行服务满40周年的纪念会,人们自发地造了一座“玉泽桥”以资纪念。玉官离开了学校,去南洋寻找心中牵挂的陈廉。小说写出了在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冲突交融中的玉官坎坷的人生与追求,突出了玉官性格的执拗与坚定。
在许地山的创作中,《女儿心》中的麟趾受尽为盗贼所虏、为艺人所骗、为土豪所抢等种种磨难,然而她却丝毫不因此而记恨父亲,始终执著地四处寻找父亲。《春桃》中的春桃,新婚燕尔丈夫被抓伕抓走。她流落京城以捡破烂为生,与同乡刘向高同居。春桃后又在街头碰见断了双腿、以乞讨为生的丈夫李茂,她将李茂弄回家,与李茂、刘向高组成了一种奇异的关系,构成了一妻二夫的奇怪的家庭。《枯杨生花》中的云姑,寻子未成,又失落了媳妇,只有在对年青岁月爱的忆念中消磨人生。虽然他们并非基督徒,但是许地山都执著写出坎坷命运中人物性格的坚定与执著,形成了许地山小说创作“天路历程”的叙事模式。
四
五四时期,以基督教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对于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俄国宗教学家别尔嘉耶夫认为:“基督教是救赎宗教,以恶和苦难的存在为前提。……基督耶稣之所以出世,就是因为世界处于恶中。所以基督教告诫,世界和人都应有自己的十字架。苦难是罪和恶的结果,但是苦难也是脱离恶的道路。在基督教意识看来,苦难本身不一定是恶,也是神的苦难。”[17:329]基督教文化被称为是一种罪感文化,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因此人一生下来就有了罪,需要上帝的宽恕与拯救。一部《圣经》其实就是基督拯救有罪之人的写照,无论是有病患的人们,还是有罪错的人们,都得到了基督的救赎;基督甚至以自己在十字架上的受难,拯救有罪的人们至福乐之地。
冰心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她的小说采取了拯救的模式叙写故事,她总是让作品中的主人公处于绝境之中,《最后的安息》中的翠儿受尽婆婆折磨,《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中的青年凌瑜悲苦至极决定投海自尽,《烦闷》中的“他”处于难以摆脱的烦闷中,《超人》中的何彬认为世界是虚空的、人们是互相遗弃的。他们都在社会生活中厌倦人生、心理失衡。冰心都设计了一些难以理喻的情节,让这些人物获得拯救:或是临死前惠姑的关爱和抚慰,或是孩童天使般的告诫,或是孩童躺在母亲怀中的爱的境界,或是世界上的母亲与母亲都是好朋友的哲理,使处于绝境中的人物走出绝境、摆脱内心的烦闷苦痛,从肉体到心灵获得了拯救。
美国神学家坎默认为:“犹太-基督教传统认为,尽管上帝的不断努力能够改善人类的处境,能够保持宇宙万物的平衡,但上帝不能消除罪恶强加于世界的苦难,上帝选择的是承认痛苦与痛苦进行不懈地斗争。”[18:76]一部《圣经》写出了诸多人物的承认痛苦与向痛苦作斗争的苦难历程,这成为《圣经》中的一种叙事结构,它总让人物处在种种的不幸与苦痛中经受磨炼与考验,从而展示其忠诚于上帝的真心真情。《创世纪》中的约瑟被推入枯井、被出卖、被诬告、被关入囹圄;《士师记》中的耶弗他被众兄弟嫌弃后的远离家门当了土匪、被迫将独生女献作敬神的燔祭;《约伯记》中的约伯备遭天灾人祸、狂风刮倒房屋、压死儿女、疾病缠身、穷困潦倒;《约拿书》中的约拿途遇风暴、被抛入海、身陷鱼腹,《圣经》大多以人物面对种种不幸与苦难的遭遇,表达“持之以恒,自有善果”、“虽受尽磨难,却永不失望”、“忍耐到底,必然得救”的信仰③。《圣经》的这种叙事结构显然影响了许地山的小说创作。
许地山的作品也大多让人物历经种种磨难与坎坷,无论是惜官的久别、被卖、逃亡,还是尚洁的被诬、被刺、离家;无论是玉官的守寡的艰难、传教的坎坷,还是麟趾的出逃、被虏、被骗、被抢,都写出人物经受不幸与苦难的人生历程,而人物又大多能在不幸与苦难中不放弃希望、持之以恒。这种叙事结构显然受到《圣经》的影响。
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提出了文化接受的三种立场:“主导—霸权立场,协商立场和对抗立场”,被称为“霍尔模式”[19]。霍尔把“主导—霸权立场”的文化接受方式称为“优势解读”。“五四”时期,在全面否定中国文化文学传统的背景中,对于西方文化的接受就成为一种“优势解读”,基督教文化成为向西方“拿来”的一部分,甚至被陈独秀赞为拯救民族的思想资源。他说:“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的问题,不但要有觉悟,使他不再发生纷扰问题,而且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那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20]“五四”时期基督教文化为许多作家重视,他们往往各取所需地拿来基督教文化的不同因素,冰心注重基督教文化中的博爱精神,构成了她的“爱的哲学”;许地山注重基督教文化中的归善精进精神,构成了他的“落花生精神”。在小说叙事中,形成了他们不同的叙事模式,冰心的拯救模式与许地山的天路历程模式,既反映了他们各自对于基督教文化的关注点,也呈现出《圣经》对于中国现代作家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
注释:
① 见周苓仲《我的童年》,见《许地山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② 见许地山《无法投递之邮件·给爽君夫妇》,见许地山《空山灵雨》,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③ 见《马太福音》第24章12—13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