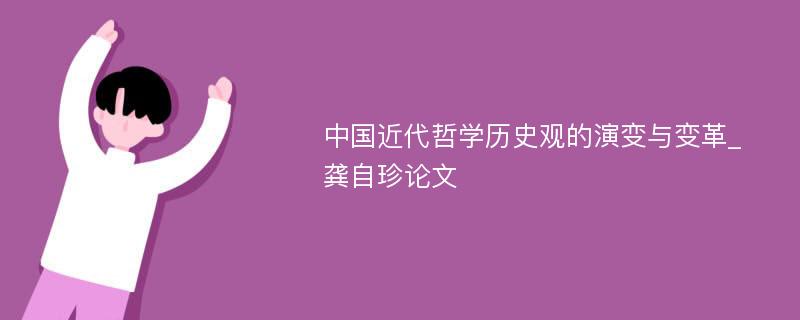
近代中国哲学历史观的演进与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观论文,哲学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揭示了近代中国哲学历史观的演进与变革,从龚自珍、魏源的变易史观,到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的进化史观,再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唯物史观,是一个梯次递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进化论。中国近代的进化论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反帝反封建最有力的思想武器。而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则实现了中国近代哲学历史观的巨大变革。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点,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人民面临着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的艰巨任务。这一斗争反映到哲学上,就体现了变与不变,进化与退化,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斗争与较量。从变易史观到进化史观,最后到唯物史观,体现了中国近代哲学历史观的演进与变革。
一、变易史观
由于鸦片战争的爆发,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的封建社会逐步解体,并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过渡。在这样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转型期,处于内忧外患的中国人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社会思潮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鸦片战争中,就有以林则徐为首的抵抗派与当时的投降派的激烈斗争。在鸦片战争中,产生了龚自珍、魏源等代表地主阶级改革派利益、主张变革的哲学家。前者写有著名的诗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里的“风雷”,就是社会变革。后者编有《海国图志》,主张放眼世界,了解世界,认真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龚自珍、魏源是晚清思想界开风气的人物,他们以《周易》中关于“变易”的朴素辩证法为依据,提出了变法更制的主张。他们主张变革的哲学基础,就是变易的历史观。
在龚自珍看来,社会历史是不断变化的,“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上大学士书》)就是说,从国家的法制,时代的趋势,到政文条例、社会风气,都在不断变化。既然如此,封建伦理纲常就决不是万古不变的。龚自珍敏锐地觉察到,当时的社会已不是“盛世”,而是“衰世”。因此他反对“率由旧章”,(《复林若州言时务书》)力主“通乎当世之务”。(《对策》)针对封建顽固派拒绝任何社会变革,指责要求变革的人“嚣嚣然争言改法度”(《拟言风俗书》)他尖锐指出,“一祖之法无不弊”,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乙丙之际篇议第七》)据此他在政治上提出了修改封建礼仪制度,“变通”以资格取官的科举制度等改革主张。
龚自珍认识到历史是变化的,事物也是发展的,这一变化发展过程可以概括为:“初、中、终”三段。他说:“哀乐,爱憎相承,人之反也;寒暑、昼夜相承,天之反也。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五癸之际胎观第五》)这一提法一方面包含着变化是对立面的展开的辨证法思想,这是可贵的。另一方面,又表明由于受到公羊三世说的影响,坚持“万物之数括于三”,(同上)而陷入历史循环论,同时,龚自珍主张的“变”,基本上是指渐变而非突变,即“风气之变必以渐也”(《与人笺》)这种观点决定了他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提出的变革主张,难以从根本上触动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
魏源是和龚自珍齐名的一位近代哲学先驱,以编写第一部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宗教等各方面情况的巨著《海国图志》,并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著名。他与龚自珍交往很深,时人并称“龚魏”。魏源十分鄙视封建顽固派的泥古不化,认为他们不过是一伙“鄙夫”,“以推诿为明哲,以因袭为老成,以奉行虚文故事为得体。”(《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疑公神道碑铭》)“以圜熟为才,模棱为德,”“以宴安鸠毒为培元气,以养痈贻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物,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他们所造成的危害,“在强藩,女娲、外戚、宦寺、权奸之上”(《默觚下·治篇十一》)。
针对“鄙夫”的因循守旧,魏源同龚自珍一样,强调变革,他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筹鹾篇》)以魏源看来,人类历史总是不断变化的,“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默觚下·治篇五》)“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同上)“故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同上)历史发展变化的总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可以看出,上述关于历史变易的观点,正是龚魏在政治上要求变革的哲学依据。在指出变易史观是龚魏变革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武器这一基本事实之后,还需要进一步指出,在龚魏的变易史观中已经内在地包含着某些社会进化的观点,即进化史观的因素,在一定意义上说,变易史观为进化史观创造了条件,准备了土壤。如前所述,龚自珍十分强调历史的“变易”,但同时又认为这种变易是“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从而把历史的变易看成是一种循环。如果再向前一步,把历史的变易看成是一种前进的运动,那便是后面将要谈到的康有为的历史进化论,即进化史观了。魏源的历史观中包含的历史进化观点比龚自珍要更多一些,针对朱熹等宣扬夏商周三代是所谓“王道”政治的“黄金时代”,三代以后的历史则每况愈下的历史退化观点,魏源针锋相对地指出,“后世之事胜于三代!”(《默觚下·治篇九》)这至少体现在三件大事上,一是汉文帝废肉刑,这表明三代残酷,后世比较仁慈。二是柳宗元写《封建论》,说明三代实行分封制是私,后世改行郡县制是公,即“其用人之制,则三代私而后世公也。”(同上),三是变世族为贡举,后世以贡举来选拔官吏,这比三代的世袭制要好。除此之外,与三代相比,“后世”在许多方面的变化也是愈来愈进步的,要想恢复到“三代以上”的老样子,“跪地以坐,见币以为货……乘车以战,”那就是“大愚”了。(《默觚下·治篇五》)魏源虽然认为历史是进化的,但他依据公羊三世说,把历史的进化概括为“太古”“中古”“来世”,历史进化到来世,就会“复返其初”,(《论老子》)又重新回到太古之世。这样,历史的进化就成了“太古”“中古”“来世”的循环往复,从而同龚自珍一样,陷入了历史循环论。因此,尽管龚自珍、魏源的变易史观中都包含有某些历史进化的观念,但都没有发展到历史进化论。
二、进化史观
如果说,龚魏的变易史观反映了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放眼世界,变法更制的愿望,那么,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的进化史观,则反映了甲午战争惨败,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为主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要求。由于受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从戊戌变法之后,整整一代求进步的中国人,都是向西方寻求真理,认为西学可以救中国。就哲学世界观而言,他们都是进化论者。信奉进化论,成为当时哲学思潮的主要特征,中国近代哲学进入了进化论阶级。从资产阶级维新方面看,康有为把公羊三世说改造为历史进化论,严复则翻译《天演论》,倡导“天演哲学”。进化论作为一种比较进步的西方学说,正是由严复翻译和介绍《天演论》而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天演论》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通过阐述生物竞争的生物进化道理,唤醒国人觉悟,激励民族自强保种。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以进化论为武器,反对复古主义、循环论的历史观,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进化论成为变法维新的哲学根据。从资产阶级革命派方面看,孙中山等在同改良主义的论战中,使进化论思想逐渐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羁绊而具备了“革命”、“突驾”、“飞跃”等新的含义,从而为推翻封建君主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成为指导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哲学进入进化论阶段的首要代表,他的变法理论是和进化史观密切相联的。他发挥了《周易》“变易之义”的哲学思想,把周易所阐述的“变通”的观点同维新派的变法主张结合起来。他说:“后人认为治法也,随时而立义,时移而法变移矣。”“易者,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中国今日不变日新不可,稍变而不尽变不可,尽变而不兴农工商矿之学不可。”(《日本书同志序》)他还说:“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自亡。”“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而不能“变其甲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二,”这种“枝枝节节”的“变”,只是在“变事”,而不是“变法”(《统筹全局摺》)康有为的“全变”,实际上就是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变封建主义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中国。这就使他在政治上同洋务派划清了界限。在他的眼里,洋务派的所谓“新政”,不过是“饰粪墙,雕朽木”而已。
康有为不仅主张“盖变者,天道也,”“无一不变,无刻不变”(《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而且把《周易》的“变易之义”同资产阶级进化论比附起来,认为“变”是自然规律,“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上清帝第六书》)这一见解已经内在地包含了进化论的思想内容,并且将《周易》中关于变易的观点同进化论思想揉合在一起,是同复古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完全对立的。在近代中国哲学中,率先迈向进化论阶段,由变易史观走向进化史观的是康有为,他倡导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哲学武器就是进化论,如梁启超所说,“先生之哲学,进化派之哲学也。”(《南海康先生传》)而康有为的进化论,是以公羊学派的“三世”说为具体表现形式的。因此梁启超称其是“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所谓:“公羊三世说”是汉代何休《公羊传注》中提出的关于历史演变的一种见解,即由:“据乱世”到“升平世”再进入“太平世”。康有为认为,孔子“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就是所谓《春秋》公羊三世说。他说:“《春秋始于文王,终于尧、舜。盖拨乱之治为文王,太平之治为尧、舜、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得微言之第一义也”。(《孔子改制考》卷十二)又说:“‘三世’为孔子之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此为《春秋》第一大义”。(《春秋董化学》卷二)
由此可见,康有为的进化论突出地表现在历史观上,他把公羊三世说与《礼记·礼运》中讲的小康,大同联系起来,提出了他的进化史观和大同理想。康有为认为社会经历据乱世、升平世到太平世,历史是进化的,“日进而日盛”。(《南海康先生传》)他又把三世说同当时世界上并存的三种政治制度,即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制联系起来,把此也看做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过程。他说:“如今大地中三法并存,大约据乱世尚君主,升平世尚君民共主,太平世尚民主矣。”(《孟子微·同民第十》),他还认为,根据历史的进化规律,“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大同书》)社会进入“人人皆得其乐,遂其欲,给其求”的“大同世界”。
如同魏源与龚自珍常并称“龚魏”一样,梁启超与康有为常并称“康梁”,梁启超不仅提出:“先生之哲学,进化派之哲学也。”而且将先生(即康有为)的进化哲学进一步发扬光大,把“三世之义”说成是:“往古来今天地万物递交递进之理。”(《读〈春秋〉界说》)梁启超认为,就自然界来说,“以草木为据乱,则禽兽其升平,人类其太平也”,就人类由渔猎、畜牧演化为农业社会、工商社会来说,“打牲为据乱,则游牧其生平,种植其太平也;游牧为据乱,则种值其升平,工商其太平也。而打牲之前尚有不如打牲之世界,则打牲已为太平;工商以前更有进于工商之世界,则工商亦为据乱。”(同上),历史就表现为这样一种“递交递进”的发展过程,从而把康有为的“三世说”运用于十分广泛的形式。
进化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共同的思想武器,但是,与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公羊三世说”的神秘进化思想不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孙中山的哲学进化采取了自然科学的简朴形式,这是孙中山进化史观的显著特点。他说:“自达尔文之书之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说,皆依归于进化矣。(《孙文学说》)根据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情况,孙中山把宇宙进化分成三个时期,“其一为物质进化之时期;其二,为物种进化之时期;其三则为人类进化之时期;”(同上)关于物质进化,他说:“元始之时,太极(此用以译西名以大也)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此世界进化之第一时期也。”(同上)关于物种进化,他说:“地球成后以至于今,按科学家据地层之变动而推算,已有二千万年矣。由生元之始生而至于成人,则为第二期之进化。物种由微而显,由简而繁,本物竟天择之原则,经几许优胜劣败,生存淘汰,新陈代谢,千百万年,而人类乃成”(同上)关于人类进化,他说:“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同上)。
由进化论引出“革命”和“突驾”的结论,这是孙中山进化史观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在孙中山看来,进化论所提供的自然界普遍发展变化的观念,正说明了事物的除旧布新、新陈代谢是不可抵抗的自然规律。因此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政治的革新,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即“此天然之进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总理全集》第1卷第1012页)在这一文明进化的过程中,“以人事速其进行,是谓之革命。”(同上),这样,孙中山就从进化论中引出了革命的结论。以进化论为根据,通过宣传进化论来倡导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个共同特点。资产阶级维新派梁启超曾提出“竞争者,进化之母”(《论近世国民之争之势及中国之前途》)资产阶级革命派章太炎,不仅接过这个口号,提出“强力以与天地竟”,(《訄书·原变》)而且明确提出“公理之未明,但以革命明之;旧倍之俱在,但以革命去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梁启超首先提出“革也者,天演界之不可逃避之公例也”。(《拜革》)即把“革”的观念引入了进化论。但是也随即放弃了这个口号,而革命者则进一步宣传和阐释了这个口号。邹容就大声疾呼:“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军》)在由进化引出革命的同时,孙中山还由进化引出了“突驾”,提出了积极进取的“突驾观”,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孙中山主张取法世界上“行之已收大效者……,而为后来居上也。”(《总理全集》第1卷第1022页)他认为,中国必须通过“突驾”赶上和超过日本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说:“中国不仅足以突驾日本也。……近世十年思想之变迁,有异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5页。)这样,就使决定论逐渐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具有“革命”和“突驾”等新的含义,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锐利思想武器。
当然,孙中山的进化史观也具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受到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的影响。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认为互助是生物和人类社会进化的主要动力,从而把互助而不是竞争作为人类进化的基础,因此,相对于达尔文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即“互竞”为基础的进化论,克鲁泡特金以“互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又称为新进化论。由于信奉达尔文的进化论,孙中山认为物种进化论的法则是互竞。又由于受到克鲁泡特金的影响,孙中山认为社会进化的法则不是竞争,而是互助。即“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42页)互助是人类求生本能的表现,人类为了共同求得生存与发展,只能通过互助来调和彼此的利益。他说:“社会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冲突。”“阶级战争(即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79页)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兽性“尚未能悉行化除”的表现。(《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42页)因此,孙中山始终拒绝承认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不仅与他进化论中的革命观相矛盾,而且也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具有本质区别的。
三、唯物史观
陈独秀、李大钊是初期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主要代表。在新文化运动前期,他们继承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精神,也是以进化论为旗帜,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制度,把科学与民主看做是人类历史进化的必然结果。1915年9月,在《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创刊号上,陈独秀指出:“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自宇宙根本大法观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途中,万无保守现状之理;”从而阐述了鲜明的进化论的宇宙观。他还说:“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优胜劣败,理无可逃。”(《抵抗力》)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遵循着新陈代谢的进化法则。他指出:“自英之达尔文持进化说,谓人类非有神造,其后递相推演,生存竞争之优胜劣败之格言,昭垂于人类,吐弃无遗,而欧罗巴之人力物力,于焉大进。”(《法兰西与近世文明》)正是有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才有了西方社会文明的发展,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他进一步认为,欧洲资本主义所以比较发达,是因文艺复兴以来在政治、文化、伦理等各方面的资产阶级“革命所赐”,由此出发,他得出了社会“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文学革命论》)的结论。在他看来,“今世万事,皆同在进化途中,共和亦然……而世界政制,趋向此途,日渐进化。可断言也。”(《驳康有为(共和评议)》)很显然,进化论是其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哲学基础。
大约在1920年,陈独秀由进化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由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如何处理进化与革命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蔡和森为此专门写信给陈独秀,探讨这一问题。陈独秀在回信中说,“尊论所谓‘综合革命说和进化说’,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骨髓,也正是有些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怀疑的一个最大的要害。怀疑的地方就是:马克思一面主张人为的革命论,一面又主张唯物史观,类乎一种自然进化说,这两说不免自然矛盾,鄙意以为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革命是我们创造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二者似乎有点不同,唯物史观固然含有自然进化的意义,但是他的要义并不只此,我以为唯物史观底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在《新青年》第9卷第2号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一文中,陈独秀概括了唯物史观的“两大要旨”,一是“社会生产关系之总和为构成社会经济的基础,法律、政治都建筑在这个基础上面。一切制度、文化、时代精神的构造都是跟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的,经济构造是跟着生活资料生产的变化而变化的,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会生活决定人的意识。”二是“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制度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有变动,社会制度也跟着变动,因为经济的基础(即生产力)有了变动,在这基础上面的建筑物自然也或徐或速的革命起来。”从而比较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实现了由进化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
与陈独秀一样,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李大钊也持进化论的宇宙观,他认为:“宇宙乃无始无终自然的存在,由宇宙自然之真实本体所生之一切现象,乃循此自然法则而自然的,因果的、机构的以渐次发生,渐次进化。”(《自然的偏理观与孔子》)“宇宙大化之流行,盛衰起伏,循环不已,生者不能无死,毁者必有所成,健壮之前有衰颓,老大之后者青春。新生命之诞生,固常在累累坟墓之中也。”(《晨钟之使命》)与这种进化论的宇宙观相联系,李大钊主张新陈代谢的历史观,即进化史观。他说:“由历史考之,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国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相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能逃者也。”(《李大钊文集》上卷第199页),就是说,新陈代谢是天演公例,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不能逃避和违抗的历史规律。这种新陈代谢的进化史观体现在人生问题上,就表现为青春哲学的人生观,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青春中体之创造”。他在1916年写的《青春》一文中,热切呼唤“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他认为,青年的责任,不在白发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他所以创办《晨钟报》,就是“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使命”。第二,“惜今”。历史是新陈代谢的发展过程,“‘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真连续,以成其永远,所以要抓住现在。”“吾人在世,不可就‘今’,而徒回想‘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今》)第三,“乐天努进”。李大钊希望青年都能有一种:“乐天努进”积极向上的精神,同种种昏庸腐朽的势力作斗争。只有乐天努进,长葆青春之我,才可能创造青春之中华与世界。
李大钊前期的进化史观中包含着许多自发的辩证因素,这为他从进化史观向唯物史观转变创造了条件。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在传播唯物史观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在1920年写的《史学思想史讲义》中,指出以往的历史观尽管形形色色,但大体都是英雄史观,表现为:“伟人的历史观”、“圣贤的历史观”、“王者的历史观”、“道德的历史观”、“教化的历史观”、“神权的历史观”、“天命的历史观”等。他进一步分析道,“历史观本身亦有其历史,其历史亦有一定的倾向。大体言之,由神权的历史观进而为人生的历史观,由精神的历史观进而为物质的历史观,由个人的历史观进而为社会的历史观,由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进而为进步的历史观。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历史观,多带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历史观,则多带进步的历史观的倾向。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则可称为新史观。”他在介绍与阐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时说,“喻之建筑,社会亦有基址(Basis)与上层(Vberbau)。基址是经济的构造,即经济关系,马氏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存在。上层是法制、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马氏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氏历史观的大体。”(《李大钊文集》下卷第346页)他进一步指出,“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使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同上,第59页》)这就比较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
四、几点结论
第一,中国近代哲学思想的启蒙是伴随着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过程开始的。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变与不变,变革还是守旧,既成为尖锐的政治斗争,又成为突出的哲学课题,与顽固派、洋务派的“道不可变”“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形而上学相对立,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龚自珍、魏源以变易观为思想武器,论证了历史的进步与社会的变革。
第二,如果说地主阶级改革派与顽固派,洋务派的斗争在哲学上主要体现为变与不变的论争,那么,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及其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顽固派的斗争在哲学中则主要体现为进化与反进化。是坚持进化论还是反对社会进化,成为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突出、最主要的哲学课题。通过宣传进化论,鼓吹维新,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共同特征。通过宣传进化论,提倡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共同特点。孙中山的进化论由于渗入了“革命”、“突驾”的新含义,这就逐步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羁绊而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近代西方资本阶级进化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并获得迅速传播与发展的,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其它任何理论,如鲁迅所说,一时间形成了“进化之语,口成常言”的局面。(《人之历史》)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初期文化运动,进化论都同时代思潮的中心问题密切联系。从地主阶级改革派龚自珍、魏源,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从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到新文化运动前期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都和进化论有着种种密不可分的联系。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之前,进化论居于时代思潮的主导地位。它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第三,新文化运动前期,陈独秀、李大钊还是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一度也是热情的进化论鼓吹者。陈独秀就曾说过,“近世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由此可见进化论之重要。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陈独秀、李大钊逐渐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进而实现了由进化史观向唯物史观的飞跃。
第四,从龚自珍、魏源的变易史观,到康有为、孙中山的进化史观,再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唯物史观,是一个梯次递进的过程。在龚自珍、魏源的变易史观中已经包含着一些进化的思想,比如龚自珍用公羊三世说来描述社会历史的发展,而魏源则具有更多一些的进化论观点,但是都没有达到历史进化论阶段,而陷入了历史循环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和改造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周易》朴素辩证法密切相联的。康有为将《周易》中“变易”的观点同西方“进化”的观点结合在一起,由变易观发展到进化史观。但是,康有为以公羊三世说为表现形式的进化史观也具有循环论的局限。孙中山的进化史观则具有“革命”、“突驾”的新的特质,但是孙中山的进化观又受到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响,认定社会进化的基础是互助而不是竞争。新文化运动前期,陈独秀、李大钊在积极宣传进化论,以进化论为依据,倡导民主与科学。到1920年前后,他们逐步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由进化史观上升到唯物史观。总之,在这一递进过程中,进化论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鸦片战争之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变易史观中就已经包含着进化论的思想;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进化论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提倡变法和革命的理论依据;在初期新文化运动中,进化论为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准备了必要的思想条件。而马克思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则实现了近代中国哲学历史观的巨大变革。
标签:龚自珍论文; 进化论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史观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达尔文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康有为论文; 天演论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孙中山选集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