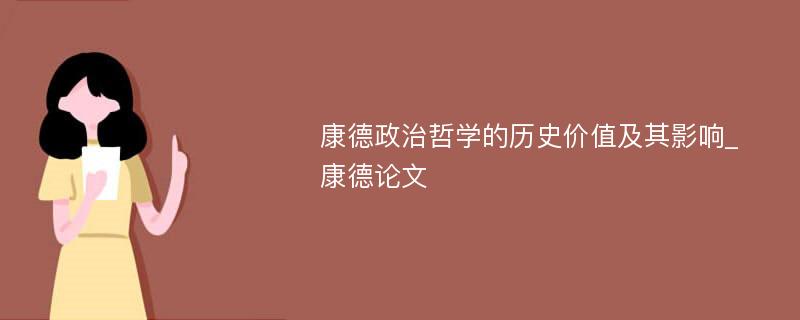
康德政治哲学的历史价值和时代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德论文,哲学论文,政治论文,价值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从西方政治思想史主要是契约论传统嬗递演变的角度,考察了康德政治哲学的若干重要观念。作者指出:康德将原始契约作为观照人类社会状况的一项纯理性观念而非历史事实,拨开了笼罩在契约论传统中的一层迷雾;康德在其政体分类原则基础上深刻批判卢梭追求的抽象直接的民主制,揭露公意与自身及自由的矛盾,主张代议、立宪、共和政体的理论内蕴,在当代具有重大影响。
笼罩在批判哲学炫目光环之下的康德政治哲学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社会政治哲学并不是批判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试图以此来抹煞其独特的价值。事实上,作为批判哲学内在延伸的康德政治哲学仍然以其先验论的思辨锋芒触及到了与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兴衰相联系的某些根本性问题,诸如自然状态与权利公说,原始契约与公意和自由的矛盾,人民主权论和非暴力反抗以及永久和平的理想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政治哲学使康德在实践理性地基上恢复和重建启蒙运动的精神这一工作更显丰富和完整,并在后世乃至当代引起广泛的反响与共鸣。凡此种种,都有着值得进一步发掘的深刻内蕴。
一、自然状态与权利的公设
康德的政治哲学在本质上属于和洛克、卢梭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契约论传统,这首先表现在他接受了在这一传统中广泛流行的关于自然状态的理论假设。当然,无论是在对自然状态的描述、还是对其作用的估价,在不同的政治哲学家那里,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对自然状态的不同描述影响着他们得出不同的社会政治结论。反过来,他们不同的社会理想和价值目标也影响到他们对自然状态的描述及其作用的估价。正如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R·诺齐克所认为的,政治哲学从自然状态理论开始有一种解释性的目的。
作为康德社会政治哲学直接先驱的卢梭状态学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含混不清的。他认为,为了正确地判定我们的现状,无论如何应当设定自然状态,这一点给予康德极大的启发。康德的见识正在于他独具慧眼地发现:“卢梭从根本上说并不想使人重新退回到自然状态中去,而只是站在他自己现在所处的阶段上回顾过去。”①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赞同卢梭,即关于自然状态的这个尚未用法律加以调节的社会状态的理性观念,必须作为讨论的出发点。重要的是如E·卡西尔所指出的,康德对卢梭的自然状态学说实行了方法论上的转变,他在其中看到的不是一种建构的原理而是一种范导的原理。由此,康德清楚地区分了卢梭理论的历史的方面和理性的方面,并且以实践理性学说对其进行了改造和发扬。
按照道德形而上学的总体构想,实践理性应当统摄法权论和德性论两个部分。“就自由法则仅仅涉及外在的行为和这些行为的合法性而论,它们被称为法律的法则。可是,如果它们作为法则,还要求它们本身成为决定我们行为的原则,那么,它们又称为伦理的法则。”②前一种自由法则即是权利科学的考察对象,而康德恰恰是以权利科学作为政治哲学的基础理论的。其权利和公共权利的公议是其理论的基石。
康德认为,“权利乃是以每个人自己的自由与每个别人的自由之协调一致为条件而限制每个人的自由,而公共权利则是使这样一种彻底的协调一致成为可能的那种法则的总和。”③按照《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公共权利又被更具体地规定为,在不可避免的要和他人共处的关系中,你将从自然状态进入一种法律的联合体,这种联合体是按照分配正义的条件组成的。康德以权利和公共权利的公议来说明从自然状态向文明状态的过渡,这使他的自然状态学说和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学说既相区别,又相联系。
从公共权利的公议来观察,康德把自然状态称为一种“无法律状态”,即一种没有分配正义的社会状态。在自然状态中,可能还存在法律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但无论如何还没有任何先验的法则作为一种必须遵守的责任。因此,自然的或无法律的社会状态,可以看作是个人权利的状态,而文明的社会状态可以特别地看作是公共权利的状态。
与自然状态相对立的文明状态是建立在分配正义之上的,正如康德所指出的:“个人权利的内容在这两种状态中其实是相同的,因此,文明状态的法律,仅仅取决于依据公共宪法所规定的人们共存的法律形式。”④
康德为了说明从自然状态向文明状态的过渡,不同意将自然状态描绘成绝对不公正的状态,因为如果在人们进入文明状态之前没有承认任何公正的获得,那么这种社会状态本身就不可能产生。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的自然状态学说乃是远离霍布斯而近于洛克的,而如果说在康德那里,自然状态失掉了卢梭赋予它的某种理想范型的意义,那是因为康德较之卢梭似乎更加信奉启蒙运动所乐观地坚持的人类历史进步的观念。值得引起重视的倒是康德在将文明联合体和社会相区别时表现出的批判精神和历史视野。在康德看来,在文明的社会组织中,统治者和臣民并不是在一个社会中彼此平等地联合起来,而是一方听命于另一方,而这在将平等视作权利的三大先天原则(自由、平等、独立)之一的康德看来,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它将这种文明联合体视作正在形成的一个社会。
与洛克本质上的利己主义立场不同,康德将从自然状态向文明状态的过渡视作一种责任和义务。康德坚持认为,“公民体制也就是处于法律强制之下的自由的人们(在他们与别人结合的整体之中而无损于自己的自由)的一种关系,因为理性本身要求这样,并且还确实是纯粹的、先天立法的、决不考虑任何经验目的的理性”⑤。这正是容易引起争议的地方。事实上,在对自然状态的描述上,康德似乎已经陷于一种左右掣肘的境地。与文明状态相对比,他将自然状态描述成远离公共正义的状态,但为了说明从前者向后者的过渡,他又反对将自然状态描绘成绝对不公正的状态。
对康德来说,自然状态的假设作为政治哲学的伟大先辈们的遗产就如同与之紧密相联的社会契约论传统一样,并不是如同非历史的后现代主义作家所建议的那样可以随意消解的。
二、原始契约及公意与自由的矛盾
康德对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观同样进行了批判改造,在这过程中,他以自己的政体分类理论为基础,通过对抽象民主制和多数统治原则的批判,深刻地揭发了公意与自身及自由的矛盾。
霍布斯依据联想主义心理学,从个人自我满足的角度来阐述原始契约。因为统治和服从是唯一能以政治方式把本是分开的原子或个人转变为一个整体并使之存在下去的力量,因此霍布斯消除了在社会契约和服从契约之间的二元论,并在实质上将政府等同于暴力。
洛克的社会契约观则是从职能的角度来阐述的,他把自然法解释为每个人生来就有权对天赋的不可取消的权利提出要求,但他没有明确说明原始契约是产生了社会本身还是产生了政府,他默认了个人之间和社会同政府间的双重契约论,这是由于他主张社会和政府都是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机关,洛克又将公民社会分为个人、社会、政府和立法机关四个层次,但他没有试图彻底弄清各种实际权力是怎样从各个人彼此平等而又不可剥夺的权利衍生而来。这就导致哲学上的不彻底性和萨拜因所谓洛克理论的复杂性。
卢梭反对17、18世纪理论家们赖以改造社会的所谓社会本能。他虽然一度同情霍布斯的政治现实主义,但在为法律和政治制度寻找基础的时候,他的公意说无疑同霍布斯大相径庭。卢梭认为镇压一群人和治理一个社会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分别,因为只有当个人自觉地使自己服从于权力,而不是权力强使个人服从时,权力才具有道德价值。客观的服从和对法律的自由承认是卢梭公意说的核心内蕴。卢梭试图改变权力本性的努力遭致后世英美自由主义的广泛弊病,但却引起康德的强烈共鸣。正因如此,卡西尔才宣称在整个18世纪,只有康德一人读懂了卢梭。
在历史法学派把社会契约看成一种历史事件并试图反驳和否定卢梭时,在休谟对独断论,尤其是契约说逻辑发动猛烈的批判时,康德通盘考虑了人的理性能力,在实践理性的坚实地基上,透过卢梭表达上的含混性而只在一种意义上把握卢梭思想的核心。《道德形而上学》上半部严格区分了正义和事实的界限,这就廓清了契约论传统中的迷雾,并从法哲学角度提高了契约观的论证水平。
康德把原始契约定义为人民把自己组织成为一个国家的法规,亦即是由普遍、联合的人民意志之中产生出来的根本法。但原始契约的历史发生问题在康德看来是无关宏旨的,原始契约的意义在于它能提供一项观念,通过此观念可以使组织这个国家的程序合法化。根据原始契约,人民中所有人和每个人都放弃他们的外在自由,为的是获得作为一个共和国成员的自由。但康德坚持认为在这样形成的国家中,人民并没有牺牲掉与生俱来的一部分自由即外在的自由,他只是抛弃了那种粗野的无法律状态的自由,以获得并未减少的全部正当的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原始契约在康德看来虽然只是纯理性的一项观念,但却有着无容置疑的实践的实在性。康德并且希望它能束缚每一个立法者,以使他的立法就犹如是从全体人民的联合意志中产生出来的,康德还把这当作一种公开法律之合权利性的试金石。
如果说康德的原始契约观远离于霍布斯,而尤其在没有对原始契约所产生的社会和政府之间加以区别这一点接近于洛克;那么,不但在观念上而且在文风上更与卢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对卢梭难以自解的自由主义的攻击和责难,康德却由于其实践理性的坚实地基而能成功地加以化解。这是因为卢梭由于对财产权在社会中的地位并无确定的想法以及从公意的高度理想性出发而否认界定权力的范围的意义,从而忽视了经典自由主义这两大教义,而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宏伟构想中却巧妙地吸收了这两者,从而引起了后世英美自由主义者的共鸣和反响。
同样值得重视的不只是康德在将自由、平等和独立作为权利公议的三大原则时对家长制(或文权制)这种最大的专制主义的猛烈抨击,而且还有康德在探讨政体分类原则时对抽象民主制和多数统治原则的深刻批判和修正。康德在澄清他所理想的共和体制和他所反对的民主体制的差别时认为,一个国家的形式可以或是根据掌握最高权力的不同的人,或是根据国家的领袖对人民的政权方式来加以区分。第一种叫做统治的形式。统治的形式根据或是一个人,或是一些人联合起来,或则是构成为公民社会的所有的人一起握有统治权力,而区分为专制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与之对应的三种权力则是君主权力、贵族权力和人民权力(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又主张君主制和一人主政即专制政体并不相同,因为前者只是代表最高权力的人即主权者,而后者则是拥有一切权力的人即统治者)。第二种即政权的形式则涉及到国家如何根据宪法而运用其全权的方式,在这方面,只能区分为共和的或专制的两种方式。所谓共和主义乃是行政权力(政府)与立法权力相分离的国家原则,专制主义则是国家独断地实行它为自己所制订的法律的那种国家原则,因而也即是将公众的意志作为统治者自己私人的意志来加以处理的那种国家原则。
基于以上的政体分类原则,康德认定在民主政体这一名词的严格意义上,作为一种国家形式,就必然是一种专制主义,因为“它奠定了一种行政权力,其中所有的人可以对于一个人并且甚而是反对一个人(所以这个人是并不同意的)而做出决定,因而也就是对已不成其为所有的人的所有的人而做出决定,这就是公意与其自身以及与自由的矛盾。”⑥
从这里可以洞见到康德在高度赞扬和认同卢梭的同时,也对其作出了深刻的批评。卢梭为了保持公意的理想性,拒斥代议的民主制,主张直接民主,他相信城市国家一类小型社会是公意的最好典范。对城邦的理想化,是卢梭的政治哲学从未紧扣同时代的政治加以论述的一个原因。但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广泛兴起的态势中,公意的外化问题却被身居哥尼斯堡,却心系世界潮流的康德抓住了。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高扬道德理性的康德,在政治哲学领域却有着颇强的现实感,他信奉资产阶级政治哲学中得到广泛信奉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最高原则,他洞察到行政权力简单化是滋长专制主义的温床,他批驳了那种认为如果君主是个好人,那么人们应该满意于君主政体是最优良的政治社会组织的无聊遁词。相对于卢梭主张直接民主制,康德认为唯有在代议制体系中共和制的政权方式才有可能,而凡不是代议制的政权形式本来就是无形式,因为在同一个人的身上,立法者不可能同时又是自己意志的执行者,而在民主制中,因为所有的人都要作主人,因而相对于其他两种类型就在根本上排斥了采用符合于代议制体系的精神的政权方式的可能性。由此,康德甚至认为:“国家权力的人员越少,他们的代表性也就相反地越大,国家体制也就越发符合共和主义的可能性并且可望通过逐步的改革而终于提高到那种地步。”⑦而在贵族政体就比在君主政体之下更难了,而在民主政体之下,则除非是通过暴力革命就根本不可能达到共和主义这种唯一完善的合法体制。
康德通过揭露公意与自身以及与自由的矛盾,深刻地批判了抽象民主制,这一批判打中了传统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要害;在这一批判中蕴含的对多数人统治原则的质疑和修正则使人联想起托克维可对自由、平等和民主之大观念相互纠结的精彩阐述以及对多数的暴政的深刻抒发,凡此均是康德政治哲学中的辉煌之处。
应当注意到的是,虽然康德猛烈地抨击了抽象的民主制,并在他的政体分类原则中为君主制涂上了一层迷人的光环,但康德的政治哲学在根本上仍然是一种人民主权论,不过,常常和人民主权论联系在一起的人民暴力反抗的权利,康德却没有赋予人民,而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加以考察的。
三、人民主权论和非暴力反抗
主权这个概念自从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布丹提出以来,一直是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部西方近代政治理论的历史,就是一部主权论的历史,只不过主权所属迭有更替罢了。霍布斯承布丹之余绪,进一步完善了国家主权论,在他那里,主权被完全赋予了“利维坦”。
回顾政治思想史,人民主权论的最明确阐述是由约翰·阿尔色修斯(Johannes Althusius)提出的。其理论的要点是,主权必须寓于作为法人团体的人民,主权是那个特定社团的特征,因此主权是从来不能转让和交由一个统治阶级或家族拥有的,权力依据国家的法律授予一国的行政长官,如若掌权者由于任何理由失去了这种权力,那么它就得归还给人民。
卢梭同霍布斯一样不信奉分权说,但主权所属者却进行了倒转,卢梭的政治哲学是彻底的人民主权论。一切政府权力,不管体现在一个人身上,或者为大多数人所行使,都只是被委托的权力,不能废除和侵犯人民的主权。按照卡西尔的理解,卢梭在自然法传统中用来精确区分个人领域和国家领域,保证个人对国家独立性的不可转让的权利概念,属于国家领域,只有公意和整体才具有决不可放弃和委托给他人的基本权利。
康德继承了人民主权论的传统,在他看来,每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只能是由人民代表的系统构成,因为联合意志是一切公共契约的最后基础,如果此项契约规定人民要再次交还他们的权力,那么人民的地位就不再是立法者了。康德明确指出,“最高权力本来就存在于人民之中,因此每个公民的一切权利,特别是作为官吏的一切权利,都必须从这个最高权力中派生出来。当人民的主权实现之时,也就是共和国成立之日”⑧。本着这样的理想和信念,康德对统治权依附于某个特殊的人这种情形是不满的,一切公共权利的最后目标,在康德看来就是每个公民能够绝对地拥有分配给他的东西,因此,“只要国家的形式依据宪法的文字规定,必须由授予最高权力的法人来体现,那末,人民只能享有附带条件的固有权利,而不是一个绝对的文明社会的法治国家。”⑨
由此观之,康德的人民主权论不可谓不彻底,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常常与人民主权论联系在一起的人民反抗和革命权利,在康德却是断然可以否认的。在任何情况下,人民如果抗拒国家最高立法权力,都是不合法的。对人民来说,不存在暴动的权利,更无叛乱权。总之,使法律生效的国家权力是不可抗拒的。康德甚至认为,一个国家中的最高权力,对臣民只有权利,并无义务。“对最高立法权力的一切对抗,使臣民们的不满变成暴力的一切煽动、爆发成为叛乱的一切举事,都是共同体中最应加以惩罚的极大罪行,因为它摧毁了共同体的根本。”⑩康德更猛烈地抨击了公开处死君主的行为,如英国革命处死查理二世,法国革命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康德用堕落、无耻来形容,并称之为国家的自杀。
应当说,康德关于非暴力反抗的观点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限于篇幅,这里侧重于从康德理论自身的特点来加以阐述。
首先,康德将原始契约视为一项理性的观念,是对组织国家的程序之合法化的说明,而否认原始契约之发生乃是一个历史事实。在他看来,最高权力的来源,对人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而且这类问题对国家充满了微妙的危险。因为为了取得判断国家最高权力的资格,这时候的人民必须假定已经在一个共同的立法意志之下联合起来了,因此也就不再有权利来经常判断应该怎样进行治理。康德阐明,在公意存在以前,人民对自己的主宰者根本就不具备任何强制的权利,但是如果已经有了公意,人民同样对主宰者不能使用强制,因为那样一来人民自己又会变成无上的主宰者了,因此在原始契约中不可能包含授权人民去推翻现存体制的条款,因为那是自相矛盾的。
其次,康德虽然认为更改有缺陷的国家宪法是很有必要的,但他认为这只能通过改良的方式来进行,而不能通过革命的方式去完成,而且在进行这种更改时,只有执行权力而不是立法权力受到影响。卢梭曾经对那种人民的立法权力只限于一次行动,因此委托人反而会因行使委托而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而感到不满。这一困扰着卢梭的问题也同样困扰着康德,这里本质上涉及的乃是自由与民主这两大观念之间的永恒冲突,而康德关于非暴力反抗的观点就正如现代政治学中广泛发展的公民不服从理论一样,一方面这只是在一个至少已接近正义的社会制度中出现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为求得这一冲突之缓解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妥协方案。
第三,康德的着眼点是以进化代替革命。他深刻地洞察到,革命可以推翻个人的专制和权势的压迫,但却难以实行思想方式的真正变革。因此康德将希望寄托在对公众的启蒙上面。他呼吁将服从和自由结合起来,因为只有服从而无自由会窒息社会的活力,而言论自由则是人民权利的唯一守护神。在他的名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他把当时的时代界定为启蒙运动的时代,而非启蒙了的时代。他要求公开运用即在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的自由,要求学者以世界公民的身份发言。他希望思想自由的风气会逐步反作用于人民的心灵面貌,并最终应作用于权力本身,从而使人类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实现所谓人类的千年福祉,达到“目的王国”这一康德哲学的最终祈向和最后归宿。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以权利的科学为中介,在这里得到了最高的统一。
在《永久和平论》的一个附录中,康德着重讨论了道德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康德将道德本身视作“我们应该据以行动的无条件的命令法则的总体,其本身在客观上已经是一种实践”(11)。而政治则是权利学说的应用,换言之,政治哲学应以权利科学为基础,应当把权利概念提高为政治的限定条件,因为在大自然的机械作用之外,还有自由以及以自由为基础的道德法则的存在,否则政治就完全是实践的智慧,而权利概念就是一种空洞的想法了。
类似于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区分开神学的道德学和道德的神学,在这里康德又提出了政治的道德家和道德的政治家之分。所谓政治的道德家是那种为了政治的需要为自己铸造一种道德的人,而道德的政治家则是那种认识到绝对有必要把权利概念和政治结合起来的人,使国家体制或国与国的关系符合于理性的观念所呈现于我们眼前作为典范的那种自然权利,哪怕这样会付出牺牲自我利益的代价。
这样,作为权利学说的应用的政治哲学也可说是广义的道德哲学即实践哲学的一部分,这也符合在《判断力批判》中所提供的更为高一级的哲学上的划分,因为权利的概念,作为把责任加于其他人的一种根据,也是从道德命令发展而来的。
归总起来,康德通过在实践理性地基上重建道德形而上学,复活了古希腊从哲学伦理学入手考察政治的传统。如果说隐含在契约论中的自然法思想给近代的社会契约论涂上了一层道德哲学的色彩,那么,通过为社会契约提供道德方面的前提,阐发社会契约中的道德含义和价值理想,康德就同时复兴了自然法学和社会契约论的伟大传统。贯穿康德哲学始终的理性精神,是对启蒙运动的高扬和重建;对人的强烈的道德关怀、则表明康德不啻为卢梭的嫡传。要言之,康德是启蒙运动和卢梭的共同产儿。
康德的政治哲学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当代资产阶级政治哲学进行自我修正时也极为重视这份理智遗产。康德的自然状态学说和社会契约观被美国当代社会政治哲学的巨擘约翰·罗尔斯加以改造,提高了更为抽象的论证水平,使之恢复了活力;康德对抽象民主制及公意与自由矛盾的深刻抒发,也进入了政治哲学的伟大文献;非暴力反抗思想更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者当中引起广泛的共鸣。就连批判罗尔斯的法兰克福学派巨子哈贝马斯也将公民不服从理论作为民主政治的必要承诺和基本准则接受下来,这无疑是因为在罗尔斯对功利主义的论争和哈贝马斯与后现代主义的论战背后都包含了同样的动机,即捍卫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和价值准则,而康德恰恰是在这个启蒙运动的遗产日益遭到侵蚀的时代让人回想起重建和发扬启蒙精神的最好代表。
注释:
①康德:《实用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页。
②④⑧⑨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4、134、177、177页。
③⑤⑥⑦⑩(11)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81-182、182、108、109、193、130页。
标签:康德论文; 卢梭论文; 政治论文; 政治哲学论文; 自然状态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法的形而上学原理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法律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