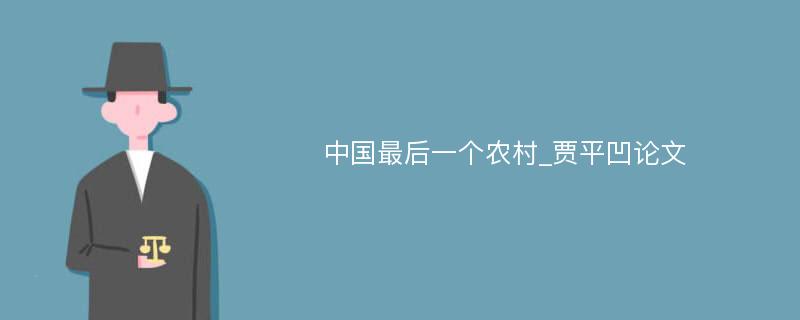
中国最后的农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和近年贾平凹所有长篇小说一样,《极花》(《人民文学》2016年第1期)也有一个不短的“后记”——交代小说的由来、背景和写法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贾平凹长篇小说的“后记”其实已经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文体。他往往会将可能伤害到小说文体的,过于直白的说明、议论和抒情移置到“后记”。这样,“后记”和小说之间有了一种彼此发微的互文关系。借助“后记”贾平凹总是成为自己小说第一个到场的批评者,他的“后记”也因此成为我们对他小说进一步阐释的原点。《极花》的“后记”中,贾平凹说:“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荒花?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①中国人对血缘家族十分看重,“一个传统的中国人看见自己的祖先、自己、自己的子孙在流动,就有生命之流永恒不息之感”②。由于客观上存在的区域发展差异,那些边远闭塞,没有赶上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改革大潮,没有分享改革红利的中国农村经过痛苦的挣扎终于“最后”般遭遇了生命之流的枯竭和断流。可以想见,一座座后继无人的中国村庄即将诞生,而后继无人,谈何中国农村的重建和再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土门》之后,贾平凹固执地记忆并书写城市化进程中颓败和凋敝的“中国最后的农村”。考察中外文学史,“最后”可能滋生挽歌文学,比如哈代、沈从文。贾平凹的《秦腔》就是这“最后”的记忆和挽歌的典范之作,但同样写农村颓败和凋敝,《极花》却不是《秦腔》那样的记忆和挽歌,而是克制和收敛乡愁引发的悲情,直面和逼视中国农村现实图景,诘问其何以至此的文化、人性等根源。贾平凹的《极花》是“激愤”“控诉”,也是“悲哀”③的。是的,由一个乡村之子宣判中国农村的“最后”和死亡,其疼痛感可想而知。贾平凹却没有躲闪和退却,而是自觉地选择做中国最后农村的见证者和记录员。如果我们进而意识到中国农村之“最后”是一个缓慢延宕的渐衰渐亡的过程,那么,贾平凹的写作在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中就有了一种与时偕行的“史记”意义。 小说的虚构和想象不意味着小说不追问我们世界的真。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学少有的将自己的写作持续地建立在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精准田野调查之上的作家。他擅长由实入虚,以小地方想象中国的小说修辞术。田野调查的“实”是他写作的出发点。贾平凹认为:“生活有它自我流动规律,顺利或困难都要过下去,这就是生活的本身,所以它混沌又鲜活。如此越写越实,越生活化,越是虚,越具有意象。”④贾平凹用自己早年的乡村记忆和不断行走的田野调查获得的天文、地理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秩序等“生活的本身”,去建构一个个中国农村的地方,并且别有深意藏焉。因此,就像他的《秦腔》,“写得实,实到使读者在阅读时不觉得那是小说而真实经历了那个叫清风街的人人事事,同时以实写虚,大而化之,产生多义,有所寄托”⑤。而《极花》之虚与实,多义与寄托,也不只是物象的象征意义——如极花之冬虫夏花与生命从冬日弱虫的凝定到夏花灿烂的转生,如“胡蝶”与庄子著名寓言有着隐秘关系的梦与真、灵与肉的迷离恍惚,而是从高巴县圪梁村这座小说家言的中国村庄天地人鬼博物志般的精准写实和描刻摆渡到更辽阔的“中国”。 确实,只要涉及现实题材,贾平凹的写作都是在充分的田野调查之后。《极花》也不例外。《极花》中,胡蝶被拐卖到圪梁村的故事母本来源于贾平凹“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的“真实的故事”。可以研究一下“真实的故事”母本如何向《极花》小说述本的演变。贾平凹自己说,他“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这个故事。贾平凹一个老乡的女儿,初中辍学来西安和收捡破烂的父母相聚仅一年,便被人拐卖。好不容易被解救后,女孩子却被媒体和闲人围观,指指点点,以至于无法正常生存,留下字条,还是回到她被拐卖的村子。熟悉贾平凹的创作,应该发现这个他“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的故事其实在《高兴》的“后记”里已经被讲述过一次。而且《高兴》“后记”讲述的拐卖故事,主人公似乎更接近《极花》的胡蝶。对勘《极花》与《高兴》“后记”讲述的故事,就能够发现,发生在现实解救过程中遭遇村民围堵的场景正是《极花》最后胡蝶被解救逃脱的梦境,只是《高兴》“后记”没有像《极花》那样交代被拐卖女孩解救回城之后的后续命运。对于《极花》,胡蝶被拐卖的故事母本来源是一个还是两个真实发生的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高兴》“后记”讲述的拐卖故事是贾平凹调查西安捡破烂群体时发生的。根据对西安捡破烂群体扎实的田野调查,贾平凹写成了《高兴》。这之后,贾平凹又写出了《古炉》《带灯》《老生》,其中《带灯》《老生》都是在深入的田野调查之后写成的。但差不多过了十年,这个拐卖的真实故事却一直没有被贾平凹征用和调动创作出新的小说,直到《极花》。那么,贾平凹在等什么?《极花》“后记”交代了这部小说在贾平凹内心的沉潜和积淀:“以后,我采风去过甘肃的定西,去过榆林的横山和绥德,也去过咸阳北部的彬县、淳化、旬邑,那里都是高原,每当我在坡梁的小路上看到挖土豆回家的妇女,脸色黑红,背着那么沉重的篓子,两条弯曲成O形的腿,趔趔趄趄,我就想到了她……我就想起她……我也就想起她。”⑥(省略号为笔者所加)心里藏着“真实的故事”,行走在乡村大地,想象那些行走路上所见的底层农村妇女和记忆中故事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这就能够解释贾平凹为什么说,故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 不仅仅是对故事女主人公命运和生命结局的关切,查阅《定西笔记》,还可以肯定的是《极花》中的那些地理、物理、风俗和人情等的“知识”和2010年的定西“行走”有高度的吻合度。更为重要的是,定西“行走”不但获得了《极花》所需要的“知识”,而且捕捉到了《极花》的“农村的味”,这种“农村的味”是贾平凹小说植根中国大地的气息,贾平凹是在等待胡蝶在他的小说中丰满,也等待一个浸透农村味儿的艺术空间安放胡蝶的生命和生长。 贾平凹的写作不是城市楼头书斋的空想,而是不断的乡村大地行走。正是通过“商州”系列以来持续的行走,贾平凹目击到边远闭塞中国最后之农村的缓缓蜕变。接下来的问题是,作为虚构的小说,选择谁目击中国农村之“最后”呢?即谁是小说《极花》的叙述者。研究中国现代乡村小说的叙述者不只是一个小说技术问题,每一个不同叙述者的叙述声音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身份和立场,以及与生俱来的擅长和局限。可以举的两个例子是:“荒村想象”是中国现代作家基于辛亥革命前后乡土中国现实的研判开创的母题,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一代作家就集中书写过中国农村的凋敝和荒芜;但回望百年中国农村,除了凋敝和荒芜,也确实有过复兴和重生的时刻,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作家笔下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解放和新生感,同样是时代中国的农村现实。这不同时代中国农村废与兴的图景出自不同的叙述者,前者往往是游子兼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者,后者则是有文化的革命实践者。预设的身份和立场带来的是对中国乡村观察和书写的洞见,或者盲视——启蒙者放大中国乡村的荒原荒芜感,革命实践者则片面强调革命带来的中国乡村变革之“新”。如果仔细考察,这两类不同的叙述者其实和作者有着身份和立场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塑造了片面和偏见的中国乡村,大量目击却不能言说者心、眼中的中国农村没有被文学充分激活和释放,成为沉默无言的乡村。 贾平凹的写作几乎是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时代同时开启的。在那个时代,共同的现代化梦想令知识分子与国家主流话语取得一致,贾平凹乡村小说的叙述者亦往往取与国家主流话语一致的改革立场,如贾平凹所说:“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十年里,故乡的消息总是让人振奋”⑦,就像他这一时期一部长篇小说的题目“浮躁”,也如小说中的州河——“我的这条州河便是一条我认为全中国的最浮躁不安的河。”⑧时代是浮躁的,却有着光明必至的未来期许,所以“振奋”。当然,也会有困惑,但贾平凹却是一个乐观的理想主义者。短暂的好时光才二十几年就成为了过去时的“黄金时代”,“就在要进入新的世纪的那一年,我的父亲去世了。父亲的去世使贾氏家族在棣花街的显赫威势开始衰败,而棣花街似乎也度过了它暂短的欣欣向荣岁月”⑨。贾平凹在很多场合说过,他的小说“老老实实地去呈现过去的国情、世情、民情”,但问题是即使在改革开放一路高歌猛进的时代,“欣欣向荣”是不是唯一的“国情、世情、民情”?还是危机从一开始就已经暗自潜伏,只是因为他选择了改革立场而被遮蔽了呢?在以《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浮躁》为代表的所谓改革小说中,传统中国农村成为改革的一个假想的对手而被置于审判台,被以阻碍现代化的名义宣判它的落伍和悖时,但即便如此,小说虚构和想象的中国农村并没有成为最后之农村,因为有一个想象的新农村来新陈代谢行将消逝的旧农村。 变化应该是在《白夜》《土门》到《高老庄》的“中年变法”阶段。贾平凹自己说,在世纪之末写完《高老庄》,我已经是很中年的人了。“我中年阶段的世界观就逐渐变化”⑩,“人在中年里已挫了争胜好强心,静伏下来踏实地做自己的事,随心所欲地去做,大自在地去做”(11)。所谓的“随心所欲”,所谓“大自在”,就是不再被宏大的国家现代化想象所裹挟,而是充分尊重个人的观察和想象。基于对中国现实社会的认知,对已经到来并不断加剧的城乡对峙,贾平凹敏锐地捕捉到城市扩张中,中国乡村空前的溃退。我们或可意识到贾平凹这些创作是在世纪之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或者“乡村重建”的时代背景下展开,并且意识到他给出的是一个个令人失望的答案——从《高老庄》对城市化有限的肯定,到《极花》借黑亮之口激愤地控诉:“现在国家发展城市哩,城市就成了个血盆大口,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物,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了!”明乎此,我们能理解贾平凹针对《秦腔》所说的:“作家是受苦与抨击的先知,作家职业的性质决定了他与现实社会可能要发生摩擦,却绝没企图和罪恶。”(12)进一步,如果我们以《土门》为界,把贾平凹写中国农村的小说进行前后对读,会看到贾平凹是如何给“传统”中国乡村“平反”的,以及如何在《高老庄》《秦腔》《带灯》《老生》,包括《极花》当中书写着《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浮躁》等改革小说的反题。但此际时间已经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了,城市化以无可挽回的姿势将乡村逼到了绝境。在《秦腔》书写中国农村挽歌之后,贾平凹从一个忧伤的抒情诗人,转而成为一个有知识分子风骨的、独立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古炉》《带灯》《老生》《极花》就是这样沛然涌动着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之作。 贾平凹“中年变法”所变的还有他的小说观,在他看来小说就是“说话”:“《白夜》的说话”,“它可能是一个口舌很笨的人的说话;但它是从台子上或人圈中间的位置下来,蹲着,真诚而平常说话,它靠的不是诱导和卖弄,结结巴巴的话里,说的是大家都明白的话,某些地方只说一句二句,听者就领会了”(13)。同样取“说话”的小说叙事态度,《极花》“让那可怜的叫着胡蝶的被拐卖来的女子在唠叨”(14)。“说话”或者“唠叨”,从叙述者角度,其实是将居高临下的知识分子视角下移转交给底层民间普通人,而且这种视角的下移和转交应该理解为与贾平凹价值立场和文学观的互动:“我的情结始终在现当代。我的出身和我生存的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15)有意味的是,贾平凹有几部小说的叙述者都是穿高跟鞋闯入乡村的城市女子——《高老庄》的西夏搜寻着村庄的碑文打捞乡村湮没的历史,《带灯》的带灯忧心着农村基层的政治生态,而《极花》的胡蝶则目睹了中国最后的农村和自己一起沦陷。如果把贾平凹这些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每一个叙述者都从一个自己的通道抵达中国农村。贾平凹最大可能地避免对叙述者的垄断和专横,而是众声喧哗,让中国农村最大可能地敞开,从而也最大可能地通向中国农村之“真”。而且,从小说技术的意义上,贾平凹“说话”的小说实践也是在尝试小说多重叙事声音平等呈现的可能性。 《极花》从一开始即充分展示贾平凹小说“说话”的魅力。胡蝶“唠叨”的都是现场感极强的村庄细事——极花的绝迹,金锁媳妇被葫芦豹蜂蜇死,顺子进城打工……除了这些,被最频繁“唠叨”到的还是农村性事——性饥渴和性匮乏。八十岁的张老撑吃血葱搞大女人的肚子;顺子一走四年、家里的媳妇竟生了孩子,以至于村子里十几个光棍互相怀疑,最后却是顺子媳妇和收极花的男人私奔。胡蝶以一个村庄的异者“她”来看,绝迹、出走、死亡、性乱、私奔……圪梁村的末日来临。《极花》小说开始的时间正是生与死之间的“极期”。所谓中国最后农村之“最后”就是“极花”之“极”,亦即“极期”之“极”,对胡蝶,对圪梁村都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小说胡蝶的“她”看和“她”唠叨,既是现实的,也是心理的。尖锐的痛感,使得每一个微小的细事都成为不能遗忘的生命时刻的痛点。恰恰正是刻下一百七十八道儿的深刻,胡蝶目击到农村的隐秘和疼痛,一个农村青年的性饥渴: 刻道儿旁边的美女图是用糨糊贴上的,明显能看出那是一页挂历画,年月日被裁去了,只剩下一个美女像。美女从脖子到脚却好像被刀砍过,刀刀深刻,以至于把墙土都砍了出来。我问黑亮:你贴的?他说:我想要她。我说:你想要她你砍她?他说:我恨那女人不是我的。 中国当代文学写乡村性匮乏和性饥渴的扭曲和变态,《极花》不是最惨烈的,更极端的如曹乃谦的《温家窑风景》写精神失常、兽交、乱伦,等等,但贾平凹不取奇观或述异的态度,而是写“性”之于中国农村青年日常生活、生理和心理以及中国农村之未来和出路的影响,用笔“刀刀深刻”。 这是一座令人不安的村庄。老老爷说“这几年村子里净出怪事”。可是,即便如此,表面上看,圪梁村仍然是一座命不该绝的有机的村庄,就像“极花”所暗示的。极花不似鲁迅在《失掉的好地狱》中所写“地狱小花,惨白可怜”,而是极其美艳:“毛拉一到冬天就钻进土里休眠,开春后,别的休眠的虫子蜕皮为蛹,破蛹成蛾,毛拉却身上长草,草抽出茎四五指高,绣一个苞蕾,形状像小儿的拳头,先是紫颜色,开放后成了蓝色”,但极花同样是死亡之花,是毛拉坟穴开出的花。贾平凹写村庄的死亡着眼村庄的“方生方死”。“生”,我们可以看村庄的风水树,四棵白皮松精神勃发生机盎然。“绿树村边合”,树是村庄的庇护。树在,则村庄的风水、精神在。因此,中国作家写村庄的由兴而废都爱从大树的斫伤和毁灭着笔,像阿城的《树王》、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都是如此。贾平凹对村树尤其属意,以至于《高兴》的“后记”写完又写了“后记二”,专门记录老家的“六棵树”,这在贾平凹的写作生涯中是前所未有的旁逸斜出。在这篇“后记”里,贾平凹写侥幸活下来的树,怅惘地追念老家村子里“那些三十年间消绝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农耕农具”(16)。《极花》还写到槐树。写槐树,胡蝶先“唠叨”圪梁村的创世传说,“世世代代的人都说,这里原来是个海子。他们的祖先就在海子里捕鱼为生”。海子里出了魔鬼魃,海子上升,洪水泛滥,神杀死了魃,海子变成荒原,魃的骨骼长出六个大梁,为了镇压六个梁长成熊耳岭那样的雪山,在每个梁上建了寺庙。“据老老爷说这些个寺庙当年香火很旺,村里人天旱了去祈雨,生病了去祷告,谁和谁闹了矛盾,争执不下,也都去寺庙里跪下发咒,你说:神在上,我要是做了亏心事,让五雷把我轰了!他说:神在上,我要是做了亏心事,让五雷把我轰了!” 说村庄之“生”还在于它有着自己生生不息绵延的地方性传统、传说和宗教。但贾平凹没有把圪梁村写成一个闭塞的化外之地,当代政治生活早也在此扎根,比如十年动乱时期对宗教活动和场所的取缔和毁弃,这出现在沿海发达地区,就像范小青的《香火》写过的,圪梁村这样的偏僻之地也劫数难逃,但这不影响宗教传统在圪梁村隐秘的存在和传承。胡蝶看到的村庄:鸡鸣狗咬,人声吵骂,炊烟袅袅,毛驴犁地,整个村庄并不像许多乡村小说渲染的死寂荒芜。那些屋舍器物——窑洞,石磨,水井一如往昔;做石活的黑亮爹和剪纸的麻子婶这些手艺人神思飞动;人们相信麻子婶受孕、学会剪纸以及昏迷后醒来如有神授成为剪花娘子的灵异故事;还有,生孩子身下铺黄土,炒五种颜色的豆子,拴彩花绳子,以及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近乎巫术的“讲究”,维持了一村人生活在这里。 圪梁村,活着却濒临死亡。因为一座活着、运转正常的村庄,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个体和各个阶层应该是秩序井然的。因此,所谓中国最后的农村当然是指既有村庄构成的失序,犹未重建。《极花》的圪梁村处于中国当代政治网络结构的基层和末梢。在这里,村长是“强势”的。他的“强势”一方面是因为他是乡村基层政治的代表,就像村长自己强调“镇政府任命我当村长”;另一方面,他的“强势”是现实性的。小说的现实是他长期霸占着几个寡妇,而且拴子不在家时,也常去拴子家;立春、腊八是他本家的叔叔,他都敢纠缠訾米;他摆排起村里这几年的变化,是村子里买了六个媳妇。他对神灵没有任何敬畏之心。吊诡的是,他渎神尊法,事实上圪梁村在他的治下却法治废弛;而声称尊法不尊神的他却会率领全村人给老老爷拜寿补粮,祝老老爷万寿无疆。“村里人脆,不停地埋”,他又让黑亮爹多凿石羊送病。 很显然,在圪梁村,“强势”的不只是村长。王斯福研究中国当代村落“确认地方及其领导的制度”,认为存在两种基本类型:“其中一种类型的制度只是基层政府的行政,另一种是由下而上的‘传统’权威以及他们在文化知识与地位上的声望等级。”(17)圪梁村的村长自然是代表着前者,而老老爷则是后者。老老爷相信自己在圪梁村的权威和声望,也自觉地承担着他的责任:“我死不了的,村子成了这个样子了,阎王爷不会让我死的”;“我不是一个人的老老爷”。事实上,大多数时刻,圪梁村人,包括村长也服膺他的权威和声望。老老爷的“强势”是因为他是村庄共同信奉的传统权威,就像村庄共同拥有的传说、记忆和“讲究”等。“老老爷是村里班辈最高的人,年轻时曾是民办教师,转不了正,就回村务农了,他肚里的知识多,脾性也好,以前每年立春日都是他开第一犁,村里耍狮子,都是他彩笔点睛,极花也是他首先发现和起的名”,老老爷能写秦朝统一文字之前就有了的字,是一个文化传人。事实不仅如此,在圪梁村,老老爷是一个兼具家族长老、乡绅和巫等多重身份的权威和偶像。有趣的是,某种程度上,老老爷的世界观和贾平凹有着一致的地方。贾平凹认为:“古人讲,仰观象于玄表,俯察式于群形。这是我们活人的总的法则”(18);“一早一晚都在仰头看天,象全在天上,蹲下来看地上熙熙攘攘物事,一切式又都在其中”(19)。贾平凹参悟的活人法则以及天地人的秘密演化在圪梁村由老老爷执掌着。对天地,老老爷看历头,算年景,夜观东井:“天上的星空划分为分星,地下的区域划分为分野,天上地下对应着,合称星野。”对人间,老老爷给村里所有人都取过名,他以为“不起名那这村子百年后就没了”;他在葫芦上写毛笔字,印德仁孝;当梁水要像黑亮一样找到媳妇,想要把压制好的极花敬到中堂,老老爷说:“中堂是挂天地君亲师的。”对鬼神世界,他可以做梦问征兆。当瞎子叔腿疼,熏艾没有用,老老爷说“有鬼了”。不只是《极花》,贾平凹《秦腔》《古炉》等小说都有类似老老爷这样的地方“传统”权威,平衡着乡村的天地人鬼神秩序。 在《极花》的圪梁村,老老爷的权威是尊重和遵从长者的文化传统赋予并自然生长出来的。“革命”并没有能够阻遏村庄“传统”权威自然的汰选和生长,更没有将其剿灭。地方的“传统”权威老老爷一直发挥着作用(村人以为“树精”附体的麻子婶某种程度上也分担着村庄的地方传统权威)。他们共同维护着中国农村地方性的“另外的信仰共同体、另外的道德权威与安全感的来源”(20)。某种程度上的现实是,中国当代乡村基层政体和地方传统权威共同控制并影响着中国农村。《极花》走山的灾害发生以后,老老爷认为村庄接二连三的死亡和走山,是因为“十几年没有唱过戏或闹社火了”,想让村长唱戏安神。在老老爷的世界里“唱戏不是热闹,也不是要谢忱帮忙的人,戏是要给神唱的,安顿了神,神会保佑咱村子的”。而村长则回应,“神在哪儿呢?哪儿有神?”“生老病死很正常,走山是自然灾害”。但即便如此,《极花》的圪梁村地方性传统和“传统”权威隐秘地活着。而恰恰是改革时代以来,地方“传统”权威的作用不断被削弱。在贾平凹的思考中,正是因地方性传统消逝和“传统”权威失势,中国农村成为信仰缺失的“废乡”。早在《秦腔》贾平凹就思考并书写这种消逝和丧失。《极花》有一个细节值得玩味。毛虫去镇上两天,让瘫在炕上的爹不吃不喝,三朵伸张正义扯着毛虫来见老老爷,让他给老老爷认罪。小说写: 毛虫说:他又不是庙里的神。 三朵说:他不是庙里的神,但他是老老爷! 毛虫说:他能给我一碗饭还是给我一分钱?我认他了他是老老爷,不认他了就是狗屁! 因此,就像有人所忧虑的:“非集体化之后的农村出现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空。与此同时,农民又被卷入了商品经济与市场中,他们便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地接受了以全球化消费主义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道德观。”(21)这种“卷入”和“接受”,不只是物质层面的财富梦想——村民疯狂采挖极花牟利以至于极花绝迹;立春带回来的訾米脑子活泛,种血葱经管温泉;黑亮拥有拖拉机、杂货店……也是圪梁村出现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空”。在《日常生活的启蒙者》的“乡土”部分,彻费恩和鲍辛格讨论了“边城僻壤”这个概念。他们认为“在很多方面‘边城僻壤’是可以与中心同步的”,“在某些品质上,‘边城僻壤’比中心还要发育健全”(22)。因此,圪梁村“边城僻壤”,远离城市和政治中心不能解释它行将消逝成为中国最后的村庄。《极花》给出的真正原因在于:农村基层机构失范,是因为圪梁村村长渎神枉法、自私专横的各种妄为;同时,“晚期资本主义道德观”似乎也在导致“传统”权威的“失势”。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写刘全喜、张耙子和黑亮他们想办血葱公司,村长知道后要插一杠子,而且提出他要承头。这意味着,农村新势力的崛起受制于贪腐的村长而被压抑和阻遏,缺少上升的空间,进而也无法带动乡村重生和重建。从中国农村未来看,重建村庄废弛的道德、法律和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必须依靠这些被压抑的农村新人。 可以进一步思考,谁是贾平凹小说的农村新人?其实,贾平凹通过《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浮躁》等小说里乡村“改革者”形象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门门和禾禾从城市里汲取了新的价值观并在农村进行改革实践。在那个时代,城市只是他们力量的源泉和打开的新世界,这些新人最终是要在乡村实现自己的成功梦,也要带动乡村的更生,就像《鸡窝洼人家》的禾禾,他们在乡村的改革实践不断失败,但他从来没有想过逃离生息的乡村。“农村青年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相应地,青年文化已经在农村出现”,“青年文化的出现同时也展现了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农村社会的多样化”(23)。这用来指认20世纪80年代改革之初的中国农村是恰当的。但到了《极花》“时刻”,出生营盘村的知识青年胡蝶却是一个彻底的逃乡者。她少时父亡,家贫,为她和弟弟读书母亲卖光几乎全部家当,接着又去城里打工捡破烂。胡蝶初中快要毕业辍学,她想的是“娘走了,我也从此再也不是学生”。于是,追随娘进城。她梦想“我已经是城里人了,我就要有城市人的形象”,所以她要把娘收捡来的两架子车废品卖掉,五百块钱买了真皮的高跟鞋;她的爱情梦是出租院房东的儿子,一个读大学的城市青年。和胡蝶不同的是,圪梁村的知识青年黑亮并没有逃乡。黑亮形象接续的是贾平凹塑造的门门和禾禾等这些改革小说的人物谱系。《鸡窝洼人家》的禾禾在村子里第一个拥有手扶拖拉机,取得养蚕事业成功的同时,也在乡村收获了爱情。20世纪80年代贾平凹的乡村是牧歌情调的,同时代的作家很多都是这样,比如张炜的短篇小说集《芦青河告诉我》。他们小说的乡村改革者在事业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和乡村里最优秀的女人缔结良缘。有意思的是,《极花》中的黑亮也是村子里唯一的手扶拖拉机的拥有者。很长时间里,拖拉机都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想象和象征,而且拖拉机联系着的往往是农村新青年的成长故事,无论是张伟的《拖拉机突突响》,还是莫言的早期小说《白鸥前导在春船》,皆是如此。可是《极花》的拖拉机手黑亮这个乡村知识青年,在圪梁村既没有事业上升的空间,他梦想中的血葱基地要依附于乡村政治权威的村长,而且也没有收获甜蜜的乡村爱情。黑亮和胡蝶,如果在贾平凹20世纪80年代改革小说中是最有可能产生乡村爱情的一对男女,不幸的是在新世纪却沦为一起拐卖妇女事件的施虐者和受害者。乡村基层政治和传统权威在乡村的危机和坍塌,新人难以真正和《极花》村长这样的乡村政治代表剥离成为独立自主的新人,农村成为没有前途和希望的涣散无神的农村——这是《极花》里中国“最后”的农村。 可以想见,胡蝶出生的营盘村,也将成为另一个中国最后的农村。客观地说,胡蝶并不能算一个真正的城里人。《高兴》可以作为《极花》的一个前史,胡蝶就是一个“女版”的刘高兴,但“城里人”却成为她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援。即使被拐卖后,她不穿黑亮娘在世做的布鞋——“我不穿,失去了高跟鞋就失去了身份”。在圪梁村,她有城里人的优越感。某种程度上,她活着的信念就是“我现在是城里人”,“我要回城市”。但当胡蝶发现自己和儿子的星星出现在圪梁村的上空,当老老爷说“地呼出的气是云,也是飞禽走兽,也是人”,胡蝶也对自己的城里人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仅仅指责胡蝶这个乡村的女儿对乡村的逃离和仇视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她宁可做一个城市的寄居者,也不愿意安居故乡?因此,中国农村之“最后”是城市吸走了乡村少女胡蝶,在乡的黑亮却难以发育为乡村新人。而且,社会阶层的固化,使得胡蝶即使曾经抵达城市,也无法在城市扎根。 很容易从国家法律立场识别胡蝶被拐卖的非法和不正义,但当这个故事被安置在一个行将涣散的村庄,将会激发出文学的潜能。在价值判断上,我们不怀疑贾平凹的法律常识。小说对拐卖妇女的非正义性没有任何的迟疑,这是他写《极花》的出发点和基本立场,也是《极花》笔调沉郁悲凉的来由,但文学会关注远比法律可以裁决的是非更复杂的人性以及人性寄生的文化和社会土壤。因此,贾平凹借助这个拐卖妇女的故事打开的是中国农村更多的秘密以及犯罪案件之下涌动的人性暗河。涣散无神的农村失去精神庇护和安全感。进而,所谓“晚期资本主义道德观”将会在中国农村长驱直入,彻底摧毁中国农村。在这种道德观左右下,老老爷代表的地方传统权威将会在挽歌声中退场。农村的新一轮资源和格局的配置将会在村长和黑亮这些新生势力之间展开。《极花》中,胡蝶是城市与乡村以及圪梁村诸种势力的交汇点。就像《高兴》一写到背尸还乡,就有人联想到张扬导演的电影《落叶归根》,《极花》肯定也会使人想到导演李扬的电影《盲山》,但正如帕慕克所说:“电影一如前现代文学叙事与史诗,多数时候并非从主角的观点,而是从外向、从远处去看片中的虚构世界。”小说则可以不这样,《极花》中,胡蝶是圪梁村——中国最后农村的目击者,也是自身命运和疼痛的目击者。“当小说人物游荡在一大片景致中,然后定居下来、与它紧密结合、成为其中一部分,这些都是让该人物令人难忘的行为姿态,安娜·卡列尼娜之所以不朽,不是因为她动荡的灵魂或是那一大堆所谓‘性格’的特质,而是因为她深深沉浸在一片包罗万象的景致中,进而让这片景致透过她呈现出所有壮丽的细节。”(24)有意思的是,这恰恰暗合了贾平凹《极花》“以水墨而文学”的叙事技术追求。贾平凹认为:“我一直以为我的写作与水墨画有关,以水墨而文学,文学是水墨的。”(25)其实早在写作《浮躁》的时代,贾平凹就有了类似的自觉,他曾经说过:“中西的文化深层结构都在发生着各自的裂变,怎样写这个令人振奋又令人痛苦的裂变过程,我觉得这其中极有魅力,尤其作为中国的作家怎样把握自己民族文化的裂变,又如何在形式上不以西方人的那种焦点透视法而运用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法来进行,那将是有趣的试验!”(26)所以,不只是《极花》,他的那些选取故事在场人物叙述视角的小说,比如《高老庄》《秦腔》《高兴》《带灯》等,都属于这种“散点透视法”,或者“以水墨而文学”。 应该意识到,《极花》的“散点透视法”,其“看者”胡蝶不是《高老庄》中西夏乡村观光客那样的悠闲景致的观察者和文化的打捞者,也不是《带灯》中带灯那样有着政府赋予权力的乡村基层领导。胡蝶是一个被拐卖者,她的“唠叨”固然建构了《极花》圪梁村百科全书式的村庄断代史,但同时胡蝶也是对自己被侮辱被施暴的伤害史的伸张和言说者。圪梁村是一个光棍扎堆的地方,有限的女性要么被城市“吸”走,要么被村长垄断和霸占。在这里,男女之间的关系已经原始化到性交和生育,女性被物质化,可以被买卖,就像兄弟分家,“谁要柜子、箱子、方桌子和五个大瓮就不能要訾米”。而胡蝶年轻漂亮,读过中学有文化,还是来自城市,这些更刺激了圪梁村男人复仇的观看和施暴的“快乐”。小说写胡蝶的反抗,逃跑,被强奸,拴铁链的受虐过程,每一次性事都是一场针对女人身体、摧毁尊严的暴力侵犯。性的欢悦在这里被亵污,女性成为泄欲和生育的物质工具。 小说可贵的是,胡蝶不是一个屈服的受虐者,而是决绝的抗争者,一个对自己的命运逐渐唤醒并关注的思考者。每一次施暴,胡蝶的灵魂都在场。胡蝶咆哮,捣乱,肆意破坏。胡蝶屈辱、愤怒、痛苦、无奈狂躁,灵魂出窍:“我的魂,跳出了身子,就站在了方桌上,或站在了窑壁架板上的煤油灯上,看可怜的胡蝶换上了黑家的衣服。”胡蝶的灵魂“游荡”体验着人间地狱。快一年,“这是我第一次走出窑来,像出了坟墓”。一个村庄对一个弱小女子的施暴,除了訾米和神神叨叨的麻子婶,无论村长,还是村庄的新人黑亮,整个村庄都成了施暴者或者看客,谁也没有对胡蝶提供哪怕是道义上的声援。事实上,相当长的时间内,无论是20世纪40年代的《小二黑结婚》,还是80年代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政府”都给予农村青年追求自由的爱情强大的法律和精神支援,但悲凉的是《极花》,镇政府任命的村长却是每一次拐卖妇女的参与者和获益者。 《高老庄》开始,贾平凹小说中的中国农村就潜藏着无尽的暴力。类似约翰-基恩所说,中国农村正在成为“暴力之域”:“在这个虚构的恐怖之域,一些人毫无忌惮地对他人的精神和身体施加残忍的暴力。他们看上去正在享受这个过程,流露出一种对残忍行为的嗜好”,“他们已经迷上了野蛮,相信暴力是必须的,而且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有权随意运用暴力而不受处罚或制裁”(27)。《高老庄》村民对地板厂的冲击,《秦腔》最后的抗税风波(小说中暗示群体性的抗税是普遍事件,而不是孤立的个案),《带灯》涉及到另外两场群体性的暴力——一次是元老海组织的,一次是田双仓组织的,小说中的这些群体暴力事件都有着民间正义的基础。如果我们仔细辨识这些小说,其暴力源头往往是因为我们时代城市对乡村的掠夺和不公正引发的。面对中国农村此起彼伏的暴力,作家往往会放弃启蒙立场的对穷人之恶的反思,转而选择与穷人站在一起,文学成为简单的抗议文学和控诉文学,比如张炜的《刺猬歌》。事实上,中国现代社会暴力植根在复杂矛盾缠绕的历史和现实大地,哪怕面对乡村正义诉求的暴力抗争,也不应该必然通向对暴力的美化。对待乡村暴力,即使是具有正义诉求的暴力抗争,贾平凹并没有简单地选择站在穷人一边,而是希望挖掘出乡村暴力背后的复杂性因由。 而且,贾平凹坚信我们世界的温暖性和神性,他在谈到沈从文时说过:“善良而宽容的作家才能写出温暖的作品”,“沈从文以温和的心境,尽量看取人性的真与善”(28)。而“说到神性,好小说都是有神性,也就是有精神的”,“沈从文写的下层社会人的日常生命状态,就是探寻的是关于人的最为根本意义上的爱、真、美,他的小说才具备了生命力”(29)。事实上,胡蝶也感受到了圪梁村,尤其是黑亮一家和麻子婶身上人性微弱的良善和美好,小说写到许多人性闪光的温暖细节:村民给自杀的顺子爹料理后事给顺子尽孝;麻子婶、訾米等同样被损害的女性抱团取暖成为胡蝶微弱的精神支援;黑亮一家摧残胡蝶却又善待胡蝶:“以为我吃不下他们的荞面和土豆,就去了镇上给买了麦面蒸的白馍。”胡蝶临产瞎子叔还“讲究”着:“瞎子就把我抱起来,他一对胳膊伸直,硬得如同铁棍,竟然是平端着,而自己却把脸侧在一边,把我放在了我窑里的炕上”;“第一麻袋驮回来,挑了三颗土豆,都是小碗大的,敬在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前”。可问题是,这些抱有人性真善美的芸芸众生恰恰却成为一场场暴力的参与者或者漠然的围观者。汉娜·阿伦特认为:“在当今时代,共同感的消失是时代危机的最确切标志。在每一场危机中,世界的一部分塌陷了,为我们所有人共有的某些东西毁灭了。共同感的丧失,就像一根探测杆一样,标出了塌陷发生的位置。”(30)当代中国还不止于“共同感的消失”,而是城与乡之间,不同阶层和族群之间以及同一个阶层和族群之间互相嫌弃和撕裂,暴力更加剧了这种嫌弃和撕裂。胡蝶觉得村里有些人不是人,只是訾米说的“人样子”,“我若要再跟她交往,将来肯定和她一样而我又没她那个性格,我只会沉沦得连个人样子都没有了”。现实却是令人绝望的,“我不再有想法了,想法有什么用呢?黄土原想着水,它才干旱,月亮想着光,夜才黑暗”。小说以无尽的哀痛写到胡蝶从“我对城市”“想”到“学会”并顺应圪梁村的日常生活。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胡蝶能够在圪梁村活下去的理由,不是因为被圪梁村的温暖性和神性打动,也不是因为找到了疗治伤害和安妥灵魂的确信,而是畏惧和恐惧。 《极花》深层的悲剧是,胡蝶和黑亮这些乡村知识青年的无路可走。敌意的城市和亡灵飘荡的农村无法安放他们,他们也无法和这样的城市与乡村一起休戚与共。视中国为圪梁村,黑亮说:“待哪儿还不都是中国。”而经过了从营盘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圪梁村,再在梦里从圪梁村被解救回到城市,再从城市漂流回到圪梁村伤痕累累的旅行,胡蝶说:“在中国哪儿都一样。”一个乡村新生代看不到希望也不愿安居于此的农村,才真正是中国农村最后之最后。看护圪梁村的精神和信仰的,不是村长,不是黑亮,而是渐渐失势和边缘化的麻子婶和老老爷——这些是需要我们深在思考、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注释: ①③⑥(14)(25)贾平凹:《极花·后记》,《人民文学》2016年1期。 ②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第2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④贾平凹:《我心目中的小说》,《小说评论》2003年6期。 ⑤贾平凹:《在首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上的受奖辞》,《关于小说》,第14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⑦⑨(12)贾平凹:《秦腔·后记》,第541页,第542页,第546-5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⑧贾平凹:《浮躁·序言之一》,第2页,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⑩(11)(15)(19)贾平凹:《〈高老庄〉后记》,《关于小说》,第108页,第112页,第110页,第10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13)贾平凹:《〈白夜〉后记》,《关于小说》,第81-8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16)贾平凹:《〈高兴〉后记二——六棵树》,第307页,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17)(20)王斯福:《帝国的隐喻》,赵旭东译,第325页,第26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8)贾平凹:《就〈带灯〉致林建法》,《关于小说》,第23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21)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龚小夏译,第26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22)赫尔曼·鲍辛格:《日常生活的启蒙者》,吴秀杰译,第14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3)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译,第17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24)奥罕·帕慕克:《率性而多感的小说家》,颜湘如译,第124、83页,台湾麦田出版社2012年版。 (26)贾平凹:《〈浮躁〉序言二》,《关于小说》,第3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27)约翰-基恩:《暴力与民主·中文版序言》,易承志等译,第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 (28)(29)贾平凹:《沈从文的文学》,《关于小说》,第138页,第13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30)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第167-168页,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标签:贾平凹论文; 带灯论文; 文学论文; 农村改革论文; 浮躁论文; 高兴论文; 高老庄论文; 古炉论文; 腊月·正月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