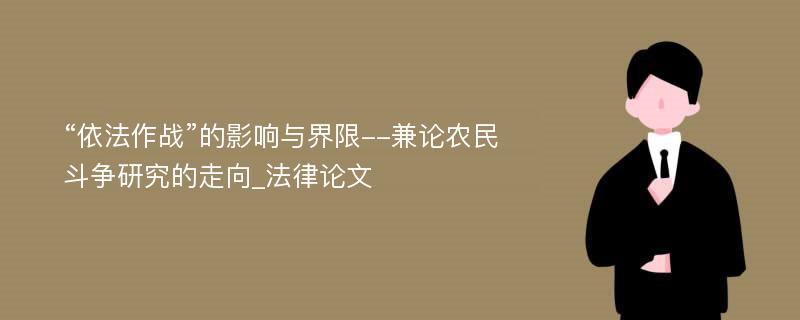
“依法抗争”的效力与边界——兼议农民抗争研究的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界论文,效力论文,走向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6)01-0166-08 “依法抗争”是李连江教授和欧博文(Kevin O.Brien)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基于中国农民减税斗争而提出的一个概念。观点提出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在国外有Susanne Brandtstadter、Lucien Bianco和R.Bin Wong等著名学者的专文讨论,在国内也很大程度上启发甚至开启了对农民抗争的专业化研究。针对不同的评论意见,O.Brien教授于2013年进行了专文回应,对其中的一些细节做了修正。本文的目的在于在联系当下社会现实的情况下,对基于上述文章而形成的依法抗争观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讨论,并尝试性地展望农民抗争研究的走向。 一、“依法抗争”是什么 欧博文教授早期在对1990年代中国农民抗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的概念,并认为其存在三个基本特征,即运作于正式参与渠道的边界,借用官方话语和承诺来反制强势的政治权力和行动效果取决于国家政治分化的程度,并且依赖于通过动员获得更大公众的支持。①后来经过对概念的进一步完善,欧博文认为依法抗争使抗争者能够运用国家的法律、政策和其他官方认可的价值来反对不遵守法律的政治经济精英,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被批准的抗争,旨在利用官方价值和有影响的行动者来向政府施压借以促使政府执行有利于行动者的国家政策。②之所以采用这个面临语词矛盾的概念,作者解释其目的在于突出依法抗争的属性,即依法抗争恰好是处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抵抗”和“政治参与”之间的灰色地带——在内容上基本上属于“政治参与”,但在形式上则明显地兼有“抵抗”的特点。可以看出此概念的关注点在于在先验性地预设了对中央政府合法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研究行动者的抗争手段和策略,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属于建立在认同基础上的政治参与的范畴,虽然是一种“找麻烦式的参与”,但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这样的参与却更多地带有对抗性质,这也就是为何作为一种政治参与的行动又被称为“抗争”的原因。 有一点需要明确,“依法”之“法”并不是指法学意义上的“法”,更多是在政治学意义上使用“法”的概念,其英文“rightful”一词本身也并无“法”的含义,更多的是指“合理的或者源自于权利的”内容,虽然李连江和欧博文在其中文论著中将“rightful resistance”译作“依法抗争”,这主要是考虑到作为行动者的农民群体“‘依法’的行动预设了对现行体制合法性的肯定,因而必定是基本发生在现行体制内”的事实,但文章中也明确指出“从内容上来看,依法抗争所依的法是中央政府制定的法律和政策,抗争的目标则是地方政府制定的不符合中央法律、政策或‘中央精神’的种种‘土政策’和其他侵犯农民‘合法权益’行为”③。而国内一些学者在对此概念进行讨论时,将“依法”之“法”仅仅限定为法学意义上的“法”,甚至狭隘地理解为“诉讼”④,实际上是对依法抗争的一个误解。 二、为什么是“依法抗争” “法”路径下的抗争研究基本经验之一来自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的抗税斗争。改革开放后中央为了解放农村生产力先后制定过一些限制农民负担的政策,比如1991年12月颁布《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规定农民负担不得超过农民上一年人均纯收入的5%,并规定,对于超过条例限制的不合理收费,农民有权拒付。但在很多地方由于各种原因,地方政府并没有落实这些政策,为了保证额外税费的征收和压制农民反抗,基层政府不可避免地会动用强制性力量。针对这些问题,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又针对基层政府税费征收方式颁布《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规定“不允许动用专政工具和手段向农民收取钱物;不允许到农民家里抓猪牵羊、强行收缴财物;不允许非法采取收回承包地等错误做法胁迫农民交钱交物”,并在2000年国务院纠风办和农业部联合通知中对这一问题再次加以强调。如此一来,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差距就不仅仅体现在征收内容和数量上,同时在征收方式上也差距甚大,这些“差距”就为农民依法抗争提供了政治空间,由此很多“减负代表”就在掌握中央以及省市级别的文件之后,利用包括耍灯、搞宣传车、贴标语、放电影等在内的各种方式吸引群众,借机宣传党的政策,抵制基层政府的“枉法”行为,⑤虽然在抗争过程中可能会伴随对抗性行为,但是总体上农民的抗税斗争始终是在中央政策的框架范围之内。⑥ 除抗税斗争之外,依法抗争的解释也得到了农村在一些“政治问题”上的抗争行为的支持,诸如反对乡村干部专制以及要求执行村民选举和计划生育政策等等。1988年6月开始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由全体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但是基层政府出于各种原因在落实选举政策上并未尽如人意,如此一来法律规定的具体性和基层政府的执行之间就出现了很大差距,这当然就会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熟悉到“几乎倒背如流”⑦的村民以抗争的根据。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计划生育领域,为了增加收入,基层政府对于上级拟定的社会抚养费标准往往是层层加码,而超生村民一旦知晓既定标准,必然会以上级政策抗衡基层政府的超生罚款。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依法抗争作为一种行动方式的存在基础在于国家的纵向政治分化,中央的“英明政策”构建了农民群体的政策预期和行动武器,⑧但基层政府在对上级乃至中央政策执行时的利己式变通为抗争者提供了借口。从这个意义上讲,政策制定与执行上下不一致的幅度越大,基层政府的行为合法性程度就越低,而抗争者的诉求就愈加“有理有据”,在“依法”名义下的抗争空间也就越大。 类似的情况在中外历史上也曾存在,晚清佃农也会以政府规定为由拒绝一些额外的地租费用,甚至当他们认为基层政府并没有按照规定程序征税时也会拒绝缴税,⑨但在反抗的过程中为了表示忠诚也会采用非暴力的方式,⑩这一点也反映出中国农民的行动方式在历史上(如前文讲述的1990年代抗税)的延续性(11);在沙皇俄国,农民也曾借用沙皇政令动员村民来抵制“不忠诚”的基层执法者;(12)在历史上的民主德国,市民也会借助于国家意识形态来开展对一些政府指导政令的“同意式抗争”(consentful contention)(13)。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类似于中国1990年代农民抗税的依法抗争在历史上和其他国家也以某种形式存在过,这实际上也从侧面反映出依法抗争作为一个解释框架的令人瞩目的解释力。 三、“有法可依”与“有利之法可依” 在分析完依法抗争框架的来源和解释力之后,本文将继续对该框架的其他潜在预设进行挖掘。对“依法抗争”概念做语义学分析的话,会发现“依法”实际上是“抗争”的前提和基础。既然如此,那么想要抗争,则首先要找到“可依之法”,这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在行动者抗争的涉及领域存在管辖之法,其二是该行动领域的管辖之法必须是“利己之法”。对于第一层含义容易理解,无论是农民的抗税,还是要求基层政府落实村民选举办法乃至降低超生罚款数额,村民均要拿出具体的法律和政策条文以作为相应诉求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和《村委会组织法》均能够扮演这个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行动者的其他诉求也可以找到明确的法律和政策依据,实际上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各种新问题新事物层出不穷,他们不可能都能够找到法律和政策依据,比如一些遭遇生产和生活困难的农民就曾将这些困难作为上访缘由,要求党和政府给予额外的帮扶和救助,甚至在已经给予低保名额的情况下仍然要求“组织照顾”(14)。这一类要求在情理上有合理之处,因为国家负有保障公民基本生活的道义责任,但是却于法无据。还有其他诸如城市中的无证摊贩的抗议行为也是如此。在这些情况下,这些领域的抗争者实际上是“无法”而且也不会选择“依法”抗争的。 相对于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则更为现实,相对于规则而言,作为理性选择主导下的农民群体对行动目标(利益诉求)的实现更为执着,收益最大化是首要的考量,(15)所以“依法”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可依之法”必须与“所谋之利”相一致,如果发现管辖法律与政策不支持甚至相悖于诉求主张时,很难想象抗争者会出于利益的考虑继续选择“依法抗争”,而实际上他们会果断地放弃“法”的途径而转求其他方式抗争。虽然新版《劳动法》做了一些有利于农民工的修改,但是在高昂的诉讼成本和漫长的诉讼周期面前,选择法律渠道讨薪的农民工依然寥寥,(16)更不用说在征地问题上了。《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个人不具有所有权,并且“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些规定意味着政府在土地处理上有完全的主导权。面对该“不利己之法”,农民群体当然会选择性地淡化“法”的作用,转而采取其他抗争手段,这也是土地领域少见“依法维权”的原因。即使频繁发生的土地领域的维权事实上大部分也是因为不满意补偿标准而发生的,而并非反对土地征用行为本身,因为纯粹的反对征地类要求很难从相关法律法规中找到支持,当然抗争者也就不会选择“依法”。以影响很大的2007年重庆钉子户事件为例,杨武夫妇在抗议拆迁的过程中拿出的是《物权法》中对私有合法财产平等保护的条款(17),而对规定政府可以征用土地的《土地管理法》采取了漠视的态度,这说明抗争者对于“法”的使用是选择性的,(18)选择的标准是是否服务于“权利”的实现而非“规则”的伸张,(19)这与法治社会条件下的依法办事有着本质区别。 另外一种情况是对法律的“创造性地误读”(creatively misread/deliberate misinterpretation)(20),当抗争者不能找到可以支持自己诉求的法律时,会寻找相近的法条进行倾向性地解读。Kelliher教授曾举例:在改革初期,安徽肥西农民为了实现大包干的想法,有意误读三中全会文件并以之为武器来抵制反对包干的基层干部的做法。其实类似的情况在农民抗争中也存在,尤其是党关于官民关系的笼统的政治原则,例如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走群众路线,因为没有具体的指向和标准,也就更容易被“联系实际”地做出倾向性的“另类解读”,例如在2012年,“苗翠花”模仿新闻发布会召开的“讨薪发布会”上打出的条幅是“不支付民工工资是破坏和谐的行为”,“和谐”没有明确的内容和具体指标,当然每个人都可以自己理解和定义“和谐”。 以上分析说明,农民群体对“法”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明显的工具性色彩,在此基础上对“法”的借助也必然是选择性和局部性的,由此提出的“依法抗争”概念,其解释效力自然会受到很大限制,也只有在“存在管辖法律,并且该法律支持抗争者诉求”的情况下才是成立的。 四、“被批准”的抗争? 欧博文和李连江教授认为依法抗争是一种被批准的抗争(sanctioned protest),之所以“被批准”很大程度上因为抗争者创新性地借助于法律、政策和其他国家倡导的价值观,通过官方认可的渠道和原则来向并不忠诚的当权“精英”施压,目的在于要求他们落实中央的“英明决策”(21)。这一论断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因为确实大部分的农民抗争的指向并非体制与法律和政策的正当性,而是执行的偏差,这也是促成一个威权主义政体中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批准甚至在某些条件下鼓励抗争活动的原因所在。(22)但是对于政府“批准”抗争而言,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其一是批准的目的,其二是批准的程度。对于第一个问题,中央和地方之间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分化现象,漫长的纵向官僚层级变相强化了地方自主权,而对中央政策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致使大量中央“政策出不了中南海”,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弱化,鉴于此,需要借助某种体制外力量来强化对地方的监督,包括信访在内的抗议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这个作用。但是这个作用是有明显限制的,一旦中央感觉到抗议活动已经对自身产生威胁的时候,就会采取压制和分化措施,这也是兴起于2002年前后的信访潮在经历了2005年顶峰之后最终在2006前后消沉下去的原因。(23)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批准抗争”是存在的,但目的在于维护中央建构自身权威以及对地方的监督和控制,而非保障公民的权利。 当然,“利用”抗争与“批准”抗争并不矛盾,但这决定了“批准”的限度,即以地方为指向且不会对社会稳定与政府能力产生冲击,(24)这就意味着公民一旦越界,即使是“依法抗争”,政府也会借用“危害国家安全罪”、“扰乱公共秩序罪”、“寻衅滋事罪”和“妨碍公务罪”等名义“依法镇压”(拘留,劳教和判刑等)。在有学者调查的一个案例中,一青年在1998年领导农民抗交提留时,与镇干部发生了肢体冲突,结果农民群情激愤,不听该青年的劝阻,掀翻了镇政府的吉普车,最后该青年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5)浙江一村支部书记为了保护村庄耕地带领村民维权,最后却被所在县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26)虽然这些对维权者的处罚都是由基层政府做出的,但是中央政府并没有明显地干预或者强令基层停止此类行为,这说明中央政府在“批准”依法抗争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批准”了基层政府对抗争行为的压制,尤其是在政府让步成本较高和抗争行动已经危及社会稳定、政策执行以及官员形象的时候,更是如此。(27) 五、社会变迁与依法抗争 依法抗争的经验主要来自于1990年代农民的减税斗争,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2006年正式取消农业税之后,再加上农村社会观念转变,村民生育意愿较之于1990年代已大大下降(笔者鲁西南χ村调研,2012),以往的农民群体依法抗争的主要议题(issue)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数据显示,现在的抗争主要领域已经过渡到土地拆迁问题上,(28)但是土地法的规定明显不利于农民群体,因为他们没有所有权,而“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面对土地被征用,农民并没有反对征用的实力和依据,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无有利之法可依”,所以就更多地选择其他非“依法”方式,比如一些学者讲的“问题化”的抗争方式(29)、“依理抗争”(30)或者“依势抗争”(31)等等。这些非“依法”方式的抗争与依法抗争的区别在于:依法抗争实现诉求的希望是在中央政府,希冀借助中央来抵制基层政府的行为,但是“问题化”或者“依势”的重点转向了行动者自己,希望通过自身造势来“迫使”基层政府满足诉求,而“依理”或者“示弱”的方式在于希望吸引社会尤其是媒体同情来驱使基层解决问题,(32)这种路径的关键在于社会力量的关注。这些非“依法”路径的存在,说明依法抗争的解释对时代变迁所引起的农民抗争方式的变化的关注是不够的,尤其是时代变迁所引起的抗争议题变化对抗争方式的影响。(33) 再者,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新兴媒体的崛起,加之长期的行动经验的积累,一些农民抗争群体已经具有相当的行动能力和学习能力。一方面他们开始利用网络等新兴媒体来吸引关注扩大影响。2012年,一位名为“苗翠花”的农民工为了讨回工资,模仿外交部新闻发布会拍摄了“讨薪发布会”并放到网络上,在引起广泛关注后顺利拿回工资,还有村民在环境抗争中将一些触目惊心的污染照片放置在网络上的做法,(34)都反映了这一现象。另一方面,借助于新兴媒体的即时传播能力,农民群体可以更为方便地学习其他抗争者的“成功经验”,通过各种“另类”方法吸引关注,向“同行”取经等等。2007年章和进通过用跳楼要挟大包工头的方式拿到了拖欠两年的欠款,事后又帮助各地农民工策划了多起跳楼讨薪事件,被称为“最牛讨薪跳楼秀导演”(35)。2013年7月冀中星首都机场爆炸维权之后,机场迅速成为“时尚”维权场所,接二连三出现机场抛撒传单、机场燃放鞭炮等等,这些事例说明维权者的效仿能力很强,为了实现行动目标会迅速尝试新的方法。为了讨要强拆补偿而状告财政部的一位老太太,对其他访民的忠告是“要学会创意上访”。为了帮助其他群体维权,一些“成功人士”会积极传授经验,策划新的维权策略,甚至出现专业的维权培训班。(36)这些事实说明抗争者在信息时代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学习能力,可以迅速效仿来自不同区域不同领域的不同类型的抗争方式,显然,在此过程中只有对诉求的忠诚,而很难看到“法”的位置。 依法抗争的政治空间主要源自于科层体制的纵向层级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37),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政策执行偏差为依法抗争提供了依据,但客观上讲,国家的纵向层级分化并非一个不受影响的常量,各种时代性的因素决定了层级分化的程度。1990年代属于改革初创时期,地方自主权很大,加之当时信息流通不畅,致使基层政府可以在辖区内为所欲为,但经过20余年发展,尤其是随着法治化进程的推进,基层政府行为的规范化程度已经有了很大提高。慑于媒介曝光带来的政治压力,基层政府在1990年代的各种不规范摊派行为已经有了很大收敛。基层政府行为的规范化意味着其与“中央之法”的偏离程度会下降,体制内的政治分化程度也会得到缓解,基于此而形成的农民依法抗争当然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依法抗争是一个特定时代条件下的政治现象,随着社会的变迁,自然也会发生变化。具体而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推动了抗争议题的变化,信息技术和经验累积则让抗争者变得更加灵活,国家的政治发展也形成了当下抗争对象与1990年代的区别。在行动诉求、行动者和行动对象均发生重要变化之后,作为一种因应抗争情境变迁的行动者抗争剧目(repertoires)也必然会有很大改变。经验表明,抗争剧目的多元化是一个基本的态势,“法”更加不具有规则性价值,在越来越专业的抗争者面前,更多的抗争资源被动员起来,行动者的抗争剧目单越来越丰富,从上访、请愿、绝食、怠工、罢工、自杀、群体诉讼和示威游行,到扮演狄仁杰、拜包公和抬“三霄娘娘”游行等“创意方法”,层出不穷。在这一进程中,行动者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能够权变和机智地运用各种策略并根据政治情境的变化而转换,(38)“法”仅仅是这个长长的抗争剧目单中的一个剧目而已,甚至不少抗争已经突破法的边界,走向对抗性的暴力抗争,(39)这些变化必然会对“依法抗争”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 六、抗争研究的走向 所有上述讨论并不是在否定“依法抗争”的解释力,而是在讨论这个解释框架的解释边界。在文章最后,结合该框架提出后的十多年里的农民抗争经验,尝试性地前瞻在策略范式的框架下,农民抗争研究的未来走向。在依法抗争的研究中,学者更多地关注国家政治的纵向分化,并认为其是这种抗争现象的基本存在依据。在承认这一基本论断的同时,我们也不免产生一个疑问:依法抗争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是否存在区域性的差异。其实不难发现,支持依法抗争的研究和材料来源是比较区域性的,陈桂棣等的调查来源于安徽,于建嵘的类似研究源于湖南,虽然从湖南到安徽的跨度足以说明依法抗争确实是一个广泛的现象,但是根据笔者在鲁西南豫东地区的访问(2012),这样的尤其是具有对抗性特质的依法抗争不多见的,虽然大部分农民也对基层政府摊派表现得怒不可遏,但是他们采取的方式更多的是隐匿财产、逃跑或者“拖”等,这显然更符合斯科特笔下的“日常抵抗”(40)范式。至少从这里可以看出,依法抗争在区域间表现得很不均衡,换言之,同样面对税费摊派压力,不同地区村民做出的反应是不同的,那么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什么,是村民的历史记忆?是不同区域间的经济水平差异?还是基层政府的治理方式?等等,这显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另一个问题,“依法抗争”提出后,受到的各种评论中有一条是对其“延伸思维”(developmental thinking)的批评,即对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依法抗争及其行动者权利意识水平之于未来中国政治发展与民主化的意义做出过度解读,(41)笔者基本赞同这一说法,包括欧博文教授本人后来也承认依法抗争的存在以及扩散并没有太多的民主化和政治变迁意义,顶多是具有某些政策影响。(42)虽然如此,但是笔者认为对依法抗争做另一种形式的延伸研究是必要的,即与制度化参与、暴力革命和合法化的社会运动之间的演化关系。作者也承认,类似1990年代中国农民依法减税斗争的做法在中国古代也存在,前文述及晚清农民也曾以朝廷政令抵制县署衙役的摊派行为(前引)。Perry教授也认为,当下中国农民的抗争逻辑与历史上的农民行为是一致的(前引),这句话其实可以做两个层面的理解:其一,依法抗争在历史上确实是一种常见方式;其二,在历史上广泛存在着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揭竿而起,斩木为兵”发动暴力起义的情形,这是否说明:依法抗争作为一种低烈度的无涉政治合法性的对抗行为与暴力革命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形式的联系?依法抗争的持续,随着农民行动能力的增强和经验的累积,加之长期难以解决问题带来的信任流失,是否最终会将依法抗争引向政治性的暴力对抗?比如类似于2014年河南几个农民因不满政府不作为而公然“撤销”邓州市人民政府并组建“邓州市新人民政府”行为(43)之前是否也曾“依法抗争”过;但另一方面,既然西方社会也存在某种形式的依法抗争,(44)但为何经过长期的演变,依法抗争基本上成功避免了暴力化走向,而被纳入和平的社会运动的路径之中,这一点是否也说明依法抗争可以被“体制吸纳”进而转化为建设性政治力量?我们当然希望看到抗争力量的建设性转化,那么对其中的转化机制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同时对历史上的“依法抗争”反复的暴力性转化做必要的防范。 最后一点,“依法抗争”之后之所以会出现其他的“依势”、“依理”等概念,就是因为后来的概念在“依法”的前提预设——“有利之法”加之“弱者假设”上提出了挑战,但实际上这些后来概念也面临类似问题,假设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概念的解释力,并“大大低估了中国民众在采用抗争手段时表现出的灵活性”(45)。中国农民在理性选择和利益最大化的框架下,任何抗争资源都会被策略化和剧目化,“法”、“势”和“理”各自路径下的表演剧目(学术用语)都不过是抗争者可供选择的长长的剧目单中的某一个剧目而已。既然如此,学者旨在提出某一解释概念的研究会更像是为剧目单添加一个新剧目而已,但对于认识行动者对各个节目的选择尤其是节目间的转换逻辑却无能为力,而实际上这个“转换”才是抗争行为的真实图景。Charles Tilly之所以在后期研究中基本上放弃了对抗争行为所作出的竞争性(competitive)、反应性(reactive)和进取性(proactive)三分法而采用抗争剧目(repertoires of contention)的概念,就是因为三分法存在明显的现代化预设而有不可忽视的目的论(teleological)倾向,(46)容易出现对现象寓意的过度解读,进而限制对抗争现象本身的研究。其实对于中国农民抗争研究也一样,对某个单一概念的开发以及过度解读也会不自觉地掩盖其他抗争手法进而不利于理解完整的抗争现象,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弄清楚行动者的行动剧目单上究竟有多少剧目(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弄清楚),而是行动者在不同的剧目之间会如何选择以及如何“换台”,研究这些内容才有助于了解真正的行动者抗争图景。 注释: ①Kevin O.Brien,"Rightful Resistance," World Politics,Vol.49,No.1,1996,pp.31-55; Lianjiang Li and Kevin J.O'Brien,"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Vol.22,No.1,1996,pp.28-61. ②Kevin O.Brien,"Rightful Resistance," World Politics,Vol.49,No.1,1996,pp.31-55; Kevin J.O'Brien,Lianjiang Li,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2. ③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载吴国光主编:《九七效应:香港、中国与太平洋》,(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年。 ④董海军:《塘镇:乡镇社会的利益博弈与协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24页。 ⑤于建嵘:《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 ⑥Jonathan Unger,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hina,Armonk:M.E.Sharpe,2002,p.214. ⑦田园:《中国农村基层的民主之路(下)》,《乡镇论坛》1993年第7期。 ⑧Kent Jennings,"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1,No.2,June 1997; Jude Howell,"Prospects for Village Self-Governance in China,"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Vol.25,No.3,1998. ⑨Mi Chu Wiens,"Lord and Peasant:The Six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odern China,Vol.6,No.1,1980. ⑩Kurt Schock,Unarmed Insurrection:People Power Movement in Nondemocracies,Minneapolis,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5. (11)Elizabeth J.Perry,Challeng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Social Protest and State Power in China,Armonk:M.E.Sharpe,2001,p.X. (12)Daniel Field,Rebels in the Name of the Tsar,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6. (13)Jeremy Brooke Straughn,"'Taking the State at Its Word':The Arts of Consentful Contention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0,No.6,2005,pp.1598-1650. (14)狄金华:《寻求组织庇护:一个农民信访解释的新视角》,第十届组织社会学工作坊,2013年7月。 (15)Susanne Brandtsta Dter,"Book Review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Vol.33,Iss.4,2006. (16)He Xin,Wang Lungang & Su Yang,"Above the Roof,Beneath the law:Perceived Justice behind Disruptive Tactics of Migrant Wage Claimants in China," Law & Society Review,Vol.47,No.4,2013. (17)“重庆杨家坪拆迁事件”,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8D%E6%85%B6%E9%87%98%E5%AD%90%E6%88%B6,2014-4-21。 (18)Susanne Brandtsta Dter,"Book Review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Vol.33,Iss.4,2006. (19)Xi Chen,"Between Defiance and Obedience:Protest Opportunism in China," in Elizabeth J.Perry and Merle Goldman,eds.,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Harvar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254. (20)Daniel Kelliher,Peasant Power in Chin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p.63. (21)O'Brien,Lianjiang Li,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2-3. (22)一些学者据此提出“抗争威权主义”(contentious authoritarianism)的说法,参见Xi Chen,Social Protest and Contentious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2012。 (23)Lianjiang Li,Mingxing Liu and Kevin J.O'Brien,"Petitioning Beijing:The High Tide of 2003-2006," The China Quarterly,Vol.210,2012,pp.313-334. (24)Lucien Bianco,"Book Review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Vol.189,2007. (25)于建嵘:《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 (26)《浙江松阳:村书记与开发商的较量》,http://www.zgmszk.com. (27)Yongshun Cai,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China:Why Protests Succeed or Fai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45; Yongshun Cai,"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Suppression of Popular Resistance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Vol.193,2008,pp.24-42. (28)刘守英:《群体性上访事件6成与土地有关》,http://news.163.com/13/1014/10/9B50LSFJ00014AEE.html。 (29)应星、晋军:《集体上访中的“问题化”过程》,载《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1),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 (30)于建嵘:《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冲突:对当代工农维权抗争活动的观察和分析》,《凤凰周刊》2005年第7期。 (31)董海军:《依势博弈:基层社会维权行为的新解释框架》,《社会》2010年第5期。 (32)这种倾向也可以见诸一些外国抗争,具体参见Michael Lipsky,"Protest as a Political Resourc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2,No.4,1968,pp.1144-1158。 (33)Doug McAdam,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To Map Contencious Politics," Mobilization: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No.1,1996,pp.17-34. (34)Bryan Tilt,"Industrial Pollution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in Rural China:Risk,Uncertainty and Individualiz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Vol.214,2013,pp.283-301. (35)《农民工讨薪“正常路”难行:相信媒体不信政府》,央视网,2013年01月24日。 (36)Cai,Y.,& Sheng,Z.,"Homeowners' Activism in Beijing:Leaders with Mixed Motiv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Vol.215,2013,pp.513-520. (37)Kevin J.O'Brien,Lianjiang Li,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65. (38)Hongping LIAN,"The Resistance Of Land-Lost Farmers In China:'Interests-Striving' And 'Struggle By Order'," Journal of Community Positive Practices,No.3,2012. (39)Yu Jianrong,"Social Conflict in Rural China," China Security,Vol.3,No.2,2007,pp.2-17; Kevin O.Brian,"Rural Protest," Journal of Democracy,Vol.20,No.3,2009,pp.25-28. (40)James Scott,"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 in Forrest D.Colburn,ed.,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Armonk,NY:M.E.Sharpe,1989,pp.3-33. (41)Susanne Brandtsta Dter,"Book Review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Vol.33,Iss.4,2006. (42)Kevin O.Brien,"Rightful Resistance Revisited,"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Vol.40,No.6,2013,pp.1051-1062; Emily T.Yeh,Kevin J.O'Brien & Jingzhong Ye,"Rur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Vol.40,No.6,2013,pp.915-928. (43)《3农民组建“新人民政府” 10名大学生投简历应聘》,大河网,2014年4月23日。 (44)Dai Haijing,"Book Review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China Review,Vol.8,No.1,Spring 2008. (45)赵鼎新:《国家政治与当前集体抗争事件的危险发展》,《领导者》2011年总第37期。 (46)Charles Tilly,"Contentious Repertoires in Great Britain,1758-1834," Social Science History,Vol.17,No.2,1993,pp.253-280; Charles Tilly,The Contentious French,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