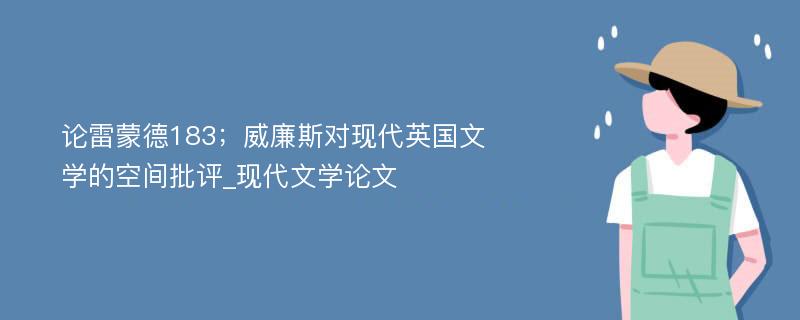
论雷蒙德#183;威廉斯对英国现代文学的空间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现代文学论文,威廉斯论文,批评论文,雷蒙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29(2007)03-0105-09
针对“19世纪沉湎于历史”的知识和思维传统,(苏贾:10)“空间转向”成为20世纪西方知识和政治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对“空间”的关注与反思导致了文化地理学的兴起,促进了跨学科发展的趋势。(陆扬、王毅:356)“空间转向”使更多的人自觉地关注文学和文化文本中对空间的表现,关注空间问题对我们思考文学史的方式的改变。菲利普·韦格纳(Phillip E.Wegner)在其长篇论文《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中声称,“这一双重规划在雷蒙德·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对英国现代文学的经典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明”。(Wolfreys:186)在威廉斯对英国现代文学的空间批评中,“城市”、“乡村”、“边界”三种空间形态及其所蕴含的“文化革命”① 力量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威廉斯文学批评的空间视野
在英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变迁进程中,乡村的没落和城市的扩张,是一个最明显的标志。“乡村”与“城市”的变迁,不仅仅是一种地理空间的变迁,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变迁。对变迁中的乡村与城市的关注,是英国现代文学的持久主题。
但是,对“乡村”和“城市”的呈现,不论是在文学或文化作品中,还是人们对这些文学或文化作品的分析中,都普遍存在着一种静止对比模式:“乡村已经汇聚了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的观念:安宁、纯朴和善良的美德。城市已经汇聚了一种已完成的中心的观念:学识、交流、光明。充满强烈不友善的联想也已经出现:城市是充满噪音、物欲和野心的一个空间;乡村是充满了落后、无知和局限的一个空间。”(Williams,1973:1)威廉斯出生、成长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的边界小镇,却工作、生存于大城市,这种独特的个人经历,使他认识到:在英国的现代历史变迁中,在人们的现实经验中,乡村与城市不是彼此隔离的封闭空间,而是处于不断的历史变化和关联中。威廉斯联系他自己家庭的实际经验写道:“我们家是一个分散的家庭,伴有公路、铁路以及当下的信件和印刷品。乡村和城市之间、中间地点和共同体之间、中间或临时的工作与定居地之间,存在着另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流和联系。”(Williams,1973:4)威廉斯的这种“边界”空间中的个人成长经验,构成了他对变迁时代从空间介入来呈现时代经验的理想文学主张:变迁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应该在历史的动荡中呈现乡村与城市的相互冲突与彼此关联。但是,由于变迁时代的作家和普通大众一样,其经验、思想、情感都是错综复杂的:他们既可以从历史的、动态的眼光出发呈现这一相互冲突、彼此联系的状况;也可以立足于“乡村”来审视“城市”或立足于“城市”来审视“乡村”。这些不同的呈现视角又以更加复杂的组合方式具体化在英国不同时期的现代文学之中,从而构成了“乡村”和“城市”的错综复杂的文学地图。因此,对“乡村与城市”的文学呈现的研究必然要涉及个人经验和文化、政治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每当我考虑乡村与城市之间、出身与学识之间的关系时,我发现这个历史是活跃而连续的:这些关系不仅是观念和经验,而且是租金和利息、情景和权力构成的一个更为广阔的体系。……乡村和城市的生活既是变化的又是当下的:通过一个家庭和一个人的历史而在时间中变化;通过一种关系和决定的网络而在情感和观念中变化。(Williams,1973:8)
因此,威廉斯对英国现代文学中的“乡村与城市”主题的研究不仅仅是要勾勒一种地理空间的复杂变迁,更是要勾勒一种文化空间的变迁,并分析其中“情感结构”的变迁。在这样的研究框架下,一方面,“乡村”、“城市”、“边界”不是一种静止、凝固的地理空间,而是各自内部充满了变化和异质性文化力量的交错的文化空间;另一方面,这些空间之间也不是彼此隔绝的封闭空间,而是处于相互冲突和关联之中的开放空间。
二、乡村:异质文化力量较量的文学空间
在现代英国的变迁中,乡村经验具有一种永恒性,对这种经验的呈现是现代英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威廉斯以时间为线索勾勒了这个传统中蕴含不同“情感结构”的三种乡村空间形态。
(一)早期“乡村别墅诗”:诗意“乡村”中的文化抵制 在威廉斯的研究中,“如何阅读英国的乡村别墅诗这个广为讨论的问题”是其研究的起点。(Williams,1979:303)威廉斯以本·琼森的《潘谢斯特》(Penshurst)和托默斯·加鲁的《致萨克斯汉姆》(To Saxham)为主要例证进行了分析。在他们的笔下,乡村别墅洋溢着宁静祥和的氛围,人与自然浑然一体,俨然一个“世外桃源”。这类“乡村别墅诗”产生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正是英国封建贵族社会濒临解体、资本主义“圈地运动”开始的时期:大批的英国农民开始丧失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背井离乡、苦不堪言。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现实状况和诗歌世界的如此巨大的反差呢?这种反差意味着什么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诗人在诗歌中所要传递的情感和伦理立场。以琼森和加鲁为代表的这些诗人创作的目的不是要呈现乡村的真实状况,而是要表现处于时代激荡时期的一部分人真切的情感体验,即:在贵族生活方式面临解体的时代,对这种生活方式的缅怀和赞美。因此,这样的“乡村别墅诗”与其说是对乡村生活的真实再现,不如说是诗人所迷恋的乡村生活面临崩溃时的一种诗意化的选择,在这样的选择中,大量的乡村景象被他们所凝视的少数乡村景象所遮蔽。“乡村别墅诗”在美化“乡村”的同时,就是对“城市”阴暗面的描述,然而乡村诗人们所描绘的作为美好“乡村”对立面的“城市”所具有的现象真的是城市所独有而乡村所没有的吗?威廉斯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指出,在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乡村绅士与城市世俗之人的对比”,但是,“贪婪和算计,如此容易被孤立和被谴责为城市独有的现象,其实可以回溯到乡村别墅及其周围的旷野和劳动者。”(Williams,1973:48—49)也就是说,“乡村别墅诗”对城市所批判的东西只不过被诗人遮蔽于对乡村的美化中,剥削和欺诈在乡村和城市中都存在,而且两种空间中的这些丑恶现象相互渗透,彼此影响,不断强化。但是,“一种理想化,以暂时的情境和对稳定性的强烈渴望为基础,试图掩盖和逃避时代的实际存在的苦涩矛盾”。(Williams,1973:45)“乡村别墅诗”中的“乡村”空间在表面宁静、纯真、祥和之下隐匿的是两种异质文化力量的激荡。
可见,诗意化的“乡村别墅诗”无疑是没落时期贵族生活的挽歌,是对代表着历史进步方向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一种逃避式的抵制。
(二)“乡村别墅诗”的流变:现实“乡村”中的文化冲突 进入17、18世纪以至于19世纪,伴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伴随乡村的进一步没落,大多数的文学家们并没有放弃对乡村的迷恋,“乡村别墅诗”并没有随着城市对乡村的蚕食而消逝,而是逐渐地从早期对资本主义的逃避式抵制衍变为直接呈现存在于“乡村”空间中的文化冲突。威廉斯通过梳理从马维尔的《关于阿普尔顿别墅》(Upon Appleton House)到波佩的《致柏灵顿的使徒书》(Epistle to Burlington)再到汤姆逊的诗歌中所存在的最重要的变迁,指出这个时期的社会变迁“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的社会性格,并且这在意识形态、调解和关于乡村的新的创造性文学作品中,也被改变了。在关于乡村隐居的诗歌中,有一个从沉思的理想到纯粹的生产性美德的理想的标志性变迁……”。(Williams,1973:55)在威廉斯看来,这个时期的“乡村别墅”诗所呈现的不再是单一的贵族秩序,而是一种交织了新旧秩序重构的处于现实中和变动中的未定型的秩序,体现出“介于一种旧秩序与新秩序之间的情感纠葛(混乱)”,(Williams,1973:58)同时也蕴含着中产阶级的一种折中式的理想:既期待社会的变迁,又抵制资本主义掠夺式的“进步”。这些作品和早期“乡村别墅诗”一样以对美好“乡村”的想象来批判资本主义,但是不同于早期“乡村别墅诗”的地方在于,这些作品对理想“共同体”的期待仅仅是以对美好“乡村”的记忆的方式出现的,其指向是未来,而不是过去。而在以汤姆逊的《季节》(The Seasons)为代表的作品中,“乡村书写的语调”逐渐成为“一种忧郁的和沉思的退隐”,(Williams,1973:71)以朗赫恩的《乡村正义》(The Country Justice)为代表的作品则“将抗议转化为回忆,直到我们死于时代”。(Williams,1973:83)至此,面对英国农村的日益资本主义化,美好“乡村”尽管还是对现实的一种“抗议”,但这种抗议彻底隐匿于人们的“回忆”结构中。“乡村别墅诗”要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抵制、对抗,需要更激进的文学方式。克雷布的“反田园诗”(counterpastoral)正是这样的代表。威廉斯以《村庄》(The Village)为例指出,克雷布制造了令人愉悦的乡村与真实乡村之间的区别,其关于痛苦的描写对抗于“田园诗”对快乐的描写:“克雷布的价值结构实质上是清楚的:因为它对建立在暗含的坦率、正直标准和负责任的生活基础上的关怀与同情有着强烈的坚持,因此它是18世纪的人道主义。”(Williams,1973:93-94)
以马维尔等人为代表“乡村别墅诗”的流变时期,是一个真正的过渡时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现实较量充斥在这些作品中,共同勾勒了这一时期复杂多变的文化冲突:既有对“乡村”的赞美和怀旧式的“记忆”,也有对“乡村”现实苦难的揭示;既有对资本主义的象征空间——“城市”的赞美,也有对它的批判。这个时期文学中的“乡村”如同现实乡村一样,其内部充满了各种异质文化的较量。
(三)“幸存的乡下人”:“乡村”空间的多维文学呈现 随着资本主义和城市的不断扩张,从19世纪后期开始,乡村英国已经附属于城市了。但是大量关于乡村过去的情感和文学中的乡村经验仍然得以存留,甚至被强化和复杂化。
威廉斯首先注意到了一种资本化的“乡村别墅”形态。在他看来,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和简·奥斯丁等人的乡村别墅已经“不是属于土地而是属于资本”,对它的文学呈现不是为了理想化更早的乡村别墅,而是让读者感受乡村的资本主义化。在这些作品中,“别墅是这样的空间,在其中,在其他地方筹划而未完成的重大事件短暂而复杂地出现。”(Williams,1973:248-9)这是对“乡村别墅诗”和“乡村别墅小说”的延续和瓦解,其延续的仅仅是这类文学作品的题材形式,其瓦解的则是对“乡村别墅”的理想化:“乡村”不仅不可能成为抵制资本或城市的空间,反倒成为后者的另一种空间符号或形式。但是,“乡村别墅小说的真正命运在于其向中产阶级侦探故事的演化”。(Williams,1973:249)中产阶级侦探故事中的“别墅”空间是“工具主义的”:它有时候是“关于传统居民的人性的中产阶级幻想”,有时候是城市人“临时的休憩空间”,有时候是“犯罪计划或阴谋活动或机密政治的一个中心”,“具有非实际功能的任意性和无关紧要性这一品格”。(Williams,1973:249-50)在此,以“乡村别墅”为代表的乡村空间完全衍化为一种文学符号,其在作品中的形态和功能完全取决于作家对“侦探故事”设置的需要,是“乡村”现实混乱与作家创造设想的产物。侦探故事中的“乡村”既不可能成为抵制资本或城市的理想化空间,也丧失了和资本或城市相对抗的能量;“乡村”彻底成为“城市人”的游戏符号或游戏空间。不过,正是这样一种文学化或符号化的游戏空间潜在的揭示出:资本或城市凯旋中“幸存”的乡村所具有的前所未有的复杂性。
另外,文学对“乡村”的呈现还表现为一种“传奇”性乡村形态,这是在“对乡村空间和人的描写在日记和回忆录中建立的最成功的模式”。(Williams,1973:254)这种乡村形态是“准知识分子的”(sub-intellectual)一种想象。威廉斯细致梳理、解读了W.H.哈德生、约翰·德林瓦特、爱德华·汤姆森等人的作品以及著名的《乡下人》(The Countryman)杂志和一部名叫《乡下人图书》(The Countryman Book)的作品选集,认为这些作品中所塑造的“传奇”性的“乡村”从根本上是适合于这个时代和特定阶级的需求而“想象”出来的,体现的是一种“外在的先入之见”的创造旨趣,其蕴含的潜在模式就是通过这种“传奇”性乡村来对“现代生活全部领域”进行“批判”。“传奇”式乡村空间的构建,表面上似乎是一种现实的记录,但实质上蕴含的是资本化或城市化世界中,中产阶级的价值趣味和意识形态。然而,“传奇”式“乡村”仍然不是19世纪后期以来“乡村”故事的全部。威廉斯简要分析了一个现代农场工人的自传:弗雷德·吉钦的《牛兄弟》(Brother to Ox)。威廉斯指出,《牛兄弟》是关于“幸存的乡下人的真实声音”,现实乡村“被精明地观察而没有阶级的先入之见”。(Williams,1973:262—3)这部作品对乡村劳动者生活十分罕见的直接而无中介的记录是“城市化”世界里“幸存的”乡村空间的真实呈现,其体现的是处于艰难变迁中的劳动者的情感立场和理想期待。
综上所述,英国现代文学中的“乡村”空间不是固定不变的地理空间,而是随着社会历史变迁而蕴含不同情感结构的“文化革命”空间;并且,这些不同时期的“乡村”空间本身也蕴含着不同的异质性文化力量的较量。
三、城市:“文化革命”的文学新空间
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在19世纪中期就取得了城市对乡村的支配性地位,因此城市经验是英国人现代经验的重要构成。威廉斯对英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勾勒了三种主要的“城市”空间形态及其情感结构的变化。
(一)“庞然大物”:“乡村”视野下的城市空间 “城市”的文学呈现,一开始是伴随人们对美好“乡村”的留恋而出现的。强大的“田园”情结,使作家在呈现“城市”空间的时候,即使体现出新的都市风格,也不由自主地蕴含传统的乡村姿态。
以对“伦敦”的文学呈现为例,威廉斯发现:“巨大的拥挤城市”(Great Wen)、“庞然大物”(monster)、不健全的“拥挤城市”(wen)等意象在伦敦的持续扩张中被反复运用于文学之中。“庞然大物”作为城市的核心或代表性意象意味着相对于乡村的闲适,城市是拥挤的;相对于乡村的宁静,城市是扩张性的;相对于乡村的纯真,城市是贪婪的。城市是“田园意象缺场”的空间,是隔绝于乡村的一个“怪物”,是对乡村的蚕食与“遮蔽”(Shadow)。这是乡村视野下的城市意象,是面对古老的生活方式被新的工业体系喧嚣的发展所逐步遮蔽的社会现实所激发的一种文学上的情感反应,它所体现出的是一种“乡村防护”(defence of the countryside)意识和对资本主义的抵制意识,其根本目的是设想一个“农村英国”以反对一个“工业英国”。(Williams,1973:196)在“乡村与城市”的对立中,“乡村”空间和“城市”空间都被作了纯粹化的文学处理:乡村仍然代表着“有机共同体”的复活,城市则象征着“共同体”的死亡;乡村成了实现革命的手段和目标,城市成了革命的缘由和对象。威廉斯的研究揭开了披在这种文学呈现上的意识形态面纱,并揭示出这种单向式呈现本身也蕴含着异质文化力量的冲突。
(二)“黑暗”与“光明”:城市空间的现实呈现 现代城市的真实状况是怎样的呢?威廉斯认为,这需要“现代城市中的双重定位”。(威廉斯,2002:60)不拘泥于“乡村”立场来看城市自身的状况,城市成了一个充满矛盾的“复合体”,城市在文学的现实呈现中体现为“黑暗之城”和“光明之城”。威廉斯对比分析了布莱克的《伦敦》所展现的“黑暗之城”和勒·迦廉的诗歌中象征“光明之城”的“灯”意象。威廉斯认为,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在17世纪早期,就存在着重要的内在分裂:西部地区属于贵族庄园,东部地区逐步成为工业城市。结合“伦敦”自身的这种内在分裂的历史状况,威廉斯梳理、研究了对城市的“黑暗”和“光明”在文学中的呈现,指出吉辛、莫里森以及其他一些作家把城市排除在“黑暗”空间的传统意象之外,就如同存在着另一部历史一样。威廉斯说:“黑暗、压抑、犯罪和卑鄙、人性降低的城市,当然也被不同地表达……因为城市仍然可以被看作一座光明之城。”(Williams,1973:228)
“光明之城”意味着以伦敦为代表的现代城市带来了一种新的人类的意义,一种新型的社会,新的城市性格和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新关系。这样一种新型生活空间、这样一种充满各种异质力量的空间,不仅被不同的作家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而涌现出不同的城市意象,而且这些矛盾的城市意象往往还共存于一部作品中。最能体现城市多样性、复杂性的就是狄更斯。不论在《乡村与城市》中,还是在《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中,威廉斯都用了大量篇幅对狄更斯进行研究,尤其是研究其笔下的“伦敦”。威廉斯认为,狄更斯的小说最终确定了我们必须看见的城市的双重状况:随意的和成体系的、可见的和模糊的,这是城市的真正意义。狄更斯不是站在城市之外观察城市,而是从街道上匆匆忙忙的男男女女的视角出发内在地观察城市,他对城市的经验就蕴含在这些普通男女匆忙的“随意”中,蕴含在他们“混杂的措辞”中。狄更斯的独创之处就在于他以“属于城市的观察”而不是非城市的观察来体验城市、描写城市、讲述城市,从而把城市自身的矛盾、悖论吸纳在他所讲述的故事中甚至讲述故事的形式中。(Williams,1984:34-35)狄更斯在其创造的城市空间中十分准确地呈现了工业革命过程中人们所触及的“选择的危机”:他描写了变化中的混乱,但不仅仅是变化的动荡,也有新秩序的浮现。这种动荡和秩序的交错往往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冲突,威廉斯以狄更斯的《董贝父子》为例分析了“城市”空间中所蕴含的伦理冲突和变化。我们从威廉斯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狄更斯的小说不仅揭示了变迁时代城市生活的矛盾和悖论,而且体察到了这样的城市空间中以伦理为核心的文化变化和冲突。
然而在威廉斯看来,狄更斯固然对城市空间的文学呈现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了过渡时期的城市状况,但没有把握住复杂的城市空间自身所蕴含的革命力量。他的小说和那些呈现了城市的“黑暗”与“光明”的其他人的作品一样,都没有预示出城市成为新的“共同体”的可能。
(三)“聚集”:作为革命新场所的城市空间 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是资本主义迅速扩张、城市迅速膨胀的时期,也是最能凸显城市经验的时期。其中最为独特的城市经验就是“聚集”(aggregation)。19世纪中后期开始,城市无可争议地成了支配性的生存空间,“即使为了反抗和抵制城市,人们也来到城市;不存在其他准备好的途径”。(Williams,1973:229)在城市的“聚集”中,哈代、华兹华斯、卡莱尔、柯勒律治和骚塞等人感受到了一种“集体意识”和共同情感缺席的“孤独”。(Williams,1973:215)但是,城市中孤独的、个体的意识却具有走向群体、集体意识的可能性。而这种“人的团结”的新的可能性早在华兹华斯那里已经初显端倪:“在那巨大城市的/大众之中,经常可以看见/动人地提出,人们的团结/比其他地方更有可能。”(威廉斯,2002:62)在威廉斯看来,新的都市文明孕育着可以被更加认真言说的东西:社会思想和社会组织的有特色的新类型正在其中被创造着,新的民主形式和思想正在决定性地扩大。威廉斯以威尔斯的《托诺·帮盖》(Tono-Bungay)为例进行了分析。威尔斯描写了一座城市和一种文明的不健全的形态,但这个“怪物”现在不是恶魔似的,它具有一种更加有人性的形态,其作品呈现了“反对城市的一条新途径”:不是通过怀旧式的纯真,而是通过有意识的进步——通过教育、科学和社会主义,
这条途径不仅不依赖于对乡村秩序的一种理想化视野,而且恰恰把那种秩序看做是病症的组成部分。……存在着反抗它的可利用的充满活力的现实力量:这些力量被新的文明中的能量所释放,却被一种虚假的社会秩序所抑制。(Williams,1973:230)
由此,城市的聚集带来的不仅是个体的聚集,也使得城市空间存在各种争取民主和教育的斗争以及成长中的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并且作为一种新型社会,它超越了对于新的且充满活力的和睦与亲密的表达:合作社、社会主义进而新的城市”。(Williams,1973:231)在新的大都市的混乱和不幸之外,对社会的新憧憬的文明力量已经在斗争中被创造出来,这力量汇聚了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的苦难和希望。
另外,“聚集”中的“集体意识”在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往往以表面极端个体化的形式来呈现。威廉斯通过对波德莱尔、陀思妥耶夫斯基、T.S.艾略特、弗吉尼亚·伍尔芙、乔伊斯等人作品的细致分析,独特而深刻地发掘出现代主义所蕴藏的“集体意识”。(Williams,1973:246)在威廉斯的解读中,现代主义的城市空间和“传奇”式乡村空间形成了互文性的联系:以极度的主观个体方式来隐匿“集体意识”并传递一种形而上的“共同体”,在“传奇”式乡村中寄寓一种“共同体”设想,这在根本上是相通的——都暗示出对急剧膨胀的“城市”空间的焦虑情结,蕴含着对新的“共同体”的期待。这样,“城市”,在城市获得支配性地位的历史语境下,成为孕育各种冲突、斗争的主要空间,成为人类新的“共同体”的滋生场所。
同时,由于“城市”成为主导性的生存空间,成为孕育新的“共同体”的场所,进而“城市”也就成为人们对未来构想的场所。威廉斯指出,在大都市经验的危急时刻,城市经验转化为一种“未来经验”,导致了关于未来的故事的本质变化。威廉斯注意到,在传统模式中,人们关于未来(或死亡之后)的空间设想往往是天堂或地狱;而在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关于未来的设想往往是“新的被发现的土地”、“新的岛屿”等。这些模式在大都市经验中被广泛吸收和改造而成为理想的“城市”空间的未来形象。威廉斯以威廉·莫里斯、H.G.威尔斯、赫胥黎、奥威尔等人的作品为例展开细致的分析,认为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关注作为大都市经验的新的集体意识,虽然他们对未来城市的构想有差异、有变化,但潜在的联系和相通在于:都期待或憧憬未来的“城市”是融汇了乡村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空间。而这样一种新的文明空间的构想直接影响到所谓的“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中对未来空间的想象。这些“小说”对未来城市的想象有两种趋势:一种是在“对文明的一种独特想象”中,文明超越了“都市和科技阶段”,人们生活在将城市、科技、工业等“内在化”的“田园空间”;另一种则是对城市自身的“一个深刻的悲观规划”,“乡间不复存在”,城市成为正在遭遇各种灾难的封闭运行空间。(Williams,1973:276—77)“科幻小说”所想象的两种未来城市的形象看似矛盾,但本质上是相通的:前者是人们对未来城市的理想化设想,后者是对城市现实命运发展到未来的恐惧和担忧,二者一正一反,传递出城市必须融合乡村才能成为理想空间的心理期待。或许正因为如此,威廉斯声称:
这些关于未来城市的小说(fiction),在精神上同长期的田园小说(fiction)相互影响。但是在田园诗的发展中,存在着远离乡村生活现实的运动,在这样的城市小说(fiction)中,出现了十分不同的作品的明显交叉:……在其中,在一个令人吃惊的新领域中,城市和乡村都已经被赋予新的而且起先几乎不被承认的界定。(Williams,1973:277—78)
文学中的“城市”空间和乡村一样,都不是纯粹的、单一的、静止不变的地理空间,它本身就充满了各种异质力量,这些异质性因素伴随社会变迁,逐步从遮蔽走向敞亮,从不可知走向可知。由此,威廉斯研究视野下的城市就成为他以“文化革命”为核心的“长期革命”的文学新空间。
四、“边界”:城乡交错空间的文学呈现
在英国现代社会的变迁中,存在着一个城乡交错的“边界”(border)空间。它既是乡村向城市过渡的地理空间,也是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过渡的文化空间。威廉斯对英国现代文学中“边界”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般人所谓的“地方小说”(regional novel)中。对这类小说,威廉斯赋予了一个更准确的名字“边界乡村小说”(border country novel)。而小说(novel),在英国作为一种主要的文学形式,本身就是“工业革命、民主斗争、城镇的增长”的现代社会的一种产物,(Williams,1984:9)这预示着:小说离不开对现代社会的象征——城市的关注,小说即使在呈现“乡村”经验的时候也会将视角触及城市。“边界乡村小说”正是强大的乡村文学传统与小说同城市密切的内在关联的一个产物。
在威廉斯的研究中,属于这类小说创造的主要作家有乔治·艾略特、托马斯·哈代、D.H.劳伦斯以及L.G.吉本。威廉斯将乔治·艾略特同狄更斯等进行了比较分析。乔治·艾略特和狄更斯一样,也都把自己的小说建立在一种“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上。不过,狄更斯小说所依赖的“社会形态”是
建立在一种城市文化上,这种城市文化在它自己的力量和软弱的混合中具有一种可以利用的、一种直接交流中的措辞。但是,乔治·艾略特的“社会形态”最多只是新兴的:一种对我们自己世界的联系的承诺,在这个世界中,其每一个分裂过程都已经越来越遥远和深入……。(Williams,1984:79)
也就是说,狄更斯的小说是对一种已经成形的社会形态——城市文化形态的呈现,而艾略特的小说则是对正在成形中的社会形态——城乡联系、冲突、较量过程的呈现。以对“方言”的分析为例,威廉斯注意到,小说家的方言(idiom)在艾略特作品中不仅属于人物,也属于作家,体现出情感与意识的组合,“这样,在小说的文本结构中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分裂:在小说家的叙事风格与她的人物的被记录的语言之间;在分析风格与对情绪(情感)的压倒性强调之间。”(Williams,1984:80)艾略特的小说世界被拓展到了农民和工匠的世界,这个世界曾经是属于她的世界,可她自己已经接受了另一个世界的教育(城市文化、“官方英语文化”)。由此,艾略特的“方言”问题实际上蕴含的是变迁中的城市和乡村的矛盾与联系问题,蕴含的是一个曾经的乡下人如何在经历城市文化的熏染后表达正在转向城市的乡下世界的问题。
哈代是“边界乡村小说”更重要的代表,“他写作于这样一个时期:当仍然存在着乡土共同体的时候,这个时期也存在着一个可见的且作为一个整体的强有力的社会网络:法律和经济;铁路、报纸和邮政;一种新的教育和一种新的政治学。”(Williams,1973:197)威廉斯认为,哈代既不是完全属于工业化世界的人,也不完全是古老乡村英国或农民的代表,他是一个变迁世界中的人,其“边界乡村”是一个变迁中的文化空间。哈代作品的复杂性源于其处于激变时代的身份的双重性:“他既是一个有教养的观察者,又是一个多情的参与者。”(Williams,1973:202)威廉斯对哈代的多部作品进行了解读,以分析其呈现的“边界”空间的复杂性。其中对《德伯家的苔丝》中的细节的分析是十分深刻而有趣的。例如,苔丝去火车站将牛奶送往伦敦去时的场景描写:在苔丝把牛奶送到火车站的时候,作者首先通过苔丝的眼睛勾画了火车站附近不同的景物、场景,进而是苔丝的一段问话。(Williams,1973:208-09)在这个场景中,“火车”是一个重要的意象,它不属于“乡村”,也不完全属于“城市”,它是城市和乡村的纽带,其蕴含的是城乡之间一种全新而真实的联系。但是,在苔丝的问话中,有好奇、有期待、有淡淡的忧郁,这些复杂的情感似乎又昭示着这样的联系仅仅是表面的,昭示着对城乡之间更为深刻的联系的期许。在威廉斯的细腻解读中,哈代的“边界”空间不只是一个物质的、地理的“边界”,更是一个充满内心复杂情愫、充满价值矛盾和联系的精神生活的文化空间。
对于D.H.劳伦斯,威廉斯明确宣称他“生活在一个边界上,这边界不只是处于农场和矿山之间……他处于一个文化的边界(a cultural border)上”。(Williams,1973:264)在劳伦斯的作品中,“农耕生活”固然被看做是“生命”的象征、“肉体对抗精神”的隐喻,“工业主义”及其各种形式被看做“死亡的符号”。但是,威廉斯认为劳伦斯反对“工业主义”的东西“不是一个农业共同体(farming community)”,相反,威廉斯发现了劳伦斯对城市的颂扬:“伟大的城市意味着美好、高贵和一种确切的显赫。……当我们赞许我们伟大的文明形式的时候,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镇。”(Williams,1973:266—67)劳伦斯不仅像哈代那样以“边界”空间真实地呈现处于变迁时期的城乡冲突和联系,而且在呈现中把这种城乡的真正联系指向未来:理想的生存空间既是城市的,也是乡村的,这或许是由现实“边界”理想化孕育出的一个新的“边界”生存空间。这样的“边界”呈现和理想,蕴含的实质是什么呢?威廉斯深刻地指出:
劳伦斯经常犹豫于一种革新思想与一种革命思想之间。他对未来的强调胜于对过去的强调,并且变化是绝对的,是源和流。但是,他把有效的革命运动看作有关所有权的简单斗争;他需要一种不同的憧憬,一个崭新意义的生活,在他做出承诺之前;否则,它将不是革新而是一种最后的崩溃。(Williams,1973:266)
劳伦斯固然把理想指向了改善的乡村或改善的城市,指向了未来的城乡融合,但是在威廉斯看来,“革新”与“革命”的犹疑,尤其是对“革命”的简单理解,最终导致的是劳伦斯理想“共同体”的崩溃。
此外,威廉斯十分看重苏格兰作家L.G.吉本的“边界乡村小说”。威廉斯细腻地解读了吉本的三部曲小说《苏格兰的书》(A Scots Quair)。在吉本的作品中,对“黄金时代”的描写既不是对这个时代的留恋,也不是把理想寄托于其中,而是为了烘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代进程的悲剧性。在作品中,对土地和劳动的神圣情感,潜伏于对新的斗争的强调:“历经在《洼地阴云》(Cloud Howe)时期的总罢工到《阴郁的冷漠》(Grey Granite)时期的饥荒边界……少数农夫、工匠和工人极端的独立性被看作向工业工人战斗精神的过渡。”威廉斯注意到吉本对时代变迁过程中的“革命”的重视,他在简要分析作品中的一个“未被理想化的革命者,正视困难和缺点的革命者”形象的基础上,指出,吉本的小说“在比其他任何一部展现30年代活跃的劳工运动的小说都更好地表现了劳工运动”。(Williams,1973:270)在威廉斯看来,吉本对“边界”空间中“劳工运动”的现实呈现是对整个“乡村文学传统”的“一个批判性的背离”,其作品以“边界”空间中艰难而剧烈的变迁展现了“长期革命”的历程。
威廉斯对英国现代文学中“边界”空间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的发现,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英国现代文学传统中“乡村”经验和“城市”经验在社会变迁中的关联性,丰富了英国现代文学传统的空间经验。
从“乡村”、“城市”、“边界”三种空间形态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历史演变出发来勾勒英国现代文学地图,并在这种勾勒中潜在的寄寓对现实生存空间的批判,对理想生存空间的期待,对新的“共同体”的憧憬,这是威廉斯文化(文学)批评最重要、最具有特色、最有价值的构成部分:一方面,对文学的空间批评从一个崭新的角度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激进立场,是威廉斯改写传统“左派”话语,实现“个人学术立场与公众政治立场的结合”(Gable,1989:ix)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这种批评突破了文学的传统研究模式,为当代“空间批评”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实践开创了范例。
注释:
①“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是威廉斯思想中的一个基本主题,参阅刘进《“文化革命”与威廉斯的写作主题》,载《上海文化》2006年第3期。
标签:现代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雷蒙德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小说论文; 狄更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