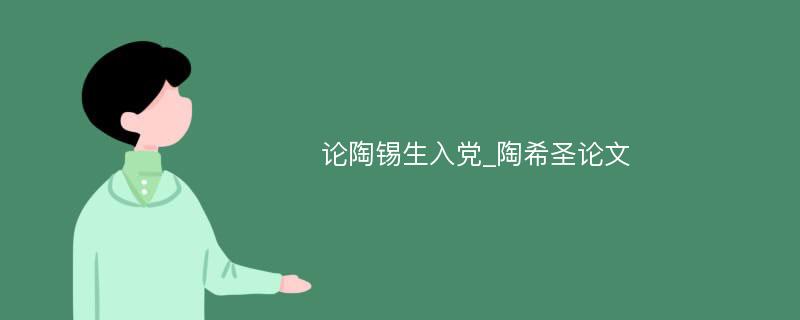
有关陶希圣加入中国共产党问题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陶希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10-0096-05
在以广州为发源地的国民革命运动中,陶希圣曾接近左翼,后来更是弃笔从戎,成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据一些书籍记载,陶希圣这段时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贤庆、陈贤杰主编《民国军政人物寻踪》一书的“陶希圣”词条下,有陶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脱党一说。[1] 陈予欢编著《黄埔军校将帅录》中也有类似记载:“陶希圣1924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上海大学教授,1927年脱离中国共产党。”[2](P1327) 此外,李克义在《沈雁冰与黄埔军校》一文中也提到,“沈雁冰受武汉分校筹备人之一、共产党员包惠僧委托在上海为武汉分校招生。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物色了陶希圣、吴文祺、樊仲云等三名共产党员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并在陶、吴、樊三人协助下,经过两个星期的招生工作,从一千左右投考者当中录取了男女学生两百多名”,[3](P144) 等等。
陶希圣是中国现代史上政学双栖的风云人物,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社会史大论战”中充当要角。他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在3年内销了8版,影响甚大,被唐德刚誉为“开创学派的社会史教授”。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陶希圣弃学从政,加入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逐渐成为国民党核心权力之要角。他因公布日汪密约和代书《中国之命运》而名噪一时,是国民党中常委、立法委员,出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主笔等要职。如果陶希圣早年加入过中国共产党,说明陶与中国共产党有段不同寻常的关系。澄清这段史实,有助理解陶希圣早年的心路历程。
一、1924年陶希圣有无入党可能
上面引文有两处提及陶希圣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第三年,组织形式仍属于秘密状态,人数尚少。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三大”召开时,党员总数只有420人,大都是职业革命者,他们往往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献身精神。如果陶希圣是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首要条件是他本人具有共产主义信仰,提出入党申请,并有一群志同道合者。
1923年12月底,陶希圣因看不惯学校闹学潮引发的派系争斗,辞去安徽法政专门学校一职,从安庆返回湖北家乡黄冈仓埠镇。1924年上半年,陶希圣为维持生计在仓埠镇和武昌之间奔忙,他和亲友计划经营一家长途汽车运输公司,但告失败。正当陶希圣消沉时,忽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聘书,陶不假思索匆忙乘船赶往上海,此时已是7月。在5天的水路中,陶希圣不胜感慨:“我在本乡是青年绅士,游武昌是世家公子,至上海是‘人海茫茫’中之一个求职雇工。”离开故乡的陶希圣不到25岁,说不上有什么远大政治抱负。在上海,陶希圣先后投宿三地,最初寄居北大同学韩觉民家。陶说:“韩觉民是中国国民党党员,似乎跨着共产党。他与恽代英共同参加建设杂志的编辑部。……恽代英时常到韩家来,每次只在骑楼的窗口之下,低声对韩觉民说一番话就走,从来不坐下,亦不与希圣接谈”,“我的床位与桌位在骑楼这一头,自然听不见,也不愿去听”。如果陶希圣这年加入共产党,恽代英不必刻意与陶疏远,陶希圣也不至于“疑虑到韩觉民也与共产党有关系”,[4](P65) 而对他们的交谈产生避开心理。不久,陶希圣就借口以“往返不便,迁居宝山路宝兴里傅东华寓所的三楼”。[5] 浙沪战事发生后,陶为安全计搬入公共租界五马路一家报关行楼上的小房栖身。
这段时间,陶希圣自称过着“每天上工放工的雇工生活,无善足陈”。为积攒家用,陶希圣勤奋工作,编校了6本书,曾下苦功研究法学与民俗学,撰写《丧服之本则与变则》论文发表,还利用晚间加班,“做了将近一个月的夜工,得到稿费一百元”。有了这笔钱,陶希圣便“斗胆回乡,决心搬家眷到上海”。[4](P66) 经过一番周折,陶终于将妻子儿女带到上海安顿下来,陶希圣深有感触地说:“从此以后,我们是失去家乡生活根据的都市人海里的漂泊之人,只有努力向前撞。”[4](P66) 此时已是1925年初。
在经济上,陶希圣也无能力关心一个要缴纳党费的组织。当时党的经费严重不足。1924年9月陈独秀说过:“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工作处于荒废状态。”[6](P529) 按照党的规定,凡在社会上兼职的共产党员,必须要把其中一部分薪水拿来交党费。当时陶希圣的家境十分清贫,一家四口只靠陶的微薄薪水,“每月收入平均是七十元。其中一半,送给北四川路内山书店偿还书账。剩下的半数为家庭生活的用途。白米一石不过八元,每日菜钱可以省了再省,最感困难的是柴价太贵。冰如(陶太太——引者注)受了两三个月的生活的磨练,学会了只用一根柴,便可烧好一餐饭。”[5] 如果没有政治信仰的支撑,陶希圣是没有余力顾及一个仍处于秘密状态的政治组织的。
直至1925年5月前,陶希圣除了为养家糊口奔忙外,全部兴趣和精力均放在他的学术天地。[5] 陶勤勉治学,由此总结出心得:“我深信治学要由博返约,好学深思,我深信做学问要虚心,留心,用心”,“仿佛行路,目的地是在远处,决不半路停留,必须全心全意全力向前进,不到达目的地不止。”[4](P70)
从陶希圣的思想倾向和主要活动来看,1924年,看不出他有加入共产党的动机,陶没有什么党朋交往,甚至他本人对社会政治也不大关心。事实上,也从没发现陶提出入党申请的历史文献。
二、沈雁冰是否介绍陶希圣入党
身在书斋的陶希圣开始“对一般社会与政治情况,渐次留心”,是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之后。五卅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促进民族觉醒与个人觉醒的两大政治事件之一,对陶希圣的思想和生活都有重大影响。枪杀顾正红惨案发生后,陶希圣援引英国普通法,评论英国巡捕枪击群众之非法。文章刊出后,引起各界人士的注意,英国领事甚至要指控陶希圣有辱大英帝国尊严,上海学生联合会则立即聘请陶希圣为他们的法律顾问。这篇影响极大的文章发表在郑振铎主编的《公理报》上,沈雁冰恰好是该报编辑,沈雁冰还是陶希圣的商务印书馆同事,两人之前相识并有往来。从1925年10月至次年4月,沈雁冰还担任中国共产党商务印书馆支部书记。李克义一文曾提及陶希圣和沈雁冰的特殊关系,这不由引起猜测,莫非沈雁冰介绍陶希圣入党?我们不妨看看他们各自参加的社团,并从中分析他们的政治取向。
五卅运动后,时为全国书刊出版中心的上海,迅速成为社会运动与思想运动的推进地,全国两大书馆之一的商务印书馆更占重要地位,集萃其中的文人学者组成各类社团或党派。陶希圣加入“孤军社”,它由陶的同事何公敢创立。“孤军社”自认为是国共两党以外的一个政团,思想倾向国家主义。陶希圣和“孤军社”成员周佛海、梅思平(梅也是陶的同事和北大校友)志趣相投,遂成好友。他们的非一般关系维持到40年代,各自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五卅运动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迅猛发展,导致各种社团急速分化。“孤军社”的左翼成员参加郭沫若的“创造社”,右翼则加入何公敢、周佛海等成立的“独立青年社”。鼓吹民族主义、民主政治和工会主义的“独立青年社”与“创造社”互为对抗。陶希圣加入“独立青年社”,并任该社《独立评论》主编。[7]
笔锋犀利的陶希圣很快崭露头角,他在《独立评论》周刊上,打出“民族自决,国民自决,劳工自决”三个口号。所谓民族自决,与右翼醒狮派推崇的国家主义有别;所谓国民自决,即是民主主义;所谓劳工自决,乃是反对“职业革命家”提倡的工会运动。[7]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认为陶希圣的“三自决”主张,符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力劝陶加入中国国民党。这是陶希圣接近国民党的第一步。[8]
再看沈雁冰介绍商务印书馆职员加入共产党的名单中,并没有陶希圣的名字。1926年4月沈雁冰离开商务印书馆,同年10月,陶希圣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9] 我们不好断言陶希圣加入国民党就一定不会加入共产党,判断陶希圣是否中国共产党党员,关键看他是否具有共产主义信仰。那么,沈雁冰日后是陶希圣的志同道合者吗?1927年1月,陶希圣辞去商务印书馆编辑一职踏上军旅之途,出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一职。依李克义一文所言,陶这一选择是出于沈雁冰的“物色”。
据陶希圣本人叙述,当年之所以弃学从戎,投身以广州为发源地的国民革命运动中,是好友周佛海的推荐。[5] 1926年秋,脱离共产党的周佛海由戴季陶介绍给蒋介石,蒋派周参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筹办事宜,并任命周佛海为军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军衔为少将。周佛海于是推荐好友陶希圣、梅思平和吴文祺为政治部教官。[5] 如果说仅凭当事人一说难免为孤证,那么,关于周、陶关系,当年担任过武汉分校政治部科员、军校刊物《革命生活》日报主编罗君强的回忆可为佐证:“陶希圣原是北京大学读法科出身,以后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编辑,由周佛海介绍到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当政治教官。”[10](P43-59)
我们再来看沈雁冰。沈与陶希圣几乎同时抵达武汉,同时被(校长蒋介石)任命为武汉分校政治部教官,他们军阶同级。李克义说的“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物色了陶希圣、吴文祺、樊仲云等三名共产党员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一句,不仅用词不当,与史实记载也有出入。至于李文说:沈雁冰“在陶、吴、樊三人协助下,经过两个星期的招生工作,从一千左右投考者当中录取了男女学生两百多名”的说法也不准确:其一,1927年1月陶希圣接到聘书后,立刻定船票,一家人启程前往武汉,并于同月抵达武汉。[8] 在这么紧迫的时间内一家五口迁移武汉,期间似乎没有充裕时间协助沈雁冰开展两个星期的招生工作,况且陶当时并不清楚军校的情况,甚至对国共合作的情形也知之不多,只是在启程前,匆忙“访问好几位国民党友,从他们的口里,得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及其现状。”[5] 其二,武汉分校的招生工作和广州黄埔军校本校的招生一样,由专门的招考委员会负责,其成员是:邓演达、陈公博、郭沫若、李汉俊、董必武、包惠僧、王乐平等。因此,不太可能由沈雁冰在陶、吴、樊三人的协助下,“录取了男女学生两百多名”,何况当时报考武汉分校达6000多人,最终录取986人。
从陶希圣和沈雁冰各自参加的社团和政治取向来看,他们显然不是同路人,而且他们之间似乎也不存在某种特殊私谊,沈雁冰介绍陶希圣入党的推测看来也不能成立。
三、另一种可能
五卅运动后,陶希圣开始以文字、演讲的方式参与革命。1925年秋,陶希圣经同事介绍,在上海大学兼职授课。上海大学素被认为是吸收中国共产党党团员和培养干部的机关。那么,陶希圣是否是在上海大学期间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并加入到党组织?上海大学为国民党所创办,校长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副校长邵力子、总务主任韩觉民均是跨党成员(即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中国文学系主任陈望道、社会学系主任施存统、社会学系教授李季、高语罕、蒋光赤、尹宽、王一飞、彭述之和郑超麟等则是中国共产党党员,[11](P227) 其中的邵力子、施存统、陈望道等还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创始成员之一。当时的上海大学,确实如陶希圣所言,“差不多是共产党的党校”,但陶希圣同时也称它为“中国国民党的前哨”,“上海大学学生秘密转往广州,致力党务,尤其投身黄埔军校者,络绎于途。”[4](P81)
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时期的产物,集萃了不少国共两党精英。类似的情形还有,《民国日报》两个主笔,左派邵力子和右派叶楚伧;编辑中,张太雷、沈泽民是左派,陈德征等是右派。同一机构有两党同人共事是常有的事,事实上,国共两党的要人也常在不同党派之间走动。① 但此时的陶希圣只是一位来去匆匆的任课教师,既不参与学校的党派活动,也不关心校内出现的两党纷争言论。
当时也确实有人说陶希圣是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陶希圣曾叫家乡的佃农叶进山到武昌,陶告诉叶说:“田地对于我没有帮助。我也决意不靠家产为生计。请你们把我自己应得的一份田地分了吧!”当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两湖农民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陶的家族于是怀疑陶希圣加入共产党。陶的三叔公一家到汉口,陶希圣去拜见时,他的三叔公劈头就是一句“你回来了,你做共产党了”。[5]
陶希圣被误为共产党人不足为奇,在武汉时期,陶确实和中国共产党党员、左派青年来往密切。1924年,陶希圣与恽代英还没有私人交往;1926年他们却成了同事,同在上海大学教书;1927年,他们更有上下属关系,在武汉分校恽代英是总政治教官,陶希圣是政治部教官。在平定夏斗寅反叛时,恽代英重用陶希圣。国共分裂后,遭受重创的中国共产党准备率部集结南昌,发动起义。在紧要关头,恽代英仍视陶为“自己人”,吩咐陶跟随他南下参加起义。但是,陶希圣毕竟不是职业革命者,没把自己的品性融入到严峻的政治斗争中去,他不愿跟随恽代英南下。在陶看来,恽代英是位严肃、沉默、坚定而受人尊重的总政治教官。对人没有私怨的恽代英在共产党人中素有“甘地”之称。但陶与恽似乎也只是上下级关系,没有史料显示他们有紧密的党派关系,毕竟陶希圣的政治信仰仍是三民主义。[8]
四、陶希圣是左派同情者
国民革命期间陶希圣的思想左倾,难免被人误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陶开始接触马克思与列宁的论著,是中国最早持唯物史观者之一。大革命失败后,陶希圣在《中央日报》提出“分共之后,仍然革命”的口号。陶希圣所要反对的,乃是国民党当权派因清共而脱离民众、丧失革命精神的官僚化腐败倾向。陶希圣对国民党很失望,同情共产党,他提到:“我们还常常说到中国国民党民十三的改组,还常常鼓吹革命……当民十三改组时,国民革命建立的是两大口号:一个是‘打倒帝国主义’,一个是‘打倒军阀’……那时候,我们还常说到农夫工人,现在农夫工人又到哪儿去了呢?革命已经失败了。新式士大夫已经抬头了。农夫工人已经躲到茅檐底下冻饿去了。”[12](P9-10) 陶批评国民党当权派官僚化腐败,他的思想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反对派——国民党改组派对于中国社会与革命问题的立场,其理论锋芒,直指国民党当权派官僚化引致的革命危机。② 于是,陶希圣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检举为“反动分子”。这一纷争,后经朱家骅、陈布雷和陈果夫等人的斡旋才平息下去。[13]
此时陶的政治态度十分接近中国共产党,但不能就此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国民革命时期,是现代中国党派意识形态的萌芽阶段,左右各派活动异常活跃。各种主义和政治思想也像党派一样,互相穿插和混合,各种思想流派的左与右,并不都是截然对立的。
陶希圣虽然是中国的最早唯物史观者之一,③ 但是,他同时“对于共产主义有学理的批评”。[4] 他赞同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社会,但他反对照搬马克思关于欧洲的研究成果到中国。陶希圣同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和“第四阶级革命论”等,这些观点与右翼的醒狮派是一致的。
陶希圣尤其不同意中国共产党的苏维埃革命,不赞同农村暴动和阶级斗争。早在1925年,陶就撰文指出:中国社会不是封建社会,中国还没有分化出极端对抗的阶级,没有阶级性何来阶级斗争?当时理论上区分中国共产党与非中国共产党的标准,主要看是否赞成阶级斗争。从陶希圣的思想倾向看,未能得出陶信仰共产主义的结论。陶希圣始终认为“三民主义为中国革命之主流”,中国的社会问题,可以通过民族、民权、民生三方面来解决。[4] 其实,在深层意识中,陶希圣属于自由派知识分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社会政治关系左至共产主义,右至国家主义,可以说是广泛。但是我的社会政治思想路线,左亦不至共产主义,右亦不至国家主义”。[4](P81-82) 陶希圣只能算是一个持三民主义的左派同情者。
1927年分共后一段苦闷而茫然的时间里,陶希圣与许德珩、刘侃元、黄克谦、邓初民等人来往密切(他们都任职于陈公博任主任的武汉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结识了一批左派青年知识分子,并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有较多的接触,但并没有加入党组织。陶希圣在《潮流与点滴》一书追忆道:“施存统有次告诉我:‘共产党未拉你入党,是留下一个左派,在党外与他们合作。’”[4](P141)
陶希圣之子陶恒生先生就其父亲是否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问题曾对笔者说过:“在先父生前言谈、著作、母亲的回忆(《逃难与思归》),与我们兄弟姐妹的了解之中,并无蛛丝马迹足以证明其事。”他还说:“……当年先父回乡,他的三叔公见他言行叛逆不满现实,劈头说‘你回来了,你做共产党了。’几十年后的1946年,我在南京念高中,因北平发生‘沈崇案’,全国民众反美情绪高涨,各地学生纷纷串联组织‘抗暴联合会’、‘抗议美军驻华暴行联合会’,发表宣言扩大反美斗争,又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公开反对美援。后来又举行‘反饥饿大游行’、‘吃光运动’等罢课运动,集体前往国府门前抗议。这些运动,血气方刚疾恶如仇的我,几乎无役不与,且在校中与同学张贴壁报批评当道。一天我参加游行很晚回家,父亲见我神色亢奋豪情未消,似笑非笑地说:‘你回来了,你做共产党了。’当时谁不反对政府?谁不讨厌国民党?谁不向往共产党?可谁又真正是共产党员呢?”
综上所述,从陶希圣的活动经历和政治思想看,我们既找不到陶希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动机,也看不出陶有过共产主义信仰,更没有发现陶的入党具体时间、介绍人和地点等历史文献。我们确实还无法证明陶希圣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有进一步发掘出相关的史料,这个问题才可能有盖棺论定的说法。
注释:
① 如中共创始人并参加中共“一大”的陈公博、周佛海,常在国共之间来回走动。像戴季陶、吴稚晖这样的极端反共者,当初也是社会主义的信奉者,甚至戴本人还是当时屈指可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
② 陶希圣于1928年12月加入国民党改组派,全称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这是一个拥汪为领袖的派别,以“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改组国民党”为口号,坚持国民革命必须以三民主义为不二法门。
③ 知名史家何兹全说:“陶希圣是个辩证唯物史观者。他的政治环境和身份,使左派不承认他是,他自己也不敢承认是辩证唯物史观者。”参见何兹全《我所经历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载《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第34-35页。陶希圣自己认为:“我的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观,却并不是唯物史观。与其说我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无宁说我欣赏考茨基的著作。”参见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11页。
标签:陶希圣论文; 恽代英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台湾国民党论文; 周佛海论文; 国民党论文; 商务印书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