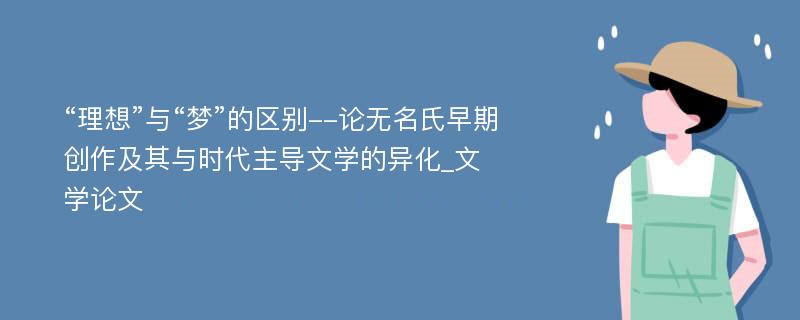
“理想”和“梦”的差异——论无名氏的前期创作及其与时代主导文学的疏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无名氏论文,主导论文,差异论文,理想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1)04-0050-07
一
无名氏30年代开始创作,成名于40年代,前期创作主要是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写成的。但他的创作却有异于特定意义上的“时AI写作作”——“抗战文学”。何为“抗战文学”?并不是抗战八年期间所出现的文学就可称为“抗战文学”,抗战文学有它特定的内涵。正像当时人们定义的那样:抗战文学应直接描写抗战与民主斗争,“要用铁的笔,蘸着鲜红的血,在大众心头着力刻画,使每一个人都怒吼,暴跳,这才是抗战的文艺”[1][P247]。无名氏的创作经历了一个与时代主导文学由亲和到疏离的过程,这种变化一方面给他带来了大量的读者,使他进入了为数不多的畅销书作者的行列;另一方面又给他招致了来自其时代的“进步文化阵营”和“保守文化阵营”的双向夹击。前者将其贬斥为一种“庸俗的”“新鸳鸯蝴蝶派”小说;后者则一直将其视为“整个抗战时期影响最为恶劣的作品”。(见台湾周锦写的现代文学史论著)主要原因在于他的作品既不合于抗战后期进步文化阵营“求民主的呼声”的主旋律,也不合于张道藩为文艺制定的“六不五要”的国民党官方文艺政策。无名氏以一种轻逸姿态跃然于这种时代对抗之上,从现代文学日益政治化的时代趋势中突围而出,重新回到了一种审美个人主义的写作立场。“轻逸”在他表现为一种化实为虚式的看待人生和现实的独特视角,一种与社会政治视角不同的审美性的超然直观视角。如果说前者是一种“增负”式的对于人的社会性、政治性的强调,后者则是一种“减负式”的个人性的对于人生意义的体验和感悟。他力图逃避社会政治的、道德的对于人的生活的归罪和裁决,为个体的非理性的人的生活辩护,强调人的生存的个体性原则。这种个体性原则是现代性文化立足的一个重要基础,它的确立与浪漫主义文学倾向有直接关系。
汉娜·阿伦特曾这样谈到浪漫主义与个人性问题:“卢梭和浪漫主义通过对社会的反叛发现了隐私性,这种反叛首先针对的是社会领域的那种欲将一切削平的要求,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内在于每一社会的顺从主义。”[2](P71)所谓顺从主义即视社会如家庭,假设人们都是仅有一个观点、一种利益的家庭成员。代表着这种共同利益和单一观点的是家长,他们根据这种利益和观点来进行统治,让大家同心同德地奔向某个目标。这是一种前现代的代表型公共领域。而现代公共领域则是“专供个人施展个性的,这是一个人证明自己的真实的和不可替代的价值的唯一场所”[2](P73)。现代公共领域为个体提供了一个让其存在、竞争、表现的公共空间,然而这个五四以来初萌的公共领域在抗战这种特殊情境中又面临被一统化的趋势,以致无名氏不得不为他小说中人物的个人选择——“出家”、“隐遁”作这样的自我辩解:“对于抗战,过去五、六年,我也总算尽过一点个人责任了。看世界大局,盟军胜利,已是决定性的了。我为我的隐遁,感到歉疚。然而,像我这样的畸人畸行,世间极少,我的生灭,对社会只是沧海一粟。尽管如此,我仍为我的扮演闲云野鹤表示遗憾。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万事万物,不能全按道义的钢模子去浇铸,例外的怪事总免不了的。”但这种用“道义的钢模子去浇铸”一切的趋势是当时的主导趋势,以致个人性情感始终被压抑于地平线以下,处于一种文学上的失语状态。而无名氏的“媚俗”之作,则让这种被压抑下去的个人性话语浮出了海面。
关于文学中的爱情主题,现实主义作家和浪漫主义作家有完全不同的兴趣和理解。自鲁迅《伤逝》一出,对新文学中的浪漫主义的爱情表现可以说是个致命的打击。鲁迅写的是从云间坠落到地面上的爱情,也就是强调“爱”是必须有所附丽的;再超凡拔俗,再罗曼蒂克的爱情,最后也得落脚于丑陋的物质之上。这固然是独具只眼的现实主义者从缠绵悱恻、光怪陆离的爱情中所发现的一个真理,但是爱情并不因为它须附丽于物质之上而失去它的神秘、浪漫、超脱和诗意。正如不能从“每一朵玫瑰花下面都看到坟墓一样”,人也应该可以有他做梦的权力,暂时离开地面想象自己像鸟一样在空中轻捷地飞翔的权力。爱情特别是浪漫主义的爱情是一个可以让人在梦想和现实交界处大做其梦的领域,爱情文学中的极品往往是集中了人性的全部精粹,借爱情来透视人性的杰作。这种爱情之作也就超越了爱情本身而具有了深厚的人性底蕴,也就是说它是通过爱情来悟生死,达到对人生更高的觉悟的。这种努力在无名氏的成名作中是非常明显的。
与同被称为“新鸳鸯蝴蝶派”的徐訏相比,无名氏是一位入世较深,生活态度也更积极、执着的作家。无名氏第一篇较为成熟的小说发表于1937年。从这篇小说所表现出的情感倾向来看,他隶属于五四时期个性反抗的文学传统。虽然这种文学在“红色三十年代”已是强弩之末,被左翼文学挤向边缘,但还有莽原社高长虹一类的作家在坚持这种对社会的个人主义的批判立场。无名氏和他们可以说是情趣相投的。小说所写的是尼采入疯人院丧失理智之前最后阶段的心理意识活动。在经历了大寂寞、大苦痛、大绝望的人生之后,尼采变得“酷爱黑暗,它里面泛滥着晔晔的芬芳,洋溢着天鹅绒似的温暖,辐射着幽秘的紫色火焰,他竦惶的但不可抗拒的拥抱它,每枝血管幽咽着一泓恬静……”这种对黑暗的酷爱实质上是对一种死亡的宁静的渴望。他并不是一位出于天性的“爱黑暗者”,只不过是因为“光明于我何所有——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来,未来的未来才是我的哪!”在他所预言的虚无飘缈的超人时代到来之前,他只能永远待在这种精神的黑暗之中。这种孤独的先觉者的痛苦在五四一代人那里是深刻地体会到的,因此他对于时代、社会的沉闷、黑暗的诅咒也就能引发一种反抗者的情感共鸣。无名氏在这里集中渲染的也正是这种不被理解的先知的愤怒:“他(尼采)从未这么气愤的憎恶过一切:这比北极还冷的社会,比金钢钻还顽固不化的‘学者’们,比驴子还愚蠢的知识分子,……他喃喃恶詈着基督、瓦格纳、野蛮的德国文化界、欧洲的阴柔主义——然而,他感到空前绵延迤逦的寂寞。”这说明在创作之初,无名氏是担负着新文学的“人的启蒙”的道义责任的,他所表达的理想与启蒙主义理想还是相通的。
无名氏这种同尼采相通的个性反抗情绪很快因抗战的爆发而转向。抗战开始,无名氏正是21岁的青年,他热情地投身到了抗战激流之中,创作了一系列真正意义上的抗战文学。最典型的当属他的长篇散文诗《薤露——“八·一三”三周年 谨献给全体死难将士之英灵》。这篇散文诗所表现出的对抗战烈士的感情是非常真挚动人的,但也是比较个性化的。它是通过对于烈士死亡之后的可怖景象的想象从反面映射出了生命的美好,人间的可爱。从热爱生命的立场上反证出自愿地献出生命的死难将士的牺牲的伟大。“坚贞的中华之子,牺牲的象征啊!你们是以牺牲为欢乐的源泉,所予的何其多,所取的何其少?……月光是恁般婵娟,海水是恁般绮丽,玫瑰是恁般芳香。为了祖国的青春,民族的青春,你们抛弃了自己的青春。世界是恁般芳香,你们都是年轻的,岂不知在绿幽幽的篱墙下,有软绵绵的温柔手臂在期待刚强的一握?然而,你们拒绝了,为了祖国。”它与“抗战时文”的区别所在就在于他是立足于一种个体本位的、人道主义的温情立场之上来看待“牺牲者”的。他没有把这些死难将士拔高或贬低到一种生就是为了死的,没有人的情感和属性的“兵蚁”的位置;没有停留在满足于以“杀身成仁”来概括的道义化的人生意义上;而是把他们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一样年轻的生命来对待。在他们还没有享受到人生应有的快乐和幸福的时候生命就戛然中止了,这种非自然的死亡所带给人的悲感就要比自然死亡要沉重得多,因而也就更是有一种生命的悲剧意味。从个人性的角度来进行时代抒情是此时无名氏创作的一个特点,他是在“时AI写作作”和浪漫主义诗情之间寻找和谐的。
他的前期小说《海边的故事》、《日耳曼的忧郁》等都取材于社会现实生活,但却都超出现实层面表达一种浪漫主义的个人情感,往往通过一种独特的个人情感经历来表达一种刻骨铭心的人生感受。《海边的故事》从写实层面上来看,写的是一位抗日志士在东北的坐牢经历。但作家的兴趣所在显然不在于反映现实、塑造人物,而是写人对于自由的渴望以及失去自由所带给人的巨大痛苦。主人公李因宣传抗日被送进监狱受尽折磨,但他却顽强地忍受下来,从没有掉过一滴泪。但当他被关了三年之后第一次被放出来到监狱门口去拔草时,他却被门外的美好的春天景色所震撼,扑倒在草地上,完全丧失了情感自制能力:“他像最虔诚的基督教徒看见灵幻的耶和华站在云端似的,不能抗拒的匍匐到青草上面,吻着青青的草与草下面的泥土,这是人们的泥土,而我不过是一个被抛弃在撒哈拉沙漠上的囚徒……我狂吻着,我狂吻着,眼泪不由自己地冲泻出来,潺潺如清泉,冲泻出来,不断冲泻出来,我哀伤得眩晕过去。”他被狱卒痛打了一顿,骂他装病不做工,将他又关进了牢里。他在牢里写出了一首歌颂春天的长诗,这首长诗被发现送到了管理囚徒的科长那里。他准备好接受最严厉的惩罚,但这位伪满官吏竟也为这首长诗所感动了,他眼圈发红,对李说:“得,我这一遭不处分你,以后你可得特别留意,别再写这一类玩意儿,你该明白,一个囚徒是没有春天的,是的,囚徒没有春天,没有春天。”小说是通过讲述这样一个硬汉子的情感隐私(三十多年来的唯一一次流泪经历)来揭示自由对于人的可贵。知道了这一点之后,人们也就可以理解中华民族抗战的神圣意义。个人自由和民族自由在无名氏这里是完全统一的。
但随后无名氏的创作既没有继续走向时代的主导文学,也没有走向路翎式地将个人主义嫁接到集体主义的道路,而是进一步走向了一种审美个人主义的写作立场,从而表现出与“时AI写作作”的疏离。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时AI写作作”开始由抗战之初的统一而呈现分化之势,如解放区文学开始着重阶级意识的表达,《白毛女》即于此时问世;大后方则主要表现为“一种求民主的呼声”,典型加郭沫若《屈原》中的“雷电颂”;国民党则加强了对文学的收束和管制,企图使文学控制在其官方意识形态之下。要之,“时AI写作作”的意义来源都是一种社会历史理想,即通过对社会历史的改造以使之达到一种理想状态。它所影响于文学的就是一种真诚的求治、求善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的形成。而无名氏所追求的则是一种审美个人主义的人性之梦。这种“梦”和“理想”的差异是无名氏与“时AI写作作”的最内在的差异。“理想”是理性追求最高的善的产物,它设想出一个完满的模式作为现实必然要实现的目标,它具有排他性、现实性、普遍性、目的性等特点;而“梦”则是个人在自由的精神状态中对人生“真谛”的感悟,它具有差异性、感受性、当下性等特点,无名氏创作的成败得失以及其文学声名的浮沉毁誉都与此差异有关。
二
《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使无名氏一举成名,它也标志着无名氏创作的一大变化。他开始与“时代”疏离,与“主导文学”疏离,确立其创作的一种审美主义的个人性原则。《北》和《塔》虽还是在现实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但作家开始力求摆脱“时代”的重负,淡化社会政治、道德色彩而凸现浪漫感性色彩,浓墨重彩地创造出一种超凡拔俗的浪漫主义人性图画。这也透露出作家本人在人生和文学的价值立场上的变化:他开始反思文学中何为“重”何为“轻”的问题。从“时代”对文学的要求来看,当然社会为重,个人为轻,政治道德要求要高出个人和文学的审美要求;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作家最应该表现的是他对人生的刻骨铭心的独特感受以及他对人性的独特理解、独到发现,而不是头绪万端而又瞬息万变的现实问题。因此超出具体的现实问题的羁绊,而游心于精神上的自由之境的“轻逸”,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一想到若干万年以后,一切现实将是一片虚妄。但刹那现实中的美的沉醉与享受,却不是虚妄。也许真正的永生正在这里。但我所指的永生,最纯粹的美的欣赏,而不是醇酒美人。”[3](P73)无名氏发现了在“时代”和“永生”之间在其时代文学中存在着的断裂。当把人完全看成是时代的“附庸”,使个人被沉重、必然、价值所占据,丧失了他的个人的、属我的感觉时,他也就成为了一个失去了自我的“时代”容器。而“永生”的意思并不是“不死的”,而是属我的、美好的、独特的人生感受和体验,它可以超出具体的时空所限,而唤起几代人的共鸣。
无名氏的《北》和《塔》所表现的就是一种超现实的精神价值的实现,一种对于人生真意的反刍和追问。由此他从一种“时AI写作作”的集体主义行列中抽身而退,开始以一种“个人”姿态现身。
这两部小说与“时AI写作作”的疏离主要表现在:
(一)与时代主导文学热情参与、介入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努力相反,他抛开了“时代”所加诸人的“沉重”,而去登山远眺、仰望星空。无名氏的这两篇小说的场景都选在远离尘嚣的华山之巅。“我”因患“脑疲症”到华山静养,陶醉于华山的奇丽景色之中,由“社会人”变成了“自然人”,摒除了一切俗虑,“脑疲症”也就不治而愈。华山隐居因此成为“我”的悟道契机,这种悟道是通过从种种复杂的社会纠葛中跃身而出,消除了身心之累来实现的。华山是个世外桃源,当时正是“抗日”时期,而华山的老道士却把“抗日”听成“炕热”,根本不问世事。“轻逸”的获得通过的正是一种“减负”方式,它使主人公暂时忘掉了“我”的社会身份,重新回归一种本然的自我。
与时代主导文学强调文学的现实功利性相反,他为小说选中的叙述者、主人公都已从现实功利境界脱身而出。《北》与《塔》的情节模式都是一样的,“我”在华山遇到一位“怪客”和“高人”,他们的乖异、古怪引起“我”浓厚的兴趣,最后在“我”的恳切请求下,他们终于向“我”讲述了他们的断肠心曲、绝对隐私。这些“怪客”“高人”都是历尽了人间沧桑的“断肠人”、“失败者”、情感、良心的负疚者。这种“失败”和“负疚”却使他们可以超脱地反省过去,平静地返观他们的人生。这种对于人生的远距离的审视本身就使他们超出了现实的羁绊。
无名氏在提到这两位“怪客”“高人”的时候,曾反复用一个比喻,那就是把他们比作“一个饱经沧海的舟子”。正如古勒律吉名作《古舟子咏》中的老船夫。“在他心灵中,一定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宝矿”,而“我”则是这个宝矿的开采者。在《塔》中,当“我”听到“高人”在月光下演奏《卡伐底那》曲子时,想到的也是“他仿佛一个饱经忧患的衰老舟子,经过各式各样的大海变幻,风暴的袭击,困苦与挣扎。到了晚年,在最后一刹那,睁着疲倦的老花眼,用一种猝发的奇迹式的热情,又伤感又赞叹的唱出他一生经历:把他一生的感情与智慧都结晶于这最后的声音”。而“我”也深为这曲子所打动,从中“我体味着黄昏的境界,又哀愁又神秘,我领略无穷的启示:它叫我懂得人生,理解感情,洞透生命中那些最宝贵最耐寻味的部分”。问题在于叙述者何以对这种饱经沧桑的老者、怪人、出世者如此感兴趣?老人固然是经验和智慧的象征,但叙述者更关心的是他们那种“过来人”所看破的“人生本相”。在老者那里,人生已不是所要完成的“事功”、所要得到的“结果”,而是已经走过的历程。“事功”、“结果”需由现实来证明,而“过程”只须自己来回味。注重“事功、结果”的是“英雄”,是“强人”,他们征服现实,让现实来证明他们的价值,它是以权力、金钱、成就、声名等来衡量的;而小说中的怪客、老者则已不需要这一切,看轻这一切,他们已从世俗之累、情欲之累中挣扎出来,而达到一种“无执”的心灵的平静。所以这个引子对于整个小说是非常重要的,它使一个单纯的爱情事件带有了感悟人生的意味。
(二)《北》和《塔》写的都是爱情悲剧。但这种爱情悲剧不同于“时AI写作作”的特点,在于它主要是一种命运悲剧、性格悲剧,而不像其时代的主流文学注重对悲剧的社会性根源的揭示。这种悲剧的形成来自于一种神秘的阻力,它不是人力能与之抗衡的。虽然无名氏先后四次对《北》进行修改,每一次都加强了一些造成悲剧的社会性因素,但仍没有改变它作为一个命运悲剧的特质。小说的素材来自于无名氏的朋友韩国光复军参谋长李范奭的一次情感经历,但经过了无名氏的加工改造,这个故事就带有了独特的无名氏色彩。他是在一种浓重的人生悲怆感的氛围中来讲述这个故事的。这种人生悲怆感来自于一种历经命运的捉弄,意识到人生的难以圆全、难以完满,因而产生的一种“天凉好个秋”的悲凉、无奈情绪。小说女主人公奥蕾利亚在他们生离死别时所写的诗中表达的正是这种情绪,这种超离了怨天忧人情感之后的平静和无奈,构成了这篇小说叙述的基调。
与其时代常见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表现出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时代命题不同,吸引无名氏的则是爱情自身的神奇性。小说中的男主人林之爱上奥蕾利亚首先是震惊于她惊人的美貌。无名氏用诗的语言极力描述了女主人公的美貌。无名氏是一位对女性的容貌特别敏感的作家,在这一点上,他不顾及人们对他可能有的“重貌不重人”的指责,因为在这种对于容貌美的关注的背后,还有他的一整套的“哲学”,无名氏将之称为一种“胴体现象学”。在这种“现象学”看来,人的肉体是一种符号,一种“浸透了宇宙和星球意味的符号”,它并不是对本质的遮盖,恰恰自身就反映着本质。这就与“相面术”的思维方式有些相似。但它关心的不是相貌上表现出的人的福祸寿夭的征兆,而是人的天性、灵魂,这是一种对于人性的非理性的直观把握。他从外貌上就可以看出女主人公是一个至性至情的女子,一个具有极大的“灵魂深度和情感强度”的女子。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原初印象,爱情就难以发生。在此之后吸引他的才是女主人公的智慧、情愫、气质、格调等等。林和奥蕾利亚的爱情是在现实背景下发生的,有它的社会性的因素。这些社会性因素阻碍着他们的爱情,但正是这种阻碍却产生出一场置之绝地而后生的惊天动地的爱情。无名氏着力表现的也正是这种爱情的神秘性、盲目性、超社会性,使一切不可能都成为可能的特性。小说开始之初,林对于爱情和幸福的看法是带有一种及时行乐、游戏人生的味道的;而他所采取的“于连”式的进攻策略,也使这场爱情一开始就偏离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真爱情的轨道。但这也正是无名氏的大胆之处。他可以在小说的高潮处来一个逆转,让一切务实的、功利的、个人的考虑隐隐消褪,让爱情的强光穿云而出,超越世俗,甚至超越生命来达到它的极致。当与这种爱情遭遇之后,林和奥蕾利亚都已不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只能听从于爱的召唤,将自己奉献于爱的祭坛之上,成为爱的牺牲。所以小说最后的结局是一殉情自杀,一虽生犹死,这正点明了爱情的不可抗拒的神秘特性。
如果说《北》所讲述的还是身处时代激流中的韩国革命者的爱情悲剧,《塔》所选中的主人公则是一个动荡时代的边缘人,与“时代”气氛极不和谐的唯美主义者。《塔》主要表现的是唯美主义的爱情之梦及其在现实中的坠落。罗圣提是以一种唯美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人生的:他认为生命里的欢笑与快乐,就是每一刹那的微妙沉醉。他倾心于生命中的那种瞬间的快意和沉醉,人生的目的就在于生命本身,他不是为实现某种预言,完成某种使命来生活的。他注重的是人生的一种当下状态,感性体验。他可说是一个典型的“耽美者”、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者,这样一种生活态度自然与严峻的时代极不谐调。但罗圣提预先为自己作了这样的辩解:“也许不少正人君子会认为这种生活观念太虚浮,沾享乐色彩。可是或者他们用岩石性的神经,面对美的感受,或者他们虚伪的掩饰自己的实际享受,或者他们否定现实生活中美的成分,否则他们就无法抹煞这一观念在痛苦的人生中的补偿价值。”罗圣提的唯美主义不是“颓加荡”的醇酒美女,而是追求一种尘世中的“灵”的享受。在他的眼中,他爱把女子看成大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生命,他宁愿花开在园里,鸟飞在天上,“不愿看花儿开在我手上,鸟走在我肩上”。他很少带冲动意味地欣赏女子肉体,认为一个女人的形体美,只有和性灵美溶合在一起时,才值得注意。他观赏一个女人的形体,与品鉴希腊雕刻维纳斯神像一样,并无多大区别。这种审美态度实则是一种将万物予以对象化的审视的态度,这种态度将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存在变成了一个美的幻象,实则是对审美对象的非人化、异化。在这种非功利、超肉欲的审美态度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对于真正生活的恐惧、逃避,正由于此,所以它与现实相遇时的悲剧性结局是无法避免的。
(三)《北》和《塔》探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方式和“时AI写作作”是迥异其趣的。时代主流文学的人生理想是将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与某种社会目标的实现统一在一起的,所以它的确立是必须建立在对个人异己性因素予以克服的前提下的。而无名氏对于人生意义的探寻方式则是个人性的、差异性的、回味、体验性的。《北》的最后,林在讲完他的人生故事这样谈到他对人生的感悟:“在生活里面,你常常可以碰到一种不可抗拒的神秘阻力。这种阻力,你年轻时还不显得怎样沉重,有时候只要你咬一咬牙关,摇一摇头,说一个‘不’字,它似乎就退开了。但是随着你年龄的增加,额上皱纹加深,它一天一天变得强大起来,到了最后,你连摇头说‘不’的勇气都没有了。不,不是没有勇气了,是没有兴趣。年轻时,你觉得这种摇头是可赞美的,中年后,你感到这是不美的,终于你承认它是一种坚不可拔的存在。……愈是认真追求幸福的人,愈不容易得到幸福。倒是并不怎样追求它的人,它却时而在他的身边团团转,而且真当幸福在你身边时,你不一定知道,等到你知道了,它常常已消失了。”
这种感悟与佛教的破除“我执”是相通的。“我”刻意的主观的幸福追求与外部世界的非理性的无情冷漠、变化无常构成对立。世界并不是为“我”所设置的,相反我为世界所造就和播弄。所以,“幸福”只能求之于内,而难求之于外。并且“幸福”追求本身就接近虚妄,《百喻经》中说:“诸佛说言:三界无安,皆是火宅;凡夫倒惑,横生乐想。”如“幸福”者,“求时甚苦,既获得已,守护亦苦;后还失之,忧念复苦。于三时中,都无有乐”。何“幸福”之有?然而作为一个浪漫、唯美主义者的无名氏并没有就此否定人生,他仍然从这种人世无常中发现了至可珍贵的“美”。他说:“解脱者也能欣赏尘世一切,……他所要享受的,只是它们的刹那,而不是它们的永久。……只有站在‘永生’的观点,才能极透彻的了解刹那的美。”[3](P69)这实际上就是告诉人们尘世中的“永久”就是刹那间的体验和感受,一种偶在的生命个体所能把握的属我的、美好的精神感受。
《塔》主要表现的是一种唯美哲学与道德理性之间的冲突。这是一种内在的心灵的冲突。罗圣提以一种唯美的、非欲望的态度来对待爱情,而这种“高尚”对黎薇则极不公平,她成了他的这种唯美的恋爱观的牺牲品,她是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爱情的。相对于男主角罗圣提,黎薇在爱情上表现得更为热情和勇敢。这位高傲的女子不爱则已,一旦爱上,便如火山爆发一样强烈。罗愿意接受这种爱,但却无法摆脱种种现实的“俗虑”:他是一个有妇之夫,他有他的相当的社会地位和优裕的经济收入,他不愿毁掉这一切。更重要的是他要反问自己有什么权利接受黎薇的牺牲?为什么自己不能为家庭、为社会、为传统、为黎薇的前途来牺牲自己?这种既不愿伤害妻子,也不愿伤害黎薇的道德忧虑,使他一手安排了黎薇的恋爱、婚姻,想给黎薇找到幸福,结果反而酿成黎薇的生活悲剧。
与五四以来“新文学”处理这种爱情悲剧式的普遍态度不同,无名氏并没有一边倒地认同“爱情至上”、“个人自由”的启蒙主义的解决方式,而是深刻感受到了爱与美和道德理性之间存在的势如水火的两难处境。这是他不相信对某种根本性的人生困境会有某种现实可行的解决方式。(无名氏曾提到纪德的《地粮》,并受其影响,不知他读没有读到纪德的《窄门》和《背德者》,这两篇小说都是表现人的感性生命与道德理性的冲突的。)爱与美的幻灭使罗圣提心灰意冷,而对于道德完善的绝望则终于使他接近了宗教。讲道德的人是凭知识、理性去谈论“善恶”;而信宗教的人则根据“实在”“幻相”去把握人生世界,从而达到与宇宙自然的合而为一。所以罗圣提“变卖了一切,隐逸华山,准备把残缺的生命交给大自然。我本来自大自然,此刻再交还它,实在千该万该。也只有在它身边,我才能获得一点慰藉”。在以道德态度来生存,仍无法解决人生的痛苦和矛盾时,他走向了对世俗人生的超越。这完全是一种个人性的选择,作家对此也只能表示遗憾、叹惋而已。
无名氏并没有陶醉于《北》和《塔》的“成功”,他对这两部小说都不太满意,而更推重后来的《无名书稿》六卷。这可称为他的中期创作(1981年赴港之后可称为其后期创作)。在《无名书稿》中,他超越了这种浪漫、唯美之梦,与“时代”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对话,从中可以看到他从个人化的文化立场对于“时代”的独特担当和思考。“轻逸”和“沉重”、“时代”和“永生”在《无名书稿》中得到了一种新的层面上的个性化的统一。
收稿日期:2001-0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