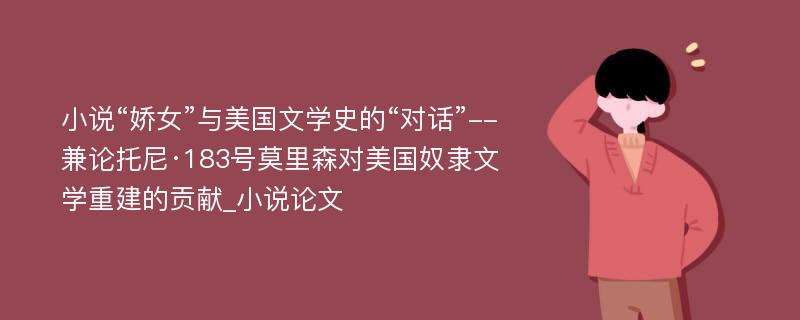
小说《娇女》与美国文学、文化史的“对话”——兼论托妮#183;莫里森对重建美国黑奴文学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黑奴论文,文化史论文,文学论文,莫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娇女》是199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当代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1931— )的代表作,被西方学术界列为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的经典作品。笔者则认为,在这部小说中,作家托妮·莫里森运用前苏联文学理论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成功地构建了小说与美国文学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之间的“对话”关系。
巴赫金通过对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周密阐述,得出了一个结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不仅在小说艺术创作领域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小说体裁——复调小说,而且在人类艺术思维发展的长河中,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复调型艺术思维。这种思维,超出了小说体裁范围之外,能够研究“人的思考着的意识,和人们生活中的对话领域”。他强调指出:“思考着的人的意识,这一意识生存的对话领域,及其一切深刻和特别之处,都是独白型艺术视角所无法企及的。这些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里,首先真正成了艺术描述的对象。”(注:米·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
按照巴赫金的解释,复调,即是由“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对话”关系。结合上述引文,我们不难看出,巴赫金所谓的复调,它的关键之点有三:一是人的意识的独立性;二是各种不同的独立意识组成的多声部性;三是各具完整价值的声音组成的全面对话性。正是这三点要素,构成了复调小说有别于传统独白型小说的艺术形式的独特性,也是巴赫金复调理论的精粹所在。而在独立的主体意识、多声部和对话的纷繁形式这三者之中,巴赫金又认为,到处存在的对话关系,是贯串于陀氏小说的最基本的特点,是复调小说的理论基础,也是人类艺术思维重大进展的最突出的表现。所以,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归根结蒂,探讨的是小说创作中的对话艺术,以及这一新的艺术领域对于推进人类艺术文化发展的意义和作用。
《娇女》这部小说,就是美国当代文学创作成功地运用对话艺术、取得卓越成就的典范。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家托妮·莫里森凭着她的杰出艺术才华,对前辈艺术大师开创的复调型艺术思维模式作了创造性的发挥,不仅将对话艺术熟练地贯穿于小说结构、人物关系结构中,而且在更广阔的艺术背景上贯彻这一艺术思维原则,让自己的小说与美国文学的历史、美国文化的历史,构成一种特殊的对话关系。
一、《娇女》与美国文学史的对话
1987年,托妮·莫里森的长篇小说《娇女》的问世,震动了美国文坛。评论家纷纷撰文,赞美这部“神奇而辉煌”的巨著。更有一些别具慧眼者,从文学史的角度给予小说以高度的评价。说它“是一部历史,字字是惊雷,句句是闪电”,称颂它“是美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甚至认为“不读《娇女》,就无法理解美国文学”。第二年,牵涉普利策文学奖的归属,还引发了大批文人充满激情的抗议,48位美国黑人作家、学者联名发表了公开信。在信中他们给小说作者奉献上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
“您参与生活,是天之娇女;您忍辱负重,是人间仙子。我们那段被人掩饰的往事里还埋藏着极其复杂的隐衷;我们这不受蒙蔽的良知所探明的事理,必将在未来岁月里激起甜美的幻想和恐怖的恶梦。在这些迷雾之中,我们发现,您矢志不渝,决心辛劳终生,一砖一石地为我们建立一座智慧之塔、发现之塔、信任之塔。您那洞察秋毫的眼睛,您那悉听万物的耳朵,从来不放过任何历史的劫难或形形色色的人生际遇,给我们的信念源源提供精神食粮。您总是那样慷慨豪爽,您将自己的真知卓见毫不保留地赐给我们,推动我们的文学,推动我们的生活。为了整个美国的利益,为了整个美国文学的利益,您将我们的道德水准和艺术水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必须依照这种道德水准和艺术水准,来检验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的国民想象力和集体智慧所体现的创新精神和爱的力度。……在《娇女》诞生问世之际,在您这最新礼品又一次丰富我们日益壮大的种族、国家、勇气和良知之际,我们怀着惊奇和感激的心情,面对您的发掘和创新所展现出来的丰富宝藏,留下这些文字,以表示我们的自豪、敬慕和珍爱。”(注:《纽约时报》,1988年1月24日。)
以上文字,绝不是过誉之辞。托妮·莫里森确是立足于过去、现实与未来,肩负起了历史与艺术的双重使命,把美国文学中长期被抑制的声音——广大黑人同胞的声音,写进了这部小说,表现了黑人种族的命运和历史文化,为重建美国黑奴文学史作出了贡献。
美国是一个在对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追求中建立起来的国家。威廉·凡·奥康纳在《美国小说思潮》的序言中,谈及了历史塑成的美国民族性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同之点,在于这个国家建筑在某种观念之上。它的历史始于一片空白,没有朦胧神秘的过去。在理智将人们从迷信中解放出来的十七、八世纪,莫尔、坎帕尼拉、培根和其他人根据想象描绘了理想的乌托邦社会。实现这个理想的机会终于降落到了生于这一新时代的人们中间,这个机会就是北美新大陆。”当第一批欧洲移民于1620年登上横渡大西洋的航船时,新大陆就意味着对某种理想的寄托,或是对战乱的逃避,或是对贵族社会的摆脱,或是对宗教自由的向往,或是对发迹机会的凯觎。这种理想主义的追求,为美国人的平等、自由、民主的思想传统打下了基础。所以当美国人宣告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统治时,《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强调的是人的生之平等,展望的是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美国:“我们认为这些事实的真理性是自明的:天下所有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神在创造他们时就赋予了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力。这些权力包括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然而,就是在这个以追求自由、民主、平等为宗旨的最年轻的国家里,存在着最不自由、最不民主、最不平等的最古老的蓄奴制。从17世纪初开始,一艘艘运奴船装载着掳自非洲的黑人源源不绝地驶抵北美海岸,数以千万计的黑人奴隶被囚禁在美国南部种植园里,在残暴、野蛮的奴隶制下过着惨无人道的生活;直到爆发一场大战、反奴隶制的民主力量取得胜利,黑人奴隶才获得极不彻底的解放。南北战争爆发前十年,斯托夫人的长篇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在废奴运动的浪潮中应运而生。小说以生动感人的艺术描写揭露了发生在南方种植园中的血淋淋的事实,蓄奴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人们甚至把南北战争的爆发归结于小说激起的强烈的废奴制的呼声,林肯后来在接见斯托夫人时也开玩笑地称她为“写了一本书,酿成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可是,在美国文学史上,象《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样为黑奴解放大声疾呼的力作,虽说不是绝无仅有,毕竟也是寥寥无几。相反,南北战争以后,在一部分描写南部的乡土作家中,甚至还出现了一股美化蓄奴制时代种植园生活的潮流。约翰·伊斯顿·库克(1830—1886)和托马斯·纳尔逊·佩奇(1853—1932)所开创的“种植园传统文学”便是代表。他们缅怀蓄奴制的“旧南方”,用玫瑰色的传奇故事掩饰奴隶主的剥削罪行,美化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乃至一些黑人作家,例如保尔·劳伦斯·邓巴(1870—1906)和查尔斯·契斯纳特(1858—1932)的创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这股为蓄奴制扬幡招魂的潮流,一百多年来没有止息,至今仍然拥有着读者。《飘》在美国与世界的风靡,便是一个显例。
总之,我们可以这么说,小说家在社会生活中率先注意到了一个与杰弗逊“人生之平等”的民主理想格格不入的严酷现实——白人奴隶主和黑人奴隶之间的绝对不平等,在美国早期文学中就注入了为黑人奴隶呼吁的声音。但在整个美国文学之声中,这一声音又是那么的单薄和微弱,不久就被淹没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美国文学是在摆脱对欧洲文化的依附中诞生的。1820年,英国评论家西德尼·史密斯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文章,讥讽“四海之内,有谁读美国书?”作为对这一诘难的回答,美国小说从这一年开始,致力于探索自己民族之声的表达,把视线转向新大陆的背景、素材、人物和事件。然而,如果以为这民族之声是包括黑人在内的美利坚各民族的声音,那是一种误解。无论是詹姆斯·费尼莫·库柏以开发西部为素材的小说,还是纳撒尼尔·霍桑散发着浓郁宗教气息的人生故事,亦或赫尔曼·麦尔维尔带有象征色彩的命运悲剧,早期美国小说诞生伊始,所热切关注的是美国这一新大陆与欧洲旧世界之间的冲突,是对所谓人人都能享有自由、民主,和有追求幸福权力的“美国梦”的追寻,而不是发生在这片辽阔疆域上的种族歧视与迫害。黑暗的意象,无辜与有罪之间的挣扎,虽说也是早期美国小说钟爱的主题,但小说家侧重记录的是个人心灵的黑暗与挣扎,探索的是怎样驱除由个人或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往事所带来的负罪感,并且往往把一切问题归结为一个抽象的“恶”的概念,强调人性的善恶之争,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结构的不合理性。即使写黑人或红种印地安人,也是逃离对社会矛盾的忠实描写,有意抹去种族的界限,表现他们与白人之间的亲善关系。
在一个强调自由、民主、启蒙、人权却又为等级制辩护的国度里,旨在表现民族之声的文学却又偏偏忽略了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黑人种族为争取人权的呼声。作为一个黑人作家,托妮·莫里森不得不经常思索这一问题。她认为,由于种族的偏见,来自非洲的美国黑人在美国文学史上长期被剥夺了应有的地位,但是谁也无可否认美国黑人存在于种族压迫的社会背景中。小说《娇女》把种族压迫的主题从背景推向了前景,将长期被抑制的声音——黑人反抗的呼声重又带进了小说,与美国文学的历史相对话,在美国文学之声中,注入了一个真正的强音。
《娇女》在我们面前重新展现了南方蓄奴制的漫漫长夜,给我们讲述了一则发生在这段长夜中的鲜血淋漓的故事:女黑奴瑟思不堪忍受肉体和人格的双重残害与蹂躏,拖着怀孕的身子,历尽艰难,逃离了奴隶主的庄园。她虽然跨过了地狱之河,却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面对前来追捕的白人,为了不愿让自己的孩子重新沦为奴隶,在迫不得已之下她杀死了自己年仅两岁的爱女。于是,她被埋进了另一个坟墓——杀生灭亲的罪孽之中。白人把她关进了监狱,连黑人同胞也都把她视作嗜血的野兽而摈弃了她。她在心灵的磨难中苦苦挣扎了18年。在18年中,失踪的丈夫没有音讯,两个儿子离她出走,支撑着她精神的婆婆撒手人寰,身边只剩下一个在逃亡途中出生、因孤寂而性格变得怪僻的幼女。虽说南北战争的结束已经废除了蓄奴制,虽说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大变化,但她困守在124旧屋中, 那悲怆的过去化作爱女的阴魂,依然无时无刻不追随她,使她在对苦难的回忆中耗尽精力,走向身心的全面崩溃。
如果说《汤姆叔叔的小屋》通过奴隶主对一个诚实善良、逆来顺受而又笃信上帝的黑奴肉体的奴役与残害,从宗教的角度出发,谴责蓄奴制的天理难容,那么,《娇女》进一步揭示了黑人种族的苦难,不仅仅是被剥夺了生之为人的自由和权利的问题,更有一个人格遭受侮辱与蹂躏、从人沦为动物的非人性逆变的问题。在蓄奴制的南方,黑人奴隶已经被贬入动物的种属,连他们的繁衍生息也是由白人一手操办的“配种”来完成的。当白人教师要学生列举瑟思身上所体现的动物属性时,尽管在瑟思的词汇里还从来没有“属性”这个名词,她凭直觉就能感到问题的严峻性。瑟思的出逃,为的是捍卫自己的人格,摆脱被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兽性;瑟思的杀女,为的是在这世界上她绝对不答应任何人再将她女儿列在“动物属性”那一栏目里。但是,无论她怎么挣扎,还是撕不掉由于种族的命运而贴在她身上的那张“动物属性”的标签。相反,越是挣扎,在那非人的境遇中陷得越深。托妮·莫里森通过作为奴隶的黑人种族被打入动物种属的非人境地,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揭开了蓄奴制下又一层沉重的黑幕。
托妮·莫里森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她没有停留在描述个别人物、个别家庭的悲剧境遇,而是将主人公个人的身世与种族的苦难熔于一炉。瑟思的婆婆贝比·萨格斯对瑟思说过:“在这个国家里,没有哪座房子不是从地板到房梁都塞满了苦命黑人的冤魂。”“白人淹死我们的人比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息过的世代人口的总数还多。”当我们随着娇女幽灵的自白,进入她的幻觉世界,就可以看到,在那阴曹地府,那些“没长皮肤的人”(白人),如何把千百万具高高垒叠、堆成小山的黑人尸体用长篙推向大海,瑟思正在跟着那些被推向大海的亡魂而去。当我们随着斯坦普·培德的脚步沿着蓝石路向124旧屋走去, 就可以听到响彻屋宇的各种躁乱嘈杂的声音,那是愤怒的黑人亡魂的嘟哝声。娇女的幽灵不再是个别家庭的幽灵,是千千万万已经死去和活着的上帝的爱子娇女的代表;娇女的冤魂不再是个别家庭的冤魂,是自奴隶买卖在美洲出现以来的300多年间,在横越大西洋或偷渡俄亥俄河时葬身鱼腹的、 在奴隶主庄园中的皮鞭下被榨干血汗的六千万、甚至更多的苦难冤魂的缩影。
历史问题的叙述带有主观性。在种族压迫、歧视的社会里,当那个读书识字的白人教师用瑟思调制的墨水,整天在笔记本里涂涂抹抹写着有关黑人的观察笔记时,黑人没有为自己写历史的权利。当瑟思杀死了自己的亲骨肉,报纸上记叙着这段“新闻”,评说着她为什么要干出那号“暴殄天物”的事情的时候,黑人没有为自己写历史的权利。托妮·莫里森把发生在124 旧屋的悲惨故事与整个黑人种族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为黑人同胞写下了这段苦难的历史,倾注了自己对这段历史的谴责与控诉,使小说在思想的广度与深度上,与美国早期文学中的理想主义相对话。
《娇女》在表现手法上,运用了美国早期小说中常见的哥特式模式。124 旧屋中喧嚣的鬼声,阻挡保罗·迪跨进门槛的“红色的幻波”,荒寂的林中空坪上紧勒瑟思的手指,与娇女的幽灵在冰冷的库房中追逐时丹佛身陷深潭的幻觉,特别是借体还魂的娇女诡奇的行为,使整个小说充满着超自然的、神秘莫测、阴森恐怖的气氛。
不过,类似的手法,表现的是不同的意象。
美国早期小说热衷于哥特式风格,或是纯粹模仿英国哥特小说的传统,用神秘离奇、悬念绵绵的恐怖情节吸引读者,如查尔斯·布罗克斯·布朗的《威兰德》;或是旨在象征人与环境对抗过程中对人怀有敌意的、难以征服的超自然的神秘物,表现开拓者对大自然的恐怖感,如库柏的西部故事和麦尔维尔的《白鲸》;或是借以挖掘隐蔽的作恶本能、从家族继承来的诅咒在人内心深处引起的骚动不安,强调的是人类自身难以回避的心理压抑与恐怖,如爱伦·坡的绝大部分作品和霍桑的《七个尖角顶的房子》。凡此种种,给人以毛骨悚然的恐怖感,让人纠缠于无穷无尽的焦躁之中的,是人物所面临的真正的哥特式困境。
《娇女》则不同。小说表层所写的虽然也是一系列阴郁可怖的哥特式场景,但这些场景并不是引起人物恐惧心理的真正根源。恐怖的根源,在于白人对黑人的惨无人道的残害与蹂躏。贝比·萨格斯所为之丧命,斯坦普所亲眼目睹,保罗·迪所为之颤栗的命运的恶作剧就是:“任何人,只要是白的,就可以将你整个的自我拿去,换取他脑子发胀时随时想到的任何事物,不仅是对你进行奴役、宰杀、蹂躏,而且还要玷污,把你玷污得从此失去自爱,玷污得使你想不起自己是何物。”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免遭这种恶运,瑟思“要把那钢锯的利齿架在那稚嫩的颏骨底下拉开;要一把捧着那娃娃喷薄而出的油脂般的鲜血;要扶正那张脸蛋,不让那颗小小的头滚落到地上;要紧紧地抱着她,克制那饱满、芬芳、生命正旺的肉体上发出的死亡的震颤”。——这一切,都是源于黑人奴隶对白人社会的恐惧感。哥特式描写制造了强烈的、悖逆常情常理的可怖气氛,这气氛又增强了暴露万恶的蓄奴制的力度。同样的艺术手段,为不同的主题服务,《娇女》比美国早期的小说无疑都要高出一筹。
二、《娇女》与美国文化史的对话
蓄奴制和种族歧视与压迫,是美国独立以后的二百多年来,一直困惑着社会政治、文化的一个严重问题。马克思曾经说过:“成为奴隶或成为公民,这是社会的规定,是人和人或A和B的关系。A 作为人并不是奴隶。他在社会里并通过社会才成为奴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20页。)事实确是如此。蓄奴制, 以及随之而来的种族歧视与压迫,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自由的非洲黑人被贩运到北美这片土地上充当奴隶,这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种手段。美国南部的蓄奴州,整个社会就是建立在强制黑人奴隶无偿劳动基础之上的。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种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存在的社会经济制度,日益显示它的反动性与腐朽性,与北部资本主义雇佣制之间的利害冲突也日见尖锐,到了19世纪中期,已经成为美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美国社会的各阶层,日渐分化为拥护奴隶制和反对奴隶制的两大阵营。双方经过旷日持久的舌战与笔战,终于在1861年酿成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南北战争。林肯在葛底斯堡国家公墓落成典礼上所作的千古传颂的演说中,以史诗般的精练描述了这场举世瞩目的冲突:
“87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块大陆上建立了新的国家,它在争取自由中诞生,奉行人人生来平等这一信念。目前,我们正进行着一场伟大的国内战争,战争考验着我们或任何一个在自由中诞生并奉行上述信念的国家能否永存。……”
战争的结果,是废奴主义的民主力量战胜了罪恶的奴隶制,工业化的北方战胜了种植园的南方,结束了有史以来最残暴、最野蛮的人奴役人的形式,证明了这个从自由中诞生的国家能够存在下去。
不过,这场战争虽然为黑人奴隶砸碎了有形的枷锁,却留下了一具无形的枷锁,一份痛苦的文化遗产——种族歧视与压迫。且不说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间,南方种族主义者对黑人的歧视与迫害从未终止过,各种各样的恐怖组织和种族隔离的措施,使“解放了的”黑人不仅享受不到自由、平等的公民权利,甚至失去了最起码的人生保障;即使经过了一个多世纪,在美国这块大陆上,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黑人的社会地位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围绕着奴隶制是非曲直的争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就在前不久举行的纪念取消种族隔离40周年的仪式上,克林顿总统还公开承认,美国依然存在种族歧视和种族分离的情况,在大街上、邻里中、工作场所和学校里都有所表现,而且认为美国现在的种族问题比40年前更为复杂。我们可以这么说,这充分表现了蓄奴制文化的滞后性,种族歧视与压迫已经渗透到了普通人的精神领域。
小说《娇女》便是在这场纵贯几百年的有关奴隶制的争论中与美国文化历史的一次对话。小说中有这么一段记叙:
“一八七四年。白人还在暴戾恣睢。一座座的城镇,黑人被斩尽杀绝。在肯塔基,一年之内竟有87个黑人被私刑处死;四所黑人学校化为灰烬;成年人象小孩一样被毒打,小孩象成年人一样被毒打;黑人妇女被流氓团伙轮奸;财产被掳走,脖子被扭折。他(指小说中的人物斯坦普)嗅到人皮的气味,人皮和热血的气味。人皮是一回事,但人血在私刑篝火上被煮熬又是一回事。恶臭熏人,恶臭直接从《北极星》报纸上散发出来,从目击者的嘴巴里散发出来,镌刻在辗转传递的信件中那些潦草的字迹里,记载在满纸皆是‘虽则然而’的字眼、呈献给政府机构审阅的那些文件和请愿书里。恶臭熏人。……”
不过,与通常的“抗议小说”不一样,在本小说中,象这样把抗争的呼声溢于言表的文字并不多。面对黑人同胞命中注定陷进美国现实中所必须经受的痛苦遭际,作家托妮·莫里森强抑住了自己的愤慨,将小说的叙事中介降到了最低限度,而是用人物自身的声音来展示肤色的惩罚所带来的黑色的愤怒,并且让众多人物以各各不同的声音相互交锋,在争辩之中共同完成对于“美国人种”的“复杂命运”的理性思索,从而提出道义的质问。借用巴赫金的话来说,作家托妮·莫里森的艺术思维具有了开放性的特点。表现在小说结构上,即是由“不同的声音用各自不同的调子唱着同一个题目”,形成了“多声部性”,即复调,而不是独白式的“同音齐唱”。
巴赫金认为,独白小说中,只存在作者一个声音,主人公在作者规定的情境中行动、感受和思考,众多人物表现为“同音齐唱”。而在复调小说中,作者不看重信念和信念通常所具有的独白性。作者探寻真理,但不把真理当作自己意识得出的结论,而是面向作品主人公的声音和议论,在众多他人的声音和他人的议论中完成对真理的探寻。所以复调小说中的主人公不仅是作家描写的对象、客体,同时也是表现自己观念的主体。他们都是些“思想式”的人物,有思想,有独立意识,爱思考和探索。作者感兴趣的,是主人公对世界及对自己的一种特殊的看法,对自己和对周围现实的一种思想和评价的立场。亦即是说:“重要的不是主人公在世界上是什么,而首先是世界在主人公心目中是什么,他在自己心目中是什么。”(注:《纽约时报》,1988年4月1日。)在复调小说里,并不是由作者的统一意识支配人物的性格、命运和行为,而是众多的人物同他们各自的世界,直接在紧张的事件、问题的探索和思考中出现。他们热衷于自我分析,并随时同他人展开争论。在激烈的内心冲突与众多意识的相互对峙中,折射出人物对自身和身边环境的叙说,张扬人物自己对人物的见解。总之,作者所描写的,不是单个意识中的思想,也不是不同思想的相互关系,而是众多意识的相互作用。而相互作用的每一种意识,都具有异乎寻常的独立性和充分价值,诚如卢那察尔斯基所强调指出的:“在小说中确实起着重要作用的一切‘声音’,都是一种‘信念’,或者是‘看待世界的观点’。”(注:米·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
在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娇女》中,就有众多的具有独立性和充分价值的声音。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类:一、主人公瑟思和她的家属人员——婆婆贝比·萨格斯,儿子霍儿德和布拉格,女儿丹佛,和屈死的娇女的冤魂;二、以保罗·迪、斯坦普·培德、艾拉、约翰、蕾娣、琼斯、尼尔森·罗尔德等组成的黑人群体;三、白人群体,包括幸福家园的奴隶主咖腊夫妇与老师及其侄儿,辛辛那提市的民主人士鲍德温兄妹,流浪女孩阿密·丹佛等。这些人物的不同声音,对同一件事件作出的不同评价,使小说结构的不同成份之间贯穿着一种对话关系,如同音乐中的对位旋律一样对立着。同时,这些不同声音之间的争辩,又在女主人公瑟思周围营造了一种复杂、微妙的氛围,逼使主人公在同众多他人意识紧张的相互作用中,以对话的方式与客观的现实世界相抗衡。
巴赫金把复调小说中的对话分成两类:“大型对话”和“微型对话”。“大型对话”是就小说整体结构而言的。即情节线索、人物组合关系上的“对位”性。“微型对话”则表现在主人公与主人公之间的非封闭式的对话之中,以及人物内心对话折射出来的他人语言,即带辩论色彩的自白体。“到处都是公开对话的对语与主人公内心对话的对语的交错、和音或间歇。到处都是一定数量的观点、思想和语言,合起来由几个不相融合的声音说出,而在每个声音里听起来都有不同。”(注:米·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作品的主题就在许多不相协调的不同声音中得到展示。
本小说中的“微型对话”,就围绕着瑟思的逃亡和杀死自己的女儿究竟有罪还是无罪而展开。
白人奴隶主声称:“那号人,本来需要特别关照和教化,才能防止这种同类相食的场面。眼下便是铁证:用那种所谓的小自由强加于他们,就是这种下场。”何况美国政府在1793年和1850年两次通过了关于捉拿逃亡奴隶并判刑的法令,所以法官把瑟思关进监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得把你关押起来。现在万事大吉了,你干得那样出色,以后有好日子过了。”——在白人的眼中,黑人根本不配享有自由。
黑人同胞称瑟思对《逃奴法案》作出的反响为“造孽的事”。用曾经接应瑟思逃过地狱之河的艾拉的话来说,瑟思犯下了触目惊心的罪行,甚至进而怀疑她的身份:“我可不了解瑟思是什么人,也不知道她的家底。……她坐着大车到达了目的地,而丈夫却下落不明,这事怎么解释?再说,在那荒山野岭里,她怎么能凭自己一人把那娃娃生下来?口口声声说绿林中冒出一个白女人,作了她的恩人。说呀,你相信吗?……我的朋友可不会用钢锯杀死自己的孩子。……”于是,整个辛辛那提市的自由黑人,都嫌弃瑟思,殃及她的婆婆与儿女。他们远远地躲避着蓝石路边的124旧屋,即使马车路过,车夫也要抽打着马儿奔驰而去。 整整18 年,124屋裸露荒郊,凄清冷落,愿意向这幢旧屋接近的,只有那齐肩的杂草。连瑟思那个在逃亡途中出生的女儿丹佛、也从小就失去了童伴。孩子们总是对她退避三舍,甚至不愿与她比肩而行。
儿女们把瑟思视为专杀小孩的巫婆,对她充满了恐惧。这是丹佛的一段内心独白:“我爱妈妈,但她杀死了她自己的亲生女儿。虽说她待我百般怜爱,因为那事,我总是害怕见到她。她差点也杀死我的两个哥哥,他们是知道的。他们对我讲‘死吧——女巫!’的故事,告诉我是怎么干那种事,要是我也想干的话。说不定正是因为他们曾经差一点死掉,才那样地想参加内战。他们告诉我,他们要去参战的。他们俩,可能宁愿与拿刀行凶的男人相处,而不愿与拿刀行凶的女人搅和。而她,必定有什么不可抗拒的理由才会去杀死自己的骨肉。这一辈子,我总是担心受怕,怕那曾经出现过的迫使我母亲杀死我姐姐的不可抗拒的理由又会再一度出现。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理由,不知道会是谁遭殃。……”
连曾经与瑟思一起身为奴隶的保罗·迪,一旦了解真情,也同其他人一样,一反常态。而且他自以为看到了更为严峻的事实:比瑟思的行为更为严重的是她的观念。下面是他与瑟思间的一段对话:
“你爱得太痴了。”
“爱得太痴了?……是爱就必须深厚,不深厚就不是爱;肤浅的爱绝不是爱。”
“是呀。那样也没有用,是不是?有什么用?”
“有用!”
“怎么有用?两个儿子出走失踪了。一个女儿丧了命,另一个又痴守在院子内不出门。怎么有用?”
“他们没有回到幸福家园。那个老师没有逮住他们。”
“那儿也许更糟。”
“我才不管哪儿更糟呢。我只需知道什么是不可忍受,怎样使他们远远避开。而这个,我做到了。”
“你做错了,瑟思。”
“什么意思,难道我应该回到那儿去?把我的孩子们带回到那儿去?”
“也许还有办法,别的办法。”
“什么办法?”
“你长了两只脚,瑟思,不是四只。”
保罗·迪也把瑟思的行为视作是违反了人性的动物行为。他的解脱办法是默认命运的安排。他俩之间的距离远远地拉开了。
而主人公瑟思自己,也在有罪还是无罪之间无休止地挣扎着。她的内心深处响彻着两个分裂的声音:对于周围的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强加在她头上的罪名,她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辩护,却又认为无需辩护。她的行为的正当性是不辩自明的。所以,18年来,她孤傲、清高地离群索居,在冷遇中忍受着124旧屋的罪孽, 又从不放下手中的利剑和坚盾。而面对自己最宠爱的女儿的冤魂,她无时无刻不在企冀弥补那把钢锯的罪过。为此,18年来,她让自己的思路迂迴曲折,死死地禁锢在苦难命运的记忆之中,她让自己的声音喋喋不休,对保罗·迪,对丹佛,对娇女的阴魂,绕着一个话题盘旋:
“这娇女,是我女儿。我的女儿,瞧,不用求,她自己回到我身边,而我不须向她解释道歉。当时,我手忙脚乱,来不及向她解释。必须当机立断。当机立断。必须把她送到妥当的地方,保证她的安全。我这一番爱心是够狠的了,但她还是回来了。……虽说没有必要了,我也要向她解释一下,要向她说明:我为什么要那样做。要向她说明:我不杀她,她会怎样死去,而我所不愿看到在她身上发生的事又会怎样发生。……我第一次挨了毒打,决不愿挨第二次。谁也不可把我与孩子分开。……我是尝够了那个苦果,不容许任何人任何鬼也逼得你去尝试。……”
瑟思的话,是内心对话的对语。她要说服的是别人, 其实更是自己。说服语调的增强,是在与自己身上的另一个声音进行内心的对抗。正是深爱,又丧失了爱的对象,导致了她最终的精神崩溃。
在小说中,唯有婆婆贝比·萨格斯对瑟思的暴力行为既不谴责也不赞扬。她对瑟思的劝告是:“放下吧,放下你手中的利剑和坚盾,不要再策划战争了。”这位饱尝了人生悲怆的老人,也曾抗争过。在儿子以前程和生命为代价赎回了她的风蚀残年,进入了辛辛那提市其他自由黑人的社会圈子以后,她还试图以“林中空坪”里的宗教仪式唤醒自己和黑人同胞的人格意识。她告诉大家,他们唯一能够获得的拯救来自于他们自己的追求和想象。然而,在白人撞进了她的院子,发生了那场惨痛的流血事件以后,在“白人赢了”以后,她的信念分崩离析了。她意识到自己关于个人身心意志的作用的思考是错误的,黑人无以主宰自己的命运,黑人的苦难绝无拯救的可能——想象的也好,真实的也好。“那些白色的鬼东西,夺去了我所有的一切,夺去了我所梦想过的一切。”她说道,“而且还伤坏了我的心。这人世最晦气的莫过于那些白人。”124屋门关起来,忍受着鬼魂的怨愤。她整个身心衰竭了, 终于卧床不起,用残余的一点精力,不懈地思索着各种色彩的意蕴,“想着人世间那些对人无害的东西”。临终的那天,她宣告60年为奴隶,10年为自由民所得出的人生教训:人世间,白人是一切罪恶的祸根,“他们作恶没有止境”。她把这一声音永远留给媳妇、孙女去咂磨品味。
我们从瑟思和贝比·萨格斯的沮丧、争辩与反抗中不难看出,这场对话的实质已经超越了众多人物意向与声音所参与的具体事件——一个女奴的逃亡与杀婴的有罪与无罪,而是指向了整个社会的蓄奴制度,是瑟思和贝比同众人就种族歧视与压迫的社会现实的争辩。这就是主人公在整个小说中要完成的任务——与美国种族歧视与压迫的历史现实和文化现实相对话。
托妮·莫里森的不凡之处,在于她并没有简单地用黑人的阵营和白人的阵营来划分两种意识、两种观点、两种评判的对立和交锋。在白人中,也有在瑟思逃亡途中尽心尽力帮助她的好心女孩阿密·丹佛;也有不愿见到有人作奴隶、对蓄奴制疾恶如仇的鲍德温兄妹,他俩为逃亡的黑奴提供衣物、马具,为狱中的瑟思奔走呼吁。可以见出真正的对立并不来自具体的个人,而是罪恶的社会制度。至于那“弥漫于空气中的滞重的流言蜚语的气味和充满敌意的恶气”;那“一个具有奴隶身世的黑人哪有资格施舍”的声音,都是出之于黑人同胞;那“整座城市的鄙夷”持续了18年,一直延续到废除了蓄奴制以后,并且还将继续延续下去,就足以见出蓄奴制文化的渗透性和滞后性了。
美国历史学家帕拉·基丁斯在庆贺《娇女》荣获1988年度普利策奖和人权奖时说:“伟大的美国小说不能回避压迫和爱这两个关键问题,美国黑人妇女恰恰被卷入这场风暴的旋涡中心。”(注:米·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
《娇女》便是这么一部名副其实的伟大小说。
瑞典皇家学院在授于托妮·莫里森199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时声称:托妮·莫里森“以其富于洞察力和诗情画意的小说把美国现实的一个重要方面写活了”。
《娇女》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标签:小说论文; 娇女论文; 巴赫金论文; 文学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美国史论文; 美国文学论文; 汤姆叔叔的小屋论文; 黑人文化论文; 托妮·莫里森论文; 文化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