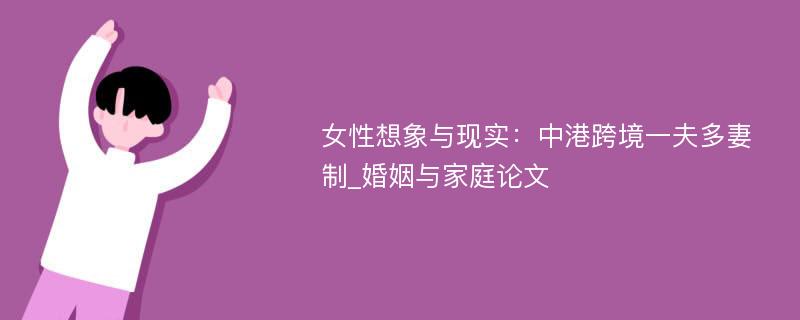
女性的想象与现实:中港跨境一夫多妻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港论文,跨境论文,现实论文,关系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人到中国内地打工、投资的人数越来越多。香港位处中国南方,所以把这种往北面找生活的移动,称为“北上”。据香港政府统计处的最新报告(2003年1月至3月之间,香港政府统计处抽样调查了1.11万个住户,受访住户内的15岁及以上人士,在过去一年北上就业的情况。调查估计约有23.8万人通常在大陆工作,而这个数字不包括只到内地洽谈生意、巡视业务或是往返两地的运输业人员)指出,2003年有接近24万香港人到内地工作。与1992年的6.4万人相比,北上的人数,十年之间增加了接近4倍,速度之快和数量之多,反映了中港两地日益密切的关系。对于这个发展,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影响方面。然而,让这个发展真正落实的、日复一日辛勤地跨越边境工作的人员,他们的经历、过程中所包含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价值的急速变化,却是为人忽略的。尤其是,移动人员中78%是男性,明显的是种性别化的流动;这种性别化的现象,指出了社会上对于男女分工和可流动性的规范、不同性别被要求对家庭责任不同的承担,以及社会因而赋予他们权力上的差异。文化上,这种人口流动也显示了传统价值观念,在新环境中所发挥的功用以及面对的挑战。北上的男性逗留在内地的时间由每星期1天到6天不等,也有不少是每月只回家一两次。可以想象,不但流动人员在个人、社会和文化层面上,都需要有所调适;他们的家人,也经历相应的改变。尤其是流动人员的家庭生活,以及他们与妻子和家人的关系,因分隔而产生疏离;个人方面,流动人员的人身安全和情绪的排遣,也牵动着留港的家人的担忧。而在社会层面上,这些因素,是否导致家庭关系和结构上的重组,其中所发生的变化,在学术上研究甚少。本研究以香港男性北上引起的婚外情“包二奶”现象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审视当代婚姻及家庭的观念。
由于跨境流动人员以男性为主,一般有关包二奶的论述之中,都以作为“丈夫”的男性角色为讨论中心。也就是说,“包二奶”被界定为完全是一种男性主导的行为,因为在这个关系里面,男性的能动性体现在他的选择权,而女性只可以被动的接受。这个观点认为,作为“二奶”的女性,像商品一样等待顾客来挑选;作为“老婆”的,只能在惶恐中等待。这种讨论忽略了女性个人(注:谭少薇(1998:439~445)对于人类学应加强对个人与女性的研究作为中国当代研究切入点的讨论。)的主体性,把女性排除在社会关系的建构和再生产的过程之外,也因此强调了男性在社会关系,特别是婚姻关系中的主导性,因而确认了女性在这种关系中的从属性。本文通过香港和内地妇女自己的说话,(注:有关包二奶的男性的看法研究甚少,可参看Young and Kwan(1995:47~59)。)探讨女性如何参与制造“包二奶”这个想象并构建为他们生活中的现实;他们又如何通过这种主体之间的互动,为延续父权中心的社会文化制度提供有利条件。
本研究资料于2002年至2003年进行搜集,主要方法是个人深入访谈和小组聚焦讨论,辅以田野考察和问卷调查。本文的讨论分析,主要建基于访问资料,包括香港妻子和内地妇女的个人访谈和聚焦小组讨论,探讨两地女性对包二奶现象理解的异同,分析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受访者年龄由18岁至52岁,教育程度由小学到硕士,职业包括家务劳动者、文员、教师和公司经理等等。婚姻状况以已婚为主。聚焦小组之一是丈夫没有包二奶的香港妇女;另一个小组由没有作为香港男人的“二奶”的内地妇女组成。个人访谈对象是15位内地的妇女,她们都有作为香港男性的“二奶”的经历。每次个人访谈或小组讨论的时间为60到150分钟,在香港进行的访谈使用广州话,在内地进行的访谈使用普通话。
二、隐晦的事实
一直以来,香港社会上对“北上”的讨论,多集中在男性个人调适问题以及其引起的家庭问题上。具体说,坊间的兴趣聚焦在已婚男性在内地发展婚外情的问题,特别是所谓“包二奶”的现象。包二奶是指男性与香港合法妻子以外的女子在内地建立固定的关系,男方以经济和物质上的供给,换取女方的性和伴侣关系,和/或家庭劳动包括煮食、照顾孩子、打扫家居等服务。现实中,一个男性的“二奶”可能不止一个,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过都统称为“二奶”。这种实质上的一夫多妻关系,往往由于跨越中港边境而变得更复杂。20世纪90年代的前5年,是包二奶讨论的高峰期,按非正式的估计,北上的香港男性6人之中可能便有1人包二奶。这个估计或许夸大,但正因为无法证实,却反映出社会上对包二奶行为的关注,甚至于形成了一种法理与道德恐慌。(注:有关道德恐慌的讨论,参看Ben-Yehuda(1986:495~513)。)因为社会上公认这种行为挑战和破坏家庭制度,而且将为社会福利构成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它违反道德、触犯法律,可是现行法规却对它束手无策。在内地,它实质上是违法行为;尤其是2001年中国婚姻法修订以后,违法的界定更为清晰。但由于香港男性的包二奶行为发生在内地,超越了香港的司法权,妻子和帮助他们的社会机构都受到很大的掣肘,要搜集有关丈夫这个行为的资料并不容易,遑论进一步把他们绳之于法了。香港男性似乎注定能够逍遥法外。这种人人皆认为普遍存在,并且为广大妇女所恐惧的越轨行为,却是难以确认,以至形成了充满矛盾而隐晦的事实,为大众提供了一个想象和构造的空间。(注:除了香港男性的婚外情,台湾商人在内地的婚外情也广泛受到关注,学术讨论见Chang(1999:66~99)。刘文成(2000)一书较普及的讨论台商在大陆面对的各种生意上、心理上,以至家庭上的问题。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参看Jankowiak,Nell and Buckmaster(2002:85~101)。)本文认为,“包二奶”一方面是一个社会现实,但同时也是一种集体的想象。在这个集体想象建构的过程中,个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与社会上对性别的文化期待和社会经济环境,互为因果,创造了并且延续了“包二奶”这个文化行为。
“包二奶”的隐晦,建立于香港社会环境里的三个矛盾之上。首先,香港的婚姻法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当一个人与多过一个配偶结婚便被视为重婚,属于刑事罪行。在1995年的一个调查中,谭与柯(1995:141~158)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香港市民,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为理想与常规。纵然如此,一夫多妻的关系在现实中是为数不少的。原因是,婚姻法修改于1971年,所以1971年以前的一夫多妻关系并不违法。由于这个历史背景,在香港,年长一辈的婚姻中,一夫多妻很普遍。故此,不少中年的香港人是在一父多母的家庭中长大的,大家对于一个男人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妻子这种现象,并不觉得陌生。就算在一父一母的家庭中长大的,不少人也觉得一夫多妻不足为奇。大众甚至认为,如果男性能够妥善安排,三妻四妾反而是一种经济和个人能力的表现,是社会地位的象征,甚至是男性所渴望的一种“成就”。故此,当香港男性在内地发展婚外情的行为形成了一个潮流,舆论似乎都集中以中港两地的经济差距为解释,认为是香港人相对优越的经济条件,让香港男性在内地以相对低廉的价钱,可以购买内地女性的服务。所以很多人觉得这是有相当经济能力的男性的一种“正常”行为,并不构成犯罪。
不过,这个解释只能说是经济环境提供了必需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不能解释为什么男性选择去包二奶。经济行为作为一种文化决定,必需建立在价值观之上,当事人作为能动者亦会衡量过得失,才作出决定。男性中心的社会关系与父权意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基础,使所谓香港男性的经济能力,变成了实际的消费女性的行为。泛滥的消费主义为“包”二奶者与“被包”的二奶提供了客观条件,把女性——特别是年青的女性——塑造成为消费品,在市场上可以被任意选择、购买。
这种性别化的消费模式,反映了香港社会以男性的需要为基础的人际关系。日常生活里面,香港女性表面上被冠以“女强人”的称号,被视为出色能干、与男性平起平坐,在工作与家庭方面都能够享受与男性平等的关系。实际上,在就业机会、经济报酬、事业发展方面,妇女仍是面对严重歧视的。举例说,相同工作类别中,妇女的收入只及男性的70%。在职业选择方面,女性受到“玻璃墙”的限制,在工种上有明显的性别割裂,大部分尤其是劳工阶层的女性往往只能获得与男性相比薪资和地位较低的工作;在升迁方面,他们受“玻璃天花”的限制,事业发展的阶梯通常不能与男性一样伸展,未能享受到平等机会;在公共事务参与方面,例如负责制订政策的政府政务官,各职级中女性只占25%~30%;在婚姻和家庭关系中,男人仍普遍当着一家之主,家庭的主要决策权是向丈夫倾斜的,妻子的权力常常限于家务劳动和家庭成员的照顾方面。
香港予人很“西化”、“现代化”的大都市的印象,容易让人觉得妇女地位高涨、男性特别尊重妇女。事实上,“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男性“风流”是可以接受的,这类保守的思想,仍然是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因此,不难理解,女性被商品化、婚姻关系中以丈夫为主导等等不平等的关系,也是“民众智慧”中视而不见的事实。以经济收入、权力的掌控、社会尊重三方面界定社会地位,明显地,女性都处于弱势。可以说,香港社会的性别观念是十分保守的。在这种背景之下,女性如何生存于一个不利的环境,并且理解包二奶这个社会现象?
三、香港女性看包二奶
在聚焦小组讨论中,我们的被访者对包二奶有一个颇为一致的定义:包二奶行为是一段长期而有固定对象的婚外情,男的一般会负责二奶的生活费,这就如男性成立了第二个家户。一谈到包二奶,被访者均认为男性在大陆工作的话,这方面的引诱十分厉害,因为在一般日常论述中,二奶是被理解为十分主动诱惑男性的。因此,“丈夫北上工作”对于妻子来说是个警号,是婚姻可能出现危机的讯号。香港的妻子的这种忧虑是普遍而真实的,甚至可以说已发展成一种恐惧。
其中一位参与讨论的黄太太(注:文中所有受访者的名字皆为假名。),是一位50岁的已婚妇女,她的职业是工厂经理。她认为,当一个男人已经结婚,而又发生婚外情,而这个第三者与他的关系是长久的,就是包二奶。此外,男方会负责女方的生活费,而女方她又会为男方生孩子。48岁的陈太太同意这种看法。她说:“(男人与二奶的关系)肯定是长期的,(二奶)亦会(跟他)生儿育女。”同样是家庭主妇的艾美更认为:“她们(二奶)的手段很犀利,我觉得她们是无所不用其极。(好像理发店)你经过她们的门口,你无心上去,她们就拉你,又故意弄湿你的头。”
作为妻子的被访者对于男人包二奶的原因,有颇为一致的看法。这些原因可以分为天性与社会因素。与天性有关的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男人是天生野性的动物,他们不甘寂寞,爱寻刺激;其次,二奶往往是比太太年轻漂亮的,对男性有自然的吸引力。与社会环境有关的则是以下两个原因:第一,男性受到朋辈的压力;第二,内地女性的主动引诱。明显地,作为妻子,她们觉得男性因为有野性的本质,当受到“适当的”引诱或压力时,便会显露出来。陈太太说:“我觉得男人都是有些野性的,也是自私的。”她更认为男人“玩女人”是会“上瘾”的,意味着“性”对于男性来说是生理主导的。艾美补充说:“我觉得没有猫是不吃鱼的……(又或)被朋辈影响你,朋友用激将法,说‘你太太唔准呀?有无搞错呀(之类的话)’。”她们认为,当男性抵受不住生理的诱惑或朋辈的压力时,便会做出“包二奶”的行为。
既然认定“男人天生是野性的”,妻子对丈夫到内地工作都会担忧不已,但同时又无可奈何。于是她们为丈夫设想到很多不会包二奶的原因,聊作自我安慰。这些原因包括两大类:一是丈夫寄情工作,能够珍惜事业,不会做破坏前途的傻事;二是丈夫是正人君子,不会到色情/容易接近女色的场所,避免受到诱惑。例如黄太太说:“他(丈夫)想做好公司就不会做这种事情(包二奶)……他没有到‘按摩场所’……没有听闻他去。如果有去的话,我觉得(包二奶的)机会比较大。”艾美也认为:“(我)丈夫不喜欢流连卡拉OK或按摩场所,而且丈夫生意很忙,根本没有空去包二奶。”
另外,不少受访者指出,夫妻间最重要是彼此信任,因此她们对自己的丈夫不会怀疑。艾美就坚决地指出:“我觉得最重要是信任。”此外,北上的丈夫对留港的妻子也会灌输一些看法,从而减低妻子的猜疑。阿芬(43岁,家庭主妇)说:“他经常同我讲,有一些女性会送上门。但他自己也会指出:这些女人与你一起是为了钱……如果跟这些女人一起,就会被她控制……所以他会好小心(处理)这种事。”对丈夫跨境生活中的行为,受访者明知道他们是无法控制的,只好用“忍”与“等”作为对策。在这种婚姻关系中,妻子无奈掩耳盗铃,把自己制约丈夫的权力放松,以致原来应当平等的婚姻契约关系,变得向丈夫那面倾斜。结果是把自己处于被动的境地。不过,分隔家庭中的妻子,也有其主动性。由于不能转变丈夫的工作结构,她们转而巩固家庭制度,以保障她的终身事业一家庭以及其中包括对她至为重要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心理上和经济上的安全感。
香港妻子对家庭和丈夫的维护,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把家庭责任的强化。这种能动性的其中一种体现是把夫妇的责任简单化,分为“男主外”:男性赚钱养家,“女主内”:女性包办其他所有家庭照顾工作。受访者中,夫妇间分工有明确的界线。家中日常的大小事务,往往由母亲独力面对和解决。阿芬这样总结她家中的分工情况:“他(丈夫)在家的工作就是和女儿玩……(子女)读书、功课完全不用他处理……我会一手包办。”陈太太说:“当子女还小时,(丈夫)就会和他们玩。长大之后,就会与他们倾诉。”连全职上班的黄太太也说:“我先生主要是工作,其余则全部由我负责,如子女的读书、功课等等。”在受访者中,普遍认为父亲在家中的角色是给子女提供娱乐,以及有问题时给予意见。当子女年幼时,爸爸会和他们玩耍。子女长大后,爸爸则扮演辅导者和倾诉对象的角色。至于日常的家务劳动和家庭成员的照顾,则必须由母亲执行,不论她是否有自己的职业,情况都是一样。可见,“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安排是根深蒂固的。
这种家庭分工把丈夫推向事业发展,把妻子推向家庭维护;也就是说,男性的成就在家户之外,女性的成就在家户之中。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男性的失败在于事业不成功,女性的失败在于家庭有问题。因此,女性对家庭的付出远比男性多,对家庭的得失也看得更重。而这个家庭是以丈夫的需要为中心的,要让这个家庭和自己成功,女性必须以丈夫的需要为核心,牺牲自己的发展,照顾好家中一切;如果这个核心消失的话,围绕它存在的家庭也就不能再存在。
如果丈夫不忠,发生了婚外情,破坏了家庭和谐,作为妻子的会有什么做法呢?黄太太认为,如果丈夫跟另外一个女人发生了性关系,即意味着他喜欢另外的她,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就变了,她个人是不会接受的。小陶是一位43岁的已婚妇女,职业是文员。她说:“对(丈夫包二奶)这些问题,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我一定会离婚。”艾美也指出:“(丈夫包二奶)我也不可接受,不论是否有孩子。”面对丈夫包二奶的可能,受访者均指出会选择离婚,因为丈夫破坏了婚姻的承诺。纵然有了孩子,她们的选择亦是一样。由此可见这些香港女性的婚姻观念是很绝对的,对婚姻关系有一种绝对的要求。他们的婚姻观是十分理想化的,而且这个婚姻是以丈夫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当这个基础崩坏的时候,建立在它上面的婚姻也就不能再存在。然而,除了“不接受”和离开之外,妻子们似乎没有其他抗衡的办法。以香港的访问资料看来,香港的婚姻和家庭观,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制度,并借着女性的主观认同和她们在日常生活行为上的不断强化,得以延续。
四、内地女性看包二奶
对比香港的妇女,内地的受访问者的看法很不相同,而且也较多元化。梁小姐是一位30岁,未婚的行政人员,她说:“结婚是一个人生阶段,包二奶也是人生一个阶段。”她认为包二奶的男人年纪比较大,他们作出包二奶的行为,是因为跟太太年龄、兴趣不一样,因此再找一个人满足他的需要。23岁的小学教师、未婚的林小姐则认为:“结婚是男性为了实践妈妈的期望,(因为母亲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很传统的,(男人)对太太的要求很高;但在现实中,与朋友接触时,他要求的是另外的一面的。”由此可见,她们认为男性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或不同的社会情景,对伴侣是有不同的要求的。似乎太太的功能就是为了应付前辈、满足社会的期望;而二奶则是满足男人自己的需要。
谁会选择当二奶?其中一位参与讨论的徐女士认为:“她们是非常年轻的小女孩,本来是从四川或者是从广西或更贫穷的地区来的,(当了二奶以后)一夜之间可以变成一个小富婆。好像我认识的一个年青女孩,她领着小狗,走起路来悠悠的……”另外,已婚的马女士(31岁,职业是文员)认为:“包二奶是一种买卖,他们中间很复杂,也不排除有真情。……(二奶)的生活节奏比较慢,她们一般都不工作,打扮非常休闲。”这样看来,二奶被认定是有闲阶级,过着一种为大众向往的消费生活,与她们原来的经济水平和教育程度相比,她们在社会上的正向移动可算是不成比例的成功。比起香港女性受访者,内地女性明显的对包二奶现象比较少敌视。受访者都说认识身为二奶的朋友或邻居,觉得包二奶在国内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可能因为在个人层面跟二奶认识,受访者较少典型化的理解,也较少绝对的道德批判,因此她们对包二奶的现象抱着一种比较包容的态度。
程女士是一位46岁的离婚女性,她认为:“这种(包二奶)现象可能就是时代在变迁,发展到这个阶段,人民在富足的情况下的一种需求,特别是男性、女性……你看,不单是包二奶,或是包小子,包什么都有。每个人富足以后,就有这种心理需求。”徐女士是位32岁的家庭主妇,她也认为当二奶是一种个人选择。她说:“现在社会已经转变、发展,可以让个人有选择,过自己的生活……对包二奶的事,我也挺宽容。……我也见过包小丈夫的,我知道她很难受,看见她的老头,我就明白。”马女士也认为包二奶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价值观转变有关的,她说:“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比较快,人的观念就是对个性的追求。情感的要求比以前高了很多,所以现在每个人对私生活都抱着非常宽容的态度。……毕竟(当二奶)是一些经济基础不好(的女孩子),为了追求改变自己的生活,追求一种生活的需要去找一个香港人,至少在物质方面提高一点,可以改善。”另一位参加者,24岁,未婚的研究生李小姐,她认为:“我觉得两个人基于感情基础的,没有什么不对。因为两个人都是非常爱对方,即使是二奶,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对。他或许会离婚吧,那么到时她可能已不再是二奶。……你(二奶)聪明一点就可能迟早跟他结婚,那要看自己,反正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对的。”这些看法,可以解释为什么内地受访者对二奶比较包容;一方面是对生活水平改善的渴求,另方面是对个人选择的重视,还有对浪漫的爱情的憧憬。然而,这些包容不是来自对女性自主的尊重,而是对男性中心家庭制度的认同,以及这种制度为女性可能带来的物质安全感和社会地位。
此外,虽然国内女性受访者对二奶持较宽容的态度,但是她们对二奶仍是持有道德批判的。程女士,46岁,离了婚,是一位文员。她认识一位当二奶的朋友,她这样说:“(我这个朋友)当年也是一个大学生,很漂亮,她一下子就给人家安住了。……但十年后,她什么也没有。……她现在很凄凉。我们这些长得不漂亮的人,全靠自己,努力去工作,把自己锻炼得强强的,各方面能力都有,老了还能找工作。我挺自在的,快50岁了,还能工作。”马女士也说:“从内心说,毕竟这不是一件健康的东西,内心不会完全接受。”徐女士对二奶的道德选择也是不赞同的,她还说:“假如我的朋友做了二奶,我会不理她,(我会)骂她。这种爱是不理智的。如果要我选择,他是不是值得?还有社会的道德?还有我父母那方面,若得不到他们认可我回家也回不了。虽然情感很重要,但也要理智。”
五、想象以外:被“包”的现实
以上的讨论包含了中港两地女性对二奶的种种想象,包括她们的外表、个人能力、事业前途、道德观等等。当事人自己的看法又如何?研究员在深圳进行田野调查,与15位内地女性作深入访谈,她们都曾经有被“包”的经验。受访者的年龄介乎18岁与36岁之间,她们的教育程度分别是:5位小学程度,6位初中程度,及4位高中程度。婚姻状况方面,以未婚为主,有少数已婚或离婚,个别也有小孩的。至于出生的地点,除了一位女士是在深圳出生,另外14位都是来自外省。她们逗留在深圳的时间由半年至10年不等;大部分有工作经验,以工厂及服务行业为主,例如工厂女工、酒楼侍应、发廊洗头或按摩师等,而且大部分曾在不同省份工作,然后才在深圳定居。在受访的15位女性当中,被“包”的次数以1次为最普遍,共13人,被“包”两次的则有2人。
至于“包”的特点有以下几点:(一)男方与女方维持较长期的关系;(二)牵涉物质的交换;(三)当事人主观认定为“包”的关系;(四)他们的关系被社会认定为“包二奶”的关系。以下逐一作详细的分析。
在“包二奶”的关系中,男方与女方维持较长期的关系,“包”的时间由3个月至8年不等,平均1年多。男方与女方的见面方式比较多样化,长期同居只是少数。实际上,一般男方住在香港,以每星期一两次从香港北上时与女方见面为主。另外,也有因男方工作地点在广州和深圳,一星期里有3~5天是住在一起的。此外,在“包”的关系中,同居的关系是普遍的,但在居住安排方面,我们发现是有多种形式存在的。在一般人印象中,是“包二奶”的男方提供金钱租用一间公寓给女方居住,但在本次调查中,这种安排只占少数,共6人。我们发现,受访者中也有双方一起出资租用一个套间,这种方式共有2人。但更有意思的是,接近一半的受访者是住在由公司提供的宿舍或与自己的女性亲戚同住。也就是说,在居住方面,所谓“二奶”并不必然倚赖男方。由此得知,所谓“金屋藏娇”现象并不是必然的。虽然使用物质来换取“二奶”的关系仍是主导,但这种趋势现在正在转变中。
物质关系在包二奶的关系中也涵盖多种不同的表达形式。一般来说,“包二奶”关系是建立在物质上,尤其是在男方给子女方的物质,以作为交易/交换。在我们接触的个案之中,男方会给女方提供定期生活费,平均每月4000元,或每次见面给予“零用”几百元至几千元不等;又或男方馈赠礼物如衣服、新型号的手机、小首饰如手链等。受访者之中两位女性曾由男方提供旅游机会,在国内旅游享受豪华食宿。此外,有一位女性由男方安排移居香港。不过,调查也发现物质/金钱的流动,或“帮助”的提供,并不是单一的由男方给予女方,也有由女方给予男方的。例如:一位女受访者协助男方还债,另一位因男方收入不足,因而拒绝接受男方给予零用;也有一位安排男方前妻的儿子移居香港。由此可见,“二奶”们并不单是被动的接受男方的施与,双方关系也并不单纯是物质交易。“二奶”与男方发生感情后,她们也会为对方有所付出。这种行为的形成,跟女方如何主观认定自己的身份,她和男方现在以及将来的关系如何界定等变量,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探讨“包二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们也需检视当事人本身的主观认定,以及社会上对男女双方关系的认定。在此次调查中,值得留意的是,虽然有超过一半(共8人)的女性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二奶”,但仍有接近一半(共7人)的受访者不知道或不清楚自己是“二奶”的身份,当中更有2人以为自己当时是合法妻子。可见一些香港男人在发展婚外情关系时,是不会清楚向对方说出自己已婚的身份,当中更有部分刻意隐瞒真相,令女方投入感情。也有部分的内地女性不想求证男方是否真的单身或其实已婚,她们追求的是眼前的享受,没有长远的目标。无论知道男方的婚姻状况与否,女方主观认定对方是伴侣,是令包养关系开始的一个因素。
访谈中,女性在理解自己的身份时,用了“二奶”、“老婆”、“女朋友”及“朋友”等几个称谓。而女方及男方对这几个称谓有不同的选择,反映了身份认同上的性别差异。在女性方面,自称“二奶”只有1人,其次共有4人自称是男方的“老婆”,最多女性(共10人)将自己视作对方的“女朋友”/“朋友”。这些称谓的差异反映大部分的女性并不想当别人的二奶,她们实在宁愿做男方的朋友或女朋友,维持模糊的身份,避免将自己界定为插足别人家庭的第三者。将自己视作男方的“老婆”的几位女性当中,有2人是被香港男人欺骗,以为自己才是合法妻子。也就是说,只有3人明知男方已婚而仍与他维持婚外“夫妻”关系的。反观男性称女方为“老婆”的超过半数,共有8人,而没有一个称女方为“二奶”的。至于称“女朋友”的共只有4人。可见男性对这些称谓的理解与女性不一样。对于明明是“二奶”的女方,男性为什么称为“老婆”?作者认为是一种策略,让女方通过这个称谓以获取身份优越感,甚或以为这个名分是将来有可能成真的。这种身份模糊性,一方面冲淡了双方的罪恶感,另一方面增加了女方对正式妻子身份的希冀。两种原因的后果,都助长了男性在“包二奶”过程中的满足和权力。
此外,女方较少向外承认自己是二奶的身份,这可能因为女性在社会上受到较多道德束缚,因而表达较明显的羞耻感。调查发现,大部分的受访“二奶”只会让少数的同事知道,这也是我们可以找到二奶的途径,就是通过滚雪球的方法转介访谈对象。只有少数的女性会将被“包”的事实告诉自己的兄弟姊妹,尤其是那些感情要好或年龄相若的姊妹。绝大部分的受访者没有将自己的二奶身份告诉父母,一方面是因为不愿意父母担心他们的感情生活和将来结婚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她们觉得做二奶是丢脸的,害怕会令父母伤心和让他们在亲友面前没面子,所以她们会选择不向父母表白。纵然作为“二奶”可以让这些女性获得更多经济和社会资源,但她们必须承担道德方面的风险,为自己制造了两难的困局。
从“二奶”的访谈,我们认识到内地女性的价值观是跟主流社会十分一致的。她们对家庭与婚姻有美好的憧憬,认为女性最重要的是建立家庭,渴望结婚生儿育女,所以她们反对破坏别人的家庭,并且认为离婚再嫁是很丢脸的事。明显地,她们接受男性中心的婚姻关系,建基在这个前提之上,她们对香港也抱有一种向往,希望通过与香港男性的婚姻关系,实现到香港和改善生活的愿望。
六、“包二奶”的建构
很多人认为,“包二奶”现象的出现,是经济供求的关系,因为:(一)男性离开家庭到国内工作,在家庭温暖和性需要方面,出现了真空。(二)由于香港和大陆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经济差距,香港男性可以花很少钱就能获得条件更佳“二奶”的服务。(三)内地经济发展不均,流动人口找工难,很多年轻女孩为了生计甘于当上“二奶”。(注:Lang and Smart2002(546~569)较综合性的讨论,以及如Yam 1995的经济角度论述。)
“包二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建构,传媒的典型化描述扮演重要的角色。香港的传媒对于受包二奶关系直接影响的三方面:妻子、二奶和丈夫,往往是应用了平面而简单化的理解与讨论。首先,妻子一方面被描述为受害者,另一方面又被视为问题之源。前者因为二奶被界定为家庭的破坏者,所以妻子的婚姻内的权利受到侵害,要承受经济、感情等各方面的痛苦,传媒与大众对“香港太太”因而抱着同情的态度。然而,妻子也被批评自取其咎,因为她婚后疏于打扮、身材发胖,不能再吸引丈夫;她又只知照料孩子而忽略了对丈夫感情的照顾;因此她实在是问题的根源,而男性在这种情况下包二奶也情有可原。(注:社会福利界主流视包二奶为家庭与社会福利问题,如明爱家庭服务,参看该团体1995年有关服务报告。)害者与问题之源两种矛盾的身份,显示了社会对妻子的双重价值观,也是让香港妻子处身两难的境地。(注:有关大众媒体对妻子的矛盾论述和双重标准,参看作者1996的专文。)
反观在对立面的“大陆二奶”,在传媒的描绘中,不是被物化就是被妖魔化。她们被塑造成年轻、美貌、身材好、容易控制,以及能满足男性的需要,以这种形象成为商品,让男性任意观赏、挑选、购买、用完即弃。但另一面她们又被描述为“狐狸精”,是妖魔的化身,破坏原本美满的家庭。表面上她们像胜利者从香港女性手上将香港男性攫夺过来,但结构上对她们缺乏平等机会,导致她们欠缺教育和工作选择的社会状况却并未受到讨论。
在这次访谈中,大部分的受访者均来自农村,平均教育水平都不高。这些外来的打工妹,教育程度由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不等,以初中为多,只能从事低薪酬及低技术的工作,如工厂女工、餐厅服务员、发廊洗头、美容按摩等。这类工作时间长,工作机械化,而且乏味,工作条件不令人满意,而且缺乏晋升机会。以部分受访者的工作按摩师为例,请假要扣钱,按摩时数不够要罚钱,客人不满意要扣钱,而且入职押金高又或不获退还等。此外,因长时间按摩而发生肌肉劳损等职业病,也常常面对性骚扰。除了顾及自己的工作前途和在特区的生计,她们也需汇款回家,经济压力不少。按摩师的社会地位低,而且常常受人误会是色情工作。不少从业员希望转换工种,但工作环境令她们身心疲累,也难有时间与多余的金钱进修,以求获取较佳的工作机会。还有年纪渐大,也要面对结婚生育的催促。去或留,突出了流动人口,特别是女性流动人口的困境。
当我们检视受包二奶行为影响的人士时,发现男女在传媒的报道中,其形象塑造及相关的社会代价是很不同的。大众传播媒体似乎对男性特别宽容,构造了一个丈夫的浪子角色与家庭责任的迷思。在传媒日常塑造下,男性在包二奶的过程中,如果同时仍负起家庭责任,社会舆论对他的责备是十分有限的。用受访者的语言说,男人对家庭的责任是:“交足钱、交足人”。在他们的眼中,作为“主外”的男性,能够保障妻儿的生计,下班以后也抽空陪伴家人,就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至于其他的行为,包括包二奶,如果为时短暂的,往往视为“逢场作戏”,不必认真看待。况且,在传媒的描述下,能够负担得起包二奶的男性,甚至被社会认同,认为他有经济成就,或者是有个人魅力,越轨的行为反而成为一种社会地位象征。例如报章往往以猎奇式的手法,报道富翁的婚外情以至三妻四妾,使用的语言或带艳羡,或是视为正常。电视戏剧节目也不乏男主角在对配偶不忠的情况下,不但获得妻子的原谅,二奶也往往能辅助他事业发展。而如果有一天他醒悟过来,重回妻子身边,他便被视作回头的浪子,不单妻子会接受他,社会、邻里及朋友也会视为良好模范,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注:以中年男性婚外情为主题的香港电视剧,最为人熟悉的是1994年的《再见亦是老婆》,至今仍是该剧种的代表作,影响深远。剧中男主角厌弃婚后发胖的太太,与年轻貌美又能干的女人发生婚外情。女主角虽然与不忠的丈夫离婚,但当他身陷囹圄,情人离他而去,他满心懊悔的时候,她便回到他身边守候。剧中女主角婚后的“肥师奶”形象,深入民心,这个名词亦发展成日常用语,泛指不懂打扮,行动不利索,没有知识,贪小便宜,惹人讨厌的中年妇女。)凡此种种,都为男性婚外情或实质一夫多妻关系,建造了理想的文化环境。香港男性在内地的实质一夫多妻行为,可以说是没有社会代价的。
香港的妻子往往希望不忠的丈夫有一天浪子回头,以保存家庭的完整。形成了妻子与二奶之间的角力,为了一个男人而互相竞争。(注:女性之间的我Vs她建构,参看Burns(1999)。)这些源于妇女对家庭价值的内化,认为女性最终的事业是家庭,婚姻/家庭的失败就是她个人的失败,加上社会资源和权力分配不均、女性欠缺支持等,往往使妇女陷入了一种过度依赖以丈夫为中心的家庭;更讽刺的是,这种家庭的维护,和对妇女个人独立自主的轻视,反过来巩固了父权意识和制度、延续对女性(包括妻子和二奶)权利的压抑。
七、结语
对于“包二奶”的问题,不论男性和女性都以熟识的男性中心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为基础,将丈夫的婚外情诠释为与婚姻关系等同的行为。因为不能超越父权意识,论述只能停留在个人道德责任、福利负担和经济利益等问题上。本文探讨“包二奶”的文化现象,认为对于家庭的学术研究应结合结构与个体的分析,以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论丰富家庭与婚姻研究,并审视婚姻与家庭制度中的性别意识(注:有关家庭研究与女性主义的关系,参看Thompson(1995:847~865)。)、权力关系,探讨其与各种社会制度的互动。(注:Wolf(1972)对于台湾社会的父系家庭的经典研究,她以日常生活中的女性行动为中心,提出“子宫家庭”的概念,指出传统上如Friedman(1970)以男性血缘为结构基础的理论框架的不足,为华人家庭研究指出以女性为重点的研究方向。Chan(1997)研究香港农村妇女争取继承权的过程,指出女儿对“家”的观念跟儿子和媳妇迥异,引申出家族中不同利益团体的存在问题。传统上有关家庭与婚姻的研究较少触及女性的角色,例外的有陶毅与明欣(1994)。)作者认为,这是关于女性的生存空间的问题。造成妻子与二奶的困境,是因为男性中心的社会结构,以及顽固的性别不平等的文化观念,限制了女性所能获取的社会与文化资本。社会现象的改变,须从不同层面进行。在物质层面上,性别之间的经济与权力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现状必需改变;在社会关系层面上,不同性别应该获得平等机会;在思想层面上,必需推行长期性别教育和反对把女性商品化,抗衡性别不平等的普及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