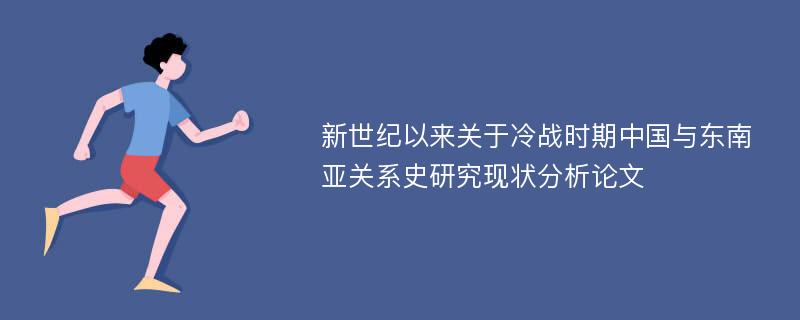
新世纪以来关于冷战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现状分析
范 宏 伟
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历史进程是以美苏两大阵营冷战对抗为主要特征和基本动力的,东南亚区域处于亚洲冷战的前沿地带。在冷战时期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地缘政治、大国对抗等各种因素不断冲击和影响着双边关系,形成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这一历史遗产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和情感以及双边和多边关系的调整与重塑。2018年6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所谓正确历史观,就是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注]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 。同月,国家社科基金开始设立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项目,其中包括“中小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别史、周边外交及中外交往史”。在此之前的2013年10月,中央曾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前所未有地强调了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重要性和优先性。之所以再度强调周边外交史、国别史研究的重要性,一是因为现实战略和利益的需要,二是中国学界对周边关系及其历史问题的研究尚显不足。
长期以来,在新中国外交史和对外关系史研究领域,同与美日苏等大国的关系史研究相比,东南亚一直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这突出表现在研究成果数量少、研究国别严重不均衡。截至目前,除越南、缅甸、泰国之外,中国与菲律宾、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家的关系史研究,尚未见通史类学术著作出版,即使中国与越南、缅甸、泰国三国关系的通史性研究仍存在较大空间,有待进一步深化和细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冷战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虽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进步,但研究数量仍然不足,无论是著作还是文章的数量均较为有限,学界尚未搭建起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较完整的知识体系和历史框架。虽然相关学术期刊和论文集就这一议题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基本是事件性、专题性、片段性的研究,且主要集中在越南问题上。这对于整体了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而言,过于碎片化,不成体系。无论是冷战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发展的宏观历史脉络,还是一些基本史实和重大事件等,均未得到充分研究,如以中国外交政策变迁为视角,从“一边倒”到实行和平共处、争取东南亚和平中立区,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历史转型进程;从中苏结盟到中苏分裂、从中美对抗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中美苏三角关系框架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变化的轨迹、动力与机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建交或关系正常化的过程;朝鲜战争、波匈事件、中国实验原子弹等标志性事件对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态度与政策影响;中国台湾与南越、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关系;中国因素与冷战在东南亚的起源和结束;等等。在研究深度和理论水平方面,不少研究缺少时代精神和国际体系变化的宏大背景意识,就事论事居多;大部分相关研究仍停留在双边关系、事件描述层面,研究的深度和理论水平不足。很多学者已就此客观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或弊端[注] 类似反思和批评可参见陈乔之等主编:《中国的东南亚研究:现状与展望》,暨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编:《中国东南亚学研究:动态与发展趋势》,香港社会科学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牛军:《三十年来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马荣久:《冷战时期中国外交研究综述》,《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2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159—166页;梁志:《“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学术座谈会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5期;王立新:《从外交史到国际史: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等等。 。
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在欧洲,英国算得上散文、随笔的大国……法国次之,而德国则颇有逊色[4]。”虽说在季老眼里,法国的散文稍逊于英国,然而当人们谈论起近代欧洲哲理性散文时,法国可以算是冠绝一时。钱钟书曾在《围城》中说道:“法国人的思想是有名的清楚,他们的文章也明白干净……[5]”谈到法国散文大家,就不得不提蒙田,他一生只写了一部作品,即世上第一部用法语书写的散文集《蒙田随笔》,该著作和培根的《人生论》、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并称欧洲近代三大哲理散文。
显然,这种研究状况无法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充分有效的智力支持。这种认知落后于形势的情况实际上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存在。1955年12月8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就指出,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存在“认识落后于形势”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对东南亚的形势估计不足;对驻在国的形势估计不足;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尤其是新中国的影响估计不足;对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友好合作的可能性估计不足[注]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701页。 。70年来,这一状况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这主要受到中国内政变化与外交重心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十年曾导致东南亚研究出现断层,从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又主要面向西方发达国家。因为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服务现代化建设是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中心任务之一,中国的外交重心自然更为关注资金和技术雄厚的西方国家。当然,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对外关系中,大国原本就占据中心地位,国力弱小的国家受到的关注程度自然会相对不足。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史研究难免出现学者所说的“嫌贫爱富”现象,无论是在外交史、国际关系史还是在区域国别问题研究领域,东南亚长期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这种现象也同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有关。同中国与大国关系史研究相比,东南亚国家均属于小众研究对象,这就与目前国内学术刊物追求文章引用率和关注度的导向不相匹配,“选择周边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研究的学者,在学界往往容易被边缘化”[注] 许利平:《期待不嫌贫爱富的周边学》,搜狐网2015年1月31日, http://www.sohu.com/a/810860_114984. 。如果研究对象太过小众,受众少,缺乏引用率,成果就不好发表,项目资助相对更少,但这些边缘化的议题和对象国研究又恰恰是学术空白和知识短缺的领域,由此在相关研究领域中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和“马太效应”。
早在90年代,就有学者从共和国史、外交史、东南亚学等学科角度,不断建言加强学科建设,提高研究水平和质量。近年来,学界又兴起了建立“周边学”的讨论与努力。无论这些讨论的结果是什么,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是单一学科和视角所无法完成的。
首先,在双边关系史研究中,双边文献、双边视角的相互印证、参照、对比是基本要求,国别史研究和外交关系史研究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史研究还应超越国别个案,将其置于中国和对象国各自的整体政治、经济、外交框架之下加以考量,两种视角不可偏废。特别是对中国学者来说,重视从东南亚视角来反观对华关系,这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不对称特性、现实战略利益所需要的。同中国相比,东南亚国家都是小国、弱国。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说,小国对大国的担心和疑惧均历来如此。无论是越南人常言所说的“天堂太远,中国很近”,还是缅甸昂山素季所言“邻居是无法选择的”,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种心态。“一带一路”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前提之一,就是必须要了解对方的民心和民意。当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史时,如不能充分利用对方文献,忽视从对方角度来审视对华关系,就无法理解他们的感受和心态,很容易让研究落入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感受推己及人,错误解读资料,甚至陷入“阴谋论”的困境。例如,东南亚国家独立后,柬埔寨、缅甸、老挝与印尼都宣称奉行中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在大国之间进行平衡,谋取国家利益最大化。如不能把其对华关系放到对象国整体的外交框架中去观察和分析,就无法深入理解这些国家对华政策的逻辑,或者是让中国学者的研究陷入民族主义的窠臼中去。为避免这种误区,美国哈佛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学术取向值得借鉴,其自我定位是推动有关非洲的知识和非洲人观点的创新、传播。这显然是一种双向的努力,一方面实现对有关非洲知识的增量即增加和深化美国对非洲的认识,另一方面了解非洲人是如何认知外部世界的。换言之,这种研究取向旨在解决美国人是怎么看非洲以及非洲人是如何看美国和外界的问题,避免陷入自说自话的困境。这可谓区域国别问题研究的黄金法则或基本规律,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增进彼此的理解,实现某些议题的共识,这也非常符合毛泽东主张采用“古今中外法”来研究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的理念[注]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0页。 ,其目的与精髓都在于“知己知彼”。
这种研究情势与当前中国外交战略以及在这一区域的定位不相匹配,也偏离了时代的命题。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基本定位是:对外,“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内,“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这种新定位和新格局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是首先立足周边,“从周边起步,以发展中国家为依托”,稳步推进[注] 王毅:《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开启新航程 展现新气象》,《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1期。 。反思、重构当下的东南亚问题研究,既是时代的要求,更是国家战略需求使然。在这种时代主题的推动下,学界兴起了建立“中国周边学”的讨论和努力。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与民国时期“边政学”兴起的场景有些相似,虽然二者的内涵和外延并不完全相同。“边政学”系当时政学两界为因应空前的边疆危机、民族危亡而创设的一个交叉学科。边疆问题、边政问题固然不能等同于今日讨论的周边外交问题,但这些议题通常是周边问题向中国外溢的重要表现,因为边疆是中国与周边的连接区域。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的外患与危机基本都是首先发生在沿边地区,外患最初体现为边患,然后再向内陆扩散。反之,中国走出去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首先要通过周边,二者演进的路径和方向是一致的,这是由中国所处的地缘结构决定的。中国有14个陆上邻国和6个海上邻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在复杂、多元的周边地缘环境中,“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注] 《习近平为什么强调“底线思维”》,人民日报客户端2019年1月29日, 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3684581/3542757?from=singlemessage. ,当属中国周边外交的底线思维之一。这种现实需求决定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史研究是单一学科所无法完成的,决定了该议题属于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范畴。
北宋党争思维下的“君子”“小人”之辨,造成党同伐异,排斥异己;不是君子就是小人的线性思维模式,长期以来无法消除其不利影响。③对此,沈松勤在其《北宋文人与党争》一书中有深刻的分析,可参阅其第二章“君子小人之辨:北宋党争的理论依据与主体性格”,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72页。这种党争思维模式,一直延续到南宋。绍熙二年,朱熹两次致书当时宰相留正,指斥党论,其《四月二十四日与留丞相书》说:
目前,国内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问题的学者主要来自三个学术圈子,即中国历史研究者(含党史、共和国史、外交史等)、国际关系史或冷战国际史研究者、东南亚区域问题研究者。三个圈子的研究各有特色和侧重:中国历史研究者以政策分析和宏观叙述见长;冷战国际史全面切入东南亚较晚,但重视档案和多边视野;东南亚区域问题研究者的专题史研究成果丰富,注重对象国视角,但一手档案文献利用不足。因此,针对目前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的研究现状,当务之急是整合多个领域学科的学者,建立起相对较为完整的双边关系知识框架和理论体系。以往经验表明,既有研究多基于学者自身的学术自觉与兴趣,研究比较分散和碎片化。在这种情势下,学术界需要把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放到整个周边外交的框架下,注重统筹规划,加强顶层设计,形成系列的周边国家关系史研究,从而改变各自为战、零敲碎打式的研究格局。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和学界实际已经有过成功的经验和尝试。1982年,胡乔木提出编写《当代中国丛书》后,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由中央宣传部组织、统筹全国力量进行撰写。这套丛书历时十余年完成,分为部门卷、地方卷、专题卷和综合卷等152卷、211册,近1亿字,迄今仍是研究共和国史的重要必读参考书。近年来,华东师范大学的冷战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研究特色鲜明,由沈志华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收集及历史研究”,整合各方力量,正在朝这一方向努力。但若有更为全面的顶层设计和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的研究就会取得更大突破,毕竟当下的研究基础、研究队伍、经费支持、研究资料等已远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可比。
其次,仅从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双边互动研究视角还是不够的,冷战时期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是近现代以来双方关系承上启下的历史阶段,若不将其置入地区史、冷战国际史等更为中观和宏观的框架下,研究就不够全面和立体,无法还原复杂的历史本原。冷战伊始,东南亚特别是印支半岛就一直是大国博弈和干涉、热战和冷战集中的区域,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在这个区域原本就十分复杂、敏感、多变。例如,若欲深入讨论中国与柬埔寨的关系,不考察柬埔寨与越南、美国、前宗主国法国以及泰国的关系,就无法真正厘清中柬关系的发展脉络,更谈不上还原柬埔寨对华政策的调整过程。
“北接松径,南通峦雉,东以达虎角庵。游者之屦常满,然而素桷茅榱,了不异人意。”[3]426此亭构造简朴,一点也不吸引游者的眼球。然而登亭眺望,胜景扑面而来,使人油然而生山水鱼鸟之情。
再次,微观层面上围绕双边关系中的事件史、专题史、问题史的研究不可或缺,其既有实现知识增量的作用,更有丰富、细化和深化双边关系史的功能。这些领域的研究者来自民族学、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是国别史、外交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学术和人才支撑。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叙事不能仅仅停留在双边的“高政治”阶段,跨国史视野下双方的边民流动、非法移民、民间交往等“低政治”议题同样值得关注。这种基础、微观、小众的研究,无疑是全面、深入、精准认识研究对象的必要元素。
(本文作者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南洋研究院教授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 吴志军)
标签:东南亚国家论文; 冷战时期论文; 关系史论文; 中国论文; 现状论文; 世界历史进程论文; 20世纪论文; 亚洲冷战论文;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论文; 南洋研究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