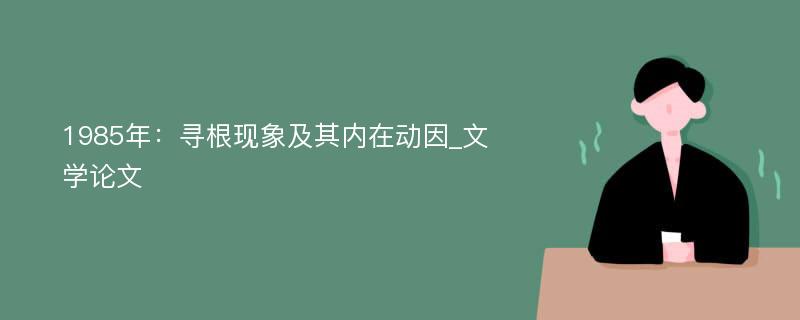
1985年:寻根现象及其内在动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5年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是“寻根文学”的突然崛起。青年作家韩少功、郑万隆、李杭育、阿城、郑义等人在这一年先后发表文章(注: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4,郑万隆:《我的根》,《上海文学》1985.5, 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 《作家》1985.6,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7.6,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文艺报》1985.7.13。), 提倡在文学中寻找民族文化之根。一时应者云集,并在批评界、理论界形成论争。
尽管在以后的讨论中,关于“寻根文学”以及关于“根”、“传统”、“文化”等前提和概念缺少必要的界说,但在这个话题之下,各种观点的纷呈及其所引起的文化界的关注,足以表明其价值;同时,由于处在不同理论维面上而使论争无法进一步展开所形成的喧杂局面,也为我们今天提供了一个进入1985年现象研究的便利的入口。
一
新时期文学的“复兴”是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背景之下展开的。面对极左思潮与文化专制主义,由于共同政治主张和文化态度,由作家、批评家所代表的人文知识分子趋同于一种整体阵容的精英意识,标举着思想上的启蒙主义和美学上的现实主义两面大旗,对传统体制及其相应的文化形态进行激烈的反抗;同时出于所面临的共同的对立面,知识分子的这种精英意识与主流意识形态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迅速结成了联盟。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无疑便是对这种联盟的充分肯定。(注:邓小平:《在第四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祝辞》。)
作为这种联盟的文学成果就是“反思文学”。那时作家纷纷开始痛定思痛,面对过去进行历史的梳理。但人们很快发现“反思”文学的路越走越窄,当有人提出从“反思文学”到“文学的反思”,力图在“反思”中把握文学的审美本性时,便意味着“反思文学”陷入了困境。这种联盟的另一文学成果是“改革文学”。如果说“反思文学”是面向过去,那么“改革文学”则是面向现在和未来。与当时的政治口号“向前看”相一致,意味着在文学上避免“反思”的进一步深入,更多的应该去讴歌我们的改革时代。但是,不断制造“乔厂长”式铁腕人物和千篇一律的改革加爱情的情节设置,也使“改革文学”日益陷入模式化的困境之中。以今天的视角来看,80年代初的这两股创作热潮很快地退去,一方面表明了当时的人们对文学和现实的关系并未认识清楚,另一方面也预示了文学本身的审美性正如地火奔突,孕育了某种艺术规范的突破和对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分离、回归自身的前景期冀。
其实,技巧上、形式上对既有文学规范的突破从新时期起步不久便开始。像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汪曾祺的《受戒》、王蒙的《春之声》等,只是他们还未构成对文学成规的冲击,并不表现为对艺术革命、文学观念突破和文学回归自身的自觉,更多的可能来源于对艺术个性、风格独特的本能追求以及外来文学的影响。而且,事实上,这种追求在当时还只是被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的范畴,成为“双百方针”的文艺繁荣成果和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宽容的显示。
大致在1984年,这种状况有了变化。这一方面与“反思”、“改革”文学日益陷入困境有关,另一方面,几年来零散的、自发的形式探索业已积累、聚集起一些新的审美规范,这些新的审美规范正在获得认可。从1983—1984年全国获奖小说中可以看出:邓刚《迷人的海》、阿城《棋王》、郑义《远村》、邓友梅《烟壶》、张承志《北方的河》、冯骥才《神鞭》、贾平凹《腊月·正月》、何立伟《白色鸟》、李杭育《沙灶遗风》等致力于小说审美本性探求的作品已在整个获奖小说中占有很大比重。批评家南帆在事后的理论概括中,曾把这种小说在技巧上、形式上的突破提升到了审美情感的变异和文学观念突破的高度上来(注:南帆:《小说艺术模式的革命》,上海三联书店1987.11.P12。)。
因此,可以说,活跃于80年代中前期的青年作家,他们以自己的审美情感与艺术观念在文坛上崛起,成为文坛主力。旺盛的创作力逼迫他们必须寻找到一个突破口。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84年12月在杭州“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的创作理论会上,如何突破既有艺术规范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而几位“寻根文学”肇始者都参与其中,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文学中的文化意蕴。紧跟着的“寻根文学”概念的提出并在很短时间内获得相当影响与拥护,热闹的背后只能表明创作界面临着停滞不前的窘况,以及对任何突破的尝试所表现出来的欣喜和渴望。
这是一次文学力图回到“自身”的努力,也是以文学之根表明与社会政治主流意识形态相裂隙分离的努力。尽管大家知道要说清文学之根是什么是异常艰难的,但“寻根”作家们还是勇敢地上路了。显然,“寻根”作家们的论述潜藏着如下逻辑判断:“大作家”或真正的文学总是“不只属于一个时代”(注: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6。),文学必须超越“住房问题”、“特权问题”、“牢骚和激动”的“现实世界”和“社会学内容”,它是“追求和把握人世的无限感和永恒感”(注: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4。);而文化则是跨越历史、跨越时代的,它“更深沉、更浑厚”,“是绝大的命题”(注: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7.6。),隐藏着“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注: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4。)。因此,追求永恒性的文学,就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高于自己的命题”。文学的“根”,在于民族文化。
对以上的理论阐述我们不应抱苛求的态度(比如当郑义宣布,“作品是否文学,主要视作品能否进入民族文化”的时候,我们可以反问:进入了民族文化,文学就成为文学了吗?它所依凭的,就是文学因素了吗?),阐述理论对于他们来说毕竟是副业,他们只是凭借艺术直觉,敏锐地发现艺术中存在的问题。因此,尽量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而不是理论学术的角度来看“寻根”,或许更贴近事物本身。
事实上,就作家来说,也许更吸引他们的并不是文化,而是民族文化中蕴藏着的审美因素。庄、禅的澹泊、宁静、直觉、顿悟本身就是超功利的美学追求;绚丽的、浪漫的楚文化带给人们更多的也是文学想象;近乎原始的莽荒、山村的粗野、强健、自由的人生状态在几十年前的沈从文那儿就得到过出色的审美表达;在现代文明的入侵下,即便是正统的、规范的儒家传统文化也具有了“挽歌”的美学效果。无疑,传统文化中有太多的东西能够激活作家的审美想像力和创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在冲破“反思”、“改革”文学的束缚时,将眼光投射到民族传统文化上,就丝毫不值得奇怪了。当然,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成功也是一个原因。因此,我们说,“寻根”文学的意义,不是在理论上,更多的是在创作实践,以及由此引起的文学观念的变革上,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想像力,展示了更大的可能性空间。
二
正如前文所述,韩少功、郑万隆等青年作家的“寻根”出发点并不在于理论的建树,而针对的更多的是创作上存在的实际问题。这还可以从“寻根”首先是由作家而非理论家发起得到说明,也可以通过考察肇始“寻根”的那几篇理论文章发现,类似随感式的文章并不具有理论上的深思熟虑。现在看来,那些文章与其说是“寻根”的纲领或宣言,不如说是一个引发论争的引子。
应该说,新时期的文艺复兴,大致是在两个相关的维度上展开,一个是强调文学的使命感,文学的战斗作用,要“干预生活”,文学不是“瞒”和“骗”,不是粉饰太平;另一个是文学回归的呼唤,文学不是政治工具,“文学是人学”,要还现实主义文学的本来面目。这两个维度在“真实性”上统一起来,也就是说文学的使命、战斗作用的强调是以文学的真实性作为前提和基础的,而“现实主义”文学最基本的特征则是真实性原则。但是,当作家们日益认识到“真实性”远不是文学的全部,当“寻根”文学更多地表现为对现实的远离时,就意味着这两个维度间的统一关系已经出现裂隙,正在不可避免地分离。而与“寻根”同年出现的马原的小说《冈底斯的诱惑》,似乎可以作为这种分裂的一个明确的表征。正是这种裂隙的出现,使人们获得一种新的眼光,可以拉开些距离,来审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进程和文艺界的论争。所以,也正是在这一年,当刘索拉的标新立异的《你别无选择》发表时,它的命运已经和前几年同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意识流”小说以及“朦胧诗”不同,它甚至入选为当年度的全国优秀小说(虽然王蒙的小说如《春之声》、《蝴蝶》亦是获奖之作,但它们仍然是被作为“现实主义”小说来接受的,现代主义色彩被淡化为仅仅是技巧、手法,而不被认为是方法,因而可以被融进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它被许多评论家认为是“真正”的现代派小说。倘若按照黄子平的观点,并不存在“真”、“假”的现代派,在“真”、“假”背后,所潜藏着的是价值的判断(注:参见黄子平《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北京文学》,1988年2期。),那么,促使人们做出“真的”判断的缘由,并不全来自于作品的内蕴,更多的是来源于这种“裂隙”的出现,在于文学观念的变化之后,所做出判断的变化。曾镇南坦言他在1984年下半年到1985年上半年“态度和观念的变化”(注:曾镇南:《缤纷的文学世界》P61-P74,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8.1。),正是这种变化, 使他在这篇小说中读出“近年来文艺界思想论争史”,“在艺术思想上具有某种解放作用”,他将它视为“一篇有力的艺术宣言”,“冲破陈旧的观念直截了当地向艺术法则中常规和正统发起挑战”,“处处闪露着对我们文学艺术教育和文学评论中的陈规旧范的批判锋芒”(注:曾镇南:《缤纷的文学世界》P61-P74,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1。)。
当曾镇南在为文学突破“现实主义”而兴奋的时候,一些批评家看到了突破将造成两个维度的分离。刘纳将“寻根”分为两种倾向,“以现代‘社会’意识观照,便要求文学担负起民族‘防癌’的责任。……以现代‘审美’意识观照,使呼唤‘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这二者之间,有相通之处,又显示着不同的归趋”(注:刘纳:《在逆现象中引进的新时期文学》,《文学评论》1986.5。);李书磊则将“寻根”分为“原始寻根”和“文化寻根”(注:参见李书磊《从“寻梦”到“寻根”》,《当代文艺思潮》1986.3。), 不管“寻根”是否可以这么划分,但分类背后的标准则表明了批评家的“裂隙”意识。所以,一些批评家开始担忧文学的战斗作用的丧失,而这正是以作家、批评家角色出现的知识分子从“五四”以来所秉持的传统。他们据此对“寻根”文学不无担忧,“一些作家便跑到深山野林中,荒凉大沙漠中去歌颂那拙扑、原始、纯净、严峻神秘的生命力量,去探寻那似乎是超时代、超现实的永恒的人生之谜……就我个人来说,却总感到不满足”,“我希望能够看到反映时代主流或关系到亿万普通人(中国有十亿人,不是小国)的生活、命运的东西”,“我仍然认为,只有战斗,才有人生(注:李泽厚:《两点祝愿》,《文艺报》1985.7.27。); 希望文学“找到审美价值与功利价值合成的黄金配方”(注:张韧:《超越前的裂变与调整》,《文艺报》1985.11.19。)。正如这种“黄金配方”可能只存在于理想之中,而分裂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一样,作家、批评家内部的分化也将不可避免地存在。尽管在1985年,缝隙还只是隐秘地存在,并未公开化、全面化,而大致在1987上半年,一批更年轻的作家以“实验小说”崛起于文坛时,人们就已经很清晰地看到这种分化了。
“寻根”在学界引发更大论争的时候已越出文学范畴,进入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讨论。“寻根”文学在1986年大致上已走向式微,但由它所引发的这场论争在1986年却成为热门话题,“文化热”由此而起。现在看来,这场对传统文化的讨论并不是心平气和的学术探讨。讨论过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体认并没有深入多少。人们更少对传统进行学理的剖析,更多的是从各自立场出发。根据对传统的态度,划分为阵线分明的两大阵营,肯定或否定,当然也有既肯定又否定的结果等于什么也没说的“辩证”态度,然后就匆匆地开战了。这表明,传统文化对于他们,是一个招牌和武器,更重要和根本的是他们所持的态度和立场,以及对拥有传统文化阐释权的争夺,传统文化成为他们获得合法性的资源。
刘再复在论及新时期文学主潮时言及“反思”的三个递进的层次,即由政治性的反思到文化性的反思到自审性的反思。这表明:一方面,从政治到文化,从对现实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这是一个深化的过程,但我们也可以将它理解为是一种策略,即从现实、政治到文化的撤退;另一方面,文化性的批判接通了新时期和“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联系,正是在“五四”那儿,新时期的知识分子才找到自己的“根”。
理解了这点,就不难理解反“寻根”论者为什么会对阿城、郑义的传统文化在“五四”“断裂”的观点(注: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7.6 ; 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 《文艺报》1985.7.13。)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因为否定了“五四”, 就等于否定了知识分子据以安身立命的东西,就是否定了他们的传统和存在的价值。
批评“寻根”是复古主义显然有失公允,但毋宁说这表明了一种态度的策略。就像批评“五四”造成文化虚无主义将导致“五四”的合法性危机,戴上复古主义的帽子,“寻根”的合法性亦将丧失。所以,秉承“五四”传统的知识分子总是极力为“五四”的“反传统”辩护。陈思和承认这种“断裂”的存在,但他从历史演变的角度论述,对“五四”的反传统予以“合理性”的解释,并把文化断裂所造成的后果归咎于抗战开始后,由于民族战争的爆发而导致的对民族文化的片面肯定,因此认为“‘五四’造成的文化断裂,不仅无过,而且有功,我们应正确认识它的价值”(注: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对文化传统的认识及其演变》,《复旦大学学报》1986.3。);汪晖、王友琴则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立论,不承认“五四”造成文化断裂,认为它是中国文化的新发展,“鲁迅等人在反封建大旗下,主要以否定和批判的方式对传统文化,其角度或着眼点并不在于否定中国文化的特点,而在于这种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社会进程的影响。正是在这种否定和批判之中,诞生了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鲁迅小说——这是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而不是断裂”(注:汪辉:《要作具体分析》,《文艺报》1985.8.31。); “五四”一代作为对中西文化碰撞、民族在现代世界中面临危机的积极应战者,他们在这种过程中建设了新的民族文化。随着岁月的推移,形成了一种不能不承认其为文化的东西,我们今日正生活其中。文化本身需要更新,并无一千年或五百年前的民族文化才算民族文化之理。(注:王友琴:《我只赞成阿城的半个观点》,《文艺报》1985.8.31。)
其实,无论是复古主义还是虚无主义的批评,尽管二者似水火不相融,但双方的目的却是一致的,就是都要证明自己是传统的合法继承者。无论承认“断裂”与否,一个共同的策略是,通过对传统的阐述使自己获得正统的地位。“断裂”是为了建立新的传统,“反传统”是为了光大传统,在传统获得新生的同时,自身亦即成为传统的一分子。这样,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其对现实的战斗、批判精神,在文化上就获得了合法的存在。这也表明,围绕着“寻根”而展开的各种论争背后,一方面意味着知识分子对自身合法性的寻求;另一方面更意味着知识分子从正面的、直接的现实批判(这种批判受到众多的限制)向稍微缓和的、远离的文化批判的撤退和妥协,力求保持着这种平衡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