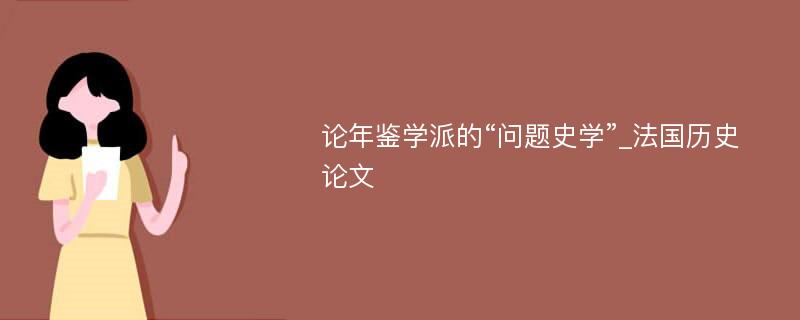
试论年鉴派的“问题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年鉴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时看到有人提及“问题史学”,史学工作者聊天时也经常会讲到这个概念或类似的提法。一般都把它归之于西方20世纪新史学的主要追求,特别是把它看成年鉴派的重要主张,但对什么是“问题史学”我们似乎还缺乏深入的思考。一些史学工作者或历史专业的研究生认为,所谓“问题史学”就是从现实需要出发来研究历史。一般说来,这样理解无可厚非,却似乎过分简单。因为“现实需要”是一个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当年“四人帮”就是打着使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幌子搞“影射史学”的;所以有必要深入理解年鉴派的“问题史学”的实质,以便从思想上和实践上把它与“影射史学”区别开来。
一、年鉴派的“问题史学”是一种科学性与有用性相结合的历史学
探讨年鉴派的“问题史学”时,马上会碰到两个互相联系的让人困惑的问题:
1.年鉴派所讲的“问题”到底具体指的是什么,或者说他们提出的是些什么问题?从字面上看,“问题史学”这个概念并未给历史学带来太多的新东西。可以说它是各民族古代史学的基本形态,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的古代史学都是“问题史学”。人类远古时代的英雄史诗既不是为了考证史实,也不是为了娱乐本部落的居民,而是企图通过歌颂本部落或本民族的光荣经历来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以便追求部落或民族的共同目标。古代史学总是承担着教育功能,既教化自己的居民,又为统治者提供统治经验。要达到这些目的,古代史家一般只关心与此相关的问题。我国二十四史中社会史的内容偏少,这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或史学家认为这些东西用处不是很大;西方的教会保留了大量教区居民生老病死的材料,因为这些材料对当时的教会很有用,是教会控制居民思想意识的重要辅助手段。前工业社会一般都不关心人们认为没有用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史学”实际上是古代史学的一般形态,我国曾有学者指出过传统史学其实也是“问题史学”。① 既然如此,为什么在20世纪里,“问题史学”得到了各国史学家的高度关注?
2.年鉴派的代表作似乎都远离现代生活,或者说似乎都与现实经济政治问题无关,为什么却能得到现代人如此厚爱?这个学派的代表作(有的已有中译本)主要有:布洛赫的《封建社会》、《法国农村史》,费弗尔的《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拉伯雷的宗教》,布罗代尔的《地中海》、《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法兰西的特性》,及其与拉布鲁斯共同主编的《法国经济社会史》。这些书名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至于该学派其他第二和第三代学者的代表作,有肖努的《塞维尔和大西洋(1504—1650)》、《16到18世纪巴黎的死亡》,迪比的《法国史》、《法国乡村史》、《中世纪西方的农业经济和乡村生活》,勒高夫的《中世纪的商人和银行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炼狱”观念的产生》、《中世纪的想像》、《圣路易》,勒鲁瓦·拉迪里的《朗格多克的农民》、《蒙塔尤》、《罗曼人的狂欢节(1579—1580)》,芒德鲁的《18世纪法国的法官和巫师》,菲雷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和社会》、《思考法国大革命》,伏维尔的《18世纪普罗旺斯的巴罗克虔诚和非基督教化》、《昔日的死亡》,《大革命心态》,阿里埃斯的《18世纪以来的法国人口史及法国人对生活的态度》、《旧制度时期的儿童及人们的家庭生活》等等。还有许多重要著作未提到,比如古贝尔的《博韦和1600—1730年的博韦人》,这是上世纪50年代的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②
从这些书名来看,年鉴派的著作内容上以经济社会史、社会生活史和历史群体的思想状态(心态)为主,时间上则集中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正如伊格尔斯说的,“年鉴派史学的焦点始终都集中在中世纪和旧制度之上③。在当代中国人看来,史学要干预现实,就该研究近现代史,或研究现代化,或研究美国史及中美关系史等,但年鉴派最有名的著作都是研究中世纪史或早期现代(近代)史的,中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著作“引起了战后一代人的共鸣”。④ 20多年来我们在介绍、研究年鉴派的工作中尚未认真涉及这个问题,而实际上,如果我们不能说明这一点,就不能说我们已经读懂了年鉴派的著作。
这两个问题与年鉴派的两点基本主张相联系:第一,历史研究的问题是无限的,历史家必须自己提出问题来研究;研究历史主要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碰到的问题或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借鉴,一定要联系现实来提出问题、进行研究,绝不是为了恢复过去而研究过去。该学派创始人费弗尔宣称:他们“‘所提出的不是一种让史料自己说话,而是由史学家提出问题的史学。’它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从现时出发来探讨历史问题,以便能在一个‘动荡不宁的世界中’生活和理解”。⑤ 第二, 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传统史学是叙述史学,是一种不科学的史学,只有向史料提出问题、形成假设才是科学的史学研究方法,所以必须从“叙述史学”向“问题史学”转变。
为什么说叙述史学是不科学的呢?因为特定历史时期内发生的事件或人物活动极其众多,但所有的叙述史学都只能通过叙述其中某些事件或某些人物活动的过程,来说明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史学家选择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的行动系列进行叙述,也就是他对这一特定时期内什么是重要的而什么是不重要的做出判断。可想而知,这种判断有很大随意性,往往取决于史家对这一特定时期历史的看法。所以这实际上是一种目的论的史学,是在“历史的终点处”先做出判断和选择,然后再来叙述事件的过程,因而缺乏科学性。比如,一个贵族或一个市民可以写出十分不同的法国革命史,即使他们所用的史料都是可靠的,但因为他们对大革命的看法从准备材料时就已不同了,所以所采用的材料和叙述系列也是不同的。姚蒙先生就此说道:“很明显,在这种史学模式中很难找寻到严格的科学解释。年鉴派明确宣布史学研究应当对历史做出分析和解释,而这两个步骤本身是建立在研究问题的提出这一基础上的。费弗尔指出:‘确切地说,提出问题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在科学指导下的研究这个程式涉及到两个程序,这两个程序构成了所有现代科学工作的基础:这就是提出问题和形成假设。’正是在这一方法论基础上,史学与其他一切科学在本质上相同了;也正是围绕所提出的问题,史学家才决定运用哪些具体方法去解答问题。”⑥
当然,仅仅从叙述史学转向问题史学并不意味着史学就有了科学性。菲雷也承认:“首先,因为有些问题和概念并不具有明确的回答;其次,因为有的问题在原则上能够具有明确的答案,但由于材料的缺乏或由于这些问题本身的性质而无法获得解决。”⑦ 实际上,阶级或政治立场的区别仍然会在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生作用。但在力求客观地说明历史,在更大限度内取得概念的明确性和占有尽可能详尽的资料等方面,年鉴派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正如于沛先生曾指出过的,年鉴派“明确提出了‘问题史学’的原则,要求在研究过程中建立问题、假设、解释等程序,从而为引入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基础,极大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⑧
年鉴派是怎样把“问题史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来使用的呢?勒高夫在回答他如何撰写《圣路易》(商务印书馆已出版了中文本)时,曾涉及过这个问题。他说道:“为了忠实于年鉴派‘问题史学’的思想,我首先碰到的困难是确定一个参照系,在这个参照系中,我可以使圣路易置于13世纪的社会环境中,成为一个与该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个体。要这样做,我得避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所称的‘传记的幻觉’,在这种幻觉支配下,任何大人物的生平都被看成是某种预先确定的命运,排除了生活中的各种偶然性。相反,我集中表现了圣路易从王室儿童以来的生涯中有过的种种犹豫、种种决定和那些关键的时刻,因为在一个人可能塑造他的生活时,他也被生活塑造着。”⑨
把年鉴派的这两点主张结合起来理解,可以看出它力图实现的是一种“科学性”与“有用性”相结合的史学。它强调历史的效用,但这种效用建立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正是在这一点上,通过进一步分析“科学性”和“有用性”的内涵,我们能比较全面地理解他们提出的“问题史学”的内涵,同时也能说明为什么他们研究的那些远离现代生活的历史题材会得到现代人的普遍欢迎。
二、年鉴派“问题史学”的科学性与有用性的具体内涵
年鉴派所主张的“科学性”至少还包含有以下几种意思:
首先,指他们的著作完全基于历史事实而写成。史学家的写作以历史事实为准绳,这是古今史家所称颂的基本史德,但实际上这不容易做到。它不仅要求排除政治偏见,还要求排除民族偏见(这是全球化时代对史学家提出的新要求)和主观认识的干扰。虽然从哲学的角度看,要完全排除主观认识的干扰是不可能的,但史学家心中有杆秤,知道什么干扰是应该避免的,什么是难以避免的。年鉴派是否完全做到了这一点,仍值得商榷,但无疑他们是努力这样做的。
在对待史料上,他们是实证史学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用了整整一章(第三章)来讨论考证和史料辩伪问题,并用不少篇幅嘲笑了那种固执于传统实证研究方法的机械和荒唐。他指出:“研究要取得成效,就必须遵循考证的法则。”⑩ 总的说来,年鉴派在批判兰克学派的“科学史学”时,扬弃了兰克学派中非“科学”因素,但坚持了其中的科学的因素。他们不仅继承了实证史学处理史料的方法,而且为了更客观地认识真实的历史,极大地扩大了史料的范围。
其次,是其历史观的科学性,即他们的历史观超越了古代和近代的爱国主义,既强调热爱祖国又强调热爱欧洲和世界。年鉴派具有开放的心态,特别谋求把法国的命运与欧洲各国的命运联系起来。布罗代尔深情地说过:“我怀着与儒尔·米希莱同样苛刻、同样复杂的一片真情热爱着法兰西,不论是它的美德还是缺陷,也不论是我乐于接受的还是不易接受的东西。”(11) 但布罗代尔绝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的代表作就是研究整个地中海的,在这部名著中,他倾注了对欧洲的爱和希望。穆罗尼指出,“在长时段文明框架内,布罗代尔保证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法国文化的地位。此外,大体说来,布罗代尔的法国仍然是使欧洲普遍化的一个希望,欧洲和法国的命运由此密切联系起来了。”杰迈利(Gemelli)则认为可以把布罗尔的《地中海》看成“对欧洲的中心地位和重要性的一种保护……布罗代尔把他的长时段的想像看成是一种注意、理解及缓和当前事件影响的一种工具。”(12)
第三,年鉴派以20世纪影响极大的非理性主义为基础,研究历史上社会的潜意识(日常社会生活)和各阶层头脑中的潜意识(心态)。伊格尔斯说道:“年鉴派历史学家与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密切关系并不令人惊奇”,布罗代尔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私人关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结构主义把动态的社会发展转移到静态的持久制度,在这些制度中,表现出持久不变的人性”,这与年鉴派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13) 当然, 年鉴派历史家也可能通过其他相关学科来接受非理性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巴勒克拉夫指出:布洛赫的《魔术师国王》、费弗尔的《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拉伯雷的宗教》等,“这些研究的原动力,无疑产生于19、20世纪之交的居斯达夫、勒邦、格雷厄姆·沃勒斯和威廉·麦克杜格尔发表的著作对社会集团行为、群众狂热、集体意识和历史上非理性力量所进行的研究。”(14) 必须说明的是,20世纪西方流行的非理性主义并非都是“科学的”,但它包括着科学认识的成分,对各人文学科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关于无意识和群体心理现象的理论特别有助于历史学把眼光从精英转向广大平民。
以上讲的是年鉴派所主张的“科学性”,与之相结合的是它所主张的“有用性”。这就是强调从现实问题出发研究历史,通过历史研究解答各种现实问题、满足现代人多方面的需要。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着重研究的历史上的“集体英雄”及历史上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和观念(心态)。这些研究成果说明了人民群众及其活动在历史上所起过的作用,指出这是决定历史变化的“社会无意识”的力量。这种平民史观既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又十分符合福利国家建立后人民群众主体意识提高时的心理需要。布罗代尔指出,“农民和庄稼……悄悄决定着时代的命运”(15)。他还说,在当代,许多人以为一切都由雅尔塔协定或波茨坦协定或人造卫星的发射等等事件所决定,这当然是不对的,因为还存在“无意识”的历史,即决定这些事件发生的基本力量。他强调说,认识这种无意识的历史并不容易,但说明它非常有价值:“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之外还有群众的历史,并且容易承认群众对历史具有强大的推动力,但不容易看到这股力量的方向和规律。这种意识今天正变得日益强烈,虽然它的存在历时已久(例如在经济史方面)。这是思想中的一场革命,人们开始正视事件的模糊部分,赋予它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甚至损害其他部分也在所不惜。”(16) 这种观念与这时普遍增长的普通群众自我肯定、自我欣赏的主人翁意识息息相通,同时这方面的内容又属于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范围,易于为他们所接受。所以保罗·利科说道:“法国历史学派之所以值得注意,也许是因为绝大多数著作都同社会史有关。群体、范畴、阶级、城乡、资产阶级、艺人乃至农民和工人,都成了历史舞台上的‘集体’英雄。”(17)
社会的无意识力量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心态,心态属无意识领域,从认识论上看,年鉴派的心态史研究与非理性主义向历史学的渗透分不开。心态史的话语本身就是当时历史学理论前沿的体现,年鉴派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别为世人所注目。
第二,在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中向人们讲述那些在历史上起稳定作用的、变化缓慢的方面,促使人们注意这些比较稳定的因素,注意到过去的生活、心态和追求与现代社会的联系,这不仅满足了现代人寻找“根”或归属感和祈求稳定的愿望(这在二次大战后特别强烈),而且提出了一些值得理论界思考的问题。比如,关于思想观念在不同的时代起的作用是否一样的问题,就富有启发性。
年鉴派以研究历史发展中的稳定因素著称。早在1946年,费弗尔就指出:“在这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中,唯有历史才能使我们带着思考而不是带着恐惧而活着”。(18) 后来勒高夫干脆说:新史学是一种使人摆脱恐惧的史学。年鉴派强调那些在貌似剧烈变化的现实世界中很少变化或缓慢变化的因素,目的是为了使人们从历史中获得现代与过去的联系感和安定感。布罗代尔有一段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吕西安·费弗尔在其生活的最后十年中反复说过:‘历史既是过去的科学,又是现时的科学。’这也是我的结论。作为时段的辩证法,历史不正是对整个社会现实的解释吗?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的教训提醒我们要防止单纯重视事件的偏向。我们不能只思考短时间,不能以为会吵会嚷的演员才是真正的演员,除他们以外,还有其他的演员,只是保持沉默而已。难道有谁还不明白这个道理?”(19)
以上是年鉴派所主张的史学的“科学性”与“有用性”的大体内容。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必须把年鉴派放在20世纪世界学术潮流、经济政治变化与法国的特定经历的大背景下来理解。他们的“问题史学”适应了现代社会群众性的需要。这些需要包括:了解自己如何在历史发展中发生作用;寻根,了解自己与过去的联系;好奇,希望了解过去人们的生活和观念;理解自己周围的人们与理解世界各地的人们;看到在变动不居的现实生活中那些稳定的力量,由此获得某种安定感。同时年鉴派也具有传统历史学的功能,它使人们具有开放的眼光,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热爱世界和平,反对战争与暴力等。
从以上讨论中我们还可以得出另一条重要结论:历史学得到社会承认,主要不在于它是否研究现实题材(搞现实题材,它肯定不如那些应用性的学科),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启发和使人反省,为人们提供各种各样的人生经验,使人们相互认识和相互理解,同时满足人们的求知欲、好奇心和现代人寻根和认祖归宗的潜意识。
三、年鉴派的不足之处
但当我们这样比较详细地讨论年鉴派“问题史学”的优点时,不要忘记年鉴派的学说也有自己的缺陷。不了解这些缺陷,我们对它的“问题史学”的认识就会显得不全面。
有一种缺陷我们已经比较熟悉,即它过分强调历史中的“稳定”因素而贬低事件史或政治史的意义。离开了短时段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是不完整的。你可以把这看成是年鉴派的矫枉过正,也可把这看成是它的偏颇,也许后一种看法更为合理。因为有的学者已指出,年鉴派强调历史上的稳定因素,非常符合法国人的心理:法国人希望忘记二战中的耻辱,希望在“长时段”中淡化对那段不光彩的历史的记忆(与长时段相比,这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温德舒特尔指出:长时段的概念“与其说源于一种历史理论,不如说源于民族主义的傲慢和怀旧的一种特殊的法国式的结合,并与他们对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所作为的羞愧感相联系”。但由此造成的后果值得我们注意:在忽视政治史的同时,历史教育受到了很大削弱。1983年的一个调查发现,只有1/3的中学生能说出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日期。过分轻视政治史造成的这种后果引起了政治家的关注,密特朗总统宣称,“‘历史教学的缺乏’是对‘民族的一种威胁’”。(20)
年鉴派的局限还有多种表现。他们“经常”在历史分析中排除政治因素,“这使他们对政治和思想文化史的探讨采用了一种非理性主义的方法”。他们无法说明个人或“事件”对历史的意义:“就运用更为严谨的概念分析那些参与了特殊历史变革的有目的的人类行动而言,年鉴派几乎无所作为。”特别是,年鉴派在研究早期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不能对从旧制度到近现代的变化做出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缺乏一种有关社会变化的综合性理论”。(21)
明确了年鉴派“问题史学”的优缺点,我们就可权衡什么是我们可以借鉴的,什么是我们不需要的或不可能借鉴的。当然,这首先需要对当前中国历史学面临的具体问题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注释:
①⑥⑦ 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的内涵与变迁(代序)”,载勒戈(高)夫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7~28、28页。
②⑤(18) 勒高夫等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13、34页。
③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
④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⑧ 于沛:《二十世纪西方史学及史学名著》,《光明日报》2000年12月22日。
⑨ Hugues Salord and Anne Rapin,“Did St Louis really exist? An interview with Jacques Le Goff”,1996,http://www.france.diplomatie.fr/label_france/ENGLISH/IDEES/LE_GOFF/le_goff.html.
⑩ 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11) 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第1册,商务1994年版,第1页。
(12) Kelly A.Mulroney,Discovering Fernand Braudel's Historical Context,History & Theory,1998,Vol.37 Issue 2,pp.268~269,267~268.
(13) 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
(14)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
(15)(20) Keith Windschuttle,“The Real Stuff of History”,The New Criterion,March 1997,http://www.sydneyline.com/Real% 20Stuff% 20of% 20History.htm.
(16) 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
(17) 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
(19) 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寻找出比较稳定及变化缓慢的力量,看起来似乎与我们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学说颇为相似,实际上两者的着重点不一样。长期来,我们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强调的是造成社会剧烈变革的条件正在成熟,及我们如何通过变革来促进这种变化,目的是动员人们投身到革命中来。
(21) 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4~85、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