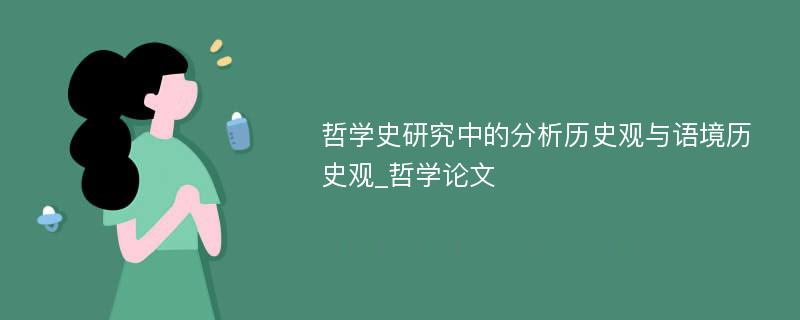
哲学史研究中的分析史观与语境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史研究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哲学”的历史,还是哲学的“历史”
我们可以把“哲学”视为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因对相似性的理解不同、偏好不一,使哲学的本性众说纷纭,哲学的理论多姿多彩;也可以把“哲学”视为在各种文化背景下和历史长河中延续、转型和交融的思想活动,从而凸显出各种哲学形态的历史性和语境化特征。正是这种多样化理解,丰富并拓展了哲学的领域和哲学史的内容,也使哲学史编纂和研究在原则、取向和方法上莫衷一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英美学界围绕哲学史编纂和研究的范式取向争论激烈,不仅深化了人们对哲学和哲学史关系的理解,而且促进了哲学史研究在方法上的自觉。若一言以蔽之,这场争论的核心即哲学史研究的进路究竟偏重于“哲学”的历史,还是哲学的“历史”。用理查德·罗蒂颇有影响的概括就是:理性重构抑或历史重构。
在《哲学的历史编纂学》一文中,罗蒂指出:分析哲学家试图对已故伟大哲学家的论证进行“理性重构”,因为他们希望将这些哲学家视为同时代人,或者能够交流观点的同事;否则还不如把哲学史移交历史学家处理。分析哲学家把历史学家视为单纯的学说汇编者,而不是哲学真理的探寻者。但这种理性重构,又遭到指控,罪名是时代误置:把历史文本打造为目前哲学期刊正在争论的命题形态。……这似乎是个两难困境:要么我们以时代误置的方式,把我们的问题和语汇充分强加于已故哲学家,使他们成为对话伙伴;要么我们限制我们的诠释活动,把已故哲学家放到他们写作时所处的落后时代的语境中,从而使他们的错误不再显得那么愚蠢。①
在笔者看来,罗蒂对理性重构和历史重构的区分凸显了对待哲学的历史的两种态度和编纂哲学史的两种范式:一种可称为“哲学家的哲学史”,即把哲学史作为哲学研究本身的素材和对象,视之为见证哲学问题和哲学论证之进步的历史;另一种可称为“历史学家的哲学史”,即把哲学本身视为历史性的学问,唯有在其特定的时代、地点和背景中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因此哲学史的研究必须将哲学文本还原到历史语境当中。尤其重要的是,这两种态度背后隐含着理解哲学的理性主义原则和历史主义原则。
历史上原创性的哲学体系往往从否定或撇清传统套路开始,以为自己诞生于革命性的自由行为,凭借理性自身就能建构崭新的哲学体系,企图将哲学思想从头来过。被誉为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就认为,要认真进行哲学思考,首先就要撇开偏见,细心怀疑我们以前所承认的意见,直到重新考察之后,发现它们是真的,才能同意它们。② 以哲学的名义驱逐传统,要么是哲学、要么是传统——这种笛卡尔式进路,在哲学与哲学史之间制造了激烈的冲突,将哲学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永恒性与时间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理性自主与外部权威明确对立起来。③ 这些冲突和对立在康德那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开篇,康德就表明了自己的基本态度:“有一些学者,对于他们来说,哲学(无论是古代哲学还是近代哲学)的历史本身就是他们的哲学;目前的《导论》不是为这些人写的。他们必须等待,直到那些致力于从理性本身的源泉汲水的人澄清了自己的工作,然后才轮到他们向世界宣告发生什么事情。”④
哲学史被康德置于理性的纯粹逻辑体系形式之下,时间性和历史要素被驱逐出去,例如把“纯粹理性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哲学史归结为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黑格尔体系虽然强调哲学史,关注历史性,澄清了许多关于哲学史的偏见,提供了思辨的和历史的两种建立精神科学的方式,但他的哲学史却被哲学吞噬,历史屈从于真理的获得过程,“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只有能够掌握理念系统发展的那一种哲学史,才够得上科学的名称”。⑤ 于是,“哲学的历史是发现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历史,而绝对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⑥ 哲学史的研究就是哲学本身的研究,这种观点容易把体系化的先天范畴强加于历史,导致结构性错误,从而经常违背历史事实,⑦ 而且也因为声称解释了最终真理而终结了历史。因此,被黑格尔主义交给哲学的哲学史,在黑格尔体系崩溃之后重新赢得了自主性。在欧陆哲学特别是德法哲学中,哲学史一直是哲学研究的主干。
然而,在英语学界,这种重新赢得的哲学史的自主性,在分析哲学取得主导地位之后,又受到不少哲学家的排斥。美国哲学家哈曼(Gilbert Harman)办公室门上贴的“对哲学史说不!”一度成为标志性口号和众矢之的。⑧ 许多偏重历史主义的哲学史家认为,其一,分析哲学家中的某些代表人物既否认哲学史与哲学相关,也否认自身的历史性;其二,分析哲学既滥觞于一种非历史性的企图,打算将哲学史扔到装满胡说的垃圾箱里,又将自己的先入之见强加到历史文本上,并忽略了那些与当代问题的当代观点不一致的古老思想。⑨ 分析哲学隐含的理性主义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康德哲学的遗产和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解读。历史主义原则则主张,哲学中没有永恒的问题,只有对个别问题的个别回答,有多少提问者就有多少不同的问题;⑩ 而要理解提问者和解答者“意指什么或做了什么,只有我们的描述能够被他接受为正确的描述,我们才能最终说他意指什么或做了什么”。(11) 当代哲学的假设、问题和区分应当而且能够被抛弃,因为它不过是偶然的历史因素的产物,只是用准确思考的深层特征伪装起来而已。(12)
面对历史主义者的诘难,葛洛克极力为分析哲学对待哲学史的实用态度辩护,认为分析哲学拒斥的其实是极端历史主义原则(主张哲学就等同于哲学史研究)和主流历史主义态度(主张哲学研究必不可缺少哲学史),二者的结果就像一句夸张的警句所说:“哲学是胡说,但胡说的历史却是学问”。(13) 在他看来,分析的哲学史家主张以问题为取向的批判性的哲学史编纂,这种实用的历史态度既优于极端历史主义者的历史相对主义,也优于某些诠释学原则对哲学史过度虔敬的态度,对哲学和哲学史都是好事。
二、分析史观与语境史观的分野
虽然在哲学史研究中,理性重构和历史重构两种思路一直相执不下,但从实际情况看,在20世纪下半叶,分析哲学的非历史性态度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六七十年代,分析哲学的语言—逻辑分析特征开始弱化,形而上学重新赢得了合法地位。七八十年代,分析哲学的非历史态度开始松动,为纯粹的历史研究敞开了一片广阔天地。到了90年代,甚至分析哲学运动本身也成为哲学史研究的对象。高质量的哲学史研究著作大量涌现,哲学史家们大多受过良好的分析哲学训练,分析技巧娴熟,虽然他们未必都认同某些意识形态化的分析哲学教条。
与此同时,不同的哲学史观之间也相互竞争,争论激烈。一系列学术会议和文集都围绕哲学史研究方法展开,(14) 学者们针对研究方法提出了多种划分方式,兹择要列举五种。斯雷对照了注解式与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法,认为前者重在尽可能完整充分地描述各个人物的观点,重构哲学家最基本假定的理性基础,后者则重在解决哲学问题,是与历史人物一起晤谈。(15) 科恩区分了“复原法”(method of recovery)和“重构法”,复原法是根据历史批判方法来理解哲学家意谓的究竟是什么,重构法则要通过当下的概念工具,使研究者有能力将自身的论证模式完整而融贯地映射到文本中。(16) 希腊哲学研究专家弗雷德主张。考察历史人物的哲学观点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哲学的方式判断该哲学观点是否为真,原因何在;另一种是以揭示历史事实的方式,强调哲学观点是特定的人在特定背景下所持有的。(17) 奥尔斯勒指出哲学史有三种写法:其一强调思想的语境,聚焦于理智的、社会的和个人的三种影响因素;其二是批判性态度,关注哲学家论证的逻辑和价值;其三则是利用历史人物来支撑自己的哲学观点。(18) 西巴区分了义理分析(doctrinal analysis)和历史分析,前者将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运用到历史材料上去,因此位于哲学创造与哲学史书写之间,后者则将材料视为历史事实和时间中的对象。(19)
上述五种划分方式各具特色,都在一定程度上与理性重构和历史重构的区分相呼应,体现出对哲学史编纂和研究方法的关注和自觉。笔者在此提出一种新的划分方式,即在方法论意义上将理性重构和历史重构转换为分析史观和语境史观这两种理想形态。理由有三:其一,对历史文本的问题分析和论证重建是理性重构的核心,而对历史文本的语境还原是历史重构的旨归。因此,分析史观与语境史观可以成为两种典型的哲学史研究思路和方法,且更清晰明确。其二,分析史观和语境史观重在方法论的运用,可以避免理性重构和历史重构所隐含的理性主义原则和历史主义原则。其三,这种转换更适于刻画英美学界哲学史编纂的实际状况,即分析史观和语境史观作为两种理想形态,虽有冲突,但展现方式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在不同的哲学史家那里各有侧重,实质上可以在不同层次上互补运用。例如在分析哲学史的研究中,罗素研究以塞恩斯伯里的《罗素》和希尔顿的《罗素、唯心论与分析哲学的兴起》影响较大,(20) 前者是典型的分析进路,而后者则具有显著的语境还原的特征,希尔顿也因此与另外一些学者一起被称为分析哲学史研究中“新潮流”的代表;所谓“新潮流”不仅采取了一定程度的语境史观,还频繁质疑早期分析哲学的流行观点。(21)
作为哲学史编纂和研究方法的理想形态,分析史观和语境史观各有其纯正派或曰极端形态。分析史观的纯正派认为,哲学史作为文化史的一部分,具有历史价值,作为教学手段,可以让学生通过解剖尸体提高哲学分析能力,但要想解决哲学问题,从而获得哲学知识,就必须独立于哲学史来进行哲学研究。所以,哲学和哲学史必须分开做。退一步说,即便我们承认哲学史的哲学价值,也必须承认哲学和哲学史皆以哲学问题和哲学论证为核心,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由于历史文本和思想的哲学性质,对哲学史的研究旨在为哲学研究提供一定意义上的背景、案例和训练,因此,即便笛卡尔本人其实也并不支持大多数分析哲学家所称的“笛卡尔式二元论”,但我们仍然可以名正言顺地讨论这种以笛卡尔命名的二元论。
抛开纯正派立场不论,分析史观大致可分为两类方法论取向。侧重哲学分析的哲学史家认为自己关于哲学史的著作与关于当代哲学问题的著作是连续且衔接的,回答的问题是:倘若我对某个哲学主题感兴趣,并且历史上某位哲学家对其有所论述,那么其论述能够给我和我的同时代人何种教益。侧重哲学史文本的哲学史家则针对历史文本,全力重构和分析以往哲学家的论证,使哲学史成为分析传统中独立的研究领域,其中近代早期哲学史研究堪称代表。
乔纳森·贝内特是分析史观的典型代表,也是语境史观倡导者的批判对象——因为他以“分析哲学的透镜扭曲哲学史”,(22) 对哲学史中的人物缺乏恭敬之心和深挚的同情。(23) 贝内特《康德的先验分析论》一书封底上的一段话被引为其方法的典型表述:“我们唯有能够以当代的术语清晰地说出康德的问题是什么,哪些问题至今仍是问题,康德对它们的解决做出了哪些贡献,我们才算理解了康德”。(24)在《学习六位哲学家心得》一书中,贝内特则倡导与哲学史人物对话的“学院派方式”:在研究文本时,我们仿佛就是作者的同事、对手,或是学生、老师,学习这些文本的收获就是我们学习哲学的收获;就像格赖斯说的,那些伟大的逝者,仿佛是伟大的活人,现在就要对我们说些什么。贝内特认为,关于近代早期哲学,好的学院式研究当然要关注和了解文本的历史背景,但是,这种历史知识与历史无知一样都有危险,危险在于我们会把所研究的哲学家过度视为影响网络中的被动节点,而没有将他们充分地视为自己思想的主动的天才。(25) 贝内特的哲学史著作因其清晰、细致、敏锐而影响极大,也不免毁誉参半。
反过来,语境史观的纯正派也不接受“以今释古”。在语境史观看来,必须强调哲学史自身独立价值,离开了哲学的历史性、对哲学的历史性理解,我们就无法处理关于哲学自身性质的哲学问题。用斯金纳的话说,“我们不应将目光局限在文本或观念单元上,而应集中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总体的社会和政治语汇。由此出发,我们最终能够将那些重要的文本放在其恰当的思想语境之中,将目光转向这些文本得以产生的意义领域,并进而为这种意义领域做出贡献”。(26)
语境(context)与背景(background)、环境(circumstances)、处境(situation)等概念一样,一直是理解和诠释的重要视角。在16、17世纪,各民族语言中开始出现contesto,contexture,context,kontext,主要用于诠释文本,特别是《圣经》和亚里士多德著作。19世纪以来,语境史观在诠释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诸多领域大放异彩,以至于在20世纪下半叶,全方位出现了所谓“语境论转向”。(27) 在哲学中,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语境观影响最大。在科学哲学中,库恩的范式理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辐射到各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政治哲学中,语境史观的代表是“剑桥学派”,在其各具特色的代表人物中,斯金纳是最有力的代言人。(28) 因为斯金纳不仅将语境史观运用到政治哲学史的研究中,而且提出了政治哲学和一般哲学的语境史观的基本原则。在这里,我们以斯金纳为代表来阐述语境史观的基本思想。
在政治哲学或政治思想史层面上,斯金纳要求让政治思想史具有真正的历史性特征。(29) 让历史把握真正具有历史性的材料,而不是滑过各种抽象的光滑如镜的表面。基于这种要求,斯金纳的研究着重在三个核心领域展开:历史文本诠释,省察意识形态(30) 的形成与变迁,分析意识形态与其所体现的政治行为之关系。按照塔利的概括,其研究步骤或主要问题包含五个层面:(31)
(1)在写作文本时,作者如何处理其文本与构成意识形态语境的其他文本的关系?
(2)在写作文本时,作者如何处理其文本与构成实际活动语境的政治行为的关系?
(3)如何确定各种意识形态,如何省察和解释其构成、变迁以及相关批评?
(4)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行为的关系如何?如何以这种关系最佳地解释特定意识形态的扩散及其对政治活动的影响?
(5)在意识形态变迁的传播与习俗化、惯例化中,包含何种形式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
尽管相对而言,政治思想史最容易实践斯金纳的语境史观,但他并不想让语境史观局限在这一领域,而是要将其扩展为哲学史的一般原则。因此在他看来,当我们把各种哲学再现为历史中完成的一系列行为,就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对这些行为的叙述“算”历史还是“算”哲学,如果二者都算,它们如何关联?斯金纳接受了来自奎因、戴维森,特别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整体论。他认为,如果我们想以真正历史的精神书写哲学史,就必须把我们研究的文本置于思想语境当中,使我们能够理解作者写作这些文本时实际上在做什么。为此,就要区分语言的两个维度:一是语义学维度,即考察语词和句子的意义与指称;二是语用学维度,即在使用语词和句子时,说话者能够做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能够理解《理想国》的程度部分取决于我们复原柏拉图行为的程度”。(32) 总之,斯金纳力图从思想史中揭示事实上并不存在无时间性的概念,只有与不同的社会相伴而生的概念。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去解释一个普遍的真理,这真理不仅关于过去,也关于我们自身:每一个时代的我们,都是历史性的行动者,而文本即行动,因此,理解文本的过程,就如同理解一切自愿的行动那样,要求我们复原文本作者的行动所体现的意图。行动反过来也是文本,行动所体现的主体间性意义是我们能够解读的。
斯金纳说:这种研究的“适用性”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与我们自己的预设和信仰体系保持距离,从而将我们与其他生活形式相对照。用伽达默尔和罗蒂最近的说法来表述,即由于这种研究能够使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陈述和概念化活动并非唯我独尊,因此对于纯粹历史的兴趣与真正哲学的兴趣之间的截然区分,能够使我们质疑这一区分的正当性。(33)
三、寻求分析史观与语境史观的平衡
分析史观与语境史观这两种理想形态之所以会出现分野乃至对立,其原因在于它们对两个彼此缠绕的问题的解答出现了分歧。
(1)相对于哲学本身而言,哲学史的地位究竟如何?哲学史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
(2)哲学史研究的重心到底是历史文本中的哲学问题及其论证,还是文本在语境中的历史精确性?换言之,理性重构和历史重构、分析史观和语境史观究竟哪一个更优先、更重要?
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涉及对哲学和哲学史性质的理解,对哲学与哲学史关系的看法,结果必定会有极大的差异甚至对立。奎因曾有一句讥诮的隽语:人们出于两个原因研究哲学,一个是对哲学史感兴趣,另一个是对哲学感兴趣。(34) 按照罗蒂的看法,奎因这句话的意思是,哲学的正确任务是解决一系列可以辨别出来的问题,这些问题源于自然科学的活动和结果。用赖欣巴赫在《科学的哲学的兴起》中的概括,就是哲学从思辨走向了科学。但是,麦金泰尔主张,科学史以某种方式统驭自然科学,哲学史也统驭其他学科。他这样反击奎因:“哲学的成就最终是由哲学史上的成就来判定的。……对当今哲学感兴趣的人,其结果注定是:百年后只有那些对哲学史感兴趣的人才会对他们感兴趣。因此,用古今关系的这种观点在哲学上废弃过去,其结果就是预先废弃我们自己。”(35)
可以看出,关于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的各种观点,背后隐含着关于哲学的古今之争。古今之争中两个强硬的对立立场是好古成癖与以今释古,二者皆有时代误置的危险。若就温和立场而论,古今之争似乎包含着两种可接受的态度之间的冲突:一是我们不能自诩比以往伟大的哲学家更有智慧;二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哲学的探索在诸多问题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的确有进展、有进步。要化解这个冲突,似乎有两个可行的途径。其一,放弃关于哲学和哲学史的一般性的宏大叙事,把二者理解为具有家族相似性特征的概念,理解为由相似性和差异性构成的丰富多彩的精神活动,探索具体的哲学问题和哲学史问题。其二,充分理解哲学的历史性特征和哲学史的哲学特征,以此为基础,通过区分探索的层次和阶段,化解哲学与哲学史的对立。在此,笔者主要讨论第二个途径。
当我们考察哲学史编纂所依赖的预设时,就会发现它们本性上是哲学的;而考察哲学活动,则会发现它们是历史性的行为。套用康德的名言,也许可以说:哲学无哲学史则空,哲学史无哲学则盲。因此,我们一方面必须肯定哲学的历史性,我们所称的哲学不是通过否定过去的哲学而产生的这个或那个体系,而是哲学的整个过去,全部历史。每一种哲学都通过一系列关系将哲学与哲学体系的总体联系起来,并相互依赖。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让哲学史成为哲学的、而不仅仅是历史学的研究。哲学史编纂不能仅限于钩沉文本,阐明事实,推究因果,还要分析概念,重构论证,彰显意义。著名文艺复兴哲学史家克里斯特勒说:我曾听到一位历史学家主张思想史太重要,因此不能留给哲学家;我回答说,哲学史太重要,不能留给非哲学家。(36) 为什么?用安东尼·肯尼简洁有力的概括就是:要诠释昔日的哲学家,诠释者就一定要为这位哲学家的思想给出和提供理由,一定要阐明和评价他的论证。这本身就是地地道道的哲学活动。因此,绘画史家不必是画家,但哲学史家却不可能不是哲学家。(37)
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分析史观和语境史观上保持必要的平衡。保持平衡的根据在于:其一,哲学和哲学史的文本都兼具历史性和可分析性(逻辑—分析的方法并不等于分析哲学的方法);其二,分析史观和语境史观实际上都聚焦于哲学文本本身,只是路向有异,取径不同;其三,分析史观的研究进路实际上是以某种当代哲学、研究者自身的哲学思想为语境的,语境史观倡导者的思想背景、学术训练、概念语汇也隐含着当代哲学的某些思想和方法。因此,即便不坚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强硬立场,二者也都面临如何澄清自身的思想语境和哲学观的问题,而这种反思会成为二者对话与沟通的契机。
首先,分析史观与语境史观的对话和沟通会让我们意识到各自的价值和局限,进而意识到取长补短、相容互补的必要性,从而唤起研究者对自身理论立场和研究方法的自觉。
我们应当承认分析史观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从理论层面上说,运用分析史观的哲学史家不仅能够呈现出哲学史中的文本、思想所关注的问题、运用的方法、建构的论证和理论的得失,而且能够敞开历史文本在哲学上的多种可能性,并将历史文本与当代旨趣相对照,使历史资源服务于当今问题的探索。从实践层面上说,近年来基于分析史观的哲学史家既从事哲学史研究,将严格的文本分析与哲学上富有启发意义的批判融为一体,写出高质量的哲学史著作,又能够在其他著作中捍卫自身的哲学观点。这种双手开弓的工夫对于哲学研究和哲学史研究都有贡献,对于弥合哲学与哲学史的不必要的裂隙也有帮助。
我们也必须肯定语境史观的重要意义。从建设的方面说,复原文本的历史面貌(物质层面),精细校勘历史文本(语文学),阐明文本语汇的时代特征(语义学—语用学),还原文本的历史语境(历史学),编纂翔实而准确的哲学史,会通哲学史与观念史、思想史、社会史。从治疗的(therapeutic)方面说,没有语境史观对各种理性神话的去魅、(38) 对似是而非的流俗哲学史的去蔽,(39) 就没有真实的哲学史,哲学家的批评也常常不过是无的放矢,臆造对手,哲学家的理论建构——只要涉及哲学史——也会成为空中楼阁。对于历史文本中主题思想的不一致之处,分析史观往往直指为矛盾,称之为缺陷,语境史观则探本穷源,务求同情之了解。
当然,无视分析史观的语境史观也面临无法避免的质疑。例如,语境的范围如何选择?语境的类型是多样的:历时的,共识的,学科的,职业的,修辞的;语境的范围也大小不一,大到思想的全部物质条件、文化状况,小到个体的学术背景。不加限制的语境史观将无法为语境定位。也正是这个原因,斯金纳将其语境定位在言语行为和语言惯例层面。又如,语境史观如何回应历史相对主义的挑战?我们不可能与历史人物共处一个语境,我们虽然有可能与同时代人共享同一个关于过去时代的理解,但这不是过去时代自身所拥有的理解。因此,由于每个时代历史知识的积累总是有限的,哲学史家自身的独立预设不免会干扰他们辨认出另一个时代的独立预设。再如,语境史观认为语境比文本更易理解,因为语境源于事实性材料,而文本总有待于诠释;但问题是,一部历史文本能够成为哲学文本,恰恰在于它在历史语境之外仍然具有持久的哲学意义。如果否认这一点,将语境意识形态化,(40) 势必导致历史上的哲学问题、哲学思想的彻底历史化、相对化;其结果如哈曼所言:哲学史中的大人物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41) 既然不存在永恒的哲学问题,我们只关心我们自身的、当代的问题就足够了。但这样一来,当代哲学还能不能从哲学史研究中获益?哲学史又与当代哲学何干?
其次,分析史观和语境史观之间的对话和沟通还能够让研究者寻求方法上的平衡和综合。在这里,我们试以格雷西亚和克里斯特勒的研究来说明。“哲学史”这门学科本身就说明它具有历史学的性质,而我们必须强调要“哲学地研究哲学史”(done philosophically)。换言之,哲学史是哲学家的辅助性学科,唯有哲学家的参与才能确保哲学史的哲学内核不被忽视和稀释。因此,我们必须兼顾分析史观与语境史观,不能将它们意识形态化,而要在哲学史编纂和研究的具体活动中使之统一在兼收并蓄的方法论原则当中,成为“基础结构性的进路”(framework approach)。
“基础结构性的进路”是格雷西亚熔铸的术语。他考察了哲学史研究的13种哲学的和非哲学的进路,强调其中任何一种都无法单独成为哲学史正确而充分的方法,但有些方法的结合,倒可以成为基础的、中立的结构性方法,运用于描述性的、诠释性的和评价性的研究。这些方法中的基本要素涉及主要概念的分析与定义,问题及问题域的精确表述,阐明解决方案,对解决方案提出反驳,阐明评价论证的标准等。格雷西亚划分了两种西方哲学主流传统,即主导欧洲大陆哲学的诗学传统和主导英美哲学的批判传统,而这些方法能够服务于不同传统的共同目标——发现真理,拒斥错误,澄清概念,更自觉地意识到哲学问题的复杂性。(42)
在克里斯特勒看来,应将文本诠释与文本批评适当分离。前者是把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学术资源用于过去的哲学文本,而后者则要掌握哲学术语、问题和论证。前者作为历史性的学问有助于我们根据可靠的材料来重构理论,这种可靠性涉及文献上和文字上的,也涉及过去思想家的生平职业、全部著作、学术交往、社会经济背景、研究文献等。后者作为哲学诠释就不能局限在转述概括上,而是要超越其体系的外在结构,分析其思想的基本洞见和基本预设,关注其思想的矛盾和分歧,并理解其调和各种思想、避免分歧矛盾的种种努力等。
格雷西亚和克里斯特勒的思考都富于启发意义。格雷西亚力图给出一套独立于不同哲学传统的基础性方法框架,使之应用于各类哲学史研究。克里斯特勒则通过文本诠释、语境进路给出了充分而准确的整套文本,对可能的理解和诠释做了限制,使我们自身的思想观点对文本理解的影响和干扰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并通过文本批评、分析方法展示出历史文本的哲学内涵。
在哲学史家中能够将上述原则融会贯通的不乏其人,如著名哲学史家柯利(Edwin Curley)。他是欧洲近代哲学特别是斯宾诺莎研究的元老级人物,在历史文本的钩沉考释和时代语境的深度描绘上功力极深,同样也致力于对哲学系统及其论证的细致分析和精心重构。如在《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一书中,他要探索一种可能性,即用现在人们熟悉的形而上学模型来理解斯宾诺莎的体系;其中,他认为他对斯宾诺莎的实体和样式概念的分析与重构,其优点是可解亦可信、确切而融贯。(43) 总之,在与已故哲学家的假想式对话中(也就是哲学史研究中),熟稔并重构哲学文本所关注的哲学问题,把握文本的历史背景、文本间的相互关系,二者同样重要。(44)
近年来,在哲学史编纂实践中,我们能够看到在分析史观和语境史观之间保持平衡的大量努力。有代表性的专业文献可见于《剑桥哲学史》系列。(45) 以《剑桥十七世纪哲学史》为例,两位主编都偏重于语境史观,特别指出分析哲学传统的哲学史家因其自身的哲学旨趣和先入之见非常强烈,常常忽视了历史上哲学文本的复杂语境。不过,编者和作者在强调更广泛的思想语境的同时,并不回避分析方法,关注历史进路也绝不意味着与当今的哲学旨趣无关。该书中用诸多案例表明,“无论在具体实践上,还是在方法论上,对文本的历史的理解和哲学的理解是不可分的”。(46)
西方学界对哲学史编纂和研究方法的探讨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和借鉴。首先,我们有必要摆脱对哲学与哲学史的简单二分,也有必要澄清哲学与哲学史的混同,否则,哲学家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流俗的哲学史书写所蒙蔽,而哲学史家被独断的哲学体系所束缚而未曾反思自身的哲学观。在这个意义上,对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自觉,对分析史观与语境史观的充分关注与平衡运用,不仅能深化我们对哲学史的认识,也能深化我们对哲学这门学科和这种思想方式本身的理解。其次,由于当代哲学和哲学史研究在技术性和精细化方面大大加强,绝大部分学者只能深入钻研某个局部领域,熟练运用少数研究方法。因此,在哲学史研究的各个环节上,分析史观与语境史观的具体运用依赖于整个学术共同体的方法论自觉和研究成果的积累。
注释:
① Richard Rorty,“The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y:Four Genres,” in Richard Rorty,et al.,eds.,Philosophy in History:Essays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y,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49.(陈寅恪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已表达了相近的观点和忧虑)罗蒂在文中实际上提出了书写哲学史的四种风格,除理性重构和历史重构外,还有以黑格尔的哲学史为典范的精神史的宏大叙事和学说汇编。不过,最受关注的还是他提出的前两种类型,因为二者虽不是哲学史编纂的全部类型,却是主要的、最有代表性的研究进路。在笔者看来,精神史和学说汇编亦可分别纳入理性重构和历史重构的范畴。
② 参见笛卡尔:《哲学原理》第一部分,第75节,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2页;参见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之原则三,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8-9页。
③ Martial Gueroult,“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s a Philosophical Problem,” The Monist,vol.53,no.4,1969,pp.563-587.
④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6页。
⑤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4-35页。
⑥ 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⑦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0页。
⑧ Tom Sorell and G.A.J.Rogers,Analytic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43ff.
⑨ Margaret D.Wilson,“History of Philosophy in Philosophy Today; and the Case of the Sensible Qualitie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vol.101,no.1,1992,pp.191-243.
⑩ Quentin Skinner,Visions of Politics,Volume 1:Regarding Metho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89.
(11) Ibid.,p.77.罗蒂认为这个观点是历史重构的原则。
(12) Calvin G.Normore,“Dox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Suppl.vol.16,1990,pp.203-226.
(13) H.J.Glock,“Analytic Philosophy and History:A Mismatch?” Mind,vol.117,no.468,2008,pp.867-897.
(14) 其中有代表性的是Rorty et al.,Philosophy in History:Essays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y(1984); Alan Holland,ed.,Philosophy,Its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1985); Peter Hare,ed.,Doing Philosophy Historically (1988); Sorell and Rogers,Analytic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Philosophy(2005).
(15) R.C.Sleigh,Leibniz & Arnauld:A Commentary on Their Corresponde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pp.2-4.
(16) Howard Cohen,“Keeping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vol.14,1976,pp.383-390.
(17) Michael Frede,Essays in Ancient Philosoph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7,pp.ix-xiii.
(18) Margaret J.Osier,“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A Plea for Textual History in Context,”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vol.40,no.4,2002,pp.529-533.
(19) Gregor Sebba,“What Is‘History of Philosoph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vol.8,1970,pp.251-262.
(20) R.M.Sainsbury,Russell,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9; reprint,1999.Peter Hylton,Russell,Idealism,and the Emergence of Analytic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21) Aaron Preston,“The Implications of Recent Work in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The Bertrand Russell Society Quarterly,no.127,2005,pp.11-30.
(22) Peter H.Hare,ed.,Doing Philosophy Historically,Frontiers of Philosophy,Buffalo:Prometheus Books,1988,p.12.此书的第一部分是持语境史观的哲学史家对贝内特的批评以及贝内特的回应。
(23) Frederick Beiser,“Dark Days:Anglophone Scholarship since the 1960s,” in German Idealism: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ed.,Espen Hammer,London:Routledge,2007,p.72.
(24) Jonathan Francis Bennett,Kant’s Analyti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6.
(25) Jonathan Francis Bennett,Learning from Six Philosophers:Descartes,Spinoza,Leibniz,Locke,Berkeley,Hume,2 vols,Oxford:Clarendon,2001,p.1.
(26) Stefan Collini et al.,“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History Today,vol.85,no.10,1985,pp.46-54.
(27) Peter Burke指出,语境论转向的一个标志是相关词汇的出现。例如在英语中,contextualism出现的记录首次见于1929年的哲学著作;contextualize则于1934年首次出现在语言学中,contextualization于1951年首次出现在人类学中,decontextualize于1971年首次出现在社会学中。在法语中,contextuel是在1963年以后被记录下来的。此外,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图书目录中,在1978-1999年的20年间,1453本书的标题中有context,其中377本书用的复数形态的contexts。参见Peter Burke,“Context in Context,” Common Knowledge,vol.8,no.1,2002,pp.152-177.
(28) 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包括:John Laslett、Quentin Skinner、John Pocock和John Dunn.
(29) Quentin Skinner,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vol.1,p.xi.
(30) 斯金纳的意识形态指语言习惯和许多著作家使用的政治语言,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一般意识形态语境,由经院主义、人文主义、路德主义和加尔文主义构成。
(31) Tully and James,ed.,Meaning and Context: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Cambridge:Polity,1988,pp.7-16.
(32) Ouentin Skinner,Visions of Politics,Volume 1:Regarding Method,p.107.
(33) Quentin Skinner,Visions of Politics,Volume 1 :Regarding Method,p.125. (34) Richard Rorty,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Essays,1972-1980,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p.211.
(35) Alasdair Macintyre,“The Relationship of Philosophy to Its Past,” in Philosophy in History:Essays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y,p.40.
(36) Paul Oskar Kristeller,“Philosophy and Its Historiography,”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82,no.11,1985,pp.618-625.
(37) 安东尼·肯尼主编:《牛津西方哲学史》,韩东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38) 在斯金纳的著名论文《思想史中的意义与理解》(1968,2002)中,他揭示了各种可归入神话或迷思的历史性谬误,如学说神话(mythology of doctrines)、一致性神话(mythology of coherence)、思想史写作的特殊褊狭(parochialism)等。参见Quentin Skinner,Visions of Politics,Volume 1:Regarding Method,pp.57-89.
(39) 所谓流俗的哲学史书写,用沃森的话说就是“哲学中的影子历史”。影子历史是关于哲学历史的一些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大多数哲学家都接受它们,即便他们知道观点中历史事实并不准确,但这些观点往往比哲学史家挖掘出来的真实情况更有影响力和生命力。参见:Richard A.Watson,“Shadow History in Philosoph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vol.31,no.1,1993,pp.95-109.
(40) Yves Charles Zarka强调,语境的运用不应变成滥用,更不应上升到意识形态层次。参见Tom Sorell and G.A.J.Rogers,Analytic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Philosophy,p.150ff.
(41) Margaret D.Wilson,“History of Philosophy in Philosophy Today; and the Case of the Sensible Qualities,” p.193.
(42) Jorge J.E.Gracia,Philosophy and Its History:Issues in Philosophical Historiography,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pp.279,319.
(43) Edwin Curley,Spinoza’s Metaphysics:An Essay in Interpreta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pp.50,78.
(44) Edwin Curley,“Dialogues with the Dead,” Synthese,vol.67,no.1,1986,pp.33-49.
(45) 目前已出版《希腊化时期哲学史》(1999)、《晚期希腊与中世纪早期哲学史》(1967)、《中世纪晚期哲学史》(1982)、《文艺复兴哲学史》(1988)、《剑桥十七世纪哲学史》(1998)、《十八世纪哲学史》(2006)、《1870-1945年哲学史》(2003)等七部著作。其中《剑桥十七世纪哲学史》虽然只是一部百年断代史,但积两位主编和数十位学者16年之功(1982-1998)而成。该书分两卷,长达1616页。其中正文分7部分,36章,注释达4929条之多;附录中有极为详尽的文献指南114页,主要人物介绍118条(包括作者的主要著作和最好的二手著作综述)。
(46) Daniel Garber and Michael Ayers,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eventeenth-Century Philoso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4.
标签: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哲学史论文; 分析哲学论文; 斯金纳论文; 史观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哲学家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