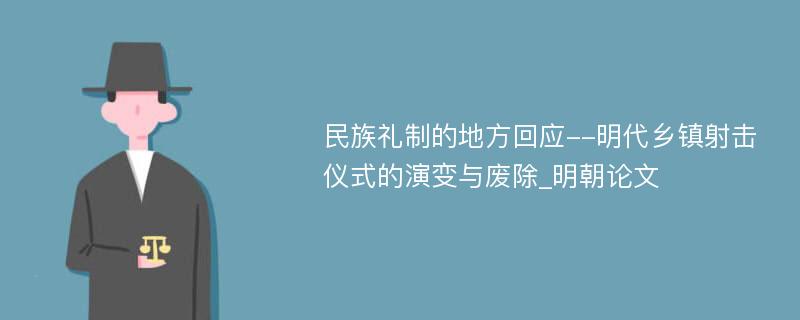
国家礼制的地方回应:明代乡射礼的嬗变与兴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礼制论文,明代论文,地方论文,国家论文,乡射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92.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7)06-0144-06
乡射礼是古代乡学中举行的一种礼仪活动,射而饰以礼乐,兼具击射尚武的精神与修身培德的教化意义①。汉唐之际举行乡射礼者寥寥,两宋时期儒学立武斋,乡射礼有所复兴。但从整个帝制时代看,明朝对乡射礼最为重视并普遍举行,兴兴废废,持续二百多年。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明洪武初就颁布了乡射礼制,但后来地方儒学所行乡射之礼多与其不同,且各地乡射礼时兴时废的情况很突出。本文主要通过明代乡射礼的嬗变与兴废,考察国家礼制在地方回应中展现的国家意志、地方态度与士人追求,以及三者是如何影响明代乡射礼的。
一、重射艺:乡射礼体现的国家意志
明朝继蒙元之后建国,政治、文化的规制多以“恢复中华”相标榜,出现了“法古为治”的趋势。以儒学教育为例,明朝恢复传统儒学的“六艺”之教。洪武二年,诏天下府州县立学校,学者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射为六艺之一,被列入各地儒学日常的教学内容,当时制定的《皇明立学设科分教格式》要求生员每日“未时,习弓弩,教使器棒,举演重石”[1](卷2,《官制·教法》)。第二年,定学校射仪。明太祖朱元璋要求各地“于儒学后设一射圃,教学生习射,朔望要试过。其有司官闲暇时,与学官一体习射。若是不肯用心,要罪过”。射圃一般为南北向,位于儒学内四周或附近地区,其射位至射鹄三十步。每月朔望举行乡射礼,选府县官员子弟和士民俊秀者分耦表演射艺,裁决胜负,凡胜者赏酒,“中的者三爵,中采者二爵”。可以看出,此时儒学的习射具有很强的军事性质,平时训练,每月朔望乡射礼实际成为守令考验生员习射成绩的一种形式。洪武二十五年,修订射仪。“遇朔望习射于射圃。树鹄置射位,初三十步加至九十步。每耦二人,各挟四矢,以次相继。长官主射。射毕,中的饮三爵,中采二爵。”[2](卷76,《学规》)与洪武三年射仪相比,乡射的射程有很大的增加,需要射者膂力强劲,其重“射”而轻“礼”的军事性质更加突出。由于习射成了明初儒学教育的一部分,从洪武三年开始,各地儒学先后建立射圃以便习射和举行乡射礼,其中在明朝统治中心的江南地区,射圃建立最为普遍。如杭州府学,“洪武三年,诏天下儒学就学辟射圃习射,本学射圃肇建于庙殿之东”[3](卷24,《学校》)。嘉兴府学,洪武三年遵旨设射圃于礼殿之东[4](卷3,《学校》)。宁波府学,“大明洪武三年八月十八日,钦命学校设射圃习射,乃仍(宋)旧址筑圃,作观射亭三间”[5](卷6,《学校》)。湖州府所属乌程、归安、长兴、武康、安吉等县洪武初俱建射圃[6](卷9,《学校》)。吴县、常熟、嘉定等地儒学的射圃都建于洪武八年之前[7](卷24,《学校》)。随着明朝全国的统一,其他地区儒学也陆续建立射圃,时间上并不一致,有晚至永乐、宣德以后者。
从礼仪论,洪武乡射礼节目疏阔,缺少进退周旋、歌诗奏乐等礼仪,过分强调击射中鹄的技艺,呈现出乡射礼尚武的军事性质。这反映了明初社会的历史特点。随着明朝政权的建立和全国的统一,国家由战争状态转向文治之世,“偃武修文”必然要提上政治日程。一方面收兵息武,让武人学习诗书礼乐,涤除其骄暴强悍的习气,使武人“文化”。另一方面为了应对内外局势,武备不可不讲。明太祖与诸将论兵政:“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蓄药以治疾,不以无疾而服药。国家未宁,用兵从勘定祸乱,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练士卒,使常有备也。”[8](卷5,《谕将士》)承平之时仍要常讲武备,总体看却以防为主,是收敛性的,且武备不应专依赖武人。明太祖朱元璋由此提出了“文武兼备”理想化的两全之策,反对专立武学、行武举,而是寓武于文。职是之故,洪武三年明太祖因为“弧矢之事专习于武夫,而文士多未解”[9](卷52,洪武三年五月丁未),要求天下儒学尚武习射。洪武二十五年再次重申射仪。此举与当时偃武修文的大政方针并不相违。其关键微妙处,明人薛应旂有论:“天厌元德,我祖肇兴,属当偃武,而射圃之设必于文教之地”[10](卷7,《重修三学射圃记》)。习射本武夫之事,文士习射于儒学,实际是并“武”于“文”,为偃武修文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偃武而不废武”的效果[11](卷15,《仲兄三兰学使射书跋后》)。当时地方官劝勉诸生习射时说:“国家举六艺之科,兼历代之长,而弓矢武备皆在所习。文以经邦,武以定乱,将相储材,万世之洪规也。”[12](卷27,《桂林府学射圃记》)也即,通过文士的习射,造就文武兼备的可用之才,兴文教之时,不废武事,既可以备国家缓急之用,又可改变对武人的依赖。当武人兵权被收,文人出将入相,才是真正的偃武修文。
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政治设计中,乡射礼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富有深意。洪武以后,明朝国家对乡射礼的关注秉承太祖之旨,强调它的“寓武于文”的社会功能。正统二年六月,英宗命行在(北京)礼部申明乡射旧制,文事武备不可偏废[13](卷31,正统二年六月乙亥)。成化三年六月,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商辂上书宪宗,要求提学官考校诸生射艺[14](卷43,成化三年六月戊申)。弘治十七年六月,礼部命提学官每月一二次令生儒习射,兼读古兵法诸书,使文事武备兼行不废[15](卷213,弘治十七年六月庚辰)。从正德到万历,《明会典》所载乡射礼一脉相承。由于明朝所行乡射礼一本太祖之制,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修改,乡射礼体现出的“重射轻礼”的特点依然如故。
二、重教化:地方社会的礼治要求
永乐以后明政府屡屡申明旧典,要求地方官和提学御史敦行如制,不时考核射艺。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家礼制在地方社会有着不同的回应。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许多儒学所行射礼迥异于国家定制。《成化杭州府志》卷二十四《学校·射艺》记:
迩者江西建昌守谢士元笃意以教诸生,谓传于抚人吴某。嗣是,苏守丘霁亦尝遣学而行于苏。顾其文颇异礼经,岂吴某尝损益之欤?然谢、丘二守不按礼部图式行,而有取于吴,岂图式岁久遗佚而二守不及见欤?以二守信尚而犹不及见,则天下之不及见者,不独二守可知矣。
李东阳《怀麓堂集》卷三十《绍兴府学乡射圃记》:
射,艺类也,君子之所不可阙,故可以正心志,可以习容体,可以立德表行,其道大矣……比年知建昌府谢侯士元始用古礼行时制,凡春秋朔望皆有射。其后知苏州府丘侯霁继之,提学御史戴君珊图下南畿诸学,又继之。成化乙未,戴君之从兄琥自南京御史知绍兴府,初政之暇,实倡兹礼。遣诸生二人往习于苏,既又与其寮佐蒋君谊辈参互考订,无戾于古,乃辟圃作堂于府学之后,山阴、会稽二县学皆会焉。
王鏊《震泽集》卷十五《吴县学射圃记》:
学之有射圃,非曰不忘武备也,盖亦学焉,而其礼废久矣。其仪虽具于《仪礼》,顾未有举行之者。往时,天台陈公选以御史董学政于吴,始命两生习之大江之西,得其仪以还,俾诸生岁时肄之……问学之余,于是游焉,息焉,揖让焉,独非学乎?即有傲慢怠惰之气,奚自入焉。盖非唯可以观德也,又可以养德焉。故曰,仁者如射。又曰,射有似乎君子。
以上三则相互补充的系统材料,让我们较为清晰地看出明代乡射礼在江南地区的变动轨迹。天顺、成化之交,江西建昌知府谢士元“以古礼行今制”,对乡射礼进行改革。其礼传之于抚人吴某,即抚州处士、当时大儒吴与弼[16](卷8,《复建昌郡侯谢士元帖(侯遣诸生习乡射礼)》)。吴氏上承程朱理学,下开明代心学,居乡“动必以礼”。他损益古礼,传之建昌诸生。既不同礼经,又大异于国家定制。不久,苏州知府丘霁遣学于建昌,经提学戴珊图其仪注,传布南京附近各学。成化十一年,浙江绍兴知府戴琥遣二生员学射礼于苏州,则又传于浙江。江南地方出现的这些新射仪不再是“重射艺”,而是注重礼乐仪式,进退周旋,这种类似艺术表演的乡射礼是“以射寓教,而非徒善其艺”[17](卷31,《华亭县学射圃记》)。故李东阳、王鏊等人在绍兴府学、吴县县学建射圃、行新仪之际无不强调,乡射礼“可以正心志,可以习容体,可以立德表行”;“非唯可以观德也,又可以养德”。可见,乡射礼“教化”意义的彰显,表明洪武时代乡射礼“寓武于文”的政治意义变得越来越模糊。承平治世,肩负教养职责的地方官推行传统乡射礼,其目的是为了以礼化俗,教化百姓,而不是习射尚武。也正因为如此,短短十余年,乡射礼丕变于江南,决不是《成化杭州府志》作者所推测的“不知礼部定式”的缘故。根本原因在于时异势殊,人们对乡射礼社会功能的期待发生了变化,洪武礼制遮蔽了传统乡射礼“修身观德”的教化意义才得以适时呈现。
乡射礼变迁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大量礼书文本的出现。这些礼书多为主管学政的提学御史、儒学教官(包括少数守令)所编撰,然后推行一方,成为各地儒学习射的礼仪指南。例如,林廷玉《古射礼节略仪注》在广东香山、新会等地得到推广,影响很大。《香山县志》载:“其礼(指洪武乡射礼)与古不同。永乐中申明出榜,亦久废不讲。正德三年,提学副使林廷玉始定《古射礼节略仪注》,新会诸生黄彦等肄习,定为春二三月、秋七八月朔望行之。又下其法于州县。嘉靖中,提学副使魏校、欧阳铎踵行之,且刊其仪为书,俾知所守。”[18](卷4,《教化志》)郭登庸,嘉靖中任湖广提学副使,刊刻陈凤梧《射礼集要》。林烈,福州人,撰《乡射礼仪节》。嘉、隆之交他在家乡嵩阳社设立射圃,率弟子一百余人以礼习射。朱缙,河南郏县儒学教谕,嘉靖十七年撰《射礼集解》,“复乃召集诸生,讲解明悉,分以执事。未几,按礼画图,举而行之,则见其雍雍然,肃肃然,容止有仪,进退有度甚矣”[19](卷135,《仪礼》)。这些新修礼书的传播范围,已经不限于江南,遍及江南之外的广东、湖广、河北、河南、福建等地区。甚至在两京国子监,射礼也不再按照洪武旧制。种种情况表明,明代乡射礼大约从成化到嘉靖完成了全面而深刻的历史变化。变化后的新射礼在内容上都与旧制表现出明显不同。例如,时间由原来的“每月朔望”恢复为古礼的“春秋朔望”;增加了旅酬、歌诗、扬觯等一些礼乐环节;弱化了射技的较量,强化了以射修德的教化性。
嘉靖中,河南郏县教谕朱缙说:“世儒者有射礼《纂要》、《直指》、《节要》等书,撰次虽为详明,而今之演习古射者,多虑漫无依据,艰于效慕。”[19](卷135,《仪礼》)为解决人们对于乡射礼“多虑漫无依据,艰于效慕”的合法性问题,他依据《仪礼》,参考群集,编撰成《射礼集解》。朱缙把新射礼的合法性建立在《仪礼》等古礼的基础上,依靠经典的力量达到改造洪武旧制的目标,又摆脱了“罔作聪明以乱典章”的罪名。因此,这种通过损益《仪礼》等古礼的路径为当时修礼诸家所纷纷采用。
林烈《乡射礼仪节》就是“节录《仪礼》经文,各略为诠释,而系之以图”。王廷相编撰的乡射礼,不仅依归《仪礼》,对《明会典》所载“今仪”也加以保留、利用。与王氏《乡射礼图注》手法一致,侯廷训的《六礼纂要·射礼篇》“亦先《会典》而附以古礼”,即在“射礼篇”前抄录《明会典》的“洪武三年”、“洪武二十五年”关于乡射礼的规定。这些做法的用心不外乎使礼制变革显得温和,减缓地方射礼与国家之制的紧张感,是利用国家制度本身的权威来表明新射礼的合法性。
《仪礼·乡射礼》是以“三番射”为中心的一组礼仪,有燕饮、献酬、作乐、歌诗、扬觯等礼乐环节,习射活动在礼乐的改造下成为一种艺术表演,不是“贯革穿皮”的军事性击射,而是《仪礼》所说“不主皮”之礼射,具有修身观德的教化意义。洪武旧仪突出射的技艺,类似古人所称的“主皮之射”,是军事训练,缺少礼乐仪式,不能满足和平时期地方礼教的需要。故以《仪礼》改革洪武旧制是实现乡射礼社会功能转变的一个途径。
此外,明人改礼也有取于《礼记》、《周礼》者。下文将具体分析《仪礼》等古礼中有关仪节对于洪武乡射礼功能转换的意义,亦即这些礼乐仪式具有什么样的教化意义。其一,饮不胜者。洪武乡射礼,凡胜者赏酒,“中的者三爵,中采者二爵”,旨在倡导争胜为先。万历时人杨儒宾说:“国家故有高皇帝钦定射仪,出于草创之世,百战之余,士无不争先命中者”[19](卷135,《仪礼》)。古礼则不同,《仪礼·乡射礼》载,在三番射之后,要让比射不胜的一方饮酒,看似罚酒。但古代敬酒尊长,寓奉养之意,故“(饮不胜者)虽行罚爵犹致敬之辞,以见不怨不矜也”。射中者免受罚酒,就是推辞别人的奉养,表现出君子谦谦之道,非奖其射艺。因此,“饮不胜者”仪节旨在养成群体之间的和敬。湛若水改革太学射礼,坚持要有燕饮、献酬之仪节,他说:“射也者,离道也,争道也,不合则离,离则争矣,非所以成德而致贤也。是故有燕、酬以合其欢,有揖让以致其敬,有乐宾以宣其和”[20](卷7,《节定燕射礼仪》)。“饮不胜者”这一仪节蕴含的和敬之教,在明代乡射礼改革中被重新认识,既见之于新修礼书,又付之于实践。如林烈《乡射礼仪节》“终射”一节有“饮不胜者”。嘉靖时广东增城县的乡射原先用赏酒之法,“中的用三爵,未用二爵”。其后去赏酒之制,“不中者取觯立饮”[21](卷11,《礼乐》)。其二,以《采蘩》为节。古人重乐教,认为乐能感人至深,可以善民心、导民和,可以移风易俗。《仪礼·乡射礼》谐射之乐有《关雎》、《葛覃》、《卷耳》、《采苹》、《采蘩》等,皆出《诗经》,故称诗乐。但洪武“乡射仪注”唯射而已,无诗乐。明代成化以后乡射礼改革以“教化”为宗旨,自然注重《仪礼》之乐教。限于时代差异,非全部搬用,多数地方的乡射礼主要以《采蘩》为主,兼用其他。如常熟县学《射礼仪注》“射诗”一节,只用《采蘩》。林烈《乡射礼仪节》初射前用《鹿鸣》,终射后奏《采蘩》。按《礼记·射义》,不同身份的人习射,所用之乐不同,天子以《驺虞》,诸侯以《狸首》,卿大夫以《采苹》,士以《采蘩》。乡射礼行于地方学校,主体为教员士子,故以《采蘩》。《采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它意在教导士人不可失职,“故明乎其节之志,以不失其事,则功成而德行立”。其三,扬觯。此仪不见于《仪礼》,而见于《礼记·射义》,据说孔子射于矍相之圃,使公罔之裘、序点扬觯。公罔之裘扬觯而语曰:“幼壮孝弟,耄耋好礼,不从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也。”序点扬觯而语曰:“好学不倦,好礼不变,旄期称道不乱者,在此位也。”听二位之语后,有些人就羞愧而去了。扬觯就是举起酒器觯,为三番射之前饮酒旅酬之动作。扬觯而语,实际成了公开、正面的道德宣教。明代中后期有些地方的乡射礼就增加了洪武旧仪没有的“扬觯”[21](卷11,《礼乐》)。如林烈《乡射礼仪节》设扬觯者二人,分立东西,位西者先扬,颂公罔之裘的话;位东者后扬,颂序点的话。广东增城,乡射时“置觯,如礼扬之”。总之,明代中后期乡射改革就是要通过礼乐的润饰,恢复其礼教的精神。明人邹廷望《重刻射礼序》说:“所谓射礼,世人率以为迂而无当……而不知圣王以之饰礼乐而观德行,其指归主于导人心之和敬而渐陶于正己之仁,非以为文具而炫人之听睹者,要在循礼之文,求礼之精意而已。”[22](《序》)
三、乡射兴废:科举时代的必然
洪武初,习射被纳入儒学教育内容,各地先后修建了射圃,每月朔望的乡射礼基本被制度化。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乡射礼不仅发生功能嬗变,其存在状态也是兴废无常。一方面,没有射圃的地方陆续兴修射圃;另一方面,已有射圃的地方乡射礼废弛状况十分严重。祝銮《重修太平府学射圃记》:“我朝稽古右文,建学造士,射圃立于学宫,射礼者之令甲,固将以三代之才望多士也。顾乃因循日久,莫或举之,圃鞠为茂草,礼视为虚器,使古人观德实效不复可见。”[23](卷2,《宫室志·学校》)应天府句容县儒学旧有射圃,建于永乐十年,“邑长学师怠驰其教,久弃弗理,遂至迷失其所”[24](卷9)。宣德九年,顺天府尹李庸奏,通州儒学旧有射圃,为军民侵占[25](卷110,宣德九年夏四月甲戌)。广东香山县原先举行的乡射礼,永乐中已“久废不讲”。到正德三年,才由提学副使林廷玉重新振举。福建惠安县射圃建于永乐十二年,射礼久废,嘉靖九年才再建射圃[26](卷9,《学校》)。江西南安府,此礼久废。苏州府常熟县儒学射圃建于洪武八年,久废不习,更筑号房,至弘治十年再建别处[27](卷3,《乐舞志》)。这些地方或者射圃荒废为人所占,或者射具不备乐器不存,即便圃存器备,官师士子也虚应故事,罕见实行。
读史至此,不得不疑惑:制度化的乡射礼为何在洪武以后迅速地废弛?这还需从明人有关议论中寻找答案。洪熙元年,有人感叹:“近年宾兴之士,率记诵虚文为出身之阶,求其实才,十无二三”[18](卷9下,洪熙元年四月己酉)。弘治时,南京礼部郎中李哲说:“我朝府县学校各有射圃,近年来士子只尚科目,而武教遂废,请行提学官每月一二次令生儒习射,兼读古兵法诸书,庶文事武备兼行不废”[15](卷213,弘治十七年六月庚辰)。嘉靖时,浙江提学薛应旂指出:“天厌元德,我祖肇兴。属当偃武,而射圃之设必于文教之地……承平既久,人情怠玩,而长才秀民又率多以空文相胜,流俗沿洄,旋失初意”[10](卷7,《重修三学射圃记》)。
以上所论有“记诵虚文”、“尚科目”、“以空文相胜”等语,点明了科举时代的崇文传统与习射尚武之间的不协调,反映了地方社会回应国家制度时具有自主性的目标指向,而自主性目标是由科举的指挥棒划定的。从国家的长治久安政治目标看,儒学习射具有重要意义;从诸生读书求功名的个人目标看,儒学习射则毫无意义。明朝科举的乡、会试内容以四书五经经义、诏诰表笺、事务策论等文事为要,从不把射、御、书、数等列入科举考试的内容。那么,学习射、御、书、数对于诸生就是一种无益之负担,明初那种以“六艺”教学、追求全才的理想设计势必难以实现,随之而来的是只崇经史,无暇他顾。不唯射礼不修,书数亦废。宣德四年,北京国子监助教王仙说:“学校教养人才,固当讲习经史,进修德业。至于书数之学,亦当用心。近年生员只记诵文字,以备科贡,其于字学、算法,略不晓习”[25](卷58,宣德四年九月乙卯)。府县等地方社会对于科举是相当重视的,有常规的财政予以支持,有披红送匾等庆贺活动,也就是说,功名也是地方社会的荣耀。而儒学习射无助于功名的取得,地方官吏当然难以热心,从而出现了类似应天府句容县“邑长学师怠驰其教”的情况。又如广东揭阳县儒学射圃为猾民侵占十之六七,“(弘治)前吏于兹土者,例视礼文之事为迂阔,而力又弗足以振之也,往往置而弗问”[29](卷4,《揭阳县儒学射圃记》)。增城县射圃嘉靖前已为废墟,“增学之士久荒射礼,其诸射器如弓矢丰觯之属,有司不为整置以教士射,士不复知射为何物?”[21](卷10,《学校》)
面对乡射礼的废弛,明朝政府屡屡申明地方要如式举行,提学御史巡历地方要加强检查督促。成化以后,随着乡射礼的变革,某些地方官吏把乡射礼与乡饮酒礼作为推动教化的重要途径,开始修复一些荒废的射圃,重新举行乡射礼。太平府人祝銮说,嘉靖皇帝继统以后,“屡敕提学宪臣申明古制(乡射礼),盖将以德艺淑人心,以礼教厚风俗,以挽先王之治。”在巡按御史刘谦亨、知府林钺等人的努力下,太平府学射圃得以重建,射礼再举[23](卷2,《重修太平府学射圃记》)。上文提及的广东地区,正德、嘉靖间提学副使林廷玉制定《古射礼节略仪注》,提学副使魏校、欧阳铎相继推广,久废之礼得以在香山、新会、增城等地举行。例如,增城“自提学魏校慨然有志于古,乃令学中再辟射地,既作射器,督教官谋士习射,岁一巡部考视之,以为赏罚,士自是知射礼焉”[21](卷10,《学校》)。江西南安府学乡射礼久废,正德、嘉靖间提学副使李梦阳等相继申明,南安府创置如式。以后稍废,知府何文邦修复举行[30](卷10,《礼乐志》)。总之,当乡射礼成为地方礼教的一部分时,它就能够存在。这时,国家以射礼造士的目标与地方礼教目标也趋于一致了。但是,乡射礼具有的礼育功能并不能使诸生在科举时代有所裨益。明人詹理《射圃记》说:
圣王教人端于蒙养之初而造于有成之日者,宜莫如射。(射)使人日徙事于持弓拾矢之节,习之不惮烦,审固以正其视,《采苹》以一其听,升降揖逊以劳其形容,体此礼所以肃此志也……。今之教者,吾惑焉。联师儒群子弟,非不烨然为可观也。顾究其志,不过口吻于蠹简之呻吟,情弊于游词之剽窃。矧纷华盛丽之习交引于外,而声利荣名之焰熏灼于中,又何怪乎?[31](卷24)
乡射礼与功名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表明乡射礼的制度化是很表面的,没有嵌入科举时代教育体制的核心,不能依靠体制本身维护其运行,只能在那些具有文化意识、注重礼治的“循吏”推动下才得以存续。然而,地方上并不总是有这样的官吏,一旦缺乏礼教热情的官吏主政,地方就难免出现圃荒礼废的局面。所以,在翻阅明代地方志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某个地方的乡射礼时兴时废,同一时期一些地方的乡射礼彼兴此废的现象。
乡射礼与乡饮酒礼都是地方儒学每年举行的礼仪活动,相对于前者,乡饮酒礼的举行较为稳定与常规化。除了乡饮酒礼通常在儒学的明伦堂举行,无须专门的场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乡饮酒礼的备办有固定经费。明代规定,府、县每年春秋两次的乡饮费用从“官钱”支出。中期开始役法改革,主要从均徭银或里甲银支出,一般为十两银子,也有多于此数者[32]。但乡射礼在明初每月朔望举行两次,明中期地方改革以后,每年春秋朔望举行两次(有的地方是四次),皆未见有关经费的记载。笔者查阅了百余种地方志,只看到惠安县设射圃看守一人[26](卷9,《学校》),浦江县曾为儒学射圃设立一名“禁子”(用银三两)[33](卷5,《财赋》)。没有固定经费,射具乐器的修整、射圃射亭的维护、献酬酒羹的备办等都无法正常解决。如果地方官或提学官关注乡射礼,他们可能采取捐资、募劝等临时措施来筹办射礼,于是礼兴,否则礼废。缺少经费是影响明代乡射礼废弛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本上讲,经费问题其实也反映出乡射礼制度化的表面性,以及地方社会对于乡射礼态度的因官而异、时冷时热。
综上所论,明朝把乡射礼作为“寓武于文”、培养文武全才的教育策略,而不是仅仅将其视为乡饮酒礼一类的礼仪活动。这种国家礼制的政治意义不久就被科举制度所消解,而面临着地方社会和士人群体的共同拒斥。但在明朝政府不断督促地方要举行乡射礼的权威下,地方社会则别开新局,改革旧制,把乡射礼由原来“重射尚武”的军事训练转变为“以射行礼”、“修身观德”的社会教化。成化以后,明朝地方的礼仪改革是在行旧制的表面下注入了新内容,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乡射礼的礼乐教化传统,以期有助于地方社会治理,故一些注重“礼治”的府县官和提学官积极推动乡射礼的改革。明朝乡射礼的嬗变与兴废于是有迹可寻。
收稿日期:2007-08-20
注释:
①关于乡射礼的性质,后世意见不一。杨宽先生赞同清人邵懿辰“《仪礼》十七篇中射礼即军礼”的说法,强调乡射礼具有军事训练和选拔人才的意义,参见《“射礼”新探》,载陈其泰等编《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学苑出版社,1998年。傅道彬在《乡人、乡乐与“诗可以群”的理论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后世的乡射礼已经被改造成可以观德行的艺术表演,具有教化意义。其实,这两种倾向在明代都存在,前后有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