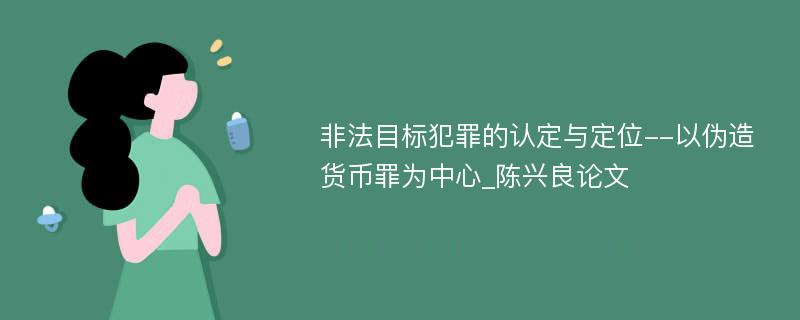
非法定目的犯的甄别与定位——以伪造货币罪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的论文,货币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学界关于伪造货币罪的对立观点
日本刑法第148条第1项规定,“以行使为目的,伪造或者变造通用的货币、纸币或者银行券的,处无期或者三年以上惩役。”据此,伪造货币罪须以行使为目的不存在任何争议。但我国刑法第170条规定的伪造货币罪,并未规定以行使为目的而只是规定“伪造货币的,处……”。在这样的立法规定下,伪造货币罪是否需要以行使为目的就是存有争议的。无疑,如承认此罪为目的犯,则本罪即属于非法定目的犯;若不承认本罪为目的犯,则本罪只属于一般的故意犯罪。对于本罪是否属于(非法定)目的犯,在我国刑法学者之间主要存在着下述两种观点之间的分歧。
(一)解释论否定说+立法论肯定说
张明楷教授认为,我国刑法鉴于伪造货币行为的严重危害程度,没有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特定目的。而且,对仅伪造货币并不使用伪造的货币的行为,也以本罪论处。事实上不以使用为目的而伪造货币的行为,也会侵犯货币的公共信用。因此,从解释论上而言,不应认为本罪为目的犯。①他指出,伪造货币罪的法益既可以是货币的公共信用,也可以是货币发行权,二者是一种选择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即只要行为侵犯了其中之一,就侵犯了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因而成立本罪。所以伪造货币罪不以具有特定目的为要件。②
但是张老师同时认为,“从刑事立法学的角度来看,或许要求‘以行使为目的’较为合适”,所以基本上可以认为,他主张解释论否定说+立法论肯定说。值得注意的是,在2003年出版的教材《刑法学》第2版和2004年1月出版的专著《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坚决主张解释论否定说的张明楷教授在2004年第3期《中国法学》上发表的文章中,下述论断值得关注。他指出,伪造货币罪,德国、日本等诸多国家的刑法都明确规定必须“以行使为目的”,但是我国刑法没有明文规定。如果认为我国刑法中的伪造货币罪也应“以行使为目的”,那么,伪造货币罪则属于短缩的二行为犯。③尽管,上述的论断未必意味着论者的立场发生了转变,但是在本文看来,论者的立场已经有了松动,不再那么坚决了。
(二)解释论肯定说+立法论成文说
陈兴良教授在新刑法刚刚颁布之后主编的《刑法疏议》中即主张本罪应有置于流通的意图。④最近,周光权博士在《刑法分论讲义》中也认为,本罪在刑法解释论上应当要求有行使、流通的意思(目的犯),即将假币作为真币置于市场上流通,从而危害货币的公共信用。单纯为了便于教学、艺术表演、私人收藏或展览而设计、伪造货币的,不认为具有行使目的,欠缺本罪故意,不构成本罪。⑤周光权博士在赴日研修之后出版的这部教材显然是受了日本刑法的影响,“为了便于教学、艺术表演、私人收藏或展览而设计、伪造货币”等,都是日本学者常举的例子。而且,周博士把本罪侵犯的客体理解为货币的公共信用,⑥从而要求伪造货币罪须以行使为目的。他的上述肯定说再次得到了陈兴良教授的肯定,陈老师并且主张非法定的目的犯的概念,同时认为对此种情况下的非法定的目的犯予以法定化为好。⑦所以,陈兴良教授的立场可以表述为解释论肯定说+立法论成文说。
二、不同观点的归结——伪造货币罪侵害的法益究竟为何?
(一)伪造货币罪的侵害法益
伪造货币罪是否以行使为目的,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刑法解释论上的问题,实际上却涉及到非法定目的犯的甄别问题。而这里的甄别标准,又首先与本罪所保护的法益相关。如果伪造货币罪侵犯的法益是货币制造或者发行权,则只要制作了假币就应构成伪造货币罪;而如果伪造货币罪侵犯的法益是货币的公共信用,则没有行使目的就难以说是侵犯了货币的公共信用,从而也就不应定罪处罚。伪造货币罪规定在1997年修订的刑法的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但是无论是旧刑法时代的教材,还是新刑法时代的教材(除了上述否定论者和肯定论者自己的著作外),对于本罪的法益的理解主要包括“国家的货币制度”、“国家的货币管理制度和国家货币的正常流通”、“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等等,大都仍旧理解得含糊笼统,这样理解的法益内容也就丧失了对构成要件的解释机能。
实际上,在日本,通说(平野龙一、大谷实、中森喜彦、町野朔、曾根威彦、林干人、山口厚等)都认为本罪所侵害的法益是社会对货币的公共信用,而国家的货币发行权并非本罪的法益。但是,学说中,尽管现在已经没有人主张本罪的法益仅为国家的货币发行权,但是主张本罪的法益除了社会对货币的公共信用外,国家的货币发行权也属于本罪的(次要的)法益的学者却也不少(木村龟二、植松正、大塚仁、西田典之等),⑧比如,西田典之教授指出,“本罪的保护法益,针对货币的公共信用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在此之外,国家的货币发行权是否也应该成为保护的法益。通说对此予以了否定,而判例以及部分学说则对此予以了肯定。确实,将国家的货币发行权理解为国家的威信、权力等的话,这样的东西作为法益是不适当的。但是,要是将之理解为货币发行量的调节这样的国家的金融政策的权限的话,就可能将其作为次要的法益来理解。”⑨而日本最高法院1947年对“新币替换事件”的判例也支持了本罪法益的“公共信用+货币发行权说”。⑩值得指出的是,陈兴良教授引述了木村博士主编的《刑法学词典》中的论断,认为伪造货币罪侵犯的法益,是社会对货币的信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交易安全。伪造货币罪侵犯的法益经历了一个从制造或发行货币以及批准权到货币信用的变迁过程。(11)但是,这本词典的主编者本人木村博士恰恰是主张本罪的法益是“公共信用+货币发行权说”的。(12)看来,一个犯罪所保护的法益究竟为何,其判断并非易事,认为伪造货币罪的法益经历了“从制造或发行货币以及批准权到货币信用的变迁过程”这样的转变,其实质根据可能还值得重新估量。
(二)对不具行使目的的伪造行为的出罪理由
对于本罪究竟是否属于目的犯的不同理解,不是单纯的学理上的探讨,它直接决定了没有行使目的的伪造行为能否处罚的问题。实际上,如果纠缠于本罪的法益究竟是公共信用还是货币发行权,就会使问题因为判断标准的不确定化而变得混乱。按照我的理解,张明楷教授所主张的本罪的择一法益不但不同于日本学界的通说(平野龙一、大谷实、中森喜彦、町野朔、曾根威彦、林干人、山口厚等)所主张的本罪法益为单一的公共信用,应该也不同于其他学者(木村龟二、植松正、大塚仁、西田典之等)的主张,木村等学者都肯定本罪的主要法益为对货币的公共信用,而认为本罪的次要的法益为国家的货币发行权。但是张老师的择一法益的主张则是不侵犯公共信用而只侵犯货币发行权的行为也属侵犯了本罪的法益,从而导致不具行使的目的的伪造行为也处罚。自然,择一法益的观点是立足于我国刑法现行规定之上的。但是这种观点能否成立本文怀有疑问。所以,就本罪来说,本文认为如果将不具有行使目的的伪造行为予以出罪的原因定位于是出于刑事政策上收缩法网的考虑的话,可能会使问题变得简单和明晰。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陈兴良教授的如下论断,“刑法没有规定伪造货币罪须以行使为目的,但从刑事政策出发对此作出限制解释,将没有行使目的的伪造货币行为从犯罪中排除出去,在刑法解释上也是可以成立的。”(13)
三、非法定目的犯的甄别标准:法益标准说(原则)+刑事政策说(例外)
法益侵害说是在与规范违法说的对应意义上被解释和展开的,立足于客观违法性论的基本立场,必然将法益侵害说理解为违法性的本质。所以,在客观违法性论的总体框架内展开的对于犯罪问题的解构,自然离不开法益侵害说的基础地位。在对非法定目的犯进行甄别的时候,法益侵害说也是必须首先予以考虑的。根据法益侵害说的观念,“某种目的、内心倾向等是否主观的超过要素,应取决于它是否说明行为对法益的侵犯及其程度。如果某种目的、内心倾向对决定法益的侵犯及其程度具有重要作用,即使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也可能将其解释为主观要件的内容;如果某种目的、内心倾向对决定法益的侵犯及其程度不具有重要作用、甚至没有任何作用,则不应该随意将其解释为主观要件的内容。”(14)可以说,法益侵害说有理由作为甄别非法定目的犯的首要标准,是必须首先考虑确定的原则。(15)
然而,法益本身是客观的、确定的,并不等于我们总是能够清楚地、准确地界定出法律所保护的该罪的法益。从法益侵害的角度来界定是否目的犯必定依赖于对于所保护的法益的理解,而在我国刑法的规定不尽周延和不尽理性的情况下,一种犯罪所保护的法益究竟为何常常缺乏判断的客观标准,常常没有任何的“立法原意”可循,见仁见智的结果可能是任意出入人罪。所以,本文尽管原则上愿意接受法益的构成要件解释机能从而承认其非法定目的犯的甄别机能,但是同时又主张必须面对在确定法益时的不确定性,从而也主张在以法益侵害说为原则来甄别非法定目的犯的时候可能需要借助其他的标准来弥补法益侵害说身后的空档。这里所说的“其他的标准”,就是作为例外的刑事政策说。
本文主张,就非法定目的犯的甄别来说,虽然法益侵害说是首要的标准,但是在立法上无法准确读出该罪的法益、而理论上又无法对该罪的法益取得有效共识的情况下,那么,无论是进行理论研究时是否将某种犯罪确定为目的犯,还是在进行司法认定时,都应该作为例外考虑刑事政策的需要,亦可称为考虑实质上的处罚必要性。从解释论的角度而言,一种犯罪被认为是目的犯(较之不被认为是目的犯扩张了构成要件从而缩小了处罚范围)的条件是只有附加上此种目的的行为才是具有予以处罚的现实必要性和实质合理性的,才是符合刑事政策的目标的,而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理解的单纯的法条本身的行为则不具有处罚的实质合理性,不符合刑事政策的理性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将此种法文上没有要求“目的”的犯罪限制解释为目的犯,此种情况即为非法定目的犯,而在此时,刑事政策的考量则作为在法益侵害说缺位的情况下甄别非法定目的犯的标准。
四、目的犯的存在形式:法定目的犯(原则)+非法定目的犯(例外)
只要我们承认立法者的有限理性(立法能力、技巧、经验等各方面的欠缺,并且立法者可能出于法条表述的简短精练等考虑,无意或者有意地将一些应该法定化的目的犯非法定化(16)),那么,刑法典就永远不可能将所有的目的犯一网打尽地规定于法典之中,所以肯定非法定目的犯的存在就是一种当然的立场。(17)同时,如果我们认为非法定目的犯属于开放的构成要件,(18)需要在认定时由法官加以填充,那么,我们就必须对这种开放的构成要件予以足够的警惕。(19)所以,本文虽然承认目的犯的立法价值(证明上的困难引发的目的犯本身的立法价值定位是另外的问题),承认非法定目的犯的存在,但是为了“在补充构成要件时持正确而且严格的解释态度”,(20)在目的犯的法定化与非法定化的对应关系上,必须明确以法定目的犯为原则,以非法定目的犯为例外。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法定目的犯与非法定目的犯的原则与例外的对应关系,不是对于我国现行刑法中的目的犯存在样态和分布状况的实然描述,就是说并不意味着本文认为我国刑法中的法定目的犯多而非法定目的犯少(当然也不意味着相反),而是主要着眼于以下两点考虑:1.从解释论和司法论的角度而言,我们必须清楚法文上没有标定目的的犯罪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能被理解为目的犯,从而要求我们在甄别非法定目的犯的时候必须谨慎地遵循相应的甄别标准。“例外”两个字本身就是告诫我们小心提防的警示灯。2.从立法论的角度而言,主张非法定目的犯肯定论的学者一般都主张其目的应该法定化,(21)这也从反面验证着非法定目的犯确实属于法定目的犯的例外。将学说上公认的非法定目的犯通过立法的方式将目的法定化,从而使定型的例外上升为原则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再有力的学说也无权去命令法官),这既可以因应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性的要求,又可以尽量避免非法定目的犯在认定时的困难和随意。可以说,这样的原则与例外的分析范式,符合法定目的犯和非法定目的犯的构造和趋向本身。
注释:
①张明楷:《刑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07页。
②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页。
③张明楷:《论缩短的二行为犯》,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3期。
④陈兴良:《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页。
⑤周光权:《刑法各论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页。
⑥前引⑤,周光权书,第272页。
⑦陈兴良:《目的犯的法理探究》,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同时,他也指出:“从不具有行使目的并不能得出没有伪造货币的故意的结论”。确实,这里周光权博士所说的“欠缺本罪故意”实际上是犯了一个细微的错误,他在不经意中将本罪的目的与故意混为一谈了。
⑧[日]山口厚:《刑法各论》,有斐阁,2003年版,第415页
⑨[日]西田典之:《刑法各论》第2版,弘文堂,2002年版,第319页。
⑩新币替换事件,日本最高法院1947年12月17日(《刑集》第1卷第94页)的判决。在1946年实施的以新货币替换旧货币的时候,因为来不及发行纸币,作为应急措施,政府就给每个国民发了相当于百元金额的验证标签,各人只要在所持有的旧币上贴上这种标签的话,就可以作为新货币进行流通。被告人从不要这种验证标签的人手中获得该标签,超过限额制作新银行券的事件中,法院认为:“伪造货币罪是通过保障货币发行权人的发行权来确保社会对货币的信用的,因此只要制作人没有发行货币的权限,该制作行为就是伪造货币的行为。”但是,这一判决遭到了学界多数学者的批评,认为在此事件中,即便是超过限额、贴附标签的旧银行券,但只要该标签和旧银行券是真实的,就是在作为真正的新银行券在使用,而且在此种场合违法做成的新币与合法做成的新币是无法区别的,因此,这种违法做成的新币也必须有效的通用,并没有侵害公众对新银行券的信用,所以不应该成立伪造货币罪,上述判决是有疑问的。例见[日]平野龙一:《刑法概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版,第256页;前引⑧,山口厚书,第415页;甚至连主张本罪的法益也包括国家的货币发行权这一次要法益的西田典之教授也指出,“确实,将在这种场合,违法做成的新钱无法被认为无效,而且,由于也没有超出本来我国所预定的货币发行量的限度,将其认定为伪造货币罪是不恰当的。”前引⑨,西田典之书,第320页。
(11)参见[日]木村龟二主编:《刑法学词典》,顾肖荣等译,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572-573页;转引自前引⑦,陈兴良文。
(12)[日]木村龟二:《刑法各论》,复刊,有斐阁1957年版,第232页。
(13)前引⑦,陈兴良文。就伪造货币罪而言,赋予其非法定目的犯的地位之后,还存在着一个目的内容的问题。在新刑法之初有观点认为,本罪应有营利或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6页),但是,正如刘艳红博士所批评的那样,“营利”是指谋求利润,“牟利”是指牟取非法利润,而“获取非法利益”实质与“营利”或“牟利”相同。本罪的行为并非一定将伪造、变造的货币转手卖给他人获取经济上的利益,也可能是供本人或者是赠送给亲友使用,不属于“营利”或“牟利”,但这样的行为仍然应该构成犯罪。所以将本罪的目的理解为“营利或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是不妥当的。(刘艳红:《货币犯罪若干问题研究》,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3期。)本文认为,本罪的目的应该表述为“以行使为目的”,因为该犯罪的危害在于伪币的泛滥和流通将严重影响货币的信用,危害交易安全。实际上,我国刑法只要是像日本刑法那样,在第170条法文上加上“以行使为目的”6个字,就可以避免那么多的争论(尽管这些讨论反过来也多少促进了理论发展),真是应该好好的在立法的科学性上思量思量。
(14)前引②,张明楷书,第191页。
(15)法益侵害说对非法定目的犯的甄别主要是通过目的的区分机能(区分罪与非罪或者此罪与彼罪)来实现的。因此,如果某种目的不具有上述区分机能,就不能将其视为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在确定不成文的目的犯时,必须牢记这一点。因为,将不具有区分机能的要素列入构成要件要素,要么导致犯罪的处罚范围不当,要么导致犯罪的相互界限不明。前引③,张明楷文。
(16)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规定了8种金融诈骗罪,但只是就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规定了非法占有目的。于是不少人认为,既然刑法条文没有就其他金融诈骗罪规定非法占有目的,那么,其他金融诈骗罪的成立就不以非法占有目的为要件。但是,“这样的理解是片面的。刑法分则的某些条文之所以明文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或以营利为目的,是为了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而在一些明显需要非法占有的目的,又不至于出现混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场合,刑法分则条文往往并不明文规定非法占有目的。这样的情况几乎出现在各国刑法中。”“刑法虽然实质上要求具备某种构成要件要素,但因为众所周知、广为明了,而有意从文字上省略刘其规定。”前引(14),张明楷书,第233页。
(17)在我国,较早研究目的犯的论文已经承认了非法定目的犯的存在。如陈立教授指出,有些犯罪,刑法分则条文虽然没有规定构成该罪必须具备某种特定犯罪目的,但从司法实践和刑法理论上看,则必须具备某种特定犯罪目的才能构成该犯罪,即所谓不成文的构成要件。对于这类尚未被立法成文化的事实上的目的犯,尤须注意。参见陈立:《略论我国刑法的目的犯》,载《法学杂志》1989年第4期。但是,在我国也有人不承认非法定目的犯的存在,认为目的犯以直接故意犯罪的犯罪目的为内容,以法律明文规定为特征,目的犯的目的必须由立法者在刑法条文中明确规定作为某种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否则,不称其为目的犯。参见段立文:《我国刑法目的犯立法探析》,载《法律科学》1995年第3期。新近的否定非法定目的犯的主张,可参见屈学武:《金融犯罪主观特征解析》,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1期。但新近的论文更多的是承认非法定目的犯的存在,如陈兴良教授认为,尽管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但可以通过限制解释将某些犯罪确认为目的犯,这就是非法定的目的犯。他进一步指出,“法定的目的犯与非法定的目的犯,是目的犯的两种表现形式。两者相比而言,法定的目的犯因为是有法律规定的,因此在目的犯的确认上是较为容易的。而非法定的目的犯,由于法律对于目的犯未作明文规定,因而容易产生理解上的歧义。前引⑦,陈兴良文。实际上可以说,非法定目的犯的存在已经在学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在我国刑法中的盗窃、诈骗、抢夺罪等犯罪中,法律条文并未明确规定行为人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但在刑法学理解释上,却没有争论地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个不可缺少的构成要件。刑事审判也同样持学理解释的观点。
(18)开放的构成要件是由威尔泽尔在与完结的构成要件相对应的意义上提出来的,前者是指在刑罚法规的构成要件规定上只记载了—部分犯罪要素,其他部分需要在适用时由法官来补充;而后者是指在刑罚法规的构成要件规定上,相应无余地表示着所有犯罪要素的情形。在国外,至少在日本,我至今的阅读范围还没有看到有谁将非法定目的犯的目的理解为开放的构成要件。日本学者—般认为开放的构成要件的主要情形是过失犯(中的注意义务)和不真正不作为犯(中的作为义务)。参见[日]大谷实:《刑法总论》,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第三版,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等。
(19)实际上,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日本,开放的构成要件概念都饱受批判。比如,耶赛克和魏根特教授认为,空缺的构成要件理论必须被拒绝,因为如果构成要件被理解为不法类型,它只能被认为是“封闭的”,原因在于它恰恰缺少类型特点。这意味着,构成要件必须毫无例外地包含全部的对某一犯罪类型的不法内容具有共同决定作用的特征,关于违法性的问题只能是消极的,也就是说,在排除合法化事由的意义上提出来。[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305页。大谷实教授指出,在开放的构成要件成为问题的犯罪类型的场合,容易导入法官的任意性判断,损害构成要件的保障机能,因此,应当弄清楚该刑罚法规中所预定的行为的本质要素,这—点,应当从作为指导原理的社会一般观念出发,对构成要件进行补充。[日]大谷实著:《刑法总论》,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内藤谦教授也认为,承认开放的构成要件,就会承认由法官的价值判断来补充构成要件,从罪刑法定主义、刑罚法规的明确性原则来看,是有疑问的。[日]内藤谦:《刑法讲仪(总论)》(上),有斐阁1983年版,第198页。
(20)[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第三版,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注3。
(21)比如陈立教授认为,为免于犯罪认定发生困难,我国刑法对这类不成文的目的犯有将其成文的必要。参见陈立:《略论我国刑法的目的犯》,载《法学杂志》1989年第4期。陈兴良教授也认为,在立法的时候,基于罪刑法定的明确性原则,应对目的犯加以明确规定。在刑法未作规定的情况下,司法解释应对非法定的目的犯作出规定,以便实现非法定的目的犯的法定化。只有这样,才能为正确地认定目的犯提供充分的法律根据。前引⑦,陈兴良文。
标签:陈兴良论文; 货币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法律论文; 刑法理论论文; 构成要件要素论文; 犯罪构成要件论文; 张明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