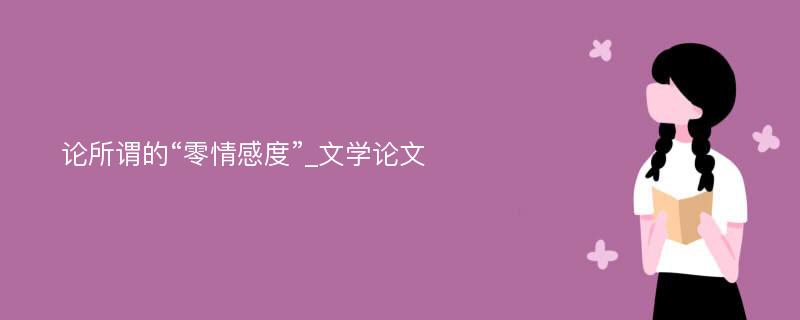
评所谓“情感的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零度论文,情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写实小说”是在复杂的社会文化背上出现的一种平实、特殊而又颇有争议的文学现象。作为创作群体的“新写实小说”作者队伍内部,他们的创作意识和价值取向既存在着共同性也表现出差异性。
可以说,标示和宣扬所谓“情感的零度”是“新写实小说”的一个关键性的理论主张。围绕着所谓“情感的零度”所展开的论争,一定程度上反映出80年代后期中国文艺领域两种完全相反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对立。
一、关于所谓“情感的零度”的论争
有的评论家认为“后现实主义要求逃避作家的主体意象,消解作家主体对作品文本进行干扰,控制的种种可能,以保证生活形态的真正还原,‘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便是后现实主义所遵循的写作原则和采取的写作态度。”(注:王干:“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北京文学》,1989年6期。)这种所谓后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和理论原则,要求文学创作和文学文本所反映和表现出一种绝对客观的“纯态现实”。这实际上消解和否定了创作主体的精神创造性和思想倾向性。
与之相反,有的评论家不同意上述的论点。他们认为“新写实小说与新潮小说都不是非意识形态性的文学现象,新写实小说和新潮小说都是从价值选择的根本点上来完成‘对当下意识形态的消解’”。(注:李万武:“新写实主义的意识形态选择”,《文艺理论与批评》,1992年2期。)“其实,‘零度情感’、‘终止判断’只是这种小说叙述方式上的特点,是一种叙述策略。新写实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性不仅鲜明、而且是强烈得很的。”(注:李万武:“评新写实小说的理论鼓吹”,《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11期。)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的论争的聚焦集中在“新写实小说”究竟有没有作家的主观倾向性和“新写实小说”是不是要消解时下的意识形态。
我认为,为了揭示这场论争的实质,必须澄清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一是“新写实小说”与“先锋派小说”的关系;二是应注意到“新写实小说”本身具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三是应当区分“新写实小说”的创作者的叙事态度和文本中叙述者的叙事态度。这些问题都不是各自孤立的封闭的自我存在,而是互相廛结和彼此融通,从不同方面的关联中这样那样地和所谓的“情感的零度”发生有机的深层的影响。
二、“新写实小说”与“先锋派小说”
众所周知,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青年作家们越来越关注文学的内部规律的研究。“新时期以来文学经历了两次选择,第一次选择是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爆炸,第二次选择是文学自身内部的爆炸。”(注:马相武:“文学潮流与时代选择——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对话”,《文艺争鸣》,1988年4期。)无疑,第二次选择是主张文学“向内转”,即由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如文学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转移到对文学的内部规律,即文学本身的审美属性,特殊规律和内部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先锋派小说”在对传统的反叛中付出了沉重的价值。应当记取这个深刻的经验教训。以马原、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等人为代表的先锋派作家们更加注重对小说叙事方式和话语风格的追求和探讨,从而远离主流的意识形态中心。由于受到相关的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先锋派小说创作的大胆试验打破了以往文学传统中许多被公认的规范和法则,旨在突现对文学意义的消解和文学价值的颠覆。这种新潮小说所体现文学观念和语言实验的叙述方式所昭示的意向指归同正常的传统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和对照。正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这些“先锋小说的离径叛道已经有些娇枉过正了,走到了片面偏狭和自我封闭孤独悲凉的境地。继之而起的新写实小说既一以贯之地承袭了反叛和超越传统的精神,又对其过度的形式实验和语言迷宫趋势作了适当的纠偏”。(注:陈旭光:“新写实小说的终结——兼及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学中的命运”,《文艺评论》,1994年1期。)
针对“先锋派小说”对文学意义的消解和远离主流意识形态中心,“新写实小说”作为对这种小说创作倾向的反拨,又重新返回和拥抱现实世界,关注人的生存方式、生存状态,从与普通老百姓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中,描写和表现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寻求和揭示他们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新写实小说”的许多文本里,表面上看来是叙述故事,仿佛并不在重视故事所赖以发生的一定时代的社会环境和开掘故事本身的蕴涵、意义和价值,然而,隐藏在这些被叙述的故事背后的深层含义却是有目的和有追求的。
针对“先锋派小说”的观念虚构和语言实验上的极端行为,“新写实小说”调整了自己的写作策略。它的观念虚构不再是脱离客观对象和生活现实的具有明显的主观随意性的胡编乱造;它的语言实验平实、淳朴,追求生活化和大众化,同时又富有表现力和嘲讽精神。不再是那种一般读者看不懂的艰深、晦涩和隐秘的语言游戏。
从文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来说,为了反叛和超越传统的主流的意识形态,作家可以采取两种态度:一是采取冷漠的态度,回避和拒斥任何意识形态因素介入文艺作品;二是以干预者的姿态,通过文艺作品中对一定的意识形态因素进行嘲讽、批判和消解。显然,“先锋派小说”的作家们的创作态度大体上可以归属为前者。而“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对待传统的意识形态同时存在着两种态度,从而可以划分出“新写实小说”的两种质态。很多“新写实小说”对人的现实生活的描写采取了第一种态度,因而多半只停留在和踯躅于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的表层,所抱孕的思想内涵十分肤浅,几乎很难觉察到有什么是非评价和理性判断。但是,也有些“新写实小说”都具有程度不同的的思想性、倾向性和现实批判性。
总之,“新写实小说”恢复了“先锋派小说”所忽视的面向生活的写实功能,有的还一定程度上承接和融入了反叛和超越传统的先锋精神。但是,从反叛和超越传统的方法和策略上看,大量的“新写实小说”沿袭了躲避和排拒主流意识形态的先锋精神,而那些具有现实批判性的“新写实小说”对被视为不合理和不合情的生活现实和社会环境则采取了揭露、批判和嘲讽的态度。
三、写实风格与批判意识
正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新写实小说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学现象。从创作实践上看,被一些理论家和评论家划到这一圈子里的作家、作品是如此之多,范围是如此广泛,这些作家和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其实存在很大差别。在我看来,有的甚至还存在着实际上是对立性的差别。”(注:尚文:“关于新写实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1992年4期。)我对上述所论是认同的。“新写实小说”确实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范式和类型。
相当多的“新写实小说”只停留在冷静地描写普通人的平凡的生存状态上。如,池莉的《不谈爱情》和《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刘恒的《教育诗》、范小青的《顾氏传人》、叶兆言的《艳歌》、方方的《白驹》和《桃花灿烂》等作品,都是以表现庸常的“纯态事实”的叙写手法取代了对社会和人生的本质的体悟、揭示和剖析,放弃了对现实生活中的困顿的、消极的、乃至丑恶和腐败的现象的深层的思考和开掘、理性的审视和评判。这势必冲淡和消解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那种震撼人心的深沉的理性自觉、历史意识和时代精神。
然而,有些“新写实小说”由于贴近生活,有主观意识的参与,仍然表现出比较强烈的现实批判性。诸如刘震云的《官人》、《官场》和《新兵连》,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等为代表的一批小说作品,正是通过对普通人极为平凡的日常生活的描写中,隐含着对人的庸常恶劣的生存环境的警示,对改变人的低下的文化心理素质和失衡的价值观念的企盼和对泛用社会政治权力所造成的恶果的愠怒、指控和抨击。
为了说明上述的论点,有必要对方方的中篇小说《风景》(发表于《当代作家》1987年第五5期)作一个简括的个案分析。方方是从中国心腹地区的大都会武汉崛起的女性作家。她置身于市民生活的环境里和氛围中,积累了细微而又深挚的人生体验和审美经验,带着温馨的人文关爱,以敏感的眼光观察和领悟与她具有血缘亲情般的市民阶层的个体的生存状态。她通过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市民的生活困境和心理危机的不动声色的描绘,寄托并流露出对恶劣到几乎要达到“非人境地”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环境的不可遏制的批判情绪,使读者看过这部小说后,从心头涌起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般的隐忍而又强烈的感受。
《风景》描写的是挣扎在城市的贫困而又脏乱的流民杂住区的一对夫妇从解放前直至现在的种种沉浮际遇的生存风景。他们栖息在汉口市江边自己搭起的一间只有13平米的“河南棚子”里,竟生下七男二女。生存空间的极端狭窄、龌龊和恶劣,致使“夫妇打架、父子斗殴、兄妹吵闹”诸如此类的家庭纠纷成为最常见的人伦风景。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都非常穷酸、愚昧和粗野,只能被禁锢在这个令人窒息的“河南棚子”中。作者虽然只是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平直真实地再现了青年们各自生活成长的过程,并描写得十分客观、冷静和含蕴,并没有刻意表达自己的爱憎态度。可是,一旦这种如实的故事展示和话语叙述被读者解析之后,总会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深深地品味到作品中所包含着的的深层意蕴:不是作家没有情感,而是作家的这种情感被强大而又威压的现实生存环境挤迫得不得不藏匿起来。因为面对这种极其恶劣的生存危机和生存困境,一切思想和感情都仿佛变得苍白无力。正如方方自己所表白的:“将新写实主义说成是批判现实主义也行”。(注:方方:“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1年3期。)这句话的寓意无疑是深刻而带有反讽意味的。
当大多数“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将小说的主人公放在现实的平凡的生活流中去表现时,却有一位新写实小说作家刘震云独树一帜,他集中聚焦,瞄准了“官员”、“官场”和与“官员”、“官场”相关联的创作天地,并用他那不动声色却又力透纸背的笔对泛用和扭曲社会政治权力的现象进行了无言的批判。有的评论家带有几分夸张的说,刘震云窥视和穿透了权力这个隐密的部位,笔锋如刀,剖析下去,“好像庖丁解牛,恢恢手游刃有余。那些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一旦投入权势方程式,顿时异常简单,简单的荒诞不经,简单得令我们瞠目结舌,不敢接受。一个单位是一张权势之网,一人地区、一个国家、一部历史,一切人生的设定,都无非是权势之手导演的滑稽透顶的戏剧,既不复杂,也无神秘性可言,人是权势的奴隶。”(注:邰元宝:“刘震云:当代小说中的讽刺精神到底能坚持多久”,《作家》,1994年10期。)从刘震云的一系列的诸如《官人》、《官场》、《新兵连》《单位》等小说所营造的世界中,人们不难发现,小说人物被置放在一种与特定的“官员”和“官场”具有各式各样的错综复杂的纷纷扰扰的关系和环境中,表现他们如何艰难挣扎和怎样曲意奉迎以至攀附升迁。《新兵连》主要写了一群新兵,即穿上军装的农民在接受训练过中发生的各种琐事,表现了特殊的有悖常规常理的军营生活对普通人的性格的扭曲和裂变,带有一定的悲剧和喜剧的色彩。这篇小说描写了“文革”期间平凡又惯常的新兵生活,通过展示质朴又落后的农民与反常的庸俗的政治和军事的体制的矛盾和冲突,揭示了人的异化与人性的畸变和失落。这些小说体现了作家对创作取材的特殊的切入点,赋予作品以尖锐而又深刻的思想锋芒,带有强烈的审视和批判现实的自觉意识,集中地表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某些制度和机制的病态、显示了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勇气和现实主义精神。
总之,面对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某些弊端,这些具有不同程度的现实批判性的“新写实小说”,不象“先锋派小说”那样采取回避和拒绝的策略和态度,而敢于对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某些弊端进行嘲讽、揭露和批判。不言而喻,对这些“新写实小说”的作者来说,所谓的“情感的零度”的说法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些小说的作者的内心和文本的深层存在着一定的情感和思想的倾向性。表面上看,作者和作品好像并来没有明显地流露出情感和思想的倾向性,这实质上只不过是一种文本叙述的策略罢了。
四、两种不同的叙事态度
小说的叙事态度实际上是作家观照生活的态度通过叙事过程中的形象体现。创作主体的叙事态度引发着、决定着对文本叙述方式和叙述策略的选择。作为叙事文学的叙述模式发展至今已经逐渐形成了三种类型:一是叙述者大于人物的后视觉,即是现实主义的全知全能的视觉;二是叙述者等于人物的同视觉;三是叙述者小于人物的外视觉,即用局外人的观察点来消灭叙述者的方式。(注:参看丁帆、徐兆准:“新写实主义小说对西方美学观念和方法的借鉴”,《文艺研究》,1993年2期。)“新写实小说”采取的多半是一种局外人的叙述方式,表现为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叙述者总是以一种超然于他笔下的人物和事件的态度来写作。以客观化的叙事态度作为情感介入的准则,叙事手段追求还原性的呈现。这种还原性的呈现要求作家从观念回到现实,注重观察而弱化判断,从有选择的描写生活的局部返归到勾勒生活的本真原态的全景,透过主体的感受和体验,承载起对生活的所谓“原生态”、“原汁原味”和“纯然事实”的展览和显示。这种被某些评论家概括为“冷面叙述”、“消解深度”和“中止判断”的叙述方式和叙述策略势必使“新写实小说”的作家将主体情绪冷却到零点,使叙述客体和叙述过程尽可能地避免主体意图的介入和主观倾向的干扰,以便逼近“原生态”的“纯粹”和“本真”。
相当部分的“新写实小说”作品中,文本的叙述者不加任何评议,不想对阅读作出明确的领启和引导,始终保持局外人的姿态。即使有的小说出现作为叙述人的“我”的形象,也只不过是一个冷漠的参与者,既不是全知全能,更不去指点江山,评判是非。这正是许多评论家之所以认为“‘新写实小说”的文本叙述进入“情感的零度”状态的缘由。
这里必须应当指出的是,有些“新写实小说”的评论家们所认定的“情感的零度”指的只是文本中叙述者的“情感的零度”,而不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情感的零度”。因此,探讨所谓“情感的零度”的时候,应当将作家的“情感的零度”和文本中叙述者的“情感的零度”区分开来。
综上所述,“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对待意识形态的两种不同的态度相应地决定了他们的文本叙述也必然具有两种不同的叙事态度。一类是作家排拒意识形态介入他们的作品,从而使他们在文本表达方式上采取回避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一类是作家想通过文本叙述对现实生活中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而心然有主观情感的参与。不管是回避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还是批判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作品文本中的叙述者的态度都是以所谓“冷面叙述”为主,不掺杂人物形象对生活现实和生活事件的强烈的主体情感评价,以达到回避或批判意识形态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