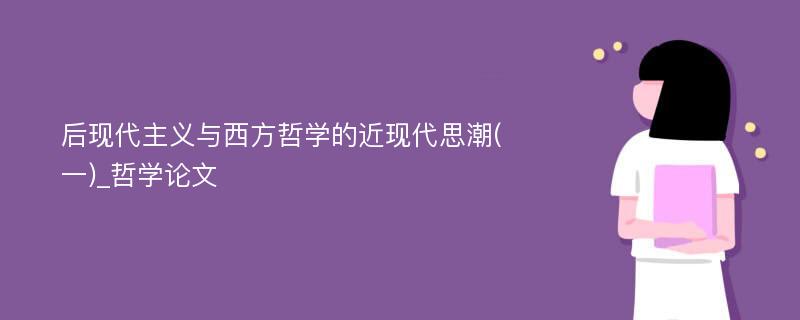
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现当代论文,走向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百年学术
最近几年来,关于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哲学)的问题成了我国哲学和文化研究中热点话题之一。但后现代主义是一个缺乏确定性的概念。西方学者对其所指很不相同,对其评价更大相殊异。有的哲学家认为它改变了哲学发展的方向,甚至开辟了哲学的新时代;而另一些哲学家则往往对其投以鄙薄的眼光,甚至称某些后现代主义议论是“胡说八道”。〔1〕中国学者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和评价也是互不相同。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这种哲学思潮呢?它的出现是否西方哲学发展中一种方向性转换(转向、转型)?是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本性超越?能否体现西方哲学的当代走向?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可能产生哪些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从不同层面和视角加以研究。本文从西方哲学现当代走向的角度说些想法。
一、后现代主义的多重含义及当代后现代主义者的基本理论倾向
为了讨论上述问题,先要对“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所指加以限定。
“后现代主义”原仅指称一种以背离和批判现代和古典设计风格为特征的建筑学倾向,后来被移用于指称文学、艺术、美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中具有类似倾向的思潮。在欧洲,由于结构主义哲学在某些方面与建筑设计、文艺创作和人类文化的研究有一定联系,而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福柯、巴尔特等所谓后结构主义者又都企图由批判早期结构主义的一些基本观念出发来消解和否定整个传统西方体系哲学(首先是“现代”哲学)的基本观念,因而后结构主义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典型形式。在美国、奎因、罗蒂等从分析哲学中分化出来的所谓新实用主义哲学家则企图通过重新构建实用主义(特别是强调杜威等人的工具主义)来批判和超越近现代西方的哲学传统,他们的哲学也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形态。一般说来,当代后现代主义哲学大多是指60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现的具有反西方近现代体系哲学倾向的思潮。
然而,在理论上具有上述反传统倾向的哲学家在现代西方的各个哲学流派中都能找到,而有些后现代主义者(包括法国后现代主义的干将利奥塔等人)很难归于某一确定的哲学流派。不少西方学者由此对后现代主义作了较广义的解释,认为凡是具有上述倾向的都可列入其内。当代美国活跃的后现代主义者之一格里芬(D.R.Griffin)就说:“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这一词汇在使用时可以从不同方面找到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它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任何共同的教条——即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2〕这样一来, 不同时期具有这种理论倾向的哲学家都可归属后现代主义。除上面提到的外,其中比较重要的还有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利兹、哈贝马斯、弗洛伊德、马尔库塞、阿多尔诺、维特根斯坦、奥斯汀、戴维森、波佩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贝尔、伯恩斯坦(R.J.Bernstein)等人, 尼采、狄尔泰等一些19世纪思想家则被当作后现代哲学的重要先驱。在格里芬编辑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1993)一书中,被当作这样的奠基者的有老一代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斯、詹姆士和杜威,生命哲学家柏格森、过程哲学家怀特海和哈茨霍恩。一句话,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最有影响的反传统的哲学家大都被当作后现代主义者。有的人甚至把后现代主义追索到帕斯卡尔、维柯和卢梭。由于这些哲学家分属不同哲学流派,其理论重点和目标也互有差异,后现代哲学自然就成了一个范围广泛的概念。
按“后现代”(postmodern)一词的西文语义,把后现代主义由60年代以来的特定思潮扩展为本世纪上半期、甚至19世纪中期以来的整个西方哲学的最主要思潮不无根据。因为“后现代”自然是“现代”之后之意,而在英语等西文中,“现代”(modern)通常是泛指西方“现代化”(modernization)运动开始以来(以17世纪产业革命为标志, 甚至可上推至文艺复兴)的整个资本主义时代。中文通常译为“近代”,modern philosophy相应译为近代哲学,因而“后现代”即为“后近代”。既然从19世纪中期、特别是本世纪初起西方哲学中就已先后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批判和否定近代哲学的思潮,自然可以说从那时起就出现了后现代主义。
只有注意到后现代主义一词的多义性,我们才能在它的某种确定含义下揭示它在西方哲学中所处的地位及其所实现的转向的性质。
如果它被用来泛指19世纪中期以来整个西方以反传统哲学为特征的哲学,那它所实现的转向从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在这方面当代后现代主义只能算是其中一部分)。在如何看待西方现代哲学取代近代哲学的性质和意义上有不少问题需要重新研究,我个人认为,这种取代是哲学思维方式上的一次根本的变更,标志着西方哲学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3〕
如果把它限定为本世纪60年代以来的当代后现代哲学,认为它实现了新的转向,那意味着把它当作超越现代西方哲学的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代表了西方哲学发展中一个最新阶段。由于它是后于具有“后现代”(“后近代”)意义的现代西方哲学,有些西方哲学家认为应当称它为“后后现代主义”(post-postmodernism)。〔4〕
当德里达、罗蒂、利奥塔等当代后现代主义者强调其哲学对现代哲学的转向或者说超越时,他们的基本理论倾向正是属于这种后后现代主义。他们在否定现代哲学时既指向19世纪中期以前的“近代”,又指向以后的“现代”。因此考察他们是否实现了西方哲学发展的新转向以及这种转向是否和怎样体现当代哲学的走向,既要揭示他们是否以及怎样超越笛卡儿以来的西方“近代”哲学,更要考察他们是否以及怎样超越19世纪中期、特别是尼采以来的西方“现代”哲学。这就需要从与现代西方哲学相比较的角度对其一些主要理论加以剖析。
当代主要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理论虽各有特色,但存在着重要的共同之处,正是后者把他们作为后现代主义者联系起来。这些共同之处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几乎都有反对(否定、超越)传统形而上学、体系哲学、心物二元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主体主义和人类中心论(人道主义)、一元论和决定论(唯一性和确定性,简单性和绝对性)的理论倾向。估价当代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哲学转向上的意义,最重要的就是考察他们的这些否定性理论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关系。
二、后现代主义的否定性理论及其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同一性
在后现代主义者的诸种否定性理论中,对基础主义的批判具有决定性意义。有的西方哲学家甚至认为“后现代主义可以说就是反基础主义”。〔5〕而罗蒂对基础主义所作的批判有较大代表性。
基础主义泛指一切认为人类知识和文化都必有某种可靠的理论基础(或所谓“阿基米德点”)的学说。这种基础由一些不证自明、具有终极真理意义的观念或概念(罗蒂称为“特许表象”)构成。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发现这个基础。从认识和方法论上说基础主义往往表现为将现象与实在(本质)、外在与内在分裂和对立起来的本质主义。17世纪以来,由于主客、心物之间的分离和对立以及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屏障的问题被突出地提了出来,基础主义便以本质主义的形式在哲学中占了支配地位。
罗蒂把几乎全部传统哲学都归属于基础主义,认为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在何种形态下以什么(例如以一般概念或经验)为基础的区别。在各形态的传统哲学中,他认为柏拉图、笛卡儿和康德哲学最具代表性,集中地对之加以批判。他把它们都看作以心物、主客等分离和对立为前提的视觉中心论(镜像论)。柏拉图关于真理和知识的学说把哲学看作是关于表象的一般理论。掌握表象意味着人的意识(人心)摹写作为对象的外物,犹如人眼的看,这就是把人心当作照耀外物的一面镜子。笛卡儿把“我思”作为出发点意味着认识是从人的内心发生的,人心成了一面映照外在世界的内在镜子。康德企图消解主客等二元对立所导致的近代哲学中的各种对立(如经验论和唯理论、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目的仍然是由人心为科学、艺术、道德和宗教等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在科学和认知领域为自然立法,在道德领域颁布绝对命令。他的三大批判实质上就是检查、修理和照亮这些领域的镜子。
总之,按照罗蒂的解释,只要是把人心(主体)与其对象(客体)区分和对立起来,把哲学的任务看作由心灵去掌握对象、并企图由此而为人们寻找知识和行为的可靠准则,那就是把人心当作自然之镜,就是遵循某种形式的基础主义,而传统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无论是其存在论或认识论,几乎都以把人当作自然之镜为前提,从而也都是某种形式的基础主义。因此,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在罗蒂那里就表现为对作为自然之镜的人心的消解和摧毁。他在其代表作《哲学与自然之镜》(1979)〈导论〉中明确提出:“本书的目的在于摧毁读者对‘心’的信任,即把心当作某种人们应对其具有‘哲学’观的东西这些信念;摧毁读者对‘知识’的信任,即把知识当作是某种应当具有一种‘理论’和具有‘基础’的东西这种信念,摧毁读者对康德以来人们所设想的‘哲学’的信任。”〔6〕在稍后出版的《实用主义的后果》(1982)中他更把上述批判扩大到整个柏拉图主义传统。
罗蒂在批判基础主义的名目下对传统哲学的否定体现了当代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共同立场。尽管他们批判的名目不同,批判的方法和方面也互有差异。例如德里达致力于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言语中心主义”的“解构”(集中地表现为对结构主义语言模式的批判)的批判;福柯则致力于对传统“认识型”(episteme)的批判。利奥塔热衷于对叙事(narrative)的探讨,特别是对所谓元叙事的批判。 就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具体研究来说,这些差异是不应忽视的。但他们的批判与罗蒂接近。罗蒂也承认自己的观点与德里达、福柯、伽达默尔等人很是类似,并认为“德里达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不过是……反本质主义的一个特例”〔7〕。 就揭示当代后现代主义者对西方传统和现代哲学的超越的性质来说,最值得注意的正是他们的这种共同倾向。
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大背景来考察,由反基础主义所体现的当代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这种共同倾向在哲学思维的基本方式上与19世纪中期以来许多反传统的西方哲学家并无实质性区别。这是因为:
第一,他们在各种新名目下所批判的仍然是这些哲学家所一再批判过的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二元论等)思维方式,只是有时对这些哲学家(特别是尼采、海德格尔等欧陆哲学家及杜威等实用主义哲学家)的批判作了某些局部的变换或者运用于某种具体领域。罗蒂就认为“德里达的大多数工作继续了一条始于尼采而一直延伸到海德格尔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的特征就是越来越激进地拒斥柏拉图主义”〔8〕而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则“是把尼采和海德格尔所共有的反本质主义运用到句子和信念的特例上去。”〔9〕至于他自己的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则正是詹姆士和杜威等人表示过的立场。因为他们的实用主义“只是运用于象‘真理’、‘知识’、‘语言’、‘道德’这样一些观念和类似的思考对象的反本质主义。”〔10〕利奥塔对语言的批判大体上就是模仿维特根斯坦。
第二,他们的新哲学理论在基本方向上也未越出这些哲学家的大范围。
罗蒂倡导的所谓“启迪哲学”、“小写的哲学”、“后哲学文化”被认为是当代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范例。然而他本人也一再指出它们源于杜威、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等人的理论,甚至是现代西方两大哲学传统(思潮)汇流的结果。从实证主义到分析哲学的传统“在以批评柏拉图主义开始而以批评(大写的)哲学本身结束这一点上与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的传统十分相似。”〔11〕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从直接的意义上说是对他以前的全部哲学的“消解”,但他并未因此而提出一种超越传统哲学范围的新哲学。他的“消解”主要只是对原有哲学文本由单义阐释转向多义阐释,而这并未越出原有哲学框架。正因为如此,他对体现了近现代两种主要哲学倾向的黑格尔和尼采这两位哲学家都既不全盘肯定也未全盘否定,而游移于这对立两极之间。利奥塔明确地把他关于语言和知识的合法性的理论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联系起来。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其他否定性理论与上述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有着内在联系,甚至可以说是其表现形式或必然后果。它们也未越出西方现代哲学的范围。
例如,对近代哲学中主体性理论和人类中心论的批判是他们对传统哲学批判的重要方面之一。他们大都认为,以作为主体的人取代神的地位、以主体性取代神性是“现代”哲学最重要的特征。然而,不管这种特征曾起过多么重大的作用,要超越“现代”则必须超越主体性。德里达、福柯等人都致力于对主体的消解。德里达之否定主体在语言中的直接在场作用和福柯之提出“人之死”概念就是否定主体性的集中表现。这种否定正是源于对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元分立、实体本体论的否定。因为主体性原则和人类中心论正是以这种分立和与之相联的主体实体化为前提的。然而对主体性原则和人类中心论的批判是尼采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中就已存在的。例如尼采认为主体无非是一种自我欺骗的产物。他所倡导的主人道德就是对维护这种主体性的奴隶道德的超越。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把主体和自我当作为语言的语法的一种特殊功能,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通过揭示自我意识之下的无意识把自我置于从属地位。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大都还以非理性主义反对理性主义(包括以诗性哲学取代理性哲学)、以非确定性(相对主义、无中心论、无整体性)否定确定性和整体性、以多元论和非决定论反对一元论和决定论。这些也都无不出于对基础和本质的否定。而它们也都早已为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以不同的形式提出过。我们在此就不一一评述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