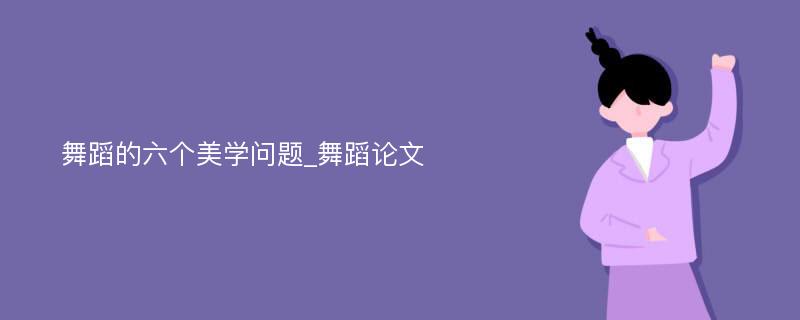
舞蹈审美六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舞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702 文章编号:1008-2018(2004)03-0010-05 文献标识码:A
一、象外之象
“象外之象”是唐·司空图的美学观点,是说“象外之象”和“景外之景”都是只可 意会不可言传,同“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相类似,在艺术欣赏之后,留有余味。
“象外之象”的前一“象”是实象、显象。是可以目睹的,是物质的,是有限的,名 为“形象”;后一“象”是虚象、隐象、是想象中的,非物质的,是无限的,名为“意 象”。二者可以互相转化,“意象”可以外化为“形象”,“形象”也可内化为“意象 ”。
“意象”一词,正式出现于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 ,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
大意是:使智慧的心灵,寻觅声腔韵律而构句谋篇,让独到的才思,根据心中的意象 而命笔成文。
舞蹈艺术本质上是表现情感,所谓“歌以叙志,舞以宣情”(阮籍《阮籍集·乐论》) 。舞蹈的创造过程,就是捕捉情感、凝聚情感、外化情感的过程。情有喜、怒、哀、乐 ,但人之情不是空穴来风,总是有感而发,故称“情感”;因事而发名“情由”;因理 而发是为“情理”。清代诗人叶燮把“情”、“理”、“事”视为穷尽万有之变的三个 美学范畴。他说:“夫情必依乎理,情得然后理真”(《原诗》)。
这一说,指点出一条明路,欲求“象外之象”除重视“情”字外,还要加上一个“理 ”字。因此,要求艺术家创作作品,必须考虑前、后两个方面,那就是表面的显象和背 后的隐象。显象要大事渲染,以情胜,情要“状溢目前”,使人击节叹赏;隐象要深层 埋藏,以理性,理要“意在词外”,让人细细品味。这就是情中含理,理中含情;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一露一藏,一显一隐,即得“象外之象”。
今举—抗日战争时期的歌曲为例:《二月里来》塞克词,冼星海曲:
“二月里来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指望着今年收成好,多捐些五谷充军粮。二月 里来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种瓜的得瓜,种豆的得豆,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 ”
是谁在中国人民心中种下仇恨?是谁侵占中国的神圣领土?是谁屠杀了中国千百万人民? 歌中“不著一字”不用明言,尽人皆知。
还有抗战时期小提琴家马思聪创作的《绥远组曲》中有一段《思乡曲》,戴爱莲听后 有感,编成了舞蹈。在重庆上演时,马思聪亲自操琴伴奏,戴爱莲独舞,表演一个绥远 的农村妇女。日寇的炮火毁了她的家园,占了她的家乡,她只得流亡他乡到处飘荡,一 切幸福美好的生活都成为回忆,成为泡影,只留下无限的伤心和长流的泪水。泪水湿透 了长长的手帕,手帕舞出了无尽的忧愁,她最后的身影停留在一个遥望故乡的舞姿上, 如同一座雕塑投影在天幕之上。这时,那婉转美妙的琴声渐渐远去,只剩下细语般的微 音缭绕在耳旁。大幕缓缓落下,但意外的是台下一片寂静,只听见有唏嘘啜泣声,良久 ,才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马思聪的《思乡曲》乡音抑扬,动人心弦;戴爱莲的舞蹈真情贯穿,感人泪下,把观 众引入了深沉的遐想家乡在哪里?何处是家乡?中国遍地烽火燃起,大半个中国在日寇铁 蹄下呻吟!“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
一舞《思乡曲》,唤起了人们爱国爱家的深情,唤起了人们誓死捍卫祖国的壮志,这 就是艺术作品感人的力量。
成功的艺术作品,必然具备两个“象”,以“明言”表现前一“象”;以“隐喻”暗 示后一“象”。这二“象”还须是“情真意切”、“情理交至”,这样才能够以个性表 现共性,以偶然反映必然,以有限包涵无限,以顷刻变为永恒,这就是“象外之象”的 真谛。
二、形神相依
中国的艺术如诗词、音乐、绘画、舞蹈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自己的创作规律,“形 神相依”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形”与“神”的关系,我国古代很早就有所注意了,《淮南子·说山训》讲:“画 西施之画,美而不可说(通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
大意是:画出了西施的面貌,虽然美但不引人喜欢;突出了战国猛士孟贲的大眼睛, 但不能让人害怕,这是没有把主宰“形”的“神”画出来。
所以说,任何艺术形象,如果只有其“形”而无其“神”,是难以动人的。
从哲学本体论的层次上说,“形神相依”是一切事物和生命存在的根本规律。艺术的 审美也是一样,因为“形”与“神”是构成艺术作品及其审美价值的两种基本要素。
从历史上看“形”、“神”关系的发展有三种不同的倾向:
(一)文贵“形似”。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载:“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 ,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是说:那时的文风以形似为贵,对山川草木进行细 致的观察和描写。
(二)主张“神似”。宋代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 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认为只重“形似”是和儿童的见识差不多的。
(三)“形神并重”。明·李贽《诗画》云:“画不徒写形,正要形神在,诗不在画外 ,正写画中态。”这是一种“形神兼备”的主张,对后世起了积极的影响。
作为构成艺术作品及其审美价值的两个基本要素是“形”与“神”。“神”不能无“ 形”,“形”不能失“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依为命。如戏曲舞蹈非常讲究形 式美,无论是手势、步法、身段、套路,十分注意眼神的配合,所谓“手眼身法步”, 在表演上特别讲究“精气神”三个字。“精”指的是动作不能拖泥带水,要精巧熟练, 精神抖擞;“气”要求剧中人物生气勃勃,活灵活现,而不是死气沉沉;“神”最为重 要,要在千变万化的形象中,突出“神”字,“神采飞扬”是艺术审美的最高境界。
《淮南子·原道训》说:“形、神、气、志,各居其宜,以随天地之所为。夫形者, 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
大意是:形、神、气、志都是按照自然规律,各居其所。“形”是生命的形态;“气 ”是生命的气息;“神”是生命的精神,其中一个错了位,其余三个都会受到伤害。
所以说一个艺术品的形式和内容所包含的形、神、气、志绝对不能错了位,特别是“ 形”字。丧失了民族的本真,丧失了纯洁,丧失了民族形式,也就丧失了民族精神。
目前,中央电视台“魅力12”专访组,访问了阿诗玛的故乡,一个撒尼支彝族的村落 ,找到了20位名叫阿诗玛的妇女,最小的三岁,最大的60岁,她们齐唱了一首无伴奏的 民歌,声音非常优美,曲调的跳跃非常奇特。20人不约而同,唱得非常自然,像是从心 里流淌出来的清泉。接下来演了一场百看不厌的“阿细跳月”,摇摆的身形,俏丽的蹬 脚,灵巧的旋转,动听的音乐,让人心醉神迷。彝族“阿诗玛”名字的含义是什么?回 答是“金子般的姑娘”,彝族的民歌也该称为“金子般的歌”,彝族的舞蹈也该称为“ 金子般的舞”,这些歌舞有中华民族的真魂、真形、真神。它光彩夺目,魅力四射,世 界无双,真正称得上具有高级审美品位的艺术。
最后,奉劝一句喜欢搬弄形式的先生们,套用外来形式千万小心,切忌不伦不类,驴 唇马嘴,使得“形”、“神”难以安宁。
三、心物交融
“心物交融”是一种艺术审美的境界。“心”是主体(我),“物”是客体(对象),主 、客体交融合——构成全新的关系,是艺术生命的深度显示。
中国古代的艺术创造,就是通过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相互 交融而达到艺术的自由呈现。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所说:“神与象通,情变所 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大意是:神思是借助于形象来表达并孕育出了情景的变化 ,万物显示美貌等待着追求,我以心中的理想对它呼应。
艺术创作是艺术家全身地投入对象之中的心灵活动,通过体验去感受生命、思考人生 ,因而在艺术创作中有“心物交融”的“物化”、“竹化”、“迹化”之说。
“心物交融”的“物化”说,最早见于《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 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其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 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大意是:以前庄周梦见自己变成蝴蝶,翩翩而飞的一只蝴蝶,悠游自在,根本不知道 自己原来是庄周。忽然醒过来,自己分明是庄周。不知道是庄周做梦化为蝴蝶呢?还是 蝴蝶做梦化为庄周呢?庄周蝴蝶必定是有分别的,这种转变就叫做“物化”。
“物化”这一美学概念,就是指“物我合一”的审美无差别境界。庄周已达到难以分 辨自己是蝴蝶还是庄周“物我两忘”的境界。
“心物交融”的“竹化”说,见于苏轼《书晁补之所藏文与可画竹三首》(文与可姓文 ,名与可,是位画竹名家):“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 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
苏轼说,文与可画竹的时候,画家已到了忘我的境界,全身心地进入对象之中,与竹 合为一体。这是一种艺术体验的精神超越,艺术家达到了这种超越,意味着进入了最高 的审美体验层次,因而能够创作出清新出尘、无穷变化的艺术作品。
“心物交融”的“迹化”说,见于清·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山川使予代山川 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于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 也。”
“搜尽奇峰打草稿”是画家对山川之美的寻觅,山川景物(对象)与画家(主体)之间的 物我感应,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使石涛觉得我就是山川,山川就是我:我的作 品是山川与我神遇的产物。可以说,惟有这种“心”与“物”的神遇,才能进入艺术之 门。
这种心物的神遇,“心物交融”的审美无差别境界,也表现在现代的舞蹈中,如:杨 丽萍的《雀之灵》,巴图的《鹰》,《追鱼》中的小鱼,《担鲜藕》中的鲜藕,戴爱莲 的《荷花舞》等,都是这一类别中的精彩作品。
以《荷花舞》为例,一群少女扮演成一朵朵荷花,这无疑是一种浪漫而又美丽的幻想 。怎样才能像荷花呢?少女们穿上长裙,裙的下沿连着一个荷叶盘,遮住了荷花女的双 足,亭亭玉立在荷叶之上,在众多的红荷花中,最突出的是白荷花(领舞者),那高耸的 发髻,风摆的穗带,洁白的身形,飘拂的轻纱,恰当贴切地呈现出“出污泥而不染”的 高洁品格。荷花女走着轻盈的碎步,像是漂浮在微风中的荷花,把人带入了一个梦幻的 境界。舞中既是荷花,又是少女;既是人,又是花;是花是人,是人是花,难以分辨, 可以说是一个超凡绝世的生命形象。她是人间的,又不是人间的;她是天成的,又不是 天成的。她有青春、靓丽、光艳的少女之美,又有洁白无瑕,一尘不染的荷花之丽。这 个舞中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绿水、红花,可以听到鸟语,闻到荷香,这里是一片宁静 ,一片生机,一片乐曲,一片阳光。
荷花之舞,是艺术家独特感知的创造性重构,是通过“心物交融”进入了物我合一的 审美无差别境界,也就是最高的艺术境界。
四、物一无文
《国语》:“物一无文。”是说:单一的物没有文采。《易·系传》:“物相杂故曰 文。”两物相杂错就有了文采。譬如:一片黑色,没有文采。如果在黑色上杂以白色, 文采会立刻显现;一片绿色中点缀一点红色,“万绿丛中一点红”,会非常醒目。
人物性格的艺术创造是同一道理,具有一种性格特征的人物,单调乏味,属于“扁的 性格”;两种(或多种)性格特征交错的人物,丰满立体,属于“圆的性格”,这样的性 格人物才能反映出生活的深度,才有较高的审美情趣。
《红楼梦》这部伟大的著作,曹雪芹写出了四百多有名字的人物,能看出性格的有百 余,其中有鲜明性格特征,属于“圆的性格”的有二十余人,最为突出的不过几人。脂 砚斋最了解曹雪芹,他对《红楼梦》的主角贾宝玉做了如下的评说:
“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庸俗平(□),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 情痴情种……”贾宝玉表现出的“至呆”和“痴妄”,造就了一个多种性格特征叠合的 奇妙统一体,使读者为之倾倒。
鲁迅赞扬《红楼梦》中的人物,在塑造方面是“善恶并举”。如王熙凤,场面上是英 才,内心里藏鬼诈,对上善逢迎,对下施小惠,当面是笑脸,背面藏钢刀。外表靓丽, 内心粗俗,外表跋扈,内心惶惑,明处大度,暗下算计,表现出性格特征的丰富性、立 体性,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舞蹈艺术怎样创造人物性格?舞蹈形式不同于长篇小说,不同于电视连续剧,舞剧长度 不过两小时,舞蹈小品只有几分钟,时空所限,不可能塑造出多种“物一无文”的规律 ,要在创意构思时代找到“一”与“杂”结合,找到人物心灵、思想、情感、性格方面 “一”与“不一”的对立统一。试举一舞蹈为例:
台湾舞蹈家、哲学博士刘凤学创作的大型舞蹈《布兰诗歌》1993年曾来北京演出,受 到热烈的欢迎。这个舞蹈取材于德国现代作曲家卡尔·沃夫的清唱剧,该剧的歌词系13 至14世纪时布兰地区圣本笃修道院的修士们所作。诗歌的主要内容反映了当时修士们内 心“灵与肉”的思想矛盾。舞蹈分为四段:“序曲”、“春”、“酒店”、“爱之宫殿 ”。基本上是A、B、A形式,即修道院——春、酒店、爱——又回到修道院。
幕启,一所灰色的、肃穆的圣本笃修道院中,一队穿着同样灰色长袍道帽的修上,他 们的面色庄严,行动静穆,他们是虔诚、坚贞的修士,他们是洗心净虑的圣徒,令人肃 然起敬。
但是,这群男女修士却尘缘未断,在他们的心灵中唱出了:
“啊,命运,你像月亮,变幻无常……黑发丛丛,转眼就白发苍苍。”“阳光普照, 一片晴朗,所有烦恼,一扫而光。”我们服从爱神的命令,享受甜蜜的时光。”
歌声像春风吹醒了大地,如春雨滋润了花朵,男女修士们抛掉了道帽,脱去了道袍, 冲开了守贞守规的堤坝,奔向爱的花丛。
在狂欢之后,好像是一场春梦醒来,修士们又穿起了灰色的长袍、道帽,道貌岸然地 回到圣本笃修道院中,似乎一切如旧。只是那缭绕的歌声未停:“啊,命运,你像月 亮,变幻无常……不仁的命运,轮转不停,……请拨奏琴弦,请与我一同悲歌!”
《布兰诗歌》中的男女修士,在舞蹈中展现了两种面目、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的 生命形象,他们既有守贞规的圣徒,又是纵情于酒色的凡夫,双重性格、双重人格的交 错叠合,矛盾而又统一;是“一”与“杂”的结合。这样的人物既有它的真实性,又存 在令人难解的惶惑。
这个舞蹈隐喻着“道与魔”、“灵与肉”、“理与情”的对立矛盾,这些人物性格行 为中的真和伪、美与丑、善和恶,谁是谁非,见仁见智,耐人寻味。这正是“物相杂故 曰文”得来的性格二重组合的奇异光彩。
五、反正相从
对于怎样认识中国民族传统舞蹈的审美特征,探索这些特征在形体上的运动规律,无 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辨别和摆脱那些游离于民族舞蹈特性之外的 鱼目混珠的东西,以保持中国传统舞蹈的特色更加艳丽。
《老子·四十章》有句话:“反者,道之动。”大意是:向着相反方向的运动,是合 乎“道”(法则)的运动的。
譬如使用斧子,举起斧子是向着相反方向的运动,劈下去是向着正方向运动。而前者 就是“反者”,它是运动的基点。
“反者,道之动”,表明老子认识到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有“正向”必有“ 反向”;“反向”会变为“正向”,“正向”也会变为“反向”,相互转化。所以“反 者”(反向运动)是事物运动变化的重要一方。
舞蹈是以人体动作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段的,舞蹈的生命力在于运动的过程、运动的路 线相轨迹,可说是千变万化,但从总体来看,“开”与“合”、“正”与“反”都是其 中的重要规律,如:“太极门”武术中,就有“开合太极”,以动作的开合为契入点阐 明太极的奥义,舞蹈艺术同样也可以以“正”与“反”为契入点进行一番探索。
中国舞蹈有悠久的传统,而且独具特色,但是怎样揭示这种特色的谜团呢?老子的“反 者,道之动”这一辩证法则带来了神奇的启示。
中国传统舞蹈动作,习惯于从“反”到“正”,以“反正相从”的动作规律,形成一 种独特的美的动态,在世界舞蹈之林中可称一绝。这种“反正相从”的动态美姿,早在 先秦已经出现在文物图像中,在东汉傅毅的《舞赋》中也有生动的描写,如:“其如兴 也,若俯若仰,若来若往,雍容惆怅,不可为象。其少进也,若翔若行,若竦若倾,兀 动赴度,指顾应声。”其中的:像是俯身,又像是仰望,像是来,又像是往……像是飞 翔,又像是步行;像是竦立,又像是斜倾……这些舞蹈基本上都是“反”与“正”动作 的组合形象,织成了一幅美不胜收的舞蹈动态画像,这样以“反正相从”审美规律的舞 蹈,仅从东汉《舞赋》算起,至今就有1900年的历史,可知以动作前的“反动作”进入 “正动作”创造美感形象的法则,并将其巧妙地运用到舞蹈艺术中,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它不但至今未衰,而且发扬光大,形成中华民族传统舞蹈的独特风格。到现在,传统 舞蹈流行的口诀中仍讲求:“欲左先右,欲前先后,欲上先下,欲放先收,欲开先合, 欲正先斜,欲直先曲,欲抑先扬;还有欲快先慢,欲短先长,欲动先静,欲柔先刚。” 等等。都是“正”与“反”、“反”与“正”、“反正相从”的动态形象,这些依然活 现在今天的舞台上。
在传统舞蹈的基本功中,演员必须熟练地掌握“动作前的反动作”,做到准确无误, 才能使整个动作完美而富于表现力。“起反儿”可能即由此而来,“反儿”即“反者” 的俗称,“反者”、“反儿”这个既是生活的、艺术的,又包含着“动”的哲理的名称 ,却淹没于历史岁月之中了,而被“范儿”、“饭儿”、“法儿”所替代。
“反正相从”的舞蹈韵律尚有许多,从戏曲舞蹈到武术动作,从民间舞蹈到古典舞蹈 ,这一特色十分突出,如现在的传统古典舞身法的训练中,就特别讲究“反正相从”的 连接规律,如“逢沉必提”(躯干的上、下动作),“逢冲必靠”(后胸向斜前、斜后对 角平移的动作),“逢含必腆”(后胸的后缩与张开),可知小至眼神的收放,大至晃手 、云手、小五花、大刀花、青龙探爪、燕子穿林、风火轮等等典型的传统动作,无不包 含着“反正相从”这一民族动律特色。
六、有无相生
《老子》中有段话颇有哲理:“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宝,当 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段话的大意是:击揉粘土作器皿, 器皿中的空间,起到容物的作用;开凿门窗造房屋,房屋中的空间,起到住人的作用。 所以“有”(房屋)是给人“利”(便利),“无”(空间)才起到(住的)“作用”。
老子的“因有用无”、“有无相生”的名言,包含着矛盾转化的道理。因“有”生“ 无”,“无”中生“有”,“有”与“无”相反相成,相需为用。这一法则与艺术创造 不但密切相关,而且是成功的奥秘。试举舞蹈一二,加以阐述。
我以舞蹈《水》为例,编导杨桂珍,表演者刀美兰,在1980年全国第一届舞蹈比赛中 获编导一等奖。节目名为《水》,舞台实际上一滴水也没有,但又要让观众看到水,看 到江水的流淌。要从“无”生出“有”,让观众“有见”却是“无物”,这是一个不小 的难题。但编导和表演者交出了完美的答卷,达到了很高的审美境界。
节目的开始是一位美丽的傣族少女挑着水罐来到江边,坐在岸边以足试水,江水清凉 明澈,她洗濯散开的秀发,在水中踏起,溅起纷乱的水花;高兴地在水中旋转,绾起头 上的盘髻,挑起满满的水罐,姗姗远去。
中国的书画艺术自古以来就有“因有用无”的传统,并视为创作的秘诀。如刘熙载在 《艺概·诗概》中说:“律诗之妙,全在无字处。”司空图《诗品》说:“不着一字, 尽得风流”。同样是指“用无”的奥义。还有戴熙《习苦斋画絮》中说:“画在有笔墨 处,画之妙在无笔墨处。”这就各类艺术创造的共同规律。
言犹未足,再以一个舞蹈《春江花月夜》为例,这个舞的编导是栗成廉,表演者陈爱 莲,1957年北京舞蹈学校首演。同名音乐古典尚存,同名诗歌有唐·张若虚及温庭筠的 作品。从《春江花月夜》的舞名来看,五个字尽是大自然的景观,每个字都包含了诗情 画意,如春的生机、江的流逝、花的香艳、月的幽思、夜的神秘,都可发挥丰富的联想 。但在空无一物的舞台上怎样用舞蹈呈现这些景观,又怎样用舞蹈切入这个主题,且看 编导者的高招。
幕启,一个古代少女在春天的夜色中漫步于江边的花丛,她身穿天蓝色的衣裳,手持 着白色羽毛的双扇,蹁跹起舞,时而闻花,时而照影,时而赏月,时而乘风,意态缠绵 ,春夜思情。这是一个抒情独舞,在原名古典优美的旋律伴奏下,更增添了舞蹈的魅力 。通过演员的妙态舞姿,朦胧地展现出春江花月之夜的少女情怀。编者通过“有形”的 舞蹈,创造出“无形”的意境;体现了“从无生有”、“因有生无”的艺术创造的奥秘 。
运用了“有无相生”的奥义,形成舞蹈艺术作品的两个层面,一是具体的艺术形象, 二是潜在的意境,两者相辅相成,前者是目见的,后者是想象的,目见的生出了想象的 ,想象的又补充了目见的而相得益彰;前者是物质存在,后者是非存在,存在创造了非 存在,非存在又丰富了存在而更加光彩。这两个层面的“有中生无”、“无中生有”构 成妙舞,使观者获得了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