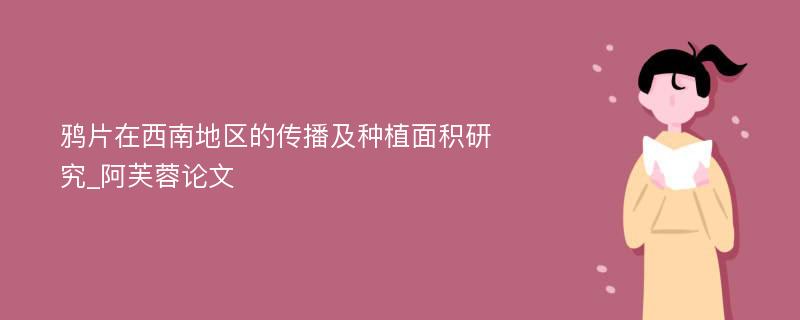
鸦片在西南地区的传播及其种植面积考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南地区论文,鸦片论文,面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检之史籍,罂粟在四川等地有较长的种植历史。早在唐代,四川已有罂粟。而后,川滇黔不乏有关罂粟的记载。如明代《洪雅县志》,将其列入花之属(注:束载、张可述:《洪雅县志》卷3《物产》,嘉靖刻本(天一阁藏书)。)。清代,各地志书中关于罂粟的记载不胜枚举。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的罂粟并不是罂粟科中的鸦片罂粟(Papaver Somniferum),而是其他品种,“华种攒瓣,如芍药;惟夷种单瓣,故结实尤大”(注:任可澄等:《贵州通志》,1948年铅印本,《风土志四》第42页。)。我们认为:鸦片罂粟(夷种)由印度引入滇西,西南地区农户种植罂粟制作烟土的时间不早于19世纪初。
嘉庆年间,瘾民增多,供应短缺,烟价上涨。利益的诱惑,滋生偷种行为。鸦片罂粟从印度经缅甸引进滇西再传至贵州、四川,影响全国。
一、鸦片传入概况
(一)鸦片罂粟传入云南概况
嘉庆末年,滇西发现偷种现象,影响逐渐扩大。云贵总督庆保、明山,云南巡抚韩克敬等均采取措施予以禁止。但受多种因素的制约,禁令成为一道道具文,难以产生效力。反之,在官吏、士绅及土司头人的庇护下,鸦片危害有所发展,“云南一属,种罂者漫山遍野,鸦片之出产,宗(总)亦必不下数千箱”(注: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78页。)。种植、贩运和吸食成为公开秘密,形成禁者自禁、种者自种、共容一地、和平相处的局面。
道光十一年(1831),御史邵正笏奏请朝廷,指出鸦片的恶劣危害,以及“近年内地奸民种卖鸦片烟,大伙小贩,到处分销,地方官并不实力查禁”等现象。道光皇帝阅读这道奏折后,深感不安,要求各省督抚饬令下属厉行查禁,严惩偷种和贩运,消除危害;并于年终时必须上奏一次,便于中枢检查督促,毋致日久生懈(注:齐思和等:《鸦片战争》第1册,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第319~320页。)。
不久,云贵总督阮元汇报:“查滇省边隅,民风素本淳朴,而壤接越南,又近粤省,遂致有鸦片烟流入滇境、效尤吹食之事。至沿边夷民因地气燠暖,向种罂粟,煎膏售卖,名为芙蓉,以充鸦片。内地民人以取罂粟子榨油为名,亦复栽种渔利(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道光十一年五月初九日云贵总督阮元奏折。)。承认偷种的事实。
在中枢压力下,阮元制定禁烟方案,采取措施加以查禁。如,每年秋季罂粟下种前,各地衙门公开告示,禁止种植;发现偷种者,没收田地;冬季及春季罂粟萌芽时,各属官员会同营员巡视锄铲;拿获偷种者,首犯充军、胁从拟徒,治以重罪;省府派遣若干委员,划分查禁范围,深入各地,督促纠察,确实禁令。民族聚居区,官吏督促土司头人积极查铲。发现偷种,予以拔毁,枷责偷种者,没收田地,作为练田,招练承种;如果土司徇情容忍,立即参究,决不宽恕(注:王梅堂等:《清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档案史料校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252~255页。),等等。不过,对此方案的实际效果,道光皇帝深表怀疑,硃批“所议皆不过纸上空谈,于事何济”!(注:《鸦片战争》第1册,第328页。)透露担扰心情。
道光皇帝的批评不幸言中,在官吏的敷衍或包庇下,鸦片危害没有得到消除,反呈现蔓延的趋势。道光十八年(1838),御史郭柏荫上奏朝廷,反映实情。“云南地方寥廓,深山邃谷之中,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获利十倍于稻。自各衙门官亲幕友跟役书差,以及各城市文武生监、商贾民人等吸烟者,十居五六,并明目张胆开设烟馆贩卖烟膏者。其价廉于他省,近复贩运出境,以图重利”(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云南巡抚伊里布奏折。)。指出云南鸦片危害久治难绝的原因,固然与烟农贪恋较高的回报、产生偷种的冲动分不开;更在于各级官吏的包庇怂恿。次年,御史陆应谷就鸦片泛滥现象向朝廷汇报,恳请高度重视,采取行动,消除危害。
但是,这些请求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偷种现象反逐渐发展。产量的增加,供给的方便,扩张了吸食习俗;大量的烟土流出滇省,贩运四川、贵州,分流华北、华中等地,培育了瘾民,扩大了消费。在利益的诱惑下,部分农民也尝试偷种,祸种北上,侵噬川省!
(二)鸦片传入四川概况
道光中叶,鸦片罂粟由云南引种四川,安宁河流域发现偷种现象。宁远知府宣瑛得知此事,饬令属员派遣差役,会同土司头人,慎密稽查,宣传烟禁,铲除罂粟,改种粮食。“如境内敢有奸民私种罂粟等花者,即将其人严拿到案,按例究办,并将所种地土全行翻犁,以免滋长”(注:四川省编辑组:《四川彝族历史调查资料档案资料选编》,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7年,第268页。),将偷种扼杀于萌芽状态。
此时,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打败清军,订立《南京条约》。战败的结局及不平等条约的订立,寓意清政府先前的禁烟行动宣告失败。在列强的压力下,清政府虽然没有放弃禁烟,事实上既难查也难禁。
恶劣的环境助长了偷种行为的蔓延,安宁河流域的偷种现象久禁难绝;黑流东向延伸,侵蚀凉山彝区。“滇土由夷地行,贱食贵买,夷人利之,由会理州至冕宁、西昌一带,分途私售”(注:袁英光等整理:《李星沅日记》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167页。)。接着,罂粟流入川中盆地,资中等地发现种植;不久,引种川东地区。涪陵夏自任在《年岁记》中记载:“次年,丙午(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鸦片渐出,屡为颇种,虽属大有,米价亦复不少”(注:蒲国树:《建国前涪陵的鸦片》,《涪陵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表明鸦片已广泛种植,成为农民家庭的重要收入。“缘崖楼栈万人家,尺地膏腴错犬牙;莫种桑麻种罂粟,东风催放早春花”(注:林孔翼等:《四川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8页。)。
此外,四川种植鸦片尚有来源广东一说。《续修涪州志》记载:鸦片罂粟是同治年间从广东引种的,因其收益较其他作物高数倍,农民趋之若鹜,不过两三年时间,绚丽的烟花满山遍野,迎风摇动,争奇斗艳。因这条资料系孤证,反映的历史也晚于夏自任的记载,姑列此处,仅备一说。
(三)鸦片传入贵州概况
道光十一年,在道光皇帝的饬令下,贵州巡抚嵩溥积极行动,广泛清查,试图扑灭。据嵩溥汇报:“臣查黔省山多田少,田土皆系倚山傍岭,零星开垦,不成片段,只敷播种粮食,藉资糊口,实无余田可种鸦片烟。其余山内,大半沙石,不堪种植,是以尚无栽种取浆、煎熬烟膏之事。”尽管偷种行为尚未发现,但因瘾民的存在,消费的拉动,利益的诱惑,部分人难免见利忘义,滋生偷种的冲动。嵩溥承认这种趋势,表示继续查禁,积极扼杀,防止萌生。“罂粟花系常有之物,既可造作鸦片烟,小民趋利若鹜,难保将来不于田内私行栽种,实属大妨耕作,自当预为防杜。臣惟督率各属,实行奉行,认真查禁,有犯即惩,并使贩者不能潜踪,食者无从购买,则来源已绝,流弊自可尽除”(注:《鸦片战争》第1册,第424~425页。)。
不久,鸦片罂粟从云南引入,黔西部分地点出现种植。道光十五年(1835),御史袁文祥反映:“贵州风俗素为淳朴,近日渐有吸食鸦片烟之人,及栽种烟草、开设烟馆之事。”道光皇帝指示黔省大吏饬令各属官员颁布禁令,告诫民众;责成保甲人等认真查缉,随时举报,尽快地消除毒患(注:《清宣宗实录》卷264,第41~42页。)。
道光十八年,因郭柏荫揭露川滇黔广泛存在偷种等现象,道光皇帝十分恼怒,颁发上谕,饬令各省大吏于管辖地面严禁载种,剀切晓喻,实力稽查;遇有违例偷种,拔毁烟苗,惩治种户。根据上谕要求,巡抚贺长龄采取措施查禁罂粟,从基础经济上消除偷种的诱因。“臣于道光十七年督同藩司庆禄、粮储道任树森刊发蚕桑编、木棉谱,通颁各属,教民栽种,以冀渐知纺织。十八年春间先于省城附近隙地试种桑秧数万株,长至二三尺时,听民移种;又于楚豫各省两次购回棉子二万六千一百余斤,并委员携赴各乡,于查毁罂粟之便,教民改种木棉”(注:贺长龄:《耐庵奏议存稿》卷6,光绪八年刻本,第1页。)。后因贺氏离任,继位者未能坚持,这些替代措施逐渐被抛弃;反之,罂粟伺机蔓延,加速扩张。道光末年,安顺(普定)“以有用之地土,置杂粮于不种,大半栽种罂粟,相习成风,明目张胆,愈栽愈多,几无正粮之地”(注:常恩等:《安顺府志》卷45,光绪十六年重刊本,第29~30页。)。
反思贵州鸦片难禁的原因,既与作物的替代未能坚持有关,还有如下的原因:一、鸦片战争的失败,禁令形同虚文,不能产生效力;二、瘾民的增加,消费的拉动,种植鸦片有利可图,桑棉等因成本偏高趋于萎缩。咸丰年间,鸦片替代桑棉成为黔省的主要经济作物,广泛种植。“农人八口,拼死尽力种耘。自秋至春,弥山遍野,无非阿堵,果汁之毒不遗旄倪,而津津者利亦随之,虽厉禁不绝也”(注:赵恺等:《续遵义府志》卷12,1936年刻本,第46页。)。
然而,与四川、云南不同地是,贵州接壤广西,毗邻广东。道光年间,英印鸦片假道广西,经黔东南流入贵阳,供瘾民吸食,故贵州也有罂粟从广东引种之一说(注:谢根梅等:《贵州烟毒流行回忆录》,《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
二、鸦片生产发展的原因及其分布特点
对于偷种、贩运及吸食等行为,清朝政府都比较重视,曾采取措施予以制止。早在道光三年(1823),道光皇帝就采取行动,通过惩治失职者,调动官吏禁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其时,针对云南存在的偷种现象,他要求滇省大吏饬令各地方官晓谕居民,严禁偷种,以净根株。道光十八年,道光皇帝再次饬令云贵川桂等省督抚于管辖地面严厉禁种罂粟;否则,将该地方官严行参办,以示惩罚,杀一儆百。次年(1819),清政府制定禁烟章程,对各类违禁案例做出明确的处罚规定。甚至在鸦片战争期间,道光皇帝还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在组织东南沿海抗击英军的同时,还指示川滇大吏继续查禁,杜绝偷种、打击贩运、重惩人犯等等,消除鸦片危害。
“从前生计总桑麻,耨月耕云几万家;才是十年风景异,春来遍地米囊花”(注:李肇基等:《开县志》卷27,咸丰三年刻本,第15页。)。鸦片战争后,在列强的干预下,清政府的禁烟行动流于形式,缺乏效力。再因外国鸦片(洋药)的大量进口,激活贩运和吸食,带动种植。此后清政府连禁政也不爱提,默认现状,实施弛禁,容忍种贩吸售活动。于是,罂粟在西南三省、特别是山区得到迅速的发展,满山遍野,生机盎然,“灿如云锦,数百里相属,可属花花世界”(注:曹昌祺等:《续修普安直隶厅志》卷10,光绪十五年刻本,第1页。)。1876年,英国人贝伯尔说:他们一行人从北京出发,至鄂川交界处,始见罂粟;进入四川,栽种尤盛;到了云南,遍地皆是。是年1~5月间,他们一直在广袤无际的罂粟地中穿行,目睹鸦片的种植、萌芽、抽蕊、开花、结果及收割全部过程(注:郭嵩焘著、钟叔河等整理:《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第572~573页。)。加上自然环境的适宜及市场拉动的影响,西南三省的鸦片生产愈加发展,逐渐成为旧中国的鸦片主产区,种植面积及产量均超过全国一半,最多时达2/3。19世纪70年代,大量的四川、云南鸦片贩运出境,销往华中及华北;19世纪末,西南鸦片已把洋药抵御在汉口以东的地区,还远销上海、广东等地;20世纪初,川滇鸦片直接与洋药争夺上海市场,最多时占沪埠输入量的40%(注: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43页。)。
由于西南三省鸦片生产具有鲜明的外向性,其种植分布也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
四川鸦片(川土)以汉口为中心的华中地区、上海以及华北等地为销场,川东地区成为烟土的主产区,约70%鸦片产于这里;以涪陵、丰都、宣汉、开县等地尤其集中。
云南鸦片(南土)以广西、广东和汉口(经重庆)为市场,故罗平、邱北、马关及昭通、东川为主产区。滇西地区因其烟土(夷方土)质量高,需要旺盛,也是重要的产区。部分缅甸烟土也经此流入内地。
贵州鸦片(黔土)以广西、湖南为销场。黔东南因自然、人文条件不适宜罂粟生长,多不种植(民国年间有所改变)。“上游鸦片弥山满谷;下游思南、平越、松桃二府一厅亦与上游无异。此外,镇远、思州、石阡、都匀四府近来亦渐此风,习气尚浅。惟黎平一府悉是苗疆,栽种最少”(注:《贵州通志·前事志四十》,第34页。)。鸦片生产集中于贵阳以西以北的地区,以安顺、兴义、遵义等地最突出。如兴义“山多田少,艺稻之外,山坡多种杂粮、包谷、荞麦之类,贫民藉以代饭。曩多栽罂粟花,制鸦片烟,以获厚利”(注:《贵州通志·风土志一》,第33页。)。烟土产量高、质量好,俗称“坝土”。
三、对西南地区鸦片种植面积的认识
(一)清季西南地区鸦片生产概况
尽管嘉庆年间鸦片罂粟从缅甸传入云南,四川、贵州等省受到影响,发现偷种现象,因种植面积毕竟不大,毒害范围有限。
咸同年间,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杜文秀等先后掀起反清斗争。十余年冲突厮杀,社会动荡,经济破坏,民众流离失所,鸦片生产萎缩,几乎绝迹。在川滇黔鸦片生产萎缩时,洋药却大量地倾销中国,增加了瘾民人数,烟价轮番上涨,形成巨大的消费市场。同治末年,形势安定,旺盛的消费、高额的价格,诱惑一些民众种植鸦片,“民间以获利厚,种植愈多,子可榨油,杆可成薪,叶可饲猪,近为收入大宗”(注:蓝炳奎、张仲孝等:《达县志》卷12《食货门》,1933年刻本,第8页。)。用土药取代洋药,满足瘾民的需要,抢占并扩大市场的份额,实现进口替代。
由于自然环境适宜,西南地区的烟土质量较好,价格便宜,产量巨大,优势明显。如光绪初年天津市场,每百斤烟土售价是:晋土三四百两银,鲁土、豫土及东北土300两左右,川土只有100余两(注:吴汝伦编:《李文忠文奏稿》卷40,光绪二十一年刻本,第30页。)。便宜的价格,增强了竞争力,导致销售的旺盛,扩大占有率;部分省份竞争乏力,只好转向其他作物的生产。
光绪后期,鸦片成为西南丘陵及山区的主要经济作物,“自咸同间,洋烟弛禁后,农民贪其利厚,土田遍种,几无隙地”(注:李世祚:《桐梓县志》卷21,1929年排印本,第2页。)。派生若干配套产业,活跃市场交易,增加民众收入。如宣汉“道咸时,以麻为大宗。故江西麻帮、万寿宫麻市,今犹可考。次黑耳,前河一带多以此起家。同光及现今,则以鸦片为大宗,每次开帮,辄百数十担或千担;次则木料;复次,若桐油、茶叶、桔子、白木耳、牛羊皮、猪毛、小肠”(注:汪承烈等:《宣汉县志》卷21,1931年石印本,第12页。)。
反思这段史事,我们认为列强不仅将鸦片罂粟品种传入西南地区,滋生并蔓延偷种行为,而且开辟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拉动鸦片生产迅速发展,导致社会经济呈现畸形。其间,清政府为抵消洋药的进口、减少利益的外溢、缴付列强等勒索的赔款,被迫改变政策,从严禁到弛禁,鼓励种植,进口替代,饮鸩止渴。
(二)测算鸦片种植面积的标准
当年,清政府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保全在外来经济猛烈冲击下的农村经济,维护社会的稳定,因之采取一些措施维护甚至涵养小农的利益。如不征收烟亩罚金,把税厘集中在贩运与售卖上,转嫁于瘾民,转移支付,寓禁于征。各属政府因之缺乏罂粟的种植面积数据(清末除外)。影响所致,西南地区的鸦片种植面积因统计者的不同,数量呈现数倍甚至十倍的差别,高低悬殊,使人不知所云。
由于西南地区鸦片生产具有鲜明的外向性,外销量约占产量60%。如欲认识罂粟的种植面积,应该考虑税收这项因素,从中推算烟亩面积。
此外,鸦片系特殊的消费品,其种植面积与瘾民数量成正比:瘾民数量少,种植面积少;瘾民数量多,种植面积多。究其原因,鸦片是进入市场流通的商品,受价值规律的调节,其供给量取决于需求的浮动与价格的升降,即或有些出入,但数量不会太大,延续时间不长。是故,瘾民数量对估算面积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西南各省瘾民的变化趋势是:清初少,清中后期增多,清末更多,民国中叶遍地皆是。“道光间,邑中吸食者十数人,闻初购于兴义,曾有因吸烟充军至湖南者。烟禁弛后,种者吸者逐渐加多,光绪初年,几乎无地不种、无人不吸。本地商人之贩运出关,与楚商之拥重赀而来者,累累然相望于道,年纳厘金约数拾万两。光宣间,与英人订禁烟条约,甫行而逊国。入民国初,政府继续实行禁绝。邑中以私种故被枪毙者十数人。民七复开烟禁,而种者还原,吸者更多青年子弟及闺中妇女,此诚凶于家而害于国矣”(注:李世祚等:《桐梓县志》卷9,第38页。)。
当然,这一发展趋势是从整体上论述的。就瘾民占人口比例而言,云南比例最高,贵州次之,四川再次之。据说,四川是数户人家有一枝烟枪,贵州每户一枪,云南最多,达到每房(每间房屋)一枪。从地理分布看,城镇较多,农村较少;坝区及交通要道较多,山区及偏僻地方较少。表现在职业上,官吏、商贩和苦力为多,农民次之,手工业者及教师等较少。“云南人民的吸烟,在城市约占十分之六七,在乡村约占十分之二三,平均全省男子(学生、军队除外)有半数已卷入黑籍……以年龄别,老年和中年人吸者最多;以性别论,男人吃者远超过妇女之数。因妇女之吃者,不过最少数之官僚太太及商家主妇而已,至男子则大多数,几乎人手一枪,在那里实行慢性自杀”(注:(成都)《新新新闻》1934年11月6日。)。
(三)清季西南地区的鸦片种植面积
关于清季鸦片种植面积,我们拟从烟土产量及税厘数量加以考证,以探索较准确的数字。据林满红说:外国人估计云南生产鸦片始于1830年(道光十年),到1879年(光绪四年),其产量已有3.5万担;其后,受四川烟土等的冲击,产量有所下降,1887年(光绪十三年)为2.7万担。四川生产鸦片的时间与云南接近,1869年(同治八年),产烟0.75万担;1879年(光绪四年)为17.7万担;据海关官员估计,1887年(光绪十二年)约15万担。贵州,1879年(光绪四年)约1~1.2万担;1887年为0.9万担。
林满红认同这些数据后,统计1879年西南三省烟土产量是22.45万担;1883年有26万担;1887年是18.6万担;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达到36.4万担(注:林满江:《清末本国鸦片之替代进口鸦片》,(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辑。)。
我们暂且接受这些统计数,据此估算烟亩面积。按每担烟土重量1100~1600两(十六进位)计算(注:当时,海关以每担烟土净重100斤,俗称海关担,即1600两。清政府各局卡亦以每担100斤计算,但包括有包装的重量,一般以净重70斤、1100两计算。民国年间,均统一每担烟土1000两。),西南三省烟土总产量在20460~58240万两间。一般而言,每亩产烟土40~60两,按50两平均产量折算,烟亩面积在410~1160万亩之间,取其中间,约800万亩。
赫德(Robert Hart)在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开列单据,认为中国鸦片产量是33.4万担。其中,四川12万担,云南8万担,贵州4万担,共计24万担,约占全国产量的72%。按每担1100两标准折算,24万担烟土约是530万亩的产量(注:鲁子键:《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册,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8年,第576页。)。
再据国际鸦片委员会报告:1906年中国烟土产量58.48万担,内西南三省36.4万担,其中四川23.4万担,云南7.8万担,贵州4.8万担。按此数据推算,西南三省的罂粟面积约800万亩(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457页。)。
综合以上三组数据,取其平均数,即清末西南地区烟土产量30万担,种植面积约600万余亩。
再观察清政府的统计数据。据度支部汇报:光绪三十一年(1905),全国烟土产量14.27万担,其中四川5.11万担,云南0.76万担,贵州1.45万担,合计7.32万担,占全国总产量48%;次年(1906),全国14.81万担,四川5.75万担,云南0.79万担,贵州1万担,合计7.54万担,占全国的50.9%;光绪三十三年,全国12万担,四川4.45万担,云南1.6万担,贵州1.23万担,合计7.28万担,占全国的60.7%(注:《政治官报》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第353号,第464~465页。本文引用的数据均作四舍五入处理。另外,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公布的各省鸦片面积与光绪三十三年(1907)相同,恕不引用。)。若折算清政府的统计数,西南三省烟亩面积在138~165万亩间,取一个平均数,约150万亩。
比较外国人与清政府的平均数,差别达3倍;若将外国人的高数与清政府的低数相比较,差别近10倍。究竟何者为宜?
先分析外国人的600万余亩面积、30万余担产量数据。按每一瘾民年均消费烟土30余两计算,1万担烟土可供30万瘾民吸食一年,30余万担可供900万瘾民。当时,西南三省自吸数量约占40%,即有瘾民360万人。单从数量上讲,不算突出,若考虑这些瘾民基本上是成年男性时,在惊讶其数据过于庞大的同时,不免有夸大其辞的感受。考证清政府的烟土统计数据,颇有疑点。且以云南为例。据锡良奏折:光绪三十二年滇省外销烟土7938担。仅这外销量就超过度支部汇报的生产量;当时云南每担烟土重量是1600两,若按1100两的标准担折算,应是12708担。单凭这两点,不能不让人怀疑度支部统计数据的真实性。
再从税收上考察。《贵州通志》罗列厘金统计表,总数649650两,其中土药厘金440400两,占2/3强。因不知其征收的具体年份,更因该表内各局卡征收的汇总数与前面引用的数目竟有10倍之差。对于这样的数据,我们根本不敢使用。由于此表附言中云:“惟光绪二十九年三十年,抽收最旺,多至三十六七万,是亦当日所悬最高之鹄,实际未企及者也”(注:《贵州通志·食货志》附表9,第57~59页。)。我们暂不考虑“未企及”的因素,就按此征收数言之,土药厘金约占总数的2/3,有24万两之谱。光绪三十年(1904)时,黔省每担外销烟土征收厘金12两,以此折算,共有2万担。若考虑自吸及漏报等因素,我们暂估计这数据为总产量的50%,认为贵州烟土产量有4万担,种植面积约80万亩。同年,四川征收的税厘数量约110万两,按每担烟土27.28两税厘折算,约4万余担;若再考虑其他方面的因素,我们认为四川烟土产量约10余万担,种植面积约300万亩(注:秦和平:《四川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6页。)。还有,这一年云南征收税厘216834两,按每担烟土征税厘21两折算,约10300余担,因滇省以1600两为一担,若转化为1100两的标准担,应为1.5万担。对此数据,我们曾有考证,认为斯时云南烟亩面积约70万亩(注:秦和平:《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25页。)。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清末西南地区鸦片种植面积约400余万亩,烟土产量约20余万担。按40%自吸量计算,约有瘾民240万人。
但是,在时人观察中,云贵川基本上是鸦片的世界,“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458页。)。耳闻目见的现实与我们考证的烟亩数量存在差距,该从何解释呢?
当年,多数农民种植罂粟时必须考虑投入与产出,基本上不把整块土地用来种植,而将罂粟套种在小麦、豌豆、胡豆、油菜等作物中,于是1亩罂粟往往是两三亩土地的面积,以综合利用土地;每窝罂粟只留二三株壮苗,以便有效地汲取土壤中的养份,增加蒴果浆汁含量,提高产量。尽管罂粟株数不多,但其占地面积不小;更因罂粟是高投入的作物,需要的劳动量较多。因而多数农户将罂粟作为副业,种植于住宅周围,便于照料。“鸦片烟,罂粟实汁也,一名阿芙蓉,冬初种子,夏首割浆,无害农时,得价颇贵,乡村篱落多种之”(注:张九章等:《黔江县志》卷3《食货》,光绪二十年刻本。)。档案反映:当年农户种植罂粟多者二三亩,少者仅几分(注:四川大学历史系录副光绪三十四年巴县各场栽种土药凭照存根;四川省档案馆藏1928年巴县四区曾家场、兴隆场、双胜场等造具烟户姓名及种植面积清册。)。有关志书也印证这些数据(注:佚名《蒲江县乡土志》(清末抄本)记载“罂粟,县属种者一千四百余家,种地五百七十八亩九分”。平均而讲,每户人家只种植三四分土地的罂粟。)。虽然,就单个农户而言,种植罂粟面积不大。因土地接踵相接,出苗时郁郁绿色,盛开时争奇斗妍,在观察者的眼中,烙下罂粟海洋、鸦片世界的印象。
事实上,这400余万亩烟地、20余万担烟土并不为少。一是它们系丘陵、山区中有限的沃土,妨碍了粮食等作物生产,以每亩养活一人而计,涉及400余万人的生存;二是20余万担烟土可供600余万瘾民吸食一年。想一想,这600余万人基本上系男性青壮年,按五口之家计算,涉及人口达3000万,占全国人口的8~9‰(注: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0页。),怎让人不感到沉重呢!
(四)民国年间西南地区的鸦片种植面积
1906~1918年,清朝及民国政府均采取措施,厉行禁烟,西南地区鸦片生产再受打击,逐渐萎缩。1919年,枯萎的烟花在军绅政权强迫下复苏,绽开怒放,像瘟疫般蔓延,于丘陵与山区。
30年代初,蒋介石凭借掌握的兵权,藉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等名义,颁布各项禁烟命令;并通过“汉口禁烟督察处”,对川滇等省烟土课以重税,限制其流量,萎缩其生产。1935年,中央军藉追赶红军之机,开入西南诸省,囤兵威胁,蒋介石伺机伸入权力指臂,控制西南地区。与军事手段相配合,蒋介石设禁烟总会于重庆,自兼禁烟总监,将禁烟命令转化为法律,藉“新生活运动”等名义,开展禁烟运动,釜底抽薪,切断军阀的大宗财源,削弱其势力,使之听命中央。在国民政府的压力下,怒放的罂粟花朵开始枯萎,逐渐凋落,除少数边远民族聚居区外,鸦片危害基本上得到消除。
有关民国年间西南诸省的种植面积,先观察这样的数据:1933年,四川65.7万余亩,贵州72.4万余亩,云南情况不详;1934年,四川54.6万亩,云南93.3万余亩,贵州66.4万亩,合计214.4万余亩;1935年,四川37.2万余亩,云南67.5万余亩,贵州37.5万亩,合计142.2万余亩;1936年,四川27.6万余亩,贵州15.4万亩,云南情况不详;1937年,四川24.4万余亩,贵州3.5万亩,云南8.5万亩,合计27.9万亩。需要说明的是,各省测算烟亩面积的标准不一。如,四川按亩产烟土130两折算,云南按亩产20两折算,两两比较,有五倍之差,对此时人表示异议(注:《四川省政府复电之一之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禁烟总会:《禁烟半月刊》第3期;《各缓禁省种烟面积产量比较表》,内政部禁烟委员会《禁烟纪念特刊》。)。事实上,这些统计数均有缩小的弊病,极不真实,特别是四川,仅为参考而已。另外,在1935年的日内瓦禁烟会议上,美国代表福勒声称:云南每年烟土产量4500吨,四川与之不相上下,贵州每年约有400吨(注:《国联第二十二届禁烟会议美代表福勒演说词》,内政部禁烟委员会:《禁烟纪念特刊》。)。以此折算,云南及四川的鸦片面积各有288万亩,贵州只有25万亩,合计600万亩。但从我们接触的材料看,四川的种植面积或许基本符合,云南有所夸大,贵州大大缩小。自然,这样的统计数也不能采用。
1928年前后是西南三省鸦片生产的高峰,我们以此为依据,认识其种植面积。贵州:1926年周西成入主黔政,积极发展鸦片生产,改革罚金征收办法,先确定总额,再估算各属产量,加以分摊,限期交纳,强化管理。其时,大批黔军驻扎四川、湖南和湖北,外销渠道大为拓展;更因周氏采取优惠政策,减轻税率,方便报关,鼓励外销烟土;以及湘桂两省实施优惠措施,吸引烟土过境,等等。贵州鸦片生产达到高潮,外销烟土一度达四五万担(注:谢根梅等,前揭文;伍效高:《我贩运黔土外销的经过》,《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另据贵州省有关部门统计,“农产内另有一种特殊物品,即鸦片烟,约计年产可五六万担,其质以西路各县为优。出产之烟,除供自吸外,运销川汉粤桂等省,约值千八百万元,近年农村经济恰赖周转”(注:贵州省政府?《贵州经济概况》,1937年铅印本,第2页。)。若按外销烟土占总量的2/3计算,贵州鸦片产量约7万担。再据国民政府禁烟督察处调查:平常年份,贵州烟土产量约6.1万担,遇丰年可达8~10万担(注:肖觉天:《禁烟督察贵州分处考查黔省禁烟情况呈文》,马模贞主编:《中国禁毒史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根据这三组不同的数据,取其平均数,民国年间贵州的罂粟面积约有120~140万亩。
云南:1920年弛禁后,该省坚持实施烟亩罚金办法,按亩征税。因政局动乱较少,其罂粟面积的数据保存最完整。1928年,云南禁烟局曾汇总全省117县历年最高额定的烟亩数,共106.8万余亩,产烟土5342万余两(注:云南省档案馆藏1928年9月王维乾调查制作云南全省各属历届最多烟亩面积统计表。)。对此数据,我们基本上认可,但考虑存在少报或漏报等因素,我们认为平常年间云南的烟土产量约7万担,种植面积在120~130万亩之间;最多时,面积可能超过150万亩。
四川:因大小军阀划分地盘,视作防区,随意征税,名目繁多,有窝捐、亩罚等等,罂粟面积难以统计。据1921~1922年间调查,全川烟亩面积是216.6万亩,其中川东等34县有152.9万亩,占70.1%(注:廖季威等:《鸦片烟在成都》,《文史精华》编辑部:《近代中国烟毒写真》,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这统计数目极不真实,难作定论,仅作参考。我们曾根据部分防区税收及烟土的外销情况,估计20年代末,四川烟土产量约20万担,种植面积约400万亩。
综上所述,民国年间西南地区的烟亩面积约700万亩,烟土产量约33万担,供给1000余万瘾民的消费。这个种植面积是否基本确实,我们再藉瘾民情况验证:四川,1936年四川登记在册的瘾民是145.89万人(注:《四川省各市县烟民登记数及戒绝数统计表》(1937.7),四川省禁烟委员会:《四川禁烟专刊》。)。但禁烟特派员肖致平认为有少报之弊,他估计四川瘾民在200万人以上(注:《四川省禁烟委员会第三次常会欢迎肖特派员茶话录》,《四川禁烟月刊》创刊号。)贵州,禁烟调查专员邓棠青认为瘾民是100万人(注:《贵州省查禁种烟专员呈报调查办理禁政情形》,马模贞主编L《中国禁毒史资料》。);云南,我们曾考证该省瘾民约有110万人(注:秦和平:《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第103页。)。三省合计,共有400万余人,年消费烟土13万担,占烟土产量的40%,符合惯例,印验我们对民国年间罂粟种植面积的推论。
需要说明的是,较之清季,民国年间西南地区人口数量没有多少增长,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负增长。此时瘾民不仅数量多、占据的比例也较高,当然造成的危害也更加恶劣!因为,这700万余亩烟地均系良田沃土,按亩产粮食1石多计算,种烟减少了1000万人的口粮。粮价高涨、供给紧张、库存短缺是必然的结果。平常年间,这恶果或许未充分地表现,一遇自然灾害,暴露无遗,官廪私藏均形匮竭,饥馑立见,哀鸿遍野,嗷嗷待哺。
环境的压迫,促使部分当政者正视鸦片的恶果,不能不考虑开展禁烟运动。更为重要的是,30年代中叶,由于日本侵略的加剧,抗日呼声日益高涨,兵役、粮政是进行抗战的基本保障,其获得依赖于禁烟。于是,禁烟成为西南三省社会各阶层的共识与一致行动。禁烟运动使川滇黔成为大后方,为坚持和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