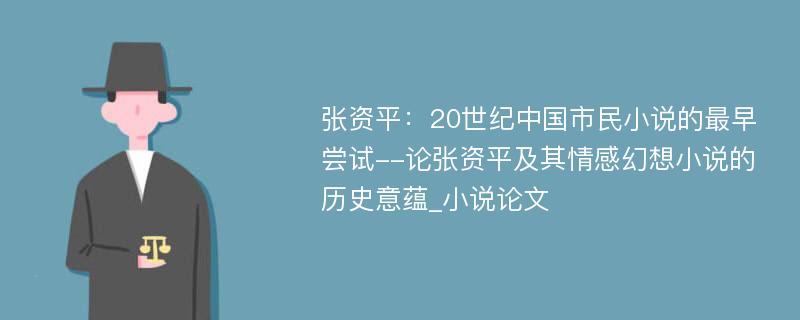
张资平:20世纪中国市民小说的最早尝试——略论张资平及其情感幻想小说的历史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小说论文,中国论文,市民论文,幻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资平可说是20世纪中国第一位市民小说家,是中国20世纪市民小说最早的尝试者,他开启了现代市民小说的风气,对以后的中国市民小说具有承前启后的启示性影响。
中国市民小说的功利性和消闲性要求最早在张资平的小说中得到同时体现,这种风格的本质,从世纪初期几乎一直保持到中国20世纪晚期的文学中。被归入海派作家的张资平,在没有去上海而在武汉之时,就已经达到了其创作的高峰阶段,并且已经明确描写了海派小说的主题,其重要作品,如《苔莉》、《最后的幸福》大多发表于在武汉的那几年。而以后几十年中在中国20世纪文学中产生影响的市民小说的不同身影,已大多在张资平小说中影影绰绰出现,如叶灵风的浪漫主义市民色彩、刘呐鸥的感伤气息、穆时英的现代都市情恋关系等。张爱玲关注市民生存中金钱与爱情的关系,她明确说过她曾迷恋于张资平的小说;施蛰存的东方心理小说有一家之风,而张资平却早于他进行了自然主义和精神分析双重交错的心理描写。甚至当代受市民欢迎的多角恋爱故事在张资平那里也早已是“旧时王谢堂前燕”。同时,他的小说又迎合时代潮流和思想,是各种社会思想、艺术学说和市民情绪的时髦而奇异的混合,如个性主义、革命、战争、浪漫幻想、自然主义、精神分析等。20世纪晚期,一些具有私人化叙述风格的的作家对于性欲望和身体行为的表现,在张资平的小说中也早就已露出了端倪,张资平明确地表现出用自然和记录的方式来写两性关系的愿望,并在其创作中努力坚持这种愿望,只是当时中国文明情境和历史状况不允许他充分发挥对于性的自然主义描写。同时,从王安忆关于上海市民生活的一些作品开始,到王朔对于市民生存的世俗化关注,再到池莉和刘震云所描写过的平庸化市民生存愿望和烦恼,以及90年代中期以后盛行起来的一些市民表象化作家,如东西、何顿、张欣、邱华栋等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平面化、零碎化描写,实际上与张资平所描写的市民生存本质都不无一致之处,然而,却又不如张资平那样具有对于文明进程思考的深刻性,也没有张资平那种对于爱欲与文明关系的复杂表现。
张资平的市民空间主要由两类小说构成:一类反映市民尤其是市民知识分子的身边问题、个人琐事生活,描写小市民的具体生存苦恼;另一类是情恋小说,这一类小说主要描写市民知识分子的爱欲与文明压抑的矛盾,描写市民阶层的精神幻想。在他的非情恋小说中,是一种非常现实化的生命现象,人们的物质欲望和肉体生存要求是无法克服的,给人们带来的是因缺少物质满足、因贫困而产生的苦恼;而在他的情恋小说中,人们却可以以自己的精神满足去逃避这一现实痛苦。张资平的情恋小说从来都不现实化,远离人们的实际生存状况,但正是这种浪漫化的精神倾向,为市民生存提供了生命幻想和安慰。
(一)
张资平对中国20世纪市民小说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延续着中国明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市民小说传统,又对其加以现代改写。
张资平的情恋小说既改写了明清以来的古典市民小说的情趣、主题和传统,又改写了鸳鸯蝴蝶派描写两性关系的闲情逸致和对才子佳人的赏玩,而产生一种现代情境中爱欲与文明相互冲突和限制的书写以及爱情至上的主题,使中国市民小说在中国的现代进程中与现代市民的生存相适应。张资平小说的情恋故事表现出市民阶层在中国现代文明进程中的苦难性和悲剧性主题,以及市民生存夹在古典文明和现代文明中困境的现实性,其女性人物既有古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情恋追求,又有西方文明所带来的爱情至上的理想主义和个性主义色彩。
张资平的情恋人物总是陷入精神困境中左冲右突,一开始就处于一种古典理性的保守之中。他的小说可分为三类,一类描写了金钱与爱情的冲突,这类人物企图以现实的利益得失来控制生命激情;一类描写了传统礼俗与爱情的冲突,而这一类的描写实际上具有中国古典传统小说主题,那些古典小说多半是写古典式的有身份大户子弟如何恋上风尘女子,而最终依然要抛弃那青楼才女的爱情,回到礼俗制度,娶个有身份的小姐等等故事,仿佛《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李甲与杜十娘的故事,如《梅岭之春》。第二类则是古典才子佳人小说的现代改写,如《苔莉》,克欧最终不是回到父母身边完婚,而是与苔莉一起殉情,这样的故事完全违反了古典小说的主题意向。第三类人物则是企图以理性来控制激情,其中包括以对宗教的信仰来克制激情,也包括以对婚姻和家庭的理性思考来控制激情。《双曲线与渐近线》已出现了张资平的基本男女主人公模式:男性总是懦弱胆怯的,女性总是热烈大胆的,充满了生命的刚烈之气。郑均松是一个传统的男性形象,他与青楼名妓私订终身,最终浪子回头,返回家园,抛弃爱情。而梅茵则是一个尤三姐一类的女性形象,但被张资平加以现代改写,不是依照传统观念和古典结局终成眷属,择嫁从良,或是愤而殉情,而是依照《圣经》教导安于名分。韩蔚生这样的青年并没有真正清除古典理性,五四新文化条件和社会条件只是给他们提供了一种外在的自由恋爱的可能,本质上他们仍在按封建理性衡量婚恋。
张资平的小说虽然注意了小说的叙事功能和娱乐性质,但他小说中的主题和内容是普通言情小说所难以具备的,他的情恋小说大都具有悲剧性质和苦难性质,他的小说很少有真正快乐,那些情恋人物很少有幸福结局。他深刻描写了爱欲与文明的冲突,决不是简单的“△”作家、消闲小说家。单纯的消闲类小说没有苦难性,主题不是悲剧性的,结局也往往是大团圆式的,并且很少包含历史文明与个人欲望的冲突;而张资平的小说追求悲剧性和苦难性,已不能单纯看作消闲小说。
张资平极端地书写爱情至上的理想主义,似乎竭力要使人生显得快乐一些,但他的故事仍掩藏不住地描写了两种主要的人生苦难景观。他的非情恋小说多写市民知识分子艰难的生存境遇和苦恼凄伤的人生,他们经济拮据,精神暗淡,为物质生存而艰难挣扎。这类身边小说早已在文学史上被承认其对于社会现实的书写价值,但张资平的非情恋类小说与郭沫若、郁达夫等的身边小说并不一样,那些作家的小说比较形而上一些,对于现实具有超越意味,而张资平的非情恋小说则更加形而下一些,具有冷峻的现实性、苦难性和世俗化主题,对现实苦难更有体验意味。张资平的情恋故事也同样书写了苦难的恋爱故事,而不是快乐的恋爱人生。张资平的情恋小说不少有一种悲剧性的气氛笼罩着,有一种必然的悲剧性结局在等待着那些情恋人物,似乎他们一开始产生情恋就伴随着悲剧性命运,似乎情恋本身就是苦难,那些情恋大多是不能完成的或失败的,情恋过程最终变成了苦难的历程,那些情恋人物对于理想爱情的追求,却给他们带来了苦难,他们不是死于与性爱相关的疾病,就是自杀身亡。但他们的可贵之处,却在于在这种经历苦难而追求爱情的过程中去发现生命价值。
(二)
张资平的小说对市民知识分子狭窄的生活空间津津乐道,但从不满足于这种市民生存的方式,并不赞美市民功利价值,而是批判市民生存的庸俗与渺小。
在张资平的小说中,市民生存从未得到真正的世俗幸福,而是往往在获得他们得到世俗幸福的同时,失去了精神价值,于是反而要依恋和追求。张资平描写的正是这种因追求世俗价值而失去天国价值的情景。那些失败的爱情故事,几乎每个都包含着惋惜、悲叹和讽刺,这是一幅幅市民知识分子在欲望前绝望挣扎的生动图景,却没有一个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者,他们对自己实行了绝望的救赎,却从未有哪个幸运地从爱情得到最后的幸福,只有短暂的幸福,他们竭力追求自己爱情的结果反而招致了生命的毁灭。那些情恋人物的悲伤故事,浪漫化地满足了当时人们对个人爱情和个人幸福的想象,表现了现代情恋要求与现实社会之间矛盾的状况,表现了在两种历史力量和道德力量冲突间的市民情感生存,这导致他笔下那些青年的觉醒性、压抑性、软弱性的同时产生,他们创造了自己的感性生命的生动性,又压抑了、毁灭了自己的情爱理想, 在现实和理想的夹击、在理性和感性的矛盾中徘徊停止下来,就象N和刘静仙,并不是寻求灵肉相融的爱的天堂,而是寻求现实生命的庇护所;或者象苔莉一样,在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在自己的现代爱欲中,毁灭自己的生命。这种悲剧性、这种被夹击的命运,道出了当时大量小知识分子的生命痛苦和酸楚。
张资平的市民知识分子的生存烦恼和生存幻想,具有一种市民化的理想主义精神,它并没有完全脱离现实去言情,而是鼓动人们在当时的现实中去追求一种理想的爱情和婚姻。张资平的情恋人物具有一种幻想性,他们都绕着一层追求理想爱情的光环,抱着恋爱至上的准则而形成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精神。中国现代市民生存的现实困境以及其教养的世俗化,使其注重利益和物质生存。但人天生有幻想和理想主义,市民生命中被压抑的理想仍然保持着,张资平的小说将其转换为情恋中的理想性和幻想性,使市民生命的现实压抑在情恋故事中得以释放,那些被市民所迷恋向往的爱情理想表现,替换了市民对现实的理想幻梦,使市民的理想集中尖锐地在情恋关系中表现出来。
市民化的理想主义,长期以来不改变其实利和现实幻想的根本性质,但随着社会文明性质和精神品质的变动,其具体的内容会有所变动。从张资平的小说到张爱玲的小说,再到王朔的小说、琼瑶的小说,市民化欲望和追求的具体内容早已大异其趣,但基本的市民理想并无根本的改变。市民化的理想主义往往具有现实的改善或美化的愿望,作为现实的一种虚幻可替代物而存在,其中灌注了过多的实际生存、现实因素,其主要特征是摆脱现实的种种束缚和压制,以幻想实现现实中没有的自由。因此,有时这种市民化理想主义具有强烈的反抗旧制度的因素,对现实社会表达不满。张资平小说中的人物也具有这样的特征,他们反对制度化现实的主要动机是实现和完成个人的自由。
市民化理想有多方面的内容和实现方式,张资平的小说代表着市民阶层对于爱欲实现的梦想。这种爱欲集中表现在物欲与爱欲两者之间的冲突中,与弗洛依德所论及的性欲动力对于生命和社会的关系有相近之处。这些小说并不单方面地针对物欲或情欲进行书写,而是以物欲为爱欲的陪衬和参照,对市民化的爱欲进行发挥和考验,并且往往最终的结果是爱欲得到升华,变为人的一种精神写照和寄托,战胜物欲,所以,人物在一段激烈的爱欲渲泄后,或者皈依宗教,或者忏悔死去,或者作为爱欲不能控制的极端而主动走向死亡。那种爱欲变为对于爱的奉献,成为市民的一种理想主义,将这种爱作为理想的一种寄托。张资平情恋人物表达的理想主义,针对着当时社会表达市民的不满,那些人物行为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传统礼制文明进行了激烈的反抗,那些情恋人物在传统礼制文明束缚中左冲右突,她们以断然决绝的情恋态度和将爱情的船与自己一起凿沉的表现,力图为自己的爱情和生命寻求一条生路,宁可毁灭于现代文明的进程之中,而不愿将自己毁灭于传统束缚之中,这种个人化行为,已转化为社会反抗行为。有时张资平小说中的人物,甚至能以精神的高尚来战胜物质的诱惑,如《公债委员》中陈仲章为了阿欢甚至丢弃“公债委员”的差事;在《忏悔》中“我”甚至可以净化和提升情感来面对生存苦恼。
张资平所开辟的市民文学空间与历史叙事空间的不同,在于它更加注重个人幸福实现的可能,这其中不应否认对于历史进步的追求。张资平情恋人物保持的理想主义精神,是以个人幸福的实现加以衡量的,那些情恋人物为追求个人的幸福,往往有一种极端性的行为,人物将爱情当作生命的唯一追求而常常过度,以爱情的实现来作为幸福的代表,这些情恋人物常常不顾一切,甚至不惜以伤害别人、耗损自己的生命来消耗爱情,以生命短暂的爱情占有和对他人的侵害,来感受片刻的幸福,而他们以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对这种幸福的追求过程中。这一类人物不顾一切地追求个人爱情和幸福而招致个人的毁灭,一方面描述了个人幸福的必要性、个人压抑的不合理性,描述了个人幸福在社会历史空间中的独特位置,另一方面描述了过度挥发个人压抑的悲剧性。同时,还表述了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间的关系,表达了个人幸福对于社会幸福的必要补充,表述了没有个人幸福的社会其实根本不具备社会幸福的价值。张资平情恋人物的个人幸福的失去,正是社会毫无幸福可言的表征,是当时社会现象的反映。对社会而言,由于他们所追求的个人幸福对每个社会成员而言都是可能和必须的,他们对于个人爱情和幸福的追求,实际上也包含了对社会实现和保障个人幸福条件的追求,因此,张资平情恋小说中个人幸福的追求无形中与社会幸福榫合在一起,而对个人爱情和幸福的追求都表达了一种对社会的理想愿望。当然,这是一种市民幸福,它更多地存在于个人空间而不是历史空间之中,它必然具有眼光短浅、注重个人实利的特点。而且追逐个人利益和幸福、发挥个人爱情和欲望,也造成了爱欲与文明、爱欲与压抑、爱欲与禁忌、爱欲与死亡的冲突。此外,张资平的那些遭受压抑的情感故事和浪漫人物,试图表现的,不仅是当时的社会即一个历史阶段试图加以抑制的东西,而且是任何文明都可能会加以抑制的,当时两种文明交错的社会情景,正是这种人性与制度、文明与禁忌冲突的独特环境。
《最后的幸福》中美瑛反复思考之后,“知道了所谓幸福并没有绝对的,只看她的欲望能否满足……有一部分的希望或欲望受了道德法律的限制或受了夫妻名义的束缚,那个女子就不能算幸福了。”美瑛的这段思考,几乎包括了张资平情恋小说的全部有关爱情幸福的主题思考。它们大致有几方面的内容:
1.满足欲望才是幸福的,对于张资平的市民化情恋人物来说,欲望满足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同时,这里的幸福是指爱情幸福,张资平树立了一个命题:没有欲望满足的爱情是不彻底的,甚至可能是虚假的,没有欲望满足的爱情幸福自然也是不可能的。
2.美瑛将欲望等同于希望,即是说,对于张资平的情恋人物,欲望不是单纯的性欲,而是包含着对于爱情实现的希望,而爱情实现对于张资平的情恋人物一定包含着欲望实现。
3.这种爱情实现应该是无限制的,不应该受到任何文明秩序和传统的压抑,这表明一种对于爱情的追求,真正的爱怀着对于对方的欲望和希望,而不是仅仅像《蔻拉梭》中的文如与妻子一样以生活保障为条件的和谐之爱。
4.这段话以及张资平的情恋小说,强调了女性之爱、女性幸福和女性权力,而这一切都要在爱情中加以实现和验证。男性之爱由于文明对其赋以权力并压抑较少,与女性不一样,并不能尖锐体现文明压抑与爱欲解放之间的关系。
(三)
张资平的情恋主题,在中期以后具有愈来愈浓的个性主义色彩,浪漫爱情和浪漫革命都统一在个性主义之下,描写了一种独特的个性主义革命者,其后期情恋人物大多从个性主义者转变为幻想性革命者。
张资平小说中的这些个性主义者大多是女性,她们的独特表现是由爱情走向革命:以情爱作为自己个性解放的目标和必然途径,但她们的希望大多寄托在男性人物对她们的爱上,而不在于反抗社会制度。这些情恋人物从沉迷于爱情到从爱情中觉醒,整个过程都具有个性主义因素,她们的主要表现或是试图固守于爱情之船而沉没,或是试图拯救自己的爱情,并将爱情与革命捆绑在一起。将女性人物的追求主题改变为觉醒主题,这个转折使张资平的情恋主题不再具有前期和中期的复杂性,也不再在理性和感性、自然和文明、爱欲和压抑之间反复徘徊。后期的觉醒者不愿将自己毁于传统文明价值的追求中,宁肯将自己毁于现代文明进程中,力图为自己找到一条爱情和生命的出路,于是将个人爱情行为转化为社会反抗行为。当然,这些革命往往是自发的、过往的、不对现实政治构成威胁的行为,它们往往是一种文学化、浪漫化、想象化的行为,但其个性主义者已明确从单纯情恋中脱离出来,这些个性主义者金蝉脱壳之后变成一个充满幻想性的革命者。
张资平的后期情恋小说,仍然保持理想与感情、自然与文明、爱欲与压抑之间的冲突关系,但理性内容有所变化。这阶段小说中,理性大半被“革命”所代替,而前期小说“理性”主要是由宗教来代表。这在张资平的小说中是个奇幻的悖论,革命本是激烈的行为,而这里革命却代表着一种冷静的理智和现代方向对爱欲的制约。何况,张资平的人物并没有什么关于革命的政治觉悟,而只是一种感性的要求。由于这种感性的革命冲动,对革命的本质并无真正的理性认识,因而他们的革命行动也往往是感性的、冲动的、悲剧性的。这种革命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与爱情相关,人物由于爱情的驱使而参与革命,这种革命行为更象是一种爱情的献身行为,它们仅仅对于故事中投身革命人物自己来说是有意义的,是为了使自己得到精神提升和情感净化,而不是实在的为社会谋得福利的理性行为。因此,这些社会行为,主要并不是作为一种历史行为出现,而是作为主人公的个人行为出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故事情节加以组织,对爱情主题加以表现,社会化行为被以革命的名义,在爱情主题和情节发展要求下被组织起来,于是出现了浪漫故事、爱情主题和革命背景三位一体的小说模式。这里多少有将个性主义与现代革命相混合的含义,同时也有将革命与浪漫爱情甚至幸福幻想相混合的含义。对于张资平情恋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必须将一种个性主义的色彩涂抹于她们所爱人物才值得去爱,于是将个性解放的主题转移到下层劳动者身上,并转变为一种以革命形式出现的下层劳动者的幸福观,以使人物更加适合张资平的情恋小说模式,适合小说中有个性主义革命主题,以表现爱情至上加浪漫革命的图景。
(四)
张资平的情恋人物处于中国古典传统的礼制文明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文明交错时期,这些情恋人物的表现,生动地呈示了两种文明交错时的生命选择和社会情景,反映了市民知识分子的爱欲与现实的矛盾,反映了两种不同文明同时对他们施加的压抑和解放。
当时的中国社会,仍主要地处于传统礼制文明的控制之下,而张资平的情恋人物具有的新世纪的文明思想和行为,当然不能被礼制文明所允许,但现代文明的优越并没有在当时强大到足以战胜礼制文明的缺陷,即是说,现代文明不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幸福保障和行为依托。他们被夹击于两种文明之间,既不符合礼制文明的规范,又超越了现代文明的原则,于是,只好超越一切文明规范,甚至不惜以生命殉爱。
张资平情恋小说人物虽对封建性古典文明的解构采取了一定行动,但也表现出对这种文明的保持,这些人物的独特之处就是在两种文明夹峙的边缘地区生存,这也是中国市民20世纪最初的生存境遇。他们处于两难地位,既想要背弃封建性古典文明,又难以舍弃他们在这种文明中的实际受益;既想要获得精神家园,又难以拒斥物质利益和世俗生存的诱惑。然而,他们虽放弃了爱情所代表的天国幸福、精神家园,寻得的却又不是世俗幸福,他们并无安宁、平静、满足、安慰等世俗幸福的价值可言,他们时刻被他们所放弃的爱情所噬咬而痛苦,几乎每个自动放弃爱情的人物都在几年之后试图追寻当年的爱情。爱情对于每个实际生存的人来说,是一种世俗的幸福,但对于张资平的人物来说,却是天国幸福,代表着一种灵魂对现实的、对身体生命的超越,也代表了市民知识分子寻求世俗幸福的艰难。
张资平情恋小说人物对封建性古典文明的保持和解构、对于个性主义的坚持和放弃,都是一种历史体现。这种体现一方面在于表现了封建文明与现代文明交错的复杂社会心态,表现了古典文明价值在现代的变幻,表现了两种文明交战在市民社会中的具体生动情景。另一方面,在于个人幸福、个人价值、个人功利的追求在历史发展中的展现。张资平情恋小说的人物大多明确把自身确定为衡量社会的价值标准,把自己作为真实、独立的个体,而表现出面临封建性文明体制和传统、面临世俗利益时的软弱特征。他们一方面对封建文明和现实物欲制约下的婚恋表示不屑,一方面又无法彻底追随神圣的爱情,将人的灵魂和精神生命超越他们鄙视不屑的现实。这种自尊又自卑、愤激又无奈的边缘化和世俗化的市民心态,表明西方文明在与中国封建古典文明相遇后,中国市民社会必然要呈现出来的文化特征,而张资平的情恋人物集中表现了这种文化特征:即被封建性古典文明和现代社会功利观念紧紧束缚的市民社会文化特征。
张资平情恋人物对于文明规范的逾越,主要来自生命的感性生存动力与理性控制之间的不平衡,来自生命的爱欲与文明对爱欲进行压抑的冲突。因此,爱欲与文明的奇异关系、人物挥发爱欲的奇异故事,构成了张资平小说景观的最独特之处。张资平描写爱欲与文明的冲突有三个特点:(1)极端地发挥爱欲,在张资平的情恋小说中, 爱欲没有适度、平和的发挥,没有爱欲与文明的和谐关系,只有极端地从感性生命的角度发挥爱欲的人物,这些人物为发挥爱欲而遭受文明的压制与处罚,以至招来生命的毁灭。(2)将爱欲作为生欲的一种尖锐代表, 将爱欲作为生命的集中表现,而爱欲的发挥伴随着死欲,这些情恋人物为发挥爱欲不仅踰越文明规范,而且踰越生命限度,骄傲地以生命快乐原则来炫耀爱欲旗帜,而爱欲本身伴随着生命的毁灭意识,这些人物似乎在死欲和生欲的同时驱动下,拼命地以爱欲为名消耗生命能量、踰越生命快乐的限度,所以那些著名的张资平情恋人物,都只有悲剧性的生命结局。(3)张资平在描写爱欲与文明的关系时, 必然地描写了文明对于爱欲的强大压制,描写了人物为发挥爱欲而在文明之前绝望挣扎的悲剧性生命情景。这种悲剧性生命情景对文明制度的缺陷和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生命代价都进行了思考,表现了生命在爱欲冲动和文明压抑间徘徊痛苦、茫然无奈的处境,爱欲必然地携带特殊的历史情境和文明压抑而在其中进行表演。
张资平情恋小说体现了理性生命与感性生命的巨大冲突,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长期排斥和压制的性欲望,还原为人性因素,将文明的现实原则和社会禁忌加以破坏,将审视婚恋的道德原则,转化为张扬人性自然的欲望原则,对封建性文明的禁欲本质进行冲击,对情恋的社会性与自然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表明生命追求的本原性质。张资平情恋人物的爱欲特点是,生命的唯乐法则与文明的现实法则产生了对抗,性快乐与性情感共同构成张资平情恋人物的爱欲以及小说的爱欲主题,它们分别代表着肉体生存和灵魂生存、自然生存和社会生存。对于这些人物来说,社会文明的很多规范和观念都是外在之物,而他们追求生命的则是无拘状态。这些情恋小说的特点似乎在于,灵魂之爱建立在身体快乐与和谐之上,灵魂救赎也建立在肉体生命救赎之上,而人物灵魂最终的飞升,则又建立肉体毁灭之上。对这些人物来说,往往先有肉体生命的渴望,然后才有灵魂生命的相爱,没有身体快乐便没有精神快乐,爱情失去身体快乐便不可能存在。这种生命的唯乐原则产生了人物的爱情法则,他们宁肯为身体快乐付出生命的代价,而在此过程中才能找到真正的爱。因此,那些人物格外注意性的肉体诱惑力和性的品质,比如处女之美被男女主人公都很看重。对于爱欲的充分发挥和对文明压抑的极端反抗,将使个体生命走向毁灭他人和毁灭自己,张资平情恋小说表现的文明与人性、现实与快乐、爱欲与文明的冲突,以主人公实行的唯乐原则与社会现实原则的冲突为标志,但基本倾向是表现人类文明原则所压抑的爱欲,而不是某个社会具体压抑的爱欲。因此,虽然他故事中的人物充满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他们自己品尝自己培植的生命苦果,但故事却看上去有些脱离当时的现实,人物这种爱欲与任何文明都具有的冲突关系遮蔽了具体的社会性。
(五)
对生命激情张资平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理性控制意识,但这种理性不是批判或歌颂的明确目标。
张资平的情恋小说表面上借理性与感性的冲突来完成故事,实质上这些故事倾向于理性,感性张扬只表现在具体细节和情景处理上,不表现在主题上,因此故事都是失败的恋情,而那些张扬性自由的新女性更是悲剧性的,人物不是制度的牺牲品和传统的现代悲剧,而是理性的悲剧和感性遭受压抑的悲剧,它们并不是简单地表现或等同于一个时代的观念和社会情恋关系的具体变化。
张资平对于爱欲的描写特色,在于将爱欲与文明冲突的生存困境书写出来,一方面描写了爱欲的充分发挥和爱欲对于文明的反抗,一方面又描写了对爱欲的理性压抑,是一种发挥爱欲与控制爱欲相悖交织的主题。这些故事,既表现了爱欲的自然本性,又表现了对这种自然本性极度释放的忏悔,因而人物大多是先表现出无所顾忌、不加控制的爱欲,然后又表现出礼俗或宗教对情恋的约束和控制。这里面表现了张资平一种隐晦的性态度:在表现爱欲与文明的两难取舍时,从根本上并不是要彻底地发挥人物的爱欲,而是表现爱欲的限度、表现爱欲的理性制约和文明压抑的必然性。故事的底层表明作者对于人物的爱欲放纵是欣赏的,承认其自然的合法性,但又顾虑其过度纵欲对文明的损毁,同时又碍于社会礼俗对个人爱欲的压制而不能完全彻底地对其加以张扬,于是就描写了这样一些对情欲先放纵再控制的故事。张资平对于情恋人物发挥爱欲有两个结局规定:一个是受理性控制而规规矩矩地沿着文明规范和社会理性生活下去。这种理性控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宗教理性,一种是中国传统的礼制理性。另一种结局,便是人物因极端纵容身体疾病或遭社会处罚而走向死亡,这是一种对于人的生欲和死欲与社会文明发展之间心理和生理关系的表达,实际上还是要表达对爱欲的适度控制。虽然人物有彻底发挥爱欲的表现,而最终这种彻底发挥爱欲的结果却是失败的和毁灭的。张资平情恋小说理性控制的特点是以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理性规范取代了东方礼制文明的理性秩序,要求宗教给予人类秩序一种理性控制,来代替礼崩乐坏的礼制文明,个体生命的肉体和精神的实在,转化为最终的无形者对生命的现实控制。张资平的情恋人物,并不追求宗教的天国幸福,而是追求神性的现实,只有神性秩序,才能使人们各守本份名位。于是,在张资平的情恋小说中,现代理性以宗教的形式出现,古典理性则以礼制传统出现。
来稿日期:1999年10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