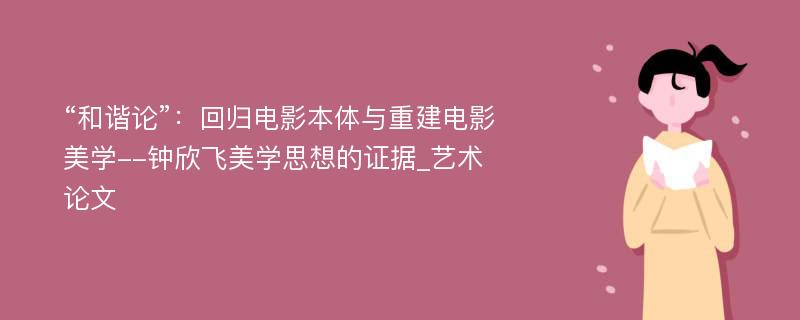
“和弦论”:回归电影本体,重构电影美学——钟惦棐美学思想疏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电影论文,本体论文,和弦论文,重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影坛,钟惦棐是一位深孚众望、成就卓著的文艺评论家、电影美学理论家,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电影和弦论”,①为中国新时期电影美学思想的重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钟惦棐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0年了,但他所提出的“电影和弦论”,今天读来依然充沛着理论的激情和新鲜的思想力量,对当代中国电影的创作实践及其产业改革的深化,仍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这是钟老留给我们的一份十分珍贵的电影美学思想遗产。
一、历劫重生:时代的昭示与美学的觉醒
1979年,与当时思想解放的主潮保持着时代的同步性,中国电影跨越了在“文革”后的两年徘徊,迎来了革故鼎新、文化重建的新时期。
文化重建的前提是: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最终结束了“左”的或极左的政治路线统治全党的历史,掀起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大潮,中华大地上骤然升起了民族复兴的曙光。人们以破除“现代迷信”和在1977年、1978年仍旧盛行着的“两个凡是”(所谓“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思想教条为前导,呼唤着人性的苏醒,呼唤着文化的重构,促成了电影思维冲破“政治本位论”的禁锢,迎来了电影艺术生产力的解放。
钟惦棐先生于1957年因《电影的锣鼓》一文陷于厄运而陆沉失语,积22年的思想沉淀,到1979年因幸逢盛世而重新命笔,形成一次历劫重生、文思泉涌般地喷薄而出,这就是他为《文学评论》杂志撰写的《电影文学断想》一文,全文共分八个段落,其中第六段的标题即为“和弦论”,也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他借用“和弦”这一音乐术语,②深刻地论述道:“用和弦代替单音,在电影题材内容上,样式以及片种上,从各个方面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甚至渴求,电影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正应该从这个根本意义上去理解它和把握它。这既符合电影艺术的特性,使电影文学家和观众都感到兴味,也是构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1]37
疏证“电影和弦论”人文思想的立足点,端在一个“和”字,这是我们中华文化传统里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孔子《论语》里曾说:“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篇)意思是以礼为本,形成的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其所贵者乃在于“和谐”。先王治国理政之道,也在于和谐,而且又是一种美的境界。钟惦棐提出的“电影和弦论”,正是汲取了“和为贵”这一中华文化的精粹资源,由此而在电影美学的重构上提升并拓展出两个方面的核心内容:其一,向“以政治统帅艺术”的“政治稀饭”模式挑战,反对“急功近利,要求电影为某些实际政治服务”的偏执,强调“电影必须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组成一个和弦。既不能全是‘最强音’,也不能全是最弱音;既不能全是长音,也不能全是短音。强弱长短是有机的配合,而不是机械的一致”,从而达成政治与艺术的和谐,如果“狭义地理解政治,也是狭义地理解文艺特别是电影,结果是对政治和文艺尤其是电影都无好处”。其二,倡导艺术民主,必须充分尊重、充分发扬电影的艺术特性,让电影回归自身艺术的本体,让许多有经验的艺术家得以尽情发挥自身创作的潜力和艺术个性,并引证列宁的读书经验和文化思想,指出,“人的精神领域如此广大!连列宁流放西伯利亚也携带着德国诗人歌德的作品《浮士德》”。进而强调说:“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须充分尊重艺术家的风格,而不是‘磨平’它。”
“电影和弦论”所期待于中国电影未来的,在钟老心目里,进入20世纪80年代,就电影艺术的内容而言,它势将渐渐洗去“浓郁的政治宣传色彩”,“势必从浮泛转向深邃,从狭窄走向宽舒”;而就电影艺术的风格、样式以及方法、体制而言,则势将在美学探求、美学创意上日渐趋向更丰富、更多样化,并以愈加民主的方式靠近广大观众。他还说:“我们肯定要吸取世界电影中的好传统和新成就,直至某些技法上的新东西。”[1]67,68-71
显而易见,“电影和弦论”并非什么天外飞来的异物,这恰恰是钟惦棐从自身个人政治命运的沉浮以及中国电影自1949年以来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思想结晶。应当特别强调的是,我们的电影理论界,似乎至今尚未清醒地领悟并肯定“电影和弦论”的理论开拓意义及其美学价值。
二、为民请命:以反潮流精神对当年的电影体制提出质疑
疏证“电影和弦论”的美学思想支点,可以清晰地追溯到早在1956年岁末敲响的《电影的锣鼓》。如果说《电影的锣鼓》的意义,在于一个“破”字,它第一个咬破了“政治本位论”的蚕茧,而咬茧者自身的政治蒙难及其悲壮性,则是被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其文化发展上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的;那么,文革之后“电影和弦论”的贡献,就是一个“立”字,要问“和弦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锣鼓”所鼓吹的核心论点在于:电影创作必须由“电影艺术特性”出发,并把列宁所批评的无视艺术特性的“政治稀饭”统统倒掉,而这却是当年尚未在美学上走出朦胧状态的钟惦棐所无力予以充分展开的。(即便是当年中国整个文化界也是不能的,这或许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不得不反思的所谓“中国特色”的历史处境)。
写《锣鼓》那一年,钟惦棐三十有七,正是血气方刚、挥斥方遒的年华。作为《锣鼓》的作者,他以反潮流精神为民请命、针砭电影时弊,质疑现存电影体制的问题,质疑电影事业主管当局的问题——一言以蔽之,“按其实践效果检验,它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性质是明显的”。[2]449
写作《锣鼓》一文,显然并非出于偶然或者“纯粹的个人动机”,而恰恰是事出有因、关涉当年整体的舆情局面的。
1956年11月14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短评:“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由此引出一场持续了三个月的热烈讨论,对电影事业的现状、领导电影的方法以及题材狭窄、故事雷同、内容概念化等创作问题展开了探讨。一些文化名人和电影艺术家也纷纷撰文并参与了讨论,如老舍的《救救电影》、吴永刚的《政治不能代替艺术》、孙瑜的《尊重电影的艺术传统》和石挥的《重视中国电影的传统》等等。
《电影的锣鼓》一文,由钟惦棐执笔,却以《文艺报》“本刊评论员”署名,刊出于同年12月15日出版的第23期,原是针对《文汇报》前一个月发起的这场关于电影的讨论,做出一种归纳和总结。该文提出的主要观点有如下四个方面:(1)重视票房价值,重视电影与观众的联系,“绝不可以把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工农兵电影’”(或只能描写工农兵),这是把党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针予以僵化、狭隘化和宗派主义化的解释,甚至割裂了中国电影的优秀传统;(2)充分尊重艺术家的风格和创作自由,改变以行政的方式领导创作和不适当地干涉创作,管理得太具体,太严,“都是不适宜于电影制作的”;(3)尊重中国电影的艺术传统,不应将过去的一些电影“统称为‘小资产阶级的电影’”。老舍先生的《救救电影》,“便说明了这些年来关起门来搞电影是行不通的”;(4)改善电影演员的工作,“他们在电影艺术干部中人数最多,问题积累得也多”。
这四个方面的问题,集中到一点上说,电影既然和群众有着最密切的联系,那么,“它的领导须注意符合电影创作和生产的规律。违背了这个规律,即不尊重列宁在另一个地方所说的:‘文学艺术最不能机械地平均、标准化,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上绝对必须保证个人创造性、个人爱好的广大空间,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大空间。’”[2]451
再需要追问的是,当年从《文汇报》的讨论到“电影锣鼓”的敲响,是不是无端而起、“空穴来风”呢?显然并非这样。历史地给予考察,笔者认为,这与当年由上而下所开启的一股文化开明和宽松的风气诚然是有关的。人所共知,毛泽东于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继又于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繁荣文学艺术、发展科学的指导方针;再后,于8月24日毛泽东在怀仁堂与部分音乐工作者谈话,涉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原则以及音乐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等广泛的学术话题。这期间,学术界就美学问题、音乐界就民族形式问题纷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而《文汇报》的讨论或者“电影的锣鼓”,则或许也都是由此而“风生水起”的吧。
今天,重读《电影的锣鼓》,钟惦棐作为一个年青而诚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那反潮流的精神、敢于针砭时弊的理论锐气,无疑是十分可贵并令人敬佩的。尽管“锣鼓”是从电影票房敲起来的,然而,其初衷和思考的出发点,或许正是为了响应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思想,即:坚持电影的艺术传统,尊重电影创作和生产的规律,以符合辩证法的方式在电影思维和电影美学层面上追求政治与艺术达于和谐。
三、坚守真理:一个年轻而诚实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生悖论
钟惦棐提出“电影和弦论”时,人届花甲,早已不再年轻,但作为他生命的再起搏,在他内心里却依然葆有着当年作为延安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可贵的激情和战斗的品格。钟惦棐的人生之路,是从“延安娃”到以革命为本色的青年战士,他的思想启蒙是在革命圣地延安,他的战士性格的锤炼,则是从抗日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的时代风云中走过来的,由此便铸就了他坚守真理、坚韧不拔、刚直不阿的品行。1919年,他诞生于四川小城江津,是一个银匠的儿子。读完中学后,从江津到了成都,十八岁时(1937年),他又从成都踏上了去延安的道路。1938年春,他从“抗大”毕业,正逢鲁迅艺术学院开办,便转入鲁艺美术系学习,一年后成为教学人员。正如他的自述:(在延安)“它使我生活在从来没有过的自由自在、丰衣足食,眼界日益开阔,知识日益丰富的理想国里。但战争和必须服从于战争的疲劳、走险和置生死于度外的思想素质,又成为生活中新的必然。”[1]418革命胜利进了城,在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北京,钟惦棐刚交而立之年,他自此便与电影结缘,工作则以电影为职。诚如他所作的自述:“我对它付出的,可谓是毕生精力——至少是我的文字生涯中的主要方面。我的命运、年华、健康和可用作思维的精力:即心之所系,气之所宗,命之所托,喜怒哀乐之所由生,也都在这里了。”继又就其工作岗位补充说,“从1951年我随周扬同志由文化部调中宣部,开始是分配在文艺处,处长是丁玲同志”。后来江青担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经她指定组成电影处的成员是袁水拍、黄钢和我。但袁、黄均未到职,电影处的日常工作便由我张罗(所谓副处长云云,是不确的)”。[3]由此可见,钟惦棐虽是普通工作人员,却是在中央主管政治宣传和电影的领导岗位上工作,日常所接触的无不与党的政策决策和舆论导向有关,这就磨砺了他的主流政治意识和社会学评价体系。钟老曾自谦地说,他只是个“电影社会学者”,“总是以社会学的角度看待电影艺术的发生、发展和作用的”,这应是实话实说的。
倘若再进一层对“电影和弦论”进行疏证,不能不说,透过个人与时代关系的角度来看,将不难发现“性格决定命运”的说法是有道理的。钟惦棐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在书斋或城市里成长的知识分子,他是在人民革命的烽火和熔炉里被铸造的年青而诚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五四”知识分子或作为进步文人的自由思想者显然是有区别的),在早于写《电影的锣鼓》一文的前三个来月,钟惦棐曾写过一篇题为《论电影指导思想中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其质疑现存电影体制的理论锋芒和概括力,显然更胜《锣鼓》一筹,因之便引起了主管文艺工作的某些中央负责同志的警觉和关注。该文当年未获发表的机会,后来在1983年编选《陆沉集》时收入书中。按该书的体例,每篇文章末尾都以括号注明原文刊载的出处,惟有这一篇的原注出处,竟被用一块小纸片粘贴上了。好在对着阳光,尚能辨认出原来所注的字迹,不妨转录如后:“注:这篇文章是钟惦棐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八月写成的,他本想交《人民日报》发表,并由此掀起电影问题的讨论。文章写好后,由《人民日报》打印分发周扬、林默涵同志,并由《人民日报》邀陈荒煤、黄钢等同志座谈,周扬、林默涵以及陈荒煤等同志都不同意他的论点,因而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后来发表的《电影的锣鼓》,其基本论点与此篇一致。”[2]447对于当事者或撰文者的钟惦棐来说,根本不曾料到这篇短短的文章竟惊动了这么几位大人物,并以“不同意”或不合时宜遭到否定,其分量可谓是“生命中难以承受的轻”。但是,盛年的钟惦棐对真理的坚持和执著,特别是他在延安养成的年青而诚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刚直不阿、不唯上、不唯书的战斗品格,使他终于不肯放弃自己的理论立场,于是,就针对《文汇报》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亲自赴上海进行社会调查,并登门访问了一些电影界的人士,还会同一些曾在《文汇报》上撰文发表言论的作者一起座谈(此举乃被意识形态主管当局定性为“煽风点火”)。回北京后,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论立场和观点,仍然以《论电影指导思想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为蓝本,将其中的主要观点全部纳入了《锣鼓》,而仅仅在行文上稍稍削弱其锋芒,去除了向上级进言、献策的口气。尽管如此,钟惦棐依旧未能逃离由这场“锣鼓”引致的灭顶之灾。
今天来看,钟惦棐或许出于政治上的天真,或许压根就没想过这场“锣鼓”竟会陷他于有口莫辩的政治困境而不复宁日,遭遇到一个年轻而诚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无可解脱的人生悖论。
试看《论电影指导思想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分列了三个小标题:
(一)关于“工农兵电影”
主要论点,已见诸前引的《锣鼓》一文,该文论述的焦点在于,“把党所规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针,错误地解释为‘工农兵电影’”,“在电影工作的实践中,由于指导思想的谬误,使电影的题材愈来愈窄狭”,并必将导致“否定人的精神生活的复杂性,需要的多样性”,而“艺术要求反映生活的丰富多彩,这种做法,则只能使它贫乏。使他们的文化生活单一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取消了他们的文化生活”。
(二)“传统”问题
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割裂电影传统,“不承认解放区以外的即国统区时期的电影”,属于“虚无主义的观点”,其危害甚大:(1)解放以前的影片很少看见了。不仅如此,今年在电影局的主持之下,还销毁了大量的解放以前的旧影片,其中还包括明星公司早期拍的影片《孤儿救祖记》;(2)对原在国统区工作的一些有经验的编剧、导演和演员重视不足,许多人长期没有戏演,没有事做;(3)不重视自己影片的民族风格,盲目地学习苏联。几年来除了翻译苏联的文章,在我国的电影理论建设上,可以说还是一张白纸;(4)关于中国电影历史的研究整理工作,几年来无人过问。对中国电影艺术家们在创作实践中的经验,未予认真的总结。
(三)关于组织电影创作及制片工作作风的问题
他说,“电影艺术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的姊妹艺术,便是它有着庞大的而且带有固定性的市场”,而“审查的层次过多,致使电影制片事业严重地脱离了市场的需要”,继而指出“用行政方法领导创作,用机关的方法领导生产”是不相宜的,更富于前瞻性地提出,“当前的问题即在于我们的制片方法被许许多多的成规束缚着。我们有电影局局长、有制片厂厂长,却没有制片家。而制片家是首先要考虑为观众服务的”。他最后则质疑说:“如果出片少、慢而又不好是社会主义的,那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呢?”[2]434-447
综而观之,钟惦棐一片拳拳之心,无不是出自对党的电影事业的真切而热诚的关注,甚至在今天来看,也还具有其不可替代的实践意义。譬如,我们真正懂市场、懂产业而具有开拓意识的电影制片家,究竟又有多少呢?!特别是,从《论电影指导思想中的几个问题》到《电影的锣鼓》再到在《电影文学断想》一文提出“电影和弦论”,时间跨度长达三十三年,三篇文章里都引证了列宁关于精神文化产品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论述,关于文学艺术绝对必须保证个人创造性的广大空间的思想,还有列宁在《做什么》一书中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只能来源于文化上的提高,而不需靠什么自发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政治稀饭”的经典性论述,这一切表明,钟惦棐正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为依据而撰文立说的,这也正是钟惦棐历经时间的冲击和洗涤,而在精神上却始终坚定不移并底气十足的原因所在。
在为《探索电影集》所写的序言中,他还别有深意地为我们叙说了这样一小段关于“芭蕉幼叶”的故事:“我在少年时代就曾惊异拱开‘三合土’而出的芭蕉幼叶——芭蕉幼叶其柔嫩远胜于丝绸,但它借造化之功,使光洁的路面为之皲裂,而后从缝隙中伸出头来。这一启示对我由‘格物’而‘致知’,也往往贯穿在我自己的生命历程之中。”[4]不妨将这段文字作为钟惦棐先生对自身人格的自况。这则文字,写于1986年5月22日,距先生人生的终结点,仅有十个月,每每读此,那片“芭蕉幼叶”便仿佛飘然如在眼前,让我们咀嚼着比“格物致知”更为深厚而温煦的人生意涵。转瞬间半个世纪过去,重读、重温钟惦棐先生的理论文字,特别是《电影的锣鼓》和《电影文学断想》,深感钟老的“电影和弦论”(还包括他近百万字的文艺和电影理论遗著),无不富于前瞻性地紧紧抓住了我们时代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核心观念的电影美学课题,这是一笔十分珍贵的思想财富,是需要我们潜心领会,认真予以疏证,并在我们今后的电影创作实践和电影产业改革的深化中不断地给以丰富、发展和光大的。
注释:
①引自钟惦棐《电影文学断想》一文,载于《文学评论》,1979年第4期,后收入《起搏书》,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5页。
②“和弦”条目:“‘和弦’作为一音乐术语,指的是‘三个以上不同的音,按一定的音程关系同时结合,即构成和弦,它是多声部音乐的基本素材。’”见《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