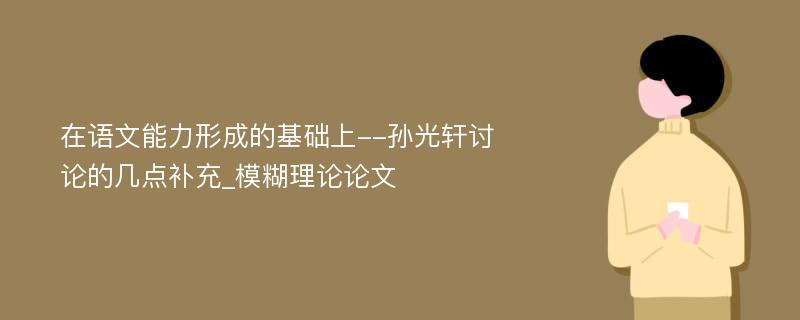
论语文能力形成的基础——对孙光萱论述的一些补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论述论文,能力论文,基础论文,孙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孙光萱先生在《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4 期发表了一篇颇具震撼力的文章:《论语文教学的误区》,提出了一个震聋发聩的问题:“语文教学高耗低效何时了”?我认为孙先生提出了当前中学语文教学中一些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孙先生论述语文教学的第一个误区是“片面理解知识和能力的关系。”认为语文学科有其特殊性,知识与能力的关系远比其它学科要来得复杂,因而不能象其它学科一样能以遵循“知识向能力转化”的普遍规律。那末如何来认识语文学科的特殊性、复杂性,如何遵循语文学科“知识向能力”转化的特殊规律呢?
我不惴浅陋,试图从语文能力形成之基础的角度,撰文参与孙先生提出的讨论。我认为形成语文能力的基础是学生的“语文素养结构”,它至少包括知识、经验和语感三个层次:
一、知识是形成能力的语文素养结构的初级层次
首先,我们有必要对知识的内涵与外延,有一个较明晰的认识。所谓知识,是人类对社会与自然界一切方面认识的概括和总结,而语文知识尽管不是概括和总结了社会与自然界的一切方面的认识,但也概括和总结了语文学科所涉及到的社会与自然的许多方面的认识。因此,知识就与人类的认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李晓明在《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一书中认为人类的认识活动中具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精确性和模糊性的特点,模糊性是绝对的、普遍的,而精确性则是相对的,是模糊性的特例和体现。二者作为对立的双方,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之中,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可以互为表现对方内容的手段,模糊思维方式可以达到精确表达的效果(注:参看李晓明:《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第一章
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 李晓明进一步引延到人类的两种知识形态。指出:罗素曾幽默地说过,知识是一个程度问题。而“知识能否表达和交流,这在很大范围内是个程度问题。按程度的高低区分,人类知识可分为“言传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即能清楚而明确表达的知识,和“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 )即默然不能表达的知识。人类每一现实认识结果都是这两类知识形态的混合物”(注:李晓明:《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第70-73页)。他进一步阐述说:(注:李晓明:《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第70-73页)
模糊不清的意会知识要比明晰可表达的言传知识更为基本。形象地说,意会知识就象场一样弥漫在人的意识活动中,是人类知识各层次融汇贯通,触类旁通的关键。言传知识则象粒子一样离散地存在于意识活动中,象网络一样把认识之网提擎起来。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前提。在一定条件下,不仅意会知识可以转化为言传知识,而且言传知识的发展又会促进意会知识的萌生、形成。需要强调的是,言传知识不等于精确认识,而且它决不是精确化认识的单纯产物。它自身也包括有模糊、不确定的因素和形式。模糊化认识也绝非仅仅产生意会知识。人的意会、顿悟能力也不意味是单纯的感觉、知觉表象等初等认识能力。相反,这种从整体上把握、领悟对象的能力,总是渗透着人类意识逻辑机制的影响。
我其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李晓明的阐释,是因为:一、李晓明从模糊性出发研究人类认识活动是符合客观认识规律的,是正确的;二、这一观点对于我要研讨的论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三、对于真正理解语文知识与语文能力的关系,确证语文知识对形成语文能力的语文素养结构具有明确的地位。
我以为,要正确理解语文知识与语文能力的关系,发挥语文知识对形成语文能力的基础因素作用,关键在于怎样认识语文知识。
有些同志将语文知识总结为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等的基本概念知识,也就是说纯然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因而要求学生精确地掌握,至少要能以言传。我以为这是一种偏颇,即只注意了相对精确化的认识方面,“言传知识”的方面,而忽视了绝对模糊性的认识方面,“意会知识”的方面。
诚然,我们讲语文知识对形成语文能力的基础因素作用,不可否认这些可以言传的、相对精确性的认识内容。但是学习这一方面知识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为了能以言传,能以进行所谓精确化(有的人转题为标准化)的考试吗?何况即使是这一类语言言传知识,也不是“等于精确认识”,“它自身也包括有模糊、不确定的因素和形式”。因此,对“言传知识”的认识,不在于如何掌握语言的概念,言者在于传也,在于如何运用的问题。所以章熊先生在《语文教学沉思录》中说的“准确地说,语文课文所涉及的,不是‘语言’,而是‘语言的运用’。没有注意到二者的区分,是当前语文教学的弊病之一。”这一论断其所以十分正确,就在于对“言传知识”,对语文教学内容的相对精确性有一个正确的清醒的认识。诚如孙光萱先生所说的,“如果要学生象研究语言一样来学习,那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弊病”。我以为最大的弊病在于把语文知识绝对精确化,去灌输给学生以形成单一的语言知识网络系统,摒弃了如何进行语言运用,形成基本的技能。这样也就失去了这一类知识作为语文能力形成的基础作用。其实所谓“双基”就是一“基”: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等这些相对精确可能言传的知识,从需要掌握概念和意义的角度言,是为基本知识;从需要运用的角度言,它又是基本技能。在教学中又太看重概念的掌握(甚至要精确化、标准化),而忽视与之相随的技能运用。因此,其基础地位就并不能具备,所谓转化为能力,也只是一句空话。
同时,教师们并没有认识到语文知识还有另外一种,即绝对模糊认知的、只能意会的知识。因为我们的课本中编选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文学作品,以及另外许多优秀的文章作品,给学生能以感知把握的是大量的“意会知识”。
李晓明说,人类认识中的模糊性是绝对的,即使言传知识,也不等于精确认识,不是精确化认识的单纯产物,它自身也包括有模糊,不确定的因素和形成。语言材料、语文课文,尤其表现出这一特点。因此,我们有必要明晰“意会知识”,或者说模糊性认识在语文中的巨大的量。
例如词语这一语言现象的教学,也许是语文教学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很多教师从语言的工具性功能出发,总以为解词释义越精确越好。然而大量词语本身就是多义的,模糊性的。从语文学角度看,形容词、概数词、程度副词以及部分名词,都具有模糊性。如“老年、中年、青年”、“早晨、中午、夜间”,这些词所指称的客观对象,其实就难划出严格的界限。受形容词、程度副词修饰和限制的短语,如“美丽的小屋”、“繁华的都市”、“优美的音乐”、“服用少量药物”、“朝阳渐渐地升起”等等,无不具有模糊色彩,无不是只能意会的语言现象,因而在这些语言的运用上只能去意会,去模糊体验与感受。语言学家琼斯指出:“我们大家,包括那些追求‘精确无误’的人,在说话和写作时往使用不精确的、模糊的,难于下定义的术语和原则”(注:琼斯:《音位的历史和意义》)。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文中就曾对资本家利用“夜间”一词的模糊性而任意延长夜间工作时间剥削工人的罪恶进行过揭露。因此,在语言中“明确的只是极端的情况。过渡的现象在其本源中,即说话人的意识中原本是游移不定的。正是这些模糊的、游移不定的现象应更多地引起语言专家的注意”(注:谢尔巴:《语言学和语言学论文选》)。在中学语文教学中,何止词语的表现如此,所谓字、词、句、篇等等其实只有相对的精确性,只是部分的“言传知识”。而绝对是模糊性,大量的是“意会知识”。象“庄严”、“庄重”、“端庄”这样的近义词教学,有的教师只在字面上去抠每个词的词义,然后孤零零地用别的模糊性词义去逐个作注,结果费力不讨好,学生如坠五里雾中。教师越望教得所谓精确,企期学生能以言传,结果是学生越学越觉胡涂,要言传则只能死记硬背,使只能模糊性把握的意会知识,变成既不能意会,也不能真正言传的东西。考试中尤其在精确划一标准答题的规范下,变成了玩弄语言游戏的一片“题海”,不仅学生负担沉重,而且更在于发展不了能力。因为失去了知识的基础作用,知识与能力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距离越来越大,又何有“转化”可言之?
至于以整体成篇的言语形式而存在的模糊性知识,特别是占课文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文学作品中的知识,(无论包孕其中的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等等所谓基础知识,还是蕴含其中的主旨,意蕴、情感、象征等等只能体味、领悟、意会的知识内容)已经不是人们在对对象类属边界和性态的认识中所产生的那种模糊性、不确定性了,而且作者刻意追求的一种审美表现性的东西,即所谓“模糊美”了。形成于世纪60年代的德国康士坦茨学派的“接受美学”理论,强调接受者能动参与创作从而使作品获得最后完成。其代表人物伊瑟尔认为文学本文所使作用的语言是一种“具有审美功能的表现性语言”,其中包含了许多“未定点”(不确定性)和“空白”,这意味着文学作品在描写某种对象或对象的环境时,无法说明或没有说明它究竟具有或不具有某种特性。他认为“未定点”和“空白”构成了文学本文的基本结构,即“本文的召唤结构”,这就使文学本文产生一种“活力性”,召唤和吸引读者介入作品中去,为他们提供充分阐释和想象的自由。另一方面,这些表现性的语言,在另一个学派——格式塔心理学家们看来,“一块陡峭的岩石、一棵垂柳、落日的余晖、墙上的裂缝、飘零的落叶、一汪清泉、甚至一条抽象的线条、一片孤立的色彩或是银幕上起舞的抽象形状——都和人体具有同样的表现性(注:见《西方文论选》)”。这就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语言本身不过是符号、载体,而它所含寓的意蕴,有许多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语文课文因其大量编选了“文质兼美”的文学作品,都是些具有表现性的语言组合,它与接受主体心理的同具的表现性相合相契,则需要意会。同时,其中的“未定点”和“空白”处比比皆是。例如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在写到为五位青年作家被捕而焦虑不安,突然获悉他们已被国民党秘密枪杀时,作者只用了一句话,两个标点:“原来如此!……”这一空白处包含多少复杂的、难以言传的、浓缩了多少情感的内容,又如何去精确言传呢?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在虚实相生中亦有许多“未定点”和“空白”,实写“胡天八月即飞雪”之后,虚出一片春意:“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借用错觉,给人“示定点”,不仅有雪景的瑰丽,更有对明媚春光的联想空间,最后写“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这一个“空”字,留下一个环境的空白,联想起二人的惜别,想象着诗人的怅然意绪,其实是只能意会的场境,只能体悟的情感。美国短篇小说之王欧·亨利的《警察和赞美诗》,法国短篇小说巨匠莫泊桑的《项链》的结尾都出人意料,奇峰突兀,留下令人寻味的“空白”,究竟“小偷”苏比面对警察是什么神态?有些什么心理活动,玛蒂尔德得知丢失的项链是只值五百法郎的假货,对于10年的辛劳。她将作何想?她会作何态?我们能精确言传吗?只能是模糊意会。而指导学生去意会的也不仅是其主旨的表现、意蕴的含寓,而且还诸如相对精确的文章作品的技法等写作知识,文章文学知识。接受者(读者)的能动参与,体味、领悟、意会,就有可能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在现代读者眼中的林妹妹,“恐怕是剪短发,穿印度绸衫的,消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别的什么模样”。
因此,语文知识的认知的模糊性是绝对的、大量的,而精确性是相对的、部分的。“言传知识”与“意会知识”两种类型的知识构成了语文知识的真正完整的系统。只追求所谓精确的、言传的知识,尤其要求在语言概念上去精确把握,进行标准化考试,自然与语文能力的形成发生了偏差,不仅不能对应而构成发展层次,而且更难能转化。只有认识到语言的绝对的模糊性,掌握相应的“意会知识”,二者相辅相成,才成为了发展能力的基础。
而且我认为“语文知识转化为语文能力”这一命题并没有错,单纯的“转”,似乎是很难的,诚如孙先生所言,语文有其特殊性,与数、理、化等其他学科不同。而其特殊性更在于语文知识的认知过程的绝对的、大量的模糊性,即使相对精确的东西也有模糊的因素和形式。所以需要“化”。“转化”的过程即是章熊先生所说的“语言运用”过程,在正确的读写听说的语言技能训练过程中逐渐形成读写听说的语文基本能力。
所以,语文知识(“言传知识”和“意会知识”的综合),应该是语文能力形成的基础因素之一。不过它还不能单一地转化为语文能力。它需要与经验(生活的与阅读的经验)以及对语言的情绪情感性感受领悟(语感)共同构成语文的基本素养结构,才能形成为语文能力。知识的掌握还只是语文素养结构的初级层次。
二、生活的与阅读的经验,是形成语文素养结构的中级层次
光靠课堂内的知识传授与掌握,即使具有了某些方面的技能,诸如读、写、听、说的技能,还是难以形成很好的语文能力的,课内的教学,只能说老师以一些例子(叶圣陶先生就说过课文不过是例子),教给学生掌握了基本的语文技能。即使转化、发展为语文基本能力,那速度也是缓慢的,程度也是有限的。
很多人把技能与能力视为一体,我以为这二者是有区别的,否则为什么要用两个词来表达?两个语词表达的就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技能是一种脑力作用下的以手的动作为基本特征的技巧行为;而能力则是指个人顺利完成某项活动的一种本领和与之相关的诸种心理因素的综合。正如一个木匠师傅和它的徒弟一样,木匠具有了建造房屋、设计打造家具等的能力,而徒弟却只具有锯、刨、砍、削等的技能,虽然他也能象师傅那样锯、刨、砍、削(尽管水平还不如师傅),但还只能说他有了一定的技能,大概要真正满师之后,他才具有了木工的能力。
因此,语文能力的形成,光靠课内教学所掌握的知识(无论言传知识还是意会知识)还只能在运用角度言具有了基本的技能,他们还正如木匠的徒弟。因而课外语文学习环境中的直接生活经验与阅读(包括欣赏等)经验,是形成语文能力的又一重要基础因素。所以许多有识之士提出“大语文教育”观念,是十分有见地的,他们看到的是问题的实质。
首先是直接的生活经验,不仅在于增加了生活阅历,更在这些阅历对于学生意会大量的语文模糊性知识,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孙光萱先生在其洋洋大论中阐述知识与能力的关系时指出:很多情况下常常表现为“能力在先,知识在后”,譬如儿童时期对母语掌握(尤其表现在听与说)的“语言习得”,并且这种“语言习得”贯穿在人之一生。这恰恰说明直接生活经验对于语文能力形成的重要作用。对于语文来说,无论“习得”还是“学得”,更多地还得益于生活经验的积累,这似乎是个不争的事实。孙先生举幼儿园小朋支能将苹果比之于自己的脸庞,将吃着的月饼比之于天上明媚圆润的月亮,就是生活经验甚至某种审美经验的萌芽。高玉宝写其自传体小说《高玉宝》时,就完全是凭生活的经验,审美的经验(爱憎明显地表露其中)来写出的。当时不要说他没有具有许多相对精确的能以言传的语文知识,甚至连某些技能都还未真正具备,譬如许多字他便不会写,而以图形代之。只读过三年书的高尔基,并非先掌握了系统的相对精确的俄语言传知识才具有了写作的能力的,他是完全在生活的“大学”里习得的。其过程、恐怕较多地是在对生活经验过的许多模糊性知识认识的体悟、意会中形成了能力。
所以,伟大的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特别重视学生这种生活的、审美的经验的获得,他一周两次把学生带到野外去,到“词的源泉”去旅行,他把这称之为“蓝天下的学校”、“快乐学校”,他曾说:
宁静的夏夜拂晓,我跟孩子们来到池塘边。印入我们眼帘的是朝霞那令人惊叹的美。于是孩子们感觉和体味到朝霞、破晓、闪烁、天涯这些词在感情色彩上的细微差别。我把一个就在这里产生的童话讲给他们听:有个勇士把我们在东边看到的那片田野种满了罂粟……每个孩子都感受到一种无可比拟的兴致;语言此刻以它那异常温柔而优雅的生命力活跃在儿童心灵中;语言越是深深地鼓舞和激励起幼年人的兴致,他的头脑对周围世界和教师话语的含义就越敏感,——千百次的观察确证了这一点。(注:(苏)苏霍姆林斯基:《帕夫雷什中学》第425页)
在苏霍姆林斯基那里,对生活的直接观察活动充满了情趣,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致,不仅体验到生活的经验,更在于获得了美感经验。教师并没有要求学生对诸如“朝霞”、“破晓”等语词作精确的、标准化的言传,而是去“感觉和体味词在感情色彩上的细微差别”,去意会那模糊美,从而转化为能力。
在“大语文教育”观念指导下,现在很多语文教师也很重视课外语文教育环境了,通过观察、调查、参观、采访等直接感知活动去获取生活的、审美的经验,因而感受到这些活动对获取经验转化能力的巨大作用。但是,现在仍然有很多学校,为应付中考,高考,将学生关在高墙之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教科书”,把学生的悟性淹没在“题海”之中。所以我们要以苏霍姆林斯基的话来大声疾呼:“不要因教室的一扇门而把学生与世界隔绝开来”!
人们在对对象的感知时,总是用所获得的知识和以往的经验来理解所感知的对象的,孔子曾形象地喻示学生:“不观于高崖,何以知颠坠之患;不临于深渊,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观于海上,何以知风波之患。”(注:见《说苑·杂言》)生活的、审美的经验,可以使学生对知识特别是意会的模糊性语文知识的理解、体悟加深,从而形成向语文能力转化的基础。问题是我们花了大量(甚至是绝大量的)时间消耗在语言知识的所谓精确性解释上,把语文教学变成了语言学教学,而只取少量时间(有的甚至没有时间)去获取生活的,审美的经验,象苏霍姆林斯基那样一周至少两次把学生带入“蓝天下的学校”者,恐怕是凤毛麟角。又如何谈得上知识向能力的真正转化并得以形成基本的能力呢?
其次是课外阅读经验。几乎每一个语文老师都感觉得到,那些语文成绩好,具备了一定语文能力的学生,无一例外地醉心于课外阅读为主体的其它语文教学活动,包括艺术欣赏、各种竞赛、演练课本剧、编班报,写日记等等活动。其中阅读课外书籍,对学生语文能力特别是读写能力的形成具有无可争议的作用。
学生对课外阅读有着格外的兴趣,因为课外阅读中,至少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独”,可以独立自主,自由选择,不受时空限制,也少受别人(包括教师、家长)限制,二是“趣”,指内容有情趣,个人有兴趣;三是“活”,灵活机动的方式,活泼活跃的方法;四是“广”,广泛涉猎,发展前景广阔;五是“新”,内容新鲜,感受新奇;六是“效”有积极的效能、效益和效果。这就为学生获取知识经验,发展而为能力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特别是对课外阅读的情趣,远比课内教学中来得深,来得大。而且儿童、青少年的阅读兴趣,各个不同年龄段有其各自的特点。据心理学研究表明,大致可分为六个发展的阶段:
第一阶段(4-6岁):绘画期
第二阶段(6-8岁):传说期
第三阶段(8-10岁):童话期
第四阶段(10-15岁):故事期
第五阶段(15-17岁):文学期
第六阶段(17-):思想期(注:见《个性心理学》)
中学生,恰好处在第四到第六阶段,这时学生在课外阅读中,会自觉地(多数是不自觉地)运用课文这个例子,运用语文知识尤其是意会知识,去体悟、理解所读的书籍内容,不仅间接获取生活经验,而且更在于获取直接的知识经验,使转化为能力的能量非常巨大,并且是在潜移默化的转化过程中。
而且,中学生课外阅读的量是十分惊人的,据有人抽样调查发现:初一学生在一学期内所读各种教科书共约70万字,读课外书籍350 万到700万字,是教科书的5至10倍; 高一学生一学期内所读各种教科书130万字,读课外书400万至1000万字。 (注:段宏谦:《农村中学要重视课外阅读》载《语文教学通讯》 1986年第6 期)如果把上述数字各乘以6,则初中阶段可读课外书2100万字至4200万字, 高中阶段可读课外书2400万字至6000万字。这个调查结果十分令人惊奇,也十分令人鼓舞。如此大量的课外阅读如能是每个学生都拥有,则中学生的阅读经验何等丰富,转化为语文能力的基础何其坚实!
我不怀疑这个调查结果的真实可靠。但以为中学生的课外阅读至少在如下方面还有距离:一是广大农村中学,由于客观条件所限(例如书源之限即购书资金之限),大多达不到这个量;二是在中考、高考指挥捧下,即使有条件的学校的学生也受到时间所限(沉入“题海”,没时间阅读)与人为之限(大部分家长包括学校一些领导及教师认为学生未务正业而限制学生阅读课外书籍),没能达到那个量;三是能达到上述量的一些学校的学生,缺乏教师的必要指导,过分放任自流,对课外书好坏不论,良莠齐阅,造成有量而质劣。真正有量有质者,恐怕还是少数。
如果我们能依据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表现、情趣特点,真正只将课文作为例子,引到课外,组织指导适当量的高质量阅读。则学生间接得到的生活经验、审美经验与阅读经验将极为丰富,不仅加强了对语文知识的学习,可提高课堂学习质量,而且更在于与直接获得的经验相合,构成语文素养结构的中级层次,奠定起转化为语文能力的坚实基础来。
三、“语感”是形成能力的语文素养结构的高级层次
孙光萱先生在论及片面理解知识与能力关系的误区时也提到了“语感”问题,诚如孙先生所言,如今“语感”在语文教学中是个热门话题。我以为,“语感”问题不仅应该是一个不应忽视、不应轻描淡写的热门话题,而且是正确理解知识与能力关系的关键话题,我甚至将其归之于构成语文素结构的高级层次,它对形成语文能力具有重要的基础因素作用。
“语感”之为热门话题,首先表现在对其概念的解释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致不下如此五种;(1)语感是对语言文字的一种感觉; (2)语感是对语言文字的一种感应;(3)语感是对语言文字的一种感知;(4)语感是对文章中语言文字的一种感受;(5)语感是对文章中语言文字的一种直觉感悟。或许还可以归出几类,有的概念甚至下得玄,转了许多个弯,最后仍不得要领。我基本上同意第4和第5种解释。“语感”应该说是一个复合名词,“语”指“语言文字”,尤其指形成文章作品并表达一定思想内容情感意绪的语言文字,这大概没有分歧;关键是对“感”的理解,说是“感觉”、“感知”、“感应”似乎都不够恰当,而应该指“直觉领悟”与“感受”为宜。我认为“语感”是指对语言文字的一种情绪情感性的直觉领悟与感受。它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语感”是指对所诉诸视觉和听觉的言语(包括口头语与书面语)的意义(包括思想、意绪及某种情感等)的领悟与感受;而狭义的指阅读中对书面语言的直觉领悟与感受。不论广义或狭义,均带有一定的情绪情感性。语文教学中主要谈的是狭义,但也不排斥“听”的语感。
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认识,语感是由语言文字引起的复杂心理过程,包括感觉、知觉、记忆、联想、思维、情绪、情感等许多心理因素参与,因而起到一种综合性作用,尤其要综合所学得的知识(特别是语文意会知识)和所获得的经验(无论生活经验还是阅读经验),在许多心理因素参与的作用下,去进行语言文字的直觉领悟与感受。直觉领悟需要感知觉、记忆、联想、思维等认识心理因素的参与;感受则必有情绪情感等意向心理因素的参与。其具体过程是怎样的呢?我以为可以概述为“认读——理解——领悟——感受”的过程。我们说语言文字不过是符号而已,但这些符号一进入读者的视觉,语感活动便开始了:首先是“认读”这些符号,然后“理解”这些符号的一般含义。这可以说是“语感”的初级阶段、基础阶段。一般的语文教学就是使学生停留在对语言的这种一般意义的感知上,这还不能称之为“语感”,还须更进一步,必须“领悟”语言文学的深层隐含意义(不仅在可以言传的语言基本知识意义,更在意会字里行间的“暗示”意义即语境意义),最后深入“感受”语言文字所蕴蓄的情绪情感感性意义(在意会的基础上的情绪情感性深入)即作者的原情原意。不难看出这种综合过程所处的高层次,一方面,它需要运用相对的精确的言传知识以及绝对模糊的意知识;另一方面又有长期的生活经验与阅读经验参与其中。这样,“语感”就不再是不可捉摸的东西,也不再纯然是古人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现”的简单重复的语言感性训练,而是建立在一定程度的语文言传知识和意会知识基础之上的、伴有浓厚的经验色彩和相当理性把握的语言直觉领悟、感受形式,这一形式构成了语文素养结构的高级层次,对语文能力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
事实上,许多语文教育界的前辈大师,都有十分重视“语感”对能力形成的作用的。夏丐尊先生曾谈到“国文科教授上的一个信念即传染语感于学生”,他解释说:“一般作教师的……对于文字应有灵敏的感觉。姑且名这感觉为‘语感’。在‘语感’敏锐的人心里,‘赤’不能只解作‘红色’,‘夜’不能只解作‘昼’的反对吧。……见了‘新绿’二字,就会感到希望焕然的造化之工,少年的气概等说不尽的情趣。见了‘落叶’二字,就会感到无常、寂寥等说不尽的诗味吧”(注:转引自周振甫:《夏丐尊谈中学语文教学》载《中学语文教学》 1986年第6期)。尽管夏先生说语感是教师对文字应有的灵敏的感觉, 但他所阐述的是语言文字使人感到的不尽的“情趣”与“诗味”,就不是指心理学上的对事物个别属性反映的感觉的意义了,而是指特殊的知觉形式——带有主观情绪情感性感受心理和直觉领悟心理了。“新绿”、“落叶”等作为语言文字,表面上不过是种种符号形式,但却给人种种“情趣”或“诗味”,实际上是语言文字蕴含的种种神韵、种种意绪情感因素。它们实际上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能模糊体悟,不能精确说明的,而要深入理解,尤其需要生活的与阅读的经验。知识与经验的结合,在情绪情感作用下,去直觉领悟和感受,形成这种种“情趣”与“诗味”的语感体味,潜移默化而为语文能力。所以,如果把语文教学变为纯语言符号教学或对语言符号作出概念解释的语言学教学,恐怕是难以转化为能力的。叶圣陶先生说:“凡是出色的文艺作品,语言文字必须是作者有趣的最贴切的符号”,“读者若不能透彻地了解语言文字的意义和情味,那就只看见徒有迹象的死板板的符号,怎么能接近作者的旨趣呢?”(注:《叶圣陶语文教学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0年版)叶先生其实说得很明白:语言符号不是死板板的东西,它是有趣的、最贴切的表现意义与情味,传达作者旨趣的符号,因而需在训练语感,对语言文字的情味、诗意、旨趣等等直觉领悟与感受。它不同于反映事物表象属性的感知觉,而是在瞬间调动起头脑中所有的潜知,跳过许多中间环节,直接从整体上迅速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本质与内涵的高级认知形式,是感性、知性与理性的融合,具有直接性、整体性、敏捷性、深刻性的领悟,同时融汇着情绪感性的感受。所以叶圣陶先生强调说:“文字语言的训练,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训练语感”(注:《叶圣陶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年版),吕叔湘先生也强调过:“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语感能力。”(注:《学习语法培养语感——访吕叔湘先生》载《语文学习》 1985年第1 期)因为语感既综合知识与经验,又调动起相应的心理因素,最终与知识和经验一起,构成语文素养结构,而转化为语文能力。
但有一点我们还得加以补充。我们平时说“语感”,总是把“语感”与“语感能力”合之一起。我认为还有必要作出区分。“语感”是一个动态心理过程;而“语感能力”是相对静态的心理能力。它是长期规范的语文知识运用和语言文字训练中养成的一种带有浓厚经验色彩的能以直接迅速地直觉领悟、感受语言文字意义的能力。它既包括在良好的语言环境中反复运用语言而不自觉地积累形成的良好语言习惯,又包括平时的语文学习中自觉运用语文知识(以课文为例子的无论言传的或是意会知识)来分析而形成的语言修养,这些习惯与修养又有经验的融合。“语感力”的形成又包括了语感训练的动态过程。因而语感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读的速度与质量,也直接影响到写作能力,与口头表达也不无关系。因而语感能力近似于语文素养结构。所以说有了这种能力,离语文能力的形成恐怕只是一步之遥了。
综上所述,孙光萱先生的文章触发了我对语文教学误区的深入思考,因而不揣浅陋,试图从理论上提出语言素养结构作为奠定语文能力转化基础的观点,这种知识、经验、语感的相连相贯相辅相成的三层次说纯属一孔之见,一家之言,未必能得到孙先生及其他大家的首肯,但愿以此就教并参与孙先生发起的讨论,集思广益,或可探路,也未可知。
责任编辑注:孙光萱同志的文章见本专题1998年第2期4~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