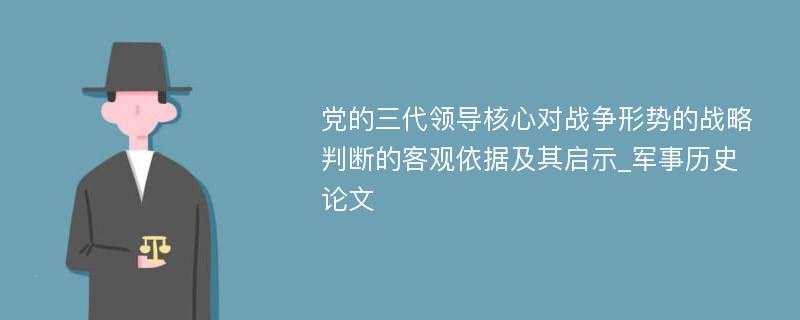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关于战争局势战略判断的客观依据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代论文,局势论文,启示论文,客观论文,领导核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国后,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都对世界大战和针对我国的全面战争或局部战争作了战略判断,为我国制定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发展战略和外交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50-70年代,毛泽东同志认为,世界发展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世界上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制约战争的因素有所增长,世界战争有可能爆发,也可能不爆发,但爆发的可能性更大,应把战争准备的着眼点放在如何对付帝国主义的大规模入侵和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上。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认真分析国际局势发展变化的新情况,改变了“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观点,提出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只要工作做得好,世界大战是可以延缓、可以避免的。同时强调指出,我们已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时期,但对战争不能掉以轻心,要始终保持警惕。
从80年代末至今,江泽民同志始终高度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多次对战争局势作出判断,总的认为,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世界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但是天下并不太平,形成了“大战不打,小战不断”的局面。今后较长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虽然新的世界大战和针对我国的全面战争在较长时期内打不起来,但诱发局部战争、武装冲突和国内动乱的因素仍然存在;虽然我国目前安全环境面临的军事威胁是潜在性的,但如果情况有变化,潜在的威胁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存在。
综上可见,我党三代领导核心对战争局势的判断是不同的。他们之所以对战争局势作出了不同的判断,与主观因素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他们所处的社会背景发生了变化。
(一)和平力量与战争力量的消长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十多年里,虽然没有爆发新的世界大战,但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连绵不断,给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那时爆发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比较大。
进入60年代特别是70年代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全球关注的主题。世界人民特别是各国政府的有识之士都在积极行动、思考对策,为寻求解决冲突与对抗、危机与贫困问题而努力,出现了和平力量增长大于战争力量增长的好势头。厌恶战争、向往和平、促进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时代潮流。以地区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为例:80年代全世界共爆发各种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26次,比60、70年代分别下降了54%和38%,且规模缩小、强度降低。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一个动荡、分化、改组和加速向多极化发展的新时期。求和平、求稳定、求发展,已经成为国际形势的主流。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力量正在壮大。一些地区性大国和区域性集团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切都有利于遏制战争。但是,由于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加激烈,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已上升为首要因素。当然,地缘政治、军事安全、意识形态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起相当大的作用。尤其是两极格局解体后,世界力量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使西方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干涉别国内政,导致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内在矛盾激化,不稳定因素增加。据统计,1990-1995年6年中,全世界共发生各种规模的冲突达205场次,年均34场次,新发生的共有65场次,年均11场次。不论年均拥有的场次,还是年均新发生的场次,均超过两极格局时期的程度。
(二)世界战争的主要危险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一直是世界战争的最主要的危险。他们推行霸权主义政策,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军备竞赛。为了争夺核优势和常规优势,双方你争我夺,使军备竞争持续发展,不断升级。美苏的军费开支约占全世界军费总数的60%。他们大力发展核武器,并维持着一支具有全球干预能力的军事力量,美苏的军备竞赛恶化了国际局势,而且有一触即发的危险,对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70年代末,特别进入80年代后,世界战争的危险性发生转机,那就是美苏的核力量相对平衡,起到了制约核战争爆发的作用。80年代初,美有核弹头9400个,总当量40亿吨;苏联有核弹头7000个,总当量57亿吨。这些核武器占当时全世界核武器总量的90%以上,可以把地球摧毁若干次。由于两个超级大国谁都不具备先发制人并一举摧毁对方全部核力量的能力,而谁都具备了实施有效还击的能力,结果形成两国核力量都很强,但谁也没有优势,谁也不敢妄动的局面。而这期间,中国等一些国家,从打破核垄断、维护本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出发,也研制了核武器,并且确实起到了威慑和遏制霸权主义侵略、扩张的作用。
两极格局解体后,过去那种一触即发的世界大战危险消除,但是战争的根源并没有消除,特别是失去主要对手的新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呈扩张之势。霸权与反霸权、强权与反强权的矛盾和斗争将长期存在,并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用“文”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就必然用“武”的办法解决,以致武装冲突增多。
(三)帝国主义征服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式不同
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帝国主义妄图以武力征服社会主义国家,把共产主义从地球上抹掉。1950年,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打的是中国的“主意”;1965年,美帝国主义逐步扩大侵越战争,公然宣布把中国当作主要敌人,声称“存在着同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但是,帝国主义的多次图谋都以失败而告终。
从70年代初开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绝对对立的状态逐步得以缓解,如中美、中日关系“解冻”。进入80年代,东西方相互交往和联系越来越多。面对现实,几个“主宰”世界的资本主义大国不得不承认:历史的较量已经证明,靠武力不可能消灭社会主义,要战胜社会主义国家,只能与之共处竞争,以和平方式进行综合实力的较量。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一方面加紧“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通过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西化、分化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又以“全球领导者”自居,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名,采用各种手段,其中包括干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以期达到最终征服之目的。
(四)我国领土、领海的“稳定性”不同
这方面有台湾、南沙、钓鱼岛、中印边境和中苏边境争端问题,也有新疆、西藏存在的不稳定因素问题,其中主要是台湾、南沙和钓鱼岛问题。
台湾问题。自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复职后,蒋氏父子一直把“军事反攻大陆”作为首要之举。为此,重整战败逃台的60余万军队,重建国民党组织体系和统治机构,竭力进行反共思想灌输,为其“反共复国”服务。在军事政策上,维持渡海登陆作战方针,并制订了“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军事反攻计划。这一计划落空后,又实施了“王师一、二、三号”、“棉湖一、二号”等反攻计划,均以失败而告终。从1949年10月1日至1970年2月10日,蒋军先后派出无数次飞机和舰只对大陆进行骚扰侦察,仅被我击落的飞机就有96架,击沉、炸毁军舰5艘。在这期间,台湾与美国签订了针对大陆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美国还向台湾提供了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加剧了两岸危机。
70-80年代,台湾局势相对稳定。除了两岸军事上没有“升温”外,还有一个稳定的因素,就是蒋氏父子没搞“台独”,继续坚持了“一个中国”的立场。台湾与大陆处于分离状态以来,台湾几任领导人都面临着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那就是能否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台湾前两任领导人蒋介石、蒋经国,曾顽固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立场,严重阻碍和迟滞了两岸实现统一的历史进程。但从另一方面看,他们不同意美国总统杜鲁门等提出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当时蒋介石称,大陆、台湾都是中国领土,割裂曲解台湾的地位是别有用心的,对西方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一直保持警觉。譬如1957年,美国加紧实施“两个中国‘一中一台’阴谋”,逼蒋介石“划峡而治”,蒋没有接受,美蒋之间的矛盾一度有所发展。70-80年代蒋氏父子仍反对“台湾独立运动”,严厉打击“台独”,尽管蒋氏父子“一个中国”的立场与我国政府“一个中国”的立场有根本不同,但在客观上维系了中国领土的完整,减少了金瓯之缺的可能。
进入90年代,李登辉上台。他加紧推行实质外交,把国际空间当作谋取“台湾实质独立”,与中国政府进行较量的主要场所,图谋加入联合国,策划“两个中国”、“一中一台”阴谋,“台独”势力不断蔓延。台湾当局调整军事战略方针,撤换外省籍将领,投入大量军费,从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购买了新式装备,同时研制包括中程导弹、防空导弹、IDF战斗机在内的“二代武器”。到2000年,武器装备将全部更新完毕,建成由“跨世纪”海军,装甲化、立体化、电子化、自动化”陆军,以及具有强大防空吓阻能力的空军组成的具备世界先进水平的军备,军事抗衡实力将大大增强。加之有他国插手的影子,使台湾问题更加复杂化。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关切。
南沙问题。我南海周边部分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尤其是乘我国“十年动乱”之机,利用地缘优势,非法侵占了我南沙群岛许多岛礁。特别是自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交联合国讨论开始,这些国家争先恐后地以单方或双方“声明”、“公告”等方式,宣布其领海、毗连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近几年,他们扩张“海洋国土”更加有恃无恐,并且已经从掠夺开发中得到了巨大利益。这些国家采取“先占后采”的海洋发展战略,既保护家门口的海洋资源,又将目光放在争夺更广阔的海域,并正在加速建设一支精干、机动性强和装备现代化的海上力量,保卫扩张的“海洋国土”。
钓鱼岛问题。钓鱼岛(含赤尾屿、黄尾屿等七个岛礁)历来是中国的领土,总计面积6.3平方公里,早在明代时期已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日本自甲午战争侵占了中国的钓鱼岛后,宣称是“无主地”先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钓鱼岛被美军占领。到1971年,美军把冲绳岛归还给日本之时,连同所占领的钓鱼岛与赤尾、黄尾等七个岛屿也一并交给日本。近几年来,围绕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中日双方的争端仍是诱发冲突的不稳定因素。
(五)我国受到的军事威胁不同
在50-60年代,我国处于被周边几个国家军事“包围”和威胁的状态。东面:除台湾想反攻大陆外,中美、中日、中韩关系都未改善。美国对我有直接的军事威胁。1950年夏秋时节,美国以支援南朝鲜军为名,发动了侵朝战争,很快将战火烧到中国国门。我国被迫派志愿军参战,历时近3年,中朝军队终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签署了停战协定。这场战争虽然在有限的朝鲜半岛进行,但参战国之多、作战规模之大、战争之残酷是少有的。美国在入侵朝鲜的同时,还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霸占了中国领土台湾。西面:印度政府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同时向我发动武装进攻。1962年10月至11月,我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南面:中越关系逐步恶化。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越关系急转直下,以致发展到后来越南明目张胆地侵占我西沙的甘家泉、珊瑚、金银三岛。北面:中苏关系紧张。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破裂,苏对我采取军事包围和威胁战略。1962年在新疆地区进行大规模颠覆活动。1969年3月2日,苏领导集团蓄意制造了珍宝岛事端,我边防人员被迫给予歼灭性反击。
七、八十年代,我周边国家,除越南对我进行挑衅,我被迫进行两次自卫反击外,其它国家相对而言,军事力量增长比较缓慢,对我直接威胁不大。加上邓小平同志在领土、领海争端问题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张的影响,我国周边环境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
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周边环境总体上是稳定的,但是我面临的军事威胁相对增大。除正在兴起的世界军事革命对我军质量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外,周边国家普遍加快军备建设步伐,对我维护领土、领海主权和安全构成了一定的现实和长远威胁。
(六)我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在国际上的影响不同
在50-70年代,我国的经济还比较落后,军事实力也比较薄弱。那时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虽有提高,但由于经济、军事的落后,仍受到一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大国的歧视。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逐步雄厚,军队质量建设不断加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尤其是我们打破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界限,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广泛联系和交往,外交空前活跃,在国际事务中更加积极主动。我国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随着联合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的日益提升,作用也越来越大。所有这些,都使所有想打中国“主意”的国家不得不想一想与中国为敌的后果。同时,也要看到,现在,别国也都在谋求全面发展,尤其是近些年随着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和对海洋发展战略的普遍重视,我国在周边环境上新、老问题日趋突出,有些问题处理起来很棘手,军事斗争准备的任务相当繁重。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判断战争局势给我们至少有以下几点启示:
(1)坚持政治条件与经济条件辩证统一。
建国以后,毛泽东在观察世界战争与和平、战争与革命形势等问题时,一直坚持从政治、经济相统一的角度进行分析,但在他的晚年,又更多地注重国际政治斗争和政治态势的变化,而或多或少地有忽略对国际经济形势、经济斗争和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以及分析这些变化对国际政治关系影响的倾向。因此,在把握战争与和平的转化条件时,主要运用的是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把侧重点放在政治上,认为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这一著名的战略判断便反映了毛泽东观察思考问题的这种方式。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战争与和平的相互转化时,曾经指出:“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一个是政治角度,一个是经济角度。”这就是说,邓小平同志在判断战争与和平相互转化的条件时,更加注重对现实利害关系和国家利益的分析,把对政治矛盾与经济矛盾的分析辩证地统一起来。他的著名的“东西南北”矛盾论,就是典型的范例。所谓“东西”是国际政治关系,“南北”是国际经济关系,但政治与经济是相互包含的。邓小平同志把二者统一起来思考,对战争与和平的转化条件作出了正确判断。
近几年来,江泽民同志分析战争问题,总是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因素一并分析,强调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已上升为首位,同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政治、军事、意识形态仍起相当大的作用。从而比较准确地判断了战争局势。
(2)应充分发挥民主科学论证。领导核心对战争局势的判断事关重大,因此,既要发挥个人的才智,也要注意发挥领导集体甚至更大范围人员的智慧,反复论证,以保证判断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在60至70年代,中央党内有一些领导人对当时军事斗争形势有着自己的真知灼见。譬如:陈毅在1959年就曾指出,总的说,美国目前还不想打大战,而是想搞局部战争。建国后长期担任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在1962年9月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建议,在世界人民力量超过反动力量、和平力量超过战争力量的情况下,不要过份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不要笼统地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但是这些意见都没有引起毛泽东同志的应有重视。
(3)应严格限定军事斗争准备的范围和程度。军事斗争准备以可能发生的战争需要为前提,着眼适应未来战争和即将发生或已经发生的战争需要。而确定军事斗争准备是局限于军事工作范围,还是扩大到军事工作以外的更大范围,事关重大。在这方面,过去我们也是有教训的。在60-70年代,我国应付世界大战和应付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实际上是全民备战。如果较为客观地估计战争形势,把准备“大打”主要局限于军事工作范围,较少干扰国内和平建设的正常秩序,就像50年代那样,情况也许就大不一样了。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全面备战之车没有刹住。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过去我们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忽视发展生产,忽视经济建设”。现在我们国家对军事斗争准备范围和程度的限定应注意既要保证战争需要,又要尽可能地使国家经济建设不受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