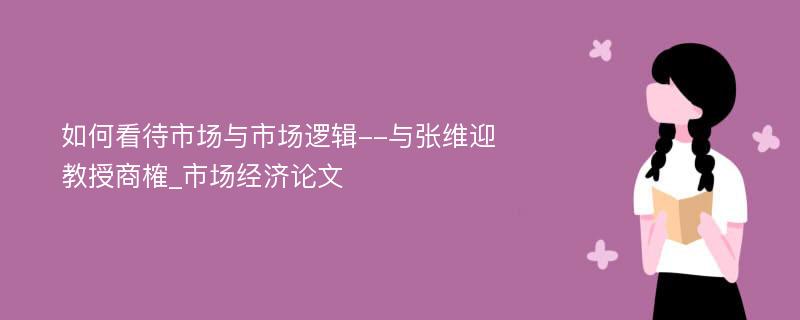
如何看待市场和市场逻辑——与张维迎教授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论文,如何看待论文,逻辑论文,教授论文,张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磕碰和交锋,就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话题和一道景观。近年来,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就市场和市场经济问题,通过《南方周末》等大众传媒,一再渲染和传播其自由主义主张。在此,笔者以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观点,认真与这位经济学家将市场和市场逻辑自然化、永恒化、绝对化,刻意为资本和资本关系进行辩护的观点作一番比较,希望对当下的相关研究能够有所启示和裨益。 一、“人的本性”与“市场逻辑”的关系 1.这位经济学家:市场经济起源于人的“自我中心”本性 张教授说:“人的本性是什么?宽泛点说,就是几乎所有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self-centered)。”就此,他搬出了亚当·斯密的观点:“亚当·斯密说同情心普遍存在,即使最坏的人也有同情心,但所有的同情心都是围绕自己展开的,同情心的大小,一是与物理上的距离有关,二是与生理上的距离有关。”例如:一个人“看到自己的亲人过世,比看到几千公里外非洲人的过世时的同情心肯定要大”,原因就在于非洲人离他很远,而自己的亲人就在身边。一个人“看到猴子被杀,比看到蚂蚁被杀时的同情心也要大”,而他“对蚂蚁的同情心,可能比对植物的同情心更大”。为什么呢?因为“猴子比蚂蚁与人的相似性更大”,而“动物在形象上、生理上跟人的相似性比起植物来更大”。因此,亚当·斯密的“同情心”就是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基础上的①。 当然,讨论人的本性问题并非这位经济学家的目的,其目的在于由此引出“市场”和“市场经济”来。一方面,“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另一方面,“任何人要生存都离不开他人的合作和协助”。如何解决其中的冲突和矛盾呢?用这位经济学家的话说:“人类怎样从以自我为中心到达合作和互助?或者说,自利的本性如何能够给他人带来好处,而不是伤害?”能够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从而“解决这个矛盾和挑战的最有效的方式”,便是“市场”和“市场经济”。因此,在这位经济学家看来,“市场本身没有改变人的本性,市场从不试图改变人的本性,拥护市场的人没有想过用市场改变人的本性;反过来,正因人的本性没法改变,所以才有了市场经济,也才需要市场经济”②。可见,市场和市场经济起源于人性的弱点,起源于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本性,是为了实现与他人的合作和互助的需要。 2.马克思:市场经济是劳动分工和私有制共同作用的产物 与这位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认为:“交换者生产交换价值的前提”,也即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前提,“既不是从个人的意志,也不是从个人的直接本性中产生的,而是从那些使个人已成为社会的个人,成为由社会规定的个人的历史条件和关系中产生的”。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和“关系”呢?马克思强调两点:其一是分工,即生产是“在一定历史形态的分工下”进行的生产;其二是劳动者的个体所有制,即生产是“作为独立的私人而生产”③。没有劳动分工,没有不同的劳动者生产不同的东西就没有商品交换的可能性,也就没有市场和市场经济产生的可能性。因此,马克思说:“他们的劳动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因此他们之间就要相互交换。”但是,“假如他们作为共同的所有者从事劳动,那就不会发生交换了,而是共同消费了”④。可见,没有劳动者的个体所有制,就没有交换的必要性,也就没有市场和市场经济产生的必要性。在马克思看来,“生产交换价值的个人的生产的私人性质,本身表现为历史的产物”⑤。同样可以说,分工、市场和市场经济也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们与“人的本性”均没有本质的联系。 3.并不存在抽象的和不变的人的本性 这位经济学家断言,亚当·斯密的“同情心”就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基础上。不仅如此,“孔子如果不是假定人是自我中心的,就不会有儒家的道德伦理体系”,因此,“儒家的一整套伦理体系也是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基础上”。在这一点上,宗教的基本假设“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没什么不同”,“所有的宗教都假定人是自我中心的”。最后,极而言之,“关于人性的假设,无论科学的宗教的,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都一样”,即都把“以自我为中心”确认为不变的人性⑥。 然而,马克思并没有把以自我为中心确立为人的本性,恰恰相反,他有句学界共知的名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⑦这句话至少包含了以下三层意思:第一,人的本质不是由单个个体决定的,而是由人所处其中的社会关系决定的。“一窝蜜蜂实质上只是一只蜜蜂”⑧。人则不然。不同时代的人具有不同的本质特征,租地耕种的农民不同于会说话的工具奴隶,雇佣工人又不同于租地耕种的农民。而且,同一时代的人也具有不同的本质特征,农民不同于封建地主,雇佣工人也不同于资本家。第二,人的本质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获得的。人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中,就会具有什么样的本性,而社会关系则是靠了人类的生产和交往,才得以建构起来和延续下去的。黑人天生就是黑人,但不能说黑人天生就是奴隶。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⑨在消灭了奴隶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情况下,黑人依然是黑人,但他们却不再是连“人格”都没有的奴隶。第三,人的本质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教可变的。社会关系决定人的本性,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性;社会关系改变了,人的本性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由此决定了人有别于动物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以及指向未来的无限开放性和超越性。人永远是“未完成”的,其本性在历史的长河中得以不断开掘、不断丰富、不断发展。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⑩“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11) 4.并不存在永恒的和绝对的市场和市场经济 这位经济学家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的“内在本性”与寻求合作和协助的“外在需要”之间的矛盾,来说明市场和市场经济的缘起。照此逻辑,只要有“人”,就会有市场和市场经济,市场和市场经济与人的存在共始终。实现“人”的合作和协助,并不存在市场和市场经济之外的其他方式;市场和市场经济是从来就有的,而不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市场和市场经济也会永远地存在下去,而不会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消亡。这些观点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这一点无须多言。 二、“市场逻辑”与“资本逻辑” 1.这位经济学家:市场逻辑就是既“利己”又“利他” 为了说明人类是如何从“以自我为中心”走向“合作和互助”的,这位经济学家还把市场和市场经济与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联系起来。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幸福,都不断追求better life”。市场和市场经济则要求,“通过让别人幸福使自己变得幸福”。具体言之,“市场就是你必须通过满足别人的需要来实现你自利的动机。……它使得你不能伤害别人,你致富也好,地位提升也罢,一定得建立在给他人创造幸福、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基础上”。换言之,只有满足他人的需要,才能使他人幸福;只有让他人幸福,才能使自己变得幸福;只有为他人和社会创造财富,才能为自己创造财富。“自我中心”体现了人的“利己”的一面,而“合作和互助”则体现了人的“利他”的一面;“利他”并非人的本意和目的,它不过是用以实现人的“利己”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也只有通过“利他”的手段,才能实现“利己”的目的。这就是这位经济学家所理解的“市场逻辑”,他坚信:“市场经济可以将人的利己之心变成利人之行。”(12) 2.马克思:要区分两种性质不同的市场和市场逻辑 没有商品生产和交换,就没有市场和市场逻辑,而同样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却可以具有不同的经济性质。马克思就严格地区分了“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是两种性质迥异的经济活动,不能混为一谈。 其一,二者所体现的生产关系不同。从商品生产的发展来看,没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就没有商品生产。但是,“私有制的性质,却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在性质上就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13)。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陷之一,便是“在原则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其中一种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它忘记了,后者不仅与前者直接对立,而且只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14)。简单商品生产建立在劳动者的个体私有制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则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 其二,二者所包含的生产目的不同。生产关系决定生产目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目的。尽管说,“在商品生产中……所以要生产使用价值,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基质,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15),但是,马克思发现,简单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目的上具有质的区别。简单商品生产的目的,是获得使用价值,以满足生产者的需要。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则不然。“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的内容和目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的目的”;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16)。对资本家而言,“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值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也“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17)。如果说,简单商品生产的目的在于“谋生”即获得使用价值以维系生计,那么,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目的就是“赢利”,即获得剩余价值以实现价值的增值。 其三,商品生产发展的程度和水平不同。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中,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范围被严格地限制在经济领域,其发展程度是十分有限的。资本主义社会则不同,商品生产和交换不仅占据了整个经济领域,而且进一步溢出经济领域。资本主义把物质生产劳动者的“劳动力”也变成了商品。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由工人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才一开始就是为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18) 其四,商品生产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同。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中,“真正的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或者大体说来,并未触及整个共同体的生活,不如说只发生在不同共同体之间,决没有征服全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19)。社会在整体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生产和交换处于从属地位。资本主义社会则不同,其经济形态完成了向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转变,商品生产和交换已经居于主导地位。在这里,社会生产过程牢牢地“为交换价值所控制”,在经济活动中“占优势”的,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 其五,价值规律作用的实现方式和表现形式不同。由于商品的“交换规律只要求彼此出让的商品的交换价值相等”,所以,价值规律在本质上是等价交换规律。只要是商品生产和交换,价值规律就会起作用。简单商品生产如此,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也是这样,马克思说:“资本家是以商品交换规律作根据的。”(20)但是,在不同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中,价值规律的实现方式和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市场价格围绕着价值而波动,价值直接调节着商品的市场价格。而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商品的生产价格,是市场价格围绕着摆动的中心”,调节市场价格的不再是价值而是“生产价格”,价值规律需要间接地通过生产价格来表现和实现其在按比例分配劳动中的作用。可见,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虽然“仍然有效”,但是“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以后所采取的那种……表现形式”,则明显是“改变了”(21)。 其六,价值规律作用的强度和大小不同。虽然说,价值规定和价值规律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并未得到充分实现和体现;但是,由于它是调节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主导性规律,所以其作用却是巨大的,由此保证了社会劳动的按比例分配,使经济在一种相对平稳的状态下运行。虽然说,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基础上,价值规定和价值规律才得以“自由展开”,才得到充分实现和体现(22);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主导性规律是“价值增值”规律或利润规律,价值规律要服从利润规律,所以其作用是很小的。马克思讲:“‘直接的’价值规定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作用是多么小。”(23)正因为价值规定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有限,所以,社会劳动的按比例分配往往难以实现,保证商品生产和交换顺利进行的各种比例关系总是遭到破坏,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致使经济运行大起大落也就在所难免。由此便不难理解,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一切平衡都是偶然的,各个领域中使用资本的比例固然通过一个经常的过程达到平衡,但是这个过程的经常性本身,正是以它必须经常地、往往是强制地进行平衡的那种经常的比例失调为前提”(24)。 因此,即使撇开劳动分工的情况不谈,单是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来看,也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私有制和两种性质不同的商品生产,一种是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小私有制”,另一种则是以他人劳动为基础的“大私有制”;与前者相联系的是“简单商品生产”,与后者相联系的则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由此决定,必然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市场和市场逻辑,一种是基于简单商品生产的市场和市场逻辑,另一种则是基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市场和市场逻辑。马克思对詹姆斯·穆勒曾有这样的评价:“经济学辩护论者的方法有两个特征。第一,简单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产品交换之间的区别,把二者等同起来。第二,企图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25)这种评价同样适合于这位经济学家。尽管说市场和市场逻辑为不同的生产方式所共有,但是,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市场和市场逻辑却有着不同的性质和内容。 3.互利互惠只是简单商品生产的市场逻辑 这位经济学家对市场和市场逻辑的描述,极易使人想起马克思的一段话:“只有当个人B用商品b为个人A的需要服务,并且只是由于这一原因,个人A才用商品a为个人B的需要服务。反过来也一样。每个人为另一个人服务,目的是为自己服务;每一个人都把另一个人当作自己的手段互相利用。”(26)但遗憾的是,这种所谓的“市场逻辑”并不属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而是属于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换。从这种市场逻辑中可以看出,“作为交换的主体,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因为,从主体方面看,他们都是商品的所有者和交换者,他们具有同样的规定,或者说“他们处在同一规定中”。“在他们之间看不出任何差别,更看不出对立,甚至连丝毫的差异也没有。”从对象方面看,“他们所交换的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是等价物,或者至少当作等价物”。作为等价物,“它们不仅相等,而且确实必须相等,还要被承认为相等”(27)。不仅如此,马克思认为:“除了平等的规定以外,还要加上自由的规定。”因为,“尽管个人A需要个人B的商品,但他并不是用暴力去占有这个商品,反过来也一样,相反地他们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是把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商品中去的人格。因此,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人格这一法的因素以及其中包含的自由的因素。谁都不用暴力占有他人的财产。每个人都是自愿地转让财产”(28)。从简单商品生产来看,人与人之间确实是一种“平等”而“自由”的关系,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那么,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的情景又是怎样呢? 4.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市场逻辑就是不平等交换和剥削劳动 与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换相比,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呈现出来的,则是另一番情形,且看马克思的描述:“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其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29)其中的奥妙在于:“流通本身不会产生不平等,而只会产生平等”。因为,在流通中,“由于工人以货币形式,以一般财富形式得到了等价物,他在这个交换中就是作为平等者与资本家相对立,像任何其他交换者一样;至少从外表上看是如此”(30)。但是,透过简单流通的表层,“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这种平等已经被破坏了,因为这种表面上的简单交换是以如下事实为前提的:他是作为工人同资本家发生关系,是作为处在与交换价值不同的独特形式中的使用价值,是同作为价值而设定的价值相对立;也就是说,他已经处在某种另外的在经济上具有不同规定的关系中了”(31)。可见,在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层面,既不存在工人,也不存在资本家。当工人与资本家发生关系的时候,这种关系决不属于简单商品生产,而是属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并且,他们之间绝不是平等的。 而在这位经济学家看来,“与市场的逻辑真正对立的是强盗的逻辑”,其要义是:“通过让别人不幸福而使自己幸福,即用伤害别人的方式为自己得到好处。”由此出发,他极力主张自由竞争,他说:“如果没有自由竞争,靠政府垄断,只允许一部分人干,这就不是市场的逻辑,是强盗的逻辑。”他极力主张私有制,反对国有企业,说什么“国有银行,赚那么多钱,有相当一部分是靠强盗的逻辑”。他极力主张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说什么“哪个地区的市场经济不发达,受到政府的干预多,哪个地方坑蒙拐骗就多。”最后,他极力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加分析地反对计划经济,说什么搞计划经济是强盗行为,虽然“有些强盗行为的出发点可能非常善,当初搞计划经济就是这样”(32)。 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市场逻辑?表面看来,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是一种“平等”的“交换”关系,而实际上,这种关系既不平等,也不是交换,而是一种“非交换”。马克思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其结果是劳动价格——尽管从工人方面来说是简单交换,但从资本家方面来说,必须是非交换。资本家得到的价值必须大于他付出的价值。从资本方面来看,交换必须只是一种表面的交换,这就是说,必须属于与交换的形式规定不同的另一种经济形式规定,否则,资本就不可能作为资本,劳动就不可能作为与资本相对立的劳动。”(33)在流通领域,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只相当于其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在生产领域,工人则必须超过其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为资本家创造出剩余价值。马克思曾明确地把资本家压低工人工资的行为定性为“劫掠”(34),并指出:“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资本家“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即窃取了文明”(35)。不过,如果说奴隶主对奴隶、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是一种“明盗”,那么,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资本借助交换的形式,不经交换就占有了他人的劳动时间”(36),就是一种“暗盗”。二者在“逻辑”和“本质”上都是“盗”,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5.不能把资本逻辑和市场逻辑混为一谈 一般认为,市场经济即商品经济,它是区别于自然经济的一种经济形态。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和交换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活动。在此意义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紧密相连的。在马克思看来,简单商品生产必然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自然经济必然发展为市场经济,“认为交换价值不会发展成为资本,或者说,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不会发展成为雇佣劳动,这是一种虔诚而愚蠢的愿望”。马克思对价值与资本的关系的论述发人深省:“在理论上,价值概念先于资本概念,而另一方面,价值概念的纯粹的展开又要以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方式为前提,同样,在实践上也是这种情况。”(37)因此,不能把价值关系与资本关系等同起来,因为在资本关系尚未存在的时候,价值关系已经是一种现实的经济关系。循此思路,可以说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尚未存在的时候,市场和市场逻辑早已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市场逻辑,既是对简单商品生产的市场逻辑的承续,又是对这种市场逻辑的超越。如果说,简单商品生产的市场逻辑是一种等价交换的逻辑,那么,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市场逻辑就既是一种等价交换逻辑,也是一种“非”等价交换逻辑,因而是对等价交换逻辑的扬弃。因为,单从流通领域看,资本家与工人的交换是一种等价交换,而一旦联系到生产过程,这种等价交换的虚伪性就暴露无遗。如果说,简单商品生产的市场逻辑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和平等,那么,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市场逻辑就既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在流通领域的自由和平等,也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在生产领域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因而是对自由和平等的扬弃。一如马克思所说的:“表示交换价值相交换的简单规定中的平等和自由”与“资本的规定性”上的平等和自由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在后者,“这种平等和自由证明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38)。因此,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市场逻辑,既具有简单商品生产的市场逻辑的一般规定,也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定,即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市场逻辑在本质上就是“资本逻辑”,不能只谈市场逻辑而不谈资本逻辑,更不能把资本逻辑归结为市场逻辑,从而把二者混为一谈。 三、“资本逻辑”与“贫困悖论” 1.这位经济学家:市场逻辑使人普遍向善并共同致富 他说:“市场就是按照你给多少人带来幸福回报你。给别人带来的幸福越多,赚的钱就越多;带给别人的幸福越少,赚的钱就越少,这就是市场逻辑。”在宏观层面上,“市场是双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一定是帮助别人的手,而不是伤害别人的手”。用当下流行的说法,市场逻辑可以使人们“互惠”和“共赢”,可以实现“共同富裕”。那么,市场逻辑何以能保证人们“共赢”和“共富”呢?这位经济学家的根据是:“市场使人的行为更符合善的要求”,并且,“从这个角度讲,市场本身是最讲伦理的”。从长远来看,“在市场中一个人能持久致富,一定是靠诚实守信,而不是靠坑蒙拐骗”,就像司马迁所说的那样:“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从世界范围来看,“哪个地方市场经济比较发达,比较健全,哪个地方人的道德水平就比较高,更诚实守信”。这样,他就把“市场逻辑”与“伦理道德”联系起来,认为:“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基础,但这一道德只能在市场中实现和找到,也可以反过来说,道德需要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那么,市场逻辑又何以能保证人们“诚信”和“向善”呢?这位经济学家的根据是:市场靠的是“制度”而不是“说教”。他说:“仅仅靠说服人,没用,还得靠制度。这个制度就是自由市场,就是自由竞争!”“仅仅靠说教,最后恰恰是人人都变得虚伪。”由此,他认为,“市场制度是最符合伦理道德的”(39)。概而言之,这位经济学家的观点,就是通过市场和市场逻辑,不仅可以在道德上使人们诚实守信、普遍向善,而且可以在经济上使人们互利互惠、共同致富。事实果真如此吗? 2.马克思:市场经济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失范现象 马克思当然不否认市场和市场经济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但从伦理道德方面看,市场和市场经济也具有自身难以根治的弊病。例如:它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疏远和漠不关心。正如马克思所说:“主体只有通过等价物才在交换中彼此作为价值相等的人,而且他们只有通过彼此借以为对方而存在的那种对象性的交换,才证明自己是价值相等的人。因为他们只有作为等价物的所有者,并作为在交换中这种相互等价的证明者,才是价值相等的人,所以他们作为价值相等的人同时是彼此漠不关心的人;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个人差别与他们无关;他们不关心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一切个人特点。”(40)在市场和市场经济中,人们关心的是等价物,是交换价值,而不是人的“个人差别”和“个人特点”!即使如这位经济学家所讲的,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就必须首先满足他人的需要,这在本质上也只是一种自私自利,而不是互惠互利。马克思把这种现象概括为:“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41)互惠互利、共同利益是做不到的。在市场和市场经济中,“诚实守信”也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一方面,商品价格围绕价值的波动,为人们之间“骗与被骗”关系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交换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博弈能力的差异,则使得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以至于,马克思不无诙谐地说:“在价格规定中(在利润上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情况)还要加进欺诈,互相欺骗……[交换的]比例为个人的骗术等等开辟了活动场所(撇开需求和供给关系不谈),这种骗术同价值规定本身毫无关系。”(42)“欺骗价格”的存在,使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市场和市场经济中各种坑蒙拐骗、买空卖空的行为和事件屡禁不止、层出不穷。 3.贫困和两极分化是资本逻辑作用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当然不否认市场和市场经济在积累和创造财富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承载了资本逻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绝不是这位经济学家所说的“共同富裕”,而是也只能是“两极分化”。 本来,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和人们富裕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劳动和劳动产品所有权的分离”,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发展生产力却成了贫穷的渊薮。因此,马克思说:“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43) 不可否认,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或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情境下,工人曾陷入“绝对贫困”的境地而难以自拔,但是,这并不能反映资本主义贫困的一般本质,否则,就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和文明面。虽然说工人的贫困是与资本家的富裕相对而言的,但是,“相对贫困”概念也不足以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贫困与此前的社会形态中的贫困现象区别开来。工人的这种贫困不仅是一种相对贫困,而且是一种具有“悖论性”的贫困。正是这种“贫困悖论”,才赋予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贫困以独特规定,从而有别于此前一切社会形态中的贫困。因此,马克思说:“只有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下,赤贫才表现为劳动自身的结果,表现为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44)在英国当时的法律中,雇佣工人被叫做劳动贫民,这极其形象地刻画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贫困的悖论性质。因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劳动使人致富;但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劳动却成了贫穷的渊薮,劳动者越劳动就越贫穷!可以说,正是广大的“劳动贫民”的存在,才使得在资本逻辑异常强势的时候和地区,社会需求和居民消费力严重不足,经济运行的各种比例关系严重失衡,最终结果就是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对此,市场逻辑是难以解释也解释不了的。 4.任何形式的私有制都不是什么“普适价值” 这位经济学家认为,市场制度是最道德的制度,只有依靠市场制度,才能实现经济的互惠和共赢。但是,要保护市场制度,就必须“建立一个好的私有产权制度”。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普适价值”。“普适价值并不是简单地把某一方的规则强加给另一方,规则的形成可能是相互妥协的结果”,即“我不能抢你的东西,我也不能强迫你买我的东西”。其要害,是强调私有产权制度应当成为“普遍认可的规则”(45)。 所谓的“私有产权制度”,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与这位经济学家的不同立场表现在:第一,在马克思看来,私有制是“社会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46)。存在着不同性质的私有制。其中,有劳动者的个体私有制、奴隶制私有制、封建制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位经济学家所说的私有制,无疑指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 第二,马克思认为,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个体私有制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取代,并不是因为后者是什么“普适价值”,而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因为,“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其缺点是:“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因此,“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47)。 第三,在马克思看来,“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地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即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这同样与是否“普适价值”没有关系,而同样是由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48) 纵观社会主义制度近100年的现实发展历程,探索和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有效实现形式,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能因为“国有企业”存在各种现实问题,就否定它作为一种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形式。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不存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性质中,而是存在于国家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和管理体制中;不能用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干部管理问题,去否定国有企业和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身。试想,若没有国有企业,怎么能有汶川地震后短时间(3年-5年)内的援建和重建呢!又怎么能有全球经济危机的危局下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和责任担当呢! 至于说“政府干预”和“计划”问题,应当全面具体地加以分析。不错,我们是有干预过多的问题,但也存在管理缺位、管理不严的问题。不能用新自由主义来衡量、评价我们的改革。历史经验表明,健康的市场和市场经济,既离不开政府的干预,也离不开计划的引导。当经济危机袭来时,美国政府要救市,欧盟也要救市,难道这不是对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干预吗!为什么在美国不是强盗逻辑,而在中国就变成了强盗逻辑呢?国有企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 5.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剥削是引发社会利益冲突的根源 在这位经济学家看来,人们之所以反对私有制这样的“普适价值”,是因为“有思想者把人类的冲突都归结为不可协调的阶级矛盾,最后将一切都归为斗斗斗”。而应该认识到的是:“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比想象的少,好多利益冲突是发生在工人内部,而不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由于“思想家”把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放大了,所以人们才反对私有制,而实际上,工人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要远甚于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49)。 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这是事实,但能说工人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大于他们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吗?在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曾谈到一个事实:“英国所有的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现在都分裂为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作会使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的竞争者。”马克思对此的解释是:“爱尔兰是英国土地贵族的堡垒……英国土地贵族事实上代表着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所以爱尔兰是英国贵族用来维持他们在英国本土的统治的最重要的工具。”(50)就是说,爱尔兰的统治者是英国的土地贵族,如果说爱尔兰工人阶级与英国工人阶级发生了利益冲突,那么,这种冲突也是由爱尔兰的英国土地贵族对爱尔兰工人阶级的统治引起的,是由爱尔兰的英国土地贵族与英国本土的资本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和竞争引起的。当然,处于“自在”状态的英国工人阶级是看不清这一点的:“英国工人觉得自己对爱尔兰工人来说是统治民族的一分子,正因为如此,他们就变成了本民族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51)可见,在相似的历史事实面前,马克思与这位经济学家的解释判若天渊! 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利益冲突问题上,引起马克思高度重视的是:“报刊、教堂讲坛、滑稽书刊,总之,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则人为地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存它的势力的秘密所在。这一点资本家阶级自己是非常清楚的。”(52)马克思曾送给庸俗经济学家这样一段话:“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不是这样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做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夸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现象,并且把它当作最终的东西。这样,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53)笔者希望人们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①张维迎:《市场制度最道德》,《南方周末》2011年7月14日。 ②张维迎:《市场制度最道德》,《南方周末》2011年7月14日。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5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2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52页。 ⑥张维迎:《市场制度最道德》,《南方周末》2011年7月14日。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7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4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2页。 (12)张维迎:《市场制度最道德》,《南方周末》2011年7月14日。 (1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2、873页。 (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6页。 (1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7页。 (1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4、265、307页。 (1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7-218、269、178-179页。 (1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8-109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5、27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68页。 (2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4页。 (23)《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50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62页。 (2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6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8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5-196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8页。 (2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5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1、243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2、243页。 (32)张维迎:《市场制度最道德》,《南方周末》2011年7月14日。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2页。 (3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1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1、23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9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4、207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4页。 (39)张维迎:《市场制度最道德》,《南方周末》2011年7月14日。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6页。 (4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4-205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9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7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8页。 (45)张维迎:《市场制度最道德》,《南方周末》2011年7月14日。 (4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2页。 (4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872-873页。 (4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3-874页。 (49)张维迎:《市场制度最道德》,《南方周末》2011年7月14日。 (50)《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05、304页。 (51)《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05页。 (52)《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05页。 (53)《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82-283页。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交换价值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张维迎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经济学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经济论文; 价值规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