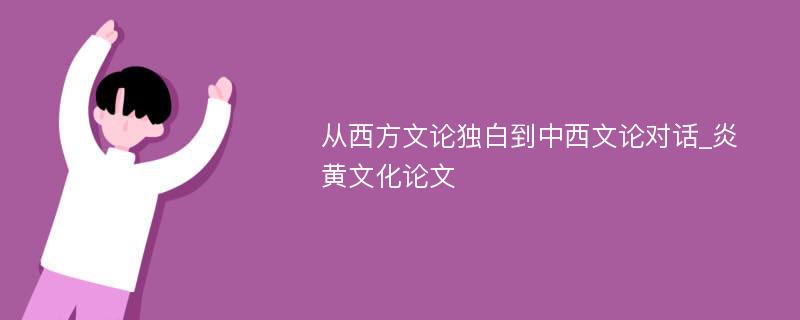
从西方文论的独白到中西文论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独白论文,中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方和西方的文学理论无疑有巨大差异,不管解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如何把差异加以绝对化,也不管伽答摩尔和德里达在语言是交往的桥梁还是障碍的问题上,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是否可能的问题上,各执一词,事情从纯理论上说起来可能比较复杂,但是在实践上,恐怕谁也很难否认我们之间毕竟存在着即使是错位的,也仍然是部分重叠的、共同的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提出中西文论对话本身就是一种充满自信的挑战。但是,这不等于中国和西方文论之间的对话就没有困难。
(一)
对话是相对于独白而言的,应该是双向的、互补的、互动的,对双方都意味着一种发展的动力。这不仅是指从对方吸收富有生命力的思想资源,而且是指更加深刻地认识、理解自身的文化/文学传统。早在本世纪初,王国维就指出:“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转引自殷国明《20世纪中西文论交流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7页。)。东方人应该如此,对于西方人也是一样。不管是坠入爱河的恋人,还是指挥战争的将领,都只能在对话(包括躯体的和武器的对话)中认识对方,认识自我,包括潜在的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懂得东方文化哲学,也就不可能理解西方的哲学和文学理论。反之亦然。
但是,中国百年来的文论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西方文论在中国文坛上的独白(我们当然不会用“文化殖民”这样的话语)的历史,而不是东西方文论的对话的历史。中国文论即使对西方文论有所影响,也仅仅限于局部和在个别人物身上,并没有达到对西方文论的发展进程起重大作用的程度,而西方文论(包括俄苏文论)不管历史条件发生什么变化,都保持着长驱直入的态势,决定着中国文论的体系和发展动向。
这里有历史的原因。本世纪初,我国古典文论面临着重大的民族的文化的危机。
中国古典文论在新的历史时代,不能回应新兴文化的挑战,一些根本的原则已经失去了生命(如宗经、征圣),有的虽然还保存着潜在的生命,但是在思维形式上,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中国传统文论长于从经验的直接概括,善于直接归纳和直观的综合,在自然科学中没有达到系统的、数学的高度,在文学理论中,缺乏对于概念的微妙差异作过细思辨的系统方法。传统文论的基本观念、范畴多少带着经验的直观的性质,其内涵具有浮动的特点。不论是“道”还是“气”,不论是“风骨”,还是“气象”、乃至“意境”,沿用千百年,都缺乏以定义来保持其概念的一贯和论证的自治的传统。没有概念的一贯和逻辑的自洽,就很难进行大规模的、系统的演绎;中国文论悠久的学术成果很难在不确定的范畴中有效地积累。
我们的小说评点、诗话和词话,虽然充满了天才和灵感,甚至提出了意境和性格这样核心的范畴,但是,概念的内涵不够稳定,常常限于在经验层次上的滑行,而缺乏逻辑的自治,又很难在演绎中深化,难以形成科学体系。正是因为这样,中国传统文论,除了早期个别的例外,都不以庞大的思辨的体系见长。
在这种文化危机的压迫下,我们不但全盘接受了西方文论的观念(范畴、话语),而且接受了他们的抽象思辨的方法。在这以前,我们没有美学、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典型、个性、风格、审美、审丑、幽默、喜剧、悲剧等等这样的范畴和话语。我们的“失语”感和文化自卑感是共生的。早期王国维式的《人间词话》式的传统话语范式并不能满足我们;乃至今天,我们之中也很少有人认同维特根斯坦式那种片断的语录式的、《论语》式的写作方式,压倒一切的感觉是,不接受来自西方的话语、范畴,不用西方的演绎法来写作论文,就不能对我们的新文学进行宏观和微观的(而不是像诗话、词话那样吉光片羽式的)阐释和理论体系的表述,就不能和世界文论接轨。
应该承认,全盘接受西方文论是历史的逼迫,目标是思想的启蒙、个性的自由、民族的独创。其结果却导致了我们对民族独创性这一宏大目标的遗忘。虽然有过朱光潜先生以西方文论为纲,融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努力,宗白华先生以中国文论为纲,融入西方文论话语的尝试,但是,中国文论的建设,甚至其局部的话语更迭都离不开西方文论的输入。每当社会大变动的关头,中国面临创造话语的机遇的时候,总是一茬又一茬的西方文论话语成为最新的、最前沿的文化的旗帜。
文论的被动还表现为连话题都是被预设了的,造成了长期以来不但在意识层面,而且在潜意识层面对于西方权威的疲惫的追随。这就难怪有些愤激的当代文论家,要用“失语”来形容中国文论的处境了。
民族的自我剥夺成了对话的前提,这就造成了不管多么真诚的民族文论的更新的努力都难免不会变成对西方文论的追踪。
对于现成话语的简单认同本身与把独立性当作前提的西方文论本身就是背离的(注:以欧洲大陆的语言哲学为例,在胡塞尔、海德格尔、伽答默尔和德里达之间显然有学术上的传承关系,但是,他们的传承和挑战、革新是相辅相成的。他们在学理上并不是以认同大师为荣的,相反,他们是以在学术上独立为最大的光荣。如果海德格尔满足于胡塞尔意向性现象的分析,而不提出对于此在的追求,如果德里达对胡塞尔的语言观,没有进行任何批判,如果伽答默尔不在形而上学的问题上和德里达针锋相对地争论,就不可能有伽答默尔和德里达的学术存在了。)。
这不能不令我们反思,引进的最高目的究竟是什么?难道不是为了独立创造吗?但是,长达百年的精神进口,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了我们的文论的创造力,又在多大程度上窒息了我们的创新能力?启蒙的结果却导致了民族个性和创造性的窒息,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吗?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这种单向的输入,对于西方文论的发展,又能得到多少回报呢?难道西方人对这种无休无止的“出超”,就肤浅到没有任何战略的眼光,就不感到理论资源的匮乏吗?
一百年来,文论交流变成了西方文论的独白,中国文论仅仅是洗耳恭听,充其量,不过是西方文论微弱的回声,对于历史,我们无可奈何,当然不应该狭隘地把这样的现象当作“文化侵略”。然而,对于未来,难道是最佳选择吗?经济全球化不等于文化一体化的霸权,文化多元化交流的正常形态应该是多声部的,至少是东西方文论的双向的对话。
(二)
当然,不可否认,对话毕竟局部发生过。文论的交流的确有过令人鼓舞的一面。
我们从深深影响了王国维的西方学者叔本华那里就看到了非常精彩的历史记录。他在对欧洲文化哲学进行反思的时候,从东方包括印度哲学,中国的《易经》乃至佛学中汲取了思想资源,这一切帮助他表达了光用西方纯粹理性和逻辑很难解说的人的生存的困惑。
远距离的文化交流比之近距离的,更能认识自身的深层文化意蕴,更能深刻地发现自身文化的局限和优长,激发出创造力。
中国的带着象形色彩的汉字,在五四运动期间,在本国的文化精英那里,已经到了快要被废除的程度,而中国的古典诗歌居然在遥远的美国引发了一场意象派(Imagism)诗歌革新运动,产生了庞德(Ezra Pound)那样的大诗人。但是这并不妨碍五四新文化的先驱把我国古典诗歌当作枷锁和镣铐,彻底地加以粉碎。
这使我们联想到,在本世纪初中国一切传统的文论话语并非一概都没有生命力,也没有完全丧失有效的阐释功能。面对历史性的挑战,对现成的文学话语进行阐释、解析和重构,揭示它们与文化环境以及意识形态的互动,保持自己的美学立场,将某些传统的话语转化为现代话语,在吸收西方话语的同时,向西方文学理论发出挑战,促使西方文论在某些根本价值取向上,发生变异,与中国传统发生交融,产生出新的话语或者派生的范畴来,这本是文论历史发展的挑战和机遇。但是很可惜的是,中国文论没有选择这条路。倒是在海德格尔的体系里,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论中道家和佛学虚静的精神的影响。在这方面,在中西文论的融通中,恰恰是薄弱环节。
应该承认,大规模接受西方文论帮助了我们,提高了我们的抽象、概括能力,帮助我们超越了传统的综合性思维惯性;用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的话来说,超越了经验(惟象的)归纳的局限,使得我们逐渐习惯了逻辑的自洽和一贯的规范。
但是我们把西方文论的自洽性看得太完美了。事实上,西方文论的逻辑的体系性和范畴的系统自洽是表面的,远远谈不上完备。
从诗学历史上来看,西方有想象(imagination)、变形(deformation)、激情(passion)、沉思(reflection)、陌生化(alienation)等一系列看似自洽的系统范畴,但是与西方诗歌文本一对照,就不难发现,它的概括并不全面,其阐释的有效性是有限的。例如,它并不能概括布来克、湖畔派诗人和歌德的一些描写大自然的诗的艺术特性,更不能阐释我国某些表现诗人的心灵与大自然相契合的山水田园诗篇。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独特的“山水田园诗”并不像五四时期风靡一时的西方浪漫主义诗风那样强调人与大自然和社会的冲突,而是突出人与大自然、人生的统一与和谐的。主要不是西方式的强烈的激情,而是东方式的温和的感情;不是借助于语意的变异,而是潜藏在通常的语义之中,更不是像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表现为语言的陌生化的。中国诗学中的核心范畴——意境,强调的是由心灵的“意”造成了和谐、融通的境界,而不是由于感情冲击了感觉造成了语义的变异的效果。“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究其话语的功能来说,并没有陌生化的效果。其诗意不是在可以直接感觉到的语言中,而是在语言之外的。中国诗歌强调“无言之美”,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与西方的语言文化理论是矛盾的,意境的奥秘不在语言而在意象的张力场中(注:当然,在海德格尔那里也常常出现类似的观念,但是,那是出于不同的哲学基础。中国传统的文论出于言与意之间的对立,而海德格尔却是从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出发的。)。
而这种大都不激烈的、温和的情感,与西方强调激情和想象的诗学传统是冲突的。
正像中国人也时有西方式的激情一样,温和的感情不仅仅是中国人特有的,西方人也有温情的时候,布来克、华滋华斯、歌德和海涅有许多诗歌,就不是激情的,而是温情的,突出的是和大自然和人的无声的交融,意象的有机和谐,好处不在字面上,而在文字之间的空白处的张力场之中。因为并不是激情的,因而虽有想象,而其感觉和话语却没有变形,就单独的词语来说,陌生化的程度并不突出。这一切如果用我国传统诗学的“意境”去阐释就可能有效得多。
中国的意境学说,所强调的恰恰与西方浪漫主义诗论相反。它的好处在语言之外,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天人合一与西欧民族与对于上帝创造的自然的赞美之间的部分重合。
本世纪初王国维借助于叔本华的学说,又部分借助于西方的逻辑方法,将意境说发展为境界说,这也应该属于两种文论的对话,但是却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对话,而是一种无声的、单向的对话,只有一方出场,而另一方是缺席的,真正的对话应该是双方都在场的、公开的争鸣。单向的对话的缺陷就在于,许多潜在的文化意味和价值的错位,常常为缺乏相关性的话题和对应的逻辑所掩盖,层次性深化和体系化难以实现。
正是因为这样,中国的境界说,在这么长的历史时期中,意没有和西方文论发生双向的交流。意境范畴未能与西方的激情、想象、变形学说和陌生化学说构成并列或者对立的范畴,未能成为世界诗学体系的一个成分。
这是一种遗憾,也许,这种遗憾在一个并不太悠久的历史时期里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传统文论是用古代汉语写成的,它很难与西方文论直接交流。交流的前提是,将中国的古典诗学范畴转化为现代话语形式。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把这个任务看得太简单了,以为这仅仅是本民族古今的话语的简单转换,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失败以后,我们才认识到,这不仅仅是古今话语转换,而且还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复杂机制。
第一,古代汉语单音词是多义的、直觉性的,一个单音词包含着一系列的双音词,而现代汉语则演化为双音词,双音词有一种意义单纯化的倾向。例如,古代汉语中单音的“意”是多义的(在与之相应的现代汉语词语中这种多义就明显地分化了:意义、意念、意想、意思、意气、意向、意会、意味、情意……),将古代汉语的多义的单音词转化为现代汉语的趋向单义的双音词就意味着选择其中之一。这就造成丰富语义的失落,甚至歪曲。
这是因为从逻辑上来说,古代文论的直觉性概括和为西方文论所同化了的、遵循同一律的现当代文论是有逻辑上的矛盾的。纯粹依赖传统文论的话语,不要说和西方人交流,就是和中国现代人交流都难免误解,其原因就在于,其间存在着两种逻辑,一个把同一律看成交流的前提,一个却把丰富的语义当作交流不可缺少的条件。
第二,古代诗学的话语往往和中国传统的文化宗教的观念结合在一起。意境的观念本来与佛学、禅宗、道教的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将意境说进行现代转化,就不但是语义的转化,而且有一种深层的文化和宗教价值的转化(注:参见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0页;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9月再版,第230—240页。)。而这种转化不但对于基督教文化背影的西方人来说,其想象和体验受到限制,而且对缺乏道家和佛学修养的中国当代文论家也具有相当的难度。
第三,最根本的是,中国传统的意境,其中的意,和西方语言文化哲学之间有着相当尖锐的冲突。意并不等于西方的言,它既是言的深化,又是言的内化,它不在言之中,而在言与言的联想的氛围之间;意还表现为情的空灵,人的虚化,情感的淡化。不到达这种程度,就进入不了诗的境界。而在这种境界中,美学性质是以无言、无声、无欲为特点的。这是中国道家和佛学的根本观念的体现,与西方文学理论的语言中心论有着相当遥远的距离。
缺乏直接沟通的范畴,在逻辑上常见的错位,再加上文化宗教心理(想象和体验)距离,有时竟是风马牛,使对话难以深入。
从古代汉语的多义转化为现代汉语的单义,虽然困难,但毕竟是表面的,可以用语言加以弥补的。而文化价值和宗教观念的、想象和体验的差距,则是深层的,语义的和心理上的失落和误解是不可弥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话总是和误读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没有误读就不可能有对话(注:在这方面,西方学者比之中国学者更容易犯幼稚的错误,在中国学者中类似的笑话屡见不鲜,就是渊博如朱光潜,在他亲临欧洲研读克罗齐的时候,还发生了许多误读。参阅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33—144页。)。
但是,我们并不悲观,诚如伽答默尔所言,理解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在历史性的误读过程中互相之间自然会深化理解(注:参阅徐友渔、周国平等《语言与哲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20页。)。
正是因为这样,意境的观念虽然由王国维在某种意义上加以现代语义化了,甚至还将它以西方逻辑化的方式,转化为二元对立的范畴——有境界/无境界,有我之境/无我之境,隔/不隔。但是,仍然没有得到西方的认同,就连中国现代新诗的评论,也很少将之纳入基本范畴作为阐释和评论的准则。这一点并不能成为拒绝对话的借口,在误读中对话,在对话中减少误读,需要一个历史过程。
对话比之独白,要艰难曲折得多了。由于母语文化的历史和传统不同,西方文论价值是错位的,双方的话语是不对称的。在这方面,我以为中国人对于西方固然有误读,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而西方人对于中国的传统文论的误读则相当的多。
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在读西方文论的时候,我们要懂得西方的基督教传统,至少熟悉圣经故事,但是西方文论家有几个是把掌握中国的道家和佛学经典当作对话的前提呢?缺乏价值的和逻辑的通约性,深度的对话是困难的。
在未来的岁月里,要改变西方文论独白的现象,形成真正的对话,就不能不考虑文化的潜在价值的错位而造成的转化的困难。这正是我们的历史任务。
(三)
回顾百年来的中国文论史,另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当代西方文论,尤其是阐释学、现象学、解构主义,都强调一切话语澄明性和遮蔽性的共生,对一切大前提,包括潜在的、预设的、暗示的大前提的批判、解构、悬搁是思想解放的开始。但是这对于他们自身却是例外的,一旦按辩论术,让他们“自我涉及”,就不能不产生悖论。悬搁、解构和批判,如果包括他们自己的前提,只能导致他们的自我取消。如他们所说,没有超民族、超历史的文学性,不管是多么澄明的西方文论,也与中国传统的、现代的文学文本有着不可避免的错位甚至冲突。
一切理论不管其澄明性如何,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与阅读经验为敌的倾向,在跨国文化的阅读中尤其是如此。当然一切阅读经验都不可能是与理论绝缘的,经验无不打上阅读者的传统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的烙印,受到某种理念的诱导,但是,一切理论也同样受到理论家自身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的制约。不管何种阅读都毫无例外地包含着作者和读者深层的观念的冲突和交融,交融表现为经验对于对方文论的认同和归顺,而冲突则表现为经验对于文论观念的挑战和质疑。除非两种文化价值之间没有任何区别,才能出现单纯的认同和归顺的倾向。这不但在民族与民族之间是不可能,就是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也是罕见的。因而凡单纯表现出认同倾向的,则表明只涉及到两种文论之间互相重合的部分,而互相重合的部分往往是缺乏特点的,甚至是肤浅的。要深化对话的层次,就不能不从阅读经验和外来文论的冲突开始。
在冲突发生过程,任何一方,很少是从理论到理论决定自己的取舍的,理论往往不能单独决定自己的方向,相反,最后起作用的恰恰是经验。相对而言,理论有两个特点,而经验却正好与其形成互补。其一,理论比较狭隘,经验以其丰富性见长;它不但包含着已经明确的观念,而且蕴含着潜在的意念。而这种潜在的意念往往比之显性的观念更为深刻,更为强有力,更多元,包含着更多的可能性,因而也就更能补充、提示理论本身的遮蔽性,从而产生出某种创造性。其二,理论是间接的,而经验则以其直接性见长。正因为此,从理论到理论,从演绎到演绎,由于演绎法本身已经把结论放在大前提中了,因而很难产生出新知识,从而也就很难有直接的原创性,而从经验中往往能产生某种原创性。理论的演绎,要产生创造性或者次原创性,不是通常流行的证明,而是证伪。据波普尔的说法,证明只能解难题,只有证伪才能发展真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防止理论崇拜和权威理论家的任何崇拜,包括福柯、德里达的崇拜。如果真正忠实地把福柯和德里达自己的观念和方法贯彻到底,他们就不应该成为崇拜的对象,而应该成为解构的对象,正像英国社会学的鼻祖亚当·福格森在文明社会史论(An Eassy of The History on The Civil Society,Oxfort Press,)所说的那样,一切权威都不能是膜拜的偶象,而只能是争辩的对手(rival)。
对话不仅仅依靠理论本身的自洽性,而且还要参照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从中揭示文化价值和语言传统的矛盾。这必然产生出一个证明和证伪的痛苦过程,不将其中的矛盾和冲突揭示出来,从而对西方文论范畴进行补充、衍生,全部或者部分地颠覆,未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建设中国现代文艺学来说,光有中国传统的和西方引进的文学理论资源,是不够的,二者同样都要一种复杂的重构过程。重构有两种,一是,从理论到理论的转化,也就是光在逻辑上讲通,是初级的,因为在实践中可能行不通。把理论的转化和经典文学文本的解读结合起来,用阅读经验来证实和修正逻辑的演绎,以经过修正的理论来引导、疏理阅读经验,才能作螺旋式的上升。如果逻辑的演绎和经验的实证不取得动态平衡,就可能变为经院哲学和教条主义。
从根本上来说,理论话语和范畴首先就是直接从文本中进行第一手的概括为范畴,然后再在逻辑上加以演绎,使之体系化、自洽化的结果,理论大师们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概括和演绎就意味着遗漏和价值观念的渗入。当然,不管是阅读经验,还是权威的理论话语都有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个人的狭隘性。但是,从当前的现实而言,受到严重忽视的是阅读经验。
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把阅读经典的重要性提高到应有的程度:在引进西方文论以后,以阅读经验为基础,对其加以修正、衍生、改造,甚至颠覆,没有这样一种气魄和精神,我们就无法取得对话的权利。
这里,举一个例子。西方文论提出的审美范畴,现在已经取得了世界性的认同。它原本是希腊人用来同理性的抽象对立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情感价值。但是当代世界文学早已越过了传统的审美阶段,而进入了一个反抒情、反滥情、反煽情的阶段。对于这一切,西方文论并没有从审美范畴衍生出相对的范畴来概括这种潮流。审美的体系性显然存在着一个历史的和时代的空白。这种空白妨碍着美学的作为一种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体系的自洽。
对话要超越独白,最根本的标志是话题的交递;如果话题是单方的,则另一方将陷于被动。话题的交递可以保证双方的主动。
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话题,这应该在西方话题的空白失误之中。比如应该有一个“审智”的范畴与西方审美范畴相对立,或者相并列(注:审智作为一个学术范畴,目前在英语中很难找到对应的词语。本来美学aesthetics,就只是感觉学的意思,是日本人在翻译的时候把它和“美”联系了起来。这个译法很有灵气,但是要把审智转化为英语,而且要让它和在汉语中一样具有与审美平等的意味,却很难从aesthetics派生出一个相应词语来。不得已而求其次,我们暂时把它译为intellct-aesthetics,或者examing-intellctural.)。一方面描述当代历史语境中的文学性的新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对于中国古典文论“诗缘情”和西方文论审美说的逻辑延伸。美学(aesthetics)本是一种感觉的学问(日本人把它译成“美学”和“审美”),相对于理性的学问。由于情感直接与感觉相联系,情感不可能直接感知和表述,它只能冲击感觉使之发生变异,所以文学繁荣的最初标志是审美价值的张扬,最高成就是通过感觉变异而进行抒情的古典派和浪漫派。这就给康德一种印象,好像审美价值就在于情趣判断。然而现代和当代文学艺术的发展表明:情感的审美并不是文学性惟一的法门——现代派艺术显示的是超越情感,反抒情,把抒情当作滥情、煽情来嘲笑;代之以超越情感直接通向智性的艺术。冷峻和智性的结合成了世界现代文学的特点。从感觉超越情感直接到达智性是世界当代文学的潮流。
西方文论对此已经作出反应,许多理论家明显地离开或是忽视文学与哲学之间的区别,有的理论家(如乔纳森·卡勒)认为,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非常模糊,可以用文学理论解读非文学文本,文学理论与文学性没有多大关系。有些西方理论家宣称,文学不过是自己哲学观念的图解而已(加谬)。当然,也有一些理论家表示反对(如布鲁姆)。
对于20世纪中后期世界文学声势浩大的智性潮流来说,西方美学在范畴上并没有在历史逻辑的统一上作出体系性的衍生(注:从美学范畴来说,现代文论还提供了一个审丑的范畴,但是审丑,仍然是与情感相联系的,严格来说仍然是属于审美范畴,审丑仍然出于情感价值,而不像审智乃是出于对于情感的超越。)。
要真正平等的对话,不能从西方文论成功的地方开始接过话题,应该从西方文论跌倒的、失落的、遗漏的、混乱的地方开始。
平等不仅是政治上的平等,而是智力上共同达到相应的水平。完全的平等并不存在,平等是动态的,它意味着在一些方面的滞后,另一些方面的超越。没有部分超越,平等只是一种文明的礼貌,而礼貌总免不了虚假,礼貌是掩盖不平等的最好手段。
俄国形式主义者分析所谓“不成功的爱情小说”得出一个公式:A爱上了B,但是B不爱A。A设法让B爱上了A,而A却不爱B了(注:什克洛夫斯基:《故事和小说的构成》,《小说的艺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这其实不仅仅是爱情小说的模式,而且是一切小说心理结构模式。人物不管是处于爱情还是处于友谊之中,不论是战火中的盟友,还是相依为命的亲人,只要是叙事的文本,都只能是“心理错位结构”。《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周瑜和曹操的心理关系,只能归入这种错位范畴(注:参阅本人《审美价值结构和情感逻辑》,华中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333页。)。这样,我们才能以概括性更为深刻而广泛的范畴与涵力不足的斯克洛夫斯基、与繁琐的普罗普和格雷马斯对话。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水平的对话的标志是转换话题,以转换话题进行挑战。
没有挑战,对话不可能成为多声部的交响,只能沦为单方面的寂寞的回声。如果所有的命题和包含在话题中的方法和价值观念都是西方提供的,我们就只能像中学生那样解难题,永远不会像《东方主义》的作者那样提出问题来刁难一下西方学者。
挑战不仅仅是为了洞察对手,而且是为了在与“他者”的对话之中更为深刻地了解我们的本质。中西文论也一直强调,弱势文化中包含着强者所没有的东西。但是并不存在着一种固定的、现成的我们的本质,我们的文化特点只有在与“他者”对话中才能发现。本质不是静态的,而是在与“他者”对话中在本来朦胧的深层中建构的,有如战争和恋爱建构着人的深层本质一样,对话也使得我们的本质更加动态化。
这一点对于强势文化,也是一样,没有挑战的独白,只能导致单调的重复和停滞。
面对未来的世纪,不管是为了认识自己,还是为了发展、更新自己的文论,都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对话上。光是悲叹我们这一代人的缺乏原创的自觉,甚至连次原创性也很少很少,不过是滥情而已。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西方文论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美学论文; 意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