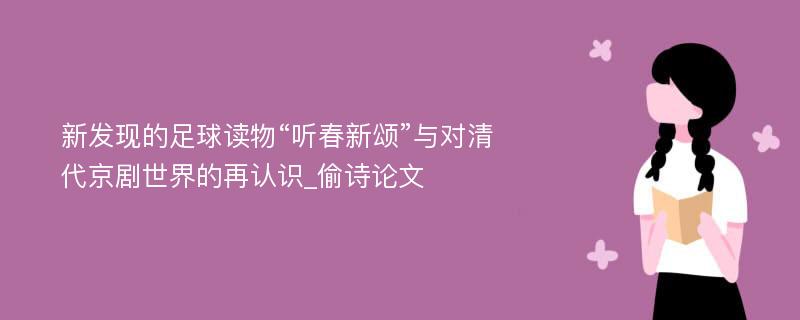
新发现足本《听春新咏》与重新认识清嘉庆北京剧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坛论文,北京论文,新发现论文,清嘉庆论文,听春新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听春新咏》是清代嘉庆年间刊刻的一部“梨园花谱”性质的戏曲史料。由于它的成书年代较早,且体例编排颇有特色,在清代戏曲史料中是较为重要的一种。其书能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而不至于湮没无闻,端赖民国时张次溪将其收入《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笔者在研读张次溪辑校本时发现其内容不全,缺失甚多。其一,根据《听春新咏》之《例言》:“先以昆部,首雅音也;次以徽部,极大观也;终以西部,变幻离奇,美无不备也。至蒋、陶诸人,音艺兼全,盛名久享,自不屑与哙等伍,特以别集标之。”①此书本应有昆部、徽部、西部、别集四卷,但现在张氏辑校本整个“昆部”都缺失了。其二,依据徽部之目录,著录徽班优伶54人,而现在的张氏辑校本仅有前18人的内容,其余三十六人均付阙如。整体来看,张氏辑校本《听春新咏》缺失内容占到整本书的一大半。然而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学术界似乎对此既没有发觉,亦无人尝试去解决问题,找出缺失的内容。从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胡忌等《昆剧发展史》、王芷章《中国京剧编年史》等研究著作来看,对《听春新咏》都有引用,但著者所见皆非全本。 近年来,笔者一直想解决这一问题。在多家图书馆爬梳文献的过程中,先在首都图书馆找到了戏剧研究家马彦祥收藏的《听春新咏》,一函四册,三卷,令人振奋的是,其书的徽部卷是全备的,遂抄录缺失部分,但仍缺昆部。后又查阅到中国国家图书馆亦藏有一部一函四册的《听春新咏》,翻阅之后,发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是四卷的足本。20世纪80年代,周育德在王芷章的指点下,找到并整理出乾隆年间刻本《消寒新咏》(据周作人藏书),成为晚近清代戏曲史料一个较重要的发现;时隔多年,笔者发现并补足嘉庆年间的《听春新咏》,又为学术界提供了清中期戏曲研究的珍稀史料。 此书的编著者,题留春阁小史辑录、小南云主人校订、古陶牧如子参阅,三人生平皆不详,大约都是由江南来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的书生。据书之序言、缘起,留春阁小史“浪迹都门”,醉心梨园,惯于听歌,“十年箫管”,“爰取鞠部诸郎”,“写就伶人小名”,“所及者,犁为四部,各缀数言”,再呼朋引类,“求此友声”,遂与小南云主人、古陶牧如子等“往来商榷”,相互唱和,汇聚诗词,编辑成书。 足本《听春新咏》的篇幅约五万字,在清代已知同类书籍中是篇幅最大的;更重要的是,其书体例上有新的创造,特色鲜明,不落前人窠臼。此书在编排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分部排列,昆部、徽部、西部、别集的分类是前此未见的。书之《例言》云:“梁溪派衍,吴下流传,本为近正;二簧、梆子,娓娓可听,各臻神妙,原难强判低昂。然既编珠而缀锦,自宜部别而次居。”当时的一般文人总觉得昆剧典雅精致,而高看一眼;对于二簧、梆子等花部乱弹则大率不屑,难入法眼。但《听春新咏》的编著者非常客观公允,对于各部、各剧种一视同仁。那种认为二簧、梆子也各臻神妙,与昆剧难以强判高下的观剧态度,在嘉庆年间的文人墨客里实在难得。昆、西、徽并列,确是有新意的编排方式。此外,编著者将三部中年齿稍长、久负盛名的优伶单列为别集,加以品评月旦也是合适的。 书内天涯芳草词人撰写的《弁言》云:“尝阅《燕兰小谱》、《日下看花记》诸书,皆所重在人,题咏俱出一手,观者每有挂漏之疑焉。小史此集,编珠排玉,专采诗词,不为群花强分去取,亦不为群花强判低昂。”假如对某部有所偏爱,在入册优伶的挑选和评价上就有可能主观随意,难以做到一视同仁,其书则不能客观反映当时剧坛的真实状况;鉴于此前同类著述存在的问题,《听春新咏》采撷广,搜罗富,且客观真切,不妄加主观判断,其史料价值自然胜过一般的同类书籍。对于同部优伶的评判,书之《例言》云:“各部中群芳林立,霞蔚云蒸,孰轾孰轩,难以强定。今惟以得诗之先后为次第。至若兼咏群花,一时并集,不得不稍分位置,然亦遍采舆评,不敢略存私臆。”尽量做到吸收大多数人的意见,公正恰当,并不掺杂多少个人的主观私心,予以强判甲乙,这也是难得的态度。故而天涯芳草词人有【浣溪沙】赞云:“赏识从无似此真,排珠比玉部居匀,惜花判得费精神。”堪称允当。总之,这部书在同类梨园花谱里,是体例新颖、史料丰富,有较高文献价值的一种。 此前,学术界所看到和引用的一般都是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辑校本;现在发现了足本的《听春新咏》,有助于对清嘉庆年间的北京剧坛重新做一番巡礼和认识。 首先,关于嘉庆朝北京剧坛的格局问题。 清代乾隆一朝,戏曲空前勃兴,演出极为繁盛,是戏曲声腔剧种演变的承上启下阶段。当时的帝都北京,市肆繁华,娱乐业发达,是全国戏曲演出的荟萃集散之地,来自全国各地的戏班、剧种在京城急管繁弦,各奏其能,相互竞争,此消彼长。正如小铁笛道人《日下看花记》所云:“有明肇始昆腔,洋洋盈耳。而弋阳、梆子、琴、柳各腔,南北繁会,笙磬同音,歌咏升平,伶工荟萃,莫盛于京华。”②从乾隆到嘉庆,京城剧坛几经变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往者,六大班旗鼓相当,名优云集,一时称盛。嗣自川派擅场,蹈跷竞胜,坠髻争妍,如火如荼,目不暇给,风气一新。迩来徽部迭兴,踵事增华,人浮于剧,联络五方之音,合为一致,舞衣歌扇,风调又非卅年前矣。③ 乾隆时,京腔六大班、魏长生的“川派”先后在京师剧坛各领风骚,彼此消长。接着徽部勃兴,风调为之一新。到了嘉庆中期,北京剧坛的发展状况又是如何?据前引之《听春新咏·例言》,嘉庆朝的演剧活动似乎已不再是那种百舸争流的局面,而是由“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渐趋于“割据山河、三足鼎立”。昆部自然是雅部正声的昆剧,而西部则以秦腔为主,但此秦腔又非陕西、甘肃之原始秦腔。《听春新咏》云:“盖秦腔乐器,胡琴为主,助以月琴,咿哑丁东,工尺莫定,歌声弦索,往往龃龉。”其伴奏乐器用胡琴、月琴,艺人多出自本京,又喜追慕学习魏长生“川派秦腔”的路数,综合判断,西部实乃是融合了京腔、川派秦腔等的“新秦腔”。徽部的情况最复杂,“联络五方之音,合为一致”,昆、乱兼演,是多种声腔剧种的聚合。昆、西、徽是当时京城剧坛最有影响的三部。 需要指出的是,三部并不是势均力敌的态势。根据足本《听春新咏》综合统计,昆部录优伶20人,西部录优伶16人,而徽部录优伶竟然达到空前的69人!(别集杂录名伶20人,其中昆、徽、西三部皆有,已分别计入各部。)从中不难窥探京城剧坛剧种之间的势力消长。昆剧,是老的优势剧种,虽然乾隆朝后期已显出颓势,但毕竟是正声雅音,根基深厚,同时还受到清廷的提倡,故仍占据重要的一席。此前未发现《听春新咏》的昆部,如只看到张次溪整理本中的徽部与西部,可能会认为昆剧在嘉庆年间已经衰落得不成样子了,这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也不利于从整体上宏观把握当时的剧坛。以魏长生为代表的川派秦腔在乾隆后期的京城耸动一时,但因其过于淫靡泼辣,发展受到朝廷的限制,且较俚俗,难入中上层人士之耳目,势头已有衰退。嘉庆时,势力最强、锋头最健、最具人气的,还得数徽部。 打个比方,虽然是“三足鼎立”,但徽部犹如三国时的曹魏,势力最大,最有一统天下之气概;而昆部、西部则如东吴、西蜀,地盘既小,又随时有被曹魏蚕食鲸吞之危险。那么诸剧种之间是何关系?它们如何相处?笔者认为,各剧种之间并非泾渭分明,也绝不是一味的王霸之争,更重要的是取长补短、相互融合的一面。任何剧种都有自身的优长,事实上,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只存在单打一的某一剧种,而是多种剧种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各剧种的协调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犹如大自然的生态坏境,剧种之间具有相互竞争、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错综复杂关系。诸剧种在交流中发生变化,碰撞中产生火花,竞争中引发新陈代谢。比如同一剧目,昆部、徽部、西部皆演绎,各具其妙。据《听春新咏》记载,昆部迎福部凌吉庆的“《偷诗》一剧,冷面热肠,描摩曲肖。殆与徽部李菊如(添寿,四喜部)作赵家姊妹矣”。同是《偷诗》,但昆部与徽部演来各得其妙,各擅胜场。《香山》也是徽部、西部皆演,而有所不同,“盖西部《香山》与徽部稍异。徽部服饰庄严,西部则止穿背甲,非雪肤玉骨者,不轻为此”,服饰大不相同,演来也意趣有别。西部双和部李小喜演《香山》一剧,“双湾纤藕,百啭新莺,与徽部张芰香各极其妙”。对于不同剧种的优伶演绎相同剧目的情况,观剧者肯定会做品评、比较,而戏班的优伶之间也肯定会互通有无、扬长避短。各剧种争奇斗艳,各不相让,最后留在舞台上的一定是经过竞争后的最有魅力、最有生命力的艺术。 学术界一般认为,京剧诞生于1840年左右,其实在京剧诞生之前一定有相当长的一段孕育时期。从《听春新咏》来看,嘉庆年间的徽部势力浩大,最有前途。以徽部为主要力量,融汇昆部、西部等,助推剧种的交流衍变,乃是大势所趋,也是水到渠成。《听春新咏》清晰地反映和彰显了这一点,毋庸置疑。故而此书对于研究清中后期戏曲剧种的交流、竞争、嬗变,特别是京剧的形成,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其次,重新认识“联络五方之音”的徽部。 书中徽部列出三庆、四喜、和春、三和、春台五部。如前所言,昆部专演昆剧;至于西部,演秦腔。然则徽部演的是什么戏?如果笼统地说徽部演的是“徽剧”、“徽调”,那恐怕只是想当然的望文生义。客观而论,徽部的情况最为复杂。书里虽提到了二簧,但何谓二簧,学术界众说纷纭,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不如姑置不论。笔者认为,不妨从徽部演出的实况来考察一番。乾隆年间,《消寒新咏》的作者说:“余到京数载,雅爱昆曲,不喜乱弹腔,讴哑咿唔,大约与京腔等。(徽部)惟搬杂剧,亦或间以昆戏。”④这位作者是在谈徽部优伶时讲这番话的,可知徽部虽然主唱乱弹,但实际也演昆剧。从《听春新咏》的实际来看,情况更复杂,徽部中实昆乱兼演。徽部的艺人特别善于博采众长,徽部的演出有昆剧,有乱弹,包括二簧、秦腔,甚至各种小曲等。所谓徽部,包容性最强,实乃合众多声腔于一部。徽部兼容并蓄的特色在当时是最为突出的。 以三庆部郑三宝为例。他“浓纤合度,亦雅亦庄,挹其丰采,如于纷红糅绿中忽睹牡丹一朵,艳丽夺目,使人爱玩不置。工于昆剧,偶作秦声,非其所好。《思凡》、《交账》诸剧,淡宕风华,好声亦为四起,毋谓阳春白雪必曲高而和寡也。”再结合《众香国》里的记载:“(郑)瘦小有神,所到处色舞神飞,刻无宁暇,座客俱为忘倦,盖生成水性也。演《小盘》、《卖肉》诸出,情致描摹,声音嘹喨,固有未可忽视者。”⑤他在徽部演二簧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同时又工于昆剧,还能偶作“秦声”,故而笔者推测郑三宝是“全能演员”,兼擅诸多声腔剧种,这就是徽部的特色,也是徽部最有市场、最有前途的原因。 徽部有的优伶在艺工昆剧的同时,还兼唱秦声。如三庆部的谢添庆,“《絮阁》、《寄柬》诸剧,歌喉圆亮,态度舂容,出字收音,颇遵法律”,虽唱昆剧,但“间唱秦声,亦委婉多风,靡靡动听”。一个人同时兼擅昆剧与秦腔,这在乾隆年间是比较少见的,纯粹的昆班中人更不屑为。但到了嘉庆年间,却由徽部中人完成了昆、秦艺术的交融。再如三庆部的陈庆寿,“演《铁弓缘》,声音浏亮,体度褊褼,论者谓有刘朗玉之风焉;至《佳期》、《藏舟》,则传派既佳,更臻妙境矣”。《铁弓缘》乃西部名剧,要博得好评,得走魏长生、刘朗玉的泼辣淫靡路子,庆寿演来,得心应手;难得的是,他演昆剧也有法有度、中规中矩,这就不易了。三和部的吴寿林“雅擅秦声曲调新”,“演《香山》、《赠镯》诸剧,吭滑停云,肤光耀雪,能使观者如堵墙”;和春部的王双秀也是“昆腔诸剧,节奏俱工”,可知兼擅多种声腔的,不在少数。 徽部演昆剧不仅不下于昆部,有时甚至比纯演昆剧的伶人还要高明。春台部的黄玉林,“《水斗》、《瑶台》诸剧,神韵颇似雪梅(张七官,金玉部),而闲暇尤胜”。黄玉林演的《水斗》、《瑶台》,不但富于神韵,表情气度似更胜昆部优伶一筹。 三部之中,徽部可以兼演昆乱,诸腔杂陈,但西部却不宜兼演昆剧。至于昆部,更是壁垒森严,放不下身价,一心守着雅部正声的正统地位,最不易与其他声腔剧种发生关联。毕竟昆剧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剧种,流动性较弱,本无足怪。三部比较,徽部无疑最具活力,既有辐射渗透其他剧种的影响力,又有吸纳其他剧种优长的熔铸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有识见的昆部伶人似乎已经意识到徽部的发展潜力,出于经济利益或其他的考虑而接近徽部,向徽部学习。比如庆宁部的钱德明,在演昆剧之外,“工唱【满江红】小调,又善弹三弦子”,金玉部的孙喜林也是“思春小曲独绝一时”,可见都是别有所长的。 以前讲徽部过于强调它腔调的“新”,笔者认为徽部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实更重要。徽部能“联络五方之音”而“极大观”,其实是兼收并蓄、诸腔杂奏的结果。较之昆部、西部,徽部在艺术上是兼容并包、细大不捐的,名为“徽部”,实则是“合班”,这是徽部的最大特色,也是徽部得以立足并迅速发展、蓬勃壮大的根本原因。其实徽部也抓住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乾隆和嘉庆朝两度打压禁止魏长生一派秦腔的演出,也给徽部的争夺市场、发展壮大提供了良机。 再次,规模庞大、富有新鲜活力的徽部。 当时徽部班社的规模在《听春新咏》里也有所反映。拿和春部为例,“群芳林立,几至百人,派戏难以遍及”,以至于该部很优秀的艺人李巧林都不太排得上戏。一个班社竟有上百人,规模之大,可想而知。当时徽部中又以四喜部人才最盛:“盖徽部得人,四喜最盛。自集中所录诸人外,如陈天福之音韵铿锵,中添喜之神情淡雅,朱宝林之折矩周规,双喜之玲珑跳脱,至宝玉、祥林、王添然、田寿林辈,或则风华研媚,或则绰态娇憨。冀北空群,江南撷秀,几谓人材之美尽于斯矣。”四喜部除了入册的十余人,尚有不少遗珠之憾,可谓极一时之盛。徽部兴盛,人才自然如小溪之归江海,尽归于斯,这也是向来人才流动的规律使然。徽部的优伶文武昆乱不挡,雅俗共赏,自然最得观众欢迎。至于昆部、西部班社的规模,虽无确切记载,但应该不如徽部壮大。 徽班具有新鲜活力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延请昆部的名教师教授子弟。相反,如果昆部请徽部、西部伶人教授,那是不可想象的。如昆旦张蕙兰,早年在《燕兰小谱》里就有记载:“苏伶张蕙兰,吴县人。昔在保和部,昆旦中之色美而艺未精者。常演《小尼姑思凡》,颇为众赏,一时名重。”⑥张氏后来教授过诸多的徽部优伶,如三庆部的赵庆龄,“近得吴下名师张莲舫(蕙兰字莲舫),留心问业,更益精纯。故《思凡》、《藏舟》、《佳期》等剧,宫商协律,机趣横生。《春睡》一出,星眼朦胧,云罗掩映,尤得‘半抹晓烟笼芍药,一泓秋水浸芙蓉’之妙,转觉卿家燕瘦,较胜环肥矣”。得到张蕙兰的悉心传授,赵庆龄技艺大进,不但演唱技巧得到提高,演戏的神情意态等深层次的技艺也有了明显进步。和春部的许茂林也是张氏弟子,“尝见其《园会》、《楼会》二剧,一写风情,一摹病态,各极其妙。后知为张莲舫所授,瓣香一缕,直接吴门,宜有是金科玉律也”。徽部中人得到昆剧老伶工的教授,演起昆剧来,也是规规矩矩、切中绳墨的。三多部的陈庆寿同样是张氏入室弟子。张氏当时在京城堪称菊坛名师,徽部中人纷纷向其请益,“盖自莲舫入都,仅经数月,而珊瑚半归铁网,桃李遍植金台。古人所云:伯乐一过,而冀北空群者”。真可谓桃李满都下。笔者推测,张氏有可能是徽部专门请到京城来教授学生的。此外,四喜部黄庆元的师傅是唱昆剧的朱宝林。徽部优伶致力于研习昆剧,会在声腔身段,乃至气质格调等多方面有超凡脱俗的变化,对于融合贯通、提高演技,乃至艺术创新是极有帮助的。 再次,嘉庆时北京优伶的地理籍贯和流动性。 就徽部、昆部、西部来说,徽部优伶的来源最复杂,54人中,扬州32人,苏州7人,安徽7人,皖江2人,本京2人,直隶1人,湖北2人,湖南1人,其中扬州人最多、最活跃,苏州、安徽人次之,直隶、湖南、湖北等地仅有零星优伶。虽曰徽部,其实并非以安徽人为主,主要是江苏人,这尤其要加以注意。昆部19人中,18人皆苏州人,仅一个安徽人,说明昆部规范严整,地域色彩最浓,最难通融。西部12人,扬州4人,本京4人,直隶1人,陕西1人,山东1人,山西1人。西部虽以“西”字冠名,但优伶来自西北、四川等地的非常少,反倒以扬州和本京人为主。这也说明,西部虽最初来自西北,但唱红后,京师和其他地方的优伶打破地域界限,竞相学习。别集共计20人,徽部占到15人,其中苏州5人,扬州4人,皖江3人,安徽2人,太仓1人;昆部1人,苏州人;西部4人,四川2人,本京1人,陕西1人。别集仍是以苏、皖优伶为多。 综合《听春新咏》全书,徽部竟达69人,昆部20人,西部16人。通过比较可知,徽部的包容性最强,优伶的籍贯最复杂,来源最广泛。徽部之中扬州有36人,西部中扬州有8人,扬州人差不多占了嘉庆时整个京城剧坛乱弹的半壁江山。值得注意的是,兼擅诸种声腔的多为扬州人,可见扬州班最没有门户之见,最善于博采众长,因为扬州班本身就是“合班”。通过《听春新咏》,可让学术界对扬州戏曲人才和班社在乾隆、嘉庆年间的北京所占的突出地位、所起的杰出作用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 过去有的学者把徽班、扬班分别而论,认为不是一回事。现在看来,显然有问题。据《听春新咏》,嘉庆时的徽部优伶以扬州人为主,徽班和扬班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一回事。在乾隆后期到嘉庆末的较长一段时间内,扬州人是北京剧坛的主力军。 据《听春新咏》,清嘉庆时优伶的流动性已较频繁,但流动的方向是有一定规律的。徽部勃兴后,优伶由昆部、西部转到徽部的情况尤其多,反之则少见。庆宁部的潘寿林,“后人迎福,转隶四喜。今秋复归本部”,在昆部、徽部之间跳了好几次槽。王桂林“初隶金玉,与陆朗仙真馥、朱香芸后先济美。后入富华,与陶柳溪、朱素春同享盛名”,先在昆部,再转至徽部的三庆部,但“演剧全仿柳溪,同守梁溪正派”,演的仍是正宗的昆剧,可知徽部最不排斥人才。陶双全也是“昔在霓翠、富华与云谷(蒋金官)齐名”,后转入三庆部的。西部大顺宁部的苏桂林,后来也转入三庆部。有的甚至于亲兄弟都不在一部,一个徽部,一个西部。优伶流动的背后是经济利益、师承关系、演技水平、班社包容性等因素的综合反映,但一般来说,经济利益是占首要地位的。昆部、西部的优伶较多转入徽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徽部的演出市场好、效益好,且更能吸纳人才。 最后,《听春新咏》记载的嘉庆时各部演出剧目和对表演艺术的品评。 根据《听春新咏》统计,各部的演出剧目情况如下(未计别集): 徽部:《思凡》、《藏舟》、《佳期》、《春睡》、《盘殿》、《杀四门》、《烤火》、《番儿》、《絮阁》、《偷诗》、《水斗》、《断桥》、《盗令》、《杀舟》、《独占》、《卖身》、《孔雀裘》、《园会》、《铁弓缘》、《十二红》、《小寡妇上坟》、《送灯》、《卖胭脂》、《庙会》、《踢球》、《思春》、《醉归》、《金盆捞月》、《交账》、《楼会》、《寄柬》、《茶叙》、《问病》、《顶嘴》、《卖饽饽》、《雄黄阵》、《背娃》、《洛阳桥》、《借扇》、《赠珠》、《扇坟》、《关王庙》、《拷红》、《炳灵公》、《荡湖船》、《醉归》、《闯山》、《捉奸》、《戏洞》、《施公案》、《打面》、《檀香坠》、《巧姻缘》、《花鼓》、《珠配》、《扯伞》、《雪夜》、《别妻》、《琴挑》、《醉妃》、《双官诰》、《寄子》、《盒钵》、《折柳》、《淫骗》、《香山》、《赠镯》、《瑶台》、《庆顶珠》、《打线》、《度卜》、《盘丝洞》、《挑帘裁衣》、《斋饭》、《打饼》、《回头岸》等,共计七十余出。 昆部:《羞父》、《痴梦》、《盗令》、《反诳》、《秋江》、《跪池》、《姑苏台》、《惨睹》、《白罗衫》、《思凡》、《荡湖船》、《拾画》、《叫画》、《跳墙》、《下棋》、《拷红》、《巧姻缘》、《游街》、《偷诗》、《折柳》、《絮阁》、《水斗》、《活捉》、《和乐》、《雷峰塔》、《翠屏山》、《赏荷》、《长亭》、《窥醉》、《藏舟》、《番儿》、《千秋鉴》、《花报》、《和番》、《瑶台》、《游园》、《惊梦》、《盘秋》、《阳告》、《夜课》、《教子》、《思夫》、《相约》、《讨钗》等,共计四十余出。 西部:《赐环》、《梅降雪》、《富春楼》、《血汗衫》、《背娃》、《百花亭》、《换布》、《打都卢》、《吞丹》、《戏叔》、《裁衣》、《剃头》、《写状》、《捉奸》、《赠镯》、《檀香坠》、《香山》、《卖胭脂》、《缝带》、《登楼》、《揭帐》、《卖艺》、《别窑》、《九钟罩》等,共计二十余出。 综合来看,徽部的剧目是最丰富的,且文武昆乱兼备,折子戏和整本戏俱有。昆部的剧目较“纯”,以折子戏为主,一般不会羼杂乱弹。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两部或三部都演的相同剧目,而这些往往是徽部优伶借鉴、改编或直接向昆部、西部学习的。三部中徽部和昆部剧目的重合最多。笔者没有对徽部剧目做更进一步的分析,譬如细分某剧是秦腔、某剧是二簧等,因为笔者认为,有些剧目可能是多剧种共同演绎的,演法不止一路,难以考镜源流。以徽部剧目为例,有些是徽部原本有的,有些可能是移植的,有些可能是改编的,情况较复杂,不便一概而论。但是研究者可以从上述三部剧目里,探查嘉庆时期北京剧坛有哪些剧目较流行,而那些多剧种都演的剧目可能是当时观众喜闻乐见的,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班社对剧目的选择和剧坛的审美风尚。 《听春新咏》一书对于嘉庆时优伶的表演艺术时有会心赏评。观剧者有着独特的艺术品位和审美见解,不抱门户之见,尤为难得。《听春新咏·例言》云:“只取登场情景,众所共见者,铺叙数语。……间作一二点缀,神之所注,笔亦随之。”可知编著者看重的是“场上”,是优伶的舞台技艺,表演艺术,而非津津于优伶之色相。那种以舞台演出为主,片言居要的批评方式,其实来源于古代传统的诗词品评。对于戏曲演出,“场上”情况稍纵即逝,早已风流云散,最难探究;而《听春新咏》恰恰关注嘉庆时的“场上”,提供了研究当时舞台实况、优伶演技的珍贵史料。 譬如,对于旦角妖娆泼辣一派的演法,《听春新咏》就提出了不同流俗的独特见解。本来魏长生是这路戏的祖师爷,后来者皆学他,但《听春新咏》认为,“婉卿(即魏)《滚楼》等剧,形容太尽,毕竟少一‘含蓄’”,反而是后来的姚翠官“酝酿深醇,含情不露”,姚的“《温凉盏》诸剧,绘影摩神,色飞眉舞,动合自然,绝无顾盼自矜习气”。由此见出著者偏于含蓄蕴藉的艺术品位,而这可能也是魏长生的川派演法在嘉庆时已随时代和观者审美而变化的一种反映。韩四喜走的也是妖娆妩媚一路,书中评价他“《背娃进府》能与姚翠官争长,而双翘莲瓣绝类婉卿(魏三),为近来诸部之冠。且其珠藏川媚,极色飞眉舞之奇;舌底澜翻,集巷语街谈之巧”。韩演戏不但有风月之浓情,眉眼留媚,又善道白,引观者解颐,真是擅绝一时,名下无虚。 《听春新咏》中还有对于嘉庆优伶各种演技的描述。如飞来凤“《蓝家庄》一剧,描摩醉色,由白而红,非强为屏息者所能仿佛,歌坛中绝技也”,这是赞赏优伶对于醉酒情态的细腻描摹。大顺宁部的何玩月擅长武戏,“《无底洞》、《杀四门》、《庆顶珠》等剧,戎衣结束,莲瓣飞扬,握槊持刀,有雪舞风回之妙,娘子军中殊堪领队”。武戏为徽部、西部所擅长,这些描述非常珍贵鲜活地反映出嘉庆京城舞台上的优伶实况,包含丰富信息,颇具研究价值。 有趣的是,《听春新咏》还对旦角优伶演唱时的“口型”问题做了分析。书云: 《断桥》、《刺梁》诸剧,精神融结,曲调清腴。赵仿云(小庆龄)、郝秋卿(桂宝)每称其口齿颇清,而强作解事者动欲吹毛求疵。然余闻广平叶氏云(吴人,最精音律,著有《中原音韵》、《纳书楹》等书行世):“旦色止取神韵,于字面不宜苛求,如‘皆’、‘来’之张口,‘车’、‘遮’之参牙,不到十分则其音不足,必使小小樱桃不逾分寸,即西施、王嫱亦变成嫫母矣。”此虽恕词,实为确论,则潘郎之妙,宁第在引商刻羽间哉。 有的字,如讲究字正腔圆,演唱时势必要五官移位,甚至龇牙咧嘴,口型难看,而旦角又无胡子遮挡,无疑有破坏美的形象的忧虑。那么演唱时究竟是斤斤计较于字音,还是点到为止,以保持女性的美丽形象为上呢?《听春新咏》似乎还是倾向于后者,所谓“潘郎之妙,宁第在引商刻羽间哉”。毕竟演戏不能太较真,过于吹毛求疵,反而失去了舞台上美的形象。 《听春新咏》生动反映了嘉庆年间北京剧坛各剧种、戏班搬演的实况,犹如当时的“观剧指南”,兼具文献和理论价值。此书足本的发现,为学术界重新认识嘉庆年间的北京剧坛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从乾隆到嘉庆,再到道光,北京剧坛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剧种声腔的交流、融合、衍变是发展主流。嘉庆一朝,在徽部、昆部、西部的三足鼎立中,以徽部为主导,荟萃五方之音,呈现洋洋大观。嘉庆时,北京剧坛的优伶以江苏、安徽人为最多。在苏、皖人主导的徽班里,诸腔杂奏,急管繁弦,不经意间孕育着新的声腔,潜移默化中发生着新的变化。以前经常讲昆乱合流,其实不够全面。所谓合流,既有乱弹与昆剧的交流,也有乱弹内部的交流,而且合流的主导方是乱弹,主要是乱弹吸收昆剧的优长,主流是乱弹融合昆剧,昆剧间接影响乱弹。昆剧本身早已定型,壁垒森严,不易于变化了。 剧种之间的竞争、交流、融合乃是孕育产生新腔调、新剧种的基础。以前学术界研究京剧的形成,向上注重乾隆朝,往下关注道光朝,似乎夹在中间的嘉庆朝可有可无。现在看来,嘉庆朝正处在承接上下的枢纽地位,道光后期,京剧已经基本形成,而嘉庆一朝实是京剧形成的前夜,其重要性可想而知。过去因为史料匮乏,对嘉庆年间的北京剧坛缺乏全面了解、认识,现在根据《听春新咏》,再加上《日下看花记》等书,可以让学术界更清晰地辨识嘉庆剧坛的真实状况,了解京剧形成前夜,北京剧坛在进行着怎样错综复杂的激烈竞争和新陈代谢。 注释: ①本论文所引《听春新咏》系征引自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嘉庆四卷刻本,下面不再注出。据友人告知,国内某藏书家手中藏有一部《听春新咏》,但因种种原因,笔者未得寓目。他日有机缘,当与此本做一比较。另,由于张次溪编纂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料》错讹较多,为严谨计,本论文所引清代文献史料一般都找到清代原刻本进行校对,特此说明。 ②③小铁笛道人《日下看花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嘉庆八年(1803)刻本。 ④《消寒新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乙卯年(1755)三益山房刻本。 ⑤《众香国》,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嘉庆间(1796—1820)刻本。 ⑥《燕兰小谱》,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间(1736—1795)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