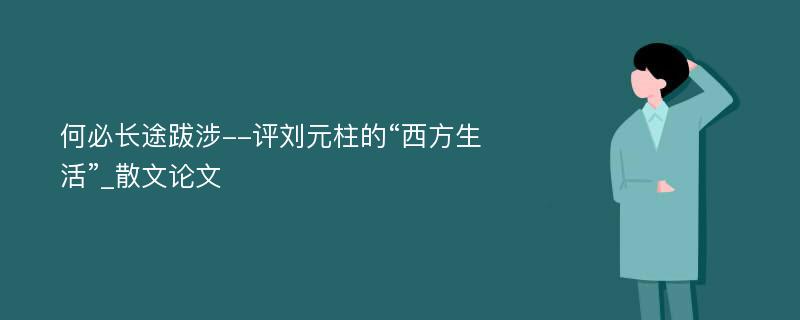
为什么远行——评刘元举《西部生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部论文,生命论文,评刘元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中国西部的荒芜冷寂,常常会带给我一种无以名状的不适感。可是作家刘元举十二万字的长篇散文《西部生命》(春风文艺出版社),从第一页就深深地攫取了我。当寒夜的星辰如同生命的滴滴汁液渗入都市聒噪乏味的夜里,我正跟随在刘元举的身后,跨越了时空无边的藩篱,从中国版图的巨大的鸡头到宽阔的鸡尾,作着艰难的漫游。河西走廊、花土沟、交河、高昌、敦煌、柴达木、黄河源……大大小小呆板枯燥的地理名词,尔今已经是视野里一幅幅实实在在的宏观图景了。十二万字,丈量着刘元举的心路历程。精神上的亢奋状态使我直到目睹了刘元举最后一个驿站,才肯安安心心地合上书页。是时,东方已现鱼白。窗外,一个人声鼎沸的都市的早晨正夹杂在人车的长河中滚滚而来。
于是,今夜的经历,仿佛是一场醒来之后难以置信的怪梦了。刘元举极力渲染的西部蛮荒,完全是“系统”之外的事,对于生活在水泥森林里的都市人来说,一切都显得不可理解,当然也不必去理解。可是西部,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在我们的思想之外,在我们的系统之外,真实地存在着。
刘元举就为我们展示了这个真实,凭借他男性的目光,和汪洋恣肆的语言。于是,没有一丝绿荫的平地与土丘,被太阳烘烤着的沙漠,干涸的河床,龟裂的土地,在他的笔端无所顾忌地伸展着;于是,我们碰触到了这样的句子:
泛着硭硝的荒漠,像月球的地貌,麻木得寸草不生;那泥岩构造的秃丘,从上到下密密地排列着痛苦的皱褶,不用细看,就会感到那一道道褶子像深深的泪槽,扭扭歪歪,憋憋屈屈。一排秃丘是这副模样,再一排秃丘还是这副模样,柴达木到底有多少这样的秃丘?这些苦难沧桑的面孔,都在诉说着柴达木的苦难,不管有没有人听,也不管听懂听不懂,它们就这么永永远远地说下去……(《从渤海到瀚海》)
刘元举把冷漠无声的自然西部当成一个有情感的人来描写,写得如此哀婉苍凉。作家极力铺展着西部粗砾茫漠、自然与生态环境的恶劣,不会是无所用心的。那不会是简单的照相,回来后仅仅是为了向人炫耀他到了别人难以到达的地方。我深信这一切描述,不过是一种铺垫,是他精神活动中的一个台阶。在此之上,他一定有着更深层的用意,破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基本破解了刘元举。
2.西部一定藏着深刻的人生命题。不然,好端端的一个刘元举为什么不踏踏实实地过自己的日子写自己的文章,偏要跑到万里之外荒无人烟的西部去呢?
当我在这个不寻常的夜晚开始撰写关于《西部生命》的随感,我首先想到的题目就是——“为什么远行”——刘元举,你为什么要远行?你曾说过你生长的大连是最美的城市,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你抛却了这最美的城市,从渤海一路到瀚海,去面对那茫漠悲壮的自然?
是为了“占有”它,或者“征服”它吗?以人类的生命力去与那亘古不变的山川大地较量,不是显得过于愚蠢吗?
没有答案。但我知道这个夜晚会因这种追问而显得不同寻常。
答案总是有的,它就掩藏在刘元举的文字中。
他写道:
不知怎么活着活着就感到没意思了。没有兴奋,没有忧伤,就连欲望都在一点一点地消失。(《远行》)
生活在渤海边的家乡人并未因为大海的陶冶而获得多少意志,他们变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敏感,越来越脆弱了。他们的孩子长得都比父母高了,下海时挎着救生圈还得他们的父母牵着手。在这些城市人的影响下,我们的渤海已经肌肉萎缩。那排浪无论下多大决心鼓多大的勇气,也没有办法撞痛海岸,海岸早已成了一块变了质的大海绵。(《从渤海到瀚海》)
这些文字描写的不仅仅是刘元举家乡的状态,而是世纪末整个人类的状态。不是吗?一切生命都是土地给的。我们的祖先曾在广袤的大地上书写他们的神话,在无边的草原上纵马挥鞭,在滔滔大河边留下他们最嘹亮的吼唱。然而,在这个机器轰鸣的时代里,这一切都如古久的书页一般枯黄脆裂,都和发霉的藏书楼一起招来了成群的白蚁。耗资巨大的城市立交桥割裂了人们的空间,如阳光下的玉米一般日日拔节的高楼将人们送入无法依赖的空中。人口越来越密集,空间越来越小,生活越来越紧张,心灵越来越受到挤压。这是一个“现代化”的时代。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曾以“生产的标准化”来概括这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如果说在以往岁月的手工作坊里,人们可以在每一件产品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个人的天才与想象力,那么在这个时代里,生产轴承的生产的都是成批量完全相同的轴承,生产发动机的生产的也都是型号分毫不差的发动机,甚至连绘画这样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在有些环境中也成了流水作业,你只管画好一棵树干,然后再到下一个工序上,由别人添上树叶。最终,人本身也被社会复制成了完全相同的“产品”。所谓的“个性”也早已被改造成了社会大机器里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齿轮。人们起初以为自己在创造生活,直到有一天,人们的感情枯竭了,才猛然发现自己成了生活的奴隶。
90年代的中国,精神的物化打碎了知识分子的人文梦想。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诗性消解”,反映在文学上,出现了“低调叙述”的高潮。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单位》等,直至晚生代作家们以“边缘人”的身份在文坛上出现,都表现了人在现代都市社会里的卑微与无奈。在散文领域里,成批量生产的“小女人散文”与“小男人散文”,还有大量养猫养狗、吃喝拉撒一类的“名人随笔”,已到了俗不可耐的程度。而文人的自嘲、自虐、自渎与自戕,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已在所难免。也偶尔听到几声鲁迅式的呐喊,却常常走入偏颇(张承志的“血脖子教”、柯云路的“气功”、北村的“基督精神”等),人们先是惊异地朝他们眨巴眨巴眼睛,很快就遗忘了,照样过自己的日子,照样沉沦,使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为一处孤绝却尴尬的风景。
这种低迷的世俗状态对人类精神的荼毒与戕害是严重的。“人在城市中所受到的各种羁绊太多了。就算你走出城市,那么你的心中也未必就能走得出来。也就是说,你很难摆脱那种城市状态。”(《河西大走廊》)明知鸦片有毒,却谁都戒不掉它。刘元举的对“城市文明”的揭示简直有些怵目惊心了。
3.刘元举的西部之行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逃逸,或者只是为了让西部巨大的山梁与高原将日益局促的心灵空间撑开。不是这样的。西部的一切,给了他一种神性的启迪。他不是旅游者,他眼中的万物也就不是风景。西部是一种历史、一种思想、一种话语。山峦无边的雪线、沙子的鸣叫,都带着各自的密码,向我们的作家传递了一种神秘信息。你看,“苍苍大漠在这个季节里赤身裸体,无遮无掩,一副放浪睡态。风沙太容易动情,却得不到回应;而煌煌大日的持久亲吻,使得巨大的肌肤荡出一片热烈,令我激动不已。”(《西部生命》)“正是这种残缺的地形地貌激活了我的才思。在我的眼里,这一大片屁股状的土丘神圣得好似万千和尚那排列有序的高深莫测的头颅。那皱褶般的沉积相全都是凝固的智慧。柴达木是一个经受过巨大苦难的地方。那每一处的残缺都在向我诉说着它遭受到的那一次次深重的摧残……”(同上)普通人在都市车水马龙的漩流里捕捉不到的那些神秘之音,我们的作家不仅幸运地感悟到了,而且同它们进行着灵魂深处的对话。这种对话,为作家本已苍白的心灵充了血。
刘元举描写世纪末都市的病态与苍白的文字并不多,却又处处都在描写它们。如同事物的两极,感悟到了这一极,也就猜测得出另一极。他是通过西部的渺远来反观都市的局促,他是通过西部的静寂来反观都市的喧闹,他是通过西部的伟傲来反观都市的卑琐,他是通过西部的神性来反观都市的人性。表面热闹的都市实际上只是荒芜冷漠的月球,而初看起来空旷死寂的西部,待你深入了它,才知晓它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世界。那种激情,让都市无地自容。
是西部赋予刘元举一种神的灵性。他于是站立在神性的高度上与自然对话。在刘元举心里,散文只有两种:人性的和神性的。至于什么抒情、议理、叙事之分,全是瞎掰。《一种生命现象的诠释》,便是一篇典型的神性散文。文中那只不死鸟,更是一只神鸟。这只困囿于沙漠的西部野鸟向比它“处境优越”的东部都市人展示了西部的魂灵与精神。“它是一种对于生命的张扬和展示,它以渺小向广阔展示,它要向比它更高级的人类展示它的存在价值。它以这种怪异方式完成了一次鸟类的最高境界。”(《一种生命现象的诠释》)这种碰撞,只属于西部这片土地。
4.很难说《西部生命》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文体,里面有历史,有考古,有建筑学,有生物学,有地质学;更有如石油般浓郁粘稠的思想。它的故事叙述得跌跌宕宕,如同小说;而那种真实的现场感,又像报告文学。也许因为刘元举曾在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诸多领域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所以他的最佳创作状态就是在多种文化之间游刃有余。但是,在我看来,纵横驰骋的情感,汪洋恣肆的写法,锐利的语感和奔腾的气势仍然是属于散文的。我太愿意将它归入散文一类,因为我们的时代太需要这样的大散文了。
我始终认为,散文是触及人类灵魂的,最锐利、最直接的文体。最高境界的散文应如圣洁的神灵之音,拨开世俗的谜象,如宗教一般普渡众生。可以说,刘元举的铁肩是承担了这样的道义的。也许是在无意之间,他从纵深两个方面对散文文体都做了开拓。他是有贡献的。而他对冰川、大地、历史、死亡充满膜拜,使他的作品充满了深刻的拯救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