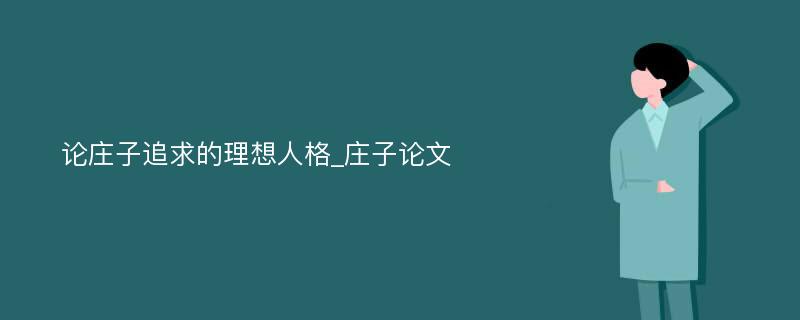
试论庄子追求的理想人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庄子论文,试论论文,人格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个贫困的隐士,一个没落的贵族,庄子深刻地体会到了自己在社会变革面前的无能为力,他不愿受当时统治者的牢笼,表明了自己的隐士品格和高傲精神。他主张“重生贵己”,顺应自然,但是,不管如何“重生贵己”,人总是要死的,死与“重生”、“顺应自然”“善待生命”是有深刻矛盾的,那么怎么办呢?庄子认为只要冲破生死关就可以了,只要人无“情”无“好恶”地面对生死,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他认为“无以人灭天”——不要人为地改变自然,只要一切因循自然,不加作为,看待生死,就能“生死如一”了。
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天命,无以注得殉命。(《秋水》)
他力图从心理上解决“不动感情”地面对生死问题。他认为人本来是可以没有情感的,因为自然就没有情感,人若能够“复归于自然”,就能“不以好恶内伤自身”,就能自若地面对生死了。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至乐》)庄子认为,人的生死不过是气的聚散罢了,气聚而有生命,人死而气散,这正如四季运行一样自然,所以人死又有什么可悲痛的呢?
仅仅“理智”地面对生死,庄子认为还不够,他进一步阐述死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甚至比生还要快乐。
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久忧不死,何苦也……。(《至乐》)人一生下来,就有忧患,年纪大的人老是怕死想不死,又何苦来呢?
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至乐》)死没有君臣的羁绊,亦无“四时之事”,比“面南而王”还要快乐。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无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宗师》)天地生人是叫人劳苦的,而老则是一种“安佚”,死乃是休息。
所以庄子宣传消极厌世,但仅仅厌世并不等于脱离人世。既然生活在人世,就必然有是非,有祸福,有哀乐,有生死,对于这一切,庄子提出了一个超脱看法——“齐物”,即把一切对立的东西都看作齐一。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有彼。……虽然,方生方死,方死主方;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齐物论》)
在庄子看来,万事万物是有差别的,又是无差别的。有无、大小、寿夭,可以是不同的,又可以是相同的。从不同之点来看,肝胆可以说有楚越相距之远;从相同之点来看,万物可以与我合而为一。在庄子看来,世俗之人不懂得齐物的道理,各执一隅之见,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以就各有一是非。强分大小、贵贱、美丑、是非,不过是一般人的偏见而已。如果把万事万物都看作“通而为一”,那么生与死又有什么不同呢?也就能真正做到“生死如一”了。
庄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奴隶社会没落而新兴的地主阶级上升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以财富为动力的社会进步有力地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展,但同时却出现了道德与物质文明进步的二律背反现象,“人间世”充满了横暴和贪婪、剥削和掠夺。他在《人间世》中说国君“……独行,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量乎泽,若蕉,民其无所矣。”面对“人间世”统治阶级的暴戾,社会的动荡,人民象牲畜一样被杀戮,人们为了名利尔虞我诈,庄子真能“心止如水”地面对生死吗,真能做到“生死如一”吗?恐怕不那么简单了。那么怎么办呢?既然面对现实无力回天,庄子只有到精神领域里去寻求超脱了。
庄子采取了“隐”的态度,不与统治者合作,不与媚世者合流,“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追求人格的独立,崇尚绝对的精神自由。
在《内篇·逍遥游》里,庄子谈了人不应受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束缚,而使精神活动臻于无挂无碍、优游自在的境界。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而降矣,而犹浸灌,其行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犹代之,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林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
在这里,庄子谈了许由不为权、位所动,对物质生活的需要只不过象鸟、鼠一样,只取“一枝”“满腹”而已,但却实现了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
庄子认为,天道是无为的,人道也应当是无为的,无为而治的政治是最妙的政治。人象鸟兽一样,是有其常性的。只要人们各安常性,不加以扰乱,所谓仁义,所谓兼爱,就都成了无用的东西。
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在宥》)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无为也。(《天道》)庄子认为,人应该顺应自然,行所无事,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人的精神的独立和自由,才能不失去“常性”。他看到了文明时代社会进化中的动乱现象,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民“失其常性”。他认为“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人们还不分亲疏;“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人们开始分亲疏;“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人们开始相互竞争;“禹之为天下,使民心变”,人们开始动用刀兵。
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骈拇》)
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候,诸候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箧》)所以庄子认为,圣知、仁义都是招致动乱的原因。一些窃国大盗,不惟盗窃国家,而且盗窃仁义之法以自守。这些人为窃贼之实,而有仁义之名。所以圣知、仁义简直成了盗窃天下的工具。在庄子看来,要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自我”人格的独立就不能受外来因素的干扰,就必须铲除人的逐名追利之欲望,铲除儒家的仁义道德对人的束缚。
他还认为儒家所谓仁义之行并不是善,真正的善是按自然本性,自由自在的生活。他认为“仁义”“圣知”是凶器,是导致天下动乱的原因,不可尽行于世。
只对“仁义”“圣知”批评还不算,庄子对圣人批判更加猛烈:
圣人生而大盗起。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胠箧》)因为天下有了圣人,才“不治”,方“大盗起”,才造成人们为名利而争斗。在这里,庄子对盗贼是“纵舍”,而对圣人则要求“掊击”,认为只有这样,天下才太平无故,才达到“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庄子对宗法、对“仁义”的虚伪和伪善的愤怒和蔑视,对儒家仁义道德对人格的压抑和精神的束缚的抗议。
庄子看到社会物质财富的进步带来的“不治”,因此,他反对技术的进步和物质生产的发展,他在《天地》一篇中,借为国家之口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
接着他又阐述了“物质财富”对人的害处,认为只有抛弃了仁义、圣知、机械之事,抛弃了对“声、色、臭”等的追求,恢复原始的朴素生活,天下方能大治,人才能真正实现不为“滚滚红尘”所侵扰的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
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同党,命月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马蹄》)
庄子知道,重返原始状态不可能,而在“尘世”又无真正的自由而言,他也只能到精神领域里去找“自由”和“人格的独立”。
在《逍遥游》里庄子表现了对他追求的最高境界——“无所待”的自由的真切呼唤和期待:
夫列子御风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返。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游,以辩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列子御风而行,轻松极了,但“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在庄子看来,若能顺着自然的规律,而把握六气的变化,以游于无穷的境域,他还有什么可待的呢!只有这样,才是“无所待”,也只有这样,精神才能够逍逍遥遥,一点也不受外来因素的干扰。
实际上,所子所崇尚的绝对自由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是建立在想象中的纯粹精神自由。在这里,一切名利财富、贪欲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作为人的人格是完全独立的,我也是“完全的自我”。
但尽管作为隐士,庄子也不能不看到社会物质财富的发展,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也带来了罪恶和贪婪,“无耻者富,多言者显”,“物欲横流”成了普遍的社会现象。由于“人为物役”,人们的人格、个性失去了独立,日益被自己所造成的财富权势所统治,并由此发生了争斗和残杀,物质财富、权势成了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这些都在他心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与他追求的“理想”相矛盾。他恐慎、拒斥,与统治者不合作,不与媚世者合流,但在“尘世”的不断冲击下,他追求的理想人格就变得庞杂、自相矛盾,甚至消极无奈了。
逍遥不易做到,因为要受到世俗的影响。怎么办呢,庄子认为,无别的办法,只有安时处顺、哀乐不入,以梦为真,以真为梦,以有用为无用,以无用为有用,身如枯木,心如死灰,甚至如原始人,呼我为马,呼我为生,都无所不可。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齐物论》)
“绝对的自由”做到了,但人还是要死的。庄子认为要想长生不死,就要“修炼”。修炼结果,是达到“真人”的境界,人只要能忘天、忘物、忘己,就可以大彻大悟,心如止水明镜,无灾无害,不生不死,就可成为“真人”。
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其寝不梦,其觉不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不知说生不知恶死,……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
“真人”在任何境遇中,都无所谓,因循自然,可生可死。“真人”在位,就可无为而治“真人”去世,就成为仙人。这个仙人精神不死,他与鬼神相类,但又不同,因他是逍遥自在的。
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天地》)
追求“无所待”的“逍遥”——即绝对的精神自由,修炼成“真人”变成“逍遥自在”的神仙,至于帝乡,这就是庄子追求的理想人格。
庄子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无所待”的自由,只有到天国里去寻找了。这样,庄子的人生哲学实际上追求的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境界。他从追求解脱来自社会的和自然的压迫,却最终归于宗教迷信;从追求人间世的“解放”、“自由”不得而最终归于天国世界;从追求绝对的人格独立和自由的理想最终归于根本达不到的幻想和梦境。
庄子的人生哲学是庞杂的,既有杨朱的“重生贵己”思想,又有“生不如死”的思想;既有“不与统治者合作”之高傲,又有“呼我为马,我则为马,呼我为生,我则为生”的虚无主义态度;既有“无所待”自由的期待与渴望,又有“安时处顺,哀乐不入”无奈与消极;既有对儒家仁义道德的批判与抗议,又有对达到“真人”境界的修炼推崇。总之,庄子的人生哲学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与他处的社会的激烈变革所带来的动荡、与统治阶级的残暴,与儒家思想的盛行,与他贫苦的出身分不开的,是他对现实观察思考的思想沉淀,是对现实无奈的一种“鸣放”。其人生哲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他开了“隐世”的先河,这可谓是“持义”的壮举,长期以来,他同儒家的“舍利取义”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人民特有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精神。其次,庄子提出的绝对自由尽管是不现实的,但作为一种批判精神却给中国封建社会的叛逆者一把火炬,使他们敢于蔑视封建的宗法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念,敢于击碎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追求个性解放和人格的独立。当然,庄子的“生死如一”“安时处顺”的处世方法对中国民族心理的劣根性之一——阿Q精神的形成也起了很大影响。
